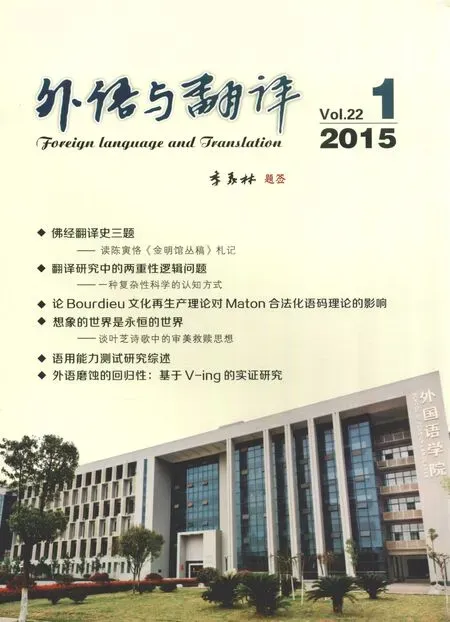想象的世界是永恒的世界*——谈叶芝诗歌中的审美救赎思想
董洪川
四川外国语大学
(董洪川: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是20世纪英语诗歌世界里名副其实的大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精美的诗篇,而且还在诗歌理论、戏剧创作方面都卓有建树。1923年,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现代英语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叶芝的一生正处西方社会巨大的变革时期,他的创作思想和诗歌风格也经历了几次转折,也因而比一般作家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故,研究叶芝自然成为学术界一个艰涩而又极富吸引力的课题。200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套影印原版“剑桥文学名家研习系列”丛书,笔者有幸应邀担任《叶芝》(卷)的“导读”撰写人。在“导言”中,笔者对英美学界以及我国的叶芝研究百年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与归纳1。要言之,西方的叶芝研究因其辞世而迎来第一高潮,主要是新批评主将从文本结构内部“细读”叶芝诗歌;而后的五六十年代,研究界则从叶芝诗歌与浪漫主义、叶芝创作与生平等方面整体考察叶芝作品的内涵;随着文化批评的兴起,叶芝研究被纳入了宽广的范畴,包括叶芝与爱尔兰、叶芝与后殖民、叶芝与性别,等等。虽然我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引入叶芝,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是从新时期开始的,主要成果在阐释叶芝的诗歌内涵、叶芝的象征体系、叶芝创作的不同阶段等,偶有论述从女性主义、后殖民、叙事学、原型批评等视角切入。总体说来,我国的叶芝研究已经有一定成就,但若比照英美学界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其距离也十分明显。
不容否认,叶芝是一位极具使命感的诗人,爱尔兰民族复兴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及未来始终是他诗歌涉及的核心话题。他一方面深刻批判西方现代世界的没落,揭示二十世纪人类的苦难并挖掘苦难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由;另一方面,他又对二十世纪人类遭遇的现代性危机充满同情,努力寻求拯救现代世界之良方。换句话说,叶芝诗歌中蕴含了丰富的审美救赎思想,而这点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当然,叶芝的诗歌卷帙浩繁,其思想也博大深邃,本文自然仅为管窥之见。
1.现代性危机、现代主义与审美救赎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降,西方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特别是从19世纪下半叶起,科技革命、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以及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彻底改变了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现实。科技发展、城市膨胀、宗教失落、传统凋敝……所有这一切都使原来井然而平静的世界动荡不安,恰如历史学家丹.贝尔 (1989)所言:“维持井然秩序的世界成为一种妄想。在人们对外界进行重新感觉和认识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只有运动和变迁是惟一的现实。”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自然选择的思想强化了人们对于一个无休止地变迁的现实的认知。特别是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世界大战,加剧了世界的动荡和人们的幻灭感,人们更加质疑“理性至上”的现代性传统。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和文化变迁打破了旧有的时空秩序和整体意识,导致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思想界对这场现代性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恰如批评家理·沃林 (2000:27)所言:
简言之,就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结论部分中生动描述过的机械死板的铁笼。现代性和现代化所导致的巨大社会变迁遭到了抵触,一代“德国学者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对这样的混乱做出了反应,那就是“灵魂丧失”的现时代之幽灵,开始萦绕在他们所说所写的一切事物之中,无论其主题是什么。到了1920年代早期,他们已经完全相信自己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危机,一场‘文化危机’,‘学术危机’,‘价值危机’,或者说,‘精神危机’”。
现代性的展开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但是“被彻底启蒙了的世界却被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导致的灾难之中” (Adorno&Horkheimer 1995:3)。人不仅没有随着现代性的展开而获得如启蒙思想家所允诺的幸福,反而被肢解成碎片夹杂在科层化的体系之中。现代主义文化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因而它在总体上朝两个向度展开:一方面揭示人类的焦虑、空虚与怀疑情绪。宗教信仰动摇了,心灵深处的乌托邦倒塌了,关于人类未来幸福的承诺也永远无法兑现,生命存在的价值也无所依托。另一方面,现代主义表现出狂妄自尊的自我扩张态势,在超越传统、突破禁忌、对抗体制等方面又充满激情。所以,我们看到了各种激进的先锋派,他们颠覆传统、张扬个性、标新立异,从形式到内容都力图有“新”的表述,以此否定历史现代性。很多批评家发现了现代性的矛盾性,即现代文化与现代存在的对抗与抵牾。Bauman指出: “现代性历史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对峙的历史”(Bauman 1991:10)。马·卡林内斯库 (2002:48)进一步指出:“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 (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标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
不过,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的“积极抱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甚至更加值得我们去挖掘。刘象愚先生指出,现代主义一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反传统、非理性倾向,对社会和人性进步流露出浓重的悲观情绪, “然而,现代主义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潜藏在非理性、无政府主义表面下重建某种新的理性与新的秩序的精神,以及蕴含在悲观绝望外壳中重建某种信念与理想的渴望”2。就叶芝等英美现代主义诗人来看,他们积极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包括从小说、神话、新闻、现代心理学等领域借鉴资源,并在句法、诗体、措辞等方面不断创新,努力以不同的诗歌形式表达一个不同的时代。但更重要也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抱负”没有止于创新形式,寻求新的表达。他们还努力探寻“重建某种信念与理想”的路径,在想象的世界中为人类走出困境制订各种拯救方案。
“审美救赎”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词。批评家们通过剖析工具理性、文化工业等异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揭示了理性的异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们还试图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拯救途径。艺术审美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阿多诺、马尔库塞、韦伯等都主张发挥艺术的审美救赎功能,以抑制理性的异化,恢复人性的完整。阿多诺相信,随着宗教的衰落,文学和艺术在提供价值根源与判断标准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属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一个制造信仰、快感和游戏的世界 (周宪 2005a:160-161)。赫·马尔库塞(2008:119)认为:“审美功能通过某一种基本冲动即消遣冲动而发生作用,它将‘消除强制,使人获得身心自由’”。韦伯则明确指出,审美有一种独特的功能,那就是把主体从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铁笼”中解救出来。他指出: “无论如何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刻板中解救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 (Gerth and Mills 1946:342)。其实,从康德开始,审美的救赎功能就一直是美学界的重要命题,席勒、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都非常重视艺术的审美对人的解放功能。席勒认为美可以让人们走向自由,海德格尔提出“诗意的栖居”,其出发点都是肯定审美的救赎功能。
面对一个传统价值崩塌、人的精神无所归依的世界,叶芝等英美现代主义代表诗人积极探寻拯救之路,赋予了审美现代性更深刻的内涵,诚如批评家埃斯特拉德·艾斯泰森 (Astradur Eysteinsson)(1990:9)所言:“现代主义被视为美学英雄主义(aesthetic heroism),面对现代世界的混乱 (一个‘堕落’的世界),它把艺术看作唯一可靠的现实和准宗教的秩序原则。艺术的统一被视为是对现代现实混乱秩序的一种拯救 (a salvation from the shattered order of modern reality)。”作为历史现代性的对立面,审美现代性从多个维度与历史现代性展开斗争,力图在多个层面对人实施“审美救赎”。譬如,就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而言,他们因不满科层化与模式化所带来的生活的刻板与平庸,以“新奇”艺术创作对抗现实生活的平庸,这是通过开启人的心灵、激活人的想象来实施“救赎”;他们反对科学追求标准性与对世界解释的唯一性答案,主张对差异与歧义的宽容 (如W.燕卜荪的诗学观)、容忍多元性,承认个性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这是通过存留个性与差异性而保持本真人性的“救赎”。从根本上讲,审美对人的救赎是一种诗意的救赎。审美救赎就是要褪去人类的精神枷锁,给人类带来自由——心灵的自由。人作为审美主体可以心无旁骛地鉴赏美的显性形式,忘却现实的利害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纯粹的情感。个体在这种情感中得以观照自身的自由本质,享受到一种由于自我的生命意识得到确证而带来的愉悦,获得某种解放,缓解人的焦虑。同时,审美所带来的这种纯粹情感也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使得空虚、焦虑的人们在此岸获得精神依托。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叶芝的诗歌则蕴含了深刻的审美救赎思想。
2.“茵尼斯弗利岛”:想象的自然家园
爱尔兰大诗人叶芝一生,正是英国诗坛历经种种变迁的时代——从后期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叶芝在每个时期都写出了真挚感人的优秀作品。纵观叶芝的创作,无论哪个时期,诗人对这个“哭声太多”(参见叶芝《偷走的孩子》)的世界给予了坚决的否定。工业革命后的伦敦,在叶芝眼里就是一个拜物教盛行、物质利益高于一切的商品世界,人的大脑和心灵被商品所吞噬:“伦敦的街上有传统,/有更难解的悲哀,更难挣的薪水——/市场上肮脏的悲哀,/悲哀吞噬着人的大脑和心灵” (见《街上的舞者》)。他的《第二次圣临》高度概括出了现代世界的疯狂与混乱: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啊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炙烈的狂热。
——袁可嘉译
这是一个四处弥漫着混乱的世界,纯真的礼仪被淹没,优秀者失去了信念。从叶芝的思想体系来看,这首诗的主题反映了他的历史循环世界观。叶芝的历史循环论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框架的基础之上的。诗歌题目指明了这点,因为按基督教传说,到世界末日之时,基督要重临世界主持“末日审判”。叶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螺旋式的旋转体,在不断的旋转中,形成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而每个时代的周期大约是两千年左右,从古希腊文明以来的基督教文明已经走完了近两千年,新的一个时代即将来临。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间,有约二百年的反文明时期,这是一个充满混乱、狂暴的时代。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正是处于这个时期。上面征引的诗行就是对这段时期的特性的总体描绘。“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啊旋转/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二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远离上帝。“猎鹰” (比喻人类)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比喻基督),人类远离上帝,心中失去信仰,所以“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只有混乱在世界上到处弥漫。最后几行,是诗人对一个邪恶世界的强烈控诉,也表达了诗人对远古“纯真礼仪”的深切怀念。
正是由于对当下这个“混乱”世界的不满,叶芝的诗歌中才充满一种怀旧的情愫。当然,叶芝诗歌中浓浓的怀旧情思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也不无关系。“怀旧 (nostalgia)”一词源于两个希腊词根nostos和 algia,前者是回家、返乡的意思,后者是一种痛苦状态,即思念回家的焦虑感。“怀旧话语在人类现代时期的生成和拓展,使怀旧成为一个现代性问题” (周宪2005b:1)。在我们看来,怀旧之所以成为一个现代性问题,这与现代时期人们的生存状况有关,特别是便捷交通工具和大都市的出现,使相当一部分人离开了自己祖辈生活的乡村,故去的“家园”离他们越来越远。由于交通与通讯工具的不断发展,现代人的生活空间也逐渐扩大,而逐渐扩大的生活空间决定了现代人漂泊的生存状态,漂泊的生存状态导致“现代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的家”(周宪2005b:5)。因而,怀旧,即思念故土或者家乡,成为现代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情感趋向,也成为叶芝对抗现代生活苦难,实施诗意救赎的一个策略:
怀旧就是现代人思乡恋旧的情感表征,它以现实不满为直接驱动,以寻求自我的统一连续为矢的,它正是现代人为弥补生活的不连续性而自行采取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至此,怀旧已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及现代社会的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现代科技的干预下,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正在于被从“有家”和“在家”的生活状态中抛离出来,家已不再,人已在外,传统意义上的归属感彻底丧失。这便是现代人普遍的生存焦虑感的关键原因,也是怀旧日益占据现代人精神生活之主导地位的根源所在。(周宪2005b:4-6)
大诗人叶芝面对“混乱”的现实世界,精神极度焦虑,返归故里成为他一生的梦想,而“故里”当然不仅仅是青少年时代居住的一座房子或者某个村落,而是一种状态,包括恬静的生活、纯洁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所以在他的诗歌里,我们不断读到诗人设造的一个个充满浪漫情调和富有泥土芳香的淳朴美丽的世界,诗人也不断表达“我要动身走了”(参见《茵尼斯弗利岛》)的强烈愿望。实际上,叶芝早期对爱尔兰民谣、神话的收集以及其诗歌中对爱尔兰乡村绮丽风光的赞美,都是诗人试图追寻文化之“家园”,寻找精神寓所的表达。
安·吉登斯 (2000:4)指出:“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和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叶芝本人的生活经历就清楚地揭示出“现代性”对人的多重“抛离”。叶芝早年家庭经济困境,加之父亲在事业上不成功以及经常性的迁居,使得诗人幼小的心灵失去安全感;十九世纪末爱尔兰政治和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更让诗人感到焦虑和惶惑。叶芝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经历都不同寻常。1865年6月13日,叶芝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郡一个靠近海边的小镇。他的母亲来自斯莱戈郡 (Sligo)的富有人家。父亲是一位先拉斐尔派的肖像画家,思想活跃,见解独到,同情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结婚时,他在学习法律,后转向梦想的艺术。叶芝出生后不久,其父为了学习绘画,1868年带领家人迁居伦敦;他希望其长子威廉能够学习艺术。父亲在达尔文和J.S.米尔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下,放弃了基督信仰而逐渐形成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世界观,希望艺术担当宗教的责任。父亲“这种与传统的断然决绝最终在叶芝的成长中产生了作用”(Holdman 2006:2)。
1880年,叶芝全家又搬到都柏林,起初住在市区,后搬到郊外的豪斯 (Howth);在豪斯的时光是诗人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地方周围是丘陵和树木,相传有精灵出没。叶芝家的女仆是一位渔人之妻,她熟知各种乡野传奇,娓娓道来。叶芝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全都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凯尔特之光》中。1884年后,叶芝去大都会艺术学校学习两年。1885年诗人创作的诗歌首次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1887年他们再次移居伦敦后,诗人在伦敦的家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聚会场所,他们在这里谈论政治、宗教、文学与文化。叶芝不仅结识了后来给予他大力帮助和提携的《国内观察》编辑W.E.亨雷,还认识了萧伯纳、王尔德等文化界名流。诗人心中一直想念爱尔兰,每到夏天,他总是要回斯莱戈去度假,住在祖父的美威尔大庄园。在童年和青年叶芝眼里,那里是和谐平静、物质富有的象征,给了诗人无限的欢乐。斯莱戈成为叶芝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那里民风淳朴、风景绚丽,成为诗人心中秀美故乡的象征。
但是,斯莱戈并不能完全减轻诗人的焦虑,因为每次返乡都必须面临重回伦敦的痛苦。这样的来回往返使他“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属于其中的某一方”(Holdman:4)。叶芝的青年时代就是在斯莱戈、伦敦和都柏林这三个地方度过的。这三个地方也成为其创作思想形成的主要中心。1891年,叶芝与伦敦青年诗人E.莱斯等建立了“诗人俱乐部”(Rhymers’Club)。这个俱乐部后来不断扩大,成员有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加利纳、道森、西蒙斯,成员们定期聚会并于1892和1894年出版了自己的诗选集。这些人受先拉斐尔派和佩特的影响,对法国波德莱尔等诗人很有兴趣,叶芝受西蒙斯的影响特别深。通过西蒙斯的介绍,叶芝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美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叶芝对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诗学观也格外推崇,王尔德主张诗人是美的绝对崇拜者,而与商业、政治等毫不相干。波德莱尔、王尔德对资产阶级市侩商业社会都抱有鄙夷态度。这对叶芝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19世纪的科学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对《圣经》上的教条表示怀疑。叶芝认同他父亲的怀疑主义思想,但他在精神上又渴求一种统一,这就使得他内心焦虑。诗人于是转向神秘智慧。1885年,诗人加入了“都伯林秘术兄弟会”,开始接触东西方神秘主义,后来叶芝沉溺于神秘主义和通灵术之中不能自拔。1900年,他甚至成为“金黎明秘术兄弟会”的领袖。他认识到诗歌所创造的美学上的统一与神秘咒语散发出的精神力量极其相似。由于童年时代在爱尔兰乡下的经历以及芬利亚(Fenian)领导人约翰·奥利里 (John O'leary,1830—1907)在政治观念上对他的影响,淳朴而美丽的爱尔兰乡村在叶芝笔下成为一个与庸俗势利的现代大城市相对立的一个世外桃源、一个象征。叶芝来回穿梭于英国与爱尔兰之间,不仅增加了对现代漂泊生活的真实体验,还对现代大都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伦敦是一个物欲横流,人情淡漠,精神匮乏的都市。也正因此,斯莱戈作为精神家园的象征意义才逐渐被建构起来。
生活场所的不稳定性和内心世界的重重矛盾,使叶芝对时代感到失望,对“时代精神”“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叶芝1992:2)。这个世界是一个技术化的世界,M.舍勒认为它“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转引自刘小枫1998:20)。于是,返回固定的、完美的、“有机”的家园成为诗人内心的冲动,成为诗人对抗历史现代性危机的重要精神力量。他在《茵尼斯弗利岛》中发出“我要动身走了”的深切呼唤:
我要动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袁可嘉译
这是一个美丽的世外桃源,“泥巴房”、“云豆架”、“蜜蜂巢”、“蜂群歌唱”构筑起一个人间天堂,宁静而自然。这里没有利益追逐,没有凡俗喧嚣,没有钢筋水泥,有的只是泥土的芬芳、蜜蜂的嗡鸣、潺潺的流水。“飞舞着的红雀”追打着午夜的“一片闪亮”,想象在碧蓝的天底下自由驰骋,人在幽静的自然环境里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心的律动与涓涓溪流合二为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茵尼斯弗利岛是爱尔兰北部一个遥远而偏僻的小岛,所以我们很容易也很自然地把这首诗同叶芝浓浓的怀旧情结联系起来,也有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诗人逃避现实的表现。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叶芝从来都没有逃避现实,他不像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而是把自己的生命紧紧与爱尔兰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不仅与友人共同修建了旨在复兴爱尔兰文化的阿比剧院,还在爱尔兰独立后担任了议员。他的一生都在为爱尔兰民族文化的独立而奔波,当然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而是作为一个诗人,所以他拯救民族的方式不是他的恋人毛德·岗那样的通过暴力革命,而是艺术。诺贝尔授奖词说:“叶芝与一个民族生命的联系,使他免于那种为了美而付出代价后的贫瘠,这种贫瘠是他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现象”(裘小龙1992:3)。因此,从审美现代性的视角或许更能把握叶芝这类诗歌的内涵。按照前述韦伯的看法,审美具有某种取宗教而代之的世俗“救赎”功能,因为审美本性上与科学的认知——工具理性和伦理的道德——实践理性不同,它赞美非理性,不受制于科学那样的证明规则,也不像技术一样实际运用于生活。对此,周宪 (2005a:158)解释说: “审美——表现理性看来有一种‘解构’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压力和实践的功能,这种表意实践在缓解人们日常性压力和刻板,舒展人的情感需求,满足想象力的自由伸展,一句话,在恢复被认知——工具理性和道德——实践理性的表意实践所‘异化’了的人的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潜能”。质言之,《茵尼斯弗利岛》所描述的温馨家园和寄寓的怀旧情感其实是诗人的审美救赎思想的生动表达。
如此看来,叶芝的《茵尼斯弗利岛》不仅通过艺术乌托邦舒展情感,把主体引入一个超然的非功利的想象和情感的空间,满足想象力的需要,让人获得心灵的自由,对刻板生活压力下的人们实施诗意救赎;而且,诗歌所设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家园”,也表现了诗人力图通过“回归自然家园”拯救现代人的努力。叶芝的《漫游的安格斯之歌》也是一首充满浪漫想象和温馨的诗歌,展示出另一个美妙和谐的自然家园:
我走出门,走向榛子树林,
因为我脑袋里有一团火在燃烧,
我砍下、削好一根榛子树棍,
又把一颗小浆果缚上了线;
当到处飞舞,飞舞着白色的蛾子
蛾子般的星星也闪烁在天际,
我把浆果抛入一条小溪,
钓上一条银闪闪的小鳟鱼。
——裘小龙译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上,皇家科学院院长艾纳·隆伯格说他深深为这首诗歌所打动:“我尤其为您那句‘银闪闪的小鳟鱼’所打动” (叶芝1992:2)。这是审美的力量,它“有一种从垂死的、惯例的、工具化的文明常规形式中使经验回复的广泛的热望”(泰勒2001:734)。作为诗人,叶芝追求的不是现时,而是永恒,想象带来的永恒。叶芝特别重视“想象”的功能,他在选编浪漫主义诗人W.布莱克的作品时说:“想象的世界是永恒的世界。那是我们肉身死亡后都要投入的圣神怀抱。想象的世界是无限和永恒的,而生息的世界是有限和暂时的。在那永恒的世界里存在着一切事物的永恒真相,而我们在造化的生息之境中看见其映像”(赵醴1998:71)。
3.“拜占庭”:想象的艺术家园
叶芝一生都在追求,都在奋斗,都在探寻。他追求的是完美的诗歌艺术;他奋斗的目标是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复兴;他探寻的是对现代人的审美救赎之路。而这些又都显示出一个民族诗人的伟大和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在努力建构爱尔兰民族文化身份的同时,叶芝一直都在为现代漂泊的灵魂寻找精神家园。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了“拜占庭”——一个伟大的理想文化圣地。拜占庭位于当今的伊斯坦布尔,曾是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和东正教的圣地,以灿烂的历史文化著称。叶芝并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只是在书上读到过关于拜占庭的描述。在叶芝看来,拜占庭具有丰富内涵和象征意义,是贵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他为空虚而焦虑的现代人设造的精神寓所。在那里,宗教、艺术与现实融为一体,和谐统一。叶芝晚年创作的《驶向拜占庭》是一首经典之作,更是一次精神之旅。诗歌这样开头:“那不是老人的国度。年轻人/相互拥抱”。这一节描述了现实世界的景象:无论是飞禽鸟兽还是人类,都沉浸在声色之中,忙忙碌碌,物质性遮蔽了一切,而更为重要更为本质的精神却被遗忘。这正是现代世界的逼真写照。作为现代性核心价值的理性以效益为最高原则,人被夹裹在一个日益理性工具化和商品交换的社会里,忙碌而模式化的生活把人变成机器,本来服务于人的物品反而成为人们的上帝,人被“物化”,成为物质的奴隶。所以,“疏忽了那永不衰老的精神纪念品”。青年本是充满活力,是人类生命力的体现,但他们“沉溺于”感官享受,迷失于暂时的欢愉。那么,老年人呢?诗人写到:“一个老年人只是一个废物,/一件破烂的外衣挂在一根拐杖上。”显然,老年人也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叶芝笔锋一转:“除非心灵的掌声和歌声传出,/赞美它那件破烂的衣裳。”在物质层面上,诗人对现代人感到绝望,而在精神层面,诗人却发现了现代人获救的秘密。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扬帆出海,远渡重洋,来到/拜占庭这座圣神之城”。拜占庭——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是一块灵与肉统一之地,一个生活与艺术统一之所。在这里,古代的圣者从历史的隧道走来,引导迷失的灵魂;在这里,世俗的心灵获得拯救:
哦,上帝圣火中站立的圣徒们,
如墙上金色的镶嵌砖所显示,
请走出圣火来,参加那旋体的运行,
成为教我灵魂歌唱的老师。
销毁掉我的心,它执迷于六欲七情,
捆绑在垂死的动物身上而不知
它自己的本性:请求你把我收进
那永垂不朽的手工精品。
——袁可嘉译
这是非常精彩的一节诗,诗人通过对比的方式,清楚阐明“我”弃离尘俗,追求永恒的决心。而永恒的获得,只有在艺术之中,即那“那永垂不朽的手工精品”。因此,我们可以说,叶芝是希望通过艺术通达永恒,这就是他提供的世俗救赎方案。诗人觉得,现代人要获得拯救,必须得到古代圣者的哲理与智慧,而古人的智慧因艺术而获得永生,它将永远地存在。所以,历史的螺旋转动会让他们获得新生。诗人祈求:请把我收进那永垂不朽的手工精品 (gather me/Into the artifice of eternity)。特别需要指出,这里的“收集”(gather)一词十分关键,“gather”指从四处收拢飘散的东西。这表明“我”在混乱的现实社会里,已经分裂成碎片。
一旦我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想
从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
二是要古希腊时代金匠所铸造
镀金或锻金那样的体形,
使那个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把我放在那金枝上唱吟,
歌唱那个过去和未来或者当今,
唱给拜占庭的老爷太太听。
——袁可嘉译
最后这节为我们设造了一个艺术的永恒世界。诗人说,一旦脱离了凡尘,他再也不想返回。“我”变成了古希腊艺人制作的金鸟,栖立于金枝上唱歌,把皇帝唤醒,向贵族歌唱过去、现在与未来。诗人借用金鸟这个意象,表达了在拜占庭艺术中获得永生的希望。诗歌开头和最后都运用了鸟儿鸣唱这个意象,形成前后呼应和有力的对比:一个是现实世俗世界的歌唱,一个是永恒艺术世界里的歌唱。世俗世界鸟儿的歌唱是制造刺激感官的音乐,人沉溺于感官享受而逐渐迈向衰老与死亡。而在拜占庭这个永恒的国度里,歌唱的小鸟是金制的不朽之躯,小鸟歌唱就象征着艺术不朽与精神永在。
设造“拜占庭”这一想象的永恒艺术家园,体现了叶芝的审美救赎思想。人要进入永恒的“拜占庭”,获得拯救,就必须经过艺术的净化。在完成《驶向拜占庭》三年之后,他又创作了另一首名诗《拜占庭》。关于这首诗的主题,诗人在日记中写到:“描述基督教第一个千年终结时的拜占庭。一具行路干尸。街角的火焰。那里灵魂得到净化。锻打出的金鸟歌唱在金枝上,在港口,背向恸哭的死者,它们也许要负载这些死者进入乐园”(王家新1996:299)。叶芝相信灵魂不断轮回转生,逐渐达到不朽境地。而在每次再生前,必须净化。该诗描写的就是在灵魂走向永恒前的最后一次净化。诗歌共五节,这样开头:“白昼的未被净化的意想后退,/皇帝那些喝醉了的士兵上床睡觉,/夜声消退,夜行者的歌声,/跟随在大教堂的钟声后面。”这里的“白昼”代表的是罪恶,“喝醉了的士兵”暗示出人们生活的堕落。“大教堂”指查士丁尼一世修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它的装饰非常豪华,内部全贴满了大理石和镶嵌的彩画,被誉为拜占庭艺术风格的代表。叶芝把它视为艺术的象征,所以在它的烛照下,现实那丑恶的面目呈现出来:全部都是乱七八糟,人类血气的污泥和狂躁。最后,象征永恒的“大理石”会把“混杂物”(complexities)彻底摧毁。第四节描写灵魂的净化过程:“午夜,皇帝的通道闪烁这火焰/那不是柴火或者钢铁的燃烧……狂躁的全部混杂物离开,/消失于一个舞蹈中”。“午夜”象征着“净化”的开始,与前文的“白昼”形成对照。 “皇帝的通道”指康斯坦丁堡广场的镶满彩画的通道,这里象征着艺术;“火焰”指炼狱中的圣火,它不是由柴火或者其他物质材料燃烧生出的火焰,而是圣火。它可涤荡人的罪恶,净化人的被世俗欲望蒙蔽的心灵。一句话,诗人认为,现实中的人内心充满各种世俗的私心杂念,必须通过艺术的洗礼和净化,方能获得新生,抵达永恒的拜占庭。
叶芝创作《驶向拜占庭》和《拜占庭》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生与死、现世与未来、肉体与灵魂,是他笔下经常出现的主题。但是,他又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整个人类命运结合起来。因而,他为自己日渐衰老的生命寻找的永生之路就获得了一般的意义,即为普世大众开出的灵魂救赎良方——在艺术中获得永恒。艺术带来智慧,艺术使人升华,艺术永恒。因而叶芝不仅毕生追求诗艺的提升,还勉励自己的同胞学好诗艺: “爱尔兰诗人,学好你们的技艺,/歌唱那被美所创造的一切”(《在本·布尔本山下》)。《天青石雕》是另一首赞美艺术永恒的诗。叶芝说:“有人把一大块天青石雕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在这块天青石上面有某个中国雕塑家雕刻的一座山,山上有着庙宇、树木、小径,一位长老和他的弟子们在登山”(叶芝1992:141)。诗人运用他那娴熟的对比手法记录了他面对这尊天青石雕刻的沉思:疯狂的战争、诡异的政治,使多少英雄豪杰忙乎于行动,而疏忽了精神世界:“她们已经厌烦了调色板和提琴弓,/厌恶那永远是快乐的诗人”,这是现实逼迫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不行动,那他们的生存都将受到威胁:“飞船和飞机就会出现在天空”,而“最后,城镇夷平,废墟重重”。但是历史证明,各路所谓的时代精英必然会在狂躁、愤怒和恐惧中灰飞烟灭,在时间的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艺术才是真正的不朽,如那天青石雕上的登山师徒:“雕刻在天青石上的是/两个中国人,背后还有第三个人,/在他们的头上飞着一只长脚鸟,一种长生不老的象征。……他们凝视着群山,/天空,还有一切悲剧性的景象。”这是一幅动人的画面,一个想象的永恒艺术场景。
按照韦伯的说法,西方现代性最核心内容就是理性化 (或者合理化),工具理性的膨胀造成了理性的独尊和霸权,进而形成了对感性和非理性的挤压。因此,反对工具理性对人的压迫,反对社会对人的异化,张扬人的感性,重建信仰,就成为现代审美思潮或者审美现代性的一条主线,恰如阿·豪塞尔 (1992:55)指出:现代美学“转向过去和乌托邦,转向儿童和自然,转向梦幻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转向能把他们从失败中解脱出来的种种要求”。而这“种种要求”,其实质就是重建价值理性,追寻生命的意义,“传统的现代主义试图以美学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宗教或道德;不但创造艺术,还要真正成为艺术——仅仅这一点即为人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贝尔1989:98)。在叶芝的创作生涯中,从表面上看,与毛德·冈的感情纠葛、与爱尔兰独立的紧密关联、与神秘心灵的不懈追问,似乎构成了他创作的主要内容。但是仔细体味,我们发现另一条主线一直贯穿于他的创作。这就是对历史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对现代人的精神救赎。从青年时代创作的诗歌《茵尼斯弗利岛》、《漫游的安格斯之歌》,到后来的戏剧《凯萨琳伯爵小姐》、《心愿之乡》和年老时写下的《驶向拜占庭》、《拜占庭》、《天青石雕》等诗歌,都反映出叶芝审美救赎的努力,也深刻蕴含了诗人的审美救赎思想。叶芝所创造的艺术乌托邦,就是他为灵魂漂泊的现代人所构筑的精神家园。
注释:
1 参见董洪川“导言”,载 David Holdeman,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B.Yeat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2 参见刘象愚为武跃速的《西方现代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作的序言,第1页。
Adorno,T.W.& Max Horkheimer,1995.Dialectic of Enlightment[M].Tr.by John Cumming.New York:Herder &Herder,Inc.
Bauman,Z.1991.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M].Cambridge:Polity Press.
Eysteinsson,A.1990.The Concept of Modernism[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erth.H.H.and C.W.Mills(eds.)1946.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C].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ldman,D.2006.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B.Yea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阿·豪塞尔,1992,陈超南等译,《艺术史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安·吉登斯,2000,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
查·泰勒,2001,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丹·贝尔,1989,赵一凡等译,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赫·马尔库塞,2008,黄勇等译,《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卡林内斯库,2002,顾爱彬等译,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小枫,1998,《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理·沃林,2000,周宪等译,《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家新选编,1996,西川译,叶芝日记选,载《叶芝文集》[C](第二卷)。北京:东方出版社。
叶芝,1992,裘小龙译《抒情诗人叶芝诗选·授奖词》[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赵醴等主编,1988,《唯美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宪,2005a, 《审美现代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
周宪主编,2005b,《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