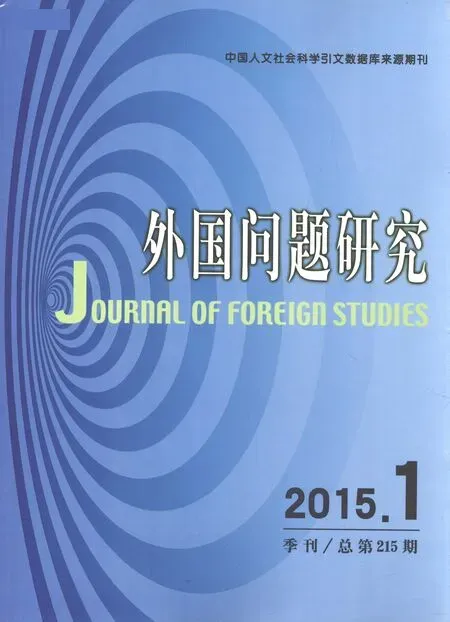大内隆雄的“满洲文学”实践——以大连时代的活动为中心
单援朝
(崇城大学 综合教育中心,日本 熊本 860-0082)
大内隆雄的“满洲文学”实践——以大连时代的活动为中心
单援朝
(崇城大学 综合教育中心,日本 熊本 860-0082)
[内容摘要]作为“伪满洲国文坛”的主要作家之一,大内隆雄青年时期受中国左翼文学思想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任《满洲评论》主编时积极关注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评论中表现出左倾的立场及理解。同时,投身于大连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先后主持两个左翼文学杂志,在其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因以上活动卷入满洲共产党事件被检举后转向。对伪满建国表现出的有良知的态度与其左翼活动的经历有关。
[关键词]《满洲评论》;无产阶级文学;满洲共产党事件;伪满建国;转向
大内隆雄为“伪满洲国文坛”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他1907年出生在福冈县山门郡柳河町的一个士族家庭,本名山口慎一。1921年来中国东北投靠叔父,1925年毕业于长春商业学校。毕业时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满铁公派留学生,同年4月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商务科学习,为第25届学生。在校期间,连续4年成绩保持年级第一,并参加满铁社歌征集,所作歌词获奖,成为满铁社歌。在上海读书期间,大内还与田汉、郁达夫等左翼文化人交往,曾在田汉主持的南国艺术学院任教,与鲁迅也有过一面之交。
从同文书院毕业后,大内回到大连,成为满铁员工,其间曾主编《满洲评论》,积极关注中国革命的问题。伪满建国以后,去新京日日新闻社工作,编过文艺副刊,做过评论部部长。1941年入满洲电影协会,任娱民电影部文学课长。后来还做过大同剧团文艺部长,满洲杂志社编辑长等工作。日本战败后回到老家宫崎县,先后在延冈市政府和市立图书馆任职。退休后做过高中和短期大学教师,于1980年2月10日去世。
大内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职业从满铁员工到报人、电影人,无不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作为一名作家、评论家和翻译家活跃于大连及伪满文坛,留下了堪称大量的创作作品和翻译作品,后者以“满人作家”的作品为主。作为“满洲文学”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还著有《满洲文学二十年》、《东亚新文化的构想》等书,为研究殖民地大连和伪满洲国的文学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在日本,对大内隆雄系统的研究主要见于冈田英树的《文学所见〈满洲国〉的位相》(研文出版,2000年)一书。因为该书主要是研究伪满时期中国人文学的,有关大内隆雄的一章主要侧重考察大内对伪满建国的态度及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情况,虽然也涉及他在《满评》的活动,但是,对其中重要的事实不是未提及就是语焉不详,对其早期的文学活动更是一笔带过。类似的研究大多如此。比如,关于他被检举及转向的问题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因此,本文聚焦大连时代的大内隆雄,通过考察他这一时期的评论及文学活动,探索其文学的原点和思想的轨迹。考察中注重对事实和细节的把握,力求对他早期的文学活动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
1929年,大内隆雄入职满铁本社,入调查课工作。这一年,他翻译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编辑的《中国革命论集》(马克思书房,1930)。在殖民地大连介绍中共的思想和动向的,他或许不是第一人,但一定是重要的一人。此后,继续关注中国社会的变革,出版了《中国研究论稿·政治经济篇》(青年书局,1936)一书,该书收录了他从1927年到1932年在杂志上发表的评论及论文,其中写于1930年的占了半数以上。两书的作者名都署山口慎一。以下摘录第二本书的目录,由此可以了解他关心的所在。一、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达的过程,二、中国国民革命的自我批判——以陈公博的论述为中心,三、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诸问题,四、中国国民党与南洋华侨,五、中国政治形势的理论上的解明,六、国民政府的对内政策批判,七、中国左翼工人运动的展望,八、另一个解党派,九、中国的农村农民状态,十、中国的人权保障问题和新文化运动,十一、中共中国的红色恐怖,十二、关于中国的租税制度,十三、中华民国的报纸,十四、南京政府的社会基础,十五、新蒙古的登场。评论的出处既有大连的也有日本国内的杂志,如《改造》等,可知他同时也为日本国内的杂志写稿。关于文章的主题和内容,可以简单区分如下:第一、五、九、十、十二章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第十三章为中国文化的问题;第十五章为国际外交问题;第二、四、六、十四章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研究;第七、八、十一章为中国共产党研究。其中第十四章翻译自朱其华的论稿。
这些评论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都是当时的热门话题,也涉及国共两党斗争。因为涉猎太广,给人留下视野宽阔但缺乏深度的印象,这可能与他的职业有关,毕竟是在满铁调查课工作,后来又主编《满铁调查月报》。甚至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研究原本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就问题的时事性和敏感性来看,笔者更倾向于把他的评论视为评论家和记者相结合的产物。问题是作者的立场和思想。在《满洲国文化细目》中担任该书解说的冈田英树指出:“评论集相当即时地追踪分析了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国民革命的挫折)后中国的动向。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认为国民党完全倒向帝国主义阵营,工人农民的未来掌握在其先锋党中国共产党手中。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有些机械。不过,倒是把当时左翼阵营的气氛如实地反映出来了”[1]。对大革命以后的国共两党的斗争,作为满铁内部的中国通,大内选择了站在中共一边。这一立场的形成要上溯至在上海与左翼文化人的交往。另一方面,他的评论基于同时代的中文文献,包括中共方面的文献,大多数为第一手资料。消化文献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作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其间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共的思想主张也未可知。
大内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成为《满洲评论》同人。时事周刊《满洲评论》1931年8月15日在大连创刊。创刊时的发行人为小山贞知,橘樸任主编,大塚令三作为责任编辑,负责具体的编辑业务。三人中小山和橘为满铁嘱托,小山同时还是关东军的嘱托及满洲青年联盟的理事,大塚在满铁资料课信息股工作,另一个发起人野田兰藏也是满铁信息课的嘱托。如此看来,《满洲评论》成为满铁旗下的杂志似乎顺理成章。其实不然,这个杂志只是有满铁的背景,却与满铁没有实质上的关系,因为满铁并未出钱经营。这也使得杂志能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实行自由的编辑方针。即对稿件质量要求较高,但立场不拘左右,以求广开言路。这个性格在大塚令三与鲁迅的对话中显露无余。鲁迅认为“《满洲评论》是一本令人费解的杂志”,因为“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写文章,而有的人却拥护无产阶级”。对此,大塚解释说:“那就是《满洲评论》大杂烩的性格,即一人一党主义的体现。没有必要统一每个人的思想倾向”。鲁迅回道:“但是,读者很困惑。可以尝试以更明确的立场做评论”。大塚的回答是“因为不是机关刊物,不得不这样做。但是,我们自认能起到宣传满洲情况的启蒙性的使命”[2]。据说同样的疑问也来自章乃器。还有,鲁迅接触《满洲评论》显然是因为和橘樸的关系。在“一人一党主义”的方针下,包括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协和会等来自各方面的作者以此为阵地,或为个人的观点或为其背后的政治势力的主张摇旗呐喊,颇有些百花齐放的气象。当然,满铁调查部的知识精英们成为最大的作者集群。鲁迅、章乃器等有所不知,在严密防共反共的殖民地关东州办一个旗帜鲜明的左翼评论杂志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杂烩的性格也是一种战略,是杂志能够长期存立的根本。战争后期,因纸张等物资供应极度缺乏,加上当局严格管控言论,在大多数刊物被迫废刊或停刊的情况下,《满洲评论》能坚持出版到1945年7月显然与其性格和立场有关。
进入1933年后,《满洲评论》组织了编辑委员会,以橘樸为首的编委会每周召开一次编辑会议。编辑方针也逐渐确定下来,开始有计划地编辑杂志了。最初的编委会由石田七郎、大上未广、小泉吉雄、渡边雄二、和田喜一郎、田中武夫组成,其中思想左倾者占了大半。并且,前4人都是满铁经济调查会的成员,和田后来也调入经济调查会,大内隆雄也隶属于经济调查会。1933年以后,杂志的编辑基本由经调派集团把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2年9月。大上未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和“满洲”的经济问题,后来回到京都大学做副教授。1942年9月21日,在所谓满铁事件中遭到连坐被京都宪兵队逮捕。被押送回新京后,于1943年3月19日死于新京千早医院。在这次满铁事件中被逮捕的还有石田七郎、小泉吉雄、渡边雄二、和田喜一郎,初期编辑同人几乎被一网打尽。很多作者也因此身陷囹圄,从杂志上彻底消失了。曾任第4代责任编辑的佐藤大四郎因为与北满合作社运动的关系,早在1941年11月4日就被关东宪兵队逮捕。1943年4月15日在新京高级法院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罪起诉,获刑12年,于当年5月10日病死在奉天监狱。他和大上的共同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
尽管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因思想或方法落难,但是思想与政治立场有时是两回事,两者不一定完全统一,尤其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比思想方法更容易决定人的政治立场。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众党从主张放弃台湾、“满洲”等殖民地的立场转为赞成“满洲事变”就是一例。何况,其间还有大正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阵风吹过。所以,不得不指出的是,以橘樸为首的《满洲评论》的基本立场是支持“满洲”独立的,只是建国理念与关东军有分歧而已。当然,支持“满洲”独立不仅仅是因为民族主义作祟,还与他们内心的知识精英主义有关。面对东北农村落后的现实,在新天地上按自己的理想建设一个新国家,这样的幻想对他们来说还是颇有诱惑力的,虽然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如后所述,大内的立场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只是他是思想左倾,和大上未广、佐藤大四郎等人方法上的左倾稍有区别。
二
1932年1月,大塚令三调到满铁北京办事处工作,大內接替他的位置,成为第二代责任编辑。大塚不愧是搞调查、信息出身的,他很早就开始收集中国共产党的文献资料,去北京后还在《满洲评论》上发表关于中共和学生运动的评论,并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史》(生活社)一书。1932年,满铁成立经济调查会,大内被任命为资料编辑班主任,主编《满铁调查月报》,此为他的本职工作。满铁刊行的杂志还有《满铁支那月志》(上海办事处)和《协和》(社员会),大内也给这两个杂志写评论。同时,满铁的青年员工组织了一个外国杂志的读书会,叫满铁二十日会,每月发行月例报告,这个报告也由大内编辑。一个人同时编三个刊物,加上文学活动,虽然有田中武夫给他做助手,大概也恨不得生有三头六臂。尤其是《满洲评论》为周刊,每期一般32页,又是在小印刷厂印刷,工作量应该是很大的。这一年里,他常去上海、东京等地出差,还和橘樸一起为日本国内的《改造》杂志编辑了《最新满洲辞典》,这个辞典最终以《改造》特别附录的形式刊出。这时的大内给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积极干练。
大内隆雄在《满洲评论》上写文章时除了署他的本名山口慎一,同时还使用矢间恒耀和徐晃阳这两个笔名。此外,《满洲评论》第3卷第2号的资料栏刊登了《南京政权和苏维埃政权》一文,此文译自发表在《红旗周报》第42期上的洛甫(张闻天)的《论目前的形势》,译者署名为S·Y生。S、Y分别为山和一这两个汉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由此可知该文的译者为山口慎一,S·Y生也是他的笔名。山口慎一在做责任编辑期间,杂志刊登了好几篇朱其华(笔名朱新繁)的文章,比如《上海事变和陈独秀》(第2卷16号)、《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第2卷22、23号)等,皆为他用矢间恒耀的笔名译出。前者不遗余力地批判国民党各派以及谭平山、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谬误;后者批判所谓第三党的谭平山、邓演达等人,指出在中国缺乏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条件。在此之前,《满铁中国月志》(满铁上海办事处)还连载了朱其华的长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性的发展》(天野元之助译,1931.8~1932.1)。大内应该与他相识,以上评论是直接为《满洲评论》执笔的。两人的关系或形成于大内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期间,也不排除通过满铁上海办事处认识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对中国革命的问题尤其是国共斗争的关注,显示出了大内的关心所在及思想上的倾向性,与之相关的评论和报道成为《满洲评论》的亮点之一。《满洲文艺小册子》第二辑《十一月》上的一篇题为《满洲文艺文化报告》的无署名文章对此有如下评论:“对于中国的文化问题,新创刊的《满洲评论》每期都有报道文章很好。我们需要那样的资料。希望把青年联盟内部的事从杂志上赶出去”。“青年联盟”就是以满铁职员为主的积极鼓吹“满洲”独立的满洲青年联盟。以上的评论转引自大内的《满洲文学二十年》。如后所述,这篇文章的作者估计就是大内本人,其中的赞扬与“希望”其实是他自己的心声。否则,他也不会在《满洲文学二十年》中专门摘录一篇无署名文章来揭示“当时满洲文学的一面”了。大内对杂志的贡献除了编辑和翻译外,自己还“以左翼的立场写评论”[3]24。主要的评论有《关于满洲经济的分析》(第1卷16号)、《单一经济与民族自决》(第2卷6号)、《政治上的亚洲色彩》(第2卷18号)、《现阶段的对殖民地政策》(第3卷18号)、《改良主义者胡适的道路——人权派批判——》(第3卷21号)、《关于取消派》(第3卷24、25号)等。从题目上看,有关政治、社会、文化的评论多于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后两篇都是关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既是他的强项,也是下力气最多的领域之一。
但是,1932年10月以后,山口慎一从杂志上消失了。对此,为《满洲评论》重印版做解题的山本秀夫如是说:“32年(昭和7)底,因为被检举,33年从满铁退职。被检举的原因不清楚,嫌疑好像与思想左倾有关”[3]24。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1935年1月28日的《满洲日报》刊登了一篇大标题为《满洲最初的红色救援会,十七人被检举》的新闻报道。聚焦1年多以前发生在大连的检举事件。从这篇报道的内容来看,大内似乎是卷入满洲红色救援会事件被检举的。满洲红色救援会是为了救援慰问因满洲共产党事件被起诉的松崎简等人及其家属成立的,在大连等地开展救援活动。1932年10月28日早晨,大连警察署高等科在奉天、抚顺警察署的配合下,一举逮捕了与之相关的17个人。17人中最终有3人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治安警察法、普通出版物取缔规则的罪名被起诉。虽然报道没有公开全部被检举者的名单,但是其中提到山口慎一与主犯金子、河村等人密谋准备开会的细节,所以几乎可以断定大内也在17人中。何况,这次检举和他的失踪在时间上也相吻合。报道称“该事件为红色救援会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首次在满洲开展具体的活动而受到社会的关注”。他最后虽然免于起诉,但次年不得不从满铁辞职。而且,可以说正是这个经历导致他转向从而躲过了后来的满铁事件的大检举,能够在大部分《满洲评论》的编辑同人和执笔同人身陷囹圄时继续为杂志写稿。因此成为该杂志为数不多的长期撰稿人之一。问题是1931年10月28日发生的满洲共产党事件中他就检举过一次了。那次事件中很多左翼作家、文化人被检举,波及很广,山口慎一的名字也出现在报上公开的满共事件被检举者名单中,并且名列第一[4]。如果报道无误的话,那这次(1932年10月)是二进宫了,并且两次都是免于起诉。这次的代价是不得不离开大连及伪满。只是第一次被检举的影响还不明了。事件后的1932年2月他还接任了《满洲评论》主编的工作,故被检举的事实还需继续核实。
话说回来,从上海回到大连后,大内隆雄作为作家同时也活跃在大连文坛。大内的文学活动始于长春商业学校学生时代。1924年间,《满洲日日新闻》两次征集长篇小说,他的《在北方的城镇》在第二次征集中被评为次席。其间还参加过《辽东新报》的短篇小说征集,数次当选,当选作品有《新年和人妻》、《一个国民党员之死》等。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一个月前,大连发行的《满蒙》1925年3月号刊登了他译的张资平的小说《植树节》,大概这是他第一次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他还在同月的《新天地》上用山口慎一的本名发表了短歌《南国集》,此时人可能已经在上海。这些经历成为一个日本的文学青年与上海左翼作家的接点。
三
说到大内早期的文学活动不得不提到《街》这个杂志。《街》起初由铃木秋花主持,为蜡刻油印版杂志。到了1931年6、7月间,改由高尾雄一经营后,改成了铅字印刷。6·7月合并号刊登了大内的随笔《旅行、女人、文学》。后年,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对高尾帮助最大的是篠垣(铁夫),其次就是笔者自己”[5]135。蓧垣铁夫就是在满洲共产党事件中因工会运动被检举的中村秀男,大内与他在文学上多有交集。高尾为杂志撰写的前言里有“走向街头的文艺运动,势必前行”等语句,面向大众的姿势已点明对普罗文艺的志向,杂志以“街”命名的寓意尽在其中。加上这一期刊登的稻叶亨二的《衣着褴褛的苦力》等作品,《街》的左翼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前后,大内自身也在编《大陆》杂志的文艺栏,因为也出少部分抽印本,故一般都称其为《大陆文学》。从刊载的作品来看,栏目的倾向性还是比较明显的。如1930年10月号上刊有大内的《长沙恐怖政治的记录》一文,是记述中国工农红军围攻长沙之战的,与两个月前发表在《协和》上的《中共中国的红色恐怖》在内容上有所重合。后者除了介绍红军对长沙的进攻外,还言及红军的根据地,展望了“苏维埃中华共和国”的前景。有关苏维埃政权的消息部分可能来自于他翻译的洛甫的文章。这一期刊登的古川贤一郎以何冰江的笔名写的诗评,对9月号的《燕人街》上的苦力诗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如第2编第1章所述,古川对北透氏的《雨天》评价很高,认为这篇诗“兼具单纯性和明朗性,完全无懈可击”。“单纯性和明朗性”正是《燕人街》的同人们作为无产阶级诗歌的特征所追求的。
大内在《满洲文学二十年》中介绍了刊登在《高粱》1933年7月号上的署名东野坚太郎的《文艺二三》一文。这篇文章回顾了大连的《移民文学》、《大陆文学》、《燕人街》、《赭土文学》,奉天的《曙人》以及满洲文艺研究会的《满洲文艺小册子》等杂志的足迹,明显带有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做总结的意思。这些杂志都属于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系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满洲”文坛风行一时。其中前两种杂志出自大内之手,《移民文学》也许是因为刊行时间不长的缘故,好像无人见过实物,成了一个传说的杂志。对杂志创办的经纬等,大内自身也不愿意多言。好在还有同时代的评论可作参考。篠垣铁夫在《1930年的文艺运动》(《燕人街》2卷1号/1931年1月号) 中曾言及“移民文学社的成立与解散”。据此,可以知道移民文学社当年3月出版了《中国·栈桥》,4月出版了《安南的少年的故事,其他》和《浅利胜集》等作品集,期间还发表了大内隆雄的《怒吼吧,中国》、柿沼实的《没有船的栈桥》、大内隆雄的《安南的少年的故事》等作品。《怒吼吧,中国》等作品,虽然现在无法睹其全貌,但从题目上来看,可谓是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与左翼文学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据篠垣铁夫介绍,大内在《移民文学》的废刊辞里写道:“今后,我们要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寻求我们的岗位努力工作。或是进入现有的报刊杂志,或是与内地的杂志联起手来”,提出了曲线坚持的“寄生”战略。对此,有人批评为“放弃阶级的独立的发表阵地”,篠垣铁夫对此表示赞同,还认为丧失了合法性,即使不需要非合法的行动时,正确的选择也不会是“现有的报刊杂志”。为此,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设问,“在受到限制的报刊上穿着红衣跳舞和在地下实施一次小小的行动,哪一个的价值更大,更应该受到评价呢?”尽管如此,最后却话锋一转:“但是,利用资产阶级媒体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通过他的批评我们可以了解到移民文学社的解散更多的是由于外部的因素,属于一种自保的行为,起因大概是因为色彩过于鲜明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同时也对大内的做法和立场有了一些了解,至少他显得比批评者们灵活一些,行动中含有许多实验的成分。同时,杂志的来去匆匆也容易给人留下韧性不足乃至投机的印象。久吕澄狂介认为:“无产阶级文艺杂志《移民文学》”的失败是因为无视了“满洲的特殊情况”,可谓“左翼理想主义的失败”[6]。他的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不像有些工人作家有底层的生活经验和朴素的阶级感情为基础,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大内的左翼思想是在后天的学习中获得的,知识的成分多于经验的感受。因所处的环境缺乏实践的机会,思想往往停留在理想及理论上,这也是容易遭受挫折的原因。
有关这一时期大内参加左翼文学活动的情况,当时在大连图书馆工作的大谷武男(大谷健夫)的回忆里如下的证言。因为他写的一篇“题为《斯特林堡的诸断面》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石川铁雄及天野元之助的注意。最先过来套近乎的文学青年是大内隆雄,某一天, 突然过来在我的桌上放下一本包着封皮的杂志,说了声‘看看吧’就进了书库。打开一看原来是《战旗》,我把封皮卸了放在桌上,大内从书库出来看见后很吃惊,就拿过去了。他是否就那样把杂志拿走了,我已经记不清了,记忆里也没有看了的印象。盯上我大概是因为我写了点偏左的东西吧”[7]。《战旗》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的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文学最重要的杂志之一,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作品均发表于此。可见大内等人还受到日本国内纳普系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同时,他的回忆也让我们了解到大内不光是自己办刊物写文章,作为骨干分子,还有传播左翼文艺思想发展队伍的地下活动。
还有一个刊物值得注意,那就是满洲文艺年志刊行会1932年3月刊行的《满洲文艺年志》。大内在提到这个刊物时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因某一事件的关系相当多的文艺人一时处于丧失自由的境地。(略)这(刊物)就是那个事件以后为了填补空白而策划的,它自然而然地对以前的满洲文学作了一个总结”[5]172。这里的“某一事件”指满洲共产党事件,“丧失自由”的文艺人中也包括他自己吧,否则不会如此转弯抹角,欲言又止。这个刊物主要由篠垣铁夫在近东绮十郞的协助下编辑完成,收入其中的作品没有直接涉及“九一八”事变的,但可以见到如下的川柳:“战争呀,时局呀,飞机呀,坦克呀,每天报道的媒体究竟要向我们展示些什么?”(大河平蛙洒《川柳杂感》)。刊物只出了这一期,形式亦刊亦书,可以看成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匆匆的谢幕式。大内为其写了《生活的一鳞半爪》一文,作为附录,还收入了他的《满洲文艺运动史》。该文署名“国际文化研究所”,完成时间为1932年1月。其中有如下自白:“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某一事件给文艺运动及几个人带来了一场风暴,至今仍然没有发表的自由”,再次提到满洲共产党事件并暗示他彼时仍处境困难。由此可知,该文写于满共事件以后,署研究所名作为附录发表实属迫不得已。同时,以上两次对“某一事件”的言及间接证明他曾经卷入满洲共产党事件。如此看来,两次被检举的经历多半属于事实,只是前一次的影响没有后一次大而已。
综上所述,大内隆雄投身左翼文学运动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来自中国的影响,主要通过与左翼文化人的接触以及翻译、介绍中国左翼文学实现,也包括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关注。其二是来自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这样的思想经历使他成为殖民地大连及以后伪满社会中一个相对特殊的作家知识分子。
对大内而言,“九一八”事变以及随之而来的伪满建国(1932年3月)成为一个分水岭。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以此时为界,满洲文化史突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177。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他究竟持何种态度,这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大内在《满洲文学二十年》里摘录了发表于《满洲评论》1932年4月16日号的《满洲文化建设私案》一文。对此,有两点需要加以注意。其一, 当时《满洲评论》正好由大内主编,其二,该文发表于伪满洲国粉墨登场之际,其中的希望建议也是作者对伪满建国的态度表明。文中写道:
这是一个奔放的空想。但是想多少能提供一点儿启发,执笔的动机是很现实的。
第一,满洲是各民族杂居,文化程度也不一样。各具异彩的民族文化的存在是不可无视的事实(看看社会主义苏联吧,各民族都在发展自己特有的文化)。
在普通教育上最需要注意的大概是民族融合精神的渗透——即培养社会连带心理。要排除侵略主义,也要压制自卑的排外主义。当然,其根本是各民族在实际生活中必须做到平等。——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
普及一种共同语言是非常有益的。为此,我推荐汉语和世界语。因为数量上中国文化(汉语)占优势,后者作为辅助语使用。
中等教育还有专门教育更不应该只是培养知识分子,分化后,实际上培养人,培养在农、工、商各方面都能脚踏实地择业而劳的人。不需要封建的,乃至亚洲型的官僚。
应该建立一个最高研究院。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要提供足够的经费,经验研究的自由。要承认研究员有研究的自由,保证他们的身份。
宗教应该是自由的,完全与行政事项分离。
在文化领域,对各种出版要给予优厚的保证。要允许内容上的自由。使报刊杂志容易发行,内容上享有尽可能多的自由。目下的暂时的过渡期过去以后,民众会真正的要求言论、出版、读书的自由。
艺术,对国际成果的摄入和乡土的(民族的)创造的发展,两者都很重要。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戏剧、音乐、电影、收音机使其发挥作用。有“公立剧场”能“巡回演出”就行。当下,应该大力发展电影和广播电台。
作者的立场是接受伪满建国的现实,但对文化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和建议。文章中“平等”、“自由”等词非常抢眼,作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跃然纸上。就算关东军在建国之初为收买人心而故作姿态对他的建议也是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提议以汉语为“满洲国”的共同语言的建议,不要说关东军,就是一般的日本人也会感到意外。只要想像一下本庄繁及关东军的参谋们操着大连口音的汉语和溥仪交谈的情景就行了。那么,提出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建议的究竟是什么人?文章署名“T.O生”,冈田英树认为这是大内的笔名,并对文章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但是,冈田并没有提示认定的证据,只是提到“共同语”之一的世界语,谓大内曾回忆起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往事及与世界语学者胡愈之的邂逅,显示他对世界语有一定的知识[8]223。
其实,这个笔名与《满洲文艺小册子》第二辑《十一月》刊载的小说《K生》有关。对作者曲传和,大内有如下说明:“曲传和为后来经营青年书店的曲传政的弟弟,当时是关东州的小学教员。(听说现在在河南省作建设厅长)。《K生》这篇小说,上段登载原文,下段登载笔者以‘T.O生’的笔名翻译的日语译文,可以说是满洲文学的一个新的尝试”[5]167。据此可以断定“T.O生”为大内的笔名。除了《K生》以外,曲传和还有一篇题为《往事》的小说刊登在前面提及的《满洲文艺年志》上,为其中唯一的中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传和”一家十七年的变迁,周海林指出:“与满洲国成立后的中国东北作家的作品相比较,《往事》明显富于反抗精神”[9]。可见在左翼文学运动中,大内还注重与中国人的连带,并热心尝试合作的方式。这个尝试成为其翻译“满人文学”的起点,意义非同一般。
冈田英树根据上面那篇文章及《满洲的民族文化问题》等发表在《满评》上的评论将“大内所描绘的满洲国建国的理念”抽象为:“为了实现满洲国内的诸民族真正的平等,其目标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取得完全的独立,对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国民党,(以下部分虽未明确提出)与代表中国民众的共产党携手合作”[8]223-224。关于后者,他举出了大内翻译介绍批判中国国民党的论文为依据,主要是指译载朱其华的论文。首先,把大内对国共斗争的态度原封不动地套入其“建国理念”是否妥当,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再则,对“理念”的主体,即由谁来实现这个“理念”,冈田英树只字未提,总不会是中国人吧?所以大内的“理念”只能是“奔放的空想”,之所以为“空想”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日本人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尽管如此,“空想”还是明确地显示了大内对伪满建国的态度。虽然他也认可伪满建国,但不得不说从“空想”的内容能看到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仅是在现在,在当时更是鹤立鸡群。尤其是关于“共同语”的建议。其实“空想”的内容,如各民族平等、出版和内容的自由等,明显来自其左翼活动及社会活动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更进一步,联想到他也被卷入其中的满共事件的导火索是满共事务局向各地邮寄以反战、反对“九一八”事变为宗旨的传单,“空想”的现实性更加突出。对此,他数年后的反省是:“以上的那些文字,多少混杂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词汇,但是,主旨大概是可以被认可的吧。后来有些东西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不管怎样,建国当初,我们对满洲的新文化并不是漠不关心的”[5]180。虽然初衷未改,也只能如此了。只能如此也就罢了,问题是后来他放弃了初衷,转变为“我赞成推进日语作为东亚文化上的共同语的意见”了[10]。
结语
大内隆雄少年时从日本来到中国东北,先后学于长春及上海,在大连、奉天、“新京”等地工作生活,历时24年,经历了民国、伪满两个时代。作为这样一个生在日本长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与中国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上海学习的经历不仅使他掌握了中文,打下了日后成为翻译家的基础,还加深了他对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认识,并使他有机会接触左翼文化思潮,接受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回大连以后,以国共两党斗争为中心,继续关注中国革命的问题,这对他的思想和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上来自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影响体现在他早期的评论活动以及参与以大连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前者表现出明显的左倾的立场和对中共的理解。后者虽然主要局限于日本人之间,且时间相对短暂,带有浓郁的实验色彩。但是,这段经历成为大内文学的原点,对现实主义文学认识的深化无疑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及翻译活动。
不过,作为以上活动的代价,两次被检举的经历,还改变了他人生的方向。他被迫选择放弃左翼思想,即常说的转向。而免于起诉的代价是必须离开大连和伪满。对伪满洲国的成立,以接受这一事实为前提,大内所持的相对开明,不失良知的态度显然与以上的左翼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转向的经历成为他以后举起翻译大旗时的精神支点。再就是他心中复杂的“满洲”情怀,作为一个中国通,那也是他自身价值赖以存在之地。虽然本文中没有展开论述,他不久就离开“流放地”东京重返伪满,其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价值的自我实现。公平地说,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取得的成就主要在“满人文学”翻译方面。转向后创作活动受阻是促使他转向翻译的一个契机。他试图打着“勤劳者文学”的旗帜,以翻译的形式重温无产阶级文学的旧梦。
但是,像大多数转向者一样,左翼思想最终未能阻止他倒向体制的怀抱。“九一八”事变及伪满建国以后,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变化既影响到中国人也影响到日本人。曾经的中国革命的理解者,活跃在文坛上的左翼作家,经历转向后,最终沦落为殖民主义文化人,为国策效力。究其原因,超越阶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应该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大内的《东亚新文化的构想》一书的“序”里有这样两句话,“就是在写这些文稿时,严酷的战斗报道也不断地冲击着我的耳膜。笔者想到提笔是为了为国家效劳,就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进入1944年后,太平洋战争的战局日趋恶化,大内的“耳膜”对此也有强烈的反映。“亚细亚的解放”的幻想已渐行渐远,精神支撑只剩下“为国家效劳”的念头了。
[参 考 文 献]
[1] [日]岡田英樹.支那研究論稿政治経済篇:《満洲国》文化細目[M].東京:不二出版,2005:119.
[2] [日]大塚令三.三つの寓言[J].満洲評論,11—8,转引自山本秀夫.「満洲評論」解題·総目次[M].東京:不二出版,1982:16.
[3] [日] 山本秀夫.「満洲評論」解題·総目次[M].東京:不二出版,1982.
[4] [日]日支事変に乗じ全満攪乱を企つ一味五十余名一網打尽捕る·満洲共産党の全貌[N].神戸又新日報,1935-05-11.
[5] [日]大内隆雄.満洲文学二十年[M].新京:国民画報社,1943.
[6] [日]久呂澄狂介.自然発生の芸術と我々[J].燕人街,1930(5):18.
[7] [日]大谷武男.満洲の回想あれこれ——『満州文藝年鑑』の復刻に際して——(満洲文藝年鑑:別冊)[M].東京:葦書房,1993:11.
[8] [日]岡田英樹.文学にみる「満州国」の位相[M].東京:研文出版,2000:223.
[9] [日]周海林.曲傳和『往事』小論:「昭和」文学史における「満州」の問題第三[M].東京:早稲田大学教育学部杉野要吉研究室,1996:358.
[10] [日]大内隆雄.言語と文字について:東亜新文化の構想[M].新京:満州公論社,1944:134.
[责任编辑:冯雅]
[中图分类号]I313.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01(2015)01-0021-08
[收稿日期]2015-03-09
[作者简介]单援朝(1953-),男,四川成都人,日本崇城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The Practice of Takao Ouchi’s Manchurian Literature:Centering on Dalian Era
SHAN Yuan-chao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Center,Sojo University,Kumamoto Prefecture,Japan,860-0082)
Abstract:Takao Ouchi,one of the typical writers of Manchukuo,was affected by Chinese left-wing literary thoughts and Japanese proletarian literary movement in his youth. He was actively concerned about Chinese revolution as the chief editor of Manchurian reviews. His comments showed a left-leaning stand and appreciation of CCP. Meanwhile,Taka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movement centered on Dalian. He sponsored and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wo left-wing literary magazines. Owing to the activities mentioned above,Takao was drawn owing to the activities mentioned above,Takao was drawn into the event of Manchuria Communist Party and then changed his political stand after he was impeached.His conscientious attitudes toward the foundation of Manchukuo was allied to his left-wing activity experiences.
Key words:Manchurian reviews;proletarian literature;the event of Manchurian Communist Party;the foundation of Manchukuo;change one’s political 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