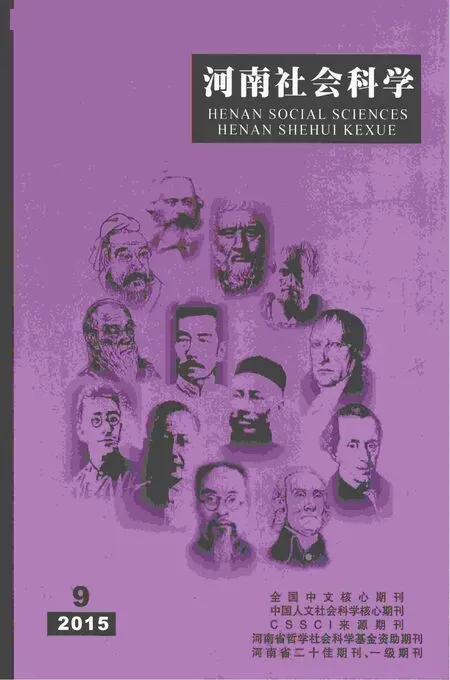乡愁的守望: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记忆与城市适应研究
郑 欣,赵呈晨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中,“城市化”与“现代性”往往与“城市适应”相伴随,认为城市适应就是一个不断城市化与现代性的过程,被城市文化完全同化,完全地融入城市社会,才被认为是真正的城市适应。于是,乡土性与城市化的相互矛盾成为必然。因此,有人提出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打工谋生本身就是一个追求“现代性”与摆脱“乡土性”同时进行的过程[1]。从广义上来看,乡土性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土”,它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记忆。也有相关研究表明,乡土记忆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乡土记忆会导致农民工的城市认同陷入困境。换句话说,乡土社会记忆干扰以及模糊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2]。
因此,如何处理乡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中应该重视的问题。当然,如果从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就意味着将农民工适应城市的最终结果看作对乡土文化的完全抛弃和对城市文化的完全认同,否则就是适应不良的表现。文化适应的研究视角恰好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提供新的借鉴[3]。其实,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现代性的发展与乡土性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相互共存的。城乡文化的冲突只是城市适应过程中一种可能的表现,而非一种结果。无限与城里人趋同只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一种理想境界,而现实就在于乡土性作为一种包含了农村风俗与生活习性的乡土文化,不可能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完全去除,因此在城市文化与乡土记忆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应该是基于理想和现实的一种新的城市适应路径。
本研究基于文化适应的视角,试图描述因为空间的转换与环境的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性在城市中呈现了一个怎样的尴尬、冲突、隐藏甚至抛弃的现实。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本研究也重点关注乡土记忆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淡化、遗忘与断裂的过程。文化的失忆与自我的迷茫,必然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双重边缘的认同危机。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还将深入探讨在城市接触与融入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如何通过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新媒体等传播方式来获得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又是如何通过媒介内容的呈现与媒介工具的使用获得乡土记忆的唤起与重建。被唤起、被重建甚至被重视的乡土记忆如何与城市文化共生而促进一种城市适应的平衡状态。
本文使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的实地调查所得。从2013年1月到2013年12月,我们在为期1年的调查过程中,分别走访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南通等城市,通过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方式,共获得相关有效访谈资料30多份。受访者均为“80后”,受教育程度多为高中及以下,他们的职业多集中在私营业主、美容师、发型师、化妆师等服务性行业,进城时间与城市经历各有差别。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刚进入城市时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到生活习惯都有着明显的乡土气息,而随着城市生活经历的不断丰富,在自我模仿和环境影响下不断努力地进行着城市化。
一、空间转换与内心留守:难以磨灭的乡土情结
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中,我们习惯性地将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视作一种单向的过程,似乎新生代农民工需要完全褪去乡土性,完全适应城市的各种文化和价值观才能算作完成城市的融入。因此,在来自城市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有着文化求同的强烈意识。他们希望从外在装扮、行为方式、语言习惯、思想观念等方面与城里人保持一致或相似,因而以城里人为角色参照的一系列行为模仿在他们进入城市之后开始逐渐显现。
在上海一餐饮店担任前台服务员的汪小姐是湖南人,起初对于说湖南家乡的土话会有一点自卑感,后来自己努力地去纠正自己不标准的普通话,甚至去学习几句上海话。现在尽管汪小姐依然不会讲上海话,但是也能听得懂顾客说的上海话。不过回忆起刚刚进入城市的时候,汪小姐认为自己的偏远地区身份以及家乡的口音让自己“很没面子”:
老家很远,每次回家要转好几次车才能到,一年最多回两次。才来上海的时候基本听不懂这边人说的话,他们都说上海话啊,我就觉得自己跟他们差距太大了,而且湖南话太土了,都不怎么敢开口,现在我终于学会一点上海话了。
对上海话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助于汪小姐快速融入城市,她描述起刚进入城市的时候不敢开口的心情,表示因为特别想能够与别人说上话,所以尽量把普通话讲好,适当地也去模仿几句上海话,好让自己看上去像“半个上海人”。“与周围人不一样”“跟本地人有差别”成为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压力,于是他们特别期望首先能够在衣着打扮、说话口音等方面与城里人一致起来。
单从外表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环境感染下,很容易去乡土化。贵州的小颖今年29岁,已经进城10年。她在厂里面做过工人,也在大商场做过售货员,曾经辗转于多个城市,如今在南通市的一家理发店做收银员,每月收入3000多元。她穿着时髦,中分的长发及肩,染成了上黄下红。回想起进城之初,她记忆犹新:
当时,我的两个姐姐都已经出去打工了,我弟弟还在上学。爸爸妈妈没什么收入。刚开始,我就跟姐姐到上海打工,在一个丝织厂里面,我说话有很重的口音,穿的也很土气,又不太会讲普通话,说家里的话怕周围的人笑,所以就不怎么说话。很自卑,当时,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觉得很孤单,上海这种大城市里面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做,我当时是有些害怕的。
小颖的回忆代表的是大多数农民工初次进城的心理感受。无论是迫于生活的压力而外出打工,还是厌恶上学而直接辍学外出闯荡,他们的初次进城都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心理上会有一种自卑与害怕的感觉,于是就会有意去掩饰身上的乡土气。在他们看来,乡村就是“土”的代表,落后的因素比较多,而城市就是“洋”的代表,现代性的成分较多。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能够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们对城市的生活感到陌生和害怕,同时又会成为他们对于城市文化求同的动力。
然而,进城之初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空间移动,空间的改变并不能瞬间磨平他们对于农村、对于家人的内心寄托,身处异地而心系乡土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的真切感受。
来自苏北的农村小伙子张某,1992年出生,目前在苏州一家工厂做数控车床的工作。他虽生在农村,家里也有一点土地,但父母都在家里的工厂务工,空闲时间才会打点一下土地。而他外出务工的真正原因不是一般认为的“经济条件不好”,而是因为不喜欢读书,主动辍学,走上了打工之路,但进城不久的他便流露出了“十分想家”的情绪。
在受访者中,来自湖北农村的吴某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目前在南京市一家理发店担任发型师。在外六年的他已经习惯了南京的生活,理发师的行业也让他更加近距离地接触了形形色色的城里人。他说在六年前坐上来南京打工的火车时,他也有着一种对家乡难舍的情感。而到达陌生的城市环境中,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对各种不熟悉和不确定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更是加深了他对家乡和家人的思念。
说实话,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城市体验一般都是苦涩的、艰辛的。想出去闯荡又觉得害怕、想独立生活却要忍受孤独,这就是他们尝试体验城市生活必然经历的事实。离乡进城的他们在陌生的城市,没有熟人和朋友,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中过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而在传统的乡土共同体中,本身就有着一套整合社会秩序、缓解社会冲突的规范和制度[4]。不过来到城市后,这些以往的习惯以及来自乡土的一些准则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他们作为城市中的游离者,多被看成是不同的、陌生的外来人[5]。城市社会不再是乡土中的熟人社会,而是一种陌生人的社会,相互之间毫无关联。而人际关系的处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新挑战,初次进城的他们并没有习惯于这种关系的发展,因而内心对于乡土社会和基于血缘、地缘的乡土社会关系有着难以割舍的留恋。
总之,从农村到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空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开始了移民般的生活。然而空间的改变并不能瞬间带走他们的内心情感,身处异地而心系乡土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后的真实感受。初入城市,涉世未深,尝过苦头,受过挫折,然而对于乡土的感情却不会马上改变,并且始终是支持他们在城市漂泊的精神支柱。可以说,为了克服融入城市的障碍,以及安抚内心的不安,不可磨灭的乡土情结让他们在精神上形成一种共同体,成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寄托。而随着城市经历的不断丰富,他们对于乡土的依赖以及对于乡土文化的记忆逐渐会被城市文化所取代。
二、文化失忆与认同危机:乡土记忆的断裂与缺失
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的从乡土到城市的空间改变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存环境的转变,在生活与工作空间的变化之中开始完成个人再次社会化的过程,从而不由自主地选择偏向城市的社会文化。城市环境的影响以及周围群体的参照让新生代农民工的农民身份与乡土意识日渐淡薄。
全家都在南京打工的小杨,1994年出生,在南京一家快餐连锁店做厨师。小杨早在10年前就来过南京了,他表示当时父母在南京城里打工,而自己在一所小学上学,因而结识了一些南京当地的同学,不过小学之后他回到老家上初中,在初中毕业之后便又跟着父母回到南京打工。因为年纪还小的缘故,小杨表示出来打工完全是没有什么目的的,就是要出来锻炼锻炼,接触接触社会:
我在南京上过小学,有几个小学的同学至今还比较熟,而且他们都是南京人,也上了大学。虽然我后来没上学,不过跟他们还玩得很好,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南京当地的人,觉得自己跟他们并没有很多差别,有时候还会一起出去玩,一起唱歌、聚餐。爸妈也都在南京打工,一家人在南京租了一小套商品房,所以很少回老家,基本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
从日常交往对象和行为方式来看,曾经在南京城里上过学的经历,让小杨拥有了更容易接近城市的机会。他早在几年之前就为自己的城市生活打下了基础,因而也比其他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强的城市适应能力。城市生活的习惯已经使他渐渐远离乡土,甚至除了户口是安徽滁州老家的之外,他与南京人并无差别。
从乡村走到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了与乡村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就像小杨一样,一旦在城市工作生活必然会受到周围同事、城里认识的朋友甚至进城多年的老乡的影响,从而能够接触城市中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对他们而言,群体参照是最为直接的城市化方式,城市中所接触到的不同群体也正在拉动他们一步一步地适应城市、融入城市。当然,这样的影响不止是来自于城市生活中的参照群体,大众传统媒介乃至新媒介都功不可没。
作为南京一家餐饮连锁店的点单员,小敏并不是第一次在城市工作,她先后在苏州和上海打过工,现在来南京工作只是为了能够跟做手机贩卖生意的未婚夫在同一个城市。为了使自己尽快融入并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一方面她将大众媒介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与城里的朋友时常联系,另一方面她又从各种媒介平台上获得很多关于城里人和城市文化的信息。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都会在城市里主动地去接触和使用各种各样的媒介,这是他们在城市生存的必要手段,也是拉近与城里人距离的最佳工具。而小敏有一个做手机生意的未婚夫,更加促进了她在新媒介方面的接触:
我会经常换手机,因为未婚夫是做生意的,他在南京认识很多当地人,也就跟我成为朋友。我很喜欢跟他们在网上留言,基本每天都会在空间里聊一聊。
上班之余,小敏喜欢在微博、微信上跟朋友交流,也会在天涯论坛上浏览各种新的帖子。这些行动都让她对城市以及城里人的日常生活更加了解,也促进了她对城市的认同。在有男朋友之前,只身一人在南京,她对家乡对小时候生活的农村还算充满感情。而随着城市经验的增加,在南京的熟人范围逐渐扩大,加上父母亲都在外地打工,这让她对乡土没有了太大的留恋,一些农村的习惯也都不再遵循了。她对于城市认同的改观就是认为自己已经是半个城里人,尽管不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城市的信息太多,需要通过网络、电视好好学习,不然跟朋友一起会落伍”,这也是她在提到对城市的感受时发出的感慨。
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实际上面临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学者在研究农民工时提出过“双重边缘人”的概念,这一概念恰恰是基于回不去的农村与融不进的城市这一必然阶段的解读[6]。
来自贵州的小琴,年近30岁的她已经有了一个10岁的儿子,目前在江苏南通做服装销售工作。贵州的家乡太过贫困,重男轻女的传统农村家庭逼着她必须自己出门谋生。起初跟老乡的一位姐姐到了南通市,在一家舞厅工作,做服务员。后来结识了当地的文华,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嫁入城市家庭,让她在城市生活和城市融入中比其他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容易,于她个人而言,也获得了更多的关系资本。人际关系的现代性引导让她完全适应了城市中的角色,对于乡土的感受,似乎已经消失殆尽,家乡成为再也回不去的“最熟悉的陌生地带”。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之所以乡土成为回不去的乡土,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目前都生活在与农村环境截然不同的城市当中,当农村的语言、仪式、事件不再会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在强烈的城市拉力与微弱的乡土记忆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几乎失去了对乡土的记忆。
进入城市前的新生代农民工们满怀希望和追求,却从城市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中感觉到了一些歧视和冷漠,从与城里人的差距中察觉到自己与城市的格格不入。他们在城市大多从事服务行业,也正是因为职业与城里人近距离接触的环境让他们体会到自己与城里人之间的一种不可融合感,他们免不了会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们眼中的自己是一个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异于家乡农民的双重边缘人,他们属于城市中的一员,同时又没有摆脱农民的身份。尽管他们脱离了对于土地的依赖,但他们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农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他们回到农村,感觉自己的过于“时髦”遭遇了村里人的排斥。他们来到城市,却又感觉自己的乡土气息与城市文明互不相容。
不难发现,这种边缘化的自我认知缺失是由于他们缺乏对于城市的归属感以及缺乏对于乡土的归属感而造成的。尽管在城市环境的长时间熏陶中,新生代农民工获得了与城里人接触的机会,也从各种媒介中了解城市的文化,但是他们在自我认知的层面必然会表现出不自信和不确定性。边缘处境的形成还在于回不去的乡村,即一种来自农村的外推力。一方面,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新生代农民工不断现代化的过程注定与农村有一点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农村人口的流动性正在加强,村民往往认为年轻的农村人如果不到城里打工或者闯荡,在村里生活并不是一个有出息的做法。在农村无形的压力下,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一个回不到农村又融不进城市的群体。
乡土的记忆是依托于乡土的集体环境而存在的,因为记忆产生于集体,并且集体记忆是关于一个集体过去的全部认识的总和[7],它可以在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中建构起来[8]。这样的乡土记忆同样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当新生代农民工脱离了村民的身份而只身来到城市,他们就已经丧失了有可能会延续记忆的共同体即原先集体,转而进入的是与城市紧密联系起来的城市集体。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乡土记忆的断裂似乎成为必然经历的阶段。
实际上,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等同于完全地被城市文化同化只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不得不承认,从进入城市以来,新生代农民工一直在追随着城市的文化,在城市环境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他们首先从自身外在展开了现代性的蜕变,其次从内在也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改变。然而他们并不能达到完全城市认同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也在发生变化的则是乡土记忆,当乡土记忆逐渐走向模糊甚至断裂而城市认同还未真正建立的时候,一个自我认同空白的状态由此产生,这种认同空白的状态意味着认同危机的出现,即认同的双重边缘化。一方面他们是还未融入城市的城市边缘人,另一方面他们却也是离乡弃土的乡村边缘人。
走出认同的困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们往往会从消费方式转型、价值观念变迁等追求现代性的层面来改变自身。而以往常常被忽视的乡土记忆实际上也是有助于他们真正走出这种认同的困境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这样的认同空白需要乡土记忆进行填补。从新的文化适应角度来看,现实的城市适应应该是基于乡土记忆和城市文化而存在的,乡土记忆的修复与传承或许是走出认同困境的重要途径。
三、媒介修复与传播弥合:一种集体记忆的再生产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城市生活体验后,新生代农民工会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媒介,从电视等传统媒介到网络等新媒体,再到如今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在乡土记忆断裂后,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的记忆有可能会在城市中各种媒介的影响下被唤醒,乡土的文化与习惯不同程度地被修复。而乡土记忆的重构并不是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现代化进程的倒退,相反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的自我调节,找到其中的平衡才是他们融入城市的理想状态。
刚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都有一点“崇洋媚外”,他们往往会觉得乡土的习俗、文化和观念是落后的,而城市的文化是他们期望追随的,也是洋气的、科学的、进步的,于是他们在城市中追求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城市生活。不过,从动态的视角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被城市文化“拉”进的同时,乡土文化也在另一边不断地影响着他们,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乡情的维系。
乡情的维系往往来源于乡土社会中人情纽带的存在,人情在唤起乡土记忆时成为一种载体。传统社会十分注重亲缘维系,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的亲朋好友大多都在一个村庄,因而从红白喜事的宴席再到传统节日的风俗,甚至一些纠纷和摩擦,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足以让他们与乡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时各种媒介往往充当着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使者。
雅婷,1982年出生,在南通一家酒店做服务员。酒店规模较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这让她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在酒店的长期磨炼下,雅婷已经从懵懂的小女孩蜕变成做事利索、雷厉风行的大堂经理助理。从18岁离家打工,她在服装厂做过质检员、在专卖店做过店员,几经周折进入现在这家酒店。每天忙碌的她喜欢在空余的时间跟同事出去唱歌娱乐。不过老家乡村的记忆在她的生命中却经历了遗忘到再次出现的过程。长期的城市生活,让她已经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媒介为她带来现代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情的维系。当追问到家乡风俗的时候,她提到关于自己结婚期间的一些记忆:
老公是老乡,结婚的时候是在老家安徽办的。上班哪有时间呢,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准备。结婚就是在家里摆好几天的酒席,现在想想都累死了……南通的朋友不是很多,亲戚都在老家,肯定是要在家里办酒席的。
留在城市但又遵循乡土的某些礼仪是雅婷身上的典型特质。尽管她来自农村,只有高中学历,但是由于没有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的经历,土地、农忙、农活对于她而言都是很遥远的记忆。然而对于雅婷这样进城十多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经历了手机的迅猛发展期,手机对于他们是一个最为便利的与家乡或老乡联络的工具。从拥有手机到与乡土建立联系,这一过程正唤起了他们内心沉寂的乡土记忆。加之随之而来的婚礼举办过程,手机更是桥梁,加深了以乡土仪式为载体的记忆。
除了作为通信工具联络乡情的手机,从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到网络新媒体,无不为新生代农民工展示了各色生活与文化。在城市生活中,各种媒介引导了他们对于城市文化的认识,自己的思想观念甚至生活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同时,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认知的增强,他们不再一味地追求城里的物质与文化,大众媒介、新媒体对于乡土文化内容的传播也唤起了他们对于乡土的感情。
在南京海底捞做美甲师的江西姑娘小陆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代表,也曾经历了孤独、退缩的想法。从想家、想回家到如今的努力工作、适应城市,她经历了很多的挣扎。如今,对于小陆而言,乡土记忆的再现来源于当地特殊的风景。家乡的风景被城里人追捧,也在网络上传播,这让她看到家乡的美好:
我在网上看到说婺源那边春天开很多油菜花,旅游的人比较多。我就觉得哦,城里人真是没事做,油菜花嘛,到处都有,还跑过去专门看油菜花做什么。网上的图片很漂亮的啊,不过我老家农田也都有这些,不觉得稀奇。不过,说我们江西美,我当然也很高兴了。
由此可见,从初次进城的担忧与不安,到接受信息的迫切与无奈,到城市化过程中的努力与尝试,到城市适应的乐不思蜀,再到“土”“洋”结合的双重认知,一种基于媒介的情感联系和乡村文化的媒介呈现为他们提供了可以追忆乡土的中介。
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进城时间长、经历丰富的新生代农民工往往还会出现对于乡土进行重新认知与评价的转变。家乡的语言、风土、人情更多时候会让久居城市的他们再次怀念起来,这就是一种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记忆。他们往往以媒介为平台,将传播的内容与历史的记忆之间建立起联系,比如通过某一电视节目中的人文地理或是风土人情,抑或是网络平台中任何足以让他们与老乡或家人流露情感的互动交流,模糊的乡土记忆会逐渐变得清晰,乡土的场景和生活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复原,沉寂在心中的乡土情结瞬间与媒介呈现产生了一种共鸣,于是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中重新记起之前一直隐藏于内心的乡村生活和乡土文化。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家乡话的态度。他们中有不少人称自己的家乡话为“土话”而不是“方言”。刚入城市,他们对于“土话”有着明显的逃避态度,一方面他们害怕“土话”与城里人说话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又担心语言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得不到城里人的认同。于是进城不久,新生代农民工开始主动学习当地语言或是努力讲好普通话,争取让自己更像是一个城里人。他们开始离不开手机,每天接触网络,有了更多的微博好友和微信好友,下班了没事干也会坐在电视机前,成为典型的媒介依赖者。然而当电视上、网络上传播的内容涉及他们家乡时,几乎成为弱关系的乡土体系则被媒介再次拉回。曾经被视为城市融入障碍的乡土习性诸如“迷信”“土话”等再次在他们心中拥有了新的地位。
如前文中在上海餐饮店担任前台服务员的汪小姐,从一开始觉得在上海说湖南话会很土、没面子,到现在也时不时地和别人说说湖南话,平时也喜欢看湖南卫视有方言的电视节目,对湖南话“土话”的认知与态度在她心中明显发生了转变:
以前不懂事,还觉得会上海话就很时髦的,现在觉得土话就是每个地方都会有的嘛,我们湖南话也没什么不好,有时候在路上遇到讲湖南话的人,都会觉得亲切。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语言的认同并没有那么顺利,从一开始对自我语言文化的不认同到对城市中普通话与城市方言的认同,而媒介中对于乡土方言的呈现作为一种拉力又将新生代农民工拉回到曾经生活的乡土之中。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两个语言核心圈,就如汪小姐一样,她说“一直在学着去说上海话”,在她看来,与城里人语言的同质性是消除农民工身份的重要方面,然而现在的她又认为上海话、湖南话“都是方言的嘛”,从这句话可以理解到,两者是并列的语言,代表着各自的地域文化。实际上,就汪小姐而言,一方面她认同了所处地域的上海语言,另一方面湖南老家的方言也是让她倍感亲切与归属的又一核心语言。媒介上内容的呈现为汪小姐营造出虚拟的乡土文化场,从而选择性地唤起了她对乡土文化的一种记忆与认同。
实际上,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对接抑或融合主要来自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意识。在促进这种主观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媒介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内容呈现的方面,作为传统媒介的电视,以影视剧、电视节目的方式呈现,作为自媒体的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以丰富多彩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方式出现,从视觉、听觉等方面无不打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弦。乡土记忆的唤起带来的不会是消极的作用,相反,它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入的主体感受。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他们对于乡土文化的认同满足了自身归属感的需要,他们的城市文化认同又让他们在城里拥有一片天地。而随着城市生活环境中大众传播媒介乃至新媒介的日常接触、人际沟通的无处不在,对于城市文化的认同得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乡土记忆也在不断通过媒介呈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中。
媒介环境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记忆重生,乡土记忆在媒介的作用下不断地修复,逐渐成为城市适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能力强,主动接受新鲜事物,也积极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而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因此集体记忆是一个建构的过程[9]。他们使用媒介作为传播工具,在乡情的维系中构建起乡土的文化。他们又广泛地涉猎媒介载体和平台,在媒介接触过程中唤起乡土的记忆,接受乡土的再现,从而让乡土文化得以回归。在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不断推拉作用下,他们很快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没有孰是孰非,而是一种促进他们融入城市的双重认同态度。
四、双重认同:乡土记忆与城市文化融合的可能路径
“双重认同”较早在移民研究中被提及。如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这一著作中,波兰农民在向美国迁移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单纯接受美国文化的过程。波兰农民进入美国,两者之间的文化传播是双向互动的。除了接受美国文化,与此同时波兰农民也将自己的文化带入了美国社会,这其实是一种文化融合和双重认同的体现[10]。波兰农民在美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由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的多元自然随之而来。而在文化多元的背后应该是新生代农民工内心需要形成的双重认同。当城里人认为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文明的、健康的、现代化的并且是正确的时候,文化的歧视并没有被打消。而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角度来看,当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依然处于不断追求城市文明、掩盖乡土文化的时候,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并没有建立起来。事实上,真正的文化共同体应该是差异化的共同体。
本文提出的双重认同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对于乡土身份与城市身份的、对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双重认同。因为只有形成一种双重认同的结果,这种差异共同体才得以实现[11]。在双重认同的具体识别中,身份认同是对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包括从经济到文化的多重维度[12]。新生代农民工区别于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打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生存理性与发展理性的观念一直引领着他们的行为取向。从作为城市“陌生人”的经济排斥、身份排斥和文化排斥到作为“新市民”的经济适应、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从作为农民工的乡土记忆保留到乡土记忆断裂再到乡土记忆的再现,新生代农民工内心的文化空间经历着斗争、抛弃、遗忘、重拾、融合等过程。这一过程中传播媒介充当了信使也充当了工具,一方面化解认同危机,另一方面重塑了身份认同。
从长期过程来看,乡土记忆与城市文化的碰撞必然会在新生代农民工内心形成一种双重认同,这样的认同方式反而促进了城市融入。从经济层面来看,他们适应城市的消费主义与财富观念,抛弃了乡土社会中依托土地获得收益的经济规则;从社会层面来看,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依然偏保守和落伍,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拥有了一些自主意识,如职业规划、婚恋观、公民意识等;从精神层面来看,他们对于身份认同有了新的理解,他们尽管秉承自由恋爱、晚婚晚育等城里人的价值观念,却在办理婚礼仪式上遵循乡土社会的规则;他们努力适应上海话、普通话等,却与家乡人保持着方言的联系;他们在城里的灯红酒绿中穿梭,游走于网吧、KTV、酒吧、餐厅等消费场所,却也会在重要的传统节日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或举办某些符合乡土风俗的特定仪式。于是,“农民”与“新市民”两种身份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积极体验城市的各种新鲜事物,接受城市的文明与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与乡土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早已习惯了乡土社会中的风俗文化。
在人类历史上,共同体是一种由共同生活中某种纽带连结起来的稳定的人群集合体,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以语言、文化等为纽带形成的民族等[13]。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也已经具备了与城里人一致的地域空间,并一直努力形成与城里人一致的共同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原始意义的共同体逐渐消失。身份的认同是共同体生成的基础,认同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自我的同一性、自我的归属感以及自我的意义感问题[14]。当新生代农民工以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无法在城里立足、而积极努力地进行现代性的发展时,乡土与城市并没有真正地融合起来。相反,乡土与城市越来越远,发生了传播的断裂。他们生活在城市环境中,努力成为城市共同体中的一员,他们完全脱离了乡土的社会也忘却了乡土的文化,甚至认为乡土是他们再也回不去的地方。然而传播却让重回乡土成为可能。重回乡土不是再次回到乡土社会中生活,而是让乡土文化再次在城市中得以立足,获得重视抑或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体不是只基于城市文明的文化空间,而是差异性的共同体,这种差异性来自于不同的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并存。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乡土记忆从传播断裂到重构则是一个嬗变的城市化路径。传播的断裂形成的文化鸿沟又得到了传播媒介的弥补。记忆可以说是一种过去,我们所记得的过去是为了现实所重建的过去[15],因此乡土记忆作为一种具体而微观的文化内容,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内心而言,一种双重认同的认同机制在内心产生。再上升到宏观的意义上,可以看到,正是因为传播对乡土记忆的重建,城乡文化从对立走到融合。由此不难看出,乡土记忆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进程中具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与功能,而城市融入的意义和目标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眼中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五、结语
“乡土”二字似乎就已经将农民隔绝于城市之外,而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去乡土化”是他们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不断努力的方向。他们脱离了与“土”的直接收益关系,实际上却从未曾离开过“乡”的社会层面。即便是外出打工“混得很好”,在城里几乎获得无压力的经济收益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如此。回到农村的老家中,他们有很多的亲人与朋友,村里的邻居还有家中的老人。在这种规律下,清明、春节等重要节日,农村的老家才是他们的“根据地”[16]。
我们应该看到,乡土记忆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空间,对新生代农民工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入有着积极的意义。乡土性不是作为城市融入的障碍而存在的,相反,在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不断推拉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多样化的文化认同,使得自己更好地适应在城市中的生活,获得强烈的归属感,对于乡土文化的“正名”也正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路径的本质是城乡文化的融合。从乡土记忆的层面来看,传播弥合了文化鸿沟,引导了新生代农民工内心的双重认同,同时也打破了原本城市化路径的“求同”原则,在“求同”的基础上给予“存异”的空间,进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在城市与乡土之间达到平衡。此时,良性且又人性的城市适应或许能够成为可能。
[1]汪华,孙中伟.乡土性现代性与群体互动:农民工老乡认同及其影响因素[J].山东社会科学,2015,(2):21—27.
[2]胡晓红.社会记忆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08,(9):42—46.
[3]李强,李凌.农民工的现代性与城市适应——文化适应的视角[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29—139.
[4]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J].社会,2011,(1):223—241.
[5]耿敬,姚华.当代乡土文化的流动性特征[J].东方论坛,2007,(3):92—97.
[6]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8):36—38.
[7]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11,(2):121—126.
[8][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美]托马斯,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M].张友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1]陈孔立.从“台湾人认同”到双重认同[J].台湾研究集刊,2012,(4):1—7.
[12]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21—27.
[13]张志旻,等.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0):14—20.
[14]潘泽泉.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J].社会科学,2010,(5):74—79.
[1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6]熊凤水.流变的乡土性:内核机理与理论对话[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39—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