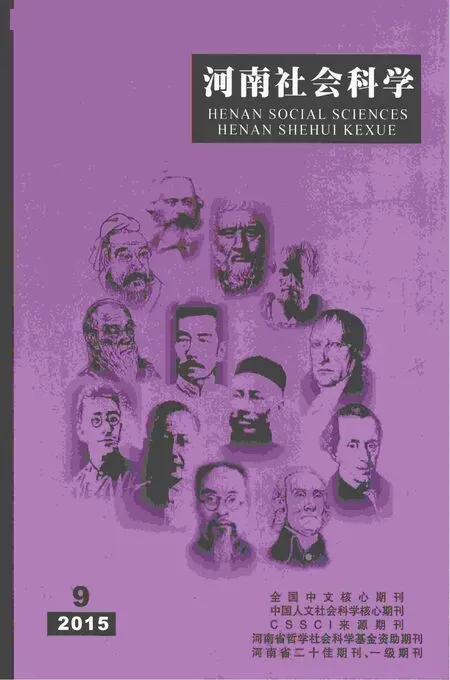剧场、表演与记忆政治——对上海民间淮剧戏班及剧场的考察
杨 子
(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 200031)
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
——唐·司空图《漫书五首》
全球化对地方性文化的削弱与摧毁在当下已成一种常态,因而,作为特定文化共同体共享的记忆,文化记忆成为人文社会学科日益关注与聚焦的主题。本文对上海民间淮剧戏班及其所驻剧场进行考察,旨在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地方性文化、建基于地方性文化之上的文化记忆和全球城市之间的关系,当地方性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被更新、被消解,地方性主体如何通过剧场及剧场中的“表演”实践构建记忆政治,进而重建共同体及身份认同。
作为移民社群的文化场域,分布在上海的苏北移民聚居区的民间淮剧戏班和剧场,可作为独特视角来考察全球语境下地方性文化的构成、生产和发展,以及“苏北人”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也即地方性社会主体的社会空间及其与客居城市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上海民间淮剧戏班的剧场与表演实践为例,探讨在全球文化流动的框架中地方性文化处于何种位置,在地方性日益被消解的全球都市空间中,全球化与地方性如何相互建构,进而探讨地方性主体在剧场表演实践的记忆政治驱动下,如何进行社区共同体与公共空间的重建。
一、地方性文化的社会属性
地方性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学性质,是关系化和语境化的,表现为特定的社会性、能动性和再现性[1]。作为非原生的上海地方性文化,上海民间淮剧戏班及所驻剧场承载着苏北移民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生命史,是他们家园情感的延续和想象力的再创造,对其在全球都市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发展态势,以及“苏北人”这一地方性主体文化记忆的考察,有必要对淮剧戏班南迁入沪进行追踪溯源,并对“苏北人”这一特定概念进行爬梳厘清。
(一)被污名化的“苏北人”
19世纪中叶南下移民进入上海的苏北人及其所带来的苏北小戏,当属外来人口及移民文化,在历经百年与城市的交融发展中,成为多样性的上海城市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对起源于苏北的淮剧在上海的发展兴衰进行回溯之前,首先对“苏北人”这一概念进行意义界定。在对“苏北人”的研究中,韩起澜指出,“苏北人这个概念源于移民格局,极有可能是一种标签,用以描述江南和上海的移民人口”[2]。
19世纪中叶,频发的自然灾害促使大运河沿岸居民南迁,包括上海在内的富庶江南地区成为首要迁移之地。这些来自苏北的移民大多数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如拉车、码头干活、澡堂搓澡等。从19世纪晚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居住在上海的一名苏北人,则意味着他是穷人[2]。当“苏北人”作为下层阶层穷人的标签,用来描述江南地区或上海的外来移民人口,“苏北作为一个地方的理念便产生出来,用以界定他们的原籍”[2]。职业的低下使得“苏北人”成为社会偏见和歧视的对象,“苏北人”被“污名化”的历史在他们南迁的背景中拉开序幕。南迁艺人将江淮戏带入上海,淮剧在上海的发展兴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北人”被“污名化”、被边缘化的典型表征。
(二)淮剧进沪
一百多年前,淮剧发源于淮河流域的苏北里下河地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北发生特大水灾,部分艺人来到上海,也将江淮戏带入上海,在苏北人群体中广为传播,观众主要聚居在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码头、市区四周边缘地带和郊区市镇等地区,大多从事拉车、环卫等工作。民国初年,江淮戏艺人主要在街头坐唱演出,1916年,陆小六子在闸北开设了第一家专演江淮戏的群乐戏园,第二年,马金标在南市三合街开设了三义戏园,江淮戏从街头演唱进入剧场登上舞台[3]。
淮剧早期能够进入的剧院远离租界,地理位置比较偏远:如南市的民乐大剧院,斜桥的黄山大戏院,闸北的凤翔大戏院,上海大西大戏院、高升大戏院,后两家戏院位于上海西区棉纺工人集中之地[3]。上海解放前,淮剧从未在公租界或法租界的大戏院里演出过,能够接纳淮剧演出的戏院,也只是拉黄包车起家、来自淮安的刘慕初夫妇所开办的民乐戏院。
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一些京剧演员加入淮剧班社,或与淮剧戏班同台演出,无论是剧目、行当、表演艺术,还是音乐和舞美,淮剧均从京剧这一剧种中获得丰富养料而被充实。抗战胜利之后,众多逃离战乱的淮剧艺人重返上海,组成众多班社,这一时期,民间淮剧戏班得到较大发展。淮剧有史以来最为昌盛的发展时期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产业工人政治及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苏北人”占据上海产业工人的大多数,这一时期,淮剧观众迅速增加,演出团体达到14个,分布于各区,演职员近千人,淮剧进入各区主要剧场演出,政府甚至出资专门设立淮剧演出的剧场,如这一时期的沪西工人剧场和黄浦剧场都是专演淮剧的剧场。同时,市区各大剧场也向淮剧开放。1951年,由马麟童领衔的麟童淮剧团和筱文艳、何叫天领衔的联谊淮剧团合并,并吸收竞成、日升等剧团部分演员,组成民营公助性质的淮光淮剧团,不久改名为上海淮剧团,1953年改为国营上海市人民淮剧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简称“三改”,也即“改人、改戏、改制”,艺人改造和剧目改编都在人民政府巩固新政权的背景下进行,艺人被赋予“戏剧工作者”的新身份纳入意识形态宣传队伍中。部分民间戏班被改造成国办剧团,对剧目的改造同步进行,一批优秀的整理传统剧目和现代题材剧目涌现,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剧目被禁演,禁戏过多导致一些剧团无戏可演而被迫解散。“文革”开始后,上海市人民淮剧团被勒令停止艺术生产,区属淮剧团则全部被解散,遑论民间戏班,更为无从生存。
(三)戏班重兴
苏北人的南迁在新中国成立后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计划经济管理下,在很长时间内一度停滞。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民间淮剧戏班在上海重兴,在一定程度归结于80年代初人口流动政策的放松。人口的自由流动为剧场的观众群体和淮剧艺人提供了新鲜力量。
上海市人民淮剧团作为上海市唯一的国办淮剧艺术团体,80年代初到90年代开始式微,观众流失严重。与上海淮剧团的市场大幅度萎缩形成鲜明对比,民间淮剧戏班迎来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的一段鼎盛发展时期。淮剧艺人在闸北、杨浦、浦东新区、虹口等区的苏北籍人居住区内设立简易剧场,低廉的票价和便利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苏北籍人进入乡人开办的剧场。据调查,这一时期出现在上海的苏北民间淮剧戏班多达17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海淮剧团在全市范围内覆盖面的不足。
(四)戏班式微
民间淮剧戏班的式微始于21世纪初。调查结果显示,到2011年年初,上海的民间淮剧戏班尚存7家,但到2015年年初,上海市民间淮剧戏班只剩4家,其他或关或转或迁回苏北。
2015年之前,全市的民间淮剧演出剧场共有6个,面积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是由工会社团和普陀区政府设立的沪西工人文化宫剧场,是正式的舞台剧场,可容纳百余名观众。其他剧场均为戏班租赁的民宅或者商铺。如位于瑞虹路的新兴淮剧团剧场由废弃的造纸厂仓库改造而成,可容纳观众50人左右。位于闸北区的杨四戏班和杜红梅戏班租用面积狭小的临街商铺,只能容纳20余名观众。这些剧场都分布在苏北籍人居住区内,观众以该街区老年苏北籍移民为主[4]。
根据调查得知,民间淮剧戏班衰微始于2003年左右,这一年“非典”爆发,但“非典”不是戏班衰微的绝对原因,是城市拆迁运动给了剧场最后的致命一击。
《上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在2000~2006年,以苏北籍人主要聚居的虹口区、闸北区和杨浦区三区为例:闸北区2002年拆迁户数最多(7643户);虹口区2003年拆迁户数最多(10417户);杨浦区于2002年拆迁户数达最高点(达10707户)①。显而易见,无论是“全市拆迁户总数”,还是“三区拆迁户总数”,2002年和2003年在这两个衡量指标上均列10年来的三甲。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03年左右会成为上海民间淮剧戏班走向式微的关键时期。在旧城改造运动中,不仅因为苏北籍人被迁于郊区而导致淮剧观众被分流,戏班赖以生存的剧场同样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二、观演场域:记忆政治的构建
民间淮剧戏班的式微显示了全球化城市运动剥夺记忆与消解历史的治理技术,以及地方性文化在权力与资本范式下的记忆政治中被消解的现实,由此引出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地方性主体如何通过“非权力范式”的记忆政治展现并保存其原有的文化形态。
剧场是民间淮剧戏班赖以存在的要素之一。演员和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的社会交往与行为,是剧场中核心的社会关系构造,为观演关系、消费共同体的构建及家园想象这几重剧场实践提供了一个彼此互相借力的互动场域。这一场域,笔者称之为“观演场域”,是一个动态的权利关系结构,是地方性主体通过剧场、表演实践所建立起来的、与权力与资本范式的记忆政治抗争的新的记忆范式。
(一)观演关系:情感认同
民间淮剧戏班实行薪水日结制,其收入主要来源于观众给演员的小费,行话称之为“彩头”。观众打彩的具体金额不等,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及自己和演员的关系深浅而定。但在节日或者封箱日,观众打彩的金额要比平日多一些。演员和戏班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演员为戏班带来收入,但若没有戏班、没有剧场的存在,也就没有固定的观众,那么,演员的收入也必定受到影响。所以,将自己所收“彩头”上交与戏班共同分成,演员对此是认可的,在经济利益共享和生存压力共存的情况下,上交“彩头”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也促使演员与戏班构成比较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演员和观众之间关系的深浅,决定了观众是否给“彩头”及“彩头”金额的大小。对演员们来说,戏班的观众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由此,戏班的经济运作模式决定了观演之间的权力场域和社会关系构架。
1.观演互动
在剧场中,观演互动无处不在——无论是在演出前、演出后,还是演出过程中。观众进入剧场,演员敬烟倒茶、热情相待。演出前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与亲热,为演出时的“打彩”奠定了情感基础。“打彩”是演出过程中观演互动最为重要的一环,观众借“打彩”表达对演员的喜爱,或因被剧情所感动而打彩;对于演员和戏班来说,“打彩”则是一种价值认同的表达,更是他们唯一的营收方式。很多时候,在演出前被演员们热情招待的观众,往往不是因为对方的演技,而是出于情面上台前“打彩”。演员在台上唱,对谁给自己打过彩谁未打彩心中有数。唱完下台后,收到“彩头”的演员一身戏装走进观众席,向刚刚给他“打彩”的观众致谢并敬烟。
观众对演员的“打彩”及演出前后的热络互动,是基于人际的情感联系与经济往来,除此之外,观众和演员所扮演的角色的互动在剧场中也屡见不鲜。
以2010年2月4日晚杨四剧场演出的《凶婆恶媳》单本剧为例:该剧是关于婆媳之间的家庭伦理剧。在恶婆周氏虐待婉贞时,台下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大声地与台上互动应答,带动全场观众笑闹起来。当艺人吉凤珍扮演的剑秋对高永梅扮演的婉贞道:“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她打你,你为什么不还手呢?”台下观众大声应和:“打,打,也打她!”而当婉贞在周氏的虐待下跪在舞台上泣唱,因天气寒冷,一位老太太起身从座前扔了一块座垫到台上,示意演员高永梅将膝盖跪在座垫上抵寒,高永梅将垫子垫在膝下,以眼神向老太太示谢,在此过程中,表演并未中断。
在这个剧场里,舞台与观众之间并不存在障碍,观演互动随时发生。当演员高永梅演至悲处、流泪悲哭时,观众上前“打彩”者众多。由戏生情,由情而动,观众完全为演员的唱做所俘获,乃至高声应和或者泫然欲泣,因为他们完全相信演员唱做所传达的含义,而忘了它是在戏台上发生的。这套认知系统实则为一种传统的力量:婉贞所唱做出的悲惨遭遇促使他们同情她的经历,他们在台下情不自禁的表现是因为他们无法认为她(高永梅)只是在演戏。惩恶扬善的传统伦理道德在此时占据制高点,中国戏曲在其特有的“情感之域”[5]中组织并运作所创造出的,是剧场中内在的、能够自洽的、使观众信以为真的标准。中国传统戏曲及其表演方式绝非关于自然和再现,它通过假设和虚拟的结构、言语、行动和音乐性等元素的风格化而产生意义。因而,在中国戏曲及审美中,正是这个全然由假定性或虚拟性行动构成的“指而可识”从本质上为观众设置了一种积极参与的角色[5]。观众的自发性情感通过舞台上的“非真”表演形态得以释放,进而接受表演所传达的一种认知或感受层面的真实。而“打彩”则是观众在这种状态下所表达的双重认同,即便这种认同是以经济手段来实现:为角色故事所感同身受及对演员的肯定,这涉及在看中国传统的“演戏”或“将虚拟性的故事的扮演作为戏”的过程中的“戏剧能”的运作意义,它不仅包括观看戏剧的场上行为,而且包括心理与行为的参与,剧场从本质上调动了人的能动性的制造。从这个意义,“打彩”是观演过程中人对演剧的直接参与和交流,是观者能动反应的具体呈现。
2.拜干亲
列斐伏尔在阐述“什么才是社会关系的真正存在方式”这一问题时[6],指出社会关系与空间之间互动的辩证关系,即“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生产了空间本身”[6]。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在剧场独特的运营机制下所建构的一种特有的观演关系,也即“拜干亲”,演员与观众所建立的一种非血缘式的亲缘关系。
“彩头”是演员的主要收入,为稳固和增加收入来源,演员将自己与观众的关系亲密化、稳定化;通过“拜干亲”的方式,以非血缘性的“亲属”关系来保证经济上的稳定与获利的最大化。
传统农村社区,人们的社会行为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网络中进行,依据传统农村社区的文化与行动系统维系村民生活与村社运转。这些来自苏北乡镇的民间艺人从原有居住地迁入城市时,依据原有社区的传统人际网络群聚而居,建立起一个独特的演艺与生活空间。观演场域中非血缘式的“干亲”关系,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城市资本竞争中难以避免的生存压力。传统农业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伦理中内含的人性关怀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非血缘的亲缘关系,作为丰富的再生性的社会资本,弥补了戏班艺人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弱小、无制度性保障的人力资本的不足。
源于剧场空间且延伸于剧场之外的空间关系——“干亲”,巩固了演员的观众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演员收入的稳定性。布尔迪厄认为,具有工具性功能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不可置换的人们自己所属的结构性网络中。在边缘化和底层性的剧场空间中所建构的“亲缘关系”是戏班艺人与苏北观众所共有的,具有最丰富的社会资本资源的结构网络,在剧场/戏班的生存中发挥着积极的最具实际意义的作用。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显示,人的关系网络涉及工具理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情感。它既是一种权力游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生活世界领域的建构上,人们在剧场中建立的对传统社会关系的承续保证了淮剧艺人与观众内心的相对平衡感,亲缘关系的传统与温情在此建构着他们对客居城市的生活意义和社会环境的适应性。显然,剧场的生存方式与运作模式内在地建构了观演之间独特的社会交往方式,而剧场空间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关系存在的基础,社会关系在生产实践中也相应地生产、稳固了剧场空间本身。
(二)消费共同体:认同机制
综上所述,观演场域中剧场共同体的结盟体现在其无所不在的观演互动,以及独特的亲缘关系的建立,而通过“打彩”建立的“消费认同”机制则建构了剧场的“接纳”与“排他”性的身份识别机制。
在调研中,笔者亲受从被冷落到被接纳的全过程。一个结构稳定的空间一旦被外来者所闯入,必定令空间中原有的社会群体产生不适感,冷漠甚至敌对情绪由此产生。在屡次对多个演员进行“打彩”后,剧场的观众大多对笔者表露出善意,甚至有几位老年观众对笔者连声道谢。在这个熟人化的人际关系网络里,观众与演员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利用加强了空间组织关系的内部合作,针对笔者这样一个外来者也即“他者”的闯入,观众自觉和演员结成同盟,观演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呈一体化状态。故当“他者”向演员——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施予友善和经济赠予时,观众们会代表演员表达感谢。而观演之间所结成的“干亲”关系,更增加了观众们“越俎代庖”代表演员对笔者的经济赠予表达谢意这一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可见,在剧场中,“打彩”这一种消费行为充当了剧场共同体的“接纳”与“排他”制度。消费行为在这里是具有生产性的活动,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而且也是社会意义上的生产。法国社会学家尼古拉·埃尔潘认为:
消费是一种“社会参与体验”的生产活动,即参与某种共同的快乐或基本福利的体验。这种社会参与体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影响到我们对自我与群体或社会的关系的定义和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活动是一种社会语言、一种特定的社会成员身份感的确认方式。[7]
根据埃尔潘的观点,剧场观众的消费行为也即对演员的“打彩”,是一种免于陷入某种社会孤立的社会参与体验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剧场既是“接纳性”的,又是“排他性”的,通过“打彩”消费,“他者”获得剧场空间所认可的合法身份而被接纳,“打彩”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识别与社会整合机制,通过它,剧场成员构成特有的“消费共同体”。
通过非血缘式的亲缘关系的建立及剧场消费认同机制的运作,一个稳固的剧场共同体得以建构:亲缘关系的建立源于演员获得稳定收入来源的利益驱动而与观众进行的利益结盟,“打彩”是亲缘组织建立的主要目的,“打彩”的剧场消费与认同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观演之间自组织也即剧场共同体的稳定,从而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剧场体系:观演场域。
(三)看戏的人:家园想象
剧场具有集群化功能,在剧场中,熟悉的乡音和共同的苏北籍身份吸引观众走进剧场,在观众高度趋同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基础上,剧场不仅是一个实在的地理空间,而且也是一个共同的历史集体记忆的载体。对于一个在外客居多年或者已与客居地同化融合的苏北籍人,在许多方面都会发生改变,但唯一很难改变的,是来自胸腔深处、与生俱来的故乡的音调。“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由先民代代相传,与所处的山川水土有关,也与漫长的社会变迁有关,是在长期的历史社会发展中建立起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话语系统,是刻写在人的思想和逻辑深处的某种声学振荡。
传播学家E.卡茨提出的“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比较立体地解读苏北籍观众对剧场的空间认同及淮剧的接受过程,他将受众对某种媒介的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指出“人们接触传媒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这些需求具有一定的社会和个人心理起源”[8]。
在对观众的随机采访中,观众的述说证实了自身对剧场(媒介)与淮剧(传播内容)的“使用”来源于特定的社会因素及由此而生发的心理因素,并由此产生对淮剧/剧场的“心理期待”。当笔者对观众提出“为什么来剧场看戏”这一问题时,观众给出的回答大多为,“苏北人就该听苏北戏”,或者“有一种熟悉的乡情在里面”。可以说,剧场、舞台传唱的乡音,是观众对故乡存在的确认,是对家园的想象和建构,也是进剧场“看戏的人”的心理期待。
剧场作为“呵护场所”,提供了人们一种和故乡家园有关的“可行的、有序的、有度的感情生活”,它“给予普遍的、分散的、持续变化的肉体感觉一个特别的、明显的、确定的形式;对我们天生就服从于它的不断变化的感觉施加一种可认识的、有意义的秩序”[9]。对于“感情生活”的发生,兰格做了如下阐释:
它是由想象力形成的感觉,它能给予我们所知道的外部世界。正是思维的连续性,将我们的情感性的反应系统化为有着明显感情色调的态度,并为个人情感提供了一个确定的范围。换言之:凭借我们的思维和想象,我们不仅有了感情而且有了感情生活。[9]
格尔茨所确认的“可行的、有序的、有度的感情生活”“是由想象力形成的感觉”,并“能给予我们所知道的外部世界”,也正是进剧场之后“看戏的人”所获得的“需求满足”。杨四剧场中的现场表演所引发的观众的想象力具有双重维度,其一是舞台上的“非真”的故事通过演员的“非再现”(nonrepresentational)[5]表演手法进行表达和演绎,令观众获得一种认知或感受层面的真实;其二,凭借想象力,听觉认知——作为一种联系着社会和人的存在的社会感官——为苏北族群建构了一个想象的家园,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园认同,剧场实践成为苏北移民族群抵达“家园”的可行路径。
三、记忆政治:乡愁,地方性生产与表演的权利
作为一个社会活动过程,文化记忆指的是“对过去社会的、建构式的理解”[10]。苏北移民通过剧场观演场域所建构的情感认同、社区共同体与家园想象,是在全球化城市运动记忆剥夺与历史消解的治理政治下,对这一族群集体文化记忆的存续与传承。
本文以地方性剧场与表演实践为例,勾勒出在一个去领土化的全球化文化中,地方性文化生产及其文化记忆存续所遭遇的困难。在资本的同一性运动中,生产地方性(作为一种感觉结构、一种社会生活特质、一种特定处境中社群的意识形态)日益艰难[1]。剧场观演场域的建构体现了“苏北人”这一移民族群在全球都市空间中通过剧场实践造就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空间,在现代都市空间规划所给予的有限空间中,展现了“看戏的人”与“演戏的人”的主体能动性。在面临集体身份危机和文化记忆如何存续下去这些问题时,剧场实践是保证断裂时期地方性文化能够生存下去的一种策略和实践方式。
作为民间淮剧戏班在客居城市赖以生存的空间,剧场中特有的由演剧实践与观演关系所建构的观演场域凸显了这一场所的文化特殊性,成为移民社群建构的记忆范式:它不仅仅是一个演剧空间,而且也是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和记录;它有着塑造记忆载体群体身份的功能,民众的生活体系很清晰地雕刻在剧场空间中;它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和生产的样式,不仅是地方性主体的社会关系、文化习惯的行为模式,且涉及他们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感知自己的空间位置,进而通过剧场实践重建公共空间与社会关系。
总之,剧场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想象资源来自于共同体成员对家园的共同想象,以及共有的生活经验与历史记忆,经由这种由共同记忆和历史认同的情感所构筑的观演场域,正是移民族群抵达“家园”的主要路径。从这个意义上,地方性主体进行剧场“记忆政治”的运作本质,是运用“乡愁”的力量抵抗某种带有敌意的或强势的社会环境,通过想象性建构,生产新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
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实践性是决定其所固有的地方性文化以何种方式进行现代性展演的关键因素,以及能动者通过怎样的实践方式将传统文化带入当下,进行延续和再造。苏北民间淮剧戏班及其剧场实践让我们重新检视,人的身体感官知觉和空间生产通过剧场被充分联系起来,同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谁的城市?谁可以在这个城市中被赋予“表演与观看的权利”?弱势族群的诉求通常被城市设计者和规划师所忽略,在这些自我营造的“剧场”空间里,苏北移民族群以“乡愁”式的家园想象参与生活公共空间的生产,显示了弱势族群自行创造的隐性城市空间,以及他们在面对巨大的社会和城市变革时,延续生活和文化记忆的本能和方式。基于“乡愁”之上的自主空间的营造,表明城市空间不应只是被体制行政力量所操控,它也是市民/移民族群自觉地向资本逻辑所掌控的城市规划体制进行抵抗的领域,尽管这种抵抗在全球化高涨的当下如此微弱,在强势的都市发展逻辑面前不堪一击,但他们通过剧场抵达家园的想象,则提醒裹挟其中的每个人不要忘记自己特有的时空“定位”(locatedness)和价值“体现”(embodiment),也即每个人都有在这个空间中的“表演与观看的权利”。因为,这个城市不仅被资本与权力所构造,同样也是情感和记忆的聚集地。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2001—2007年。
[1][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维度[M].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2][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M].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3]《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中国戏曲志·上海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4]杨子.剧场作为“空间的再现”——以上海市民间淮剧戏班为例[J].艺术百家,2010,(8):315—321.
[5]颜海平.情感之域:对中国艺术传统中戏剧能动性的重访[A].高瑞泉,颜海平.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发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7][法]尼古拉·埃尔潘.消费社会学[M].孙沛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10]张俊华.社会记忆研究的发展趋势之探讨[J].北京大学学报,2014,(5):132—143.
——江苏省宝应县泾河镇中心小学“淮腔今韵”文化项目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