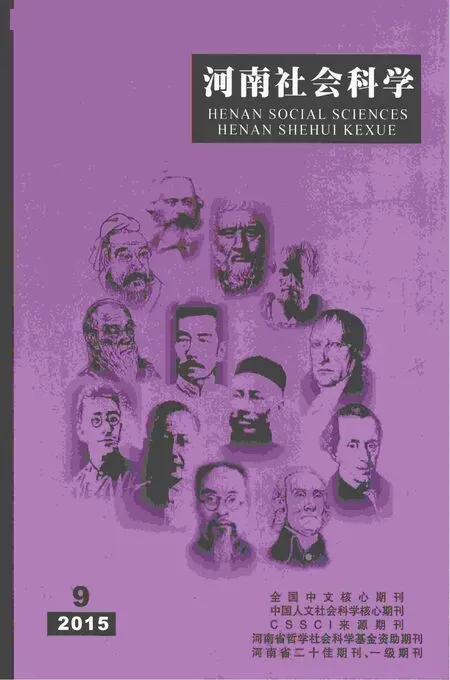创伤与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表征与美学再现
段吉方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自从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创伤理论以来,关于文化记忆与创伤研究就成了当代文化社会学研究中的焦点之一。亚历山大认为:“创伤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事物。”[1]亚历山大的创伤理论强调文化创伤建构中的社会属性,创伤研究具有融入一定社会思想文化的文化记忆特征,他的这一理论观念对文学叙事中的创伤体验与创伤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文学叙事中的创伤体验毫无疑问也无法忽略或剔除某种社会建构的属性特征,特别是某些具体个体创伤体验续写特征的创伤叙事,更是一种受社会文化建构制约的文化记忆形式。因此,从创伤叙事入手,探讨文学叙事层面上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超越个体文学书写的经验现实,才可能重构文化记忆的历史与现实,走向具有人类属性的文化创伤研究。
一、 从创伤叙事到文化记忆
在文化研究理论中,文化记忆和文化创伤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方向。文化创伤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杰弗里·亚历山大。2004年,亚里山大在自己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中提出:“当个人和群体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并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1]相比人类历史发展的前现代现实,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毫无疑问凝聚了太多亚历山大所说的创伤记忆,“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等两次战争的历史创伤早已将这种文化创伤理论映照进现实,关于“文革”的政治创伤记忆也长久地成为几代人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面对这些文化创伤记忆的反思有多种角度,像奥地利著名社会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在他所著的《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中,从现代社会和文明发展的角度进行反思是一种形式,他强调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文明罪孽”,认为20世纪威胁人类生存的种种危机,包括生命系统的机能障碍、人口爆炸、生存空间的破坏、追逐金钱过程中的恐惧性忙碌、“快乐刺激”中情感的暖死亡、否定传统后的文化危机、现代大众传媒的“灌输危机”等,这些“文明罪孽”“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它们不仅使人类的现代文明出现种种衰竭征兆,而且使整个人类‘物种’面临着毁灭的危险”[2]。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内在思想反省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面对20世纪的社会文化,别尔嘉耶夫曾这样表达他的体验:“孤独是我生命的基本旋律,我时感自己十分孤独。但依从自己的积极性和战斗性,我又周期性地进到现实的众多领域中去。然而现实总那么令人沮丧,幻灭感总时时折磨着我。”[3]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的层面上,对文化和历史的创伤体验,可以说像康拉德·洛伦茨的关于“文明罪孽”的外向反思和别尔嘉耶夫式的内省式反思兼而有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创伤与文化记忆研究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中,关于战争、杀戮、饥饿、死亡、苦难等创伤叙事文本屡见不鲜。20世纪初鲁迅的“幻灯片”事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伤叙事的代表,稍后萧红的《生死场》也具有个体和族群意义的创伤叙事特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文革”文学更是将创伤叙事引向高潮。90年代以后,无论是世界范围内还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创伤叙事更是屡见不鲜,《辛德勒的名单》《美丽心灵》《金陵十三钗》《归来》等一批艺术作品再度引发文化创伤和历史创伤创作和研究的高潮。在这些创伤叙事文本中,既有民族创伤的伤痛,也有政治的悲剧,当然更不乏表征历史和政治悲剧的个人化的创伤叙事维度。确实,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文本叙事似乎都能归结到创伤叙事上来,但在这些创伤叙事中,可以说叙事的过程与结果最终都大同小异,难以真正深入文化记忆的层次。关于战争、杀戮、饥饿、死亡、苦难等文化创伤记忆的历史该如何被书写,历史创伤该怎样表达,或者说在今天该如何被记忆,一直以来是中国文学的叙事研究没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有待深入研究的东西。
一个个体乃至群体的创伤从它发生,到成为永久的记忆,到最终产生不可磨灭或用亚历山大的话说成为“不可逆转”的文化记忆,这其中个体以及群体书写该如何有效恰当地表达,社会文化起到了怎样的建构作用以及传承作用,又如何让它跃出纯粹的创伤书写的层面而真正在一个社会的知识、理论、文化构成中起到历史和政治警醒的功能?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探究的。比如说,在中国文学叙事中,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创伤体验都能成为文化创伤的内容,也不是所有的创伤体验最终都能够上升到文化记忆的层面。创伤叙事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充分的社会化和公众化的过程,个人的创伤经验不但无法得到群体性的认同,更无法得到恰当的政治评价,像莫言在《蛙》中所说:“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4]这种书写人生不堪回忆的“苦难史”叙述,如果不经过社会美学和公共文化的中介表达机制,是无法得到时代和群体认同,更无法发挥应有的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是当代作家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在这部作品中,社会个体的记忆因素在文本叙事中连续呈现,但它是一种有选择的创伤记忆,基本停留在讲述“苦难家史”的层面上,还没有深入涉及文化和思想的记忆语境,只满足了文本书写层面上的创伤叙事的必要。类似于《蛙》《饥饿的女儿》这样的作品,都有点儿对文化创伤记忆“反过来讲”的意思,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停留在历史如何造成了不堪回首的创伤记忆的层面,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在一定规范中讲述创伤的故事。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内容,在一定规范中叙述苦难与创伤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历史语境的再现与政治悲剧的反思。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亚历山大的理论对文学的创伤叙事有重要的启发。在亚历山大看来,从自然的创伤到文化的创伤记忆,二者有很大的区别,无论是《饥饿的女儿》还是《蛙》,这些作品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自然创伤的书写层面上,还没有上升到亚历山大所说的群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层面,更缺乏某种权力架构下的政治悲剧反思。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创伤叙事引发的个体自然创伤体验正体现了中国文学叙事的危机,即创伤叙事体现了一种有选择性的文化记忆方式,缺乏群体性的认同和文化记忆层面上的政治反思,缺乏从自然创伤到文化创伤的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中介表达机制的洗礼,这样的叙事惯性造成了一种极为恶劣的叙事影响,那就是在这些文本中,好像每个时代的创伤记忆都是来自历史宿命与偶然伤害,从创伤叙事到文化记忆,仍然缺乏能够触及一个时代的心灵烙印和灵魂深处的全面反思。
二、文化创伤与苦难叙事批判
苦难叙事毫无疑问具有文化创伤的思想特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文化记忆重要的历史表征和美学再现方式,在文学叙事中,通过苦难叙事,有利于将某个特定时代和历史中的创伤记忆以审美化的方式再现出来,从而构成审美维度上最富有感染力的文化记忆要素。苦难叙事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与回忆,它所蕴含的叙事张力曾是很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竭力表达的主题,正所谓幸福的故事好听但难写,不幸的遭遇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经典之作秉承“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叙事美学,从而使苦难叙事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作家艺术家笔下屡试不爽的叙事武器。但是,从文化记忆的理论来看,仅仅从苦难层面上展现某种创伤是不够的,在苦难层面上建构创伤记忆在叙事伦理中或许是恰当的,但在文化记忆的层面上,缺乏政治伦理考察的苦难叙事则极有可能简化创伤,最终使苦难叙事仅仅构成了文化记忆的浅表层诉说,而缺乏深刻的美学再现仪式。典型的,电影《一九四二》提供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苦难叙事模式。在这部电影中,关于一群饥饿的人的苦难叙事收获了大量观众的热情关注,但仔细思量,这种苦难叙事的最终指向是苍白的,因为它仅仅从一种历史再现的层面上诉说苦难事件,而淡化乃至过滤掉了更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反思,饥饿是天灾还是人祸不但毫不涉及,而且以极为浓烈的片段化的饥饿场景化解了历史反思和政治批判。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是缺乏政治伦理的。在电影中,也表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如何救灾不力,国民党军阀如何趁火打劫巧取豪夺,但这些政治层面上的叙事目的是为了增添叙事中的苦难成分,而不是这部作品的真正的美学表现,说白了,电影还是停留在苦难叙事的历史偶然层面,缺乏关于文化、政治和思想的反省层面,它是被简约化和过滤后的苦难叙事,是一种缺乏政治伦理而直面阐释背景的苦难叙说。
与电影《一九四二》中的苦难叙事相得益彰地简化苦难和文化创伤记忆的则是时下文化艺术发展中的某些极端个案,典型是各种“抗日神剧”和“鬼子片”。如果说类似电影《一九四二》的作品是以简约化的苦难叙事规避文化和政治批判与反思的话,那么,各种“抗日神剧”则千篇一律地在简化苦难甚至逃避文化记忆,其叙事仅仅在于满足感官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文化创伤缺失的结果,在各种“鬼子片”中,普通民众很容易在快感消费中走向创伤记忆的“一体化”观感,即从“鬼子”对中国人的杀戮到日本军人被神奇的中国军人“手撕”的观感,其创伤体验是从咬牙切齿的恨到痛快淋漓地虚假释放的过程,最后被简化的是战争的创伤、民族的创伤乃至人类的创伤,被消解的是民族与文化的政治批判。这与鲁迅当年的“幻灯片”事件何其类似,鲁迅聚焦的不是杀人的日本人,也不是被砍的中国人,而是无意识的麻木的民族魂魄,现在来看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创伤的缺失;时下各种“鬼子片”聚焦的是被“手撕”的“日本兵”,体现的都是一种对文化创伤消费需求而导致的“围观效应”。
20世纪的100年充满了战争、杀戮、饥饿、苦难,在这个危机动荡的百年中,中国文学不缺乏苦难叙事的历史症候,但从苦难叙事向文化记忆迈进,仍然需要更深刻的政治伦理方面的思考。所谓“政治伦理方面的思考”就是要辨析哪些创伤事件是自然的个人创伤事件,哪些创伤叙事是政治和制度的悲剧。在个体创伤和群体文化记忆之间,超越个体乃至民族层面的那种有选择的苦难和创伤书写才是值得被铭写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区别于苦难叙事,就在于苦难叙事更多地体现社会个体艰难时世层面上的“有选择记忆”,如何避免这种“有选择的记忆”,是文化记忆研究值得借鉴和反思的内容。特别是在今天,苦难叙事和创伤叙事几乎成了文学的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在很多层面上是为了感官消费的需要,而不是文化记忆的责任。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记忆一定是那种超越创伤叙事和感官化或视觉化的“围观效应”的,因为那种感官化或视觉化的创伤记忆极容易简化了政治伦理方面的思考,消解了政治和制度悲剧的思辨考察,它的后果正是哈耶克所说的“真理的终结”,即“特有的全民思想的‘一体化’”[5]。
三、 超越建构性的文化记忆:文化创伤与“见证”
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文化记忆研究包含的问题非常广泛,苦难叙事和创伤叙事既是文化记忆的一种重要的样式,同时又是它的内在建构的起点。但文化记忆研究如果仅仅停留在建构性的层面上仍然是不够的,建构性的文化记忆形式很有可能将文化记忆陷入某种情感主义状态之中,从而过滤掉来自政治、制度和社会演进层面更为丰富的文化面相,这也正是文化记忆理论需要更深刻地引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文化要素的原因。在引入这些文化要素的过程中,关于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维度或思想维度不容忽视,那就是文化记忆研究中的“见证”理论。“见证”理论同样来自于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看来,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构成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的要素极为复杂,有时甚至是变动不居,社会属性的参与有时不一定完全能够把握每个时代的文化记忆的主体特征,这就需要某些特殊的主体、事件或场景再现创伤记忆,从而构成了某种“见证”。“见证”是形成永久记忆的必要形式,同时也是文化创伤研究的重要内容。
由于“见证”理论的引入,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研究具有了超越简约化叙事化的延展空间,同时也会避免由于某种“集体遗忘”而造成的某些重要的文化事件遭到政治的粗暴抽离。正像有的研究者说的那样,“创伤记忆通过创伤见证、讲述和倾听的方式在家庭、集体中传播,社会因素为创伤记忆塑造了社会框架和文化语境,并引发或内在地塑造了个人记忆和身份”[6]。在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的视野中,关于“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等世界性的文化创伤记忆都离不开这种“见证”的功能。“见证”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使文化创伤与记忆能够有效地突破某种区域限制、政治抽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历史的真实景象可以通过“见证”的过程而揭示出来,从而还原关于文化创伤的真实面目。
在创伤叙事的文学研究层面上,“见证”文化同样不可缺失。陶东风先生就指出:“从文化记忆的理论看,见证文学即是创伤记忆的一种书写形式,是通过灾难承受者见证自己的可怕经历而对人道灾难进行见证的书写形式。”[7]在他看来,这正是“见证”文学对文化记忆所起到的重要的政治伦理和制度悲剧的反思功能。从创伤叙事到文化记忆,需要“见证”文学的引入,这其实也是一个创伤叙事不断“被见证”的过程。因为在“见证”文学的有效引入下,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研究需要破除的正是那种简约化的创伤叙事形式,再拿时下的各种“鬼子片”而言,在“见证”文学的引入中,就是要深入思考,在某种历史表征下,民族的创伤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有没有文化的要素值得深刻反思?如何在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层面上再现民族创伤?从这个角度而言,“叙述”创伤显而易见远不如“见证”创伤更具有集体认同的效应。所以,无论是“南京大屠杀”的民族灾难的创伤记忆,还是时下各种“鬼子片”中的文化创伤的书写,如果缺乏“见证”文化的维度,就缺失了文化记忆必要的记忆载体,也失去了来自于历史表征和美学再现的矛盾和冲突,没有了这种矛盾冲突,文化记忆就会产生很大的断裂感。
四、文化记忆:从创伤美学到跨学科文化
“见证”文化为超越建构性的文化记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记忆载体,使创伤记忆有可能超越个体化、建构性的文化形式而凝定为永恒的记忆。但在创伤叙事面前,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当这些“见证”的资源或者说个体不在了之后,我们如何去表达文化创伤进而形成有效的文化记忆?这对中国目前文化界或者说思想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警示价值的问题。就“南京大屠杀”的个案而言,在当下文化记忆的“见证”资源越来越稀缺之后,它有可能被简约成中国现代历史政治巨变的一种“遗迹性创伤”,而不是文化记忆。这种“遗迹性创伤”承载的更多是民族国家层面的历史伤痛和仇恨之感,进而引发民族国家层面上的集体认同。不排除这些是中华民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化记忆的当然内容,但是,过于强化这种民族国家层面上的记忆内容,也会使它的文化记忆中的某些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内容被稀释,比如身体创伤的隐私、个体的尊严以及民族、文化层面上的必要反思,比如,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去做“汉奸”,一种文化记忆如果缺乏这种最起码的民族与个体尊严的反思,即便具有有效的“见证”文化,这种文化记忆也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狭隘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需要立体呈现。所谓“立体呈现”就是思考如何在充分吸收多角度多层面的历史背景、知识背景和记忆方式之后,不断跨越民族、地域、阶级和国家限制,走向人类视野的文化创伤记忆研究。就像我们面对“南京大屠杀”,仅仅满足于民族、国家层面的文化创伤研究,甚至是某种地域性的文化记忆研究,那肯定是不够的。这种跨越民族、国家、地域限制,走向人类视野的文化创伤记忆研究,正是目前文化记忆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方向。这种跨学科方向强调对于某种文化创伤事件的全面叙写和立体讲述,要在破除线性历史叙说模式的基础上,借助于媒介发展,综合融入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情报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历史,真实呈现文化创伤与文化记忆,特别是通过某些战争遗迹的发现、当事人讲述以及历史档案的重新发掘,增加文化记忆的历史厚重感和历史现实感,更主要地,通过媒介文化的引入,特别是媒介史研究的新发现,跳出线性叙述的历史视角,更深刻地观照某种文化创伤事件的历史文化表征,“从而把一般意义的历史研究上升到了历史文化的系统观照”[8]。
跨学科的文化记忆理论展现了文化记忆研究的纵深视野,呈现出了多重思想资源影响下创伤叙事的政治伦理的回归,它让某种创伤记忆超越纯粹个体层面和苦难叙事层面,而上升到人类学反思的高度。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文化的引入,特别是媒介史的研究成果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首先,媒介文化的发展与媒介史研究视角的引入,会让文化记忆的传播途径更加丰富,特别是借助于某些特定文化事件的反思感受,媒介史研究成果的发现可以让文化记忆超越某些意识形态厘定的叙事框架,走向“反抗叙事”;其次,新兴媒介文化的引入,使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本身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借助于媒介,在种种“见证”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某些创伤记忆的过程更加立体,不仅仅在历史曾经发生了什么的层面上记忆,而且不同媒介记录的见证差异增加了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的政治伦理层面上的反思。这种跨学科的文化记忆方式既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理论。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对于文化创伤和记忆更多地停留在线性历史叙述的层面上,满足于一种凝固的历史述说。要打破这种“凝固化”的视角单靠苦难叙事和个体创伤呈现是不够的。文化记忆理论的跨学科视野可以很好地弥补这种文化记忆研究的缺陷,它的意义在于超越创伤美学而走向文化记忆的跨学科文化。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等的研究,在创伤美学的层面上,线性历史叙述简化文化记忆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线性历史叙述更多地告诉人们历史曾经发生了什么,而对于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现在我们该如何反思、如何批判,线性历史叙述要么走向历史的说教,要么走向民族国家的情感聚集,很难达到那种群体性文化记忆的层面。那种凝固化的创伤美学研究的缺陷则在于容易流于个体化的文化记忆,这种个体化的文化记忆常见于个体创伤“抢救性”的“现身说法”,但是,当这种个体记忆的资源日趋稀缺之后,那种永恒的文化记忆仍然是难以留存的。正是从这个层面考虑,当代文化创伤和文化记忆研究需要进一步超越既往苦难叙事的简约化叙事路径,更需要超越审美化的记忆方式,在文化记忆的层面上,简约化和审美化的叙事对于文化记忆而言只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激发性因素,但如何从这种激发因素中发现更深层的批判和反思的空间,这恰恰是当代文化记忆研究需要深入思考的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研究而言,走向跨学科文化的文化记忆研究是我们所期待的。
[1]Jeffrey C.Alexander.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A].Jeffrey C.Alexander(ed).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康拉德·洛伦茨.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M].徐莜春,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3]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徐黎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4]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
[5]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王欣.创伤叙事、见证和创伤文化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75—81.
[7]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当代文坛,2001,(5):12—17.
[8]陈卫星.战争·记忆:媒介史研究的方法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