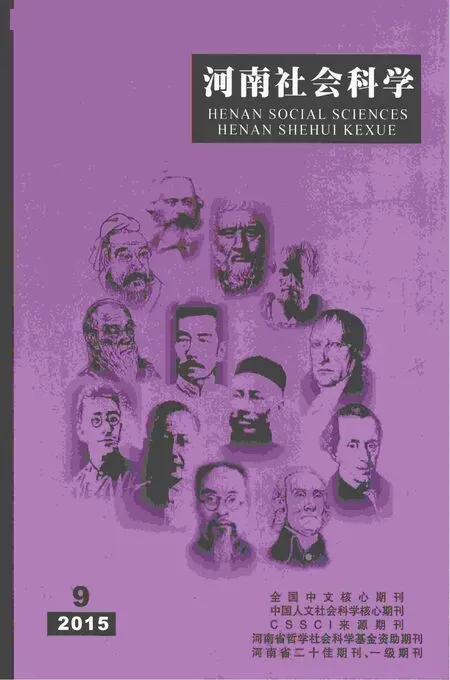行为犯之基本问题研究
王志祥,黄云波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一、行为犯概念的讨论基准
行为犯与结果犯是一组相对的理论类型。刑法学界之所以在行为犯与结果犯的概念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学者们对于行为犯概念的讨论基准认识不一致。因此,要想在行为犯的概念等基本问题上形成统一认识,首先就需要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基准予以统一界定。
笔者认为,行为犯、结果犯这一划分是针对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而言的,即行为犯与结果犯是被当作犯罪既遂的类型加以研究的。这是因为,虽然刑法分则是以单独的既遂犯的规定为原则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犯罪都能够达到既遂,也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由单独的犯罪人实施的。易言之,除了单独的既遂犯之外,还有未遂犯和共同犯罪等情形存在。法律的表述方式只能是语言①,语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将所有情况予以一一规定。因此,对于未遂犯与共同犯罪等其他特殊情形,立法者一般是通过刑法总则对其进行概括式规定②。在刑法分则中规定单独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而在总则中对未遂、共犯等形态加以概括性规定的立法模式是各国刑法的通例,我国刑法同样如此。我国1997年系统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上规定表明,对于预备犯和未遂犯的处罚规定,我国刑法规定得并不十分明确。对于预备犯、未遂犯的处罚,需要与既遂犯的处罚规定相“比照”。即以既遂犯的处罚规定为参照物,在这一基础之上再根据预备犯或者未遂犯的具体情况予以修正。“法条是法规范的载体”③,法学必须尊重规范,紧扣条文④。我国《刑法》对预备犯、未遂犯的规定业已表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其实就是既遂模式。正是基于此,多年以前我国学者就已明确指出:“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都是以犯罪既遂为标准的;在刑法理论中,一般也是以犯罪既遂状态作为研究的标本。”⑤
在对行为犯与结果犯进行研究之时,如果忽略了行为犯与结果犯这一划分是针对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而言的这一讨论基准,就有可能导致理论的混乱。如有学者指出,“依据构成要件,有的不需要有结果产生而仅把行为(身体的活动)当作要素。但大部分的罪行,都要在行为以外产生一定结果,才被认定为构成要件的要素。前者被叫作行动犯或单纯行为犯(例如伪证罪、行政犯的例子很多),后者被叫作结果犯(例如杀人罪)。而结果犯一词,有结果加重犯之意。所谓结果加重犯,即指在一个基本的构成要件成立后,进一步引起一定的严重后果因而加重处罚的犯罪,这种后果是与上述结果不同的”⑥。有学者认为,“以结果在刑法中规定的情况为标准,可以分为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是以单独犯为标准)”⑦。很显然,在这些论述中,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是被当作并列的几种犯罪类型来对待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上述学者所言,结果加重犯这一犯罪类型是在“基本的构成要件成立后”或者“发生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重结果,对该重结果刑法规定更重刑罚的犯罪”⑧。也就是说,结果加重犯并非针对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而言,而是针对基本犯以外的其他派生犯而言的。结果加重犯和结果犯、行为犯其实是处于不同层面上的几种犯罪类型,将其与结果犯、行为犯相并列纯属理论上的错位。
此外,刑法学界也有学者主张将结果加重犯纳入结果犯之中。如有学者认为,“作为结果犯的一种,有结果加重犯”⑨。有学者指出,结果犯中包含结果加重犯。结果加重犯是行为人以基本构成要件的故意,实施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却产生了超出基本构成要件的加重结果,而最终符合加重构成要件的犯罪⑩。从这些论述可知,结果加重犯的研究对象是超出了基本犯的构成要件范畴的,换言之,结果加重犯与结果犯、行为犯所针对的对象是有所区别的。将结果加重犯纳入结果犯之中,事实上就是将结果加重犯的研究对象——派生犯转换成为基本犯,但这与上述学者们对结果加重犯的定义是相矛盾的。而且,在将结果加重犯纳入结果犯范围的情况下,还可能导致对加重结果的忽视,无从突出结果加重犯的加重结果已经超出了基本犯的罪质范围的这一特征[11],结果加重犯的理论意义由此也被削弱。
二、行为犯概念的界定标准
(一)关于行为犯概念界定标准的理论分歧
行为犯概念的界定标准,其实就是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划分标准。关于这一问题,在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既遂标准说与成立标准说之争。
既遂标准说认为,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应当以构成犯罪既遂是否需要犯罪结果为标准。具体而言,这种观点认为,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是行为犯;既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还要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是结果犯。结果犯既遂的标志是法定犯罪结果的发生[12];行为犯的既遂的标志是具体犯罪规定的法定行为的实施,而不要求造成一定物质的、有形的危害结果[13]。
成立标准说主张根据犯罪的成立是否需要发生结果为标准区分结果犯与行为犯。这种观点最早由张明楷教授提出,他认为,发生结果才构成犯罪的是结果犯,如过失致人死亡罪;无需结果发生就可以构成犯罪的是行为犯,如故意杀人罪[14]。黎宏教授也持相同观点。他虽然没有采用“犯罪的成立”或“构成犯罪”等用语,但是,他明确指出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因为根据刑法规定,成立故意杀人罪,并不要求具体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要存在“故意杀人”的行为即可;而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结果犯。由此可见,对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标准,他与张明楷教授观点一致,采用的也是成立标准说[15]。
(二)行为犯概念界定标准之评析
1.对成立标准说之否定
笔者认为,成立标准说存在诸多不足,因而将其作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界定标准并不可取。
一方面,成立标准说中的“犯罪成立”本身并不明确。不可否认,危害结果是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以及少数直接故意犯罪之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志。对这些犯罪而言,犯罪只有成立与不成立之分。特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与否,是判断这些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对于这些犯罪,可以认为,犯罪成立可以作为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确定标准。但是,在大多数直接故意犯罪的场合,犯罪成立的状态则不是唯一的[16]。换言之,“犯罪成立”本身就不具有确定性。因为,不仅犯罪既遂属于犯罪成立,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等几种犯罪未完成形态也都从属于犯罪成立。所以,犯罪成立与犯罪既遂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前文分析表明,对于预备犯、未遂犯等特殊形态的处罚我国刑法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而是要求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只有既遂犯才是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基本模式。所以,犯罪既遂比犯罪未完成形态更为明确,对犯罪既遂的判断比对犯罪成立的判断更为简便。
另一方面,以成立标准说对行为犯与结果犯作界分,可能导致同一犯罪既是行为犯又是结果犯。例如,成立标准说认为,成立故意杀人罪,只要具有“故意杀人”行为就够了,不要求引起具体的危害结果。因此,故意杀人罪是行为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故意杀人罪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在直接故意的情况下,行为人只要实施故意杀人行为,即使没有出现死亡结果,其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对此,依据成立标准说,故意杀人罪属于行为犯没有疑义。但是,当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为间接故意时,犯罪的成立取决于特定危害结果的出现。也就是说,在间接故意的场合,行为人不仅需要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而且只有在死亡结果出现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才构成故意杀人罪。此时,依据成立标准说,故意杀人罪却又属于结果犯。犯罪的分类应当是一个确定的状态,同一种犯罪不可能从属于相互对立的两种类型。显然,以成立标准说作为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界定标准是不合理的。
2.对既遂标准说之质疑
一方面,既遂标准说与犯罪停止形态理论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主张既遂标准说的学者一般认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这些犯罪的停止形态是针对直接故意犯罪而言的,过失犯罪、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这些犯罪停止形态[17]。以此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间接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不存在犯罪既遂形态,因而也就不存在行为犯与结果犯之分。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划分仅仅适用于直接故意犯罪。但是,与上述认识相矛盾的是,这些学者还认为,间接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二者都是结果犯,即以实际发生危害结果作为成立的必备条件”[18]。由此可见既遂标准说亦有不合理之处。
另一方面,既遂标准说将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局限于直接故意犯罪范围之内,降低了行为犯与结果犯这一理论区分的价值。类型分析法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刑法所处罚的犯罪行为,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由于各种类型有其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因此,分析犯罪类型除了有助于概念的厘清之外,也有实际上的区别实益。”[19]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就是我们认识犯罪的方法。通过这一区分,我们可以将众多的犯罪分别纳入其中,突出该种犯罪类型与其他犯罪种类的不同特征,从而更好地认识犯罪。然而,依既遂标准说的观点,行为犯与结果犯这一区分却被局限于直接故意犯罪范围之内,间接故意犯罪与直接故意犯罪被排除在这一区分类型之外,由此导致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
(三)行为犯概念的界定标准之确立
笔者认为,与成立标准说相比,既遂标准说应当说更具合理性。但如前所述,这种学说同样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在这些方面还需予以完善。
一方面,要改变对犯罪既遂存在范围的通行认识。传统观点认为,犯罪的完成形态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犯罪的完成形态一般称为犯罪既遂。由于只有直接故意犯罪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因而犯罪既遂对过失犯罪来说没有存在的余地和意义。间接故意犯罪也不存在犯罪未完成形态,所以同样不存在犯罪的既遂形态。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观点同时认为,犯罪既遂,就是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完全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要素[20]。“犯罪既遂是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态。”[21]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否认间接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也可以具备犯罪的完成状态。因为,任何犯罪都会存在最终停止状态。不论是间接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要最终构成犯罪,都必须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所以,“应当认为凡是完成刑法分则条文对某种犯罪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的,就是既遂”[22]。直接故意犯罪的完成可以称之为犯罪既遂,间接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完成同样可以称之为犯罪既遂。
另一方面,非物质性结果应纳入结果犯之结果的范围之内。传统观点认为,以危害结果的存在形态为标准,可以将危害结果分为物质性结果与非物质性结果。以物质性形态为存在形态的危害结果是物质性结果,物质性结果具有直观性、可测量性;不以物质变化为存在形态的危害结果为非物质性结果,非物质性结果具有抽象性,需要根据一定的社会价值观予以评价[23]。结果犯中的结果只限于物质性的结果,是犯罪行为通过对犯罪对象的作用给犯罪客体造成的物质性、可以具体测量确定的、有形的损害结果[24]。
笔者认为,将结果犯之结果限定为物质性结果是没有必要的,非物质性结果也应纳入结果犯之结果的范围之内。因为,首先,非物质性结果同样是客观的、是可测量的,只不过其测量的方法与物质性结果有所不同而已。对于非物质性结果虽然不能直观感知,但是却可以通过对行为状况、行为时间、行为地点、行为对象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察予以确定。因此,非物质性结果与物质性结果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表现形式更为直观,后者的表现形式更为抽象,但二者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其次,只要认为非物质性结果对定罪量刑有影响,对于非物质性结果就必须认定。一方面承认非物质性结果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对非物质性结果没有必要予以认定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因而,如今一般认为,“物质性结果和非物质性结果都可能属于构成结果,也可能属于非构成结果”[25]。最后需要注意,如前所述,非物质性结果与物质性结果没有本质区别。立法者在某些犯罪中对非物质性结果没有明文规定,其实只是因为这些非物质性结果具有抽象性,难以用简练的语言予以概括,但这并不能否定非物质性结果在构成要件中的地位。对于这类犯罪而言,犯罪既遂仍应以非物质性结果的出现为标志。因此,对于结果犯之结果而言,非物质性结果理应包含其内。
三、行为犯概念与犯罪的本质
关于行为犯的概念,刑法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观点,不仅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行为犯存在各种不同认识,即使是同一国家的学者对行为犯的认识也可谓五花八门。以日本学者对行为犯概念的界定情况为例:第一种观点认为,行为犯是指在构成要件中,只把行为人一定的身体动静作为构成要件性行为的犯罪[26]。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犯是无需法益侵害,甚至连法益侵害的危险也不需具备的犯罪类型[27]。第三种观点认为,举动犯就是单纯行为犯,这种犯罪不要求发生一定的结果,只要具备作为构成要件的行为的人的外部态度即可成立[28]。第四种观点从法益的侵害、危险性角度来理解,认为结果犯与行为犯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时间间隔,存在时间间隔的是结果犯,不存在时间间隔的是行为犯[29]。第五种观点认为,被称为单纯行为犯的犯罪,看上去像是仅有行为就能成立,但其实这些犯罪只是结果与行为同时发生或者几乎同时发生,而其他犯罪则是行为与结果的发生之间存在时间的、场所的隔离而已[30]。
以上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均从形式上指出了行为犯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即行为犯的构成要件中只包括行为要素,而不包括结果要素。就形式概念而言,这两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第二种观点认为,就行为犯而言,连法益侵害的危险都不需要即可成立犯罪。这种观点其实是犯了将行为犯与形式犯相混淆的错误,行为犯应当属于实质犯,因此这种观点所界定的行为犯概念并不合理。第四种和第五种观点基本一致,均认为行为犯的成立在本质上仍然需要产生结果,只是这种结果与行为同时出现,因而没有必要再对结果予以单独强调。但是,这两种观点以是否存在时间间隔,或者以时间间隔的长短来区分行为犯与结果犯,就现实情况而言,可以说,这两种观点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
结合前文所确定的行为犯概念的讨论基准和行为犯概念的界定标准,参鉴日本学者对行为犯概念界定之得失,笔者认为,所谓行为犯,是指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仅包括行为要素,并以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法益侵害的危险性,作为基本犯成立条件的犯罪;所谓结果犯,是指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包含了结果要素,以结果的存在作为基本犯成立条件的犯罪。物质性结果与非物质性结果,实害结果与危险都应包含于“结果”之中。需要说明的是,本概念在界定行为犯之时所采用的事实上是修正的既遂标准说。因为,行为犯是针对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而言的。同时,由于笔者改变了犯罪既遂存在范围的通行认识。笔者认为,不论是直接故意犯罪,还是间接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都存在犯罪既遂形态。所以,笔者所界定的行为犯与结果犯概念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均可适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行为犯与结果犯其实是对犯罪的一种形式分类。笔者之所以在界定行为犯概念时揭示行为犯的处罚根据是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法益侵害的危险性,目的在于澄清学界对行为犯的一些误解,表明行为犯也符合犯罪的本质要求,行为犯应当属于实质犯范畴的这一特征。
作为国家对公民生活和权利的最严厉的介入手段,刑罚的使用应当受到法治原则最为严格的限制[31]。因此,不论是什么犯罪类型,都不能违背犯罪的本质。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对犯罪的本质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有学者从犯罪实质的角度来解释犯罪的本质。该学者指出:关于犯罪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传统上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现在则认为是违法与责任[32]。也有学者从犯罪的侵害对象的角度来理解犯罪的本质,由此而产生了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义务违反说、规范违反说、综合说等不同学说。此外,还有学者试图调和上述两种思路,主张折中说[33]。不过,在经过多年的学术论争之后,应当说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的“法益侵害说”[34]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赞同[35]。可以说,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这一点已经获得了现代刑法学的普遍承认[36]。我国刑法学界一致认为犯罪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危害性,其实,这就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37]。如今,“法益侵害说”在我国也获得了较为一致的认可。“法益侵害说”认为,犯罪的本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法益论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38],其存在价值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39]。因此,立法者只能将有法益侵害或者侵害危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笔者所界定的行为犯概念是否符合这一犯罪本质呢?笔者对此予以肯定回答。
笔者认为,一方面,行为犯的处罚根据是法益侵害的危险。根据“法益侵害说”,立法者之所以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其原因就在于这种行为对社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或者说对法益具有现实的侵害或者有侵害的危险。通常认为,刑法中的危险是一种法益侵害的可能性。在哲学上,可能性是指“具备了实现的充分条件,或不缺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只有充分具备了实现的条件,才是可能的,即只有现实的才是可能的”。可能性“指的是还没有成为现实,但又不排斥成为现实”[40]。因此,虽然可能性意味着现实尚未形成,但是,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已经具备现实产生的条件。而且,危险是“根据现有的具体情况,产生损害被视为极有可能,产生此等损害的可能性近在咫尺”[41]。正是因为“危险距离侵害仅仅一步之遥”[42],所以,立法者认为,虽然这种行为尚未对法益造成现实损害,但这种具有法益侵害危险的行为,也需要以刑法手段予以规制。行为犯虽然尚未造成现实的损害结果,却仍然被立法者作为犯罪处理,原因就在于这种行为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
另一方面,行为犯的危险是行为本身所具备的危险,是一种抽象的危险。有学说认为,根据具体表现形式或者抽象的程度,可以将危险犯分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以具体危险为处罚根据的是具体的危险犯,以抽象危险为处罚根据的是抽象的危险犯。不过,在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的区分标准上,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第一种观点认为,具体危险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判断,抽象危险由于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不需要具体去判断,而且还不允许反证。因而,即使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产生危险,也不会妨碍对抽象危险的认定[43]。第二种观点认为,具体的危险需要司法上具体认定,而抽象的危险则是从立法上推定的[44]。第三种观点认为,具体的危险与抽象的危险的区别在于危险的程度不同。其中,具体的危险是紧迫的、高度的危险;而抽象的危险是缓和的、低度的危险。前者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后者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较小[45]。
笔者认为,以上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是以刑法的已有规定为前提的,论者所采取的是一种司法者视角。这两种观点的产生,是建立在论者对现有刑法规定的分析之上的。其实以上两种观点并不冲突,具体的危险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的,需要司法上的具体认定;而抽象的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并不需要予以具体判断。这同时也决定了对于抽象的危险在实践中不允许反证。因为一旦在实践中允许对于抽象危险反证,就等于将抽象的危险与具体的危险相混同。主张第三种观点的学者采取的是立法者视角。立法者通过对不同程度的危险的比较,将紧迫、高度的危险作为具体危险,而将程度较为缓和、低度的危险作为抽象危险。至于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之间的界限何在,在立法者这里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精确的刻度。就民主立法的情况来看,某一法案的通过往往需要多数意见的支持。“刑法立法因需要而产生,也因需要而运作”[46],当多数民众认为某种危险行为需要用刑法予以规制时,立法者就应对这些意见进行考虑[47]。因此,从立法角度看,具体危险与抽象危险的区分只能取决于多数人的判断。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具体危险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是一种高度的、紧迫的危险;对于具体危险,需要司法上根据具体的情况予以认定。危险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需要以客观条件的存在为前提。由于具体的危险已经是一种紧迫的危险,其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很大。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需要建立在充分的条件之上。由此也就决定了,这种危险在表现形式上已经能够显示为一种外在的事实状态。这种事实状态是一种由行为所造成的法益侵害的可能性,是一种“危险结果”,或者说是“作为结果的危险”。这种“危险结果”已经超出了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属性,演变成了一种可辨识的事实状态。抽象危险是一种缓和的、低度的危险,发生侵害结果的可能性相对而言较小,这种危险是立法上推定的,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抽象的危险是一种缓和的危险,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相对而言较小。与具体危险已经表现为一种法益侵害的事实状态不同,抽象危险还没有和行为相分离,仍然是一种蕴含于行为之内的法益侵害可能性,属于行为本身所具备的危险性。因此,也可以将抽象危险称为“作为行为的危险”。人道主义刑罚理论认为,“刑罚唯一合理的动机是预防他人犯罪,或者矫正犯罪人”[48]。从犯罪或犯罪人影响社会的角度来看,其实也是要求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的危险超过人们的容忍限度。所以,要保持刑罚的人道性,还需注意,虽然抽象的危险是一种缓和的危险,但这种危险依然有侵害法益的可能性,已经逾越了刑法所允许危险存在的程度,因而仍需以刑法对其予以规制。
行为犯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并不包含结果要素。司法者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成立行为犯时,其着眼点在行为本身,即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法益侵害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还没有表现为行为之外的独立状态,所以,行为犯中的危险属于抽象的危险。
四、行为犯概念与结果犯概念之间的关系
行为犯与结果犯之间是什么关系?行为犯与结果犯这一对犯罪类型的区分是否可以包含所有的犯罪?或者说,在行为犯之外,是否其他犯罪均属于结果犯?学者们对于这些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以结果在刑法中规定的情况为标准,可以分为行为犯、结果犯、结果加重犯(是以单独犯为标准)”[49]。第二种观点主张,犯罪既遂可以分为结果犯、行为犯、危险犯、举动犯四种不同类型。也就是说,这四种犯罪之间是并列关系,在结果犯与行为犯这种区分之外,还同时存在危险犯和举动犯[50]。第三种观点认为,犯罪既遂可以分为结果犯、行为犯和危险犯这三种类型[51]。第四种观点则认为,在行为犯、危险犯、结果犯这几种类型之外,还需加上阴谋犯[52]。
笔者在前文已经对第一种观点做过分析。行为犯与结果犯是针对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基本犯而言的,结果加重犯已经超出了基本犯的范畴,是针对派生犯来说的。因此,结果加重犯既不应与行为犯、结果犯相并列,也不属于结果犯之下的犯罪类型。对于另外三种观点,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危险犯、实害犯不应当与行为犯、结果犯相并列。因为,危险犯与实害犯是以其处罚根据的不同为标准所作的区分,而行为犯与结果犯是以构成要件要素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所作的区分。不同区分标准下所作的分类,当然不能并列。其实,危险犯与实害犯是对结果犯的进一步划分,其区分标准是危害结果的不同表现形态。这就类似于对于结果犯而言,根据结果的具体表现形态,将其又区分为物质性结果犯与非物质性结果犯一样。其实这两种区分都只是在结果犯之下所展开的进一步分类。其次,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学中,行为犯和举动犯是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的[53]。因此,在这一语境之中,不应将行为犯与举动犯相并列。对于行为犯和举动犯的关系,我国刑法学界则存在不同认识,综而言之,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并行关系说、种属关系说,以及同一关系说[54]。并行关系说认为,行为犯与举动犯是有所不同的,二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一经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完成,并完全符合构成要件,成立犯罪既遂的是举动犯;而在着手实施犯罪实行行为之后,还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并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视为行为完成,构成犯罪既遂的是行为犯。简言之,举动犯的完成无需发展过程,行为犯的完成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应当认识到,其实不论是何种犯罪,从行为的着手实施到行为实施完成都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一过程的完成所需要的时间有长短之别。由此看来,行为犯与举动犯其实仅仅是在这一发展过程的时间长度上有所区别。如果一定要进行区分,举动犯不应当与行为犯相并列,而应属于行为犯这一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标准是犯罪的客观要素中是否存在结果要素;而对于行为犯与举动犯的划分,所采用的标准却是实行行为的着手与犯罪的完成之间时间间隔的长短。显然,在对以上两组犯罪类型进行区分之时,采用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对事物进行同一次分类只能运用同一个标准,将行为犯、结果犯、举动犯相并列是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的。最后,所谓阴谋犯,是指立法者基于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在刑法分则中设置的只需实施自然事实意义上的预备行为就应给予既遂否定评价的构成要件类型[55]。就此看来,刑法对于阴谋犯的规定,实际上是将某种具有特殊侵害性的预备行为提升为犯罪实行行为,其立法目的是实现对法益的提前保护。因此,在阴谋犯的场合,当然不能等到法益侵害结果出现刑事措施才予以启动。也就是说,立法者不可能将危害结果作为阴谋犯的构成要件要素。就这一点而言,阴谋犯也应该隶属于行为犯。
总之,不论是危险犯,还是举动犯、阴谋犯,将其与行为犯、结果犯相并列都是存在问题的。以上关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关系,或者说对犯罪既遂形态所作的犯罪类型区分的各种观点,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均存在一些误解和不足。因而笔者认为,只要采用行为犯与结果犯这一区分,就可以涵盖基本犯的所有类型,二者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择一关系或者对立关系。由于行为犯与结果犯是针对犯罪既遂的基本犯而言的,因此,二者又统一于犯罪既遂形态之中,共同构成了犯罪既遂形态的全部内容。
注释:
①许永生:《刑法解释的限度到底是什么——由一个司法解释引发的思考》,《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②[27][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③聂慧萍:《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纠缠与厘清》,《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
④孙笑侠:《法律思维方法的“器”与治国理政的“道”》,《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⑤杨春洗、杨敦先:《刑法讲义》,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
⑥[日]福田平、大塚仁:《日本刑法总论讲义》,李乔、文石、周世铮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页。
⑦⑧[23][49]林亚刚:《刑法学教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5、151—152、155页。
⑨[34]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93页。
⑩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册)(增订10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11]王志祥:《犯罪既遂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12] [17] [20] [21] [24] [25] [50] 高 铭 暄 、马 克 昌 :《刑 法 学》(第 5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44、147、146、148、75、147—149页。
[13]于志刚、孙万怀、梅传强:《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6页。
[14][37]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273页。
[15]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16]王志祥、袁宏山:《成立犯罪最低标准意义上的犯罪构成理论之批判》,《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
[18]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19]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22][35][52]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334页。
[26][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103页。
[28][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9][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30][日]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31]王云海:《日本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相互关系》,《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4期。
[32][日]林干人:《刑法总论》(第2卷),东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6页。
[33]陈家林:《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9页。
[36]邹兵建:《论刑法公共安全的多元性》,《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2期。
[38]杨萌:《德国刑法中法益概念的内涵及其评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9]胡莎:《法益批判论——以犯罪未完成形态基本理论为突破口》,《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
[40]刘永富:《哲学概论(纲要)》,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41][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42][德]约克·艾斯勒:《抽象危险犯的基础和边界》,蔡桂生译,《刑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33页。
[43][45]张明楷:《危险犯初探》,马俊驹:《清华法律评论》(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页。
[44]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46]马荣春:《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3期。
[47]包涵:《刑法解释界限与行为犯罪化的矛盾与消解》,《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5期。
[48][英]C.S.路易斯:《论人道主义刑罚理论》,罗翔译,《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
[51]苏惠渔:《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53]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页。
[54][55]郑飞:《行为犯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