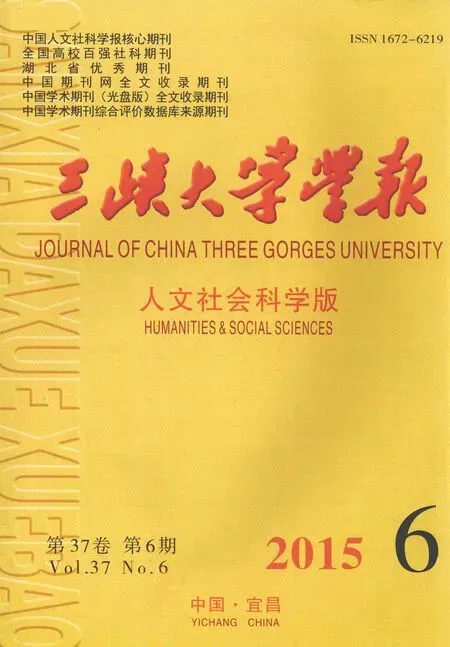也论《屈原列传》疑案(中)——《屈原列传》研究论争述论
刘凤泉,孙爱玲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广东潮州 521041)
四、窜入说存在软肋
在解决《屈原列传》矛盾的观点之中,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一文提出的“窜入说”,影响最为广泛,且为许多学者认可,如聂石樵《屈原论稿》便采纳了汤氏的观点[1]31。董运庭先生认为,汤先生的研究结论,“仍是最有见地和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从总体理清了前人所列出的疑点,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已经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2]34。然而,也有学者对汤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窜入说的软肋所在。
汤氏回顾写作因由说:“太炎先生《訄书·徵七略》有云:‘《御览》引刘氏书,或云”刘向别传“,或云”七略别传“。今观诸子叙录,皆撮举爵里事状,其体与老、韩、孟、荀,儒林诸传相类。盖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太史公尝直举其文,以传屈原,在古有征。而晚近为学案者,往往效之,兼得传称,有以也。’先生又自注云:‘班孟坚《离骚传》引淮南《离骚传》文,与《屈原列传》正同。知斯传非太史自纂也。’先生之意盖谓《史记·屈原列传》全文,皆非史迁‘自纂’,乃取刘安《离骚传》为之,无所增损。……当然,《屈原列传》中的刘安语,无论如传统解释为史迁的引文摘句,或解释为《屈原列传》全文皆为刘安之《离骚传》,皆无法说明《屈原列传》前后叙事矛盾龃龉这一客观存在的重大问题。我之《〈屈原列传〉理惑》正为此而作。”[3]41-42
《〈屈原列传〉理惑》,表达汤氏对今本《屈原列传》的看法。他说,《屈原列传》前后矛盾,首尾错乱,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一是《离骚》之作,究在怀王之世,抑在襄王之时?二是怀王之世,屈原究竟是被疏,抑或已被放流?三是子兰之怒,究竟是怒屈子赋《骚》,抑是怒屈子之“既嫉”子兰?四是“《离骚》者,犹离忧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与“虽放流……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紧密相承,为什么插入“屈平既绌……屈平既嫉之”历叙数十年秦楚兴兵的一大段,致前后互不相蒙?五是何以屈原、屈平交互错出,称谓混乱?[4]11-12这些是他总括前人意见提出的《屈原列传》矛盾问题。
首先,汤氏认为,司马迁没有见过《离骚传》。《屈原列传》矛盾问题是后人窜入刘安《离骚传》而造成的。《屈原列传》中有刘安《离骚传》之语,班固、刘勰皆有论及,然历来认为这是太史公引用刘安语。而汤氏断定那是后人的窜入,他提出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他说:“刘安《离骚传》之写成,虽略早于《史记》,而史迁实未得见。”[4]14既然司马迁没有见过《离骚传》,自然也就谈不上引用它,而今本《屈原列传》有刘安语,说它为后人窜入也言之成理。所谓司马迁未见过《离骚传》,究竟有何证据?汤氏提出两条证据:
一是《史记》没有一字提及刘安的著作。他说:“史迁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只云:‘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叛逆,未有因也。’而关于淮南王所著书与辞赋,则一字未及。”又说:“考史迁书例,凡前人著述,或叙其书目篇卷,或录其作品原文,或具体,或概括,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而著述宏富如刘安者,竟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一字未提,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刘安的《离骚传》等,史迁并未见过。”[4]15
二是武帝因爱秘而未公开《离骚传》。他说:“(《汉书·淮南王传》)始增补下列一段:‘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革及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而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食时上。’高诱《淮南子叙目》亦云:‘初,安为辩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又说:“史迁当时之所以未见淮南王所著书及《离骚传》等,盖当时这些书,虽已献之武帝,而未宣布于世。故史迁并未得见,当然更无从著录于本传,更无从采入《屈原列传》。淮南王书当时之所以未布于世,推其原因,盖不外其始武帝”爱秘“之,故未予宣布。”[4]15,16
对于这些证据,熊任望先生提出了质疑。他说:“所谓武帝‘爱秘’《离骚传》,是高诱《淮南子叙》中的错误说法。(高《叙》甚至误武帝为文帝,《离骚传》为《离骚赋》)《汉书·淮南王传》写得明明白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武帝爱秘的是《内篇》,而不是《离骚传》。……《离骚传》是对《离骚》的注释,‘爱’是可能的,‘秘’则毫无必要。刘安‘旦受诏,日食时上’,可见《离骚传》早已完成。在武帝看到它之前或之后,都有可能流传于世。……多方搜集材料为刘安立传的司马迁,对刘安所领导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不能毫无所闻、所见——纵使未覩其书,也当耳受其事。如有所闻见,而在传中一字未及,必有其他原因。这种情况,在《史记》列传中并非仅见。”[5]11-12
这其他的原因,连赞同汤氏的廖化津,后来也竟作出重要补证。他说:“《史记·淮南王传》对刘安《离骚传》‘一字未提’,有特殊原因。刘安是武帝的叛逆者,而司马迁又得罪过武帝,为刘安立传,必然有许多顾忌。因此《淮南王传》只写其‘为叛逆事’,其他情事一概未记,不提作《离骚传》不足为怪。”[6]23这便以如山铁证,瓦解了窜入说的立论基础。
其次,汤氏认为,《屈原列传》两段议论都是窜入的刘安《离骚传》。《屈原列传》对《离骚》评论肯定为刘安《离骚传》文字的,历来认为只有班固《离骚序》引用的那几句。而汤氏则认为,“由‘《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段文字,都是后人割取《离骚传》语窜入本传者”[4]17。他为此提出两条理由。
一是,《屈原列传》两段文字是刘安《离骚传》总叙。他说,刘安《离骚传》包括总叙和注文两部分,班固称刘安以为“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胥也。及至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有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此指注文,故王逸称“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班固引‘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此指总叙。而今本《屈原列传》窜入者,乃是刘安《离骚传》的总叙”[4]18。他通过将《屈原列传》两段文字与班固《离骚序》、王逸《离骚经章句序》进行比较,从而推论出的刘安《离骚传》的原型。汤氏认为,“它们虽论点不尽相同,而其结构层次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也许是班、王袭用了刘氏旧例的原因。”[4]18
二是,前段文字是刘安《离骚传》前半部,后段文字是刘安《离骚传》后半部。前半后半不仅文笔风格完全一致,而且结构层次也脉络相通。两段合起来,犹可以看到接近完整的《离骚传》的梗概[4]19。
对于汤氏的理由,熊任望也提出了质疑。熊氏认为:一是从文章体例看,总叙主要是评介作者和作品。与作者有关的人和事有所选择,而无须另加评论,以免枝蔓。他也将《屈原列传》两段文字与班序、王序作了比较。结果发现班序、王序合乎总叙要求,而《屈原列传》包含非总叙所该有的内容,如“大段抨击怀王的文字,无论从性质,还是从数量说,都是刘安《离骚传》的总叙所不可能有的”[5]11。二是刘安奉武帝召作《离骚传》,而《屈原列传》两段议论多有激愤之语,如“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王之不明,岂足福哉”等,这种言论根本不符合刘安朝王的身份,以及武帝对其著作“爱而秘之”的情境[5]9。可见,汤氏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张叶芦也不同意汤氏的观点,他具体分析了两段议论与叙事的密切关系,指出:“这两段议论相互之间,以及其各自跟前面叙事之间都有紧密联系,使全文结合为一个整体,这显然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才能做到的”;“如果说这两段议论是他人文章‘羼入’,竟与叙事部分扣得如此紧密,真正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那简直不可思议,更不用说其抒情切合司马迁个人身世之感了。”[7]148,149所以,从文理而言,两段议论也不可能为后人窜入刘安《离骚传》。
笔者以为,《屈原列传》两段既不是刘安《离骚传》原型,而所谓“前半后半不仅文笔风格完全一致,而且结构层次也脉络相通”也照样可以理解,因为它们都是司马迁精心结构的结果。如果剔去了两段议论,反倒如佛顶剥去金光,而令《屈原列传》黯然失色了!
再次,汤氏认为,传内评论与传末赞语存在矛盾。他说:“但考之本传赞语,史迁对屈原所作的评价,其主要论点却跟传内所引刘安语完全相反。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刘安的两段话,决不是史迁引用的,而是后人窜人的。”[4]27汤氏揭橥出观点矛盾有二:一是传内肯定屈原“死而不容自疏”、“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而传末赞语又同意贾谊“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既赞他不离开楚国,又怪他不离开楚国。这样矛盾的观点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二是“同生死,轻去就”,与传内窜入的刘安观点不同。以传末赞语衡量,两段议论决不是史迁原文,而是后人所窜入的[4]28-30。
熊任望对此作了细致辨析,否定汤氏所谓矛盾的问题。他先从语言角度辨析,指出“死而不容自疏”有不同的断句,杨树达云:“通读以‘不容自疏’为句。黄侃以‘自疏’二字属下读,是也。《汉书·扬雄传》云:‘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王逸《章句序注》引班固《离骚序》云:‘愤懟不容,沉江而死’,皆本此文,是其证矣。”所谓“自疏濯淖污泥之中”,意为自远于污浊社会,并不涉及屈原离开楚国的问题[5]13。至于,“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说的是屈原的情感,并不涉及作者的评价,而“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之后,接着指斥怀王的愚妄,正表达了对屈原的惋惜。这与传末赞语“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根本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5]14
笔者以为,传内与传末尽管表述不同,但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太史公“悲其志”、“未尝不垂涕”正是对屈原不幸遭遇的同情,因而“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他认同贾谊看法并不难理解。至于“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这与传内评述也不存在矛盾。“同死生,轻去就”,本是贾谊的观点,司马迁读了《服鸟赋》后,受到强烈的思想冲击而“爽然自失”,正说明了他原来的观点并不如此,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同生死,轻去就”与所谓刘安的观点相矛盾的问题。
此外,关于《屈原列传》中“屈原”、“屈平”两种称谓交互出现的问题,也不能成为窜入说的充分理由。《史记》传主多种称谓亦非《屈原列传》仅见,褚斌杰认为:“《屈原传》已清楚指出‘屈原名平’,绝无怀疑为两人之可能。《屈原列传》‘平’、‘原’互见,或为史迁行文如此,或为流传中传抄问题,今已难确考,然终无碍对《屈原列传》之理解。”[8]8至于,言“后人窜入”,这后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窜入刘安《离骚传》?这些问题,汤氏都没有作答。当然,本来不存在窜入的问题,也就无须回答了。
综上所述,窜入说立论基础不实,成为它的致命软肋。诚如褚斌杰所言:“窜入说似是能快刀斩乱麻,但终嫌尚缺少根据。”[8]58所以,虽然“窜入说”影响颇广,其实它并不能成立。
当然,不能因此而否认汤氏对《屈原列传》研究的贡献。譬如,对于屈原赋《骚》的年代问题,他解决了《屈原列传》与司马迁其他处表述矛盾的问题。《屈原列传》云:“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言屈原被疏之后而作《离骚》。而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则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9]2735;《太史公自序》亦云:“屈原放逐,著《离骚》”[10]3300。又皆言屈原被放逐之后而作《离骚》。刘永济说:“史迁一人亦有两说,理不可通。”[11]200对此,汤氏以传记文与抒情文行文措辞不同来进行解释。他说:“抒情体的《报任少卿书》,则以其发泄其愤懑之情为主”;“盖史迁因情之所激,奋笔直书,致与传记体的列传有所出入。”又举“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亦皆不符合本传史实。因此,“‘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传其事。”[4]24,25这就解决了所谓司马迁一人两说矛盾的问题。
五、拼凑论不合常情
与错简说、窜入说的视角不同,也有学者将《屈原列传》矛盾的责任归咎于司马迁,认为《屈原列传》的矛盾问题,是由于司马迁写作不严谨造成的。此可谓之拼凑论。
孙作云先生《读〈史记·屈原列传〉》便持这样的看法。他说:“《史记·屈原列传》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第一篇自开头以至‘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止,是讲《离骚》撰写经过及其内容大意的文章,我在下文中将证明:此即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如班固、王逸之《离骚经章句序》同;其次是《渔父篇》(不知何人所作,非屈原作。旧说为屈原作,误)——用这篇妙文代表屈原被放逐以后的生活,主要的是发挥屈原刚强不屈的思想;其三是屈原的绝命词《怀沙》,用《怀沙》来表现屈原宁死不屈的精神,并以此结束屈原一生的行事。在这三篇文章之间,司马迁仅仅添了十几句连缀的话,用以连系上下不同之三文。如在第一讲《离骚》大段之文及《渔父篇》中间,添上以下几句话:‘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以下便引《渔父篇》正文。在《渔父篇》之后,《怀沙》之前,添上一句:‘乃作《怀沙》之赋。’在《怀沙》赋后,又添上一句:‘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12]25
按照孙氏的看法,司马迁只是将他人文章拿来,用了不到五十个字连缀几下,随便拼凑而成为《屈原列传》。这种看法显然存在毛病,拼凑他人的文章而为纪传,恐怕不符合太史公的一贯作风。司马迁隐忍苟活写作《史记》,“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要将《史记》“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怎么竟会如此草率地杂凑成篇呢?加之屈原是感动过他的人物,他曾咀嚼屈原作品,瞻仰屈原遗址,悲悼屈原志向,怎么竟会如此随便为屈原立传呢?
《屈原列传》引《渔父》、《怀沙》,因为那是屈原的作品,引用传主作品是《史记》纪传的通例,这自然勿须多议。而孙氏以为,《屈原列传》从开头到“岂足福哉”,全是刘安《离骚经章句序》,则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孙氏的理由有三:一是从开头到“岂足福哉”止,是单独的一篇文章,“全是以《离骚》为中心,——讲述《离骚》撰写经过及其内容、大意的文章”[12]24。二是“古人作文往往在文末引《诗经》、《易经》语作结束”,《屈原列传》有“《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由此亦可见在‘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以前,确为一篇独立文字。”他特别举证曰:“孟、荀之文即多有之。《淮南子》中亦多其例:如《傲真篇》、《修务篇》就引用《诗经》作结;《缪称篇》一篇就曾六引《易经》,三引《诗经》。”[12]24三是“从与班固、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的对比上,也可以推知,因为它们是同类文章,而且说不定这两位后辈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就是学习或节略他们的老前辈刘安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的”。“由此亦可见刘安《离骚经章句序》名虽佚而实未佚,它完好地保存在《史记·屈原列传》里。”[12]26,27
其实,这些理由并不能证明这部分就是刘安《离骚经章句序》。
首先,司马迁以《离骚》为屈原代表作,他读屈作先标《离骚》,且又言为屈原作传由来曰:“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以《离骚》为重点给屈原作传,自是题中之义。况且,从开始至“王怒而疏屈平”,从“屈原既绌”至“怀王入秦而不返也”,都是叙述屈原的生平事迹。说它“像是一篇解释《离骚》的文章,而不像一篇以屈原一生事迹为中心的传记”[12]23,显然并不符合文本实际。
其次,荀子文章有引《诗经》语以曲终奏雅者,《缪称篇》引有《易经》、《诗经》语,但并不都在文章的末尾。由此推断出引用《易经》语,便标志着文章结束,这种推理起码是不周延的。
再次,通过与班固、王逸《离骚经章句序》对比,认为它们“内容相同,主题相同,所以在结构上,甚至在文辞上也这样地相同,从这三文的对比中,更可以相信:《史记·屈原传》原本为刘安《离骚经章句序》。”[12]27孙氏的假设实在够得上大胆,却始终没有拿出真凭实据,充其量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其结论自然难以让人信服。孙氏的假设也启发了汤炳正。后来汤氏以《屈原列传》与班固、王逸对比,以证成《屈原列传》窜入《离骚传》的观点。关于汤氏的推论,前面已有辨析,可以相互参看。
对司马迁《屈原列传》不满意的,还有谭介甫先生。在《屈赋新编》中,谭氏多处文字非难司马迁,嫌《屈原列传》“太简”、“混乱”、“不易解”云云[13]39。于是,他从对屈作“各篇研究中认识出怀、襄二代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和其他关节”,竟以所谓“文史合一”的方法重新编撰了一万多字的屈原生平[13]。然而,谭氏写的屈原生平显然不能与司马迁《屈原列传》相提并论?何其芳指出:“屈原是中国第一个伟大诗人,然而由于他生在二千多年以前,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材料保存至今的却很少。如果我们要给他作一个传记,几乎说越简单就可靠性越大。越详细就难免推测之词就多。”[14]219所以,轻易责难司马迁,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汤氏窜入说被质疑之后,便不能再回避窜入说的软肋了。廖化津先生的《〈屈原列传〉解惑》一文,坦率承认司马迁见过《离骚传》,从而抛弃了汤氏所举未见的证据。然而,廖氏又提出:《屈原列传》插入《离骚传》,不是后人好事者的窜入,而是司马迁自己插入的[6]22-23。这就将问题又归因于司马迁,从而与拼凑论的观点接近了起来。
廖氏认为,“《屈原列传》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有初稿和定稿的分别。《屈原列传》的初稿,本来没有对《离骚》进行评述”[6]21。他的证据是:“《屈原列传》末尾‘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屈原列传》中记录了《怀沙》的全文,‘太史公曰’中却未提及《怀沙》。……为什么《怀沙》不在‘余读’之列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体例写法的关系。……以《怀沙》例推之,《离骚》如果在传文中已经评述,结语中就不会再提及《离骚》。……结语中首列《离骚》,则《离骚》也当是传文中未曾提及的。由此可见,《屈原列传》的初稿,本来没有关于评述《离骚》的内容。”[6]21
这个推论太过于轻率了,同一篇《屈原贾生列传》便有反例存在。其云:“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而“太史公曰”:“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5]2496,2503显然,《史记》并不存在所谓结语提及的,传文就不会评述的体例写法。假如真有这样的体例写法,为什么在所谓定稿中,司马迁倒违背这种体例写法呢?
《太史公自序》作于《史记》完成之后,其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列传》。”廖氏认为:“作辞”,即指作《离骚》,因为下文所说“讽谏”、“连类争义”是“《离骚》有之”的。“讽谏”,指《屈原列传》中《离骚传》语“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连类以争义”,指《屈原列传》中《离骚传》语“举类迩而见义远”。《太史公自序》已经提到《屈原列传》中《离骚传》的词语、意思。说明《屈原列传》的定稿已有了关于《离骚》的评述,证明将《离骚传》插入《屈原列传》当作对《离骚》的评述的人,是司马迁自己[6]23。
笔者则以为,《自序》对《离骚》的评论,表现了司马迁对《离骚》的深刻理解,而不能证明所谓定稿中已经插入《离骚传》。司马迁不会低能到只有插入了别人的意见,才能发一些附和的言论。《屈原列传》对《离骚》的评述,乃是司马迁自己的意见,当然是在吸收前人认识基础上,他对《离骚》意蕴的深刻理解。
此外,廖氏认为:“《屈原列传》初稿,叙述清楚,层次分明”,而所谓定稿插入了《离骚传》导致“叙事错乱”。而“要解决关于《离骚》作时的争端,只有将《离骚》的定稿还原为初稿,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将《屈原列传》的定稿还原为初稿,即把《离骚传》语从《屈原列传》中抽出来,使它们不纠缠在一起,恢复它们各自的本来面貌。这样,《离骚》的作时问题,在《屈原列传》中就不存在了。”[6]25
本来“叙述清楚”的初稿,到了定稿反而“叙事错乱”了。这样认识问题,显然不合乎正常逻辑,好像太史公不仅低能,而且简直老糊涂了。
笔者以为,拿不出切实有力的证据,而将《屈原列传》矛盾归咎于司马迁,这是很不慎重的态度。作为“史家之祖”的司马迁,竟然会随意拼凑,草率成篇,愈改愈乱,矛盾纠缠,这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六、维护说趋近真相
与各种疑古论调不同,亦有尊重《屈原列传》的学者,他们据理力争维护司马迁的著作权。林庚先生指出:“屈原是中国最早的一位大诗人,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是中国最早的一篇诗人传记,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篇传记。一则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家,《史记》是一部庄严的有科学性的历史著作。二则司马迁距离屈原不到二百年,我们现在距离屈原已经两千二百多年了,我们在两千多年之下所以还有可能比较清楚的知道屈原的生平,老实说,首先就是靠这篇传记,何况这两千多年来我们并没有发现比《史记》更早更可信的有关屈原的资料,那么这一篇传记应当怎样的被我们珍重尊敬才是。”[16]40林氏的态度无疑是对待《屈原列传》的正确态度。
不少学者秉持了这样的态度,如郭沫若、熊任望、张叶芦、褚斌杰等人。熊任望先生致力探讨不删不改如何能够读通《屈原列传》原文。他认为:《屈原列传》“所叙屈原政治生涯的大脉络还是清晰的”。而“感到不足的是,‘放流’问题未作明确交待;关于《离骚》的创作时间,因分在两处叙评,容易引起误解;子兰因何发怒,因在‘屈平既嫉之’下叙评作《骚》一事,不易看出与子兰的直接关系。”[5]1,2他肯定《屈原列传》,又指出不足,所言实事求是。如果能够合理解释上述所谓不足,《屈原列传》的矛盾就会焕然冰释了。
首先,“放流”的问题。熊任望认为:“‘放流’,指的是屈原在怀王时的遭遇,跟后来顷襄王时的‘迁’不是一回事。”[5]5他说:“据屈原作品《抽思》等篇得知,屈原曾被放于汉北,可与本传所说‘虽放流’相印证。”[5]4所以,“本传所说的‘放流’,或许也指屈原当时的这种处境”[5]2。他对“放流”的理解,倾向于在怀王朝屈原被放汉北;而对此又有些游移不定,故用“可能”、“或许”来表述。熊氏没有能够弥合“放流”造成的矛盾,于是只好说:“可能是,本传所叙在细节上有疏漏。”[5]2
褚斌杰先生认为:“‘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大段,主要写的是怀王时事。此处用‘虽放流’,似乎说明屈原在怀王朝曾流放过,这与《屈原列传》上文在怀王入秦不返以前只是‘疏屈平’,‘屈平既绌’、‘屈平既疏’的记述不符。”[8]56既然两者不符,那么何者正确?褚氏分析说:“这时,顷襄王虽已立,但怀王囚居于秦,尚未死。屈原此时的情况,应仍属《屈原列传》前文所言是‘既疏’、‘既绌’、‘不复在位’。《屈原列传》紧接下文在评论怀王时:‘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说的仍只是‘疏’。屈原在楚怀王朝的事实如此,正不宜因此处的‘放流’一词,而无视多处的提法。”[8]61褚氏强调多处的提法,而回避了“放流”问题,这虽表明了论者的看法,而《屈原列传》矛盾依然存在。
郭沫若先生是最早直面“放流”问题的。他说:“‘放流’两个字当作流谪解,是后来的人讲错了的。其实‘放流’就等于‘放浪’,并不是说屈原在楚怀王朝时就遇到流刑。”[17]331又说:“向来把‘放流’二字即解为放逐,因此便生出许多龃龉。其实,‘放流’只是放浪,屈原被疏之后居于闲位,曾向四处游历过而已。”[17]18因此,他认为屈原在怀王朝只是见疏,而未被放逐。郭氏的解释缺乏词义依据,不免有信口开河之嫌。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说,他“不以辞害志”的理解,独具慧眼而予人启迪。
张叶芦先生便赞同郭说,且努力弥补郭氏所缺乏的词义证据。他说:“《屈原列传》‘放流’的‘流’意同《管子·宙合)‘君失音则风律必流’的‘流’,尹知章注‘流,荡放也。’《礼记·乐记)‘乐甚则流’、‘酒之流生祸’的两个‘流’字,均为‘荡放’义。亦同《孟子·梁惠王上》‘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的‘流’(指第二个‘流’字)字,即赵歧注所释的‘放游’义。《荀子·劝学》用‘流鱼’,屈原《离骚》和《远游》并用有‘周流’,‘流鱼’即‘游鱼’,‘周流’即‘周游’。然则‘放流’犹言‘放荡’,亦犹言‘放游’,即郭氏所说的‘放浪’也。”经过一番辗转的训诂,“本传意思便一致而没有龃龉了”[7]156。
“放流”一词并不冷僻,典籍多有运用,如《礼记·大学》云:“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18]225王充《论衡·恢国》云:“(驩兜、共工、三苗、鲧)罪皆在身,不加于上,唐、虞放流,死于不毛。”[19]303唐甄《潜书·善游》云:“诛戮直臣,放流贤士,乾坤晦塞,君臣昏迷,虽有善道者,亦无所施其术矣。”[20]150这里,“放流”的本义就是“流放”、“放逐”[21]414。张氏于“放流”本义弃之不顾,不惜辗转为训,这样解释显然有违“放流”本义,实际运用语言当不会如此。所以,笔者认为,尽管各位做了努力,而“放流”问题尚未解决。
其次,《屈原列传》两段议论的问题。《屈原列传》的两段议论,前段从“《离骚》者,离忧也”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段从“屈平既嫉之,虽放流”至“岂足福哉”。错简说、窜入说、拼凑说等均对之质疑,而维护说则极力肯定它的原貌。
针对所谓“文气不畅”、“自相违戾”、“不合文律”的批评,陈子展云:“太史公之文,雄奇酣恣,反复终始,不知端倪,数数如此,非必时有首尾横绝,不相照应之失。”又云:“言楚人已咎子兰,屈原也旋复嫉子兰也。下文突用虽字作开拓连词,似与上文不接。晴天霹雳,惊奇之至,自‘虽放流’以下,暗用追溯法。”又云:“此遥接法”等等[22]10,9,11。他将文理失次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修辞手法。
张叶芦则以行文布局来解释,他引用《古文观止》注家对《屈原列传》的评注,如“屈平既绌”后注曰:“间接,又如叙事”;“令尹子兰闻之”后注曰:“接上‘屈平既嫉之’,妙!”[7]147别小觑三家村先生的眼光,其实他们的理解很有道理。在这些认识基础上,张氏以破折号来标识《屈原列传》两段议论的结构特点。即:“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平既绌,……屈平既嫉之。——虽放流……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顷襄王怒而迁之。”[7]146这样别出心裁的作法,确实可以消除许多误解。因此,他说:“《屈原列传》这两段议论,或为前面叙事所感触而引起,或在议论中紧扣前段叙事;同时后段议论跟前段议论亦遥相呼应。议论与叙事,议论与议论,其间都有严密联系,从而使文章结构成有机整体。”[7]147然而,古人既不用破折号,这种以今律古的解释恐怕也不完善。
两段议论存在着问题,而褚斌杰仍然说:“我的意见还是俯就《屈原列传》此处原文,做些必要的分析,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解决。”[8]58对于前段议论,他认为“除掉刘安窜入的几句话外(笔者按:指传统认为太史公引刘安的几句话),其思想观点与司马迁全传中所表述的对屈原的看法是一致的,行文上也是衔接的。”[8]39对于后段议论,他认为“《屈原列传》中此段文字,是最为难解的”[8]57。特别对“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他的看法是:“长久以来,这里的‘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被理解为指《离骚》。实际上关于《离骚》的创作时期,背景和内容等等,在《屈原列传》上文早巳写得很清楚了,绝不应在这里蛇足。那么这里所指的作品应是什么呢?我推断,或正是‘太史公曰’中所举的四篇作品之一《招魂》。”[8]59
褚氏的看法之外,也还有其他的看法。如林庚认为指《哀郢》[16]56,也有人认为指《抽思》[23]623,陈子展则认为统指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举的几篇”[22]722。张叶芦对这些认识均作了澄清。他引《古文观止》注家评语“忽又转到《离骚》上”,认为此处“文思极为严密[7]150。前文未出现《哀郢》或《抽思》,怎么突然冒出‘一篇’之称指的是《哀郢》或《抽思》?有这种没头没脑、来路不明的文章思路吗?”[7]150至于“一篇”指《招魂》,或统指几篇,张氏认为,它们“都是说不通的”[7]151。
与张氏的看法一致,熊氏也认为,“一篇”乃指《离骚》。他说:“两处分叙,可以较好地照顾到创作动机和定稿时间两个方面。如集中在前面写,读者将误以为《离骚》作于被疏之初,与实际情况不符;如集中在后面写,又要重复说明根由,行文不便,还有结构上畸轻畸重的毛病。”[5]3这样来理解,《离骚》的作时似乎也逐渐清晰。熊氏结论是:“据本传定《离骚》完成并发表于怀王入秦之后。”这与“老冉冉其将至”、“及年岁之未晏”等《离骚》内证也颇相符合[5]4。
褚斌杰认为:“关于《离骚》是创作于早期怀王之世还是后期襄王之世,一般还是要从《离骚》本文来取证。”[8]29而“就《离骚》全文来看,所谓‘延伫乎吾将反’,‘退将复修吾初服’,‘吾将上下而求索’,‘吾将远逝以自疏’,以及就重华陈词,向灵氛问卜,向巫咸求出路等等,都表现了他在进退去留问题上极为复杂的心情,最后眷恋祖国而不忍去,均较为符合被疏失位时的心情,而与其后期更遭不幸,被放迁时情事不合。”[8]34这些意见使《离骚》作时问题愈来愈接近于最终的解决。
再次,子兰因何发怒的问题。熊任望回答的很干脆:“一是‘屈平既嫉之’;二是《离骚》中有明显影射子兰之处(本传未指出)。本传所叙‘令尹子兰闻之大怒’,紧承二事之后,当兼指二者。”[5]6
张叶芦与熊氏观点只有部分一致。张氏的看法是:“‘闻之’的‘之’字显然是指代‘屈平既嫉之’……‘屈平既嫉之’的‘之’字,是指代其上句‘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7]152。张氏不同意“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是由于《离骚》,认为《离骚》作于“王怒而疏屈平”之后,而距离“子兰闻之”已过去了十余年,难道《离骚》写成藏于名山,十余年后才传之人间?[7]151-152
张氏认为,这种错误观点是对《离骚》原文的产生了误解。朱熹云:“使其果然(按:指‘兰’为令尹子兰,‘椒’为大夫子椒),则又当有子车、子离、子榝之俦,盖不知其几人矣。”[24]175他反对将兰、椒坐实为具体个人。而清人陈本礼则云:“兰、芷、椒、榝,皆实有所指,子兰闻之,所以怒也。”[25]10127近代以来,主张坐实《离骚》花草的不乏其人,如所谓《离骚》对子兰的“千古奇骂”,又如谭介甫草派与木派党争之说[13]37,真是愈辩而愈玄了。对于这些荒诞无稽的说法,张氏的辩驳无疑有醒脑作用。
对待这个问题,褚斌杰颇为重视。他说:“‘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里所说的‘闻之’是指什么?是指读了《离骚》,抑或是指其他?”[8]56他的看法是:“文中所谓‘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这里的‘反(返)’,正应该是指欲怀王返归楚国说的,又说‘反复之’,正是就返归楚国就其君位而言。”屈原“欲楚怀王归返的意图和感情,因而引起了子兰的大怒,以至‘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因为楚怀王的归返,是与他们既得的权位不兼容的。特别是当初劝楚王人秦的就是子兰。对于怀王入秦被囚的事,他当然有不可推托的罪责,正因为这样,在怀王回归的问题上,子兰的反应也就异乎寻常的强烈。”[8]59
笔者以为,以“屈平既嫉之”为子兰所怒的原因,理由似乎并不充分。他只是与楚人一样“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实不至于引起子兰大怒,更不会引起襄王发怒。而以屈原欲楚怀王返国复位的政治意图,才是子兰、襄王所怒的真正原因,这样理解接近于事情真相。褚氏洞察此义,可谓难能可贵。
(文章未完待续)
[1] 聂石樵.屈原论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董运庭.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总体廓清——再读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J].重庆师院学报,2005(3).
[3] 汤炳正.楚辞类稿[M].成都:巴蜀书社,1988.
[4] 汤炳正.汤炳正论楚辞[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5] 熊任望.楚辞探综[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6] 廖化津.《屈原列传》解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4).
[7] 张叶芦.屈赋辨惑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8] 褚斌杰.《史记屈原列传》讲疏[M]//褚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 (汉)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1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刘永济.屈赋通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2] 孙作云.读《史记·屈原列传》[J].史学月刊,1959(9).
[13] 谭介甫.屈赋新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4]何其芳.屈原和他的作品[M]//蓝棣之.何其芳全集(3).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5](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林 庚.林庚楚辞研究两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7]郭沫若.郭沫若文集(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8]礼记[M].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9](汉)王 充.论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20](清)唐 甄.潜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55.
[21]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汉语大辞典(5)[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12.
[22]陈子展.楚辞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23]杜松柏.楚辞研究[M]//楚辞汇编(1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
[24](南宋)朱 熹.楚辞辨证[M]//楚辞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3.
[25](清)陈本礼.《离骚》精义[M]//吴 平.楚辞文献集成(14).扬州:广陵书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