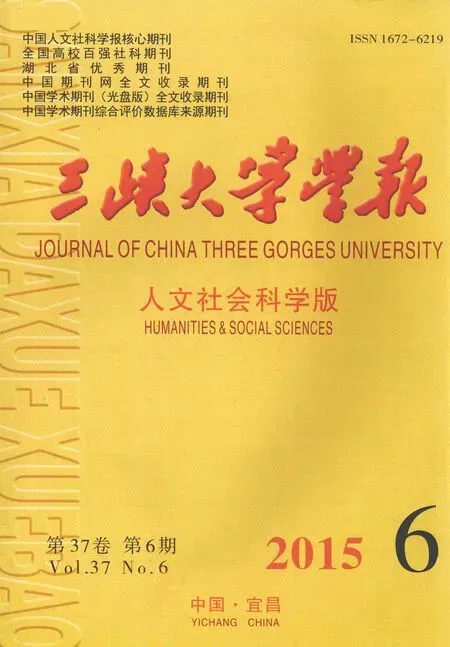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音乐”抒写
黎保荣,蓝燕玲
(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肇庆 526061)
一、张爱玲的音乐素养以及对音乐的兴趣
张爱玲散文《谈音乐》的开篇便是:“我不大喜欢音乐”[1]140。一个自称不大喜欢音乐的人,在她的小说中却不难发现一段一段的音乐抒写,随处都有跳动着的音符,飘扬着的旋律。灵动飞跃的钢琴声、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如泣如诉的口琴声、富有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忧郁的歌剧、气急吁吁的伦巴舞曲……各种乐器,各类乐种,古今的,中外的,信手拈来,好像她不只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个全能型的音乐家。谁还会相信张爱玲是个“不大喜欢音乐”的人呢?对一件事或者某种东西如果真的没有兴趣,是很难把握它的内在特点,并且将它运用得如此在行的。正如欧阳修在《书梅圣俞诗稿后》中所说的:“乐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于心,应于手,而不可述之言也。听者善,亦必得于心而会以意,不可得而言也。”[2]张爱玲能用如此灵动的语言将音乐描写下来,可见她对音乐的掌握已达到了比“得心应手”更深一层的程度了。
其实她所谓的不大喜欢只是相对于颜色和气味来说,因为颜色给了她喜悦感和真实感,气味虽然只给了她“小趣味”,但也能让她获得短暂的愉悦。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即使是所谓‘轻性音乐’,那跳跃也像是浮面的,有点假。”[1]140在她看来音乐缺少了一种真实感与存在感,是冷冷清清的,虚无缥缈,稍纵即逝的。
但我们谁都不能否认张爱玲的确具有良好的音乐素养以及她某个时期对音乐的浓厚的兴趣。
客观上,张爱玲时代的上海,完全有能力,有条件为所有像张爱玲一样喜欢音乐的人提供所需要的大环境。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因为她的洋派与摩登,因为她的时尚感觉与异域风情,因为她有旗袍香水,有高跟鞋与霓虹灯,有手摇唱机和屋顶花园而深入人心。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是这么描写上海的:“1930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美丽的世界。”[3]3-4。如果把上海比作是一个成熟的活力四射的、优雅性感妩媚的大姐姐,那么当时的香港充其量只是个瘦小的尚未发育的黄毛丫头。这个如万花筒般的休闲与娱乐世界,为培养张爱玲的音乐素养提供了一个设施齐全、自由开阔的大环境,这也是作为一个前提条件而存在的,如果换作任何一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小山村,恐怕就很难做到了。
社会条件具备了,家庭条件当然也不可或缺。众所周知,张爱玲家世显赫,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千金。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都是清末大名鼎鼎、举足轻重的人物。祖上的余荫让后代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虽然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名副其实的清朝遗少,他没有像外祖父、父亲那样大的作为,但当时靠祖上留下来的遗产,张家也是生活无忧,足以享乐,所以有一定的能力供张爱玲学音乐,培养她的音乐素养。
主观上,张爱玲对音乐的兴趣首先来自母亲的影响。张的母亲黄逸梵是个出过洋、留过学的进步女性。她回国的时候,也同时带回了西洋的风尚和礼仪,所以有能力教张爱玲钢琴、绘画和英文。
张爱玲在八九岁的时候开始接触音乐,那时候她母亲和姑姑刚从国外回来,每天都在练习钢琴和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受到音乐的熏陶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她在散文《谈音乐》和《私语》中很详细地描写了这方面的一些细节。
张爱玲的母亲曾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将张爱玲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淑女,所以格外注重张在音乐这方面的训练,尤其是钢琴,仿佛一弹钢琴,脸上眉间便会浮现“淑女”二字似的。但不管怎么说,张爱玲的确是受到了母亲和姑姑的直接的影响,耳濡目染,于是也对音乐产生了兴趣。当母亲和姑姑弹琴的时候,张爱玲总是喜欢待在旁边听,但其实她真正喜欢的不只是钢琴本身,还有那种充满音符的空气。“我非常感动地说:‘真羡慕呀!我要是能弹得这么好就好了!”[1]143所以母亲和姑姑都以为她是个罕见的懂得欣赏音乐的小孩,这方面的天才难能可贵,不能浪费了,于是立即送她去学弹钢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4]62。这句有点狂妄味道的话正是出自张爱玲之口,但纵观其一生,你会发现,她的确有资本做她的“天才梦”。
在散文《天才梦》中,张爱玲说:“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绘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4]63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字眼都极为敏感,弹奏钢琴时,她把那八个音符想象为穿着鲜艳的衣帽手拉着手在舞蹈,并且赋予了每个音符不同的个性。这就是张爱玲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她思维活跃,心思细腻,能够准确地捕捉每个音符的特性,让它们在指尖上飞跃跳动。在散文《私语》里,她说:“画图之外我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淑女的风度的”[1]107。这个时期张爱玲对音乐的浓厚的兴趣为她的音乐素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不管是不是小孩子的一时兴起,或者三分钟热度。她拥有着不同寻常的灵性,能够在音符里自由驰骋。虽然后来因为伸手问父亲要钱交学钢琴的费用遭拒绝、受冷落,以及对教她的琴先生的惧怕等原因,张爱玲对于钢琴完全失去了兴趣,但她还是有一颗对音乐极其敏感的心,如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她说:“再过一家店面,无线电里娓娓唱着申曲,也是同样的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先是个女人在那里发言,然后一个男子高亢流利地接口唱出这一串:‘想我年纪大来岁数增,三长两短命归阴,抱头送终有啥人?’我真喜欢听,耳朵如鱼得水,在那音乐里栩栩游着”[4]149。一般人听到这些,也许会觉得是噪音,左耳进右耳出,转眼便忘记了,但张爱玲却是欢快地享受着,这也是张爱玲音乐素养的体现。
繁华的上海,丰厚的家底,母亲的影响,个人的聪慧,这些条件无一不支撑着张爱玲的音乐素养。所以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音乐”抒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音乐”抒写在文章中有着不同的意象功能,也有着深刻的意义。
二、音乐的表现功能
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评论张爱玲的文章时指出:“张爱玲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5]340。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除了比较常见的几个视觉意象,如月亮、楼梯、镜子之外,还有听觉意象——音乐。
“意象具有的最重要的功用,已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而实现表达的生动性,而是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以传递和负载相应的意义和内容”[6]55。
罗小平在《音乐与文学》一书中指出:音乐与文学的联系点之一在于,声音是两种艺术依存的物质载体;音乐的文学性表现在叙述性、戏剧性和典型性,而文学的音乐性则表现在语言的和谐和音调的抑扬、节奏美以及音响模式等方面。音乐对文学体裁、构思也都有影响[7]。
“音乐”作为一个听觉意象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其表现功能与意义是不可忽略的。它既可以表达人物的情感,可以渲染周围的环境,也可以揭示人物的命运。
1.音诉情衷:“音乐”抒写可以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
从音乐美学和听觉审美体验来看,音节的起伏缓急能最充分表现那飘忽无端的内心的情调。所谓“真情之流”是旋起旋落的心灵体验的浪涛,只有音乐的声波才最善于暗示和象征它[8]。
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最直接的方式是进行心理描写,但当人物的内心情感太过细腻,或者变化起伏比较大的时候,往往就很难找到准确的词语来描写,所有的形容词、动词都会显得不恰当、不到位,甚至苍白无力。张爱玲很巧妙地用“音乐”抒写来解围,让人物的内心情感在音符、旋律中自由驰骋,充分表达。
《金锁记》中有这样一处描写:“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9]21在这里,音乐代表着喜悦。七巧本来以为姜季泽是上门来借钱的,所以处处小心防备着,但在姜季泽的一番来势汹汹、脱口而出的“真情告白”之后,她很明显把戒心放下了,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欢愉,但内心防范的围墙早已被姜季泽的告白推倒了。回想着这些年来跟姜季泽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七巧低着头,感觉自己沐浴在光辉里,光辉里流淌着细细的、轻轻的音乐,这些带给她的都是喜悦,只有喜悦。那时的她像是一个待嫁的新娘子,娇羞,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张爱玲仅用了21 个字,便将曹七巧当时的心情直接“剖开来”给读者看。如果是用心理白描的手法,恐怕就不是21 个字能胜任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音乐”抒写也为作者表达人物内心情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薇龙上楼的时候,底下正入席吃饭,无线电里乐声悠扬。薇龙那间房,屋小如舟,被那音波推动着,那盏半旧红纱壁灯似乎摇摇晃晃,人在屋里,飘飘荡荡,心旷神怡。”[9]126飘着的音波竟然能将小屋如舟般推动,就像薇龙此时因紧张和兴奋而疯狂加速的心跳,将心中的涟漪层层泛起。薇龙怀着浓烈的好奇心成功入住姑妈家,这里的一切人和事对于她来说都是新鲜的,她的好心情此刻正随着无线电里悠扬的乐声飘荡着,仿佛看到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未来。
《半生缘》中:“街道转了个弯,便听见音乐声,提琴奏着东欧色彩的舞曲。顺着音乐声找过去,找到那小咖啡馆,里面透出红红的灯光。一个黄胡子的老外国人推开玻璃门走了出来,玻璃门荡来荡去,送出一阵人声和温暖的人气。世钧在门外站着,觉得他在这样的心情下,不可能走到人丛里去。他太快乐了。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同样地需要远离人群。他只能够在寒夜的街沿上踟躇着,听听音乐。”[10]52这里的“音乐”抒写准确地表达出了沈世钧内心的欢乐。跟自己暗恋的对象表白,刚好对方也喜欢他,这无疑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沈世钧想要独占这份快乐,他怕去到人丛里,快乐就要跟别人分享,甚至会被别人抢走。这时音乐对他来说也许只剩下模糊的旋律,但东欧色彩的舞曲,带给人的是无限的热情和欢乐,而沈世钧内心的热情和欢乐绝不会比这音乐弱,所以寒夜再寒也无所畏惧了。
再来看看《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另一处音乐描写:“街上卖笛子的人在那里吹笛子。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一扭一扭出来了,像绣像小说插图里的梦,一缕白气,从帐里出来,涨大了,内中有种种幻境,像懒蛇一般舒展开来,后来因为太瞌睡,终于连梦也睡着了。”[11]139这里还运用了通感的手法,笛声变成了白气,又像懒蛇,这使得描写更传神,更形象。这样一来,佟振保内心的空虚和倦怠便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了,连“梦”都被尖柔扭捏的笛声给催眠了,可见人内心的空虚无聊程度。佟振保心里忘不了、放不下王娇蕊,当她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一切对他来说便失去了意义,变得无聊透顶了。
英国批评家辛·刘易斯认为:“同诗人一样,小说家也运用意象来表达不同程度的效果,比方说:编一个生动的故事,加快故事的情节,象征地表达主题,或者揭示一种心理状态。”[12]108“音乐”意象为作者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感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音诉情衷,跟着那音乐,便能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2.乐与境同:“音乐”抒写可以渲染周围的环境
在组成中国传统小说基本情节的四个喻象(喜、怒、哀、乐)中,张爱玲似乎最喜欢“哀”[13]235。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苍凉”、“荒凉”等字眼出现的频率很大,她的绝大部分小说都没有幸福的结尾,只有苍凉的回声。在《自己的文章》中,她也曾明确地表达这一现象:“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1]14。
1929年鲁迅说:“在音乐上,和温色及冷色相当者,有长音阶的音调和短音阶的音调。……短音阶和哀愁同义,长音阶和快活同义。”[14]短音阶的音乐使环境充满哀愁苍凉之感,所以在营造“苍凉”意境中,“音乐”抒写是功不可没的。
《倾城之恋》中:“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9]46最后一段同样是对胡琴的描写:“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来过去,说不尽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9]87首尾呼应,通篇都回荡着苍凉的气息。正如张爱玲在《谈音乐》中说的:“胡琴就好得多,虽然也苍凉,到临了总像是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1]141
欧阳修在他的《试院闻胡琴作》中说:“胡琴本出胡人乐,奚奴弹之双泪落”,张爱玲在开篇便以“咿咿哑哑的胡琴声”来奠定全文的基调——苍凉。白流苏与范柳原的故事就是在这样苍凉悲壮的环境中开始的,也在这样苍凉悲壮的环境中结束,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苏,让她成为范柳原“名正言顺的妻”,这是张爱玲所有小说中唯一一个看起来比较完整的结局,幸福的结局也许还算不上。胡琴在这里是苍凉的代名词。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一路行来,只觉得荒凉。不知谁家宅第里有人用一只手指在那里弹钢琴,一个字一个字锨下去,迟慢地,弹出耶诞节赞美诗的调子,弹了一支又一支。耶诞夜的耶诞诗自有它的欢愉的气氛,可是在这暑天的下午,在静静晒满了太阳的长街上,太不是时候了,就像是乱梦颠倒,无聊得可笑。振保不知道为什么,竟不能忍耐这一曲指头弹出的琴声。”[11]107
佟振保当时正在欧洲旅行。巴黎这一座时尚之都,浪漫之城,却不能让他焕发出一丁点文艺气息,相反的,在巴黎僻静的街上,振保心里满是伤感,怅然的味道。因为他觉得外国总是有意无意不接纳中国的苦学生,在他的回忆中,“英国只限于地底电车、白煮空心菜、空白的雾、饿、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还在为自己到巴黎之前仍是个童男子而耿耿于怀。种种原因让他很难高兴起来,这时候的钢琴声并不悦耳,也不动听,耶诞节赞美诗的旋律也没有了往常的欢快。总之,在佟振保眼里,巴黎的傍晚是哀伤的,怅然的,甚至是荒凉的。越是浪漫的城市、晴好的天气、欢愉的琴声,越是显得环境的荒凉,也许荒凉的不是眼前的环境,而是看着这环境的人。
音乐描写虽然是听觉上的描写,但张爱玲凭借良好的音乐素养、敏感的心思和细腻的笔触,让读者将听觉上的描写转化成视觉上的享受,她总是能让跳动的音符跃然纸上,与所要渲染的环境合为一体。
3.声随命动:音乐抒写可以谕示人物命运
音乐是一种最富于暗示性的艺术,同时具有一种超乎具象之上的抽象性,而文学中的内在情绪在抽象性、节奏性和感染性等方面与音乐存在共同之处,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中常出现用“音乐”抒写来谕示人物命运的例子[15]252。
张爱玲的“音乐”抒写,还往往和人物的命运有着关联,或者说有一种谕示作用。
《金锁记》中有两处有关长安的音乐描写:“她从枕头边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来。犹疑地,Long Long Ago 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不能让人听见了。为了竭力按捺着,那呜呜的口琴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歇了半晌。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黑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状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长安又吹起口琴。”[9]27
长安悠悠忽忽听见了口琴的声音,迟钝地吹出了Long Long Ago——“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长安着了魔似的,去找那吹口琴的人——去找她自己。”[9]41
长安生命里仅有的两次快乐的时光——上学和初恋,都因为母亲曹七巧的干涉而夭折了。Long Long Ago 的曲子就是她命运的写照,原来很久很久以前,她就注定得不到快乐,注定找不到自己,怎能教她不苦闷?
《倾城之恋》中的胡琴声不仅有渲染环境的作用,同时也有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的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在这里,时间可以任意调整,生命像胡琴一样可以任人拉过来又拉过去。苍凉、滑稽、无可奈何。白流苏忍受不了牢笼一般的白公馆,终于逃了出来,以为从此可以呼吸到新鲜一点的空气,但到底,她还是姓“白”,不能因为离开了白公馆而改为姓“红”,或者姓“金”。所以她终究还是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只能在苍凉萧瑟的琴声里挣扎。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有一处堪称绝妙的音乐描写:“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舞;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曲;柔滑的软缎,像《蓝色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盹了一会,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了。楼下正奏着气急吁吁的伦巴舞曲,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跳起伦巴舞来,一踢一踢,淅沥沙啦响。”[10]127
用不同的音乐来比喻不同布料的衣服穿起来的感觉,视觉以及触觉都巧妙地用听觉来表达,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薇龙被这满橱的衣服惊艳到了,她刚开始还以为这是姑妈忘了把这橱腾空出来,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准备的,薇龙心里已经明白了姑妈准备这些衣服的内在目的——“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但搭配衣服的,是人,这人就是梁太太。但薇龙还是闭着眼睛接受了这一切,同时也接受了未来的命运——被姑妈掌控的命运。
《封锁》中:“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毅然打破了这静默。他的嗓子浑圆嘹亮:‘可怜啊可怜!毅然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音乐性的节奏传染上了开电车的,开电车的也是山东人。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抱着胳膊,向车门上一靠,跟着唱了起来:‘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10]202
“开电车的放声唱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10]212
电车封锁期间,翠远跟宗桢短短地交谈了几句便“恋爱着”了,她想着,“以后她多半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绝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般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她为这样的相逢而感到高兴,但当封锁开放时,她明白了宗桢的意思:“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翠远也是可怜的,乞丐没有钱难以“生存”,而她则缺乏感情滋润,“生命”空白乏味。翠远整个的命运都是可怜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连环套》的开头有一大段戏院音乐会的描写,也谕示着女主人公霓喜对“这个世界要爱而爱不进去”的“下死劲”的挣扎,昭示着人物命运的纷乱和悲怆。
意象抓住最富本质性的瞬间,将“存在”的真相凝聚在某个特点的“形质”上,不断地把人引向深处[16]。
张爱玲小说中的音乐抒写有着这样的作用,无论是表达人物内心情感,渲染周围环境还是揭示人物命运,都一语中的,不浪费一点笔墨。
三、音乐抒写和电影蒙太奇手法
“在中国,美国电影比任何国家的电影都受中国人的欢迎。除了美国电影的奢华铺张、高妙的导演和技术,中国人也喜欢我们绝大多数电影结尾的‘永恒幸福’和‘邪不压正’,这和许多欧洲电影的悲剧性结尾恰成对照”[3]108。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引用了诺斯《中国电影市场》里的一段话,说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在上海十分盛行。
张爱玲是个货真价实的影迷。尤其是对美国好莱坞电影,其入迷程度是别人很难想象的。“除了文学,姐姐学生时代另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电影。她当时订阅的一些杂志,也以电影刊物居多。她的床头,与小说并列的就是美国的电影杂志,如Movie Stra,Screen Play 等”[17]78。“三四十年代著名美国演员主演的片子,她都爱看。如葛丽泰·嘉宝、蓓蒂·戴维斯、琼·克劳馥、加利·古柏、克拉克·盖博、秀兰·邓波儿、费雯丽等明星的片子,几乎每部必看[17]79。
甚至有一次刚到杭州第二天,她从报纸广告看到谈瑛(她喜欢的中国影星之一)主演的电影《风》正在上海某家电影院上映,不顾亲戚朋友的劝阻,毅然赶回上海连看了两场。看来那时候的张爱玲也是个疯狂的“追星族”。迷电影迷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是很少见的。
张爱玲曾经用中文写过影评,发表在《万象》杂志上,后来还写过电影剧本《不了情》。
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张爱玲的小说里也充满了电影的味道,读她的小说就像是在观看一部电影。有人将张爱玲的小说形容为“纸上电影”,这是一种很贴切的说法,她的小说有流畅的对话、通俗的故事、近乎完美的舞台与电影的叙述手法。张爱玲的特长是:她把好莱坞的电影技巧吸收之后,变成了自己的文体,并且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技巧结合得天衣无缝”[18]。而她小说中的音乐抒写片断往往给人一种极其强烈的画面印象,声画结合,很好地利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蒙太奇手法是电影的构成形式,也是电影艺术的最主要的叙述手段和表现手段之一。
最典型的是《倾城之恋》中的这一段:“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搬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9]46
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电影镜头。“咿咿哑哑的胡琴声”是背景音乐,电影的人物是一个光艳的伶人,人物的动作是唱、笑、用袖子挡住了嘴,然而镜头一闪,却什么都没有。“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前后两个镜头形成的强烈反差效果让读者印象深刻,属于电影中的隐喻蒙太奇,通过镜头或场面的对列进行类比,含蓄而形象地表达创作者的某种意义。伶人的表演本来就是要应和胡琴声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假想,更加突出了环境的苍凉与寂寥,为故事奠定了基调。
《倾城之恋》还有另一处“音乐”抒写也是运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来进行处理:“阳台上,四爷又拉起胡琴来了,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得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对镜子这一表演,那胡琴听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走了几步,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关了。”[9]53
这里,胡琴声依旧是作为背景音乐而存在的。白流苏在镜子前自导自演了这一整套奇怪的诡异的动作,表现了她受到三爷和四奶揶揄后的尴尬,她那种自哀自怜的状态便立刻闪现在读者面前。胡琴声是一种持续进行的声音,而流苏的每个动作正是特写镜头,声音和镜头组合起来就构成了自成首尾的蒙太奇段落。
《金锁记》中的音乐抒写片断也体现了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她从枕头边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来。犹疑地,Long Long Ago 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不能让人听见了。为了竭力按捺着,那呜呜的口琴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歇了半晌。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黑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状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长安又吹起口琴。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9]27
因为母亲去学校“兴师问罪”,长安觉得在老师和同学面前丢了脸,心里很不高兴,半夜睡不着起来吹口琴。Long Long Ago 的调子虽然是长安吹出来的,但这里可以当作是背景音乐,而后面一系列对月亮的描写则组合成一组镜头,从上到下,镜头慢慢推进,让月亮来诠释人物的内心世界。
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让张爱玲的小说镜头感十足,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也强化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运用蒙太奇不只是拓展了单篇作品本身的艺术表现空间,整体来看,更重要的是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冲破旧章回小说叙事模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6]63
四、结语
张爱玲出生在对的时代,降生在对的家庭,再加上天资聪颖,艺术细胞发达,所以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良好的音乐素养。作为作家,张爱玲并没有埋没她的音乐才华,而是在她的小说中给了这种才华一席之地,让它恰到好处地为文字添彩,为文章加料。应该说张爱玲是个具有艺术才华的聪明的作家,她的绘画才能让她能为自己的文章配图,而她的音乐才能则能为文章配乐,这种“乐”就像是文字的弦外之音,当人物的情感、周围的环境以及人物的命运很难找到恰当的文字来表达、来描述的时候,“音乐”抒写便能代替一切干瘪无力的文字,弦外之音很准确又很巧妙地表达作者的真正意图。这是“音乐”抒写在小说内容方面的重要意义。而在另一个层面上,“音乐”抒写对小说的形式也有明显的意义,即增强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与“弦外之音”相对应,后者可以称之为“弦外之画”。张爱玲小说中的“音乐”抒写通常都运用了电影蒙太奇手法,让小说极具画面感和镜头感,小说中出现“音乐”描写,本来已经是跨艺术的表现,再在这基础上融合电影蒙太奇手法,便是跨艺术和双重艺术的表现了,“音画结合”极大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音乐”抒写都为张爱玲的小说带来了无穷的生命力,甚至可以成为张爱玲小说的一大特色。
[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2]欧阳修.欧阳修散文全集[M].北京:今日出版社,1996.
[3]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4]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二1939-1947年作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6]陈 晖.张爱玲与现代主义[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4.
[7]罗小平.音乐与文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8]朱谦之.中国音乐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9]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中短篇小说1943年作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10]张爱玲.半生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1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中短篇小说1944年作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12]辛·刘易斯.意象批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108.
[13]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4]鲁 迅.鲁迅译文集:第6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5]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16]费 勇.言无言——空白的诗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47.
[17]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8]李欧梵.不了情:张爱玲和电影[M]//苍凉与世故.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