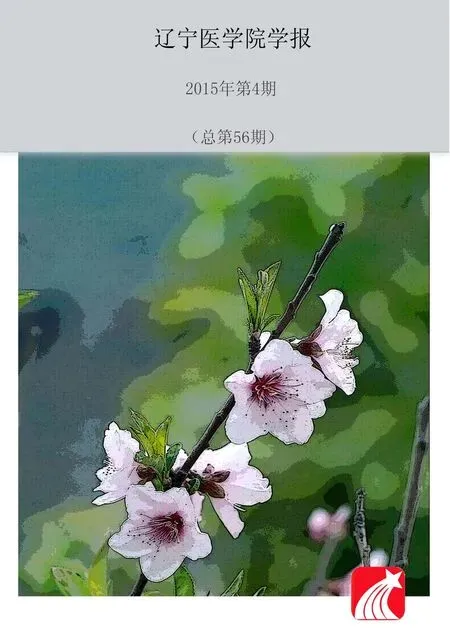《泰西人身说概》与合信《全体新论》对西医解剖学在华传播研究
胡莲翠,张晓丽
(安徽医科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泰西人身说概》与合信《全体新论》对西医解剖学在华传播研究
胡莲翠,张晓丽
(安徽医科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2)
《泰西人身说概》与《全体新论》是来华传教士翻译的关于生理解剖学的两部著作,代表了不同时期西方解剖学发展概况,在传播解剖学理论、冲击传统中医解剖谬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出发,对《泰西人身说概》与《全体新论》在译述主体与目的、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与范围及传播效果与影响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探析二者改变国人解剖学观念、传播西方解剖学知识的意义所在。
《泰西人身说概》;《全体新论》;传播
西方医学开始在中国传播并被民众甚至贵族阶层接受,起到媒介作用的一直都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西方医学的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就是翻译西医书籍,并且以人体生理学知识为主要传播内容,因关乎人体健康,社会效果比较显著。其中解剖学译著较多,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著作是明末清初时期邓玉函的《泰西人身说概》,此后比较著名的有罗雅谷的《人身图说》、巴多明的《人体解剖学》和《解体全录必得》,近代有合信的《全体新论》、柯为良的《全体阐微》、德贞的《全体通考》等。这些译书对当时的中国在传播生理知识、破解人体解剖愚昧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弥补了一直以来中国在解剖学研究领域上的不足,其中以《泰西人身说概》与《全体新论》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
一、 《泰西人身说概》与合信《全体新论》概述
1.《泰西人身说概》。《泰西人身说概》 (后简称《说概》),学者普遍认为由瑞士耶稣会教士邓玉函译述、明朝官吏毕拱辰润色而成。《说概》成书时间与出版时间由于史料不详,学者争议较大也尚未形成统一,一般认为在1622—1643年之间。目前《说概》版本只存一种刻本,藏于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另有九种抄本在世[1]。关于《说概》的底本问题,洪性烈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对之前学者,如郭文华、牛亚华、马伯英等,所持的包因的《解剖学论》底本说以及邹振环等学者的维萨留斯《人体之构造》底本说进行了驳斥,主张《说概》底本问题尚未解决无法定论[2]。《说概》是邓玉函在杭州期间,居于官员李之藻家中译述完成的,后经毕拱辰在汤若望处所得到书稿《人身说》二卷,因“恨其笔俚而不能挈作者之华,语滞而不能达作者之意”[3],对《说概》进行了润色和校订,最终得以刊刻问世。《说概》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十五章,下卷八章,附录利西泰记法五则。涉及人体运动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内容。《说概》作为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解剖学的著作,虽然因为刊刻原因导致流传不广,但其中的解剖学内容基本反映了西方16世纪解剖学概况,国内士大夫阶层、医家得以接触到与中医解剖理论截然不同的解剖学说,为清朝末期解剖学译述与传播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2.合信《全体新论》。《全体新论》由英国传教士合信与中国学者陈修堂译述、周励堂绘图合作完成的。1851年在惠爱医馆初次出版,1853年、1855年分别在惠爱医馆、墨海书馆再版,1857年日本也将《全体新论》进行了翻刻,影响深远。《全体新论》是合信等人“集西国医谱,参互考订”而成[4],这里的西国医谱有学者研究认为主要包括William Benjamin Carpenter的 Animal Physiology、Jones Quain的Elements of Anatomy、ErasmusWilson的The Anatomist’s Vade Mecum与William Paley的Natural Theology[5],书中插图也多引自这些书目。译著《全体新论》的目的,合信在序中作了解释,考虑到解剖学是医学基础所在,而中国医者多不了解其功用及与疾病关系,合信利用其医学教育和解剖实践经验,与陈修堂、周励堂二人分工合作,以当时的西方解剖学著作为参考,完成了这部近代以来第一部系统阐述解剖学的巨著。1851年(咸丰元年)在墨海书馆翻刻版是《全体新论》流传较广的版本,全书分为39论,插图271张,介绍了人体运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内容,其中运动系统篇幅较多,内容也较为详细,书中多幅插图构成了《全体新论》最主要的特色,出版后受到了中国各界人士的称赞,成为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生理解剖学代表著作和基本读物,在传播西方解剖生理知识方面贡献颇大,甚至影响了诸如孙中山、鲁迅、梁启超等人对于西医的观念认识。
二、《泰西人身说概》与《全体新论》解剖学传播的分析
《泰西人身说概》与《全体新论》都是来华传教士所译述的解剖学作品,代表了不同时期西方解剖学发展概况,在传播西方解剖学方面二者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西医解剖译著中影响比较深远的两部著作,对二者的传播过程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其解剖学传播历史价值。
1.译述主体及目的。《说概》与《全体新论》的主要译述者分别是邓玉函、合信,二人虽然分属瑞士耶稣会与英国伦敦会差会,年代也从明朝晚期跨度到清朝道光年间,但在译书过程中二人在医学教育背景、译书目的以及助手方面表现出了相似性。邓玉函与合信在赴华前都在大学接受过正统医学教育,接触或学习了从十六世纪由维萨里建立起来的现代人体解剖学,为其后的解剖学书籍翻译奠定了基础。其次,二者译述西书并不是单纯的向华人介绍西方医学,而是或多或少地借书籍内容传播吸引华人入会,宣传教会组织。邓玉函译著的《说概》中“大主”、“造物主”等多处可见,《全体新论》中也出现“上帝”、“造物主”等词,宗教色彩明显。在翻译西书过程中,如何将西方名词转化成华人易理解和接受的汉文是传教士在译著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邓玉函与合信都选择了与中国学者或官吏共同合作翻译,将中国传统知识引入西书翻译从而迎合读者趣味。《说概》是邓玉函口述,李之藻家中一文士笔录,毕拱辰校订而成。《全体新论》则是合信与中国学者陈修堂同撰、周励堂绘图而成。
2.主要传播内容。《说概》与《全体新论》都是关于人体解剖学的著作,以解剖学知识为主要传播内容,其中少量涉及生理学。从二者反映的西方解剖学发展概况看,《说概》既保留了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也涉及到一些文艺复兴时期最新解剖学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西方16世纪解剖学概况。《全体新论》成书于19时期中期,内容主要反映西方17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解剖学研究进展,包括1628年哈维发现的血液循环、1661年发现毛细血管网、1837年发现氧和二氧化碳,人体运行通过血液循环进行等都在《全体新论》中提及[6]。其次,从二者内容涉及人体系统来看,运动系统是两部译著的共同重点内容,对人体骨骼、肌肉等介绍都比较详实,除细节部分外基本正确。不同的是《说概》未涉及人体内脏部分的解剖内容,有学者分析是出于宗教传播的考虑,感觉器官较内脏更能传递神学信息[7]。而《全体新论》中对于内脏部分则分章论述人体胃部、大小肠部、肝部等内脏的功用、部位,并附插图以供参考。再从二者宗教色彩来看,《全体新论》宗教内容所占比例较《说概》大为降低,仅为7%,这也反映出19世纪的西书翻译更加倾向于单纯介绍和普及西方科学理论,宗教目的淡化。总的来说《全体新论》较《说概》内容更为具体、科学,更能反映现代人体解剖学知识理论。
3.传播对象与范围。从《说概》与《全体新论》的传播对象来看,前者主要是局限在学者及上层阶级领域内,影响范围较为局限。16世纪中期,以汤若望为首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掀起了第一次西学东渐高潮[7],明朝政府及官员的倡导崇尚西学倾向使传教士在华活动日益活跃,官员、学者与传教士之间交往频繁,由传教士翻译的西方科技著作首先就在这些人群中得以传播。史料记载阅读并引用过《说概》的有毕拱辰、刘献廷,清朝医学家王学权、学者俞理初、姚衡、郑复光等人。作为中国最早的西方解剖学译著,学者、官员以及对西方解剖有兴趣的中国医学家成为《说概》的主要传播对象,因此也导致《说概》传播范围的窄小,限制了其解剖学传播价值。而《全体新论》以其图文相应的解剖学介绍,一出版就获得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与社会民众的推崇。以王韬、胡琨、潘仕成、医学家王士雄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读过《全体新论》后,对书中所著的有别于中医脏腑理论的解剖内容啧啧称奇,称赞不已。两广总督叶名琛曾为《全体新论》写“赞”,推动了《全体新论》在社会上的流传。《全体新论》成为当时一些医学校的教材,是医学生的基础读本。在上海仁济医馆内还提供有《全体新论》刻片,“如有欲阅者,自备纸墨,就板刷印,分文不取”,使得社会普通民众也能轻易获得,《全体新论》的传播对象与范围较《说概》更加广泛和普及。
4.传播效果与影响。从传播效果来看,《全体新论》较《说概》影响更加深远,体现在出版量、西医教育及引用推广方面。在出版量上,《说概》从明末至今,只流传存有一种刻本,即藏于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版,其次还有九种抄本在世,分立各处。《说概》版本稀少极大的影响了其解剖学传播,其次《说概》中包含的盖伦等错误解剖理论以及其具有的明显基督教神学色彩,导致《说概》在内容上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说概》流传版本稀缺以及内容上的滞后性成为影响《说概》传播效果的主要原因。但仍有学者留下了对《说概》的赞誉之词。毕拱辰在序中评价《说概》“缕析条分,无微不彻”、“真可补《人镜》、《难经》之遗”[8]。
《全体新论》在19世纪50年代期间经多次出版重印,广受欢迎,在日本、朝鲜等国也很受重视。合信将人体解剖学基础知识图文并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并在较大范围内得到快速普及传播。其次《全体新论》还被作为医学院西医教育基础教材,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有使用,在这一方面的传播作用明显逊于《全体新论》。在引用参考方面,《全体新论》更是在一些文人墨客的笔中留下了浓重色彩,王韬在《园文录外编》中赞曰“无不精详赅备,洞见要处”[9],康有为将《全体新论》列为学生阅读书目,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收录《全体新论》,除此之外,《全体新论》还被收录在《东西学书录》、《增版东西学书录》、《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等西学书目中,成为书目必载西医书。
三、《泰西人身说概》与《全体新论》对西医解剖学传播影响
1.改变人们对解剖学观念。中国古代对于解剖学认识由来已久,《内经》、《难经》中都有详细的人体脏器、骨骼的描述,汉代有王莽对敌军、宋朝对欧希范等人的解剖记载,中国解剖学发展基本停留在《内经》、《难经》的认识程度,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直至明末清初第一次“西学东渐”高潮的到来,利玛窦、邓玉函、罗雅谷等人关于解剖学译著的出现,西方盖伦、维萨留斯等人的解剖学理论开始被传入中国,进入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士大夫阶层的视野中。《说概》的出现,让一些思想开明的士大夫阶层接触到与经验主义中医完全不同的实证解剖学。到清末民初第二次西学东渐,更多医学传教士翻译的解剖学译著的出现使得西医解剖学理论开始被国人接受,中医传统脏腑、骨髓理论受到质疑和批判。免费的刷印方式让《全体新论》的传播趋向大众化,上到士大夫,下到普通民众,《全体新论》改变人们对于传统解剖学的观念,认识西医解剖学。从《说概》到《全体新论》,可以说是西医解剖学在中国的启蒙过程。经历了长期解剖学发展停滞阶段,中国的一些医学家也开始绘制和编撰全新的解剖著作。
2.普及近代西医解剖知识。《说概》与《全体新论》是17世纪与19世纪在中国出版的西医译著,代表的是不同时期西方解剖学成果概况,虽然内容上仍存在一些错误,但在普及解剖学理论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以《全体新论》为甚。《说概》因其刻本稀少,中医界仅以抄本的形式流传,解剖学知识的普及范围有限。作为近代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解剖学译著,《全体新论》在出版量及西医教育这两个方面最大化的普及西医解剖学。在仁济医馆的木刻本中,刊有“咸丰元年刊《全体新论》……板片具存上海仁济医馆”字样,除此之外《全体新论》还于1853年、1855年再版,1856年广州学者潘仕成将《全体新论》与合信其他四本译著合成《合信医书五种》重新刻印出版,持续畅销。《全体新论》一经出版后即被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选为博济医院的医学基础教材,成为医学生的解剖学读本,在西医教育领域向医学生传播普及西医解剖学理论。直到20世纪20—30年代,近代医学家张山雷主持浙江兰溪中医专科学校时,还以《全体新论》作为学生读物。《说概》与《全体新论》作为一种与我国传统医学大相径庭的医学体系,其所著的西方解剖学内容对我国的医学界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科学普及解剖学知识方面作用巨大。
3.奠基中国近代西医解剖学。中国解剖历史发源较早,早在三千年前殷商时期就有尸体解剖记录,其后出现了诸如《灵枢经》、《内经》、《欧希范五脏图》、《存真图》、《亲见改正脏腑图》等关于人体解剖著作或绘图。但是这些解剖学成就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家思想等封建传统之上的,《黄帝内经》被历代中医家奉为经典,中国解剖学束缚在“遵经崇古”中发展缓慢。明末第一次“西学东渐”带来了西方科技著作翻译风潮,《说概》在此背景下诞生,成为中国最早传入的西方人体解剖学著作,带来了强调实证与系统的西方解剖知识,但是由于诸多复杂原因《说概》解剖学传播并没有给中国古代解剖学形成巨大冲击,整体影响较小。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解剖学译著的不断传入,中国开始建立起比较系统完整的解剖学。《全体新论》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吸收了西方当时最新的解剖学成果并绘图二百七十多张,开创了近代西方人体解剖知识输入中国的先河,在中国士大夫、学者等阶层中备受称赞,影响深远。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此后又出现了如德贞《全体通考》、《格氏系统解剖学》等影响较大的解剖书籍,但是《说概》与《全体新论》作为两次“西学东渐”高潮中解剖学译著的开创之作,对于近代中国解剖学创立具有奠基作用,在中国解剖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笔者通过对于《泰西人身说概》与《全体新论》的比较,阐述二者的成书过程、版本流传、主要内容以及影响方面,论述西医传播中解剖学译著对于近代西医传播的重要作用,传播、普及近代人体生理解剖学知识,形成“全体学”独特方面,在近代医学传播中作用深远,开始改变人们的传统解剖观念,建立起近代解剖学知识体系,促进西医的教育发展以及西医医疗活动。以《泰西人身说概》与《全体新论》为代表的西方解剖学译著在中国近代解剖学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1]邹振环.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20-321.
[2]洪性烈.《泰西人身说概》底本问题初探[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34(2):143-158.
[3]毕拱辰.泰西人身说概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231.
[4]王扬宗.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261-262.
[5]陈万成.《全体新论》插图来源的再考察—兼说晚清医疗教育的一段中印因缘[J].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30(3):257-277.
[6]袁媛.从《全体新论》到《体功学》—我国早期生理学著作的编译和演变[J].医学与哲学,2010,31(7):74-77.
[7]邹振环.《泰西人身说概》:最早传入的西洋人体解剖学著作[J].编辑学刊,1994,(3):85-87.
[8]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231.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Anatomy Communication with Taixi Renshen Shuogai and Quanti Xinlun
Hu Liancui&Zhang Xiaoli
(Anhui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230032)
TaixiRenshen Shuogai and QuantiXinlun are aboutphysiology and anatomywhichwere translated bymissionaries,representing developmentsituation ofWestern anatomy in differentperiods.These twobooks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pagating anatomy theory and affec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anatomy theory.S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this passage compared these two books in translator and purpose,communication content,scope and effect,in order to probe the significance in changing the concept of human anatomy and spreadingwestern anatomy knowledge.
Taixi Renshen Shuogai,Quanti Xinlun,spreading
R-052
A
1674-0416(2015)04-0064-04
[责任编辑:刘 芳]
2015-05-22
本文系安徽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基金项目《近代中国科技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编号:XJ201029)的研究成果。
胡莲翠,女,1989年生,安徽肥西人,科学技术哲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张晓丽,女,1965年生,安徽舒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