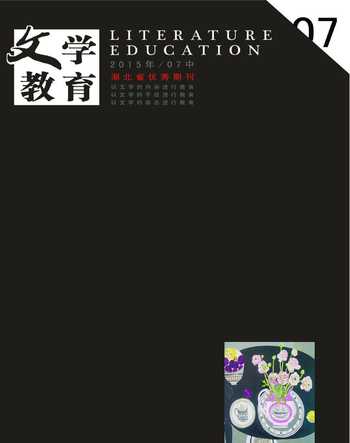《红高粱家族》与《蛙》中的民间生死观
周静如
内容摘要: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与《蛙》中展现了大量的生死图景,其背后蕴含的儒家重生理念以及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民间信仰勾画了生命的崇高与民众对生命的渴望。中国民间对于丧葬的重视不仅受到儒家礼俗观与孝道观念的影响,还内在地包涵有灵魂不灭等民俗观念。精神、道德被后人传诵是民众所追求的永生,而通过种的繁衍来超越肉体的死亡则是民间生生不息的终极意义。在民间生死观中生与死紧密相连,死是生的延续,生与死在矛盾中和谐统一。
关键词:生死观 民间信仰 儒家思想
古人云:“生死事大”,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由于宗教和传统民间信仰的影响,生与死这两大通过仪礼关涉到了大量的民俗事象与图景,使得它的民俗意义更加丰富完整。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与《蛙》就呈现了典型的中国民间生死观,凸显了传统文化在民众思想中的深重影响。
一.生的渴望与执著
“生”在民间社会中的含义包括生命与生育。由于传统儒家观念及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形态,民众对生命的珍视与对生育的执着追求都表现出人的本真性。又由于传统民间信仰对民众价值观的导向,民众对于“生”的渴望与执着呈现出了一卷壮阔波澜的诗篇。
1.儒家思想中的“生”
传统社会将生命的开始看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生是人之始,是自然发展的常道。《周易·序卦》中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不可替代的生命才是人生的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生育在民间因此有着重要意义。在民众的观念中,生育意味着生命的延续,是不可遏制的。
在莫言小说中,重视生育与生命的民间观点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如《蛙》中对姑姑给人接生时的描写:
姑姑是个阶级观念很强的人,但他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那一刻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她体会到的喜悦是一种纯洁、纯粹的人的感情。
儒家重视人的生命,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生命的宝贵在儒家传统中得到了高度重视。儒家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它始终强调仁德,重视人和一切生命。《周易·系辞下》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命的延续乃是天地之大德。儒家对杀戮生命进行了强烈谴责,这种观点在《蛙》中有鲜明的表现。“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遭到了百姓们的强烈反抗,因为这是对生命的戕害和杀戮。如:
你姑姑不是人,是妖魔!岳母跳出来说,这些年来,她糟蹋了多少性命啊?她的双手沾满了鲜血,她死后要被阎王爷千刀万剐!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个人的生命与宗族生命的延续息息相关。生,是宗族中的一员;死,就成了祖先的一员。这一家庭结构使得民众必须以宗族的利益为重,个人的子孙后代的繁衍也就是整个是宗族生命的延续。于是民众必须承担为宗族传宗接代的任务。“多子多福”这一传统观念使得民众坚持着绵延子嗣、扩大宗族的信念,所以生养是使家族人丁兴旺繁盛的一个重要途径。
2.民间崇拜
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民众内心的寄托和期许大多投入到各类信仰中。于是从民众的行为中可以看到许多民间崇拜的映射。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与《蛙》中,最主要的民间崇拜就是生殖崇拜与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形式。原始初民相信各氏族与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具有血缘关系,所以将其视作本氏族的保护者和象征,它也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保护和崇敬。从表面上看,图腾崇拜是对动植物或无生物的崇拜,但实质上,民众将图腾作为同源共祖的凭证,图腾也就成为了维系部族成员的重要纽带,部族精神与感情上的信仰对象,更是氏族生命力的代表。图腾崇拜内在地映射出生殖崇拜的意味。生殖崇拜是原始而神秘的,是原始先民对于生命强力的崇拜。
在《红高粱家族》与《蛙》中,各有一个突出的崇拜对象,即红高粱与蛙。
在高密东北乡,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最野生最原始最民间的红高粱成为了东北乡民众的主要粮食来源。在原初社会里,能够成为原始先民崇拜对象的事物,不仅仅是能够供给生活,更多的是它拥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和生命力。这种对强大生殖能力的崇拜源于先民自身对于生育能力的渴望。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力落后,繁殖能力成为了保证氏族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于是原始先民对了这种多子饱满、生命力旺盛的植物产生了崇拜心理。
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中对“红高粱”这一植物表现出的图腾崇拜及其内涵的生殖崇拜是隐藏在行文中的,那么《蛙》中对“蛙”这个图腾的崇拜则鲜明地在小说中有所体现。
由于蛙类的繁殖能力强,产卵数量多,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部落产生了蛙的图腾崇拜。何星亮先生认为:“娲即蛙当无疑义,而女与雌义同,所谓女娲其实就是‘雌蛙。大概雌蛙原是某氏族部落的图腾,后来图腾演化为神,雌蛙也演变成女娲。”赵国华先生认为:“女娲本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女性的象征,尔后再演为生殖女神。” 在《蛙》中也展现了蛙与生殖力的关联。小狮子认为“蛙”与“娃”同音,婴儿刚出母腹的哭声与蛙声相似,是因为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喧闹的蛙叫声正代表着旺盛繁茂的生命力,这便隐含着了对蛙的生殖崇拜。
《蛙》这部小说中的生殖崇拜不仅仅展现在“蛙”这一高密东北乡的图腾,还体现在许多民间信仰中。民间由于对生育与繁衍非常重视,于是产生了许多生育神,民间对这些生育神都要定期祭祀。《蛙》中民众对送子娘娘虔诚祭拜,争抢娘娘手中的婴孩,都展示了民众根深蒂固的对生育生殖的信仰与崇拜。
从“红高粱”到“蛙”再到民众对“送子娘娘”的顶礼膜拜,一种对生命及其繁衍的渴望与崇拜呼之欲出。这种崇拜生命与繁衍的背后是民间对原始、野性的生命强力的真正渴望与追求。红高粱的强韧坚强灿烂的生命张力与蛙的生命强度以及民众极强的求生欲念,民众对生的渴望与对死亡的恐惧都是表现出了真正的生殖崇拜的内涵。这种生殖图腾崇拜已经渗入中国民间民众的内心,无法拔出,因为人类永恒追求的都是生的强力。
二.“死”的庄严与神秘
人类自有了自觉的意识后,就不得不面对死亡。中国传统社会的观念中对“死”的态度集中表现在丧葬仪式。儒家宣传的隆葬厚仪及影响中国千百年来的“孝道”观念以及祖先崇拜使得中国民众将厚葬当成了一个“集体无意识”的心态。同时永生信仰与灵魂不灭的观念也使得民众重视“死”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丧葬。这种对“死”的态度在民间丧葬祭祀中有大量展现。
1.儒家对“死”的态度
儒家所关注的并非“死”本身,而是“死”对社会、家族、个人产生的影响。儒家推崇“事死如事生”、“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礼俗观,通过重视丧葬来展示儒家的礼教特色,表达“孝道”,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论语·为政》中所言,“孝”就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庸》中:“事死如生,如亡如存,仁智厚矣。”由于民间传统文化的千百年来的心理影响与深厚历史地位,造就了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于是人们不自觉地用“孝”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表达对长者的敬与畏。
集中表现孝亲之道的是《红高粱家族》的高粱殡。在从传消息、定殡期、聚群众、设灵柩开始,到行三跪六揖九叩之礼,再到出殡,下葬等一系列礼仪使得整个殡葬过程充满了仪式化的意味。儒家认为“送死可以当大事”,于是强调在殡葬中的礼制化,通过这种隆葬厚仪来表现出亲人哀痛的心情。同时儒家以“孝”为基点,构筑其殉葬伦理思想,在对戴凤莲出殡的描写中鲜明地表现儒家思想对礼制的讲求,以表达孝亲之道,为之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2.灵魂不灭
孔颖达《左传》中写道:“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各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直承认灵魂的存在,人肉身死去后灵魂不死,这种灵魂观对民众来说是神秘不可琢磨的,所以民众首先对死亡及灵魂产生一种畏惧与尊敬。
《红高粱家族》中充满大量的对死亡、亡灵充满畏惧的描写,如:
奶奶的棺材在清晨明朗的光线里,显得狰狞可怖。原先覆盖着它的那层庄严神秘的紫红色已被火焰剥蚀,三指厚的细纱布清油被烧爆,像涂了一层凹凸不平的臭油。奶奶的棺材罕见的巨大,十六岁的父亲站在翘起的棺材大头前,虽然棺材只齐着喉结,但父亲觉得它高大无比,压迫得他呼吸不畅。
人们内心对死者遗体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的。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一面是对于死者的爱,一面是对于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 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这两方面似乎是合而为一,互相乘除的。这种情形,在当前行动的自然流露上可以看得见, 在丧礼的程序上也可以看得见,不管在尸体的装殓或处置上,也不管在葬后的礼仪或祭祀上,都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反感与恐惧同真诚的爱恋混在一起。”
其次,人们认为灵魂的世界与生者的世界十分相似。所以在生者为了让灵魂在它的世界过得更好,会准备丰富奢华的陪葬品、华丽的墓室来表达对亡人灵魂的告慰,希望它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上安逸的如人间一样的生活。在之后的日常祭祀中也会给逝者烧纸钱使其能够一直过着舒适的生活,也是生者和灵魂沟通的方式之一。如在葬礼上常见的纸扎、纸钱等,都是这一思想的映射。
三.中国传统生死观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讲求“和谐”。传统民间信仰主要追求人与宇宙、人与他人及人与自己三者间的和谐与圆满,而且人所面对的宇宙,即是自然(nature)本身及其现象。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基本社会组织是宗族,所以在传统中国中,“人”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人”。所以这种宗族社会与这种宇宙观是和谐的。
这种和谐的思想体系给中国传统生死观造成了很大影响。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中国传统生死观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随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根植在民众的脑海,成为了全民族的文化观。
首先,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所强调的永生是其道德功名精神被后人传诵而流传千古。从这个角度,死亡是生的延续,不仅仅是因为灵魂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死亡让生命得到升华。在《红高粱家族》中,英雄葬在高粱地的一幕幕正展现了精神得到的真正永生。传统社会强调入土为安。当英雄们葬在代表他们自由狂野精神的高粱地时,他们才真正得到永生。这种永生的意义不在于肉体的不朽,也不在于灵魂的不灭,而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神的永照后人。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重生死。重生强调的是宗族、群体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强调生育繁衍的目的。所以对于蛙和红高粱强大的生命力的膜拜是民众对生命永恒种族延续的渴望。重死既是对生的缅怀也是对灵魂的尊重,更是对再次重生的期待。死者已矣,肉体已死,灵魂成为先祖,保佑家族的枝繁叶茂。所以在这个角度看重死即重生。都是为了宗族生命的延续。
第三,中国民间文化强调生死循环,生死转化。肉体死亡后,灵魂转世得到重生。所以重死是对重生的期待。在《蛙》中“姑姑”与郝大手结合,制作一个个泥娃娃,为的是心灵的救赎,而这种救赎所展现的就是一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景象。
投胎降生是佛道两教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融合的文化概念。中国人相信轮回转世,所以这种生与死的转换是一种循环,灵魂不死,只为转世再生,生生死死永恒循环。
四.结语
《红高粱家族》与《蛙》展现了死与生的壮丽图景,这种图景来自长久以来经过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儒教将礼义仁孝带入了民间生死观念,源于人性本能的民间崇拜在民众的内心深深扎根,宗教的观念也随之影响了这种生死观念的形成变化和发展。传统的中国社会重生死,重生是因为对生命强力的渴望与崇拜,重死是因为对前人的追思以及对重生的期待。生死循环,死是生的延续。中国传统价值观追求“和谐”,生与死这一对看似永恒的矛盾,在中国民间社会中达到了平衡与稳定,因为“和谐”是传统社会追求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得以让社会稳定,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个人灵魂的永生在于道德和精神得到了永存;从社会群体来看,家族的永生在于超越死亡的繁衍生息。受到儒家思想和民间信仰影响深远的中国民间生死观就闪耀着这种人性的和谐光彩。
参考文献
1.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孔子.《论语》.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7
5.朱熹著,乔俊辰、杜玉珠译.《大学中庸孝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81
6.左浩坤、杜波.《生命的执着与死亡的否定——从中国传统葬俗看中国人的生死观》.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0).238-255
7.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28
8.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30
9.崔昌源.《中国古代丧葬仪礼结构之分析》.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第28卷.第三期.7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