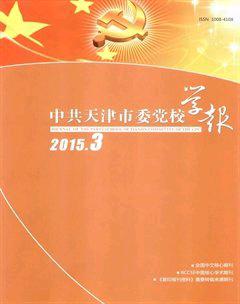走向多元融通之路:对公共行政学的批判性重构
[摘要]基于敏锐积极的反思性态度,批判性研究方法旗帜鲜明地表现为拒绝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否定主流意识形态和挑战社会现实。然而批判性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处于弱势且不够成熟的研究路径,由于过于强调其话语——理论方面,从而忽视了实际的研究与行动,造成实践在批判性研究中的失语状态。作为对解释性及诠释性研究的重要补充形式,批判性研究方法理应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中获得一席之地,并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生长点,以此促进公共行政学研究从一元导向走向多元融通的发展道路,进而影响中国的治道变革。
[关键词]公共行政;批判性研究;一元导向;多元融通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3007206
哈贝马斯曾指出,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模式可以被归类为三种典型形态:解释性、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就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而言,解释性研究是主流的研究类型,余下两种研究方法较受忽视。然而,正如怀特和亚当斯所说:“已有的历史和认识论证据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存在于公共行政的重要真理,即单一的研究路径并不足以解释公共行政中的所有问题。理性思维指导下的研究也需要实现研究途径的丰富化和多样化”[1](P14)。因此,在公共行政的知识增长及理论发展的过程之中,应该跳出固有的研究思路,运用多种方法。从逻辑上看,每一种能够增进公共行政知识发展的路径都应被赋予同等重要的地位。包括解释性、诠释性和批判性研究在内的三种途径,没有哪一种应该在理论构建或知识获取中被武断地去除。批判性研究致力于打破对经验规范的一般性描述,深化对研究对象在意义上的理解,并引导实践者意识到那些影响自己信念或行动的“无意识”因素,在此基础之上寻求社会改革,实现自我解放。从这个角度而言,发展批判性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批判性研究提供的知识和理论挑战社会现实,并不认同价值中立的行为,而是旗帜鲜明地在人类解放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社会科学领域,批判性研究逐渐被一些学者接受、重视与发展,而且已经涌现出一些视角独特、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相较于实证研究而言,批判理论与公共行政的联系比较少。为改变此种现状,十分有必要针对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进行审视和反思,梳理并分析批判理论的研究谱系与批判维度,这将帮助研究者们了解并深入认知真实世界的公共行政,挖掘隐含于公共行政背后的无意识因素,进而实现巩固和夯实公共行政合法性地位的重要目的。
一、公共行政学中的三种研究模式
如前所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三种研究模式——解释性、诠释性及批判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典型的诠释性研究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文学批评等内容。在批判性研究领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则是精神分析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批评。上述三种研究模式的逻辑是在跨越科学学科、哲学传统和人文学科的一系列辩论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比主流社会科学宽泛得多的关于知识及其使用的理论,并发展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代表性组成部分。每种研究模式都可以根据其目的和逻辑简要地加以界定。
在目前的公共行政研究领域,解释性研究模式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研究模式遵循的是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解释性研究试图构建能够解释和预测自然与社会事件的理论,理论的构建需要发展一套相互关联的并可以验证的法则,这些法则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控制自然事件和社会事件的最终目的,解释性研究的逻辑遵循解释和预测的演绎-法则模式和归纳-概率模式[2]。演绎性解释试图将事实置于法则般的概述之下,而演绎性预测则是用这种法则般的概述去预测特定事件的发生。马斯洛的激励理论就是演绎性的,因为它从需要满足的一般概述转向关于行为的特定结论。归纳性解释则运用统计学中的概率规则,说明在构成随机试验的某种前提条件之下,某种结果将会以特定的比率发生[3](P35)。当此前提发生后,它们为某一事件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的结论提供归纳性支撑。归纳性解释从对特定事实的观察转向对更大总体的推论。组织行为学的大部分研究采用归纳模型。例如,对影响某个企业工作满意度的因素的研究经常会被用于解释和预测其他企业的工作满意度[4](P116)。演绎模式和归纳模式都能够提供解释并使预测成为可能。解释性研究可以进行预测的事实说明,至少在原则上控制自然和社会事件是可能的。如果资源和技术许可的话,人们可以通过改变条件来促使或是阻止某件事情发生。解释性研究假定公众的行为就像是自然界发生的事件一样,具有秩序和规律性的特征,因此,可以将这些特征归纳起来,并预测其未来的行为模式。诚然,在科学或行政中,对事件施加控制的资源要素并不总是可获得的,也存在着技术匮乏的困境,但这并不能降低控制在解释性研究中的重要性。
诠释性研究则能够让我们对社会环境行动者的言行进行深度解读。例如,一个实证主义者可能通过检验对激励和职位设计的既有假设,来尝试解释为何一个特定的工作丰富化工作丰富化(Job Enrichment)是指增加垂直方向的工作内容,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有较大的自主权,同时肩负某些通常由其监督者来做的任务规划、执行和评估的工作。这可以使员工有更多的自由度、独立性和责任感去从事完整的活动,同时可以获得回馈以评估自身绩效,了解存在的缺失并加以矫正。项目未能提供预期的效果。而一个诠释主义者则会深入该情境,询问工人们对于该项目的想法、该项目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做。目的是发现该项目的意义;它与先前的规范、规则、价值和社会实践如何相符;该项目与最初对社会情境的界定可能如何冲突;还有那些新兴的规范、规则、价值和社会实践会是怎样的。诠释性理论希望改变学术研究者以及涉入社会情境的人们对于该情境的理解。诠释性研究的发展根基是现象学、诠释学和语言分析哲学,它致力于分析行动者身处某一社会情境的意义,以及给予自身及他人行为的意义。诠释的逻辑体现在研究的循环上,在对社会事件的意义进行解释时,诠释性研究着重于对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它特别强调在研究过程中进行比较和对照,对某一社会事件的理解是通过将之与已知某物进行对比而得到的。其基本逻辑是,事件整体可以对事件部分进行说明和解释,反之亦然。诠释性研究遵循循环往复的逻辑,而不是线性思考的单一逻辑。诠释性研究模式能提供更为全面的解释,在此基础之上探索和挖掘人类的潜力。来自于组织文化的研究就显示了诠释性方法对很好地理解组织中的规范、价值和信仰系统的重要性。endprint
批判性研究则是在调整和改变人们信仰和行为的基础上,引导他们意识到影响信仰和行为的无意识因素,进而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5]。它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努力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张状态。在批判性研究看来,理论的重要作用是去揭示这些隐含的冲突和未知,进而允许我们追求自身的自由,实现对现实情境的改变[6](P167)。或者说,通过批评,指明真实与虚假、善良与丑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驱使人类遵循真实与善良的行为准则行事[7]。批判性研究以不断自我反省为基础,进而与外界环境进行联系,反思自身的思想和实践[6](P182)。批判性研究的这种特质将人类引向某物并使之深刻地认识自我。这一点是对社会事实和价值开展判断工作的根基——发现社会事件并不总是表里如一,应该运用多个思路进行理解,卷入事件的行动者则应该考虑如何进行改变。换言之,在分析某一社会事件时,一旦认为它是真实或是善良的,就理应假设它可以与某些虚假或丑恶的事件相联系。缺少这样的联系,我们就难以做出批评性判断,而只能通过了解某人对某事的想法来判断。为避免这种问题出现,就需要搭建一种自我反省的关系类型。
批判性研究试图打破对经验规范的固化描述和对意义的单一性理解,引导人们寻求社会变革,并将自己从各种压迫性的约束中释放出来,进而满足自我需要[8](P16)。它强调研究者以强烈的批判意识和鲜明的批判立场对社会理论与实践开展批判性的反思。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也在积极寻求这方面的突破,闻名遐迩的公共行政学者登哈特指出,公共行政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要摆脱这种困境,则需要运用批判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反思。一些行政学理论家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迈克尔·戴尔蒙德在探索行政行为的精神分析模型时就采取了此种方法,克里斯·阿吉里斯和唐纳德·肖恩从批判的角度研究个体实践者和组织学习,吉布森·布鲁尔和加思·摩根针对公共组织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与反思,被后人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说明[3](P35)。可以说,现有研究拓宽了对批判性研究形式的认知与理解,因此也实现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启蒙和解放。
二、批判性研究模式:
基本特质以及为什么被忽视? 在开展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批判性研究有其自有优势,即以推动社会改革为己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而内化为自我革新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批判性研究能够提供不虚伪承诺“价值中立”的知识,并且态度坚决地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实现人类的自我解放[9]。在塞蒙特利和阿贝尔看来,这样的主旨组成了下列“批判特质”,并自始至终贯穿于批判性研究之中[4](P67)。
(一) 批判性研究模式:基本特质
1.对决定论的拒绝。批判性研究有异于其他研究路径,在对占据主流的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进行抨击的基础之上,批判性研究认为在人类事务中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决定论。批判性研究认为这些思维模式不仅没有反映及解释真实世界的原貌,而且还对现实世界进行了误读。批判性研究认为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思维模式忽视了“社会的”世界中蕴涵的人类历史及其制度。例如,在许多批判理论家看来,经济制度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利益、需要以及心理因素的一种外在表达,它并非无形之手的作用所导致的结果[10](P92)。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很多制度是被社会建构的,其合理性存在一定限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制度会不断调整,以细微渐进的方式满足社会个体的需要[11](P157)。
2.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否定。批判性研究认为,现实世界是在社会和历史的情境中得以构建的,基于此,压迫以及社会不公的结果必将出现[12](P228)。为此,批判性研究总是倾向于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否定。在对历史过程、技术理性、现代性、性别歧视等社会事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它不断对外表达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内在冲突。于是,公共行政批判理论的研究重点会比较着重于解构占据主流地位而且得到社会精英全力支持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行动方案及社会政治组织[13]。
3.对现实的挑战。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是批判性研究的本源所在。辩证思维提出,真理是存在于批判的过程之中的。而批判的首要之义就是自我批判,即通过对社会既定现实发起挑战,针对现实背后隐含的虚假进行反思,以便实现对现有状态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术研究者们希望在社会现实中挖掘出批判理论的潜在能量,并促使它们在实际行动中予以践行[14](P62)。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性研究需要既通过话语形式又经由实践行动才能实现[15](P34)。
(二)公共行政领域的批判性研究:为什么被忽视
由于深刻的智识基础、跨学科性、对社会的深刻分析等特点,极大地吸引了那些站在激进主义立场上的不满于现状的人们试图通过批判性研究去重释那些现象。由于承认现实的辩证复杂性,公共行政学研究者们因而能够运用批判性研究来认识现实环境下各种各样的权力、统治与控制的模式。但是,批判性研究并不是没有缺点。其最为持久而棘手的困境之一就是在批判性研究中呈现出精英主义、冷漠和过度智识化的趋势。可以感觉到,批判性研究由于过于强调其理论成分,而付出了牺牲实践的代价。自登哈特首次提出要发展公共组织的批判性研究起,距今已有三十余年。关于批判性研究的一些阐述,登哈特曾在许多著作中作过精妙绝伦的论述,并得到其他许多人的回应,然而,尽管这方面的文献还在增加,但公共行政的批判性研究依然还是“边缘化”的[16]。这是为什么呢?
1.由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发展而成的批判性研究与实践存在一定脱节。诚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开发批判工具和构建批判观点方面做出了卓越而富有成效的努力,然而,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理论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做出区隔,这使得其研究结论对于社会变革并无指导性意义[17](P119)。值得深思的是,这样一种方法,仅是纯粹的批判,而与实践没有明显的联系,总是被人们抱怨说它对现实无法产生任何触动,而该方法的初衷是要为现状寻求变化。与实践的明显脱节,为批判性研究带来严重后果。endprint
2.对于哈贝马斯的思想,后辈极为尊崇和追随,但是人们极少关注哈贝马斯还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哲学方向及其政治意义。在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中,我们能够十分清晰地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力,同时,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也为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提供了扎实的方法论基础和严谨的框架结构[11](P92)。在较晚的著述中,哈贝马斯尝试复兴理性主义的思想理念,提出很多具有“激进自由主义”(radical liberal)特征的重要观点,这在实际上与其早期论著的观点是相互背离的。哈贝马斯在其较晚著述中的这种哲学辩思更加符合美国自由民主的需要,但是它没有带来批判理论提倡的结构性变革。这是由于哈贝马斯只是打开了批判性研究领域的一扇窗户,提供了一种用于改变社会思潮和期望的辨别能力,但是没有提供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实践机制。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能够比较轻微地变革或修正现有状态,但这只能是一种停留于边缘的小打小闹。它无法在理论-实践的沟壑之外提供具有实用意义的方法,而仅能供应在社会现实中无法践行的抽象化的先验指标。
3.批判理论使理论和实际(即探索的实际行动)在研究传统中有效地联结起来。而在对批判理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认为它缺乏操作性。但是,要让批判理论不仅仅停留于思辨状态,而且能对公共行政实践发挥实质性影响力,则需要批判理论类似于某个领域的研究项目一样,具备一定的操作性特征。那么操作性意指为何呢?在实证研究中,操作性强调的是研究人员能够比较清楚地描述其分析对象是如何被界定、被测量、被研究和被评估的。操作性的优势是将理论、问题和实践勾连在一起,在此基础之上为研究者的经验研究提供参考性的分析框架。
当然,这并不意味批判性研究需要遵守实证研究的基本程序和规范。要取得切实的进步与发展,致力于发展公共行政批判理论的学术研究者需要跳出理论的圈层,与实践相结合,并且提供一些实际有用的替代性方法。否则,人们将无法自省,陷入无休止的迷思,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壑更是无法填补。举例论之,相较于不公平与压迫而言,公平与自由要好,这一观点虽然正确,但是无法给予人们切实的收益。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一条走向人类解放,获取公平、自由的路径和方法。正如扎内蒂所言,要想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需要在哲学层面的演练上继续努力,将真实世界中的实践代入进去,并为社会现实开出具有治疗意义的“处方”[18]。对此,马克思曾断言,“哲学不应该仅仅停留于理解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19](P145)。换言之,只有在批判性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成为一体的前提之下,人类解放才有可能实现[10](P92)。
三、批判性研究模式的新方向:参与式研究
从广义上说,批判性研究必须正视社会,呼应现实,进而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切实有用的替代性办法。在不断涌现的批判性研究方法的大家庭中,参与式研究格外值得注意。它最初产生于保罗·弗莱雷的大众教育实践,后来又受到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政治激进主义影响。参与式研究为批判理论概念的操作性提供了这样一种手段:它是更为紧密的联系实践的一种方法,如果操作得当,可以避免在理论建设的学术实践中落入激进思想的陷阱。
参与式研究与社会运动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由于参与式研究关注的是边缘化群体的权利,通过促进大众批判意识的觉醒,瓦解既有的统治秩序,旨在创造一个自立、自强、自决和自足的社会。扎内蒂指出,从具体的操作及分析过程上看,参与式研究遵循的基本思路具备极强的民主化特征[18]。其原因在于参与式研究将尊重被研究对象的经验作为研究者的重要职责,而非针对研究对象强制性地施加解决办法。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开展对话的结果就是将传统科学中主观-客观关系实现转换,构建成一种主观-主观的关系类型。在这种关系类型中,学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享有共同的知识,这导致双方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切地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并能够提出改革的建议和策略,从这个角度而言,参与式研究的重要意义就是在专业与经验知识之间重新构建起了一道桥梁[20](P184)。
博克斯也认为,在一些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领域,参与式研究已经有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公共行政学研究领域,这种批判性的反思方法则应用得比较少,从这个角度而言,该研究领域亟待加强这种研究方法的使用[16]。福里斯特曾经强调,变革的力量不应局限于研究者,公务人员、决策者都可以参与其中[21](P75)。在扎内蒂看来,在构建公共行政学的批判理论时,运用参与式研究有三大优势。首先,参与式研究可以发展包括学术研究者、决策者和公务执行人员在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可以集结形成一种变革的新生力量,通过与普通公众一起努力,学术研究者、决策者和公务执行人员可以共同了解并揭示存在于政治环境中的压迫、排斥和非平等关系。其次,依据参与式研究所汲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规避某些不良反应,包括针对公共问题所提出的工具式、技术统治式、专家式解决方案中的父权特性或者监护型影响[18]。换言之,参与式研究可以在主流实践之外贡献新的解决方案,而非仅仅停留于纸上谈兵,这使得批判理论能够成为具备真正实践目标的研究方法[13]。最后,参与式研究可以为话语理论提供其所欠缺的教育性和政治性因素,进而将对社会变迁有益的改革要素保存下来。
四、小结
毫瓦德·E·麦克科蒂和罗伯特·E·科利尔里在《为什么我们不能解决公共行政的研究议题?》一文对学位论文层面缺乏足够的研究工作表示了焦虑,并引用研究结果说明最近很少有论文“达到社会科学对谨慎、系统研究的传统标准”。与麦克科蒂、科利尔里的观点相同,马骏也指出,虽然二十多年以来,在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的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研究文献在数量方面已经累积形成一定规模,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我国的公共行政学学科在研究范式上仍然存在局限性,特别是批判性研究方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研究者的批判精神甚至是批判意识存在欠缺,这反映到研究质量上,则是表现为相关知识的重复但是缺少质量上的提升[22]。endprint
从这一点看来,要推进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应在充分汲取解释性和诠释性研究养分的基础之上,汲取批判理论的合理和有用成分,特别是要大力提倡批判意识,形成并拓展批判性研究的基本思路,构建针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总体性批判。批判性研究方法不应被遗忘于公共行政学发展的角落之处,而应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借此实现公共行政学研究知识的增长与研究品质的提升,进而促进公共行政学研究从一元导向走向多元融通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美]杰伊·D·怀特,盖·B·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郭小聪,肖生福.中西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建设比较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7.(1).
[3]戴黍,牛美丽,等.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Linda W.Chapin,Robert B.Denhardt.Putting “Citizens First!” in Orange County,Florida[J].National Civic Review,1995,(3).
[6]Denhardt,R.B.Theories of Public Organization[M].Wadsworth,1993.
[7]Denhardt,R.B.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Public Organization[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1,(41).
[8]马骏,叶娟丽.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吴月,赵小燕.从单一走向多元中的公共行政学批判性研究方法[J].社会科学家,2012,(6).
[10]Jürgen 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M].Beacon Press,1970.
[11]Jü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M].Beacon Press,1971.
[12]Jü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M].Beacon Press,1981.
[13]戴黍.公共行政领域中批判理论的特质、缺陷及其实践性尝试[J].公共行政评论,2010,(2).
[14]Herbert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M].Beacon Press,1941.
[15]Cheryl Simrell King,Camilla Stivers.Government Is Us[M].Sage publications,1998.
[16]Box,R.C.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aradox of Discourse American[J].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5,(25).
[17]Theodor Adorno,Max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M].Continuum,1944.
[18]Lisa A.Zanetti.Advancing Praxis:Connecting Critical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J].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7,(2).
[19]Marx,K.Theses on Feuerbach[M].W.W.Norton and Campany,1978.
[20]Yvonna S. Lincoln, Egon G. Guba.Naturalistic Inquiry[M].Sage Publications Inc,1985.
[21]John Forester.Critical Theory,Public Policy,and Planning Practice:Toward a Critical Pragmatism[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
[22]马骏.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责任编辑:张新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