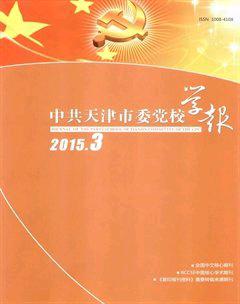互联网时代政治信任困境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曹峰旗
[摘要]政治信任具有明显的嵌入性,渗透在政治生态硬件要素之中。乐观派认为互联网改变了政治信任的主体与客体以及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而悲观派认为这是数字崇拜想象的产物,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乌托邦。互联网已经并将继续对政治信任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生态的结构。在互联网时代,可以从加强公民教育、建设透明的信息生态、加强网络立法以及积极回应网络危机等方面提升政治信任。
[关键词]互联网; 政治信任; 政治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5)03004107
信息是政治信任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作为信息传递重要途径的媒体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理应受到人们的关注。大萧条和二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使人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广播作为新媒体对于政治信任的作用。时间仅仅过了三十年,当电视成为新主导媒体时,有学者则认为电视媒体对政治信任具有负面的和反政府的特性。迈克尔·J.罗宾逊认为,电视起到了强化政治冷漠的作用,使公众与政府疏远[1]。而另一位学者帕特南对美国社会进行了三十年追踪研究,也将政治信任降低归咎于电视的影响[2]。
当我们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应对电视媒体时,互联网时代已经走来。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媒体生态正在发生急剧变革,互联网已经超越信息传播,成为表达、参与、互动渠道。在中国,互联网的使用有着较为强烈的政治性与新闻性特征,互联网越来越多地成为挑战与质疑官方声音的途径,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体制外政治参与的平台,如何理解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政治理论研究的深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拟从政治生态学视角,观察政治信任结构、探讨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以及培育政治信任的路径选择,旨在提供另一种对政治信任的认识视角。
一
政治信任一般被定义为民众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能够产出和他们预期结果相一致的信念或信心[2]。政治信任属于政治心理,而政治心理又属于政治文化。如果说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治规则是构成政治体系显性的“硬件”,并成为政治生态系统存在的基础,那么由政治态度、政治信念、政治情绪和政治价值等组成的政治文化则构成政治体系隐性的“软件”,成为政治生态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政治生态系统的这种构成特点,也决定了政治信任与其他政治文化一样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渗透在政治生态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各个硬件要素之中且具有明显的嵌入性,政治生态系统的显性结构不但是政治信任的载体,同时也决定政治信任自身的结构特点。
首先,政治信任主体。政治信任是政治生态要素间的一种状态,体现着环境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主客体信任关系。政治信任主体即政治信任发生、存在的载体,也就是施信者。政治信任主体首先应该是有产生与保持信任能力的个人。玛格丽特·莱维认为:“只有人才能信任或者去信任,但值得信任可以归属为个体或制度。”[3](P80)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政治中,都处于直接或间接政治关系之中,每一个人都是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因而每一个人也都成为政治信任的主体。显然,处于政治系统中诸如领袖、官员、公务员等个体也是政治信任的主体,但他们有着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作为社会人,他们可以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政治系统表达信任与不信任;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他们更多地是作为信任的客体,成为信任与不信任指向的目标。
政治信任主体还涉及一个问题: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能否成为政治信任主体?肯定观点认为,在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形成共有的价值、态度等心理特征,有共同的归属感与认同意识并进而影响行为方式,在政治信任方面也会形成共同的指向或投入,群体组织理应成为政治信任的重要主体。否定观点则认为,群体没有心理或思维的品格,无能力反思现实政治关系,因而不具有施信者的品格,不能归属于政治信任的主体[4](P41)。本文认为,群体与个体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是部分与整个关系,我们不能否认群众对个体的心理影响,群体共同心理的形成是以个体心理为前提的,二者有着一致性;但在学理与实证没有得到厘清之前,尤其是在群体心理学成熟之前,把个体作为政治信任主体更为稳妥,群体组织独立地作为政治信任的主体存疑。
其次,政治信任的客体。政治系统处于环境系统之中,而正是民众构成了环境系统,民众作为政治信任的付出方或者说是政治信任的供应者,体现着环境系统对政治系统的期待,也影响着环境系统对政治系统生态要求输入强弱以及要求输入的积极与消极。因此,政治系统构成政治信任的客体,承载着民众的期望,成为政治信任的客体。
然而,对于政治系统的内涵认识并不一致。政治系统论创立人戴维·伊斯顿把政治支持对象分为三个:“我把系统的三个相关联的方面视为三个基本的政治对象:当局(the authorities)典则(regime)和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5](P199)罗伯特·达尔则认为:“政治系统是政治关系的一套模式”,“让我们大胆地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和持续模式”[6](P1528)。无论如何表述,不难看出共性的东西:任何一个政治生态系统的核心都是政治权力,政治系统正是由权力编织而成的一种政治生态,围绕政治权力形成了作为政治行为主体的组织与个人、作为政治原则规范的制度与渗透其中的政治价值观,这些构成政治信任的静态对象。必须看到,政治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政治生态系统的生存、运动与发展的过程表现与产出结果同样也构成政治信任指向的客体。
第三,利益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原点,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关系是政治信任产生的动力。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就像生物基因决定了生命体必须首先满足自身需要否则就不能存续与发展一样,政治生态系统生命力则植根于利益需求的满足,没有任何利益追求的政治生态系统是不存在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某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7](P286)。信任是一种复杂和多维度的心理状态,一般产生于当个体处于一定的不确定性或困境状态下,是对客体的一种期望,认为对方不会有对自己不利的想法与行为,是“基于对另一方意愿或行为的积极预期而愿意接受自己处于不设防易受害境地(vulnerability)的心理状态”[8]。可以看出,信任产生于对自身利益安全的考量,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一种本能防护,在本质上是相信他人是否会侵犯自己利益的判断。因此,能否保全自身利益不但是政治系统生成的原因,也是信任产生的逻辑起点。endprint
政治信任作为政治生态的一种状态,是政治生态系统在自身功能与价值展现的过程中自身系统结构运行趋向合理性的一种表现,也是契合环境要素需求的结果。这种互动需要动力来推动与维持,而这种动力则来自于政治系统内部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张力,本质上来自于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张力。政治权利作为民众即政治信任主体利益需求的升华成为政治生态能量输入的源头,而政治权力即政治信任客体则必须对环境要求做出反馈性的输出,由此形成政治信任的动力机制。
第四,政治信任的沟通系统。政治生态系统的生命力植根于要素之间能量与信息的传递,如果说利益与信息对政治生命体如养分与氧气一样,那么政治生态的传送系统就是政治生命体的血液循环体系。政治生态系统存续与升级的过程就是环境系统与政治系统通过沟通体系把政治能量与政治信息输入与输出、刺激与反馈的互动过程,同时也是信任产生的过程,公民主要通过沟通系统尤其是大众媒介获得与政治体系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然后形成对政治体系的评价,进而形成对政治体系的不同心理评价:信任、不信任或政治冷漠。
在现代政治语境下,政治信任的生成有赖于沟通系统的信息生态平衡。政治信息影响着个体的政治信任,而传媒是现代公众获取政治信息的重要途径,公众需要依赖传媒提供的信息,适时修正自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所以政治信息内容与政治信息传送结构成为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假如政治生态出现信息的品质问题,如信息虚假泛滥,出现信息不均衡、不对称结构性问题,如信息垄断、数字鸿沟、信息荒漠化等,会导致政治生态的失衡,使政治系统功能紊乱,误导民众的判断,导致政治信任消解与转移。只有在信息开放、透明、平衡的状态时,才能为民众提供评判客观与真实的依据,让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判断变得可以预测,为政治信任的产生创造条件。
二
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说:“传播是工具,社会之所以称其为社会全赖这一工具。”[9](P1)从古至今,从造纸术、印刷术到广播、电视,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每一次新传播技术的出现都会极大地影响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刺激政治生态的升级,引发政治信任结构的新变化。以互联网为主导的现代信息技术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突破了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单向的、线性的信息特点,以数字化、网络化、交互式、个人化、压缩时间和空间的特点快速迎合了社会需求,催生了微信、微博、博客、播客等网络媒体以及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等新媒体。信息传播技术已经成为政治信任一个重要的生态变量,对传统的政治信任的生态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也是当前政治信任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
面对互联网对政治生态的影响,在理论界与现实中都出现了乐观与悲观两种不同的态度。乐观派认为,互联网技术催生了网络政治或虚拟政治,颠覆了以往政治信任形成的时空观念,改变了政治信任的主体与客体,因而网络时代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也发生了改变。在现实中,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性、直接性和普遍性打破了政治信息的官方垄断与控制,网络对权力系统的监督程度前所未有,这打破了传统政治生态的平衡,刺激着政治生态自我调适升级,公民也在为网络反腐的成效而欢呼,而官员网络恐惧症似乎也在印证互联网对政治信任提升的巨大潜力,折射着人们对互联网的政治期待。
第一,互联网影响着政治信任主体。政治信任作为一种多维度的心理状态,情绪与动机是重要的变量,有着非理性的特征,但政治信任包涵着认知的基础,理性判断是政治信任产生的主要条件,因此,政治信任主体的政治认知能力有着前提性的意义。一方面,互联网时代民众能更为迅捷地接触到更为丰富多彩的政治信息,为增强民众政治知识、总结前人与他人的政治实践、获取更多政治信息、拓展政治视野提供了可能,为民众形成政治认知、政治价值取向提供了条件,加快并缩短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周期,互联网时代意味着民众政治信任认知能力提高的可能。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媒体的开放性、互动性与平等性,有可能激发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也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的技术平台,表达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观点,体验政治生活,形成对政治体系的感知,调整对政治信任客体的心理预期。
第二,互联网影响着政治信任客体。信息时代网络以其公开、透明、快捷、影响面广的特性而获得蓬勃发展,社会环境系统必然对政治体系提出新的需求,而政治生态系统必须做出回应,优化政治生态结构、升级政治生态功能,形成新的政治生态,有利于构建政治生态系统与公众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关系。一方面,借助计算机和网络为政治系统降低运动成本与提高效率提供了条件。在新传播技术条件下,政治系统对于信息的收集、储存、处理与传递等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与经济,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更为直接,将程序性与事务性工作“搬进”或“搬上”网络,通过网络与社会互动,使政治系统对于环境系统的回应更为高效,网络媒体有助于政府管理与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另一方面,网络时代为舆论的凸显提供了可能,新传播技术的扩散与使用有助于环境系统对政治生态的“倒逼”压力,推动政治生态系统价值理念的转变,在功能上由传统的管制向以服务为主转变,在过程上由封闭向公开、透明转变,改善政治生态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张力,为被信任提供前提。
第三,政治信任沟通机制的影响。互联网使政治信息在方向上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递,传统媒体(无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的信息传递方向是单向的,不管是民意的表达还是政治系统的反馈,都没有克服主体与客体在时间上的同时在场与空间上规模范围的局限。互联网技术使时间与空间不再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信任不对称的局面,实现了对话性质主客体同时在场的互动,使直接监督成为可能,也使直接的民意表达与直接政治系统回应成为可能,传递渠道由间接转向直接。网络时代的政治信任传递方式更为直接、及时,这降低了传统媒体中间环节人为的影响,减少了变异程度。传统媒体在信息内容与范围上受到限制,有着比较明显的弱选择性特征,而网络时代传递内容由传统的单一转向多样,政治信息内容传播的公众话语权的强度越来越强,官方独霸话语空间的局面正面临被颠覆的局面。endprint
悲观者则认为,互联网带来的乐观的政治信任前景不过是数字崇拜想象的产物,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乌托邦。计算机科学家、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的结语中说:“我天性乐观,然而,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10](P267)互联网的匿名性、隐蔽性、发散性和随意性会给政治带来更多的不可预测性,很多学者对此也表示深深的忧虑。传播学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则更大。”[11](P7273)在悲观主义者眼中,互联网意味着政治生态的失衡,意味着怀疑甚至敌视,意味着价值观的混乱和危机,意味着对政治系统的认知失调,意味着公众政治信任的下降或丧失。
第一,互联网的信息泛滥会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互联网的开放性、便捷性与共享性的特征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方式,但也导致了信息泛滥,在互联网上组织、个体都可以自由、快速、低成本地传输政治信息、发表政治意见、表达利益诉求,海量信息带给民众的往往是无所适从、难以判断,使公众不敢轻易相信网上信息,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信任。正像萨托利所言:“就数量而言,问题大概不是信息太少而是太多了。”[12](P117)波斯曼也认为:“信息的失控、泛滥、猥琐化和泡沫化使世界难以把握。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可能会被无序信息的汪洋大海淹死。”[13](P7)
第二,互联网的虚拟性使网络信息真假难辩。互联网的匿名性、隐蔽性、发散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再加上互联网没有责任性,使其成为一些组织与个人牟取自身利益的工具。通过网络发布假消息、假新闻,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可靠性不易辨别和确认,使政治信息在民众面前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消解民众对政治系统的可预测性,导致对政治系统的不信任滋生。任意一条不实信息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都可能会对政治信任产生破坏作用。
第三,互联网信息内容的多元性引起价值观的紊乱。互联网的开放性带来了政治信息的多地性,这不但冲破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也突破了政府对媒体垄断的局面,加速了各种文化的传播、吸收和交融,使互联网成为多种思潮碰撞的空间。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网民不但有可能弱化现有的政治价值观、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还可能使个人主义张目、走向极端,并且模糊政治评价标准,降低对既有政治体系的认可。
第四,互联网的娱乐性引起政治冷漠。互联网功能日益多样化,其泛娱乐化功能也正在凸显,国内娱乐互联网的发展遥遥领先于商务网、政务网与企业网,网络游戏与绯闻八卦充斥媒体,娱乐成为网民在互联网上的直接动机。尼尔·波兹曼提出过警示:“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4](P4)这种现象不但会削弱一些人的政治信仰,使他们选择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距离、与政治渐行渐远,社会责任和主流价值观被淡化,政治信任为政治冷漠或犬儒主义让位,冲抵对政治系统既有的政治信任。
第五,数字鸿沟产生新的政治不平等。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的实质是区域间、组织间和个体间的信息差距[15]。这在政治领域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信息贫乏者被排斥在网络政治资源之外,与网络政治参与无涉,引起政治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网络政治诉求失声,大大降低了参与政治的热情;二是可能会导致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乏者的对立,不管是信息富有者话语权的主导还是信息贫困者不能有效地向政治体系输入利益表达,都会引发对政治系统的不满,政治体系可能失去认同与支持,消解政治信任。
三
现实中层出不穷的网络事件已经展现了互联网的威力,也使我们感受了互联网对政治生态的搅动,五花八门的网络反腐事件使我们见证了互联网对政治生态净化之魅力,但“郭美美”等网络事件也使我们感受了互联网对政治信任冲击的切肤之痛。
政治信任危机一直是困扰现代政治的普遍问题,把信任危机归因于互联网成为流行的普遍观点。然而,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质疑,认为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政治信任下降的关系并不明显。澳大利亚学者约翰·柯蒂斯与皮帕·诺里斯认为:“互联虽然改变了我们如何做,但并没有改变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行为取决于动机并不取决于技术的有效性。”[16]张明新、刘伟的研究结论是: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17]。
没有人会否认互联网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政治信任乃至中国整个政治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在政治信任方面,对互联网的过度忧虑与过度期待都不是理性与客观的态度。必须看到,互联网技术的影响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生态的结构,或者说没有改变政治信任的结构。在主体层面,政治生态环境主体亦即政治信任主体仍然是社会公众,网民在外延上并不是全体公民,政治性使用互联网的个人更不是全体公民,在内涵上互联网时代民众作为权利资格主体与利益表达主体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互联网发展并不意味着主体利益要求的自动实现。在客体层面,政治信任客体压力与机遇并存,但作为权力主体的地位也没有动摇,政治体系必须以自身的作为与绩效来回应民众的要求、接受公众的评判。在动力层面上,政治信任产生的根本动力仍然来自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动,网络的虚拟性并没有改变网络言论表达的现实利益性,网民对公权力的信任与否,都是现实政治生活的折射。在沟通途径层面上,网络信息的内容、传播的方向以及流量并没有完全摆脱权力的影响与控制,更没有达到无等级、无中心、无权威政治信息的流动,网络信息传播工具性价值仍然大于其主体价值。
我们不可能逆转互联网时代回到从前。当前我国面临着政治信任下降的政治生态压力,尽管互联网不是影响政治信任的决定性生态因素,但也不失是一个思考如何消解政治信任危机与提升政治信任的视角。endprint
第一,加强公民教育,增强政治信任的能力,培养政治信任的生态基础。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态语境中,政治信任已经不能像传统政治一样想当然地获得,传统社会民众对政治体系天然信任的基础逐渐瓦解,人格依附基础上的政治信任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生态条件。后传统社会政治信任映射的是政治系统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公众是评判政治系统的信任主体,公众的诉求与政治系统的作为、能力构成影响政治信任的基础与核心。然而,这种互动有赖于公民意识的存在,因为只有对权利和义务有自觉认知的公民人格才能真正形成良性的政治信任的生态环境,只有政治生活中获取更多、更精确政治信息才能形成政治信任的判断能力,才能对政治系统做出有效的回应,保证政治的良性运作,进而增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度。这样,公民教育就必然成为提升政治信任的主渠道,通过公民教育使民众的公民意识得以形成和充实,对政治系统和政治现象具有明晰的政治认知、保证政治心理健康发展才是生成政治信任主体与环境的根本之道。
第二,建设公开透明的信息生态是提升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现代政治生态人民主权的价值本质要求决定了政治系统公开透明的应然性,公众知情权成为其公民权利实现的基础,也是政治信息产生的直接前提。只有信息公开,民众才能充分了解政治系统、监督政治系统,确保其行为的可预期性,从而产生政治信任。互联网让政治系统的活动无所遁形,任何信息封闭与回应迟滞都很容易被公众误读,导致谣言滋生与矛盾激化,潜规则大行其道,引起信任危机。这在传统媒体时代如此,在互联网时代更加凸显,近几年发生较有影响的信任危机事件无不与政府在信息上的垄断性和封闭性有关。因此,建设公开透明、快捷回应的信息生态,这已经不是讨论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到的问题。如果在信息公开方面不能走出信息封闭的惯性,不能做到从被动到主动、从个别到全面、从单向到互动、从单一到多样、从滞后到及时,政治信任提升则无从谈起。
第三,加强网络立法、增强政府信息的权威性是提升政治信任的保证。作为政治平台,互联网正在显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生态功能。然而,互联网双刃性也如影随形,交流便利性与隐蔽性并存,知情权扩大与隐私权减少相随,理性的表达自由与非理性的表达任意同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私权利不合法表达与公权力异化越来越威胁着政治生态的秩序,进而消蚀着政治信任。因此,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加强网络管理、推进网络规范有序运行、保护互联网上合法的权利、规范互联网的公权力成为必然。一方面,通过立法加强对公权力的互联网行为约束,使网络管理有法可依,既要防止公权力不作为造成管理缺位,又要防止公权力任性与冲动造成的越位。另一方面,要通过立法防止个人与组织网络犯罪,惩治网络推手与“水军”,保护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与个人隐私权。我国网络立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明显落后于现实需要,存在着立法层级低、法律法规相互抵牾等问题。在立法过程中,探索如何在保证互联网有序运行与保证互联网活力释放,在公民权利保证与约束公权力之间找到平衡点与松紧度,这不但是政治生态建设的需要,也是提升政治信任的保证。
第四,积极回应网络危机是提升政治信任的重要契机。近几年如“周老虎事件”、“郭美美事件”、“瓮安事件”、“躲猫猫”等信任危机均由网络发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危机事件的高发、频发时期。网络危机的实质是政治信任危机,主要指向公共权力系统。现实中权力机构面对网络媒体放大与聚焦功能显得始料未及,实践也证明了无视、拖延、删除等措施的无效性,从众多网络事件可以看到一个共性:危机扩散与蔓延的原因恰恰是权力机构应变网络危机能力的缺失,根源是相关权力部门回应渠道不畅、回应速度较慢、权控媒体“报喜不报忧”、“以正面报道为主”,导致危机时信息缺席。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这样做无疑于自毁正面引导舆论平台的主导权、走入“塔西佗陷阱”(即当权力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使政治信任生态难以修复。也应看到,信任与不信任有着内在相通和可以转化的功能机制,信任危机也往往是政治信任产生的重要机遇,如果权力机构能够利用其互联网资源优势,及时对网络事件与公众诉求做出回应,以负责、真诚的态度公开信息、还原真相,表明政府态度和处理办法,满足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就能使公众理性和客观地看待事件,为重构政治系统与民众的信任关系提供契机,进而在新的高度上建设新的政治信任生态。
参考文献:
[1]Robinson, Michael J..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6,(2).
[2]Hetherington,M.J.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4).
[3]Margaret Levi.A State of Trust, in Trust and Governance[M].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8.
[4]上官酒瑞.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逻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5][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中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6][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8]Rousseau,D.M.,Sitkin,S.B.,Burt,R.S.,& Camerer,C.F.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A Cross–Discipline View of Trus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
[9][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0][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1]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2][美]乔·萨托利.新民主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3][美]尼尔·波斯曼.技术的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刘远亮.网络政治传播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基于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4).
[16]Curtice,P.Norris.Epolitics?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in A. Park, J. Curtice, K. Thomson, C. Bromley and M. Phillips (eds.),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the 21st report,London: Sage, 2004.
[17]张明新,刘伟.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J].公共管理学报,2014,(1).
责任编辑:何敬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