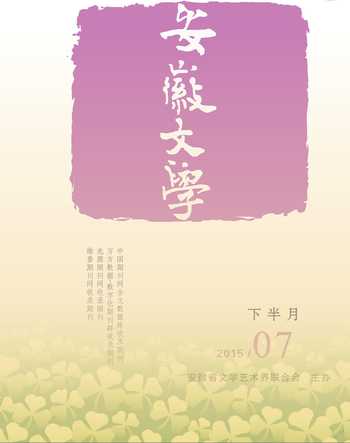琦善炮灰论
滕元慧
摘 要:琦善是清末有名的大奸臣,卖国贼,声名狼藉。他对政府缺乏起码的诚实,对外人不免卑屈,对敌方的认识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是一无所知,1949年后宣传中的琦善是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的汉奸形象。然也有很多史学家为其翻案,认为琦善卖国之罪名是言过其实。本文以《天朝的崩溃》为参考内容,提出琦善炮灰论的观点,分四点一一叙述:(1)琦善是道光皇帝妥协政策的执行者,是封建皇权的替罪羊。(2)琦善是封建忠奸理论的牺牲者,为中国旧体制承担责任。(3)琦善是主张妥协的代表者,是民族危机加深时为警世计的靶子。(4)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从人物的褒贬出发即批判琦善等人的卖国更容易解释鸦片战争的失败。最后,本文提出琦善是有先见之明和自知之明但无法摆脱传统的旧官僚的观點,并结合当下对琦善成为历史炮灰一事做出反思。
关键词:《天朝的崩溃》 琦善 炮灰论
一、琦善是道光皇帝妥协政策的执行者,是封建皇权的替罪羊
清朝封建皇权高度集中,是封建专制的顶峰时期。皇帝和大臣的关系类似于“主子”和“奴才”,皇帝掌握生杀大权,臣子只是皇帝命令的执行者。琦善作为钦差大臣,其一切行动都是向道光帝做了详细汇报并按照道光帝的指示去做的,虽然其中免不了有谎报、隐瞒、夸大其词等等,但是总的来说琦善只是道光帝的工具,并没有自主意识和权利,这也与中国当时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特点相符合。“如果我们再细心地核查琦善在鸦片战争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除在一些细小之处,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举动外,在根本问题上,他大体是按照道光帝的决策行事的,尽管在广东谈判的后期他过于执著而不惜于抗旨。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因此,妥协的责任,本应更多地由道光帝来承担,而不是由琦善来承担。”[1]15在皇权至上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皇帝多么昏庸无能,最终失败的罪责总是要臣子来承担的。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世人,出于思想的自觉,没有一个人敢把矛头对向皇帝,于是琦善这个执行者就成了替罪羊。所以说妥协的政策是道光帝定的,但是所带来的后果却必须由琦善承担,因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是不会错的。可以想象,道光帝主战之时,主战派将领在战场上失利,肯定也不会是道光帝主战的政策有误,而是将领们或者贪生怕死,或者指挥无方造成的。若道光帝没有罢免林则徐,而林则徐在广东战场上一败涂地,林则徐必定也要承担战败的责任。总之,为了圣上的“英明”,琦善这顶“卖国贼”的帽子是戴定了。
二、琦善是封建忠奸理论的牺牲者,为中国旧体制承担责任
奸臣欺蒙君主、陷害忠良、结党营私、施威作恶,被视为国运衰颓的根源。作者称之为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这种理论和模式,具有劝善惩恶的功能,又有掩护昏君昏聩无能的作用,屡屡被官僚士子们用来解释那些他们不能解释或不愿解释的历史现象。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战争中,英军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清朝使出剿灭、安抚的手段都无济于事,最后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中国割地赔款,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道路。堂堂天朝居然败在区区岛夷的手下,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也不能解释的事实。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影响深远,当时的中国人对英国一无所知,自然不可能从中英双方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对比中寻找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国人怀着不服输、不认输的心态,但又不能抑或是不愿去追究“圣明天子”和“天朝体制”的责任。于是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被用来作为战争失败的解释就十分方便可行了。“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夭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1]19于是,人们在不愿意触及中国传统体制的根本的情况下,让以琦善为代表的“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保全了中国的传统制度的地位,做了中国旧道统的替罪羊。琦善背上骂名的根源在于:天朝思维坚持旧路,被打败也不服输。
三、琦善是主张妥协的代表者,是民族危机加深时为警世计的靶子
“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并未中止,接连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更是欲灭亡中国。在这么一个世道面前,前期的士林学子和后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为警世计,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官员‘无不进行猛烈的抨击,对历史上的一切主张抵抗的官员,无不加以热情的褒颂。很明显,这一时期对琦善之流的批判,无疑是对当时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人们发出的警告。”[1]20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妥协—投降—卖国”的模式被大量地运用到历史领域,琦善也就从原来的“奸臣”,变成了“卖国贼”。琦善的角色变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一切向帝国主义妥协或投降之辈的敌视。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社会功能其中的一项,但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因个人的情感、主义的差别而无意造成的“将真迹放大”,此时在现实需要的驱使下,在“善善”“恶恶”原则的运用中,已经人为地将真迹尽最大可能地放大。借由批判琦善卖国来影射当时出现的妥协、投降的倾向,于是,琦善只能担了这个骂名,无可奈何地做了时代的炮灰。
四、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从人物的褒贬出发即批判琦善等人的卖国更容易解释鸦片战争的失败
纪传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以纪传体为正宗的中国传统史学,过多地注重了人物的褒贬。“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当归结于中国的落后与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前者从中国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解决起来十分困难,后者似更注重人物的褒贬,对策又似明快简单。”[1]24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对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多以琦善、林则徐的对立作为叙说的主线,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抵抗路线,与琦善为代表的卖国投降路线对立消长的两条路线斗争。人们更愿意相信是琦善这样的奸臣误国,也不愿承认天朝体制的缺陷,归根结底,是天朝思维坚持旧路,被打败也不服输这种思维渗透在了历史学的研究里。
五、琦善是有先见之明和自知之明但无法摆脱传统的旧官僚
从琦善自身的角度来看,他没有恶意卖国的动机和行为。琦善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和策略达到驱逐外夷的目的,妥协虽是一种屈辱,但至少是能减轻损失,将来未必不能再次恢复天朝的荣光。琦善本人的确已意识到中国面临危机,但这种认识时代背景和个人才智的局限未能转化为有效的解决措施。琦善虽能嗅到新时代来临的气息,但是无法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导致其视野的广阔性受到限制。就爱国热情而言,琦善并不输于林则徐或当时的其他爱国士大夫及官员,在他的奏折、言行中,也时时体现了自己对国家前途和战争形势的忧心忡忡,但最终得到的结果却离初衷相距甚远。琦善反对开战,是因为他看到了英夷的力量,他看到了中英军事差距太大几乎无战胜的可能。难能可贵的是,琦善在战时一改清朝官场普遍扬胜讳败,隐匿实情的痼疾,向皇帝报告当时真实的军事实力对比。琦善选择了一条办实事的路,从实际出发不惜违抗上意。抗旨的出发点也是因为认识到中英实力悬殊,且认为妥协会成功,并因而会减少清王朝的损失。琦善审察形势,权衡利害,知道中国无法战胜故致力于外交。同时,在明知军力不敌的情况下,琦善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维护中国的利益。
琦善的种种优点,也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个臣子的“优点”,他逃不脱自身的局限——他终究只是个封闭落后帝国的官僚。琦善只是传统封闭的中国一个无知傲慢的官僚,墨守“天朝”观念,对世界大势浑浑噩噩;使用舊官僚外交的技巧却弄巧成拙——用官场狡狯手段糊弄洋人却最终自食恶果,有旧官僚的务实却没有远见,没有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主动反思,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出任何有益的事。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而在19世纪险象环生的世道中,如此苟安只会将中国一次次带入噩难,是不值得推崇的。
六、以史为鉴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1]25《天朝的崩溃》把鸦片战争的研究推上了新台阶。书中提及的有关于对中国史学的看法,让我们深思,在其他民族战争的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是不是也存在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的影响? 是不是也存在“打肿脸充胖子”以及用假话、大话、空话自欺欺人的现象呢? 历史应是反映事实,莫让历史成了一种工具。再者,《天朝的崩溃》描述的古老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故事对当今仍有借鉴意义。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于中国足球,把皇帝换成体育总局主管,巡抚换成足协主席,球员换成士兵,民众换成天朝子民,把体制的缺陷说成是官员腐败和球员爱国拼搏意志不够坚强,你会发现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变化,我们还是需要一种突破体制的勇气。
参考文献
[1]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北京: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