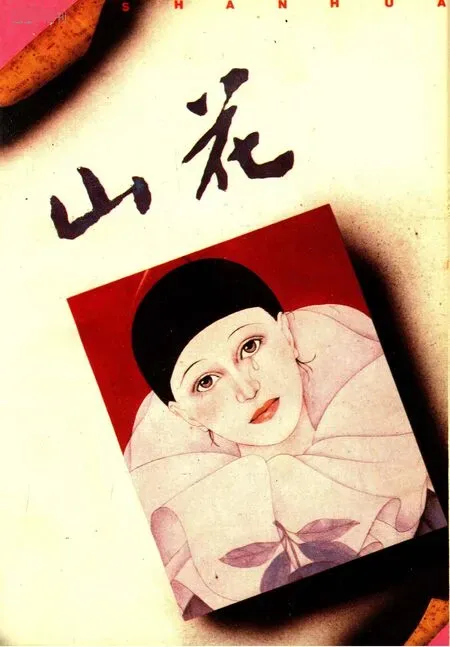港台地区艾柯研究综述
孙慧+张瑞玥
艾柯研究的早期阶段:传播与翻介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在其以中西诗学比较视野阐释文艺批评观点的《管锥篇》中,曾先后两次援引艾柯小说《玫瑰之名》做例证,一处是272页,一处是601页。钱钟书先生将艾柯小说置放于中西比较诗学视域中加以审视,为国内学界的艾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口益频繁,国内文化语境渐趋多元化,文学进入了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问,盛极一时的现代主义思潮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取代,具有鲜明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艾柯以后现代主义大师的身份进入国内学界的研究视野。一些港台学者如翁德明、耿占春等发现了艾柯并且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这些先锋学者的推动之下,艾柯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逐步风行起来。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往往是从翻介西方学者、学术思想的原典开始的,艾柯也不例外。港台学界开始接触艾柯,便是从翻译艾柯的小说入于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玫瑰的名字》便进入台湾翻译界视域,随后《傅科摆》《昨日之岛》等小说也被翻译过来,这股翻译热潮其势滔滔,一直没有停滞,不仅填补了大陆艾柯译介方而的留白还盘活了大陆学界的翻译现状,其中由作家出版社负责出版的艾柯三本小说都是参照台湾版本翻译而来。在台湾出版界,翻译艾柯作品的重镇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与台北市皇冠文化有限公司,艾柯作品在台湾的中译本几乎都出自其于,此外像台北市桂园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台湾究竟出版社等随之其后,壮大了艾柯作品出版的队伍。席卷台湾出版界的这股译介潮大大促动了艾柯作品在数量上领先于大陆。像艾柯新著《意外之喜——语言与疯狂》《丑的历史》等早己在台出版,而大陆学界这两年才有翻译出版的版本。而香港本土对艾柯作品的译介相对较少,相比台湾早期有翁德明的译著,同时期仅有杨孟哲和蔡孟贞等学者对艾柯小说和论著的翻译,香港学者对艾柯作品的翻译并不多,除了香港学者黄灿然对采访艾柯文章的翻译之外,其他译介作品罕有。1995年,香港学界引入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王宇根翻译的艾柯的《诠释与过度诠释》。此书在大陆有简写版本,较为遗憾的是,作者只是对艾柯就诠释问题展开的学术论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转述,但并未对其观点进行深入评析。
随后,1998年刊于香港文学期刊《素叶文学》题为《艾柯谈达里奥福得奖》的文章中介绍了艾柯有关戏剧文学与表演的看法,艾柯比较了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表演的福戏剧和由美国演员表演的福戏剧,他认为尽管戏剧上的表演是重要的,但戏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比戏剧表演本身更重要。文章虽没有全而展开论述艾柯的戏剧理论观点,但却提供了艾柯研究的新视角。
限于翻译现状,早期阶段的艾柯研究主要集中在介绍艾柯的学术思想观点方而。作为当今符号学界四大家之一的艾柯,其地位丝毫不亚于符号学泰斗级学者罗兰巴特。因而,艾柯研究者都不会逾越其符号学的扛鼎之作置若罔闻。
在台湾学界,艾柯研究总少不了年轻人的身影。淡江大学西洋语文研究所杨镇魁的硕士论文《记号迷宫:安倍托与(玫瑰的名字)中叙述方式及类别混淆之分析》,以安倍托·艾柯《玫瑰的名字》为研究对象,对小说进行了细致研读。论文探索了小说的叙述方式及主题之一“笑”所引发的类别混淆现象。此外,作者还分析了主人公威廉侦破案件的于法及推论,试图展现艾柯的符号学理论。
由于艾柯兼具小说家及符号学理论家的双重身份,使得小说在“阐释”的议题上呈现出颇具理论深度的哲思。国立政治大学黄涵榆的《诠释的竞衡: (玫瑰之名)研究》对艾柯《玫瑰的名字》进行了符号学、阐释学研读,分析了小说中文本互涉与对话论的概念,作者企图将艾柯小说置于当代理论背景之下,以期验证艾柯的小说与当代理论同等理论化,并试图得以检视小说与理论的界限。如张鸿彬的《乔叟、笛福、艾柯与网络文本交织问题》,从文学来源于现实而又高于现实的角度出发,较为客观地提出艾柯小说恰恰证明了文学不仅是自然、现实的模仿者,同时也能构建出与真实世界独立又依存,交织而重叠的虚拟时空。此外,还有一批优秀博硕士论文也在视察艾柯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之问的关系,如国立台湾大学康慧敏的《(玫瑰之名)与侦探小说的成规》,探究艾柯小说与传统侦探小说的共性与差异性,指出艾柯小说对侦探小说的创新之所在;国立中正大学杨哲铭的《建构后现代理论:后设小说与戏拟》则从“戏仿”文艺范畴入于,解析艾柯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苏中扬的《论安倍托艾柯(玫瑰的名字)中诠释、误解与翻译》是从诠释学理论出发,阐释艾柯小说中凸显出来的诠释学观点;中国文化大学谢幸纹《艾柯(玫瑰的名字)中的中世纪身体概念》则探究了艾柯小说与中世纪文学的关系。
不予置否,这些学术青年以“新出之犊”的胆识与“敢为人先”的精神为国内艾柯研究带来了一股青春新鲜的学术之风。这些学子的论文虽显稚浅,但无论从研究视角、学研方法还是逻辑思路等方而,都呈现出令人可喜之势,可以说,艾柯的学研地域得到了进一步延展与开拓。
与台湾学界相似,香港学界也是从关注艾柯符号学理论入于的,1990年,郭恩慈在《香港文学》第70期上,发表了《作者的死亡读者的诞生——接受理论介绍》,简要介绍了艾柯的读者反应理论: “文本”应放在语言学的层而上研究,经由接收者链接、聚合,才可能成为(文字)艺术的对象。“文本”本身足不完美的,接受者(即读者)才足真正的文本运作者,他接触到“文本”上出现的词字意义,作出自我的选择,并且在连续参照一连串既定的语法结构中认识及了解词句的用法及内容。
郭恩慈指出艾柯在他的阐述中注意到“文本”内出现的结构层次间的断裂及空白。艾柯称这“文本”中文字的“弦外之音”的复杂组织为“未名”。“未名”并不在文字的表意层上展现,“未名”组织正是使内容能被了解及实现出来的条件。由此,艾柯更进一步指出,若严格地界定,我们不能用语言学去研究传播学。读者必然依循他既有的文化、社会及学识的条件进行对“文本”分析才可能给予任何一个“文本”无穷的阐释。就读者与作者的关系而言,作者必须理解读者于阅读时的符号系统运作过程,以便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应该知道在哪个地方要带导读者,在哪个地方要给予读者自由地去解释他的文字的权利。艾柯指出,每一类型的文字都要求相应的读者,也会要求读者具有对应的符号系统的知识层次。例如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理想读者,应该是具备有极为丰富的联想能力,同时最好具有与小说读解相匹配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程度,否则可能就无法了解书中所展示的不同困难程度以及多层,歧义的众多符号/参考系统。
在郭恩慈看来,艾柯理论研究视点实则是读解“文本化”的过程,他的文艺批评理论是基于其符号学理论观点的延续与再阐释,因而其研究视角是关注文本阐释、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可以说,郭恩慈意识到了艾柯文艺思想的维度之一——文艺符号学理论的重要性,较为精炼提取其理论观点,但遗憾的是,在介绍艾柯理论观点的同时,并没有将其放置于艾柯文艺理论体系的宏阔视野中去关照,加之篇幅所限,给读者以语焉不详之感。
近期阶段的研究与拓展
随着国内学界对艾柯学术思想的逐步深入,近期阶段的艾柯研究,无论是翻译领域还是学研领域,都呈现出欣喜的成果。台湾艾柯研究队伍人数众多而且都是学术专业研究人士,像彭淮栋、翁德明、谢瑶玲、杨孟哲、林佩瑜等一批翻译界学者,他们肃谨的翻译态度、温婉适宜的译笔之风给读者以美的享受。2000年,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黄寤兰翻译的《悠遂小说林》,同年,谢瑶玲翻译的《玫瑰的名字》再版。随后,基本每年都有艾柯作品的译本问世,尤其是在2004年、2008年还形成了艾柯作品翻译的高潮,让人可喜。
台湾学界对艾柯思想的研究基本与西方学界研究步伐保持一致,研究视野也相对阔达,他们不是局限于艾柯思想的某一方而或者抓取某个范式去具象分析,而是将其置于人文学科系统中去审视与查勘。台湾辅仁大学张大春先生便是其典范,他不仅为艾柯小说的台湾译本写序,还在其作品《小说稗类》中细致阐释艾柯小说作品(见《将信将疑以创世——一则小说的索隐图》《不登岸便不登岸——一则小说的洪荒界》)。他认为在艾柯的小说中都存在着对一个主题的探索,这个探索在《傅科摆》和《昨日之岛》等中体现为对“被禁制的知识”的探索。作为符号语言学家,艾柯赋予小说丰厚的知识背景,让其呈现解谜般的符号推理过程,他将被宗教或政治打压、缩减或利用的“知识”这一主题融于叙事体例当中来,创造字句背后的隐秘信息,让读者产生新鲜感。他还指出艾柯惯于用“百科全书”式的态度和模式运用各种譬喻来将“符码的反复性”进行系统书写,知识渊博的角色存在于艾柯作品的每一处角落,对历史的解读并在虚构中重塑历史人物,让读者对知识产生敬畏感。张大春先生不是跳脱于文学作品之上而做纯理论诠释,而是置身于文学实践去革新文艺评论方法,显露出不同于其他研究者独特的文学品评姿态,引领了作家分析文本的新叙事风格与文艺论说方式。
被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艾柯,其思想以跨学科的综合性与复杂性见长,因而艾柯研究队伍较为小众,多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也就不难理解了,但这并没有让研究者们望其项背,只做高山仰止状,他们以孜孜不倦的研究热情持续关注着艾柯其人其作。据可查资料显示,以艾柯为研究对象的台湾博硕士论文将近二十余篇,数量虽不繁盛却也显现了艾柯研究者们学术探索的先锋精神。其中,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张玉燕的博士在《符号、知识与时空:艾柯四本小说中的迷宫》中,便以艾柯符号学理论观点为依托,探讨了艾柯在其小说中展示的认识世界与知识探索的三个过程,并以三种迷宫模式为喻进行剖析。可贵的是,作者试图还原艾柯小说呈现出来的符号学理论的三种思维模式,并以其差异为出发点解析艾柯文学作品,较为客观地探讨了蕴含在艾柯文学作品中的人文学科方法论的三种维度,进而以艾柯所推崇的开放式迷宫思维方法去剖析时空概念的演化,这无疑伸展了艾柯的研究视域。作为艾柯研究的砥柱力量,淡江大学与台湾大学也有质量较好的论文,如郑雅玲《(钟楼怪人)与(玫瑰之名)》将建筑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相结合,以建筑美学批评理论审视雨果的《钟楼怪人》与艾柯《玫瑰的名字》,创新了艾柯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艾柯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之问自由穿梭、随性转换的跨域能力,使其在美学、符号学、叙事学与小说创作等领域不断地追悉、研索,硕果频出。艾柯文艺思想丰富性深深吸引着研究者们孳孳不息地探寻,他们试图跟随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不同学科、不同种类和研究维度中悠游的行踪,以此解开其思想多样性与综合性的奥秘。
概而言之,港台地区艾柯研究者的专业性、研究视角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以及研究成果的丰硕性在国内学界一马当先。这些研究成果无论从某一视角具象研讨艾柯文艺思想还是将历时性研究艾柯文艺思想的心路历程,共时性研寻与其他学者学术思想的共性、辨比其差异性,都从不同程度上弥补了大陆学界艾柯研究的缺失。当然,目前港台地区研究成果还存在某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港台地区艾柯研究成果势必为大陆学界的艾柯研究带来灵动的学术启示,使艾柯研究成为西学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