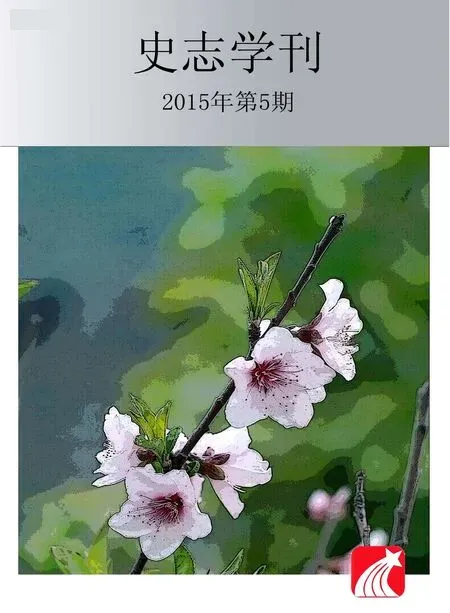张燧《千百年眼》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咸宁437005)
张燧《千百年眼》在明清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朱志先
(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咸宁437005)
张燧系晚明湘潭人士,曾著有《千百年眼》《经世挈要》等书,尤其《千百年眼》一书,万历四十二年刊印后,备受世人关注。明清时期,《千百年眼》出现多种印本及改名本,许多学人对其进行征引、评析及校勘。通过梳理《千百年眼》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及其接受情况,有助于学界了解《千百年眼》的学术价值。
张燧《千百年眼》明清时期
张燧,字和仲,湖南湘潭人,约出生于万历初年,卒于崇祯末年。曾著有《千百年眼》、《经世挈要》等书。其中《千百年眼》十二卷为张燧的读书笔记,从刊刻以后,自明末迄今,备受学人赞誉。明清时期,《千百年眼》的刻印本较多[1]朱志先.晚明张燧《千百年眼》版本述要[J].史志学刊,2015,(2).,甚至传至日本[2]朱志先.张燧《千百年眼》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J].史志学刊,2015,(4).。不少藏书楼收藏有《千百年眼》,如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等藏书楼书目中载有《千百年眼》一书。还有的藏书家对《千百年眼》进行评析,阮元《文选楼藏书记》言《千百年眼》“撮举经史之疑义者,分条辨论,断以己说。”[3]阮元著,王爱亭,赵嫄点校.文选楼藏书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P151)缪荃孙《嘉业堂藏书志》称张燧“读史有识,不为高论,亦不作模棱语。与陈眉公《狂夫之言》相类,中未见有忌讳语,而入之《销毁书目》,何耶?”[4]缪荃孙著,吴格点校.嘉业堂藏书志[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P385)明清时期,浙江、江苏、福建众多知名藏书楼对《千百年眼》的收藏,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藏书家对《千百年眼》的喜爱,也说明了《千百年眼》一书流播较广。通过梳理《千百年眼》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及其接受情况,有助于学界了解《千百年眼》的学术价值。
一、《千百年眼》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千百年眼》刊于万历四十二年,在崇祯年间刊刻的图书中已有对《千百年眼》的大量抄录或征引,诸如何详《史取》全书抄录《千百年眼》五十余个条目,邹泉《尚论编》征引《千百年眼》颇多[1]佚名.尚论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89册[Z].齐鲁书社,1987.。
《尚论编》中未有抄录者的真实姓名,仅题借绿轩录,印须子评《尚论编》七卷,刻于明代末年,属于史钞类。但抄录者不是杂乱无章的拼凑,而是以时间为序,自先秦迄宋代,抄录相关历史人物的事迹,均注明所征引文献之作者,主要有宋代苏轼、苏洵,明代杨慎、王世贞、李贽、陈继儒及张燧等,其摘录明代学者的相关著述为主,共261条,其中有27个条目注明是源自张燧之著述(其卷二“荆轲”条,当是他人之著,而误注为张燧)。钱茂伟曾言“崇祯年间出版的《尚论编》曾18次引用《千百年眼》中的话,说明《千百年眼》在当时确有较大的影响。”[2]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360)

明末刻本《尚论编》七卷征引张燧《千百年眼》一览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尚论编》的编纂者对《千百年眼》是比较熟悉的,除了没有征引《千百年眼》卷一和卷十二之内容,其余十卷均有征引,且分布于《尚论编》七卷的各卷。抄录者为便于体例统一,对于史事的抄录均以人物的名称为标题,故而在完整抄录《千百年眼》相关条目内容时,将标题皆作修改。抄录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辑录,达到“是编成而忠臣义士喜原心也”,“有功于世道人心”[1]佚名.尚论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89册)[Z].齐鲁书社,1987.(P663-664),即有裨于世用。因此,《尚论编》中仅有对《千百年眼》中相关内容的抄录,而未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有何评价。但是,从《尚论编》七卷中的内容源自《千百年眼》,足见辑录者对《千百年眼》之认可与喜爱。
徐(火勃)(1570—1642),《徐氏笔精》卷五“元章逸诗”:
近阅《千百年眼》载赏心亭一绝“晴新山色黛,风纵芦花雪。尽日倚阑干,寒宵低细月”。皆可补《志林》之缺者也。
按:徐(火勃)所言“近阅《千百年眼》”,其所阅内容见于《千百年眼》卷八“唐、宋逸诗赋”,说明徐氏读过《千百年眼》,且认为其内容可以补史缺。据《徐氏笔精·邵捷春序》可知《徐氏笔精》为崇祯壬申(1632)刻本。
方以智(1611—1671)《通雅》卷二十有文“张和仲云:东坡祖名序,故作叙,王介甫初字介卿,父名,盖故作。盖又曰老泉是子瞻号”,张燧之论见于《千百年眼》卷十“老泉是子瞻号”条,说明方以智当看过张燧之书。并且方以智对张燧之文予以补正曰:
按允明《嘉佑集》,十数年前有一老翁苍头白发,伛息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洵甃建亭而为之铭。《眉州志》老翁泉在蟇颐山东二十里,或允明时书其地名,而子瞻落款时亦偶书此地名耶。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舟”条有文:“张燧曰虞允文采石之役舟中踏车行船发礟”。《物理小识》卷八“器用类·火爆”条,有文:“张和仲记虞允文采石舟中发霹雳礟,乃纸为之,实以石灰硫黄坠水而火自水跳出”。《物理小识》中所言张燧之文见于《千百年眼》卷十一“采石之战有先备”条。
方以智《通雅》《物理小识》中皆有对《千百年眼》的征引,认为“学校、选举、赋役、兵屯、河漕、盐钱诸事,利弊时宜,贵知要领……《古论大观》《实用编》《学古》《适用编》《弋说》《千百年眼》《尚论》《快编》皆可折衷,指其偏礉拘胶之两病,以醒后人。”[2]方以智.通雅,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第857册)[Z].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29)
《千百年眼》以观点奇异为胜,多是对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的挑战。王夫之《船山全书·俟解》称“读史亦傅文之事,而程子斥谢上蔡为玩物丧志。所恶于丧志者,玩也。玩者,喜而弄之之谓。……近世有《千百年眼》《史怀》《史取》诸书及屠纬真《鸿苞》、陈仲淳《古文品外录》之类,要以供人之玩,而李贽《藏书》,为害尤烈,有志者勿惑焉,斯可与于博文之学。”[3]王夫之.思问录[M].中华书局,1956.(P1-2)
明代学人主要是依据万历刻本《千百年眼》,对其内容进行抄录、征引,诸如《史取》《尚论编》等书中大量抄录《千百年眼》的内容,对于《千百年眼》的传播颇有裨益。另外,明代学人从不同角度对《千百年眼》的评析,是明人接受《千百年眼》的具体体现。
二、《千百年眼》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
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千百年眼》被列为禁毁书目,浙江省第六次呈进书目中有“《千百年眼》十二卷,明张燧著(禁毁书),三本”[1]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M].商务印书馆,1960.(P120)。另外,在乾隆四十年五月三十日,及“安徽巡抚裴宗锡奏续查违碍各书遵旨解送折”中,指出“又《千百年眼》《李氏藏书》、《李氏焚书》三种,虽非野史,亦无悖逆诋毁之处,但立论诞妄,毁谤圣贤,甚有关于世道人心,应请一并销毁,以免贻惑后世”[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405-406)。乾隆五十年四月三十日,安徽巡抚书麟上奏的禁毁书的清单中即有“张燧《千百年眼》四本,全”[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P1935-1936)。
尽管乾隆年间《千百年眼》被列为禁毁书目,但此书仍为士人不辍读习。周广业《冬集纪程》中有文:
(乾隆甲辰正月)初二阅《千百年眼》,殊无甚好议论。王半山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惟书亦然。余岂不谅作者苦心,漫为菲薄乎?然欲上观千百年,非眼大于箕,未可易言。美名炫世,正恐不免。是书潇湘张燧和仲纂,明万历年人[3]国学扶轮社校辑.古今说部丛书(第9集第6册第2版).中国图书公司和记1915.(P51)。
根据前文汪辉祖《题冬集纪程四绝》中所言可知此文《冬集纪程》记述了周广业从乾隆癸卯(1783年)十二月十八日到甲辰(1784)年二月十五日的行程体会,或者说是日记。周广业在1784年二月初二阅读《千百年眼》,由此可知,尽管当时《千百年眼》被列为禁毁书,也屡次进行收缴,但在社会上还是有流传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当时已是收缴图书的尾声了,但周广业仍能阅读张燧《千百年眼》。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当时收缴违禁书的力度也不是很大,因为汪辉祖《题冬集纪程四绝》的落款是乾隆丙午,即乾隆五十一年(1786),对于周广业阅读违禁书的情况,王氏还评曰“独报闲情搜古义,惜阴心事卷中知”;其二,可以窥见以考据著称的周广业对《千百年眼》的评价不高,认为《千百年眼》“殊无甚好议论”,不过是“美名炫世”。有关孟子是否三年丧的问题,《千百年眼》卷三有“孟子不行三年丧”,系抄录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辩证类·孟子不行三年丧”,认为孟子未行三年丧。周广业《孟子四考》卷四有文:
孟子居母忧三年,非丧事不言,独充虞一答为丧葬,尽礼之大者,故记之。自齐至止嬴十一字该括数年行止。后人误认止为舍于逆旅。遂致异说纷起。有谓葬毕即求仕者。张燧《千百年眼》载许竹君曰:孟子劝人行三年丧,而其身乃不终丧于家。此说固谬。顾宁人谓为改葬。阎百诗谓终丧于家而后入齐为卿,并非[4]周广业.孟子四考(卷四).续修四库本(第153册)[Z].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P143)。
可见,周广业还是认真阅读了《千百年眼》,并对其中的论说予以批判。
也许是受乾隆时期禁书政策的影响,《千百年眼》在国内的流播一度受到限制,但此时期仍有学者对《千百年眼》的内容予以抄录,像法式善《陶庐杂录》、徐松《登科记考》、尤侗《艮斋杂说》等。
光绪十四年(1888),浙江王惕斋在日本铜版缩刊《千百年眼》传入国内后,随之出现几个不同的刊本:光绪二十五年龚氏石印本、光绪二十八年王增祺抄本、光绪二十九年成都三鹤山房刻本、光绪三十一年《重校本千百年眼》,甚者还有《千百年眼》的改名本《古今史要》及《四千年史论惊奇》。据胡玉缙所作校记可知《四千年史论惊奇》刊于1905年,另据王惕斋铜版缩刊本《千百年眼》卷十二“理财急务”条,前重复抄录了标题“理财急务”及“昔孔门三尺童子,羞称管、晏,而汉、唐以来,俊杰比肩,将相接踵,卒未闻有一人过”。而《四千年史论惊奇》一书,此处亦如此,可见《惊奇》一书乃源出于此本。众多《千百年眼》刊印本的出现,说明《千百年眼》在当时比较流行。光绪十五年所刻《湘潭县志》卷十言“《千百年眼》张燧撰,王船山时,《千百年眼》书盛行,后遂湮没,今始重刻于江苏”。众多《千百年眼》刊本的产生对于其内容的传播不无裨益,尤其是这些刊本中相关序跋对《千百年眼》的评介,更容易激起世人对《千百年眼》的阅读。
光绪十四年日本铜版缩刊本孙点《千百年眼跋》称张燧“读书好古,不求闻达”,在明末天下混乱之时扶桑东渡,随身携带《千百年眼》,并且与酒井藩主关系很好,颇具明代遗民的传奇色彩。评价《千百年眼》“网罗美备,持论尤极平允”,“洵杰作也”,但此书比较稀缺,“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孙点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颇具煽动性评说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界对此书的关注。
俞樾《古今史要弁言》言:
《古今史要》一书,明张仲甫先生之所纂也。网罗散失,渊博精详,因考据行其议论,远可追知几《史通》,近之则赵氏之《札记》,王氏之《商榷》也。原书本名《千百年眼》,久佚无传本,有友人以重价购自东瀛,将付石印,意犹豫,因贻书嘱予审定[1]张燧.千百年眼[M].光绪三十年重校本.。
按:俞樾此序可见于光绪三十一年《重校本千百年眼》,但落款为光绪己亥(1899年)。其中透露出两点意思:其一,俞氏对《千百年眼》评价较高,认为此书可与刘知几《史通》、赵翼《廿二史札记》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相媲美;其二,当时有《千百年眼》的改编本《古今史要》。
王承平《古今史要序》言:
是书为前明张和仲先生所著,上下数千年,碎玉零金,无美不备,原名《千百年眼》,其命名之意深焉矣。先生生于明末,遁迹扶桑,不求仕进。三百年于兹是书,乃得以由东岛而入中土,然则吉光片羽之幸未泯灭者,彼都人士珍藏之意可见,好古之意以可见矣[1]张燧.千百年眼[M].光绪三十年重校本.。
按:王承平对《千百年眼》的评析基本是沿袭孙点之说。
正是由于孙点、俞樾、王承平等人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的高度评价,使《千百年眼》在晚清及民国期间有了更多的读者市场。
1901年7月,蔡元培在其《日记》中载:
二十九日秋帆来,欲印《普通学报》,分八门,乞同志分任撰译,每期四页或二页,属元培任经学门。经学者,包伦理、论理、哲学,大约偏于理论者。致林少泉书,为译林中法令全书事。普通学书室购书:《化学定性分析》《白话丛书》、和文《论理学》《保全生命》《千百年眼》[2]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P180)。
清代王仁俊(1866-1913)之《西夏文缀》长沙刻本,刻于光绪三十年(1904)出自实学丛书[3]莎日娜主编.蒙古学金石文编题录[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P685)。王仁俊在撰写《西夏文缀》时曾参阅过张燧《千百年眼》[4]胡玉冰.浅谈清代学者王仁俊对敦煌学、西夏学的贡献[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2).。《西夏文缀》卷二“购夏竦榜”系源自张燧《千百年眼》卷九“夏竦不值一文”。
1906年《复报》第1期,有作者敌公“谭丛·张和仲”,其文为:
明张和仲著《千百年眼》,目无余子,壁垒一新,洵独具只眼。其论元世弊政,中有“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得则屠之,其残忍过曹操,命西层杨琏直珈,掘故宋诸陵,其贪暴倍项羽。”详哉言之!我谓此等举动,固异族入主中国惯用手段。宋之南渡,金虏掘宋皇陵。张焘言“金人之祸,上及山陵。”此实录也。又如清虏南犯,杀人几千万,其惨过于元虏。顾炎武羌湖引言“四入郊圻躏齐鲁破邑,屠城不可数。”然则十日杀三次,屠又何必扬州、嘉定耶?和仲适当其时,能无愤懑乎!彼故曰“士生斯世,何不幸哉!总之,夷夏倒置,已是古来未有之变局,何论其他!”呜呼!何其沈痛乃尔耶!彼读之而不动心者,果何人哉[5]敌公.谭丛·张和仲[J].复报,1906,(1).!
敌公论述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国所采用的屠城政策时,灵活运用了张燧“元世弊政”条,且认为张燧所论可谓“详哉言之”,以至于感叹“彼读之而不动心者,果何人哉!”
另外,在晚清《千百年眼》还有一部改名本,即《四千年史论惊奇》[1]佚名.四千年史论惊奇[M].光绪铅印本.。胡玉缙在校勘《四千年史论惊奇》时,多有批注及校勘,且《四千年史论惊奇》就是以光绪十四年铜版缩刊本《千百年眼》为底本的改名本,但未署名作者。通过胡玉缙的校记可知此本刊于光绪乙已(1905年),胡氏可谓系统批阅了此本,批注有墨批,有朱批。在批注位置上有眉批、夹批。胡玉缙认真批阅、校勘《四千年史论惊奇》的过程,实际就是其接受《千百年眼》的过程。
胡玉缙对《四千年史论惊奇》的总体评价为“是书明人张燧著,原名《千百年眼》,大都翻案文字,虽有过当处,而精核语甚多。此刻易其书名,并没其姓氏,坊贾之妄,一至于此,可恨也。玉缙记(以上为竖批)”。胡玉缙首先判定了《四千年史论惊奇》的作者及其本来书名,充分展现了这位考据家之博学,另一方面也说明胡玉缙对光绪十四年铜版缩刻本《千百年眼》比较熟悉。
胡玉缙对《四千年史论惊奇》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相关条目内容予以评析或补正。《四千年史论惊奇》卷一“夷、齐辨”条目上面有墨笔眉批:“刘大櫆《海峰文钞》有读《伯夷传》一篇,大意因此以为迁于伯夷,独增其传,曰之三言,迁亦故存其言,未必深信其事。”卷三“吕不韦之愚”,《惊奇》本此处有朱笔眉批:“李斯为不韦门客,《吕览》之成,斯其有力,斯得荀卿之传,故多礼说耳。”卷四“古文多譬况”,《惊奇》本此条有朱笔眉批:“此条孙秣陵附会。”卷四“古书之伪”,《惊奇》本有朱笔夹批:“《三坟》《三略》《六韬》《子华子》皆伪书,余或后人有羼入语。”卷七“阿堵”,《惊奇》本有朱笔眉批:“‘阿堵’犹这个也。”卷八“《周易举正》”,《惊奇》本此条有朱笔眉批:“所举各条均不见利不动与集解本所载虞法合,余皆不合,但取其文,汉字顺易于解说耳。《提要》云王祎手札不可信,并唐郭京之名亦在有无疑似之间,信然。”卷九“寇莱公奢俭不同”,《惊奇》本此处有朱笔夹批:“案此事益阳胡氏论之甚平允,见子《弟子箴言尚节俭门》。”卷十“宋乐屡变无成”,《惊奇》本此条有墨批:“《宋史·乐志》蔡京主魏汉律之说。”胡玉缙的批注多则近百个字,少则几个字,基本上体现了他对《惊奇》内容的理解,甚者在批阅卷八内容时能与卷九的内容联系在一起,足以证明胡玉缙对《千百年眼》的内容是非常熟悉,达到了触类旁通之效果,此亦是其接受《千百年眼》之效果。
其二,勘误《惊奇》刊刻之错谬。胡玉缙读《惊奇》很仔细,进行了详细的批阅校改。《惊奇》本误刻处甚多,胡玉缙在阅读时,直接予以校改处很多。如《惊奇》卷二“曾点二事俱不类”,本此处为“岂所谓状者之过耶”,胡玉缙径改“状”为“狂”;卷三“孟子性善无定论”,《惊奇》本此处为“表石公曰”,胡玉缙径改“表”为“袁”字;卷三“孟子不尽信《武城》”,《惊奇》本此处为“城”,胡玉缙径改为“成”字;卷三“孙叔敖碑考”,《惊奇》本此处为“优孟鲁许千金贷吾”,胡玉缙径改“鲁”为“曾”字。胡玉缙校改处,均为《惊奇》本误刻。
校勘学家胡玉缙对《四千年史论惊奇》(《千百年眼》)的评注及校勘涉及到该书各卷,足以说明胡玉缙对《千百年眼》是颇为重视的,其评注、校勘的过程亦是其接受的过程。否则,作为一代知名学者不会花费这么多精力去辨伪、批注及校勘一部明代笔记。
明清时期,《千百年眼》一书的传播,是通过多种途径,主要表现在对其的刊刻上,产生了不同印本,如光绪二十五年龚氏石印本、光绪二十八年王增祺抄本、光绪二十九年成都三鹤山房刻本等;甚者对《千百年眼》进行改名出版,如《古今史要》、《四千年史论惊奇》,足见《千百年眼》一书在当时是广为传播的。对《千百年眼》接受的形式是以抄录其内容为主,说明这些学者是认可《千百年眼》之内容,同时又通过自己的著述,使《千百年眼》得以再传播。其间亦有少量的评析(像胡玉缙进行系统批注的较少),褒贬不一,褒者认为其可补史料之阙,“壁垒一新,洵独具只眼”等;贬者则认为其“立论诞妄,毁谤圣贤”,“美名炫世”。
(责编:高生记)
朱志先(1976—),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代史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2YJC770079);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史源学视野下张燧〈千百年眼〉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1LW 01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