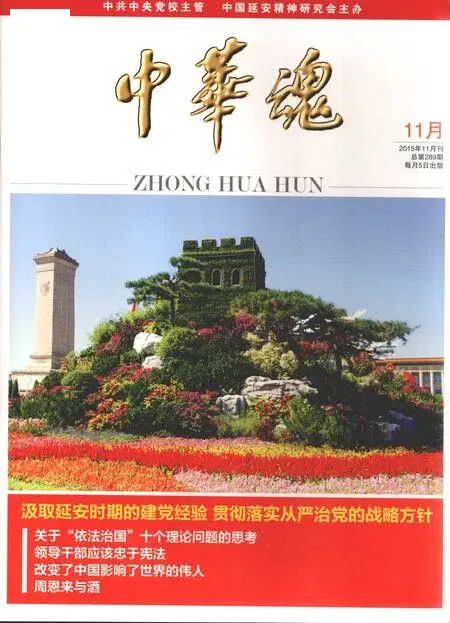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话史识史德
文/孔见
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话史识史德
文/孔见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被任为太史令,故在《史记》中以“太史公”自称。他作《史记》时,在每篇传记的最后都加上“太史公曰”,进行点评,发表自己的议论。这成为古代写史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种传统。如《汉书》为“赞”,《后汉书》为“论”,《三国志》则直书“评”,其他或为“述”、或为“议”,等等不一,都以这种形式发表史家自己的看法。有的还在历史的叙述中加以点评式的议论,也算是夹叙夹议。这些文字,有的反映了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对人物的褒贬,对历史事件的是非议论;其中也不乏取媚、诽谤或掩饰之笔,使一些历史人物遭到了歪曲,也使一些史事更加扑朔迷离,真假难辨。但应当肯定,司马迁的“太史公曰”,是很有生命力的、批判性的专评,使叙述的历史更加灵动;对人物的是非善恶的评析,也表现了作者非凡的历史眼光。
作为历史学家,贵在秉笔直书,重在掌握史料,并能够依据史实作出正确的叙述和判断,这是检验其史识史德的重要标准。司马迁青年时期有博览群书和实地考察史迹的经历,他继其父为太史令后,又以五年时间整理先人之旧闻,即其父的遗稿,并勤奋阅读皇家石室金匮之古书,有了相当充分的知识和史料准备,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42岁那年才开始编写《史记》。司马迁卒年约为60岁,大致在这10多年时间里完成这部52万多字的巨著。他在《自序》中表达了编史是以《春秋》为志向,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也就是说,他著史是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来说,这种治史的志趣是十分高尚而有见识的,是值得后人称道和钦佩的。
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曰”的评议中,就表现了这种史识史德。他在这里,确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独立人格,“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敢于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评论,自成一家之言。他不但批评前朝诸如秦始皇、秦二世的暴政,而且对当朝君王的评议也时有微词。如在《吕后本纪》中评议吕后时说:“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表达了对这个女人夺位专权的不满。他在本纪中有吕后而缺惠帝,也包含了这一层的意思。吕后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女人,刘邦死后,其子惠帝继位,但大权掌握在吕后手里。吕后把刘邦宠幸的嫔妃一一折磨处死,像戚夫人被砍去双手双脚,扔在厕所里,称为“人彘”。惠帝看到这种惨状后,病了一年之久,从此荒废政事。所以对吕后,司马迁是加以贬斥的。而对汉武帝,作为臣子的司马迁也敢于大胆批评,他对武帝频繁使用武力征讨一事加以谴责,认为“因勤远略,使得天下萧萧然,民穷财竭”;而对武帝晚年为求长生不老,迷信鬼神,求助巫术,也讥讽有加。他在指点评论历史人物时,不但敢于赞美同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而且对当时诸如韩信、黥布一流的失败英雄,也表示了惋惜之情。司马迁在人物评议中,无论是诸侯还是卿相,凡是佞幸之徒及酷吏,都加以鄙视和斥退,而对于草野豪侠之士,则极为赞美。如对游侠,就称赞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曷可少哉。”司马迁的这些言评,表现了十分鲜明的是非观念和无所畏惧的品格。
由上可见,司马迁作为一个古代的史学家,能够垂范后世,不是偶然的。正确对待历史,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史德史识的修养,是一个历史学家必备的条件,二者不可偏废。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人民。一个正直的史学家,应该仰无愧于先人,俯有益于来者。那些戏弄历史、亵渎历史的人,实际上是对自己人格的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