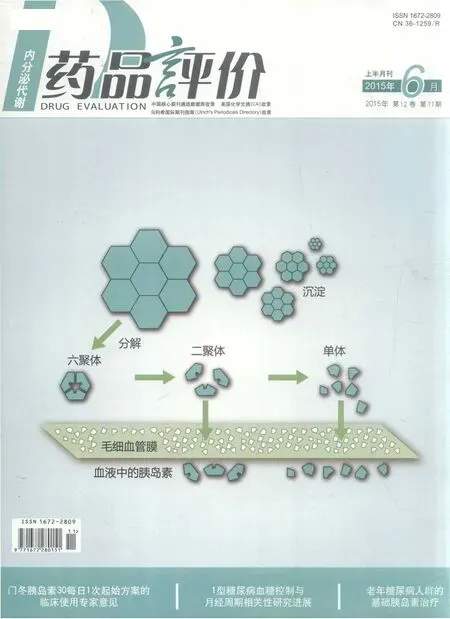绝经综合征的激素与非激素治疗
北京积水潭医院 赵芳 孙丽芳
孙丽芳 北京积水潭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硕士学位。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8年,特别在妇产科危急重症抢救以及妇科肿瘤、妇科内分泌疾病、盆底器官脱垂等疾病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现为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妇产科学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生殖学分会委员,《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中青年审稿专家、《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特邀审稿专家。
绝经是妇女生命进程中重要的生理过程。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医疗技术不断更新,妇女的预期生存年龄明显增加,使越来越多老年女性经历更长时间的绝经时期。多数女性约三分之一的生命在绝经期度过。绝经后卵巢功能衰退所致的内分泌失衡和雌激素缺乏产生一系列绝经相关的问题或疾病,如潮热、出汗等血管舒缩功能异常,泌尿生殖道萎缩,以及后期出现的绝经后骨质疏松、认知功能减退等严重影响着广大中老妇女的身心健康,从而降低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因此,越来越多的绝经问题引起多学科专家的关注。激素治疗(hormone therapy,HT)能迅速有效地解决绝经症状,尤其缓解血管舒缩功能,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治疗手段[1],至今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虽然人们对激素治疗的认识经历道路坎坷,对其使用“利”与“弊”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对激素治疗的认识逐渐上升、更科学、更接近其本来面目了。有必要对绝经期妇女的健康问题采取多学科、多层次的综合干预管理,使个体在激素治疗中最大获益,最小风险,个体化选择药物及方案。在“窗口期”内、无激素使用禁忌证的患者给予激素治疗;对于有禁忌证,或接受激素治疗有顾虑的女性,给予治疗血管舒缩功能的选择性 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中药植物药、植物雌激素以及治疗骨质疏松的双磷酸盐等其他非激素治疗。
激素治疗
1. 激素治疗发展史
绝经预示着妇女生殖能力停止,是指女性在卵巢功能完全衰竭之后出现的月经永久性停止,是正常女性的生理现象。围绝经期综合征指在围绝经期由于雌激素水平波动或下降所致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心理、神经症状。绝经激素补充治疗是针对女性因卵巢功能衰退性、激素不足所导致的健康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的临床医疗措施。曾有几个与其相关的名词,如激素替代治疗(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激素治疗(hormone therapy, HT)、雌激素治疗(estrgen hormone therapy,ET)。目前,2013年国际绝经学会的最新指南[1]中采用了绝经激素治疗(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MHT),不容易引起歧义,相比其他几个提法更准确。
1942年,结合雌激素作为第一个应用于绝经激素补充治疗的药物正式上市,由于有效地缓解绝经症状,被认为其可以推迟、解决一切女性老化问题。在今后的十多年,HT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迎来了第一次高峰。单一使用雌激素而没有孕激素对抗的结果是导致子宫内膜增生过长,子宫内膜癌增多,导致其进入第一次低谷。20世纪80年代,孕激素的应用成功地应对了子宫内膜癌带来的负面影响,连续联合应用解决了周期性阴道出血,迎来了HT的第二次应用高峰。各学科的大量的研究发现,HT防止老化,解决血管舒缩症状,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心血管,改善认知能力。这个高峰维持了近20年,ET甚至作为冠心病的二级预防被列入指南中。但是,英国“百万妇女研究”结果显示,HT增加乳腺癌风险、随后引起轩然大波的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女性健康启动项目(women's health initiative,WHI)[2]。WHI是目前唯一的一项评估绝经后妇女使用激素补充疗法的益处和风险的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研究,该研究发现雌孕激素联合不仅不会对冠心病有预防作用,反而会明显增加脑卒中、静脉血栓风险,总体健康危险大于获益,使得研究在进行到5.2年时被迫中止,HT治疗再次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2. 正确评价妇女健康研究
近10年来,对HT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对WHI研究的再分析成为科学审视HT治疗最重要的部分[3,4]。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WHI研究结果与早期大量的对照观察研究如护士健康调查等研究得到的结论大相径庭,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①WHI的失访率过高,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失访率达到42%和38%;②纳入研究对象的年龄63岁(50~79岁),年龄跨度较大,多数为绝经晚期的女性,相当一部分人在试验之前曾用过雌激素;③个体基础病理状态不同,有的具有心、血管高危因素;④研究试验的用药途径和用药种类单一。而这些因素均与MHT的某些结局存在一定的相关性[5]。随着更多的理论证据的不断积累,对MHT治疗的认识更科学、更接近其本来面貌了。如何科学应用MHT,使收益最大,风险最小逐渐成为专家的研究热点。
对激素治疗的认识也是跌宕起伏,尽管WHI研究以后美国与欧洲在MHT领域曾经有过比较大的分歧[6,7],但从2012年底到2013年初,在国际绝经学会(international menopause society,IMS)的倡导下,国际上绝经领域的各主要团体进行了充分论证,达成共识,并两次更新指南[8]。2013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在2009版中国指南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9,10]。目前,基于MHT的主要争议点已达到共识。
3. 治疗时间窗
时间窗即合适的最佳治疗时间,是2007年IMS提出的概念,也称雌激素应用窗口理论,是指MHT应尽早开始。在治疗窗口期围绝经期,也称窗口机会期,即60岁以前绝经10年以内启动获益更多,长期使用可以保护心血管、降低糖尿病风险、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其他心血管风险。如果未在窗口期启动而在绝经晚期使用,不仅获益很小,甚至可能增加某些风险。研究结果和最近观点都证实了这一理论,2011年IMS提出MHT在窗口期应用除了保护心血管系统外还可以改善认知,保护神经系统[11]。2013年更多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佐证了时间窗理论。
4. 绝经激素治疗的利弊
关于绝经激素治疗的利弊问题的讨论永远是绝经领域研究的热点,MHT对健康的若干环节都有影响。总体的获益尤其对于<60岁或绝经10年以内的女性,MHT益处远大于风险。MHT的益处属于A级证据的有缓解绝经相关的血管舒缩功能,缓解泌尿生殖道萎缩,防止骨质疏松。具体来讲,MHT是缓解绝经症状(如血管舒缩症状、泌尿生殖道症状及与其相关的睡眠障碍等)的首选和最重要、有效的治疗方法,适用于任何年龄的女性。MHT是预防绝经骨质疏松的有效方法之一,包括有骨质疏松症的危险因素(如低骨量)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推荐在窗口期[12]使用标准计量的雌激素可降低冠心病发病率和全因死亡率,但雌孕激素联合治疗的证据不足[13]。
丹麦骨质疏松症预防研究(Danish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study,DOPS)是一项多中心、开放、随机对照试验,其目的是研究长期MHT对绝经近期启动MHT的妇女心血管结局的影响。尽管样本才1006例,但其针对绝经近期启动MHT的妇女,研究时限长,其中随机对照部分长10年,随诊长达16年,失访率低等,其结果很具说服力。DOPS发现MHT显著减少了妇女的总体死亡率、心力衰竭或心肌梗死率,同时并不增加乳腺癌或中风发生率。
MHT治疗的不良反应集中在静脉血栓风险、缺血性卒中和乳腺癌、卵巢癌及肺癌风险方面。具体来讲,窗口期使用MHT治疗,冠心病风险明显降低。对于深静脉血栓和卒中,风险级别均属于罕见级别。口服激素治疗会增加发病风险,但小于60岁的窗口期使用绝对风险非常低。对有深静脉血栓或卒中高风险的患者,经皮治疗风险明显降低。乳腺癌的发生为复杂问题,风险与孕激素使用有关,而不是雌激素,主要与孕激素本身及其种类选择相关,也和应用时间有关,天然或接近天然的孕激素更安全[14],乳腺癌的风险在雌孕激素联合使用3~4年后开始增加,绝对风险罕见。源于MHT治疗的乳腺癌发生风险低,停药后风险下降。已知患有乳腺癌,禁用MHT。肺癌和卵巢癌风险级别属于罕见或非常罕见。
由于个体差异不同,个体年龄、绝经年限不同,雌激素水平、个体对性激素的吸收利用和代谢的不同差异,靶器官组织对性激素的反应性,存在的健康问题及严重程度,对HRT的意愿和依从性等,使得 MHT的风险既有共性,又有个体差异[15],强调个体化评估风险。
5. 激素治疗方案和药物选择
MHT方案选择应从女性生活质量、健康优先、个体风险因素等方面考虑,药物选择应遵循最低有效剂量、天然、短效原则。
5.1 方案选择
5.1.1 单用孕激素 单一孕激素方案适合围绝经期妇女,是首选治疗方案。围绝经期卵巢功能下降初期雌激素水平并不低,周期使用孕激素可以避免内膜过度增生保护子宫内膜,调整月经紊乱和阴道不规则出血。
5.1.2 单用雌激素 适用于已切除子宫,不考虑保护子宫内膜者。
5.1.3 雌孕激素周期序贯 适用于有子宫、有MHT适应证、已经进入绝经期体内雌激素水平低,单用孕激素不足以撤退性出血者。该方案适用于年龄较轻、绝经早期、有来月经愿望的女性。每周期连续服用21~28d,停药后出现撤退性出血,进入下一周期。目前,除了有戊酸雌二醇和地屈孕酮配伍使用,还有应用广泛的复方制剂,如克龄蒙、芬吗通等。
5.1.4 雌孕激素连续联合 连续服用同一剂量的雌孕激素制剂,没有周期性撤退性出血,适用于有子宫已绝经、不希望来月经的绝经晚期妇女。目前,可以戊酸雌二醇或结合雌激素,同时加用地屈孕酮,复合制剂有安今益、倍美罗。
替勃龙作为选择性雌激素活性调节剂,具有微弱的雌、孕、雄激素活性,可作为替代方案提供给老年绝经后妇女。它在骨骼大脑以及阴道中产生雌激素作用,而在子宫内膜和乳腺组织中则不表达。而且,因其具有一定的雄激素活性,可改善性功能,提高性欲,不需加用孕激素。
5.2 药物及其使用途径选择
5.2.1 雌激素 具有血管舒缩功能、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对于仅有阴道干涩或性交不适症状的患者,单纯解决局部生殖道萎缩症状,可首选局部低剂量雌激素治疗;轻、中度肝脏问题,血栓高风险,血脂异常特别是甘油三酯高,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可选经皮雌激素;临界高血压可选含屈螺酮的MHT;乳腺疼痛、甘油三酯高、性功能障碍、情绪异常可选替勃龙。
5.2.2孕激素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MHT中的孕激素除具有保护子宫内膜作用外,可能与乳腺癌的发生有关。 选择天然的、安全的孕激素是MHT整体策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屈螺酮具有抗雄激素和抗盐皮质激素作用,不会影响血压和体重,对乳腺细胞的刺激比其他孕激素小,引起乳腺癌的风险低。
6. 使用剂量、使用时限及随访
IMS和NAMS指南和全球共识声明中反复强调个体化治疗[16],即从女性生活质量、健康优先、个体风险因素等方面考虑,具体到年龄、绝经年限以及静脉血栓、卒中、缺血性心脏病、乳癌风险等方面考虑,个体化地选择MHT的剂量和周期方案。无论任何年龄,MHT不推荐用于冠心病的预防。在早期窗口期介入的MHT可以缓解绝经症状,不仅不会增加心血管等风险[17],相反,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应用最低有效剂量,以期最大获益,最低风险。
雌激素是MHT的核心,其使用剂量可随妇女年龄的增加而适当减量。在绝经早期妇女的使用剂量往往高于绝经晚期。对于卵巢功能早衰的患者或绝经年龄小于45岁者,推荐全身使用MHT,至少应该持续到自然绝经的平均年龄[18]。我国的指南也指出,采用规范化的接诊、临床处理和随诊步骤,认真判断禁忌证及其慎用药物情况。对不同主诉的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诊疗,综合评估使用目的和风险,个体化用药,不必限制MHT的使用时限。开始MHT后,1~3个月复诊,后可3~6个月,1年后复诊时间拉长为6个月至1年。如果患者出现异常的阴道流血、乳房胀痛等其他不适症状随诊,并根据复查情况调整用药和剂量,鼓励患者继续坚持MHT以期长期获益。在围绝经期、绝经早期介入的MHT女性,年龄达到60岁以上是否继续使用,需要进行风险-获益分析再评估。
最新的指南重视饮食、运动、戒烟和适当饮酒等生活方式对围绝经的影响,强调MHT是维持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的健康全部策略的一部分,对绝经女性应进行系列的多层次的健康管理。
非激素治疗[19]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倡对绝经期女性采取多层次干预,以激素治疗作为绝经管理策略的中心环节,配合选择合适的药物和治疗方案,推荐合理营养膳食、环境因素有害物质控制、限制保健品摄入、合理运动、生活习惯指导、神经心理辅导等综合措施,建立绝经女性管理保证体系。
具体来讲,健康的饮食,合理营养、平衡膳食可以延缓衰老、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减少并发症。规律运动可以改善情绪、改善心血管功能、降低冠心病高危因素,增加骨密度,是目前防止骨质疏松的唯一非药物治疗。戒烟可以减少对卵巢的功能损害,推迟绝经,增加骨量,减少骨质疏松高风险。适当饮酒可以通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保护心血管、改善认知。保持乐观心态、自我调整、健康情绪,可以使循环血量和神经细胞处于最佳工作状态,提高机体抵抗力。适度的性生活可以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1. 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是一种中枢神经递质调节剂,对潮热最有效,最大可改善50%~60%的潮热症状,但效应短暂。改善情绪的作用不依赖于对潮热的效应,对性欲影响小,但长期使用可以产生撤退症状。
2. 植物雌激素
植物雌激素指在植物中存在的非甾体雌激素类物质,结构与雌激素类似,可以雌激素受体结合,产生雌激素样活性。植物雌激素分为三类:异黄酮类、香豆素类、木质素等。研究的比较多的是大豆异黄酮。有研究认为,其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改善血脂,曾作为非药物治疗方法首选而风靡一时。然而,植物雌激素对潮热、骨质疏松的作用以及对子宫内膜、乳腺组织的抗雌激素作用并未被证实。尚无证据表明,植物雌激素可以作为代替品激素用于围绝经期。同时,其负面影响,如促进雌激素敏感性肿瘤发展、损害认知功能、影响生殖功能、影响新生儿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的发育等问题尚需明确。因此,其仍是保健品,应用于绝经期需要进一步论证。青少年和生育年龄女性不主张补充植物雌激素。
植物药是用现代工艺从升麻类植物中提取的非雌激素类纯天然植物药,称黑升麻异丙醇萃取物及升麻乙醇萃取物。非雌激素类纯天然植物药无雌激素活性,主要用于缓解女性围绝经期综合征出现的潮热、出汗、失眠、焦虑、抑郁等症状。其作用机制为抑制下丘脑-垂体轴,减少促黄体素的释放,通过抑制中枢5-羟色胺受体、多巴胺受体和阿片受体缓解症状。
3. 中医药与针灸治疗
我国中医药与针灸治疗对神经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发挥了一定作用。
[1] Villiers TJ, Pines A, Panay N, et al. Updated 2013 International Menopause Society recommendations on 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 for midlife health[J]. Climacteric, 2013, 16: 316-337.
[2] Writing Group for the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Investigators. Risks and benefits of estrogen plus progesterone 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women[J]. JAMA, 2002, 288: 321-333.
[3] Stefanickml, Anderson GL, Margolis KL, et al. Effects of conjugated equine estrogens on breast cancer and mammography screening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hysterectomy[J]. JAMA, 2006, 295: 1647-1657.
[4] Rossouw JE, Prentice RL, Manson JE, et al. Postmenopausal hormone an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by age and years since menopause[J]. JAMA, 2007, 297: 1465-1477.
[5] Sturdee DW, Pines A, International Menopause Society Writing Group. Updated IMS recommendations on post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 for midlife health[J]. Climacteric, 2011, 14(3): 302-320.
[6] Gompel A, Rozenberg S, Barlow DH. EMAS board members:The EMAS 2008 update on clinical recommendations on postmenopausal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J]. Maturitas, 2008, 61(3): 227-232.
[7] Santen RJ, Allred DC, Ardoin SP, et al. Post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 Endocrine Society scientific statement[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0, 95(7 Suppl 1): s1-s66.
[8] Villiers TJ, Gassml, Haines CJ, et al. Glob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J]. Maturitas, 2013, 74(4): 391-392.
[9]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绝经过渡期和绝经后期激素补充治疗临床应用指南(2009版)[J].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0, 45(8): 635-638.
[10]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绝经学组.绝经期管理与激素补充治疗临床应用指南(2012版)[J]. 中华妇产科杂志, 2013, 48(10): 795-799.
[11] Sturdee DW, Pines A. international menopause society writing goup, et al. UpdatedIMS recommendations on post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 for midlife health[J]. Climacteric, 2001, 14(3): 302-320.
[12]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治指南(2011版)[J].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 2011, 4(1): 2-16.
[13] 陈蓉.绝经激素治疗新进展[J].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014, 30(1): 38-40.
[14] Fournier A, Berrino F, Clavel-Chapelon F. Unequal risks for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ies: results from the E3N cohort study[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08, 107(1): 103-111.
[15] IMS Writing Group. Update IMS recommendations on post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 for midlife health[J]. Climacteric, 2011, 14(3): 302-320.
[16] De villiers TJ, Gass M, Haines CJ, et al. Glob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J]. Climacteric, 2013, 16(2): 203-204.
[17] Schierbeck LL, Rejnmark L, Tofteng CL, et al. Effect of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on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recently postmenopausal women: randomised trial[J]. Bri Med J, 2012, 345(2): e6409-e6410.
[18] North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 The 2012 hormone therapy statem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menopause society[J]. Menopause, 2012, 19(3): 257-271.
[19] 郁琦.绝经学(第一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158-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