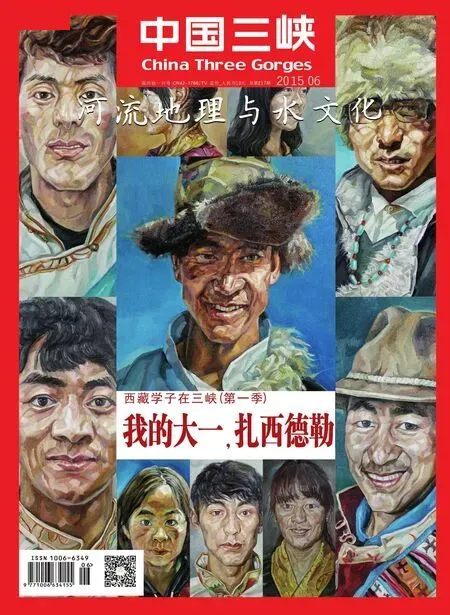茶的事
文/黄运丰 编辑/李颜岐
茶的事
文/黄运丰 编辑/李颜岐

茶道。 插画/王进城/CFP
从小喝茶喝到大的我,却不敢说懂茶,比如茶的品种品类,比如功夫茶的“功夫”。我是到了广州之后,才知道有叫普洱和铁观音的茶。
说了不怕笑话,我钟意于喝茶,在乎的也就只是其中的苦涩滋味,可以咂巴咂巴的那种味道。除此之外,我怕是也说不出来什么。
我的家乡大别山腹地,群峰起伏,自成风云,有着种茶出茶的好山水。那里出产的茶的品种,随便说说就一连串了。比如,但凡我同外地人讲我是六安人时,他们大多都有的一个反应:“哦,六安瓜片”;比如属于黄茶类的“霍山黄芽”;比如我们那个有全国第二将军县之称的著名贫困县金寨县产的“金寨翠眉”;比如和我们乡一岭之隔的河南信阳产的“信阳毛尖”……除了瓜片,其他都算是小众的区域性品种,不一定有许多人知道。
我们乡里出的茶,也就是我从小喝到大的那种茶,据我懂行的二姨夫说,都算是“毛尖”。他是河南人,和我们乡就隔着一道青峰岭,岭那一边的茶地差不多都是他们家的,所以他也有一个茶厂,出的茶自己命名为“青峰云雾”。
小时候有那么几年,每年清明前,我和表弟都会去姨夫家帮忙采茶。十岁左右的样子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花半天时间采的还不如大人们半个钟头采的茶量多。若是等炒过烘干后再看,我们小屁孩儿一天茶大概也就一小把,想必都不够现在一天喝掉的。有时候,我们也是真用心采摘,细心挑选嫩嫩的芽儿;有时候却没什么耐心,甚至把上一年的大叶子也捋了来。
往往在姨夫家呆了两天回到本乡地界后,就是钻进姥姥家面积相对小许多的茶地里,在姨妈们的带领下开始采茶运动的收尾表演。姥姥这时也会上阵,她的双手像钳子一样精准,能轮番且快速地掐断嫩茶根,常年劳作使得她的多数手指关节光亮,手掌却乌黑又粗糙。攀上桑树摘桑葚吃得满嘴发乌的我,远远看着瘦小的姥姥抓采茶树顶端嫩芽的样子,这场景成为我多年后重复听《水手》时频频闪现于脑海的画面,姥姥像一个机警的水手,总是那般扬起手眺望海面……如今在外,每次和她通电话,虽次数极少,我都以为她差不多是以同样眺望的姿势在拿着话筒。
姥姥采的茶会用柴火灶炒出来,一箩筐的新茶倒入热锅中,亲上双手快速翻炒,直至新绿变了深绿,再变了黑绿,而后盛起放在簸箕里,接着晒干,最后封存,自己留点儿喝,再给儿女们分发点,当然除了我二姨家。所以,我相信我对茶最早的味道记忆——苦涩中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也就是姥姥的手艺了,肯定不是机器能烘炒出来的。
到今年,我知道并尝过一种单枞之后,品味间仿佛又找寻到了那种远隔千山万水的记忆。
这像一种缘分,一种际遇,一种难以言传的味蕾密语。
后来和朋友张罗寻得了一批这种单枞,订制成了我自己的“黄茶”。有些懂茶的朋友见了这名字后,笑我不懂行,我不愿多解释,只说“此黄茶非彼黄茶”,其实我在乎的并非人们懂不懂我的茶,而是他们是否懂我这个人。

春日采茶。 摄影/何东平/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