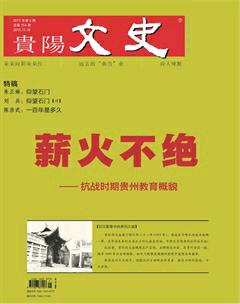北宋的古大臣之风
罗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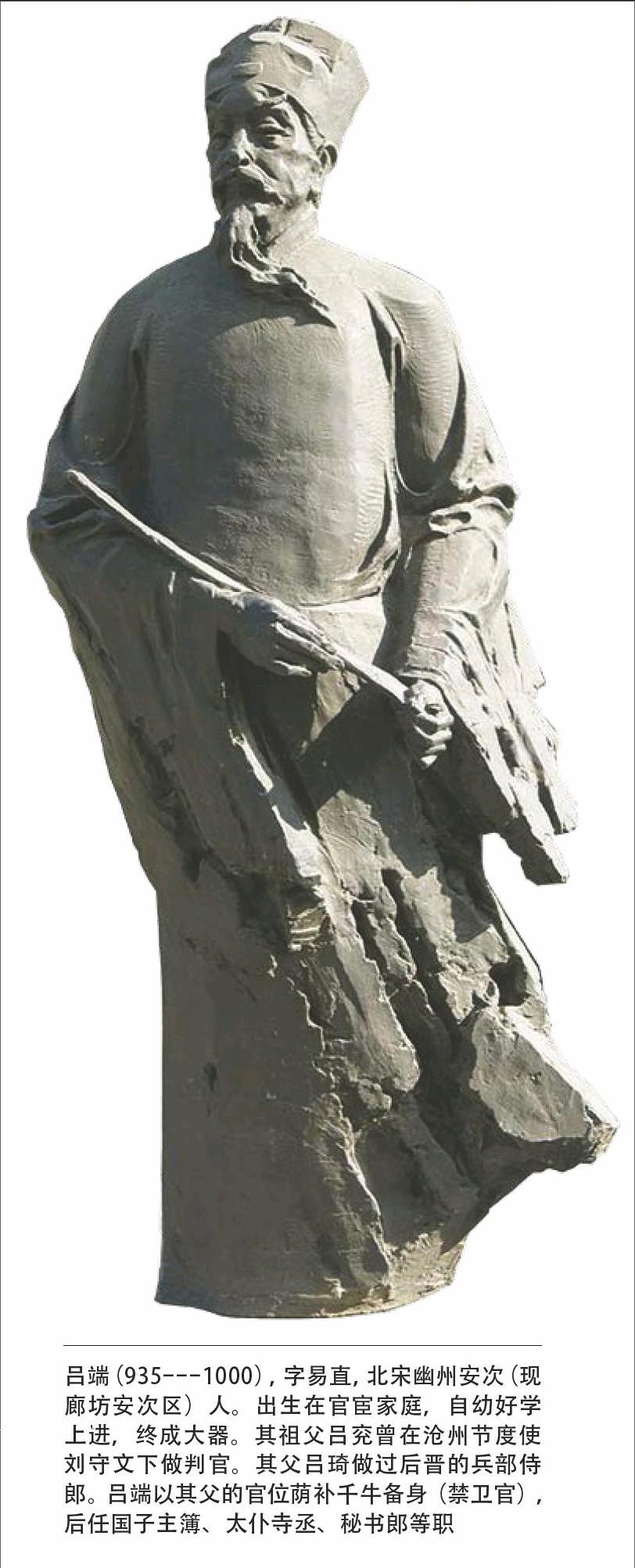
我们在读史过程中,常常能看到“古大臣之风”这个词语。“古大臣之风”往往是指一些在君主专制下的大臣,他们能够不畏威权,坚持正直原则,也指相对能够焕发自己坦荡光明、健康自由的人格品质。毛泽东所称道“诸葛一生唯谨滇,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就是一位具有“古大臣之风”的北宋宰相。我曾经在《遇上宋仁宗幸运,遇上宋徽宗遭殃》一文中说过,北宋前期,尤以宋仁宗时期为代表,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优质时期:在这个时期,君主们大多尽力约束自己,让他们所执掌的公权力基本正常地行使,而执政和台谏等朝廷大臣,也多有“古大臣之风”。这种比较理想的政治状态,曾经作为正面力量,鼓励过程朱修补和继续幻化儒家的封建伦理政治理想。
那就从吕端入手看看北宋的“古大臣之风”。
人们通常关心的官位高低、金钱多少等世俗问题,吕端却总是淡然处之,所以留下“糊涂”的历史名声。宋太宗要提拔吕端为宰相,吕端并没有为得到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沾沾自喜,相反,他此时想到的是朝廷执政班子的团结问题,为此不惜放权和让位,因为他身边还有一位声望卓著、才能优异的名臣寇准,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寇准性子刚烈,吕端怕他内心不平衡而影响朝政工作,于是请求太宗另下一道命令,让副宰相参知政事,寇准和自己轮流掌印、领班奏事,得到了太宗的批准。后来太宗又有诏旨:朝中大事一律先交吕端,然后才上报;然而吕端仍然遇事都与寇准商量。最为奇特之处在于:吕端后来干脆主动让位给寇准,自己降格去当副宰相参知政事。再后来出征澶渊的历史证明了吕端为天下惜才的眼光,也证明了寇准确实是一根比吕端更为重大的朝廷栋梁。
寇准不但有“古大臣之风”,而且应该说就是传说中的古大臣典型。寇准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率性可爱的封建政治家。坦率地说,自秦始皇始,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集权政治严如寒冰,而在北宋能够出现寇准,却也能够给人一缕温暖的慰藉。
寇准19岁考中进士,然而钦点进士之际,宋太宗会在大殿平台上目测和提问,年纪太轻的往往会被罢去。后来的明太祖应该是学宋太宗,曾经把神童解缙打发回家历练几年再来。有人给寇准出主意:增报年龄。寇准回答:我刚准备踏上仕途,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怎么能欺骗皇上呢?最终19岁的寇准被录取了,授予大理评事。
寇准的“可欺君耶”应当不属愚忠,而是出于一种“忠君爱国”的传统理念。后来的事实证明,寇准官运亨通靠的决不是阿谀奉承、依附权贵,而是刚正不阿、抗颜直谏。用《宋史·寇准传》的话说:“会诏百官言事,而准极陈利害,帝益器重之。”有一次寇准与太宗在办公室讨论问题,寇准据理力争,惹得太宗愤怒地站起来,想以非正常方式结束争论,哪知寇准不干,拉着太宗衣服“令帝复坐”,直到问题解决,太宗与寇准才各自回家——《宋史》没说是什么具体问题。
1004年10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南下攻宋,北宋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一片惊慌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自己的故乡南京,枢密院事陈尧叟主张迁都自己的故乡成都;宋真宗自雍熙北伐惨败之后,对辽国就一直心存畏惧,既无心抵抗、又怕担负道义责任,六神无主;此时,只有帝国栋梁寇准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而且告诉宋真宗,如果往南逃跑,整个国家的人心就会崩溃,敌人乘势追击,大宋江山将无法保存。宋真宗这才被迫与寇准一道御驾亲征澶州。
宋真宗时代,黄河是流经澶州的。真宗到了澶州南城,怎么都不愿去宋军主力所在的北城前线。寇准一面坚持推进北城“取威决胜”,一面宽慰北宋第一位在深宫里长大的真宗皇帝,说他自担任兵部尚书以来,对这场战争就有所准备,如今更有王超劲兵屯驻中心以扼契丹锋锐,李继隆和石保吉大军拖着契丹左右双臂,四方驰援的队伍也会很快来到。宋真宗仍然下不了决心。寇准出帐寻找“援军”,恰遇太慰高琼前来办事,寇准先把高琼抵入道义高台:“太慰深受国恩,今日有行动报答吗?”寇准拉着高琼重返帐中,据《宋史》记载,寇准“厉声”对宋真宗说:“请陛下问太慰高琼。”高琼简洁四字:“寇准言是。”宋真宗这才半推半就地渡过黄河。
宋真宗把澶州北城的军事指挥权完全委托寇准,自己回到行宫中,还不断派人到城上观察寇准。深知真宗心思的寇准,与杨亿在城上饮酒博彩、谈笑高歌,这下真宗赵恒心里踏实了:寇准都如此神态轻松,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寇准这个“桥段”,使我们想起诸葛亮的“空城计”,前者是真实的稳定军心,后者是虚构的麻痹敌人,但其智慧含量应该都是一样的。《三国演义》成于元明之际,罗贯中的灵感有可能来自寇准这个“桥段”。
虽然在局势有利于北宋的情况下,缺乏英武气概的宋真宗仍然不顾寇准的强烈反对,在契丹人搭起的和谈台阶前,以每年进贡辽国30万金帛的条件签下“澶渊之盟”;但是,寇准毕竟在关键时刻,以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安定了社稷,可以说对帝国功重如山。
寇准走到自己的政治顶峰,因奸臣王钦若“寇准把真宗当‘孤注一掷”的挑拨,宋真宗第二年就罢了寇准的相权。宋真宗病重期间,刘太后暗中参政,寇准培养的丁谓已官至参知政事,但丁谓觉得自己拜相还欠火候,又把外放的寇准请回来。虽几经宦海沉浮,寇准高洁的秉性依旧率真可爱。当饭后丁谓用衣袖为寇准拂去胡须上的菜叶时,寇准不但不领情,反而教训丁谓:“参知政事是国家大臣,应该操劳国家大事,哪有给长官拂须之理?”为此,寇准后来被丁谓和刘太后联手贬到雷州,一年多后终老雷州。
寇准之后的韩琦当然也是北宋名臣。他参加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虽然他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或者是失去锐气,或者是缺乏见识,但他身上闪现的“古大臣之风”,仍然是北宋历史上的亮点。
韩琦虽然出生仕宦之家,却20岁就以第二名高中进士,后来多次出将入相,《全宋词》还录其词4首。宋仁宗嘉祜二年,刚中进士的苏辙曾写过著名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表示了仰慕和求见高人之心,这个“高人”就是时任“军委主席”的韩琦。韩琦曾经“相三朝,立二帝”,“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欧阳修对他的评价是:“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宋史·韩琦传》采用的大概也是欧阳修意思:“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厚重比周勃,政事比姚崇。”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评价更高:“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
宋仁宗驾崩之时,已宣英宗进宫继位,但仁宗的手突然又动了一动。左右大臣见状心六神无主,都盯着宰相韩琦。此时的韩琦真有欧阳公所说的“社稷之臣”风采,他临变担当、当机立断:新君照旧迎立,如果仁宗醒来,就当太上皇。事后有人劝韩琦:“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回答说:大臣死生以事君国而已,哪能如此患得患失?宋神宗也是韩琦所立“二帝”中的—帝,神宗继位,有人不满韩琦专权三世,御史中丞王陶告他跋扈,韩琦为表示不恋权位,竟然潇洒地坚决辞位。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古大臣之风”,则表现得更为文人化和戏剧化。两人均曾经被任命“同修起居注”,也就是为皇帝写流水账日记,然而两人都坚决不干:虽然给皇帝写日记有更多亲近皇帝的机会,但王安石想干实事,不愿当这个闲差;司马光干脆说自己“不愿为四六”,也就是瞧不上“起居注”这种无聊文字。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最大相同点,虽然政治理想方向相反,但他们都能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被后人誉为历史上的两位“拗相公”:王安石坚持变法不合糊,要当宰相就得按自己的政治理想干,而且为了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的理想,他具有罕见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洫”的政治家气魄,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政治理想干,那就宁愿不当宰相。宋神宗在变法运动中曾经几度动摇,王安石也就曾经相应地几次辞相。司马光的政治态度也很鲜明坚决,就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基于权术考虑,曾经非常希望司马光出任枢密副使,与王安石互相支持,也互相监督,但司马光向宋神宗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废除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数次劝说都无效,更无法满足司马光先决的条件,司马光干脆离开朝廷,躲到西京洛阳“独乐园”里写自己的《资治通鉴》。
我在《王安石的政治梦》中说过,以王安石的政治经历为例,可以看到北宋社会的政治宽容性有点像个童话,我还说到过一个民间调查:如果可以自由穿越中国历史,许多知识分子都愿意回到北宋。北宋大臣这一片人格亮丽的精神风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诚如张宏杰所说,自秦始皇建立帝制后,中国的“国民性”在君权专制之下便江河日下;如果要找出其中直堕黑暗的时段,那应该是始于农民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我们看看嘉靖皇帝一朝,夏言、高拱、除阶、张居正,甚至包括严嵩,应该说都是人中之杰,但是,他们被—个修道炼丹的皇帝治得人格扭曲;到了明熹宗时期,皇帝都可以不出面了,躲在宫中干他的木匠活儿,只要一个太监魏忠贤,因为能口衔皇权,就有多少知识分子叫他亲爹?就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全国给他修了生祠?令人心碎,不堪回首。
(作者系新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