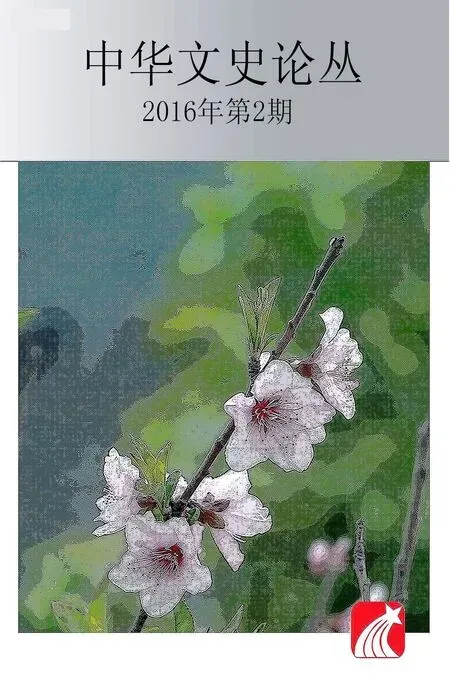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
——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高 波
“嘉道的主體性”與“在清朝發現歷史”
——評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
高 波
一 “嘉道的主體性”
對二十多年來的清中葉及以後時段的歷史研究,柯文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語,恐怕是引用頻率最高的幾句話之一。①具體見柯文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柯文原作出版於1984年,中譯本出版於1989年。這句看似明確但其實含義頗不清楚的話,與該領域的元問題之一“現代中國從何時開始”緊緊纏繞在一起,刺激着每一位在這一領域內探索的學人的思考。張瑞龍的新著《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的政治、學術與社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下簡稱“張著”)就做出了明確的探索。
天理教事件發生於嘉慶後期,直接開啓了道光朝前期的政局,實爲兩朝間一大事件。但與此相對,在清朝歷代帝王年號中,嘉慶與道光卻可能是最少被連接起來的兩個(臨近如乾嘉、道咸、咸同,皆已如同專屬概念)。在作者看來,嘉道這一名詞之所以被冷落,是受限於既有史學敍述:“1950年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大陸學術界關於嘉道時期的學術思想研究多以鴉片戰爭前後爲界,嘉道兩朝極少被視作一個獨立學術時段,而是被分別置於‘乾嘉’和‘道咸以降’(或‘晚清’、‘近代’等)兩個學術時段下進行。這與其時中國大陸學界建設馬克思主義史學,近代史分期上以發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爲開端有很大關係。”①作者認爲:“嘉道學術時段下的清代學術思想研究”“尚未出現即使是‘一家之言’式的較爲全面的探討。”(頁30)王汎森也認爲:“大概從嘉慶後期一直到道咸年間,也就是1800—1850年之間,是晚清的一個重大變化期。我注意到許多清代思想史、學術史,往往是在寫完考證學之後便接着寫洋務運動及西學東漸,但是夾在兩者中間大概有半個世紀的時間,卻是一個重要的變化期。”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序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鴉片戰爭作爲我們常識中的近代起點,畫開了清朝中前期與晚清,更進一步被作爲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分界點;而費正清學派主張“衝擊—回應”說,强調西人東來對近代中國的決定性作用,雖然問題預設與評判標準有異,但對這一時段畫分最初同樣沒有異議。
有另一點作者雖未言明,但與該書立意緊密相關。在費正清學派第一代後(包括第一代中很多人自身的轉向),美國中國研究界開始反思過分强調西方衝擊、忽視中國自身能動性的問題,强調“在中國發現歷史”,即要發掘中國內部因素對“中國進入現代”這一問題的意義,因此刻意降低鴉片戰爭的重要性,將視線轉向乾嘉之際,認爲晚清巨變的一大前因即爲此時的政治與社會危機,舉凡吏治、漕運、河務、民變,不一而足。這一對乾嘉之際的新關注,在近二十多年來,對國內學界同樣有着深刻的影響。
張著同時面對着以上兩種學術傳統。作者將清朝衰落、現代中國誕生這一宏大過程的起點,既不繫於第一次鴉片戰爭(道咸之際),也不繫於1800年前後(乾嘉之際),①這兩種思路皆有其合理性。“道咸”是政治層面的斷限,兩次鴉片戰爭依次發生在這兩朝,自然構成一個段落;樸學在乾隆朝中後期取得主流地位,大部分重要學術成果則完成於嘉慶朝,故“乾嘉”在學術史上也是連續的。而是繫於兩者間的嘉慶朝中後期(嘉道),着力挖掘“嘉道的主體性”。在作者看來,不管是道咸之際還是乾嘉之際,雖各有其合理性,但離清朝人自身的羣體“經歷與體驗”(experiences),②見E.P.湯普森著,錢乘旦等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前言,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頁1—2。仍有一定距離——兩種學術傳統雖有幾分意識形態上的對立性,卻都默認“清朝的衰落”與“現代中國的孕育”是同一個過程(或者更明確地說,將前者僅視作後者的某一方面),着力尋找的,是現代起點而非王朝興亡意義上的清朝衰落時刻;但這未必合於清朝人的關懷模式與思考順序——他們念兹在兹的問題是“清朝何時衰落”,而“現代中國何時開始”則相當晚纔作爲一個有明確意義的問題出現(大致在甲午至戊戌前後)。然則兩者有何不同?若以現代起點論,則馬戛爾尼使團就是至關重要的;但若以王朝興亡論,則該使團實無足輕重——古語有云內憂外患,清人從未以馬戛爾尼使團與白蓮教起義並置,亦未以阿美士德使團與天理教事件並置,而惟以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並置。蓋因這一對間有某種相互牽連(鴉片戰爭後開放傳教引發以基督教變種爲宗旨的太平天國起義),前兩者則內外渺不相涉。
這一起點之爭,與中國近代轉型是內生還是外生這一問題有關。以西方衝擊—中國回應的視角,第一次鴉片戰爭確是近代的起點;但若就清人自身的視角,反而是嘉慶五年(1800)的庚申之變及其引發的王朝政教的大震動,纔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內在起點。若以調和的眼光,則兩者分別可算是近代的“外在”與“內在”起點;而乾嘉之際(1800年前後)與嘉道之際的不同也可以此得到初步理解——乾嘉之際民變、吏治、河務、漕運、鹽務等方面的頹勢,並未被清人當作世運已變的象徵,而是常規性地視爲對盛世的干擾;而天理教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讓嘉慶的清朝人意識到,盛世已經結束,就此“內在”地確認了清朝從盛世到衰世的轉折(白蓮教事件的意義也由這一新透鏡回視而得)。①當然,這幾個起點並不完全矛盾。不同的起點如同不同的光源,照出歷史“無知之幕”後的不同面相,多可互相補充。事實上,對起點的追尋是史學敍述的內在要求,關乎史學的力量與限度(後現代史學對此反思極多)。因此,張著這一新視角,實爲一有益嘗試,即並不是要否定道咸或乾嘉的“主體性”,而是試圖展示之前視野所遮蔽的歷史,使其豐滿而更具歷史感(尤其是清朝人自己的歷史感)。
另有一點,嘉道兩朝延續近六十年,而古人慣以一世(三十年)或一紀(六十年)作爲觀察世運的單位。大致可說,一世爲一自然的代際更替,一紀則爲一代人由生至死(即在歷史舞臺上由登場到退場)的全過程。而人羣更替與時代演變總是緊密相聯——不管是古代歷史中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一幕幕,還是現代政治與文化的代際更迭,都顯示出這一“中程”歷史時段的重要性。張著也正建築於此一時段之上——以嘉慶初期到道光中期(1805—1835)爲一世,正構成乾嘉與道咸間的獨立一環。
綜合言之,不管是立足於傳統—現代轉型這一長程問題,還是乾嘉至道咸演變這一“中程”問題,都需要對嘉道之際的作出新理解,而這也將爲重新理解近代中國的“起點”提供可能性。毋庸置言,近代中國正陷於“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與此相應,在新文化運動後,傳統與現代截然斷裂的心態在國人中取得主導地位,促使他們努力在晚近中國史中尋找切開二者的根本轉捩點。實則歷史如水,非抽刀可斷,轉折往往以平凡而迂曲地方式呈現自身,起點也絕非一個“點”,往往是個時而急驟時而拖遝(以後來人的眼光)的過程,①如王汎森認爲,嘉道時期的宋學復興可視爲中國近代思想轉型的起點(見王汎森《方東樹與漢學的衰退》,載《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就與張著將天理教事件視爲近代起點的觀點互相補充。而在驚天動地的事件與此種“平凡”變化之間,又有一中間地帶,即時代心態與精神,古人以“風”喻,庶幾近之。士風與世風緊密相連,風隨草偃,隨物賦形,上以氣運連天道,中以風氣通士心,下以風俗表衆庶。故張著雖以天理教事件切入,但所關注者,卻在此一時期士風與世風的轉移,而天理教事件,則是此風賦形之物。②對“風”這一概念所蘊含的史學思想的闡發,見王汎森《“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載《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
二 政治史與思想學術史
張著的另一特點,是試圖將清中葉以降的思想學術變化與當時的王朝政治演變結合起來。這一立意針對着兩條互有聯繫的史學脈絡,其一爲梁啓超、錢穆以來的近世思想學術史研究。此一研究傳統直接承續梁啓超新史學一脈,以反對傳統以王朝興衰爲中心的歷史敍述爲目標,故梁、錢二人影響極大的同名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皆明確放棄王朝斷代,將王朝政治與思想學術變遷分離。其後學者雖在局部多有修正,但整體仍多循梁、錢二人矩矱。③近年來的國內思想學術史研究,漸開始突破這一經典範式,轉而强調王權與皇帝個人對思想學術演變的巨大影響。就清史領域,可參看楊念羣《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另一脈絡爲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與西方的庶民史研究。不管是傳統革命史學中的農民起義研究,還是海外中國研究中的民間宗教與叛亂研究,皆試圖突破傳統的王朝史學框架,挖掘庶民階級的主體性(不管這種主體性是奠基於階級、社羣還是文化)。①革命史學將農民階級塑造爲能動的歷史主體,賦予其積極的(甚至是惟一的)歷史創造力;而庶民史研究則視底層民衆與中上層精英爲有着複雜互動的對立主體——建制宗教與民間宗教、大傳統與小傳統之分都體現了這一點。但爲建立此種“主體性”,傳統王朝政治與時代思想學術演變間的種種微妙關聯,往往會被有意無意忽視。
張氏沉潛以上兩條學術路向有年,對其利弊稔熟於心,故框架與二者皆不同。在“嘉道之際”這一背景下,張著在結構、脈絡與敍述上,有三個次一級的主體——天理教、嘉慶帝與士人,整體大致可歸入廣義的“影響研究”——探討天理教事件對清朝“嘉道轉型”的影響(從政治到學術)。在敍述中,天理教處於遠景,作用是啓動歷史過程;近景中活動着的,是嘉慶帝(略可對應書名中的“政治”)與士人(略可對應書名中的“學術與社會”)。另外,多章章名中即有“震撼”、“整頓”、“轉變”、“轉向”等詞,也明顯可見影響研究的特點。若分別而論,第三、四、五三章均以嘉慶帝爲中心,探討天理教事件後嘉慶帝心態與認識的巨大變化——包括振刷吏治的努力(第三章),改變對邪教政策(第四章),以及調整文化政策(第五章)。接下來則是天理教事件對士風、士習與學術的影響(第六、七兩章)。作者的抱負不限於該事件,而是試圖打通上下,勾連當時的政治、學術與社會。②作者對既存研究進行了全面細緻的考察(見第一章“緒論”),發現除少數論著外,多有目的論傾向以及“倒放電影”的問題,“仍不脫就學術思想史論學術思想史的窠臼,極少注意外部社會、政治等具體歷史環境對學術思想產生的影響”,“遠沒有深入這一時代,回到歷史場景,對這些學術思想所以產生的原因及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做具體而微的細緻考察”(頁31—32)。作者認爲,“由於任何歷史事件在其歷史場景中都作爲一個整體出現,故任何單一方法的運用,呈現的都是某一側面。當年震撼朝野的天理教事件,在當時的政治、法律、教育、學術和思想等多個領域都引起過較大反應,這就爲我們在研究方法上綜合運用政治史、社會史、學術史和思想史等多種方法提供了可能。如:運用政治史的方法研究清廷在天理教事件發生後采取的一系列統治政策的調整,用社會史的方法考察天理教事件消息的傳播及其對朝野的震撼,用政治史、社會史、學術史和思想史相結合的方法綜合考察天理教事件與嘉道之際學術和思想轉向的關聯、因應與互動等。力圖使政治事件與當時社會、學術與思想的有機互動,得到具體而微的呈現,盡量避免就學術史論學術史、忽略學術思想產生的具體社會歷史環境的局限,或落入那種把對外部政治、社會環境的討論變成是對社會性質的定位或宏大歷史背景描述的窠臼”(頁37—38)。他探討的並非天理教的演變與1813年起義的過程,而是該起義引起的各式“反應”(從事件發生後不久,到整個嘉道時期),尤其是嘉慶與士大夫階級的反應。如此則庶民在歷史舞臺上看似退場,卻又以不斷被他人表述與解讀的方式持續“在場”,看似缺乏“主體性”,卻又無處不在。①對比作者與《千年末世之亂——1813年八卦教起義》(韓書瑞著,陳仲丹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一書,可知不同。作者這一選擇,也是因爲就天理教事件本身而論,不管是革命史學中的農民起義研究,還是海外中國研究中的民間宗教與叛亂研究,都已各自羅掘甚深,開拓空間不大,有另闢新徑的必要。
這種結構方式,有幾分暗合傳統王朝的歷史邏輯。古人以天時與人事密不可分,觀風即是觀天道人事之推演。天心自我民心,則民衆代表天命,自如天命本身般難測與不可知,而民變作爲民心向背的預兆,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士大夫由此“察勢觀風”以察知王朝是否仍保有“天命”。用王汎森的話說,此種“被表述”正表明民衆有“消極性的創造力”,②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序論。借助影響君主與士大夫,最終塑造歷史。
這一傳統王朝史學在近代遭到嚴厲批判。梁啓超以“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貶之,③梁啓超《新史學》,載《飲冰室合集》(1),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3。極盡揶揄之能事。然而,此實爲矯枉過正——這忽略了當時人(包括天理教衆在內)的思想與意義世界。對他們來說,天命有無、王朝存廢都是思考生活的基點——天理教衆深信紅羊當興、清朝當亡,清朝君主與士大夫以民變爲上天示警,思及王朝興衰,皆爲此類。因此,王朝史學自有其價值,梁啓超可謂倒髒水將孩子一同倒掉。而作爲新史學的後來者,張著則試圖調和新史學與傳統的王朝史,不僅要“在中國發現歷史”,更要“在清朝發現歷史”。
之前就听我妈说过,这家人成分是很微妙的。家里男人是鄂州搞房地产的,经常不在家。儿子和我一个小学,马上要上初中。而现在和孩子在家里的是他的后妈。
但這一努力面臨着先天困難。首先是影響研究的限度——到底什麽可以歸入天理教事件影響的範圍?對嘉慶時期的士大夫而言,這一事件到底有多重要?自然,對傳統王朝而言,民變具有生死般的重要性——蠻夷猾夏有時會被認爲是肘腋之疾,民變則從來都是心腹之患;但此處要探討的,並非民變的政治重要性,而是它對這一時期士風與世風的影響程度。漢之黃巾,元之紅巾,皆別啓一世局;而如白蓮教起義,雖規模浩大,但對乾嘉時期士風與世風卻影響不大;反過來,太平天國起義則直接造成了一代人士風與世風的轉變,開啓了所謂的“中興時代”(更因西人東來而具有現代史意義)。
比較而言,天理教這樣的小規模起事,造成的社會與政治危機並不致命,主要在於文化與心理衝擊層面。因此,其對士人的影響更爲微妙,既不同於白蓮教起義,也不同於太平天國起義——不像前者那樣對士人羣體觸動不大,也不像後者那樣幾乎重塑了他們的精神世界。對那些究心於河務、漕運、鹽政或痛心於吏治敗壞的士人,此事印證(而非引發)了他們的某些思想傾向;因此,天理教事件的單獨影響頗難分離,若强行分離,反而會損傷此一歷史時期的整體性。另外,此事對不同位置的人的影響大不相同——對如被嘉慶斥爲全無心肝的顢頇官員,或如姚鼐這樣飽經世故的老者,再或更年輕的在嘉慶朝成長起來的管同與姚瑩等人,影響方式與程度都很不同。張著對既存研究掌握十分全面,但似涉入過深,反受其限制——既存研究視嘉道時期爲無關緊要的過渡階段,張著爲凸顯其主體性,强調這一時期的“變”而非“常”,结果相對忽視了天理教事件引起的改變的限度。①張著第二章對天理教事件傳播的研究,探討的是該事件的直接後續影響,考訂紥實而細緻,具有確實性, 足以爲全書地基。第三、四、五章圍繞嘉慶帝所做的探討,大致亦可歸入天理教事件的影響範圍。但天理教事件對士人以及當時社會與學術的影響,要複雜迂遠很多,因此第六、七兩章討論士風、士習的變化,與天理教事件的關係就顯得不那麽分明——舉凡考據學的衰落、理學的重新興起等,影響因素都十分複雜,天理教事件僅是諸因素之一。實際上,士風士習、思想學術的轉型問題,內緣與外緣相互纏繞,單一因素的影響如同投石入水,漣漪愈遠愈弱,頗難分辨。
事實上,國家政策與政治運作可因某一事件發生極大變化,羣體思想學術的變動則往往緩慢而多歧,除非是甲午這樣天崩地坼的變化,纔會造成士大夫內在精神結構的根本顛覆——彼時轉變多且劇,反而難看出到底什麽是不變的。天理教事件帶來的衝擊,尚未到此程度,更多是在已醞釀或發生的改變之上增減其程度,而非根本改變其方向。如此則該事件的影響是彌散而非爆炸性的,如同“風”般隨物賦形,卻很難具體感覺,更難確實把握與描摹。張著的價值在此,困難也在此。
但重要不重要本是相對問題,有賴於作者的視角。我們既要尋找天理教事件影響了什麽,更要探究這種影響在什麽地方減弱,又在什麽地方消失——後者刻畫出這一無形之風的形狀,並可對其所賦形之物(嘉道之時的官僚與王權、士人的社會情態等)有更深入理解。若如此,則變或不變就退爲第二位問題。
更進而言之,一代士風演變往往有其內在節奏,除與包括民變在內的世變有關聯,也與王朝政治的內在節奏相表裏。王朝衰則士氣往往轉亢,所謂橫議時代,明末清末皆此類。傳統士人皆飽閱書史,豈不知自古無不亡之朝?到天理教事件爆發,清朝開基已近二百年,以士人的歷史常識,由盛而衰實意料中事。古人亦不缺乏把握此種長程歷史變動的思想資源,文質論、①文質論在傳統政教體系中的含義與作用,見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301—324;文質論在清朝政教體系中的含義與作用,見楊念羣《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頁149—229。三統五德論與公羊三世說、②與嘉道之際相對應的,是龔自珍的世分三等說:“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乙丙之際箸議第九》,載《龔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6。借鑑於龔氏之說,錢穆認爲嘉道之際是“酷熱已消,衰象已現”的“初秋之世”。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614。佛家成住異壞四階段論均可爲代表。以此把握朝運、世運,則天理教事件就既是變化之因,更是變化得以呈現的“機”與“緣”。
最重要的變化來自嘉慶帝。在傳統政教體系中,士人具有政治人與學術人的雙重品格,從一開始就與王朝政治密不可分;皇帝則處於整個政教體系的中心,不僅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也是教化之主,對士風士習皆有巨大影響。清朝皇帝多大權獨攬,又有君師合一傳統,此種影響更被充分發揮——康熙朝褒揚理學,乾隆朝中後期褒揚樸學,皆影響到一時代思想學術之轉移。張著針對之前研究忽視皇帝對士風士習的影響,列專章研究嘉慶朝文化政策的轉向(第五章),可謂深有所見——嘉慶實爲天理教事件影響未曾親歷其事的士人的關鍵中介,略作比較就可看出其重要性。道光帝同樣深受鴉片戰爭結局刺激,卻選擇敷衍度日,使士林幾乎未受到實質性觸動,直到二十年後纔被庚申之變震醒;而嘉慶帝在深受天理教事件刺激後,主動試圖更法,增强了該事件的轉折性意義與全國性影響。
這一問題還可以反過來,對皇帝個人來說,這一“轉折”意味着什麽?這就需要站在嘉慶帝的角度,將他的個人抱負與作爲納入王朝政治的整體節奏,從而將他的個人生命史與王朝興亡史聯繫起來,非如此不能貼近皇帝的根本處境——宗廟社稷連貫、家國一體的傳統政教體系。創業之君與守成之主,自我期許與對世運的判斷雖皆不同,但最低都希望保住宗廟社稷。《尚書·洪範》“五福”以“考終命”最爲難得,此點對君主尤有意義——既爲個人善終,更意味着王朝延續。而其最高期許,則爲實現王道,以王朝政治達至不朽——在歷史具有極高神聖性的傳統中國,每一代帝王身後的謚號與廟號、正史中的褒貶,是他們這一自我期許的體現,又對其構成天然的約束。
具體到嘉慶帝,毋庸置疑,天理教事件對他有着極深的刺激,可謂他生命歷程中的轉折性事件。概因此時他已即位近二十年,本人亦已即五十知命之年。而此種前所未有的民變(直接進攻皇宮),似爲天心將改的徵兆,有整體否定他作爲皇帝的功業與價值的危險。在此種深刻的挫敗與焦慮下,他痛下罪己詔,以天命民命論表達對個人與王朝命運的憂思。對比白蓮教起義即可看到不同——他對白蓮教與天理教事件態度迥異,是因爲白蓮教起義爆發於乾隆仍在世時,如果以此爲盛世結束,則將使乾隆有晚節不保之虞,使他有“子議父”之譏,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以“守文”爲志,實是父子君臣禮法下的自然選擇;而天理教事件則完全不同,該事件發生於他執政十數年後,因此不僅是對王朝的挑戰,也是對他個人的政治抱負與生命價值的否定。簡言之,天理教事件纔是完全屬於他的歷史事件,也因此對他具有無與倫比的“當代重要性”。
歷史的複雜性在於,王朝自身的演變節奏與君主個人的生命節奏經常會有激烈的衝突。張著所展示的嘉慶即位初年欲“守文”而不得、天理教事件後欲改革而不能的困境,就體現了這一點。清朝懲前明“官橫士驕”之弊,“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①江南生語,見龔自珍《江南生〈橐筆集〉序》,載《龔自珍全集》,頁205。乾嘉之際,士人在長期禁抑後迫切尋求發舒,這種“天下嗷嗷新主資”的局面,與嘉慶“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家國認同爆發衝突,以洪亮吉案的發生而暫告一段落。在天理教事件後,感到危機的嘉慶帝放棄“守文”,試圖求言與更法,卻困於官僚的顢頇因循與士人的自我禁抑。簡言之,君主是王朝政治中最具能動性的主體,但其“主體性”仍受各種內在與外在限制,需要史家進行語境化的分析。
使人略感遺憾的是,張著受限於天理教事件的影響研究這一格局,必須時時讓天理教在主位出場,無形中削弱了嘉慶帝本人的“主體性”——只展現出他對天理教事件的“反應”,未及深入探究其自身生命歷程與嘉道思想學術變遷的關係,令人有意猶未盡之感。換言之,本書架構似未能讓作者充分展現其對嘉道之際的整體思考——若能置嘉慶帝於主位,置天理教事件於客位,或許能令作者更自由地達成其溝通這一時期政治、學術與社會的研究企圖。
綜上而論,本書凸顯了王朝政治更長程也更一般性的問題,即王權與士大夫的關係。在王朝政治的脈絡下,士人階級與官僚集團皆各有其演變節奏,與王權往往並不同步調。列文森認爲,中國的王權與士大夫階級間充滿張力,此種張力也是中國君主制的力量所在。②約瑟夫·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58—167。孔飛力則在其經典的對乾隆朝中後期“叫魂”案的研究中,提示了官僚系統的自利性與惰性對王權的限制。③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具體到嘉道時期,龔自珍觀察到,學術重心有從京師轉向山林之勢,①龔自珍《尊隱》,載《龔自珍全集》,頁87—88。具體論述,見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3。如此則王權影響士林的能力正在削弱中。這到底是嘉慶困局的原因之一,還是更大轉變的表徵,也似仍有未發之義。而其所提示的政治史與思想學術史的複雜勾連,則具有更一般的普遍性意義。
三 “在清朝發現歷史”的可能意涵
最後略作引申。該當如何理解“在清朝發現歷史”與“在中國發現歷史”的關係?晚近興起於美國的“新清史”研究試圖重新釐定清朝與中國的關係,已激起極大的爭論。②相關討論,見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本文不擬具體探討這一論爭(張著重點也不在此),只强調一點,對清朝人(不論滿漢)來說,“中國”絕大多數時候都必須通過“清朝”的中介纔能得到理解——超越於具體王朝之上的“中國”概念,只有在特定時期對特定人羣(如易代之際的遺民)纔可能具有某種意義。這就提示我們,必須更嚴肅地對待這一段歷史中的“王朝”因素,以更貼近清朝人思想與意義世界的方式呈現歷史。
在此視野下,近三十年來影響近世中國史研究甚巨的國家—社會二分模式,也有重新思考的必要。試圖在前近代中國發現市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種種學術努力,都受制於一個根本問題,即所尋找的“普遍”樣態實際上誕生自近代早期以來歐洲的歷史脈絡,直接應用於近世中國史(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前),很難避免變爲“格義”或目的論溯源。
事實上,傳統王朝史所內含的“政教”視角,可能倒是發掘近世中國演變脈絡的更恰當入手點。即使不論及傳統政體與社會的特性,僅就現代史學意義上的政治史與思想學術史研究而言,傳統王朝政教體制與思想學術變遷關係至巨,其間層次繁複。欲“在清朝發現歷史”,於方法層面必然要求政治史與思想學術史的綜合。此種要求自然牽連出傳統的“政教”視角。更進而言之,對古人而言,“政教”並非僅是認識論意義上可以選擇的視角,而是傳統政體與社會的惟一構成原則。在其所規定的世界內,皇帝、士人、普通民衆、儒學、民間信仰、京師、地方等因素,皆有着多層次的互相指涉關係,共同構成內在於近世中國歷史的意義之網,編織此一時期歷史演變中連續與斷裂的複雜糾葛。
此種連續與斷裂的複雜關係,鮮明地見於張著所着力探討的“嘉道的主體性”問題。長期以來,清中前期史與晚清史研究,如同兩個獨立的領域——前者爲中國古代史的一部分,或作爲明清之際諸般變化的延伸;後者則被置於鴉片戰爭所開啓的現代史脈絡下。由於問題意識、史料類型以及價值判斷標準等方面的隔膜,兩領域內學者所塑造的歷史圖景多有不能相合之處,兩時段間的實際歷史聯繫也顯得頗不分明。而兩領域的交疊時段,就是“嘉道”時期。近世中國政治與社會史中的轉型問題,以及思想文化史中的內在與外在理路問題,皆隱伏於此一時期。張著試圖挖掘這一被忽略的時段的歷史意義,以重建“嘉道的主體性”的方式達成“在清朝發現歷史”的目標,其學術努力實有啓發之功。
不過,嘉道時期的主體性的張顯,決不是要以犧牲乾嘉或道咸以降的主體性爲代價,毋寧說,進一步要挖掘的恰恰是這幾個“主體”的“主體間性”,而此種“主體間性”的挖掘,是爲了考察中國自身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脈絡,在這一關懷背景下,“明清”、“宋元”乃至“唐宋”、“秦漢”等超越單一王朝的時段也會自然浮現出來。換言之,“在清朝發現歷史”絕不意味着以清朝爲孤立主體,而是意味着將探尋每一王朝內在脈絡與發掘各王朝的“主體間性”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發現歷史”。此實需要致廣大而盡精微式的研究意願與能力,該界域研究的進一步展開,吾人也將拭目以待。
附記:感謝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青年史學沙龍諸位學友對筆者的思想激蕩。
(本文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本文係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晚清士人天下觀研究”(項目號:15XNB036)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