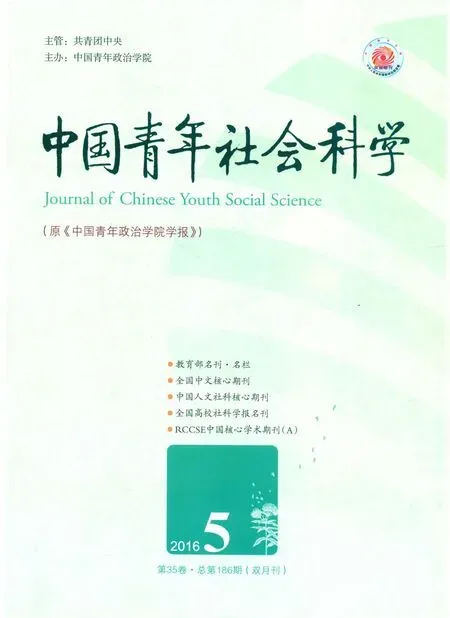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知识与权力
——对“研究生李某死于导师工厂”事件的反思
■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高校研究生教育中的知识与权力
——对“研究生李某死于导师工厂”事件的反思
■ 卢德平
(北京语言大学 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在知识教育诸层次中,对知识类型和领域的制度性分类,以及围绕知识的处理方式而形成的角色构成,反映出从强分类到弱分类的阶梯式变化。与知识处理方法的阶梯式分类路径同步,高校师生关系处于一种弱分类的框架下,教师和学生在知识接力和生活连接两方面出现界线模糊的地带。当教师一方将知识类型的弱分类策略转移到生活连接面,则教书育人的公共空间和师生的生活空间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叠。如果教师模糊了课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这两类知识的界线,超越教育制度的规定将两种知识类型整合为一,且在诸个知识领域表现出“无所不能”的权威性,学生会对课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的作用和功能混而不分,并对师生关系发生判断和实践的错位,而错位的极端可能导致悲剧的发生。
高校师生关系研究生教育知识类型权力话语
2016年5月23日,华东理工大学教师张建雨创建的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爆炸,造成近200平方米的彩钢板厂房坍塌,研二学生李某受导师张建雨指派在该工厂实验、实习,在事故中身亡*参见王瑞锋:《华东理工研究生死亡调查导师的“工厂”》,载《南方周末》,2016年6月2日。。高等教育界为之震惊,一时议论四起,成为新闻事件,折射出当前我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中,师生关系的扭曲和错位,导师和学生之间实际成为强制性雇佣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的生命而言,这种雇佣关系存在潜在的威胁。这一事件已超出了偶发个案的范畴,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生命的夭折与自然死亡周期之间的逆差所折射出的不公,也不仅仅是学生死于导师的“最安全”之手所产生的伦理性异常,而是揭示出在一种扭曲和不对称的人际关系中,弱势一方已经丧失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基本处置权,对于生命方式的选择权,以及提出异议、进行抗争的基本话语权∶研究生明知危险环境会对自己的身体构成威胁却不得不去做实验;读研期间没有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因为实现这种选择则意味着研究生生涯的终结;导师不让发表论文就只能不发表论文,导师让去工厂实验就只能去实验,不敢提出异议。研究生之死,不过是上述诸种基本权利丧失所导致的极端后果。但问题是:整个社会对于这种充满危机的师生关系长期保持失语状态;在师生关系这一漫长的扭曲过程中,沉默是大多数,但沉默或失语的权利又是谁赋予的呢?从沉默到发声,似乎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纠偏需要以生命的代价来提供勇气和动力,那么这个社会本身需要彻底体检、医疗,直至恢复健康的纠偏机制。
一、师生关系的错位与断裂
作为人际关系的一种传统形式,师生关系理应成为教师和学生的安全庇护和增益平台,并能有效去除一般人际关系的风险因素。事实上,人面临的风险因素有环境、人际、自我等几种典型的来源,而构成“风险社会”的主要因素在于人际源的风险[1]。人际关系的风险就其主要来源而言,包括人际陌生、时空遥远、交际环境的不可控、交际主体意向的不可把握等。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在于如何减少这些风险因素,以增进主体的福祉,而文化的再生产,一个主要的功能正是在于帮助人们趋利避害,减少风险。社会构成的基础是人际交流以及由此形成的关系,而围绕人际关系形成的各种制度规定,无非是为了降低人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减少其中的风险因素,朝着社会团结的方向运行。为此形成的契约文书、连带责任条文,以及一般人际关系形成过程中常见的介绍、推荐等前奏性阶段,都是为了降低人际交流的风险,建立一种安全、信任、增益的社会关系,构成有效的社会资本。人际交往是社会构成的先决条件,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与人的本质构成密切相关,因此,不存在为回避人际交往风险而陷于自我孤立的生存和发展路径。
无论是依据传统的文化界定,还是现代的教育制度设计,师生关系始终属于一种质量较高的人际关系类型,其交往的低风险甚至零风险、互动过程的增益性、交往效果的未来指向性等,都是一般人际关系所不具备的。那么,这种低风险的人际关系何以酿成死亡的高风险呢?一方面,需要审视研究生李某所处的师生关系的性质,是否这种师生关系已经由低风险,甚至零风险的人际关系转化为高风险的人际关系,而这种转化又是由什么因素推动的;另外一方面,需要考察这种转化在我国是否具有普遍性?否则,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为什么没能阻止这种风险的产生呢?
师生关系的形成来源于社会对知识的处理制度。为实现知识的文化接力,在教育的制度设计上对于知识的传递者和接受者这两类人给予了特别的分类和界定,这种制度化的界定拥有数千年的传统。师生关系实质上包含两个基本层次:在知识的处理方面二者扮演的制度性角色;在知识的接力过程中相互建立的人际关系。教师和学生作为知识接力的分工者面临着一种制度性分类[2],这种分类包括强分类和弱分类,前者规定了二者在知识处理职能上的明确界线,后者则允许二者间存在角色临时变换的弹性。分类还涉及对于所要传递和接纳的诸种类型的知识之间的界线问题。例如,如何厘定教学知识与课外社会实践知识之间的界线,教师是否有权同时介入这两类知识的传递,学生是否必须接纳来自教师对这两类典型知识的传递介入。强分类要求明确划定两类知识的界线,并相应地划定教师和学生围绕两类知识所形成的角色关系,而弱分类则以淡化两类知识的界线为基本原则。
对不同教育层次的考察发现,从学前教育,到基础教育,再到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中较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对知识类型和知识领域的制度性分类,以及围绕知识的处理方式而形成的角色构成,反映出从强分类到弱分类的阶梯式变化。从强分类到弱分类的这种阶梯式教育制度设计,在知识的处理方式和方法上赋予了高等教育较大的自由空间。但这种自由度的前提是:成年学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高校教师对于知识的处理具有高度理性的判断能力;教师具有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和能力,不会混淆知识类型之间的界线,也不会不当或过度介入学生对两类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过程。与知识处理方法的阶梯式分类路径同步,高校师生关系同样处于一种弱分类的框架下,教师和学生在知识接力和生活连接两方面出现界线模糊的地带。当教师一方将知识类型的弱分类策略转移到生活连接侧面,则教书育人的公共空间和师生的生活空间不可避免发生重叠。当教师模糊了课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的界线时,或者当教师超越教育制度的规定将两种知识类型整合为一时,学生会对课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的作用和功能混而不分。或以前者替代后者,或以后者替代前者,极端言之,可能以对社会实践知识的学习全面替代包括课本知识在内的所有类型知识的学习。目前在不少地方出现的以社会实习长期替代学校知识教育的做法,已经把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转化为社会分工体系里的廉价劳动力。与这种转换同步发生的是,教师在课堂知识领域里的权威性转化为各种知识的权威性,或以课堂知识的权威性证明在各个知识领域的权威性,自然也延伸到学生在整个社会生活场域所获知识的权威性。在教师“无所不能”的权威性面前,学生很容易丧失自己学习和生活的双重信心。这就为驱使学生在教育体制之外的社会领域充当廉价劳动力准备了条件。高等教育制度设计的弱分类留下了师生关系的灰色地带,而控制这一灰色地带的因素主要在于教师的道德自律和学生的理性判断。研究生李某的悲剧恰恰源于高等教育制度弱分类下的教师弱道德自律和学生弱理性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错位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缺少了师生间的对话元素,也不是教师和学生之间围绕知识处理的社会分工发生了错位,而是对于知识的分类框架催生了颠覆性错乱。是弱分类的制度安排存在着过于仰仗教师道德自律和学生理性判断的前提条件,为机会主义者留下了可乘之机,使得弱道德自律的教师通过模糊不同类型的知识界线,并借助泛化的知识权威性而对所有的知识领域进行控制,从而使学生将师生关系理解为一种无需批判和反思的被动性知识传递和接纳关系。在这一过程里,教师视学生的无条件服从为应有状态,而学生视教师的全面权威为知识和生活场域的绝对决定力量。这种师生关系既超出传统师生关系的范畴,也远远逾越了高等教育对于师生关系的制度规定。
因此,这是一种错位的师生关系。在这关系下,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均以外在的权力意志为自我的行动逻辑,以自我对他者的无条件适应为行动条件。教师完全屈从于外在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内在的道德要求,学生完全屈从于教师泛化的权力意志而放弃了内在的理性批判,以此建构形成的“自我”完全工具化。无论是研究生李某,还是其导师,二者的“自我”构成已经转化为另一种“自我”,后一种“自我”的实现以前一种“自我”的让渡为排斥性条件,并表现为主体意志的绝对让渡。对于这种错位的师生关系的质疑,伴随着对于所转化的另一种“自我”的合理性、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错位的师生关系的质疑。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普遍评论,恰恰也说明了当代中国的高校师生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错位,而普遍化的错位,则有可能使合理、健康的师生关系形成断裂的常态。事实上,这种错位甚至断裂的常态已经持续多年,动摇了人们对于师生关系的既有概念框架,指向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师生关系的本质构成上所发生的裂变。问题在于这种错位的师生关系正在演变为师生关系的常态和趋势,对此,个体无力改变,社会也无力改变,而且有赋予其合法性的明显迹象。如果不对这种师生关系的颠覆性错位进行反思和批判,并谋求一种新的方向性调整,那么其演变结果将为整个社会所普遍接受,并形成全新的高等教育规则或潜规则去约束后来者。如果教育的制度设计朝着更符合人性圆满的方向优化,让师生关系重新恢复到中国几千年验证过的合理模式,那么李某的血没有白流,其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在此后的岁月里不断显露。
但是,一个经过数千年验证的师生关系模式何以会发生颠覆性错位呢?错位的行为主要源于主体的价值判断。如果一种教育制度以收费和服务的经济关系来框定师生关系,则教育的制度性设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教师以赚钱而非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自己的职业定位,则教师的本质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学生视导师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非知识和道德的传授者,则学生在师生关系的认识和判断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三种根本性变化发生于过去三四十年间,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讲,已经构成了至少两代人习见的常态。如果不是这一事件撕开了师生间的颠覆性错位关系,可以预见很少有人会对这个常态做反思和批判。相反,对于反思和批判,会有更多的人将其批判为对陈旧、过时的师生关系的挽歌,也会有更多的人以进步的旗号赞扬这样的颠覆性错位。
二、师生关系的实践逻辑:传统与现代
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具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拟亲属关系特点,这在西方国家极为罕见,然而在一些东方国家,如日本却保留至今。与血缘关系构成价值类比,知识的传授也使得传授者和接受者之间确立了类似于父子(女)/母子(女)之间那种以情感为核心的关系,形成数千年的教育传统。在这种拟亲属关系的价值框架下,教师兼具传道、授业、解惑等多重功能,并且把学生当作弟子,学生也视老师为再生父母,是需要感恩的对象。这种拟亲属关系首先为师生双方筑起安全的屏障:血浓于水,血亲是安全的最后防线。但这种拟亲属关系性质的师生关系仍然以学生一方的拟孝道行动保持着师生间的界线,而不以拟亲属关系介入彼此的私人空间。但在一方求助同时,另一方仍在道义上肩负起对对方的多元责任。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使得二者一旦确立这种关系就具有不可逆的作用,学生中途更换门庭显然会遭到道德的挞伐。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分类范式,在安全屏障和非工具性情感侧面,具有等同于血亲同盟的拟亲属关系功能,而在知识传授的工具性侧面,则具有超出一般职业要求的严苛性,并不以拟亲属关系的亲近性而消弭职业要求的距离感。这种远近维度的完美结合又是单纯的血亲关系所不能实现的:父母对于子女的严厉往往伴随着子女对父母亲的疏远。但是,中国这种传统的师生关系存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师生关系的数量限制。当这一前提消失,出现一个教师同时指导多个学生的情况,传统的拟亲属关系性质的师生关系则会遭遇危机:教师面对众多学生时有效的情感分布发生困难,而众多学生在面对同一教师时,则容易将共同的师生关系泛化为缺少责任归属的公共产品,部分学生产生搭便车的心理,索取多,付出少。过去4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招生数量年年攀升,为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积累了现实的制度性基础。
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并非瞬间完成,而是从教师和学生的“自我”重构开始,并且以具备重构的现实土壤和制度环境为重要前提。置换的第一步是对拟亲属关系性质的瓦解,伴随的结果是教师和学生互相放弃在拟亲属关系条件下对对方的无限责任,并将二者的关系逐步缩小到传授知识和接受知识的职业关系。置换的第二步则是在这种职业关系中引入经济学概念,即教师处于知识销售者的角色,学生则通过支付学费而获得知识购买者的角色,伴随的结果则是购买行为结束后彼此不再存在过多的关系。置换的第三步则是将第二步的经济关系推向工具性商业关系,伴随的结果则是学生成为教师获利的工具,教师则是学生收入的来源。通过上述典型的三个步骤,师生关系从传统的拟亲属关系被颠覆性置换为商业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市场经济法则为这种理性行为提供了充分的注脚。
研究生李某的悲剧恰恰发生在上述第三阶段。不仅如此,李某的死亡证明了这一阶段的恐怖,同时这种恐怖如果得不到遏制,还有可能进入第四个阶段,即工具性商业关系演变为商业性剥削关系,伴随的结果则是恐怖的不断放大。这一不断放大的恐怖性在于师生关系已经突破了法律的界线和良知的底线。消除师生关系的非常态性,进而消除各种错位的人际关系,是建设一个正常的教育体系的必要途径。形成这种非常态的根源不仅仅是社会的结构变迁和制度变迁,更重要的在于人们的主体意识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不能正视自我的根源,而全部归咎于外部因素,是自我怯懦的表现,根除自我的怯懦,比根除外部因素更加艰难。
中国社会变迁历经数千年,东方国家如日本等也历经无数次社会变迁浪潮,传统的拟亲属关系性质的师生关系并未同步消亡,何以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就促成了这种置换呢?对于其原因的反思,远没有阻止这种无止境的置换的社会行动来得重要。
阻止师生关系颠覆性置换的社会行动应始于解构导致颠覆性置换的权力关系和话语体系。在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的过程中,无论教师还是学生,甚至整个社会都放弃了维护原有关系秩序的权力要素和话语系统,而代之以新的形式。权力是对约束对象可能性的控制,话语则是围绕权力的有效实施而形成的合理化解说。在师生关系中,问题并不在于对权力进行排斥,也不在于非要对教育过程的权力因素进行解构,并形成犬儒主义式的话语表述。权力既是控制又是协调,其基本实践目标指向秩序的确立和维持。当权力进入人际关系,其合理性需要落实到合理人际关系的确立和维系,而这也是社会构成的必要条件。任何类型的师生关系的确立,实质上都不可能排除权力的行使和对权力的遵从。权力的构成基础需要包括权力行使和权力遵从双方的合理意愿,且对于权力的行使和遵从可以增进双方的合理利益。师生关系的异常并非直接导源于其间的权力关系,而是对这种权力的实践方式。只要对师生关系中任何一方权力过度放大,且权力的实践方式超出师生关系的合理、合法边界,就会导致双方权力的失衡,形成权力压迫,进而在长期的权力滥用中扭曲主体的意识和认知。
在传统的师生关系中,拟亲属关系的权力伦理学基础规定了师生彼此的权力构成,并为此形成了维护权力秩序、约束权力界线、延续权力效果的话语体系。在这样的权力构架中,教师对于学生的道德可能性、知识可能性,以及生涯发展的可能性均具有规范和约束的义务,并强调言传身教的重要作用。教师对学生诸方面均有了解的权力,学生也有向教师多方面咨询的权力。在学生违背道德、知识、生涯发展诸方面的社会规范或师生间确立的特殊规则的时候,教师拥有多方面批评的权力。由于拟亲属关系的基本条件,教师视学生如己出,故将权力触角延伸到学生的诸个侧面,而学生亦不把这种拟亲属关系性质的权力控制视为对“自我”自主性的威胁。这种拟亲属关系框架下的权力关系因而获得了关怀伦理学(ethics of care)的基本特征[3],从而减轻了权力的强制性。正如诺丁斯所说“关怀始于家庭”[4],具有真实性的情感关怀首先产生和持续在熟悉或亲近的人们之间。师生间拟亲属关系的确立,使得这种关怀成为传统的师生间的义务,构成相互主体间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传统的师生关系中,关怀的伦理为权力关系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据,同时也使得这种权力关系获得了道德约束,而非单纯的外部强制。师生间内生的这种控制和遵从相结合的权力关系,由于关怀伦理的先决条件,以及拟亲属关系的情感设定,根本上成为诉诸对方利益关切的权力实践。这种师生关系的权力模式具有明显的双向性:教师拥有控制学生诸方面可能性的权力,也因关怀伦理的基础而使教师获得了学生内生性尊重的权力;同时,学生也有获得教师在道德成长、知识进步、生涯发展等各个方面予以指导的权力。在这样的双向权力结构下,不仅教师能够把握学生的诸种可能性,形成权力的有效实践,而且学生也对教师在指导的立场、态度、方法等诸方面的可能性拥有了合理的预期,形成对整个教育过程的把控权力。
如上所述,传统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经历了三个步骤,并且存在向第四个阶段发展的趋势。这三个置换步骤实质反映了师生关系中的权力基础和权力结构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传统的师生关系的权力基础——拟亲属关系,被商业经济关系所代替;基于情感设定和拟亲属关系从而具有边界约束力的权力实践,被教师基于单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权力滥用所代替;师生权力的双向性被教师权力的单向性所替代。这种替代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因素:第一,教师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频繁使用商业话语,以赚钱的哲学替代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话语体系,并和学生生涯发展的实用性联系,形成有效的劝说效果。第二,重构的师生关系已经远远偏离了传统的师生关系的设定范围,对于教师以商业话语替代传统的知识传授的话语策略构成认同,并在生涯发展的实用性联系上寻找到重构的合理化依据,因而客观上成为这种颠覆性置换的同谋。第三,学生在教师的话语霸权和单向权力过度控制的条件下放弃了合理的主体性,以及对师生关系应有状态的把握,成为教师话语体系的非批判性接受者,为教师滥用商业性权力提供了条件。第四,市场经济的理性人逻辑为传统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提供了背书,使短期的经济回报优先于长久的知识积累的行动逻辑获得社会的广泛接受,使师生关系的商业化趋势获得合理化。第五,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他人,如父母、亲戚、同学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于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的趋势持默认甚至支持的态度。上述诸种因素的叠加为教师以市场法则的名义滥用、控制学生诸种可能性的权力提供了方便。权力的触角延伸到学生的学业、就业,甚至生命安全等各个方面,而在失去传统师生关系所具有的关怀伦理的权力基础之后,教师对于学生的权力控制完全被置于商业利益的原则之上。逐利的原则只能使权力不断放大,并使权力敢于冒险超越法律和道德的边界。传统师生关系中的情感和道德条件恰恰为教师的权力提供了约束的边界,而且为师生关系中的权力双向性提供了日常实践的保证,使得这种权力的实践远离法律的红线和道德的底线。对于这种传统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拟亲属关系对于权力的情感和道德约束力遭到漠视,而这种软性的约束力恰恰维持了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达数千年之久,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福柯指出,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存在着生产技术、符号技术、权力技术、自我技术四种重要的“技术”[5],这四种“技术”既是人的社会行动的痕迹,又成为制约人的社会行动的规则。研究生死亡事件所揭示的师生关系中的权力失衡和权力滥用,以及对于这种权力的传统约束力量的置换,实质上又是四种“技术”同步变更和综合作用的结果。四种“技术”因各自的秩序和规则而构成必要的区隔,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在师生关系上出现的颠覆性置换,实质发生了“技术”类别的错位和挪用,是将生产技术领域的经济法则挪用进符号技术场域,构成不同于传统师生关系的话语体系,由此推动了权力技术场域和自我技术场域的规则变更。虽然我们还能看到分类的沿袭,但四个技术场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可以说是社会的本质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是研究生李某之死所揭示的从师生关系的变迁指向整个社会变革的一条看不见却存在已久的逻辑线索。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反映了权力场域和话语(符号)场域的颠覆性规则变换,同时也是生产场域和自我场域剧烈变化的结果,只是生产场域作为行动的背景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状态,自我场域的变化更是由于个体躯体的间隔而隐性化,甚至不为人们所意识到。
三、师生关系的重构
由于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折射出生产、符号、权力、自我四个技术场域的错位和变化,因此返回传统师生关系的努力所面临的挑战将是深层次的。重构一种安全、合理、增益的师生关系,需要从四个技术场域进行生态修复,这显然已经超出当今社会的能力。从逻辑路径看,需要将生产技术对于符号、权力、自我三个技术场域的介入清除掉,但以经济形态呈现的生产技术更多处于背景状态,构成其他技术场域的底色,清除起来尤其困难。但是,生产技术对于其他技术场域的介入本身并不构成颠覆性置换的充分条件,关键在于:对传统师生关系的颠覆性置换,是以生产技术的规则去替代其他技术场域的原有规则,并彻底改写了其他技术场域的内在结构。这才是泛市场化,以及经济利益至上的社会浪潮改写教育观念、颠覆性置换传统师生关系的本质问题所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凡束脩以上,有教无类”的生产技术对于其他场域介入的先例,也说明了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完全为了教育的观念和理想放弃基本的物质需求。但生产技术对于其他场域的介入需以不改变其他场域的既定规则为前提,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模式对于这一点把控得非常到位。
将颠覆的师生关系复原到传统的模式存在着上述难以逾越的社会结构障碍,但参照传统的师生关系模式,应充分考虑当今的社会发展特点,重构一种包含传统师生关系合理内涵,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又具有较高适应性的新型师生关系,可能是一条现实且不得不采取的合理路径。这条路径将市场经济法则控制在师生关系的适度范围内,明确划定不可逾越的界线,是当代教育制度设计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同时,确立教育场域中的合理权力规则和相应的话语体系,从质的规定性上区别开一般市场经济的生产技术,是保持教育应有内核的需要。这样的教育内核,秉承传统,但在呈现方式上又契合时代的社会变迁,体现了教育本质连续性中的手段和方式的变化。由此出发,学生缴纳学费接受教育,所购买的仅仅是上课的资格和学习的时间,而不是教师的智慧,更不是教师的人格和学生内生性尊重的权力。“凡束脩以上,有教无类”中的经济手段不过是建立师生关系的见面礼,而不是为购买某种商品所需要支付的全部金额。教师也不以一手“束脩”一手授课的商业销售方式来实施其教育活动,而是以教师特有的人格和尊严,以对学生超乎功利的教诲为教育实践的先决条件。教师不因学生缓缴、少缴、甚至不缴学费,就停课罢讲,而据此剥夺学生受教育资格的永远是非教师序列的行政官员。教师的这种形象具有传统的投影。据此建立的师生关系,才具有超越生产技术的传道、授业、解惑的遗风。即使是这样的师生关系重构,其过程都是复杂和艰难的,其结果也未必能达到预期。但是,没有这样的重构努力,传统的师生关系将离我们越来越远,直至彻底无法重构。
研究生李某之死应该不会是个案,其导师也不是当今高校校园里的少数派,由此建立的颠覆性师生关系模式也不会在短期内遭到摒弃。但是,很多教师在通过日复一日的教育实践重构着合理、健康、增益的师生关系,而这样的教师在当今的高校校园里也不是少数派。二者的分化似乎是事实,而时代提出的课题在于:我们正处在分水岭上,放弃或努力,都有可能改变一种趋势。重构一种结合传统内涵和时代变迁的新型师生关系是改变颠覆性师生关系的关键力量。
[1]Beck Ulrich,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2,pp.127-138.
[2]Bernstein Basil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Transmission (Volume III),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3a, pp.77-86.
[3][4]Noddings Nell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pp. 29-31.
[5]Foucault Michel,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7,p.225.
(责任编辑:张宇慧)
2016-07-10
卢德平,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符号学理论和汉语国际传播。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关联国主要社会场域汉语传播的推拉因素及其对传播过程影响的研究”(课题编号:15JJD74000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