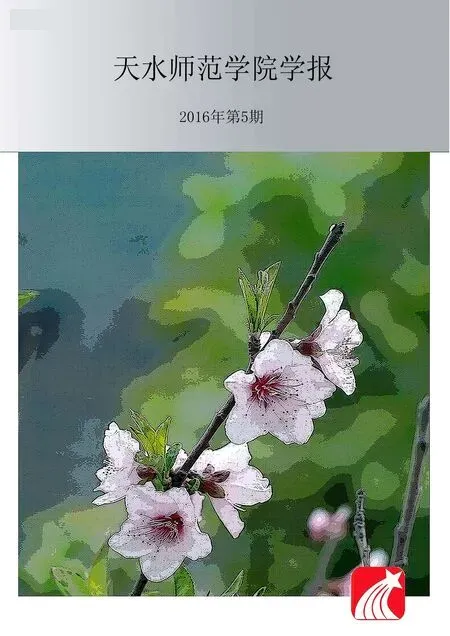陇东南红色歌谣的产生背景探析
李天英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陇东南红色歌谣的产生背景探析
李天英
(天水师范学院 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歌谣以隐喻又稍带几分幽默的方式表达着淳朴的革命情怀,其影响遍及全国,成为包括陇东南地区在内各个根据地不可获缺的宣传方式。“两当兵变”失败的教训让革命者更加意识到宣传方式的重要性,也凸显了红色歌谣能够将宣传教育潜移默化地转换成革命精神的价值。陇东南是一块深受压迫又有持久反抗精神的土地,为创作和接受红色歌谣提供了思想基础;当地人民与红军共同奋战的经历与鱼水情,为红色歌谣的产生提供了题材来源;陇南人表情达意的方式及其地域山清水秀和诗情画意的特质,又成为红色歌谣接受与传播的基础。
红色歌谣;革命思想;宣传;产生;陇东南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不稳定的状态为新生的革命力量提供了不断成长的契机,中共中央发出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白军变成红军”的兵变指示,全国各地武装兵变四起。1932年2月,甘肃庆阳正宁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这在西北武装斗争史上具有转折意义,也意味着新阶段战争的开始。1932年4月2日零点,习仲勋、吕剑人等同志领导士兵们在两当县打响兵变的枪声,“这次兵变对于牵制国民党在西北的兵力,瓦解敌军力量,减轻对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的压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1]6
在每一次战斗打响之时,通过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来传达战斗精神是让士兵进入战斗状态的有效方式,杨林在回忆西华池兵变时也特别强调平时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兵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刘书林在《习仲勋随军驻防凤县及领导两当起义》中说到,当时,该部队在习仲勋同志的领导下鼓励士兵向长官斗争,要求民主,反对压迫,宣传不要迷信命运,要进行斗争才能翻身,做自己土地上的主人,宣传苏俄是我们的忠诚朋友,我们要联合苏俄及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民族进行斗争,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除此之外,还在沿途墙壁上贴标语,如“反对围剿红军”、“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些宣传工作为进一步的战斗争取到了更多的群众基础,也为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革命思想宣传的重要性及红色歌谣的产生基础
1932年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制定了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任务,并责成陕西省委加强杨虎城及其他国民党驻军的工作,“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1]3巩固和扩大陕甘游击队,除了在国民党驻军中组建共产党组织,还要“加强对士兵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和爱国思想。”[1]4他们以各种隐蔽的身份和方式召开会议,散发传单,“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纳、贪官污吏对农民的刹削和压迫,以及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压榨掠夺人民的罪行;鼓动士兵向长官清算伙食、被服、军械等经济帐,争取实行经济民主,反对长宫打骂、欺压士兵,争取实行政治民主;教育士兵不要迷信命运,要进行斗争”。[1]65此外,他们还通过各种关系,比如同学、老乡等发动士兵的日常斗争意识;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如兄弟会、委员会、读书会、研究会等把士兵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各部队内的党组织还充分利用这些组织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如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要求按时发饷、发鞋袜、发衣服、发烤火费,要求经济公开等,并结合宣传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民主生活,号召士兵团结起来,打死反动官长,投奔红军游击队。”[1]5
从上到下的宣传和思想鼓励不断激发战士们的革命情绪,明确斗争的对象。“在兵暴比较频繁和活动时间较长的地区,通过宣传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为我党以后在这些地区开展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71932年10月25日,《陕西省委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更加明确地提出加强宣传的目的和方法。首先,在士兵的生活举步维艰的时候,为他们指明,革命兵变、投身到红军的战斗中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其次,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采取政治鼓励和教育的方法,注意提高士兵战斗情绪和政治觉悟;最后,采用书面和口头的形式让士兵明确党的思想,为党组织争取更多的力量。
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张秀山在《甘肃、宁夏兵运工作回忆》中提到,军阀部队中的士兵经常吃不饱肚子,但是,精神食粮却是丰富充实的,他们经常举行政治学习,开学习会、辩论会、上政治课、探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学兵队里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我记得大家还编了许多秧歌,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反动军阀搜刮老百姓、反动军官欺压士兵的丑恶行径。”当时,学兵队的同志写的歌谣和诗词大量的都是揭露军阀混战不休、土匪猖撅、人民遭受巨大苦难的情景。有如“甘肃封建割据,搜刮剥削,苛捐杂税。官兵变土匪,土匪变官兵,民不聊生,十室九空。”[1]49还有反映穷人生活的歌谣,内容丰富,情感真切,令人感动,如“天上的星星沙沙稀,地上的穷人穿破衣。焦头头筷子泥糊糊碗,穷人的日子难上难。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眼泪把心淹。吃了上顿没下顿,揭不开锅来难死人;穿了冬衣没夏衣,六月天翻穿老羊皮;一没铺来二没盖,又饿又冻实难挨。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咱可怜。庄稼里数不过糜子光,人里头数不过咱凄惶。为人哪个不想活,这样的光景实难过。要穷就穷也安生,财东家要账如催命。天气越冷风越紧,人越有钱心越狠。驴打滚利钱还不完,狗腿子把门槛都踏断。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天生下受苦人活受罪。黄连树上吊苦胆,穷人的苦处哟说不完。青天蓝天紫蓝的天,老天爷杀人不眨眼。”[2]12也有揭露地主的贪婪和对穷人的压迫:“庆阳城,地势险,连的东西二架川;庆阳城里八大家,东西二川全霸占。八大家,心太残,地租债利重如山;又开当铺又开店,穷人血汗要咂干。”[2]17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闹革命,终于让穷人看到了生活的盼头,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则溢于言表,孙万福写在《歌唱毛主席》中写到:“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毛主席好领导,天下尽清官,他一切为百姓,赛过活神仙,边区办的呱呱叫。一片好河山,毛主席定计划,遍地开红花,老百姓拿大权,再不受欺压,自己的事情自己管,人民坐天下。”[2]117这些歌谣没有矫饰的语言,没有宏大的叙事,却又句句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即使是抒发感情也是直抒胸臆,不但能够表现苦中作乐的情操,又能以短小精悍、隐喻叠加又稍带几分幽默的形式,一针见血地反映现实,让人有一吐为快的爽快劲。总之,战争时期的中国,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在宣传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适应环境的需要,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除去主要的民间形式以外,也包括‘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形式,戏剧、曲艺、诗歌、散文等各式具备,其中又以歌谣、戏剧、通讯报导所发挥的作用最大,最受欢迎。”[3]
二、红色歌谣在战争年代的重要意义
歌谣是由集体创作、口头流传于民间,反映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的一类民间文学,它具有“合乐为歌,徒歌为谣”的显著特点,它主要传播在中央苏区和各个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它以浅白平易、生动鲜明、朗朗上口的艺术表现形式宣传革命思想、壮大革命声势。陇东南红色歌谣是指“两当兵变”之前、期间以及兵变之后的革命时期,流传于陇南、天水和陇东的红色民谣。红色歌谣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性的方式唱响了内心对革命的需求,也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对生活诗意的向往。歌谣极大地降低了说教的枯燥,以诙谐幽默、通俗的方式认识新事物,拉近八路军与人民的关系,比如“八路军是抗战的,五十七军是逃难的,张里元是捣乱的,三十六师是要饭的。”利用形象的方式让美的更美,丑的更丑,将对国民党的嫌恶之情潜移默化到读者的心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中把红色歌谣运动作为“农村俱乐部运动”。中国共产党古田会议明确提出并强调,要运用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学形式编写各种教材。之后,各区乡都成立自己的俱乐部,俱乐部内设体育、墙报、晚会等委员会和剧团,几乎村村有墙报。此外,《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也称,要“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责督促及调查之责”。
1934年,《青年实话》出版了《革命歌谣选》,其中的歌谣内容广泛,推动了群众歌谣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还贯彻执行了一系列比较先进的革命教育方针和政策,实行普及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革命歌谣选集》的序言明确地写到歌谣在革命中所发挥的现实作用:“一九三三年的广州暴动纪念节,代英县芦丰、太拔两区的少年先锋队,举行以区为单位的总检阅,并举行游艺晚会。”在演艺时,妇女们组成的山歌队通过互唱山歌的方式,鼓励青壮年能够参军,壮大红军队伍,“因为他们是指着名字来唱,所以格外动人”。结果是“太拔全体出席检阅的队员加入红军”,芦丰的“七个队员加入红军”。革命歌谣的感染力和宣传力量渗透在革命的每个角落,有不少地区在“扩大百万红军”运动中,青年都唱着歌去参军。于是,歌谣成为红军表达各种情绪最令人振奋、又喜闻乐见的方式。
歌谣能够成为革命宣传重要的方式,也得益于毛泽东同志的启发。在抗日革命的浪潮中,毛泽东看到了民众不可估量的力量,尤其在抗日宣传中重点强调全民总动员,他认为不论是工人、商人、学生、知识分子,还是妇女儿童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1937年8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上的讲演”就以歌谣的形式激发将士抗日的热情:“我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平律!保卫华北!收复东四省!八一运动大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4]215宣传简单平白,句子短小精悍,铿锵有力。1938年8月7日,《街头诗运动宣言》就号召:“有名氏、无名氏的诗人们啊,不要让乡村的一堵墙,路旁的一片岩石,白白的空着,也不要让群众会上的空气呆板沉寂。写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唱吧——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我们要争取抗战胜利的这一大时代中,从全国各地展开伟大的抗战诗歌运动——而街头诗运动,我们认为就是使诗歌服务抗战、创造新大众诗歌的一条大道!”[5]10
其实,将歌谣这种“伟大的艺术”作为有意义的民间艺术早在1920年12月北大成立的歌谣研究会的活动中就早有体现,这场轰轰烈烈的7年歌谣运动改变了人们对歌谣的看法,使之成为具有很大价值的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研究会创办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刊物《民谣周刊》也被看做是中国承上启下的一场文化变革运动的结晶。歌谣与正统的文学不同,它简单通俗,但是却裹挟着正统文学中缺乏的鲜活的生命力和表现力,它来自民间,也形象地再现着民间生活的个性特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前后,红色歌谣再次发挥所长,以活泼生动通俗的形式记录、诠释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和这个年代的特殊的情感。
三、兵变前后陇东南红色歌谣的产生背景
陇东南是一块深受压迫的土地,百姓持久而彻底的反抗,为创作和接受红色歌谣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早在1915年,陇东南就以“鸡毛传贴”抗交苛捐,1929年,正宁县成立“红枪会”抵制压迫,后来还有在华池南梁、乔河一带出现“哥老会”、“扇子会”,葫芦河两岸的“镢头队”、“门袋队”都发出了反抗的声音。“地处秦岭深处的两当县,用红色革命之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早在1932年,在这里就发生过鲜为人知的‘两当兵变’——陇南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在这里诞生。”[6]68
当地人民与红军共同奋战的经历与鱼水情,为红色歌谣的产生提供了题材来源。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两次过境宕昌的哈达铺,沿途生活艰难,陇南人民为部队筹备粮草物资,在红军的宣传鼓舞下,陇南地区就有8000多人参加游击武装,5000多名陇南儿女应征入伍,哈达铺的磨难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转折点,确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去向。“红六军在两当期间,和广大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深得群众信任,军民形成了鱼水关系。一些健在的老人,至今还记得红军为群众做好事。他们有的帮助群众进行秋播;有的为驻地群众挑水、砍柴。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部队临走时,还给农会干部和当地群众赠送了许多纪念品。”[6]73全县上下参军的青年农民达80多人,如杨松林、张许珍、麻生保、罗成录等。他们用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也诠释了军民情。在红六军走后,太阳寺农民王普的母亲用自己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行为,在敌人大搜捕时,硬是冒着失去性命的危险,收留了一位因伤掉队的女红军,一直到女红军伤痛痊愈才被送回部队。1937年,“两当县抗日救亡剧团”,在两当、成县、徽县、天水城乡编演抗日节目、许多陇南抗日先锋队专门成立抗日宣传队,到街头、乡村宣传革命思想等,这些亲力而为的经历形成红色歌谣经得住考验的现实基础,真所谓“红军来了晴了天,红色歌谣万万千”。
陇南人用歌谣表情达意的方式是红色歌谣产生的接受基础。《古谣谚》中记载,从汉初至明末,陇上都有以歌谣叙事、记人和抒情的记载。如《陇水歌》:“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7]82《陇上为陈安歌》:“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囗骢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弃我囗骢窜岩幽。天大降雨追者休,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阿呼呜呼奈子乎,呜呼阿呼奈子何!”[7]112《庆阳军中为张良臣语》:“不怕金牌张,惟怕七条枪。”[7]229《陇头俗歌》:“陇头流水,呜声幽咽。运望秦川,心肝断绝。霞关遥望,秦川如带。”[7]332近现代,陇东南用来表达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诸多歌谣更是早已自成体系。比如《陇南地区民歌集成》中将民歌分为号子类、田歌类、花儿类、山歌类、小调类、社火秧歌类等,其中非常详尽而形象地记录陇南各县人生活的内容和感受。《中国歌谣集成》中,在以汉族为主的陇上歌谣的简介中认为,作为汉文化的陇上歌谣,与其他地方相比较,歌谣门类较为齐全、成熟,这是当地人接受习惯沉淀的印记。当代,陇南地区的诗人也是蔚然成风。
气候湿润、山清水秀的陇南有着催生诗情画意的特质。严汉万在《忆长征中在陇南山区休整》中说道:“徽、成、两当、康县地区,山清水秀,乌语花香,气爽宜人,足可和江南的自然条件相媲美。我们初到时,对这样的环境既喜欢又迷惑。喜欢的是好像回到了家乡、迷惑的是北方还有这样好的地方?感到有些费解了。刚好群众送来了慰问的大米。一个同志看到大米不禁吃惊地问道:‘啊!这里是北方还是南方?’好像不相信自己走的方向了。”[8]120吕剑人在其诗歌《红军长征到两当》写到:“9月,瓜果飘香广香河沿岸,红军战士攻占两当和群众打成一片……10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广香河畔笑语欢天。八十多名青年农民参加红军,无怨无悔。”[8]208很多的革命者和诗人每每想起两当及它的历史,也常以诗歌表达心中的感慨。比如,陈靖《渔家傲·两当忆》、峭冰的《闪闪红星照两当——赞两党兵变及红军两次在两当》、苟昌盛的《放歌两当兵变》和《红军长征到两当》、曹建国的《两当·1932》、阎志良的《奔向大海的溪流——纪念两当兵变75周年》、徐小林的《我与逝者有个约会——观两党兵变遗址有感》等。
或许陇东南红色歌谣所反映的场景已经离我们远去,仅仅停留在对事实的还原又会使研究偏离方向。但是,当研究的触角延伸至文化的主观层面时,就会发现不管过去多久,精神在时空中总是相通的。吕彬的诗歌《不止是高山仰止的举敬》中有一句话,用来表达这种精神是再恰当不过:“勇士走了,信念还在;战争停了,精神还在!是的,置于我们心底的是—份信念的坚定、是一种精神的永恒。”[8]218
[1]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汇编:第三缉[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2]高文,巩世锋,高寒,编.陇东革命歌谣[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3]唐韬.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地:文献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5]中共中央委员会.街头诗运动宣言[J].新中华报,1938,(8).
[6]郑宏,主编.陇上红色之旅[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
[7]杜文澜,辑.吴顺东,等,点校.古谣谚[M].长沙:岳麓书社, 1992.
[8]夏建华,主编.红色两当[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艾小刚〕
On the Revolutionary Songs’Emerging Background in Southeast Gansu
Li Tiany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Gansu741001,China)
The revolutionary songs’influenc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du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eriod,and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way to publicize revolution.The failure of Liangdang Mutiny taught the local people the importance of propaganda,and they realized that the revolutionary songs could evoke revolutionary spirit among the people,and basically southeast Gansu had been a land where oppression had also existed and the people were possessed with rebellious spirit,which provide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and acceptance of revo⁃lutionary songs.The local people and the Red Army had common experience of fighting,and this prepared sources of materials for revolutionary songs.
revolutionary songs;revolutionary spirit;propaganda;emerge;southeast Gansu
I227
A
1671-1351(2016)05-0054-04
2016-06-19
李天英(1978-)女,陕西武功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
甘肃省社科项目“‘两当兵变’陇东南红色歌谣整理与研究”(YB08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