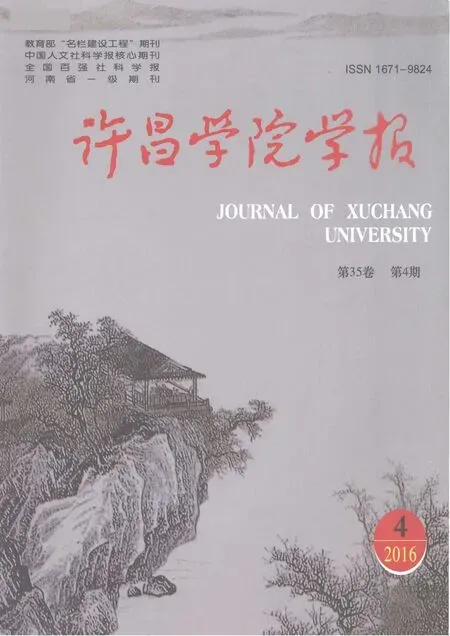《李尔王》中父子冲突的伦理法则
张 松 林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李尔王》中父子冲突的伦理法则
张 松 林
(商丘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戏剧《李尔王》中的父子冲突体现了多重伦理原则。首先,父子冲突体现了社会伦理的演变,父权传统遭到了新思想的挑战,子辈中出现了敢于反抗父权的叛逆者,他们不择手段化解父权带来的焦虑和威胁,并最终在冲突中胜出。其次,父子冲突中对自然法则的崇拜破坏了人类社会文明,力量至上的丛林法则让传统道德伦理蒙羞,使其成为不堪一击的社会稳定遮羞布。从美学原则上看,善恶冲突具有使善者价值更为璀璨的作用,文学往往通过恶来衬托善,并通过恶带来的恶果来反思社会伦理的作用。
李尔王;父子冲突;父权;丛林法则
梅娜德·迈克认为:“人类生存在《李尔王》中是悲剧性的,因为人类生存与人类关系密不可分。”[1]111剧中充斥的暴力破坏人际关系,令人绝望的描写印证了这一观点。具体到父子关系的恶化,李伟民认为:“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宇宙秩序,一是人类天性……子女对父母忘恩负义就是违反自然与传统的西方伦理道德。”[2]本文对中西方亲子伦理加以比较,提炼了父子冲突体现的伦理内涵。在前人基础上,本文将聚焦于剧中伦理层面,从社会伦理、自然伦理两方面来考察父子冲突的社会文化意义,在还原时代文化本色的同时剖析文学对其所处时代的态度。
一、父子冲突与社会伦理
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重要的组成之一,其中蕴含了人生的幸福与哀怨,集中了对传统的传承与颠覆、对抗与和解。人类文明史中“父亲”的含义被赋予了许多特殊的象征意义,夹杂着感情因素,并成为人类种族记忆映射在人类文化长河中。荣格认为,父亲原型是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常见的原型:一方面,父权观念标志着人类社会“秩序、权威和人类的理性法则”[3]7的形成,父亲象征着权威、尊严和力量;另一方面,父权对儿子来说是一种束缚和压制,引发儿子反叛的欲望以证明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因此,儿子对父亲的态度会呈现为一种尊崇与反叛交织的状态。儿子既需要在父亲的荣光中证实自身价值的优越,又想推翻压制在身上的束缚而获得现实力量的确认。这种矛盾的心态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此消彼长,当社会稳定时,儿子尊崇父亲,当道德失范时,儿子反叛父亲。
莎剧《李尔王》的故事即发生在一个伦理混乱的社会转型时代,混乱构成父子冲突的社会背景。正如葛罗斯特所说:“爱情冷却,友谊疏远,兄弟分裂;城市发生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发生叛逆,父子关系崩裂。……我们的好日子已经过去,现在只有阴谋、欺诈、叛逆、纷乱,追随我们不安地走向坟墓。”*本文所引莎剧剧本均引自《莎士比亚全集》(第6卷),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只注场次,不再赘述。(一幕二场)文艺复兴时期,混乱的价值观使人们像野兽一样残暴,君臣、父子、夫妻关系被颠覆,人们互相吞噬、攻讦。
在此背景下,国王李尔准备退位,把王权分配给三个女儿。李尔采取了一个较为特殊的方案,要求三个女儿以口头表达的方式阐明自己对父亲的爱戴,从而换取对王国的统治权。大女儿和二女儿见风使舵,讲出些动听的谎言打动父亲的心以换取馈赠。狂妄自大的国王很享受谄媚之语,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能控制子女,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受控制的人会臣服自己并怀着感恩之心回馈。这是父权思想的惯性思维,然而这一思维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遭到了挑战。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处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代,资产阶级刚登上历史舞台,势力尚不足以抵抗强大的封建势力,但二者在生活观念和价值理念上的冲突已势成水火。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与封建势力狂妄自大的特质相较,前者更能在冲突中获取更多利益。《李尔王》中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子女们,在强大的父权权威下发展自己的力量,等待反击的时机。诚实木讷如科迪利娅无法顺应父权权威,终因忠臣、正直的言语见弃于李尔。故此,剧中呈现出两种类型的父子冲突,一是父亲与温顺子女的冲突,一是父亲与不孝子女的冲突。二者分别从两个侧面撕裂了父子关系,撕碎了传统伦理。
秉持传统伦理的李尔王是个顽固的父亲,他同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一样,喜欢以权威身份向子女施威,通过激起子女的焦虑证实父亲权威。权威培养焦虑在君臣关系上最为明显:“王权话语充满了爱与淫威的悖论结合,臣民无休止地表达他们对君王并非自愿但也不完全是伪善的钦慕,这种迫于压力之下的表演行为本身就使王权得到了稳固。”[4]118当代西方精神分析学批评家雅克·拉康的思维延伸到了父子关系中:“父亲代表了文化规范和法律,他强行实施这些文化规范,如果我们不予服从,他则会用阉割来加以威胁。”[5]父亲成了掌握绝对权力的形象,其王位或爵位本身就是一个威胁。这种传统的父权神授的观点长期支配着社会结构,当文艺复兴之势汹涌而至时,由臣服烘托出来的权威并不牢固。国王依然执迷不悟地以权威身份控制子女言行的父权思维,是李尔王同子女们冲突的根源。
西方父子关系中,从远古时期起,父亲就享有对子女的绝对控制和支配权,希腊神话中乌拉诺斯以残忍的暴力对待众子,激起儿子克洛诺斯的反抗,并最终取而代之成为神王,克洛诺斯重走了父亲控制儿子的旧套路,又引出以宙斯为首的新神反抗并建立了以宙斯为核心的俄林波斯神系。《俄狄甫斯王》、《俄瑞斯忒亚》三部曲都延续着父子冲突的主题。后来,“作为权威的父亲形象由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父权制资本主义社会土壤培植出来的‘父与子’关系,已演变为自然关系与契约关系”[6]。也就是说,父子之间维系关系的纽带除了天然带来的血缘外,儿女们会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依附于父亲。换句话说,一旦这种需要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双方就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盛行,父子之间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利益关系。在新时代,子女们不惜忤逆而追求自己的利益。埃德蒙在制造的伪信中写道:“这一种尊敬老年人的政策,使我们在最好的年华只尝到世界的苦味。”(一幕二场)有专制的父权,有不安分的子女,冲突发生成为必然。
父子冲突既有观念差异导致的矛盾,又有涉及家产交接招致的交锋。在父子对抗中,更擅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方往往更容易取得胜利,而另一方或因昏聩或因软弱等因素在父子冲突中落败。《李尔王》中叛父的子女都有崇拜“丛林法则”的倾向,丛林法则是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的自然法则,如同叛父者希望在弱肉强食的争锋中以自己的利爪撕裂无法超越的伦理规则,谋求个人利益。这种理念本身与无神论相关,与传统理念相悖,但却是逆子夺权的精神支柱。
二、 父子冲突与自然伦理
自然(nature)一词,在伊丽莎白时代具有宽泛的含义,既可指大自然,又可指人的天性、性格,还可指社会法则。我们常说的顺从自然,其实内心是以自然和谐和善作前提的,而事实上,自然既有和谐发展的一面,又有残酷的一面,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最好的例子。文化的力量体现在对人的思维和行动的潜移默化上,传统文化虽压制了子女们的权利,但也使叛父者忌惮。他们必然要寻找另一种信仰和原则来为自己的行为张目,丛林法则、自然崇拜和无神论思想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叛父者的新宗教。
丛林法则的信奉者给自己贴上无神论的标签,从而给自己否定传统、否定既定价值构建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莎士比亚时代,人对自然的那些传统想法已经部分地崩溃,这对人性的旧概念和道德的传统准则好像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到了十七世纪初期,有人认为自然不像是神所规定的秩序,而像是一股超乎道德的势力。那么人本身只是这样设想的自然中的一部分,人们会说,人们不应责难人的自然冲动;而自然冲动无疑是指那些比较强大的动力,是指性欲、统治欲等而言。”[7]288这与当时社会秩序下人应依照的原则相悖,如前所述,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中,每个人都拥有既定的身份,并按照社会身份和角色做事。欧洲封建体系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后,人的社会身份又多了一重宗教束缚。文艺复兴时,人本身的欲望得到认可,人甚至不惜采取作恶的方式来反抗权威。马克·布洛赫在20世纪中叶出版的《封建社会》一书中曾写道:“在我们称之为封建主义的这个时期,社会环境所独有的人身保护和依从关系开始膨胀的同时,亲属纽带也真正地绷紧起来,因为这个时代多灾多难,公共机构软弱,个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地方群体的联系。以后的数世纪中,真正的封建主义逐渐崩溃或发生蜕变,随着大的亲属群体的瓦解,这几个世纪也出现了家族连带关系逐渐衰落的早期特征。”[8]244人们认为既然既定秩序可以被怀疑、被打破,那么人的欲望就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手段而得以实现,于是对力量的崇拜就成了想要改变自己地位之人的必然选择。
丛林法则源于古希腊哲学家安提西尼的寓言:百兽聚会中小动物盼望平等的理想被狮子的利爪撕碎,弱肉强食的原则是森林中的真理。后来人们将此法则在社会中的表现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采取非常规手段排除异己、打击对立势力的时候往往会祭出这一理念。埃德蒙深谙此道,对丛林法则大声呼唤:“大自然,你是我的女神,我为你的法律尽职效劳。”(一幕二场)他扬言:“出身不行,让我凭智慧得到产业;只要目的达到,一切手段对我全都合适。”(一幕二场)在丛林法则武装下,埃德蒙首先将矛头指向哥哥埃德加,并最终打倒父亲葛罗斯特,取得了所有财产。
李尔王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寻找作恶的借口,二人鄙弃老父之情溢于言表。戈纳瑞:“他一向最爱小妹,现在他把她撵走,可见他多么糊涂。”(二幕四场)里甘回应道:“这是他年老的昏悖,而且他向来缺乏自知之明……父亲,您既是衰弱的老人,应该有相应的表现。”(二幕四场)
《李尔王》剧中,恶女先以甜言蜜语获取了李尔王的信任,继而弃之如敝屣;大臣肯特的二儿子埃德蒙采取同样的方式逼走大哥埃德加,再迫害父亲。这两组对应的父子冲突,均以父亲惨败结局。照自然丛林法则来讲,可以说这符合新旧更替的规律,新生事物以自己的力量取代阻碍自身前进的旧势力本是理所当然。然而在家庭体系中运用丛林法则不合时宜,因为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绵延至今的一大秘诀就是人能尊崇理性,能够以社会赋予人的行动规范来约束自己,以社会伦理来衡量自身行为。美好的理想总会落空,一旦社会步入动荡期,规范失衡,朝纲混乱,道德沦丧,丛林法则就横行于世。《李尔王》剧中的叛父者在行动上采取了暴力的手段,在伦理上变成了恶者。叛父者以“暴力”方式彻底断绝父子之关系,从而颠覆“父亲”权威,并对传统、权威、生命与文化本原进行自残。父子冲突中显示出恶的力量,恶势力以强大的破坏力使传统伦理蒙羞。
信奉丛林法则的叛父者必定接受价值虚无论,自然神论成为他们可资利用的又一标签。欧洲社会多信奉基督教,并在王廷与教廷双重鼓励下使之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基督教秉持原罪观,提倡爱与宽恕思想,相信末日拯救学说。叛父者抛弃宗教观念后,成为无神论的信徒。剧中的埃德蒙根本不相信超自然的神力,陷害哥哥时还对自己说:“这真是现世愚蠢的时尚:当我们命运不佳——常常是自己行为产生恶果时,我们就把灾祸归罪于日月星辰,好像我们做恶人是命运注定,做傻瓜是出于上天的旨意……由一颗什么行星在那儿主持操纵,我们无论干什么罪恶行为,全都是因为有一种自然的力量在驱策我们。”(一幕二场)这既是对原罪观的否定,更是鼓舞自己作恶的号角。
三、父子冲突的美学原则
叛逆常被当做负面文化来看待,它除了给人带来痛苦之外,还会对主流倡导的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在双向文化互动中彰显出审美的价值。如果我们将叛逆视为丑恶的话,那么文学书写丑恶的目的便是寻找其对立价值观的意义。正如雨果曾说:“丑就在美的身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9]30有生命的人也本能地有自然的欲望,但相对于动物来说,人有理性来约束这种欲望。支配人性的,有两种与生俱来的能力:自私和理性。前者使人的本能行为发动,后者引导人克制冲动。人无法否认这种内在的善恶两面性,丑恶的情欲有时候还会支配人的身心,让人堕入深渊。中外造世神话中往往都会出现正邪大决战后的现世清平世界,但是善恶斗争事实上却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中做永恒的斗争。
叛父者挑战父权,在父子冲突中扮演着恶的角色。父亲的真正爱戴者与父权维护者也后继有人,李尔王的小女儿科迪利娅和葛罗斯特的长子埃德加承担着维护秩序的责任。面对父亲给出的难题,同样心怀焦虑的科迪利娅沉默寡言,以诚实的言语说出按照女儿的本分来爱父亲;埃德加则是在诚实地尽儿子本分的生活中被弟弟陷害。因此可以说,剧中的父子冲突与好人无辜受难的哲学难题相连,而在善恶冲突中磨砺出各自的价值。
首先说冲突中落败的父亲,他们本是权威的化身,传统的坚守者。在新时代不能延续传统规则时,他们遭到了巨大挫折和戕害,随后父亲们都在痛苦中反思自己以往的过错——对近臣不能明察,对下层体恤不足,故在疯狂中对现实人生深有洞见。李尔遭受两个女儿欺骗与鄙弃后疯狂,并疯狂地同暴怒的自然力搏斗,骂风雨雷电是“卑劣的帮凶……滥用天上的威力……没有文明装饰的人不过是像你这样一个寒伧的、赤裸的、两条腿的动物”(三幕四场)。他开始体会到了平民百姓的痛苦。
同样,叛父者让妄自尊大的父亲变成了盲人,痛苦的葛罗斯特想跳崖以结束自己的苦难,“疯子”埃德加带领盲父葛罗斯特前行,哄骗他说有一个悬崖,它高耸的绝顶可怕地俯瞰着幽深的海水。崇父者为盲人描绘出深渊的深度,这个深渊既存在又不存在。说其存在是因为葛罗斯特无法观看,他在埃德加的描述中确实认为有这样一个悬崖;说其不存在是因为这是埃德加臆造出来的一个令人惊心眩目的地方,他想让老人在虚幻、有惊无险的跳崖中走出绝望。葛罗斯特轻轻一跃,双脚离地又落地后被埃德加叙述为神佑化险为夷,以此来增加葛罗斯特的信心。虚幻深渊的场景可谓绝妙,因为当时老人痛不欲生,急欲通过死亡来解脱。这是威权自以为是的代价,它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得到了双重惩罚。老人被挖去双眼后心却亮了,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和现实的残酷,这是实实在在的痛苦的深渊。这个深渊通过崇父者来描述,带有浓重的伦理意味,被误解的埃德加不但不怨恨父亲,而且还想方设法重新鼓舞他对生活的热情,对宗教的信仰,对规则的尊崇。他对盲父不离不弃,带着他艰难跋涉寻找李尔,又让他在虚假的跳崖后相信神灵保佑,继而找到李尔以尽人臣之分,最终父子和解。这是一个曲折而完整的伦理叙事,暗含着作者对传统、规则的恪守之心。
结 语
父子冲突是西方文学的传统主题,在戏剧《李尔王》中该主题得到了生发和运用。作品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和象征表达了莎士比亚对现实和人生的体悟,凸显出了蕴涵于父子冲突中变化的伦理原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代表新生力量的子辈,对父权的反抗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新生力量要求自由发展的体现;同时父子冲突也破坏了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宁静,导致传统伦理解体。从自然伦理角度来讲,子辈崇拜的丛林法则和力量至上原则与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相抵触,是利于强权者不择手段发展自己的理论。父子冲突中的伦理交锋也彰显了多种文化价值,恶以否定性和破坏性的力量在给人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教会人反思人生,提醒人以更理性的头脑生活;善以宽容和慈爱的柔情给人以慰藉,使人于穷途末路之时得到心灵的慰藉,并得以自我救赎。总之,在《李尔王》浓郁的悲剧气氛中,父子、父女冲突充斥其间,它们的表象及本质,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作者对威权、传统、伦理的思索。
[1] 梁坤.新编外国文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李伟民.李尔王中的“孝”与“爱”[J].四川戏剧,2009(2):57-59.
[3]巴巴拉·阿内尔.政治学与女性主义[M].郭夏娟,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4]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培养焦虑:李尔王和他的继承人[M].冯伟杰,译.//梁坤,主编.新编外国文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 于雷.唤醒沉睡的父亲[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58-63.
[6] 杨经建.以“父亲”的名义:论西方文学中的审父母题[J].外国文学研究,2006(1):159-165.
[7] 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8]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M].张绪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 雨果.雨果论文学[M].柳鸣九,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郑国瑞
Ethical Rules in the Father-son Conflict in King Lear
ZHANG Song-l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The father-son conflict in the play King Lear embodies multiple ethical principles. First, the conflict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ethics and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y was challenged by new ideas. The young generation appeared bold enough to rebel against patriarchy. They did anything to resolve anxiety and threats coming from patriarchy and eventually became the winner of the conflict. Secondly, the conflict shows worship for laws of nature which destroyed the civilization of human society. From aesthetic principles, the conflict between good and evil highlights good. So literature tends to zoom good in the background of evil and reflect social ethics through negative consequences brought by evil.
King Lear; father and son conflict; patriarchy; law of jungle
2013-05-16
商丘师范学院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伦理‘恶’”(2015GGJS03)。
张松林(1979—),男,河南开封人,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和戏剧文学。
I106
A
1671-9824(2016)04-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