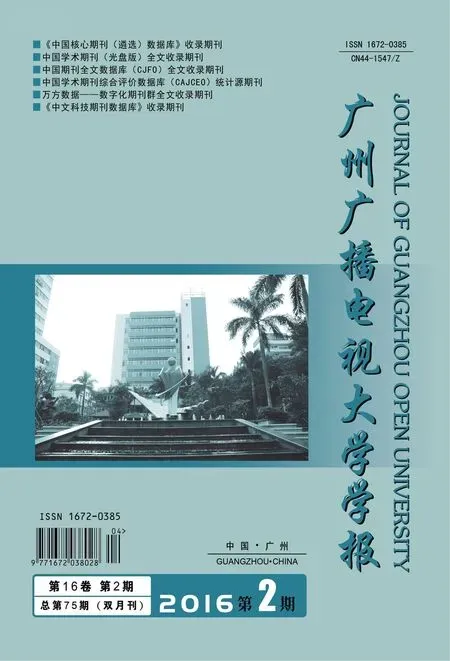也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被当乐府的非乐府
牟德余(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也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被当乐府的非乐府
牟德余
(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张若虚作为“吴中四士”之一,其才情在当时应是高妙的。但是,张若虚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作品只有《春江花月夜》和《代答闺梦还》两篇,这不免有些遗憾,然而有“孤篇压全唐”之作也应是遗憾中的一丝欣慰。文章从“乐府”、“横纵比较”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得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是其“诗心、诗情、诗才”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首独立的,纯粹的,高妙的写景抒情诗而不是乐府诗。
关键词:《春江花月夜》;乐府;抒情诗
张若虚作为“吴中四士”之一,其《春江花月夜》是唐诗中的名篇,其才情在当时应是高妙的。但是,张若虚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作品只有《春江花月夜》和《代答闺梦还》两篇,这不免有些遗憾,然而有“孤篇压全唐”之作也应是遗憾中的一丝欣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被郭茂倩收录在《乐府诗集》第四十七卷“清商曲辞四吴声歌曲四”本身就是一种误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是否是乐府诗,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张诗是其“诗心、诗情、诗才”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首独立的,纯粹的,高妙的写景抒情诗而不是乐府诗。
“乐府”
“乐府”一指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管理音乐的官署,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一指搜集和创作的歌词。到后来的一切有韵的音乐文学都叫乐府。这是概念的扩大。如苏轼的词集《东坡乐府》。“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梁•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第七》[1])。明确表示声音的高低要合乎吟唱的音律,音律要与五音相和谐,用乐律来配合声音。“声”、“永”、“律”三者处在一种“永”的音乐关系中。由此可见,刘勰所说的乐府,也是从唱这个角度出发,配上音乐演唱的韵文才叫乐府,没有配上音乐的就是诗。杜佑《通典•乐三》[2]:“大唐高祖受禅后,军国多务,未遣改创,乐府尚用隋氏旧文。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正雅乐,至贞观二年六月乐成,奏之。”①这句话很明确的指出唐代的音乐(音乐机构)袭用前代的规范和制度。这里的“乐府”与创制时的“乐府”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这里所说的“旧文”就应是“音乐体制沿用隋制”。“贞观二年六月乐成,奏之”表明唐有了自己的体制,并不是完全改变前代的建制,而是一种更适合本朝气象的乐歌发展和完善。罗根泽把乐府分为“入乐者”与“不入乐者”,这里着重讲“不入乐者”。“不入乐者”分为三类:用乐府旧名者,摘乐府歌词为题者,自拟题制词者。“而由广义言,则凡未入乐而其体制意味,直接或间接模仿前作者,皆得名之曰乐府”。②[3]吴相洲也指出“其实乐府专指宫廷音乐作品,宋代以前指向从未变化”。③可见,各家的观点有不一致之处。这就是吴相洲教授所说的“概念不清”的问题。那么,在这里讨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乐府”在唐代是怎样定义的。由前面可知,唐沿用隋的“旧文”,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炀帝继承了后主的《春江花月夜》,从音乐的继承上来讲,到唐代,《春江花月夜》的乐府性质是不变的,唐前人的乐府定义与前代无异。这样看来,张若虚的《春江》也应是乐府了?其实不然。乐府既然是朝廷的音乐机构,亦或是这个机构演唱的歌辞。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一不在宫廷也不是这个机构演唱的歌辞。又怎么能算得上是乐府呢?张煜指出:“总而言之,‘乐府’一词在唐代或是指与宫廷有关的音乐机构,或是指这些机构演唱的歌辞,所描述的总是大多不离开宫廷内外活动,唐前人所谓的乐府的含义,到唐代没有扩大。”④[4]这也可以看出,张诗远离宫廷,丝毫没有宫廷习气。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乐府?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曾智安在《清商曲辞研究》[5]一书中也指出:“到唐代为止,‘清商音乐’已经无可争议地指当时清商署所管辖的南朝遗乐,包括中原旧曲和吴歌、西曲两个主要部分。郭茂倩在这一基础上,有选择地把其中的中原旧曲淘汰出去,从而在事实上讲‘清商音乐’界定为东晋到唐代的江南本地乐歌。因此,《乐府诗集》所谓清商音乐完全来自郭茂倩的界定。”⑤张开《初唐乐府诗研究》一文中,分音乐、文献、文学三个方面论述,音乐上,乐府的两重含义没有发生变化,文献上,辑录出《乐府诗集》遗漏的其他乐府诗。文学上分出的太宗朝乐府与高宗武后朝乐府两个断代,前者因袭为主,后者变新较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精神内涵。由此看来,乐府在唐代意义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依然是“声依永,律和声”。郭茂倩根据自己的限定把《春江花月夜》划分到清商音乐中,只要是乐府题名,一概选入,而不顾事实上的“不能唱”。他并没有把作品放入当时的环境考察而是以当下的主观选入。可以用现代观念关照前代概念但不能认定这种观念就是正确的。郭茂倩就是用宋代的乐府概念定义唐代的乐府,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有学者认为,张若虚实用乐府旧题,其实,这与我的观点是不矛盾的,是不是乐府与用不用旧题无关。用了乐府的旧题,就能说它是乐府?不用乐府旧题,就不是乐府?在唐代,乐府的概念还是很清晰的,到宋以后乐府概念开始混乱。在我看来,定义一首诗是不是乐府,不能看他用不用乐府题名,要么是宫廷音乐机构及其机构搜集的歌词,要么能唱。除了这两方面,就不能定义为乐府。宋词可以称为乐府,元曲可以称之为乐府,杂剧也可称为乐府,因为他们能唱。若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是“旧瓶装新酒”,乐府的《春江花月夜》的这个瓶子未免也太不完整了,除了盖子是以前的盖子,连瓶子本身都不是以前的瓶子了。如白居易的新乐府,新在哪儿?唯一与乐府相关联的,也就是题目了。主题,内容,思想,审美等与乐府毫无关系。名曰新,也是一厢情愿罢了。加个乐府古名,说什么“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在我看来,与“君权神授”一样,借个名罢了。
因此,从乐府的定义上来讲,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就不是乐府,他既不是宫廷机构,也不是这些机构演唱的歌辞,亦不能唱。宋人郭茂倩所说的乐府,已经不是唐人的乐府了。
横纵比较
单从“乐府”的定义,就能很好的说明张诗不是乐府了。为更进一步说明其不是乐府,还可以从横纵比较的这三方面的论述。
一、时空上影响甚微
我们应该考察《春江花月夜》的由来。郭茂倩《乐府诗集》[6]卷四十七下“清商曲辞四•吴声歌曲四”《春江花月夜》七首。引《旧唐书•乐志二》:
《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后主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
这句话是值得细细品味的,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陈后主所作”;其二,陈后主喜欢与宫中女学士和朝臣唱和;其三,也是最重要一点,这些唱和“尤艳丽”。这说成调情取乐,讲点荤话应该不是很过分。从“以为此曲”能断定《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绝对能唱。那也就是说,它是“乐府”这完全没有任何质疑。但“以为此曲”中的这曲到底是谁作的这里没讲清楚。从“《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这句话中,我们还应该有这样的疑问:后主作出的这三篇到底能不能唱?是后主有才情自己谱的曲还是太常令何胥谱的曲?“以为此曲”以“尤艳丽”为标准。因此,《春江花月夜》为“艳曲”。
从时空上来看他们之间的影响。《陈书•卷六》[7]本纪第六:
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为皇太子。
……
三月己巳,后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鄴,入于长安。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薨于洛阳,时年五十二。
由此可见,后主生于553年十一月,569年正月立为太子,604年十一月卒。享年52岁。
《隋书卷三》[8]帝纪第三炀帝上:
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
……
上崩于温室,时年五十。
炀帝“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时年十三”,开皇元年是公元581年,也就是说,公元581年,炀帝13岁。那么倒推13年,应是公元569年。可见,隋炀帝生于公元569年,卒于公元618年。
后主与炀帝两人年纪相差16岁,从文学上来讲,这应该不算大跨度。再者,作为“曲子”的“尤艳丽者”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可以推测,后主时代的《春江花月夜》到炀帝时,变化应该不大。或许根本就没有变化。炀帝时的《春江花月夜》依旧是后主时的《春江花月夜》。因此,炀帝时的“尤艳丽”特征依旧没有变化,两者是相同的:主题思想,审美特征等方面没有发生变化。“乐府”性质没有变化。
诸葛颖的相关记载,《隋书•卷七十六》[9]列传第四十一:
诸葛颖,字汉,丹阳建康人也……
炀帝即位,迁著作郎,甚见亲幸……
后征吐谷浑,加正议大夫。后从驾北巡,卒于道,年七十七。
隋炀帝征吐谷浑,是在公元608年—公元609年,按此来说,“卒于道”,诸葛颖卒于608年或者609年。由“年七十七”,倒推得诸葛颖生于公元531年—公元532年。我们可以通过这段记载得出,诸葛颖的《春江花月夜》无疑受到了炀帝的影响。或者,炀帝的《春江花月夜》受到了诸葛颖的影响。由于两首诗的创作年代不详,但,二人之间不管是谁影响谁,乐府性质的《春江花月夜》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张子容与孟浩然(公元689-740年)是朋友(《全唐诗》[10]卷一一六•张子容:张子容,先天二年擢进士第,为乐成尉,与孟浩然友善,诗一卷。)张子容的生卒虽不详,但是,通过“朋友关系”,其年龄与孟浩然相差应该不大。因此他们所受音乐形式,文学思想,社会形态等必是相同的。乐府《春江花月夜》的乐府性质在这一时期亦不变的。张子容时期的乐府与炀帝时的乐府没有发生变化。
张若虚生卒年不详,与贺知章、张旭和包融齐名,被称为“吴中四士”的记载是事实。大致出生在初盛唐之间。
从纵向上来看,从陈后主到隋炀帝,如果考虑到创作因素大约15-20年,可能更短。因此,炀帝受到后主的影响应该比后面几个诗人大。后主→炀帝→诸葛颖→张子容→张若虚,近百年时间,张若虚受到其影响应该是很小的,几乎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没有影响。那么,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在纵向上受到的影响,或者说继承是可以分辨得清的。
二、结构上相去甚远
从结构上进行横向比较可知,《乐府诗集》中《春江花月夜》题下一次是炀帝、诸葛颖、张子容、张若虚5位诗人,温庭筠在张若虚之后,这里不分析。
隋•炀帝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诸葛颖
花帆渡柳浦,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覆船楼。
唐•张子容
林花发岸口,气色动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石潭里,宜照浣纱人。
交甫怜瑶佩,仙妃难重期。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
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炀帝和诸葛颖的三首《春江花月夜》带有五言绝句的味道,五言四句。张子容《春江花月夜》五言六句。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七言三十六句。这里可以看出,炀帝和诸葛颖的五言四句到张子容的五言六句,只是句数增加了两句,每句的字数却没有变化。这是一种渐变,张子容的五言六句到张若虚排律形式的七言三十六句,在句数上增加了5倍,比杨、诸葛增加了8倍。而且,在每句的字数上也有了变化,从五字变为了七字,容量大大增加,这是一种骤变。也就是说,张若虚的这首《春江花月夜》在文本的结构上已经大大超出了前人《春江花月夜》,可以说,在这种形式下,以一种新的面目示人,新面目下的张诗,完全看不出来前代的影响。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已经不再是前人所作的《春江花月夜》了。
另一方面,从音乐的角度上讲,原为5字的句子变成7字,可以有衬字的情况,若把张若虚的七言三十六句看成入乐的乐府,或为旧题的乐府,每一句读有两各衬字,这也是不符合音乐的规律的。这样来讲,张诗就不是乐府诗了。
炀帝“平不动”是为静;“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一去一来是为动,“花正开”为动,特别是一“将”一“带”字,“动”中没有“乱”相,而是一种平和的自然的画面。天上的月,与地上的人和江、花等,从上到下,又由下到上,由“人”的视角的切换而变化,转化。“去”“来”在水平上的“远”与“近”的自然切换体现了“此人”对自然的动静结合,高低相行,情景相谐。诸葛颖诗在结构上与炀帝两首诗几近相同。诗中表现的是一种安静的画面。张子容在后面加上了“艳在骨”的尾巴,就显得不那么高妙了。而张若虚的诗在结构上却显得那么复杂。具有多重艺术结构:抒情写意的情节结构、复杂曲折的情节结构、音尺和韵律构成的音律结构、意象化语言的内在结构。⑥文本结构上,张若虚分不同层次来变现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前八句、中八句、后二十句,分别为“对人类童年的讴歌、为中年的沉思与叩问、暮年的孤寂与苍凉”⑦。张若虚诗与前人对比,构思巧妙,缜密精巧,高低可判也。在这样结构中,游子思归也好,人生哲理也好,宇宙意识也罢。都没有“艳”的成分,更不会有“其艳在骨”⑧的内容倾向。因此,没有“艳”的《春江花月夜》已经不是真正的《春江花月夜》了。不是真正的《春江花月夜》,也就不是乐府诗了。
三、内容上区别甚大
从内容这一方面进行横向剖析,炀帝“暮江”句是一首写景诗,由“春”、“江”、“花”、“月”、“夜”五种意象组合,点染出了一幅水墨画。“夜露”句,前两句写月夜间的所见,花上露珠闪烁,月光照在水面,在风的挑逗下,摇曳多姿。后两句,用吴小如先生的话说应是“字面虽不‘艳’,故事内容却有‘艳’的成分”,这就带有“宫体”的“艳”的成分了。诸葛颖的《春江花月夜》,也属纯粹的写景诗,“月色含江树,花影覆船楼”中一“含”一“覆”却也点得贴切。张子容的两首诗中,“其艳在骨”,这似乎也符合“采其尤艳丽者”的条件。再看张若虚的七言三十六句,是一首高妙的写景抒情诗。胡应麟《诗薮》[11]内编卷三七说此诗“流畅婉转”。但从景上来讲,“春”、“江”、“花”、“月”、“夜”五种意象是有机组合的,且五种意象在诗中也有侧重,有变化。以“江”“月”为主,“春”“夜”为大背景。而握住这条主线之“人”在这个大背景中尽情泼墨,这个“人”,在特定的时间见到了特定的景,勾起了特定的情。或者也可以这样讲,这个“人”的情一直都在,只是被埋在了心里,也只是在此刻,遇到了这样景,更牵引了情的流露。一为“内化”,即触景生情;一为“外化”,即寄情于景。我认为这是从“外化”到“内化”再到“外化”的过程。毛先舒《诗辨坻》[12]卷三:“张若虚《春江潮水》篇不著粉饰,自有腴资,而缠绵蕴藉,一意萦纡,调法出没令人不测,殆化工之笔哉。”在“春”与“夜”的大背景下,“‘江’与‘月’虽似互相关联……既然从月升到月落,概括了一个完整的夜,那么对‘夜’的本身自然也不须多写明写……这种顾全局而重点突出、一环扣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艺术构思,也是唐以前的诗人所不易做到的。”⑨吴小如的此番解读是颇有见地的。从整体对照上来看,炀帝诗“暮江”一首,有空澄灵动之气。“夜露”一首、诸葛颖和张子容“春江”,有秾丽浮艳之味。“艳”到了“骨子里”。再看张若虚的“春江”一首,透露的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空灵澄净。张若虚超出前人,不仅在写作技巧上,在内容上,构思上,主题上都是巨大的变化。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诗并不是沿用乐府旧题《春江花月夜》而来,更不是“乐府”诗。张若虚完全有“诗心,诗情,诗才”,并完美体现“三诗”之旨。他只是恰巧用了这个题目,而这个题目刚好是乐府之体,或者可以说,这个题目在诗中完全是根据创作主体的写作需要来确定的,契合了诗人的“三诗”,具有主体承载力,与乐府诗《春江花月夜》没有多大关系。张诗是一首独立的,纯粹的,高妙的写景抒情诗。
注释:
①(唐)杜佑.《通典》第一四三卷,第36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②罗根泽.《乐府文学史》,第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③吴相洲.《学科视野下的乐府学》.光明日报,2014年1月28日第016版。
④张煜.《新乐府辞研究》,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⑤曾志安.《清商曲辞研究》,第2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⑥邹建军,赵令珍.《〈春江花月夜〉的多重艺术结构》、《名作欣赏》2003年第2期。
⑦刘忠阳,刘勇强.《对〈春江花月夜〉的文本结构分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第2卷第4期。
⑧⑨吴小如.《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五期。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4]张煜著.新乐府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曾志安著.清商曲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唐)姚思廉撰.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9](唐)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全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全唐诗》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6)02-0065-05
收稿日期:2015-12-16
作者简介:牟德余,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