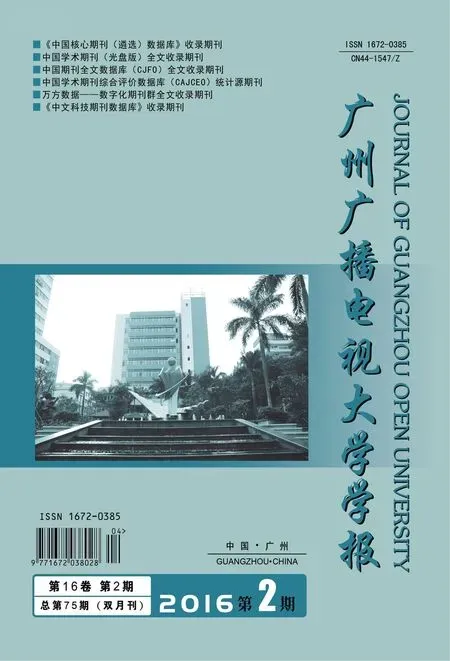虚假诉讼的治理与防范
朱启骞(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225700)
虚假诉讼的治理与防范
朱启骞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225700)
摘 要:民事诉讼向来注重民众的意思自治,而司法的“不告不理”恰恰给了虚假诉讼衍生的契机。实践中民事虚假诉讼的现状表明该行为治理的难度,法律规制不一、第三人撤销之诉作用范围的限制等都使民事虚假诉讼的治理呈现出滞后性,更遑论行为的事前防范。司法改革却带来了新的契机:立案登记制度虽然客观上使得民事虚假诉讼行为进入诉讼程序的可能性加大,但同时也引导我们从立案阶段将民事虚假诉讼遏制在摇篮里;审判信息化工作的发展、阳光司法工作的深化都给发现该行为引入了外部机制,利于识别和监督民事虚假诉讼行为;证据制度和法官责任制的完善和落实也倒逼法官加强审查民事虚假诉讼行为,以防漏网之鱼。
关键词:虚假诉讼;司法改革;治理与防范
引言
市场机制之下,一方面,曾经的熟人或集团共同体内部的共识已经被打破,诉讼已经成为解决纠纷的常态化机制;另一方面,在法律对促进利益的价值行为划定了合法范围内,愈加理性的经济人也愈加精细地进行利益的计算与衡量,虚假诉讼似乎总戴着低风险高回报的光环,同时,不诚信的行为在多元价值充斥的社会中越来越得到一定程度的包容,于是虚假诉讼便成了他们“经济合理”的选择。司法改革背景下,诸如立案登记制、审判管理信息化、法官责任制度、司法的进一步公开等都给虚假诉讼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检视我国虚假诉讼及其治理的现状,或许可乘司法改革之风来破虚假诉讼之浪。
一、虚假诉讼的基本内容
虚假诉讼滥觞之下,合法权利安有完卵?当前,虽然新《民事诉讼法》已经对虚假诉讼行为作出了描述性的规定,对于这一行为本身并没有确切的界定,这就导致了治理对象的模糊。
各地对该行为认识上尚存差异,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和2010年先后出台了《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虚假诉讼行为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江西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制定《关于预防和惩处虚假诉讼的暂行规定》。这就导致了行为规制上的不同做法,有的地方存在漏网之鱼,有的为惩治这一行为而错杀很多。这就有必要界定这一行为,否则会架空法律中已设置的打击手段。
(一)虚假诉讼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
虚假诉讼的概念关系着这一行为的构成范围,也反映着人们对虚假诉讼认识、理解上的差异。
1.虚假诉讼的不同观点及简要评析
有观点认为,“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取虚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或裁定的行为”[1]有的认为,“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虚假的证据,提起民事诉讼,破坏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促使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或裁定,而使自己或者他人达到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目的的行为。”[2]
上述观点基本体现了虚假诉讼的主体、行为等基本要素,而在构成要素上各有侧重,但还是有些缺漏:一是在主观要素上提到了行为目的,但没有突出双方的恶意;二是行为后果上局限于法院的裁判而将特色调解制度排除在外,事实上缺乏对抗性的调解虚假可能性更大,隐蔽性更强;三是在行为发生场域上局限于法院审理过程,结合虚假诉讼当事人的目的即实现自身的非法利益,法院的执行是其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但上述概念中却没有体现,略有程序断层之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虚假诉讼的关注重在前面的程序,这也是执行中虚假诉讼难以规制的原因之一。四是虚假诉讼的本质在概念中没有体现出来。
笔者认为,虚假诉讼是指一种本质上缺乏诉的利益,而由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利用虚构法律关系、伪造证据等方式使法院作出错误判断以实现其非法预期利益的行为。这一概念正是从虚假诉讼行为产生机制入手,遵循了该类行为发展的特点和过程而做出的界定,以期对虚假诉讼行为的识别有所裨益。
2.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
虚假诉讼行为的形成具有一定发展过程,且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它也是一种特殊的侵权,构成要件上呈现出主客观方面的特点,通过分析其构成要件往往也有助于行为的识别和判断。
首先,主观上,预期目的的非法性。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非法的预期目的,这种目的因案件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比如为了借贷案件中与他人合谋,虚构与他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达到不偿还借款的目的。
其次,主体特殊。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的虚假性就在于当事人对此根本就没有诉的利益,纯粹是为了实现非法的利益需求,那么这就需要双方的配合与合作,与诉讼所要求的对立结构不同,双方当事人此时是利益的共同体,这其中就存在共谋的问题,双方主体间是存在特殊的关系的。毕竟很多诉讼是给付之诉,败诉一方是存在法律义务的,这对配合虚假诉讼行为的一方来说其也承担一定风险。同时,虚假诉讼的犯意产生者也承担一定的风险,那么为了更确定地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其也会优先选择自己信任的人,这种主体的特殊关系也就在所难免。
再者,客观上,行为方式隐蔽与多变性。虚假诉讼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虚构法律关系,伪造证据,但这一方式往往在诉讼中难以查证,而且利用诉讼这一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非法利益,是以合法形式掩盖了非法目的,从这两方面看其行为均具有一定隐蔽性;同时,其行为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形式也是多变的,不能一一列举。虚假诉讼的行为方式要结合具体的事实情况,以客观行为为主,综合其主观方面看。
最后,本质上缺少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是指诉中所具有的法院对诉作出实体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3]虚假诉讼中是根本不存在诉的利益的,因为虚假诉讼中当事人之间是虚构的法律关系,法院的裁判成为了当事人获得非法利益的一种手段,判决的必要性与实效性根本就不存在,某种程度上法院是其欺骗的对象,这是对司法资源与公信力的一种极大伤害。
(二)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的关系梳理
当前存在将恶意诉讼等同于虚假诉讼的情况,“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采用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提供假证据等方法,通过民事、行政诉讼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4]这一概念是与虚假诉讼的概念等同了,有的学者则将恶意诉讼纳入虚假诉讼的范围中:“依据虚假诉讼虚假的类别并结合虚假诉讼的参与主体,可以将虚假诉讼行为划分为恶意诉讼、滥用程序以及串通诉讼三种类型。”[5]
笔者认为,两者关系有些微妙,一来两者有诸多共同点,总的来说都是一种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二来两者侧重点不同,虚假诉讼侧重于行为的虚假性,而恶意诉讼侧重于目的的不正当性。具体差异为:本质上,笔者认为,虚假诉讼的虚假性就在于缺乏诉的利益,纯粹是为实现非法利益需求,这就需要双方的配合,与诉讼所要求的对立结构不同,双方当事人此时是利益的共同体,“基于趋利避害的天然动机,如无特殊关系,一般人不会配合参与虚假诉讼。”[6]而恶意诉讼中诉的利益存在与否不影响行为的构成;而借助刑法的犯罪行为构成要件模式来看,主体上,虚假诉讼是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而恶意诉讼往往是当事人一方的行为,具有单向性,从杨立新教授所认为的恶意诉讼概念中可见一斑:“指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致使对方在诉讼中遭受损失。”[7]主观上,虚假诉讼中的恶意往往表现为一种共谋或串通,恶意诉讼中的恶意则是一方所产生的;客体上,虚假诉讼侵害的一般是第三人的合法利益,恶意诉讼侵害的可以是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的利益。诉讼结构上,虚假诉讼中的对抗性是有瑕疵的,甚至双方利益是一致的。由于事先双方的恶意串通,两者的对抗更像是一场排好的戏剧,法官则成了这场闹剧中被愚弄的无知迷茫的观众。这种虚化体现为“一是自认多。诉讼当事人双方对于案件事实大多不存在争议,法院对于案件基本事实认定,大多通过当事人自认的方式予以确认。二是鉴定少。三是类似于督促程序的诉讼版。”[8]而恶意诉讼的对抗性结构则相对完好。
二、我国虚假诉讼的现状及规制中存在的不足
由于虚假诉讼成本低廉,而获利良多,市场经济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这里起到了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无锡市一案件当事人就曾经以25元的诉讼费“玩转法院”—当事人因被解雇而起诉公司,采取不同的诉讼手段先后起诉了13个案件。而诚信日益缺失的社会环境也助长了虚假诉讼的风潮。
(一)我国虚假诉讼案件现状
据报道显示,广东省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识别了虚假诉讼案件940件,其中以房产纠纷和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为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调查发现,该省大部分基层法院法官在日常办案过程中都曾接触过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江苏全省法院2011年、2012年经审判监督程序认定原审生效裁判存在虚假诉讼情况的共104件。”[9]上述数据仅仅是已经识别出来的虚假诉讼案件,而虚假诉讼手段多样性、隐蔽性表明其数量是远远高于调研结果的,审判程序并不能淘尽虚假诉讼的沙子,以至于很多虚假诉讼的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给真正的利害关系人造成了损害。
虚假诉讼在法律空隙中如鱼得水,其所带来的危害可见一斑:首先,诉讼对抗制度对整个诉讼结构的稳定起着支柱型的作用。其“基本前提是公民个人的自治性和主动性。诉讼当事人或其律师在向法院展示事实和呈示案件方面负有责任。”[10]案件的事实通过积极对抗浮出水面。笔者认为,虚假诉讼中当事人虚构法律关系,虚化了诉讼的对抗制度,程序愈加形式化与虚拟化,在程序合法外衣的掩盖下,非法利益得以暗度陈仓。其次,虚假诉讼侵害的是第三人的合法权利,法院裁判使得第三人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且难以追回自己的合法利益。再者,法院被动成为当事人实现非法目的的工具,一来随意地改变诉讼结果将破坏司法的稳定性;二来若不改变诉讼结果,法院成为不法行为的帮凶,无论哪一角度,司法权威与公信力都遭受巨大损害。最后,诉讼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是不经济的,更何况缺乏实质争议的虚假诉讼违背了诉讼解决纠纷的目的,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
正如古话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虚假诉讼是当事人为了自身非法利益而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进行的,因此案件的类型也相对比较集中,基本上都与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有关。当然,也不否认某些案件中当事人有其他的非法利益诉求。目前,虚假诉讼主要多发于以下几种类型案件中:
一是民间借贷案件。有的是为了不偿还第三方的债权,而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假借与第三人间的借贷纠纷逃避债务;有的是离婚一方为了多分财产,与第三方同谋以借贷纠纷损害另一方的财产利益。二是房产合同案件。主要表现为虚构与第三人的房屋买卖合同,有的是为了逃避银行贷款,有的则是为了顺利获取已被查封的事实,有的是为了逃避税费的缴纳。三是离婚案件。按照目的不同,主要为三种:一是为了不偿还所欠第三人的债务,双方假离婚,虚假调解和解侵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二是为顺利卖房屋、少交房产税而假离婚;三是为了多获得拆迁补偿费而假离婚。四是商标侵权案件。商标所有人避开与商标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并越过行政管理机关,通过虚构与第三人之间的商标侵权纠纷,利用法院的裁判来实现确认自己所拥有的商标为驰名商标的目的。五是骗取车牌号。当事人通过相对低成本的诉讼来获得价值相对高的知识产权、车牌,这无疑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但司法却不得不面临与行政权的正面博弈,因为在行政管理关系中,当事人所获得的利益是非法的,法院却用裁判文书、调解书将其合法化,冲突之中难免让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坐收了渔利。上述五类案件主要侵害的是案外人或另案当事人的利益,还有些案件是借程序侵害本案正当当事人利益的,即第六类。如破产管理人等非实体权利主体与对方当事人串通,诈害实际受和解、调解约束的实体权利主体;如委托代理人、代表人等实际实施诉讼行为的人假借和解、调解损害委托人、其他共同诉讼人或所在单位等名义当事人的利益等。
笔者认为,这种类型化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虚假诉讼的多发类型,有利于引起法院的关注,但这种虚假诉讼类型分类有不少弊端:首先,基于各类型的特殊性又有不同的规制方法,但这种列举式的方式是无法穷尽的,若针对这些类型再设置不同的规制方法,则无疑会增加国家司法等有限资源方面的负担;其次,这些案件类型其实只是行为人掩盖自身非法目的的形式,借此实现“金蝉脱壳”,这种表面形式是无法体现行为人行为实质的,简单粗暴的分类方法反而如“遮羞布”般掩盖了事实,并不利于虚假诉讼的识别。另外,上述分类有的是基于诉讼表面形式,有的则着眼于虚假诉的实质目的,进而导致了某种程度上的重合。
(二)虚假诉讼行为治理中的不足
针对虚假诉讼,我国并非没有相应的规制手段,但这些规制并没有达到良好的效果。目前针对虚假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只是做出了单一的规定,一方面是针对虚假诉讼行为人的惩治,即虚假诉讼行为构成犯罪则通过刑事法律来处理,另一方面是针对权利受侵害的第三人的,即第三人撤销之诉。表面上看,这些规定充分考虑了虚假诉讼的侵害人与受害人,惩治与保护一体,但事实上这些手段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规制的疏漏无形中让虚假诉讼钻了制度的空子。
1.规制手段单一滞后
我国对虚假诉讼行为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分类,只笼统地将构成犯罪的行为交由刑法来规制,规制手段比较单一,而且对行为程度不加具体区分,对不构成犯罪的虚假诉讼行为仅仅予以罚款和拘留,利益之下不足以威慑行为人。同时,治理手段滞后,往往建立在已经识别虚假诉讼行为的基础之上,但既然审判程序无法起到过滤虚假诉讼的作用,那么这一基础便无法建立,事后型治理的作用无疑大打折扣。
2.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范围有限
尽管第三人事后可以通过撤销之诉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实际上,由于法律将第三人局限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大量的虚假诉讼中受侵害的第三人往往不在上述范围之内;另外,法律对第三人撤销之诉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门槛,同时司法实践中对这一程序与再审程序关系仍存在盲点,导致这一诉讼有虚置之嫌。因而,第三人撤销之诉无法实现规制虚假诉讼的预期目的,甚至是如理想国一样只能在现实中空置。
3.实践中虚假诉讼行为法律规制适用不一[11]
一方面,各地针对虚假诉讼行为有不同的法律文件,由于对虚假诉讼的限定范围不同,因而惩处的宽严程度也就存在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刑法中并没有与虚假诉讼相对应的罪名,如伪造证据罪、诈骗罪等一些相关的边缘性罪名的适用有着不少弊端:一是这些罪名只有行为人为符合构成要件的特定行为时才能适用,有时难免有类推适用之嫌。二是与虚假诉讼行为颇具亲缘性的诈骗罪能否与之契合仍是个悬案,目前有的法院按照诈骗罪处理,理由是“构成了“三角诈骗”。在以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虚假诉讼中,主谋者和帮助者实施了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的欺诈行为,法院产生了错误认识,作出了错误裁判,并通过裁判处分了第三方财产,行为人据此获得了非法利益,第三方因此遭受了财产损失。”[12]如金刑初字第263号案件中,被告人王连丰伪造证据后通过虚假诉讼行为骗取钱财的行为就被认定为诈骗罪。[13]有的法院则认为不构成诈骗罪。
在建设法治中国这一精神理念的指引下,各项改革措施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虚假诉讼的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和机遇。
三、虚假诉讼的治理与防范
法律并非如石猴般凭空出现,而是内生于社会的。虚假诉讼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严重违背,这一原则更多是基于一种道德考量,寄希望于当事人自觉遵守并不现实。虚假诉讼的屡禁不止说明事后救济机制的滞后性,亡羊补牢式的治理手段并不是解决的良方。所谓防患于未然,笔者认为,事后救济机制只是规制虚假诉讼的一个侧面,而针对虚假诉讼的积极事前防御机制将更有利于虚假诉讼的治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打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还公正于民,又要给法官减负,遏制虚假诉讼成为一个难题。其实虚假诉讼最难却根本的是对这类诉讼的识别,司法改革则带来了一股新风。
(一)阳光司法机制监督虚假诉讼
立案登记制改变了法院年底不立案等现象,但立案阶段的形式审查客观上令更多虚假诉讼得以进入审理程序,如当事人用假身份证起诉,形式审查难以发现。但这也启示我们探索从立案阶段对虚假诉讼案件进行堵截,防患于未然。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建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从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生效裁判文书的公开到执行信息的公开,司法公开的维度不断扩大,这对社会监督诉讼程序打开了窗口,便于从外部发现虚假诉讼,拓宽了虚假诉讼发现的渠道,这些都给识别虚假诉讼提供了可能。
审判管理信息化理念之下,司法工作网络化,在当事人有虚假诉讼嫌疑时,通过系统查询列出所有该当事人所涉案件,便于案件的评查;同时网络化办公,可以实现全市乃至全省、全国法院系统的案件信息互通共享,以便各地区间对虚假诉讼发生相对集中的案件及人员进行备案,并相互通报,[14]以便立案阶段将虚假诉讼行为人挡在门外,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同时,须畅通立法与司法间的信息共享。毕竟司法实践中总结的虚假诉讼案件中问题通过立法才能上升到一定高度,并有实践的依据。此外,通过一定技术手段记录虚假诉讼行为人的不诚信行为,并与其以后的借贷、工作等各方面相互联系,这种伴随式的打击将是沉重的,也将更具效用。
(二)证据制与法官负责制倒逼审查虚假诉讼
《四五改革纲要》中证据裁判原则以及完善证据规则的要求,都强化了法官对证据的审查职能,虚假诉讼难以蒙混过关;同时对胁迫等情形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有所提高,促使虚假诉讼中利益输送将耗费更高成本,便于从经济根源上遏制。一方面,法院要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履行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的义务,促进当事人诚实举证;另一方面,要落实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双方无争议但涉及三种利益的情况责令当事人举证。尤其是在涉及他人合法权益这一方面,往往难以识别,这就要提高法官对虚假诉讼案件的警惕性。上述明确了法官的两种积极义务,此外,也要规定法官怠于履行时要承担的明确责任,否则这也将是对权利损害的另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主审法官终身负责制的重责之下,法官审查案件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加强,职权主义色彩更加浓厚,毕竟要求当事人诚实信用地履行诉讼义务作用有限,法官作为审理者,在虚假诉讼中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虚假诉讼尽管有着“72变”的外形,但当前虚假诉案件形式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集中性,方便了虚假诉讼案件的识别;而且随着对抗式与审问式诉讼模式弊端的显现,各国也逐步将目光投向了混合式的诉讼模式,这给虚假诉讼案件的发现提供了契机,可以允许法官在典型案件上的职权探知,凡有理由认为该案件存在虚假诉讼可能的,加强对其进行审查,并要求双方对彼此的关系提供充分的证据。对于虚假诉讼的识别可针对不同类型有所侧重地审查,如对民间借贷,侧重审查案件债务产生的时间、地点、基础合同、双方的经济情况;对房地产权属案件,侧重审查产权证书、是否存在以房抵债等,江苏高院《关于在民事审判中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的意见》对十类案件审查重点有所规定,可以予以借鉴。此外,用不同的方法来治理方能对症下药。比如对冒名虚假诉讼案件,“在没有直接规则可以适用,从法律适用技术角度仅能适用驳回起诉的情况下,应该裁定为驳回冒名者的起诉。”[15]因为冒名虚假诉讼人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再如针对驰名商标虚假诉讼,在认定驰名商标时存在标准问题,这是解决这类案件的前提。
(四)分梯度惩处虚假诉讼行为
正如卡多佐所说,“如果规制与现实行为漠不相关,法律的功能就被扭曲了,应当通过规制本身来适应现实需要。”[16]当前刑事诉讼法中的粗糙规定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这个愈加精致的社会,也更需要精细的法律制度设计。
笔者认为,在科学划分案件类型基础上,可以根据虚假诉讼行为的轻重缓急,将其纳入侵权法、行政处罚法,通过不同类别的惩罚措施,以实现“罚当其罪”。
首先,借鉴合同法中有关强制性的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做引致性规定,将虚假诉讼行为的规制导向侵权责任法和刑事法律。
其次,在侵权法中增设虚假诉讼的特殊侵权行为要件及后果。正因为这一行为借助了法院的裁判或调解,法律文书带来的既判力便成为了纠正违法行为的障碍,撤销裁判文书或调解书将是第一步。[17]这一特殊性也决定了增设虚假诉讼特殊侵权的必要性。同时,基于虚假诉讼行为往往与财产性利益有关的特点,对于那些侵害了案外人财产权利等民事权利的行为还可以借鉴国外的损害赔偿之诉,允许案外人在发现权利被侵害时提出损害赔偿之诉,以此作为正在审理案件的中止理由,并将不予执行判决与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作为损害赔偿之诉的结果。[18]
再者,对相对严重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虚假诉讼行为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法作出特殊规定,以1000元为基础按照情节进行罚款、拘留,这样也可分担法院的负担,减少司法资源的损耗。
最后,在程序法方面,还可以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范围进行调整,赋予案外人对虚假诉讼形成的生效裁判文书、调解书的撤销权。毕竟大量的案外人才是虚假诉讼的受害人,这一撤销权无疑是其防备虚假诉讼之矛的一面盾牌。另外,为避免检察监督的事后性所带来的迟延缺陷,检察机关也要加强对虚假诉讼典型案件的关注,通过监督及时涉入案件进行调查。毕竟无论是识别还是惩治方面,法院都有些力不从心,拥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则处在积极能动的地位,在法检良好的信息互通基础上,能弥补法院在这方面的不足。
其实,针对虚假诉讼行为,无论是哪种种治理与防范措施,都应该形成一种常态化机制,不断增强事前防范、事中发现与事后监督的程度,形成全方位的法网,不让任何虚假诉讼行为成为“漏网之鱼”。
四、结语
虚假诉讼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愈加开放与多元时代的产物,治理这一行为的第一步便是理清虚假诉讼的概念,当然对这一行为的治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立法问题或国家义务,它需要的是各方的共同努力。另外,虚假诉讼行为的治理对诉权所形成的寒蝉效应也值得警惕,不能为了打击虚假诉讼行为,而损伤在中国土壤上日益成长的公民维权意识。毕竟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不是目的,公民以及其权利才是目的。
正如康德所言,“能够震撼我内心的,一是头顶灿烂的星空,二是人类崇高的道德法则。”虚假诉讼对司法的愚弄总会终结在那些不断完善的法律之中以及对不诚信这一行为之恶的约束中。在法律的镣铐下跳舞,这才是玩转规则世界的生存与生活之道。
参考文献:
[1]钟蔚莉等.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中发现的虚假诉讼的调研报告[J].法律适用,2008(6).
[2]杨玉秋.虚假诉讼行为定性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法治论坛,2008(4):66.
[3]李浩.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4]周其华.检察机关应当对恶意诉讼实行法律监督[J].人民检察,2007(17).
[5]王飞跃.虚假诉讼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3(4).
[6]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82).
[7]朱健.论虚假诉讼及其法律规制[J].法律适用,2012 (6):143.
[8]周翔.虚假诉讼定义辨析[J],河北法学,2011(6).
[9]唐伯荣,刘振,马倩.江苏省高院关于治理虚假诉讼的调研报告[N].人民法院报,2014(1).
[10](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绮剑)•伍著.蔡彦敏,徐卉译.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从历史、文化、实务的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5.
[11]尚海明,彭雨.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基于对虚假诉讼发生与司法实践状况的实证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2).
[12]黄曙,陈艳.虚假诉讼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人民检察,2011(14).
[13]王永亮,彭勇,邹莉.情节严重的诉讼欺诈行为构成诈骗罪[J].人民司法,2009(4).
[14]王进.虚假诉讼现象的分析及应对[J].法律适用,2009(11).
[15]崔永峰.冒名虚假诉讼的案件如何处理[J].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9(6).
[16]卡多佐.法律的成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65.
[17]毕慧.论民事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J].浙江学刊,2010(3).
[18]肖建华.论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4).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6)02-0088-07
收稿日期:2015-12-14
作者简介:朱启骞,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