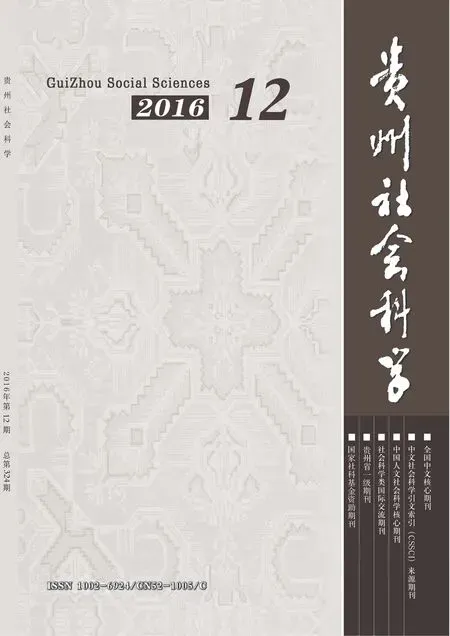山水与义理:早期桐城派作家游记中的“义法”呈现
师雅惠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山水与义理:早期桐城派作家游记中的“义法”呈现
师雅惠*
(厦门大学 ,福建 厦门 361005)
与晚明文人把“游”审美化,肯定“游”本身的价值不同,清初离家远游的士子,通常怀抱着一种漂泊无奈之感。以戴名世、方苞为代表的桐城派早期作家的行记、游记创作,即反映了这种寒士、穷士的心态。他们的游记作品,抒写了当日下层士子对世路艰险的感悟,恢复了被晚明山水小品作家中断的“山水—俗世”的认知框架,重视对山水所引发的的人世义理的表达。
戴名世;方苞;桐城派;晚明山水小品
在已有的桐城派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桐城派的兴起,是为了“助流政教”[1],桐城派早期文论如戴名世所提倡的“道、法、辞”,方苞所提倡的“义法”、“雅洁”,均是古文家对当日朝堂之上厘正文体、倡导“清真雅正”文风的回应。这种说法固然有合乎事实的一面,但是却忽略了早期桐城派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实际上,桐城文章向“清真雅正”靠拢,是在《南山集》案之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迫的选择。从戴、方的创作实践来看,他们有不少作品,反映的是寒士、穷士的心态,是“不平则鸣”,而非雍容大雅的颂世之文。这类作品中,游记、行记占了很大部分。与晚明性灵派的山水小品不同,戴、方的山水游记,在格调上较为萧瑟,在写法上则注重人世间“义理”的表达。对此,现今学界尚未有深入论述。
一、 山水娱情:晚明文人的“游”观与文学表达
游记文体的起源,可追溯到南北朝时的地记与行记。但其真正地创立、成熟,则在唐代。一般文学史均以柳宗元《永州八记》等记录山水之游的文字作为游记的成型之作。柳宗元游记中的作者心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偏于老庄之道的“恬适”,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另一类则是仍不能忘怀世事的哀怨,如《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等。这两类情感,在柳宗元山水记中,错综交会,即使是同一篇作品内部,也经常呈现出不同的声音。晚明文人的游览活动及山水游记,较多地继承了柳氏山水记中“山水娱情”的一面,即附着在“游”这一活动上的家国责任、人事之思被剥离,山水本身的审美价值及山水对游览者品格的助益得到发掘和重视。
晚明文人,特别是东南地区文人,有着好游的风气。[2]在万历以后涌现出的大量游记作品及与“游”相关的表述中,可以看到,许多文人把“游”作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认为“游”是士子完成艺术生命、养成超旷人格的重要手段。如公安派袁氏兄弟,亦推崇“游”的生活,袁宏道认为“溺于山水”与“溺于酒”、“溺于书”、“溺于禅”一样,都是一种通人达士的生存方式[3]卷五十一《游苏门山百泉记》,1484,并表达过与王士性类似的“与其死于床第,孰若死于一片冷石”[3]卷三十七《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1145的态度,去世前不久,还意欲“于青溪、紫盖间结室以老”[4]《游居柿录》卷五,1207。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在三十九岁后即以舟为家,过着半游半居家的生活。其《游居柿录》开篇,认为远游有“涤浣俗肠”、“安坐读书”以及访问师友、切磋学问三种益处[4]《游居柿录》卷一,1105,常为学者所称引。稍晚于袁氏兄弟的竟陵派文人亦好游,钟惺认为“山水者,有待而名胜者也”[5]卷一六《蜀中名胜记序》,243,山水须借助事、诗、文,才能成为名胜,而诗、文显然是文人的能事。如此,文人便成为具有搜剔、凸显山水精神之能力的价值创造者。游览成为文人体现自身才华的活动。
“游”的艺术化、日常生活化,在晚明游记创作上的影响,除了作品数量的大幅增加外,还表现为写法的开拓与创新。首先是细节的丰富与层次感的增加。许多文人强调“游”要深入细致,要有舒缓的节奏与专一投入的心态:“不论迟速远近,庶几遇好山水,好友朋,可以久淹其间,极登涉盘桓之趣”[4]《游居柿录》卷一,1105,在登临中讲究穷蒐遍讨,并且伴以各种富有文化内涵的举动,如访碑、赏字画、题壁、构建亭台、聚会清谈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游记,对山水的描写更为细致,对游者的情感和社会化活动的记述也更多。最典型者如袁中道的长篇日记体游记《游居柿录》,全文共十三卷,十余万言,记述了作者从万历三十六年十月到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年间的“游居”生活,既写山水,也写山水中人,恍若一幅水边林下的文人行乐长卷。这种细致描绘的手法,与南北朝地记有类似处,但较之南北朝地记,又增添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其次是对山水精神的体会、捕捉。晚明文人在描写山水时,往往不满足于对山水外在形貌的描绘,而是力求写出山水内在的精神,如竟陵派的游记,常被认为造语尖新,林纾《春觉斋论文》中即批评谭元春游记中多“矜情作态”、“张皇”之处。[6]《论文十六忌·忌轻儇》,100—101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刻意“陌生化”、故作矜张的句式,正是作者追摹山水内在性格的一种尝试。如《再游乌龙潭记》中,写风雨雷电中的乌龙潭,“苍茫历乱,已尽为潭所有,亦或即为潭所生”[7]卷二十,558,乌龙潭被作者视为有生命的物事,奇幻的雷电与波光,不过是它生命力的表达。又如谭元春《游玄岳记》:“琼台峰落落有天地间意”[7]卷二十,550,“桃花开我立处,松古于门外”[7]卷二十,550,“两重山接魂弄色于喧霁之中”[7]卷二十,547;钟惺《中岩记》:“诸峰映带,时让时争,时违时应,时拒时迎”[5]卷二十,325;《岱记》:“壑穷,亭之,声光相乱,水木莫敢任”[5]卷二十,337等等,皆意在凸显景物本身意趣。这种写法,与以姜夔为代表的南宋后期咏物词中对物的“客观表述”十分相似,都可视为对“咏物言志”传统的疏离与背叛。[8]7
二、“我辈是游民”:早期桐城派作家游记中的人事之思
与晚明游记中对“游”的本身价值的凸显不同,在清初文人笔下,“游”不再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审美活动,而是承载着家国、人生责任的悲壮、无奈之举。顺治及康熙初年,许多遗民文人的远游,具有隐身避祸及图谋恢复的政治意味,著名的例子如顾炎武的北游,屈大均的东北、西北之游,阎尔梅的西北之游,魏禧的吴越之游,傅山的南游等。康熙中后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定,以及遗老们的日渐凋零,文人的出游目的又有所变化,谋生、求利禄,成为许多文人,特别是下层文人出游的主要动力。除例行的赶考之外,许多文人还应聘成为各级官员的幕僚,由此展开他们的行旅生涯。[8]康熙年间陈维崧《王怿民北游草序》中,对当日不得不离家远行的士子之心态,有极为真切、同情的描述:
士之出游者,其间水陆之所经,南北之所限,必有舟车跋涉之劳,霜露风霰之苦,波涛栈阁之危;至于一介行李,又必僦邸舍,雇仆马,料费用,非如輶轩上使所至,有供亿之繁,驿馆之盛也。以故駪駪征夫,劳苦倦谷丸,往往自言其伤者极多。矧夫士之于役者,不惮千里之远,犯险阻,冒雨雾,重趼而至,固将见用于世也。而或摈斥于有司,使其琐尾流离,为乡里小儿所笑,自非上圣,流连怼激,而为不平之鸣,庸讵免乎!”[9]陈迦陵散体文集卷一
仕宦者出游,可借助驿传资源,而贫寒士子出行,则须自备旅费、仆役,自觅舟车、旅舍,因此旅途更为艰辛。此外,士子的出行,往往具有极现实的“进身”目的,而世路多风波,他们的出游理想,并不那么容易实现。本文所要论述的早期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在中进士之前皆有过离家远游的经历,他们的游记创作中所体现的作者心态,便更多地继承了柳宗元游记中“怨”的一面,并不那么“温柔敦厚”。这种悲怨、愤激的心态,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对“客游之困”的自叹自伤。这以戴名世的诸篇《日纪》最为典型。戴名世生长于桐城,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外为衣食奔波。康熙十二年始,即常年在桐城附近庐江、舒城等地教馆。康熙二十五年考取拔贡,此年冬北上入都。在国子监肄业后,先做过八旗官学的教习,又曾入山东学政任塾、浙江学政姜橚幕,其间数次南北往返,直至康熙四十八年才中进士,授编修,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戴名世自言一生“遍历江淮、徐泗、燕赵、齐鲁、闽越之境,凡数万里,每行輙有日纪”[10]卷十一《北行日纪序》,291,这些日记,今所存者有四种,分别为记录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到七月从南京到北京行程的《乙亥北行日纪》,康熙四十五年四月至五月从北京到苏州行程的《丙戌南还日纪》,以及记述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四十年两次应浙江学政之聘,随其视学浙江各地的《庚辰浙行日纪》、《辛巳浙行日纪》。这几篇纪行文字,特别是《北行日纪》与《南还日纪》,对冬夏间路途气候的迫人、南方士子对北方风俗的难以适应,以及“盛世”中的人情鬼蜮,有着细致生动的描绘。在《北行日纪序》中,戴名世表示,这种充满艰险的出游,并非自愿,而是迫不得已:“呜呼!客游之困未有甚于余,而驰驱奔走之无益,亦未有如余之甚者也。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也。’陶渊明诗曰:‘饥来驱我去,出门何所之?’以余之狷隘,忧愤满怀,而仆仆于朝市之间,所往而辄踬,固早自知之,然而不能不为此者,诵子路之言与渊明之诗,其亦可泫然而流涕已矣。”[10]卷十一《北行日纪序》,291远游并不能助他实现人生理想,也不能给他愉悦的审美享受,数万里的旅途,充斥着的只是艰辛、狼狈与屈辱的体验。远行途中的颠沛不适,还加重了他的岁月蹉跎之感,诸篇《日纪》中,常见此类感想,如《乙亥北行日纪》六月十七日、十八日:“忆余于己巳六月,与无锡刘言洁自济南入燕,言洁体肥畏热,而羡余之能耐劳苦寒暑。距今仅六年,而余行役颇觉委顿,蹉跎荏苒,精力向衰,安能复驰驱当世?抚髀扼腕,不禁喟焉而三叹。”[10]卷十一《乙亥北行日记》,296《庚辰浙行日纪》五月十八日:“(余)年近五旬,而无数亩之田可以托其身,经岁傭书客游,闭门著书之志将恐不得遂,为之慨然泣下。”[10]卷十一《庚辰浙行日纪》,297羁旅伤怀,是从宋玉《九辩》开始的行旅词赋的主题,戴名世则用散文的形式,继承了前代文人“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咏叹。
(二)对山林的向往和对人世的厌弃。在魏晋以来的文学传统中,“山水”往往具有与“俗世”相对的文化品格,山水被认为是超脱于世俗功利的所在,游览者不仅可藉山水体悟玄理,而且可依凭山水对抗世俗人生。晚明山水游记中,对人与自然精神互动的描写十分丰富,但“游”的艺术化、日常生活化,使得在这一时期的游记作者那里,“山水”与“俗世”的对立被淡化了,甚至山水即是人间。戴名世、方苞的游记,则回到“山水—俗世”的框架中,“俗世”再次成为他们观赏山水时的潜在参照。如戴名世《河墅记》,河墅为潘江在桐城龙眠山中的别业。此文在记述河墅周围环境后,不无欣羡地表示:“此羁穷之人,遁世举远之士,所以优游而自乐者也。”[10]卷十,280又说:“小子怀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过先生之墅而有慕焉。”[10]卷十,280以山水为避世之理想场所。据戴廷杰《戴名世年谱》,此文作于康熙二十一年戴名世三十岁时,此时戴氏在舒城教馆为生。如果说此文中的“遁世之思”还是青年人的故作姿态,那么康熙四十年所作《雁荡记》,则是作者历经沧桑后的心境写照。此文末段,在描述自己望见雁荡诸峰,“怀抱顿仙”的感受后,沉痛感叹道:“呜呼,余怀遁世之思久矣,辗转未遂,至是垂暮无成,万念歇绝。他日人见有衣草衣,履芒鞋,拾橡煨芋而老于此间者,必余也夫,必余也夫!”[10]卷十,276此时戴氏在浙江学政姜橚幕下,年华渐逝,老大无成,不免有归隐山林、与人世相决绝的想法。只是这一心愿,在现实生活压力下,并不能付诸实行。戴名世曾于康熙四十一年在桐城南山买田归隐,但种田收入,并不能满足家用,因此他无法常居于家,“每岁不过二三阅月,即出游于外,奔走流离”[10]卷十《砚庄记》,283,不得不继续远游的日子。
较之戴名世的“性好山水”,方苞与山水的接触似乎不多,但同样表现出对山水清气的敏锐感知与向往。又如康熙三十三年在涿州教馆时与友人信:“所居左山右城,岗峦盘纡,草树蓊翳,四望无居人;鸟鸣风生,飒然如坐万山之中,平生所乐,不意于羁旅得之。”[11]集外文卷五《与刘言洁书》,668康熙五十七年所作《游潭柘记》:“林泉清淑之气,旷然与人心相得。”[11]卷十四,422然而因现实所迫,更因不能放下入世理想,山水对方苞来说,终究只是一个遥远、虚幻的所在。在《游潭柘记》末段,即表达了这种在“山水”与“俗世”之间矛盾不已的心情:“昔庄周自述所学,谓与天地精神往来。余困于尘劳,忽睹兹山之与吾神者善也,殆恍然于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乡,昔之日,谁为羁绁者?乃自牵于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负此时物,悔岂可追耶?……余老矣,自顾数奇,岂敢复妄意于此?”[11]卷十四,422—423写作此文之前五年,方苞蒙皇恩免治《南山集》牵连之罪,此时以白衣供职蒙养斋。俗世虽可憎,但身为罪人,劫后余生,又受知遇,自应尽心王事,不宜再“妄意”于山水。这种依违徘徊,可说是文人“山水之思”的一种曲折表述。
(三)世事难料、人生如梦之感。戴、方游记中,常常笼罩着一种对世事的忧虑、不确定感,如戴名世《西园记》,先记明孝陵及其旁坟墓、碑碣的颓败,再将明魏国公徐达之西园的易主与园中六朝松的独存两相对照,得出“凡治乱兴亡之故,盖有难言者”[10]卷十,267的感想。自然山水是人事沧桑的见证,戴氏的文字所要表达的,亦是一种在永恒山水面前涌起的关于人世历史的虚无感。又如方苞作于雍正元年的《封氏园观古松记》,在记述一日聚会中种种突发状况后写道:“以一日之游,而天时人事不可期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万变,能各得其意之所祁向邪?”[11]卷十四,429“天时人事不可期必”,即人无法掌控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走势。从这一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晚年方苞的内心中,除“抗心希古”、锐意求道之外,还有消极甚至惶恐不安的一面。
戴、方游记中,虽也有“因游悟道”的记述,如方苞《记寻大龙湫瀑布》,认为舆夫畏远,不愿入山之深处,正类似于小人千方百计阻挠君子,令其不得接近先王之道。又其《游雁荡记》,对儒家山水“比德”说进行发挥,认为雁荡“岩深壁削”,能使游者“严恭静正之心不觉其自动”,进而领会“圣贤成己成物之道”[11]卷十四,428,等等。但这类醇正“近道”的篇目并不多。对自然、人世双重“行路难”的抒写,仍是二人游记的主调。乾隆年间人黄景仁在回顾自己的行旅生涯时曾言:“若绳三尺法,我辈是游民。”[12]卷十四《偕少云雪帆小饮薄醉口占》从上文所述戴、方游记中的作者心态来看,戴、方亦是把自己视作是“盛世”中漂泊无定、物质上和精神上都不得依止的寒窘“游民”。
三、以我观物:“义法”理论与游记创作
早期桐城派最具代表性的写作理论,是方苞的“义法”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11]卷二《又书货殖传后》,58戴、方的游记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义法”理论,为我们理解“义法”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首先,戴、方所认为的文章之“义”,涉及世间人情物理的多个方面,并不局限于儒家义理。戴名世、方苞学宗宋儒,都是“文以载道”说的拥护者,戴名世在谈论时文写作时有“道、法、辞”的议论,认为文章之道,“具载于四子之书,幽远闳深,无所不具”[10]卷四《己卯行书小题序》,109。方苞亦认为儒家义理是文章之“义”的根本:“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11]卷六《答申谦居书》,164他又解释“言有物”说:“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其下如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志欲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故纪事之文传。荀卿、董傅,守孤学以待来者,故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达于世务,故论事之文传。凡此皆言有物者也。”[11]集外文卷四《杨千木文稿序》,608即以儒者的功业、德行、思辨议论为文章之“物”的主要内容。但是,依据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二人游记中的“物”,并不一味“雅正”,而是既包括儒家道理,也包括人世间种种情态,既有对圣贤典训的体悟,亦有游离于“安贫乐道”等正统观念之外的愤激之思。这种创作和理论之间的偏差,或许并不是由于笔力所限,而是作者的“有意为之”,这一点,可以从方苞对柳宗元游记的态度上见出端倪。方苞对柳文总体评价不高,认为柳宗元于道术所得不深,文辞亦不够“雅洁”[11]卷五《书柳文后》,112。但对其山水游记,却极为赞赏,认为此数篇能一空依傍,自铸新词:“言皆称心,探幽发奇而出之,若不经意”[13]《柳文约选·始得西山宴游记》评语。其编选于雍正十一年的《古文约选》中,选入除《柳州东亭记》之外的柳氏全部山水记。而稍早于《古文约选》的几部思想方面较为“正统”的文章选本,如《御选古文渊鉴》、张伯行选《唐宋八大家文钞》、蔡世远选《古文雅正》中,柳氏山水记均未收入。可见方苞论文,所持的是“主文”的文学家眼光,而非“主理”的道学家标准。亦因此,他所说的文章之“义”,便不仅仅是儒家之“道”的复述,“义法”说,也并非“文以载道”说的翻版,而更多的是一种对文辞本身结构的阐释。
其次,在“法”的方面,对人世之“义”的看重,使得戴、方游记侧重“以我观物”式的主观表达,并在章法和语言上都呈现出简洁、含蓄的特点。晚明人山水游记,多长篇,或成系列,以细致描摹、穷形尽相为能事。戴、方游记则因重点不在山水本身,故很少作长卷式的描绘,而是多截取片段之景,余者点到即止,或留一虚幻语,不作实写。如戴名世《唐西浦记》,记述西山唐西浦之梅溪,而以“常寻其去径,去径复隘如来径,数里不能穷”[10]卷十,265作结。《游西山记》只写龙湫、来青轩二处,其余则以“进而深焉,其幽窅奇怪不知当何如也”[10]卷十,269一句带过。《游浮山记》更是只记了一个舟中远望浮山的印象,一段“过而未能游”的遗憾,欲以“先为记之如此”[10]卷十,266的方式,表明自己终将优游于此的决心。方苞《游丰台记》、《记寻大龙湫瀑布》,亦是断片而非全景。王立群在论及古代游记时,认为文学游记“或以客观之景为主,或以主观之情为主”[14],并据此将文学游记分为再现性与表现型两种。以此为标准,戴、方的大多数记游文字,均属于“略景重情”的表现型游记,以山水描写作为抒发义理的缘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为山水而山水”、缺乏主观情感之弊,使文章具有“物色尽而情有余”[20]卷四十六《物色》的特点。清初古文体系下的批评家看重游记的“寓意”,如何焯认为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多寓言,不惟写物之工”[16]《始得西山宴游记》评语,1647,林云铭认为“叙山川之胜与见闻之奇,且得尽所游之乐”,是游记的常调,但若只如此写,“有何意味!”只有在观物基础上“发出一番大议论”,文章才称得上精采。[16]《游褒禅山记》评语,1790戴、方的游记创作,亦与这一重“义理”、讲“言外之意”的时代思潮同趋。
游记重“义”、重作者自我表达的理念,在戴、方之后的桐城派代表作家如刘大櫆、姚鼐那里得到继承,刘、姚游记,亦有较多的主观情感在内,如刘大櫆《游大慧寺记》中对士人独立人格的提倡,《游万柳堂记》中对富贵浮云的感悟,《游晋祠记》、《游三游洞记》中对自身生命微贱的哀伤,姚鼐《观披雪瀑记》中对世事无定、人事难期的慨叹,《游双溪记》中对自身处境的怨望等。虽然桐城派作家的游记中,也有一些只简述地名、方位,类似《山经》、《禹贡》等地志的作品,如戴名世《雁荡记》的前半部分、刘大櫆《游浮山记》等,但从整体上看,人间情思与自然风景的结合,以“情”统“物”,依然可以说是桐城派游记的主要特色。
[1] 张光亚. 桐城派的主要特点及其历史借鉴[M]//桐城派研究论文选. 合肥:黄山书社,1986:9.
[2] 魏向东. 晚明旅游地理研究(1567—1644)——以江南地区为中心[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43.
[3] 袁宏道. 袁宏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 袁中道. 珂雪斋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钟惺. 隐秀轩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 林纾. 春觉斋论文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 谭元春. 谭元春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尚小明.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5—18.
[9] 陈维崧. 陈维崧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6.
[10] 戴名世. 戴名世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方苞. 方苞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2] 黄景仁. 两当轩集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36.
[13] 方苞,选. 古文约选[Z]. 清雍正十一年刊本.
[14] 王立群. 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J]. 文学评论,2005(3):155—160.
[15] 刘勰,撰. 陆侃如、牟世金,译注. 文心雕龙译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95:552.
[16] 姚鼐,编选. 吴孟复、蒋立甫,评注.古文辞类纂评注[Z].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郑迦文]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桐城派早期作家群与清初文坛状况研究”(12YJC751067)
师雅惠,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I206.2
A
1002-6924(2016)12-056-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