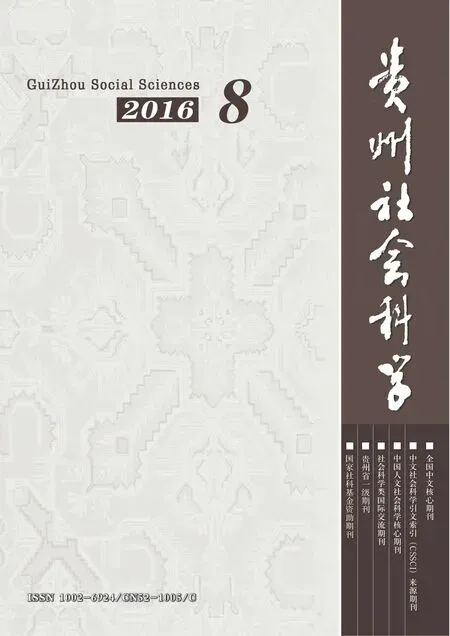风险社会境遇下的道德迷思与教育应对
赖 芳
(1.成都工业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0; 2.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610059)
风险社会境遇下的道德迷思与教育应对
赖芳1,2
(1.成都工业学院,四川成都611730; 2.成都理工大学,四川成都610059)
风险社会作为道德存在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着“个体化”危机造成道德行为规避、“有组织不负责任”导致道德信任危机、人为的“不确定性”增强道德预期疑虑和“反思性”引发道德模范形象批判等道德迷思,而这源于对风险社会特征以及道德风险对道德教育冲击的非理性认知。面对风险社会下的道德迷思,需要学校教育开展风险教育培养风险意识、提升反思性社会批判能力与发挥学术的力量推动道德(教育)制度设计完善等措施进行教育应对。
风险社会;道德迷思;学校教育;风险教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道德风险是其主要表征之一,但当人们还在为老人摔倒“扶与不扶”进行争辩的时候,当我们在探讨道德风险存在几何的时候,我们的学校道德教育却岿然未动,对于外界的道德辩论处于一种“边缘人”状态,这也要求我们当道德风险逼近甚至进入学校,对学校道德教育进行正面“挑衅”甚至“正面攻击”时,不能“无动于衷”或“坐以待毙”,更不能“画地为牢”,而应对作为“社会事实”的道德风险予以回应,为风险社会中的道德风险规避与消解做出自身的努力,这要求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便是道德风险的社会空间——风险社会及其特征为何?其次明晰传统道德规范与信仰带来的迷思如何?而我们学校又如何进行教育应对,而本文即是一种尝试,以期求教于方家。
一、风险社会:道德存在的社会空间
道德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因此也是道德存在的社会空间。而风险属于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风险不是已经发生的社会事实,而是一种不可预期的后果,“表明了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121。也就是说,风险是一种人类创造出来的“非预期风险文明”,而风险社会则是这种“非预期风险文明”存在的温床。
虽然学界对于风险社会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如“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由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组合而成,“具有普遍的人为的不确定性原则的特征,它们承担着现存社会结构、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更加偶然和更易分裂的社团组织转型的重任”。[2]19同时认为风险社会的“中心议题”是各种“现代性后果”,“都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化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无可置疑地让那种通过制度使副作用变得可以预测的做法受到挑战,并使它成了问题”。[1]119
而对于风险与风险社会特征已形成共识,即“全球化”、“个体化”、“不确定性”和“有组织的不负责”和“反思性”。“全球化”是指风险存在于全社会,而不仅仅是某个地区的风险;“个体化”是指社会问题逐步分解为各个个体身上而不再呈现整个社会结构的“病症”;“不确定性”风险与社会个体化密切相关,个体的自由消解了社会结构的确定性而增加了风险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性;“有组织的不负责”是拥有话语权的专家、官员构建出一套自我“解脱”的措辞,将自己制造的危险推脱成社会风险而不需要承担任何后果;“反思性”是人们通过理性思考对现代性社会的一种质疑与批判。
二、道德迷思:风险社会境遇下的“后果”
风险社会的这些特征与现代社会道德迷思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为:“个体化”危机与社会道德行为规避密不可分;风险“不确定性”增加了人们对道德预期的疑虑;“有组织的不负责”造成道德信任危机;而“反思性”引发人们对道德模范形象的质疑。
1.“个体化”危机造成道德行为规避
根据层次进行划分,道德分为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两个层面,在风险社会之前的社会中,社会伦理层面的道德占据主导地位,一旦个人做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便会遭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指责甚至抛弃,但在风险社会中,社会通过“制度化”设计给予个体更多的选择自由,这种自由导致现代社会成为“个体化社会”,集体不再是他们进行思想与行动衡量的唯一标准,而是更多关注个体的诉求,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与之期望相一致的证书与能力,从而实现自我发展。[1]70社会中的个体不再遵循社会的道德认同,开始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而进行着道德选择,即使所做出的道德行为与已有的社会道德认同相违背,也不会像以往社会那样受到大众与媒体的一致指责,反而会使用各种借口与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并能够获得赞成自己行为的肯定与支持。
风险社会的“个体化”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解读:解放的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祛魅的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原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以及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在这里它的意义完全走向相反的东西——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3]156“脱离”造成人们对本应做出的道德行为开始规避,如媒体对社会中的好心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的报道层出不穷,使得人们对自己的道德行为选择产生困惑,为此卫生部也出台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但却丝毫没有平息对于社会道德滑坡的社会声音,究其根本也是“个体化社会”中社会个体的不道德行为与其他个体的道德行为产生道德交换的不对等,由此造成人们道德行为的规避。
2.“有组织不负责任”导致道德信任危机
乌尔里希·贝克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认为风险社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权威专家了,因为专家已经作为个体生活在“个体化社会”中,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体化”的基本属性,在面对自己制造的社会风险时,专家和权威机构会构建出一套“话语”体系来为自己的措辞推卸责任,这被贝克称为“有组织的不负责”,使得其在进行事件解读与界定过程中不但没有解除公众的对于事件的困惑,反而对专家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进行怀疑,也使得公众对整个社会权威产生信任危机,如在对药家鑫杀人案中药家鑫杀人行为进行解读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李玫瑾教授将之解读为“钢琴杀人法”,此言论一出便遭遇信任危机与质疑声一片,虽然后期她解释为“语境错位”,但对于权威解读的随意性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娱乐消遣的谈资。造成这种原因是“在风险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产生的危险或人为的不确定的特性与结构和内容植根于以前世纪性质的不同的普遍的定义关系之间,出现了错配”。[2]145也就是说对风险社会的道德信任危机的解读已经无法使用以往已有的理论或体系。
3.人为的“不确定性”增强道德预期疑虑
吉登斯将风险社会分为“自然风险”与“人造风险”,同时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最令人不安的威胁是‘人造风险’,它们来源于科学和技术的未受限制的推进。科学理应使世界的可预测性增强。它往往正是如此。但与此同时,科学也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其中许多具有全球性。对这些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基本上无法用以往的经验来消除”。[4]乌尔里希·贝克也从风险维度的角度认为风险社会人们更多的关注风险分配逻辑问题,而不是工业社会时代的财富分配问题,而且这种分配不再按照阶级属性而是按照阶层属性进行分配的,“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3]36这也造成个体道德行为的风险分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看到老人摔倒时,过路人并不是不想扶,而是由于其无法对摔倒老人的道德行为预期以及弄清其可能性风险的分配逻辑,在通过社会报道的一系列讹人事件之后,即使绝大多数的热心人都被证明自身是清白的,但是讹人的摔倒老人和责骂好心人的家属却没有承受其应有带来的道德甚至是法律风险,再比如2013年四川达州3位小学生因扶起自己摔倒老太之后被讹而后经过警方调查才还其清白,学校教育中的学会“尊师敬长”、“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烂熟于心的道德要求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对于两年之后再次回到原点开始重新生活的小学生及其家人却仍然对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对于是否仍然会去扶摔倒老人变得纠结,甚至其中一位学生家长为了避免日后可能的风险而已经搬离达州。[9]这种不平等的道德风险分配逻辑降低了人们的道德预期,也强化了人为的“不确定性”导致的道德信任危机。
4.“反思性”引发道德模范形象质疑
作为风险社会后果之一的“个体化社会”假定每个人都是可以进行自我反思的,风险社会的反思不同于以往工业社会是因为人们不再以自身经验而是通过理性思考来对道德行为进行判断,这也更多的导致人们对于自身以及他人行为的“高度反思”,个体如若在社会上生存就需要具备反思的能力,这并不是因为个体在社会中变得更加聪明,而是因为“专家(包括科学知识)制造的信息不再能完全局限在特定的团体中,相反,普通人在自己的日常活动中习惯性地对它加以诠释并作为行动的依据。”[6]而且这种反思不仅是对事件结果的反思,更多时候是对整个事件过程,使得个体在每一个环节都会对自己的思想与行动进行不断的批判性反思,以达到思想与行动始终确定统一彼此一致。[7]这使得人们开始对以往确定性与绝对性的事实进行质疑,同样对于传统社会的道德模范形象也开始进行反思甚至是批判,而道德模范形象是否经得住这种反思与批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引起人们的质疑。
“选树榜样是营造道德氛围,提升道德力量的重要内涵。社会转型时期的榜样教育,既承袭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努力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开展了有意的尝试,不断取得进步”。[8]但在进行道德榜样教育过程中,也出现了要求榜样至始至终的善意表达、无所不包的榜样行为与“全人化”道德形象等道德苛求的问题,“由于缺少足够的角色意识,不注意区分复杂情况下不同主体的道德权利和责任,这一点使得我们的公共道德标准一直显得不够成熟和稳定。长期以来人们谈及道德时,总是热衷于从抽象的人性和个人出发,……将各种问题都归结于对一般个人的道德诉求,而当代(职业)角色道德建设的特殊意义,则一直不能提升到它应有的地位”[9]。这导致虽然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也对此榜样学习存在质疑,但在整体性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中,共同的道德基础消解了个体的道德要求。在道德价值多元化与“个体价值多元化”的风险社会中,“孤独的个体”代替整体性与集体性,对所树立的道德榜样真实性与共识性提出了质疑,不再苛求“个体化社会”中“孤独的个体”成为普遍性的道德榜样。
三、风险社会境遇下道德迷思的教育应对
如同工业社会的道德危机一样,风险社会的道德迷思的厘清对于道德社会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风险社会和工业社会一样,教育在道德风险应对上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风险社会,我们教育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面对道德冷漠,教育不能成为“旁观者”或“边缘者”,甚至成为道德风险放大的帮凶。[10]针对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
1.开展道德风险教育增强风险认知
风险社会的全球化特征已经表明整个人类社会处于风险之中,学校不再是一方“净土”,一个封闭式的教育场域,其与其他场域(家庭、社区、社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校中不存在或者极少发生的道德风险不代表其他场域不存在或不发生,因此学生需要对风险社会加强认识,这需要针对性的开展道德风险教育,以此增强学生对于风险的认知。
那么如何开展道德风险教育来增强学生的风险认知呢?学者斯特芬·埃尔摩斯和沃尔夫·迈克尔·罗斯提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能力的培养来帮助学生为风险社会做准备,即“自我决定;对积极的社会参与;帮助那些没有自我决定和参与社会能力的人。通过对特定问题的彻底了解,即了解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来发展人的上述三种能力”。[11]这要求我们无论从德育课程设计还是课程实践教学活动都应该将风险教育纳入其中,增强道德风险教育的实然性,结合应然性帮助学生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认知,并通过开展社会实践、社会观察、阅读等活动提高学生预防风险和适应社会种种变化的能力。
2.提高反思性道德批判能力
传统社会里的人类“确定性追求”在风险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但贝克指出:“世界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主张或鼓励在风险和人为的不确定时代里恢复控制逻辑。这是现代化第一个阶段的简单措施。相反,在世界风险社会,控制逻辑从根本上受到质疑。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社会可以变成自我批判的社会的一个原因”。[12]因此,道德风险的“不确定性”与道德行为的“个体化”要求学校提高学生对道德的反思批判能力,这种培养不在于夸大个体的“英雄主义式”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基于学生个体的经验,而是学校系统的理性思考训练与培养。一方面学校需要培养作为风险社会中“孤独的个体”的学生交流与对话能力,虽然传统社会中的共同社会价值与社会共识基础已经丧失,但在同一语境下的道德观点对话与交流仍有存在的可能与必要,这需要教师在进行道德教育过程中创造开放的道德对话氛围,帮助学生树立一种对话的道德观念,确立交流与对话的教学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学生群体的“理解性批判”达成“批判性共识”,“理解性批判”是指学生通过对自己及他人生活异同的比较分析获得对对方的理解从而形成一种道德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既不同于“团体公正法”,也不同于“价值澄清法”,是一种教师指导之后学生自我反思性道德批判能力的生成与建构,并最终形成“重叠共识”。
3.发挥“学术的力量”推动道德(教育)制度完善
风险社会已经告诉人们单纯的道德自律已经不能维护社会的道德规范运行,而制度设计才是道德的根本保证,一般认为道德制度设计与完善属于法学、伦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范畴,教育者只是对他们设计出的道德制度进行推广与执行,事实上,对风险社会中道德风险进行预防与消解教育不能缺位,对其针对性的道德制度设计教育同样不能缺位,因为教育不能仅是一个“隐形”参与者,可以发挥“学术的力量”推动道德制度和道德教育制度完善,对于社会中的道德事件话题如“南京彭宇案”、“小悦悦事件”、“幼儿教师虐童事件”等,教育学者运用已有的知识同其他学科学者一道对这些事件进行学术分析,并从教育学理论视角提出针对性的道德风险预防与消解建议,通过改进现行道德教育课程实现社会与学校道德教育一致性。
[1](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薛晓源、周战超,主编.全球化与风险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尹宏毅,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218.
[5]张柄尧、周子铭.达州“扶老案”当事人退还“委屈奖”举家搬迁[EB/OL].http://money.163.com/15/0908/09/B2VTKMT000253B0H.html.
[6](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M].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
[7](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3.
[8]彭怀祖.论道德模范和道德苛求的消解——以提升榜样效应为视角[J].伦理学研究,2013(2):23.
[9]李德顺.道德转型的足迹——对我国近30年若干伦理事件的评述[J].江海学刊,2010(4):17.
[10]高德胜.道德冷漠与道德教育[J].教育学报,2008(3):80.
[11](丹)斯特芬·埃尔摩斯、(加)沃尔夫·迈克尔·罗斯.全民素质教育:为风险社会做准备[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6):48.
[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再思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48.
[责任编辑:黄昇]
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川西藏区生态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及模式研究(2015SZ0224)
赖芳,成都工业学院副教授,成都理工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D64
A
1002-6924(2016)08-10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