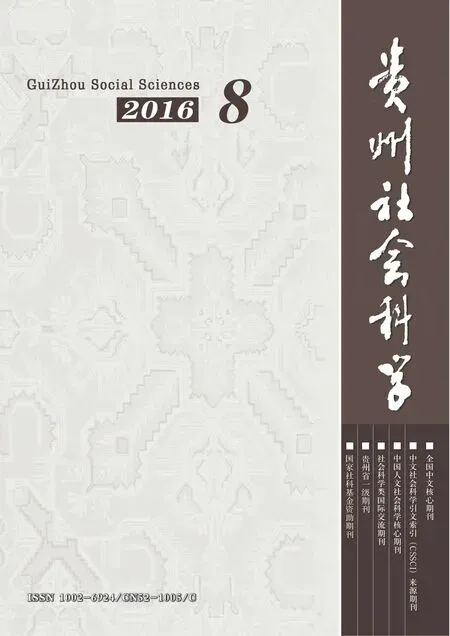中国现代佛教文学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贾国宝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中国现代佛教文学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贾国宝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233030)
当前中国现代佛教文学的研究并不发达,主要聚焦在苏曼殊、弘一等重要僧人作家上面,故而导致若干学术“盲点”的存在:现代佛教思潮对僧人创作的巨大影响尚未深入分析,五四以后的学僧作家群长期湮没无闻。为此,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以进一步推动其研究进展:考虑到现代僧人作家的创作实际,“僧人文学”作为专门的概念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开展现代佛教思潮、民国佛教期刊与僧人创作“三位一体”的综合研究;运用比较方法,推动现代重要僧人作家如八指头陀、苏曼殊与弘一等研究的深入;中国现代佛教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加强其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考察。
佛教文学;现代佛教思潮;佛教期刊; 学僧; 僧人文学
中国现代佛教文学,作为中国佛教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虽不如中国古代佛教文学丰富,但在现代佛教思潮、民国佛教期刊、重要僧人作家等方面取得一些较大进展。是以拟对其略作综述,并提出展望,若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补正。
一、中国现代佛教文学研究的回顾
(一)现代佛教思潮的研究与民国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
现代佛教思潮,是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研究著作颇为丰硕。海外方面,美国学者霍姆斯·维慈的研究最为典型,其《中国佛教的复兴》着重揭示了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实践与艰难。在台湾,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代表著作是释东初的《中国佛教近代史》(中华佛教文化馆,1974年)。著者释东初作为这股思潮的参与者与亲历者,一方面增强了此书叙述的现场感与亲近感,另一方面理论分析的缺乏与不足也随之相伴而生。在大陆,此研究甚晚,但从1990年代起,研究专著才开始陆续出版,如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以及唐忠毛的论文《20世纪中国佛教思潮及其研究反思》,都充分显示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关注。较为遗憾的是,这些论著基本拘囿于现代佛教思潮这一社会思潮层面,未曾揭示其对现代僧人的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或者将其作为现代僧人作家创作的思潮背景给予考察,但这些研究为推动中国现代佛教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期的准备,这是不能否认的。
在民国佛教期刊出版方面,近些年来取得重大进展。《海潮音》作为民国时期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佛教刊物,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更为重要的是,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及补编和《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报纸)》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编辑出版,集汇了民国时期的一切报刊杂志。民国时期,僧人作品,尤其是青年学僧作家的创作,基本发表在这些刊物上。可以说,佛教期刊的整理出版,对于推动现代僧人创作研究的深入可谓居功至伟。
(二)现代重要僧人作家研究
迄今为止,对现代僧人作家给予整体研究的专著比较稀少。张长弓的《中国僧伽之诗生活》(著者书店,1933年),简略地梳理了东晋以来僧诗的创作,指出晚清诗僧八指头陀和苏曼殊为中国诗僧的“殿军”。孙昌武的《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2010年),内容全面丰富,僧人创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从东晋一直写到近现代,虽论述八指头陀、弘一、宗仰等重要僧人的创作,却对苏曼殊*孙昌武在《中国佛教文化史》论及近现代僧人作家,对苏曼殊只字不提;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将苏曼殊放置在“居士学者篇”里,都是源于其僧人身份的质疑。在笔者看来,苏曼殊既无公开声明还俗,不曾仕宦,也无娶妻生子,只是僧家本色淡薄而已,故而仍认定其僧人身份。只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谭桂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较早发现到现代佛教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的关联,虽提到苏曼殊、弘一,但着墨不多。王广西的《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是从寺院诗系的角度梳理近代僧诗的创作,指出五四思潮对近现代僧人创作的影响,却并不深入。贾国宝的《传统僧人文学近代以来的转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则是近年来以近现代僧人作家作为整体研究的专著,宏观考察中国佛教文学在近现代发展的新变与不变,折射出中国佛教文学现代转型的艰难,但也存在僧人散文创作的遗漏,除弘一、太虚外,其他高僧没有给予研究。
就现代重要僧人作家而言,个案研究远胜于整体研究,其中苏曼殊研究最火热最持久。20世纪20、30年代,当时社会上兴起一股“苏曼殊热”。柳亚子编辑出版的《苏曼殊年谱及其他》、《苏曼殊全集》,对这股热潮的兴起与推动可谓功不可没。1950年代后,苏曼殊研究在中国大陆变得更加沉寂萧疏,可是在台湾、香港及海外仍然保持了不衰的势头,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六册《苏曼殊传记资料》便集中显示了这方面的成就。1980年代后,大陆的苏曼殊研究重新复苏。首先是作品及注释的大量出版,诗歌方面有施蛰存辑录的《燕子龛诗》、刘思奋的《苏曼殊诗笺注》、马以君的《燕子龛诗笺注》;小说方面有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苏曼殊小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曼殊小说集》;小说诗文合集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苏曼殊小说诗歌集》、曾德珪的《苏曼殊诗文选注》、花城出版社的《苏曼殊文集》、东方出版社的《苏曼殊集》。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苏曼殊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这从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和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两部著作就可以看出这一变迁。其次是1990年代后,苏曼殊传记写作的日渐兴盛,如李蔚的《苏曼殊评传》、张国安的《红尘孤旅:苏曼殊传》、毛策的《苏曼殊传论》、邵盈午的《苏曼殊传》、刘诚的《情僧诗僧苏曼殊》、日本学者中薗英助的《诗僧苏曼殊》,这些传记著作或用文学的笔法,或偏重学术研究,为世人展示传主生动奇特的人生,丰富了苏曼殊的研究。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积极评价了苏曼殊及其文学创作对五四一代青年作家的现代影响。黄轶的《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苏曼殊文学论》,作为苏曼殊研究的专著,将苏曼殊的文学创作放置在现代启蒙语境中,阐释其文学创作的现代意蕴。最后是与苏曼殊相关的研究论文的刊发,更是汗牛充栋,其中陈平原的《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不能不提,它较早运用比较的眼光,揭示出五四前后的现代作家与宗教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他们的宗教情怀。苏曼殊研究不仅包括专家学者,僧人也参与其中。早在1930年代,青年学僧掀起了一股“曼殊风”,1937年《人间觉》半月刊推出“苏曼殊研究专号”,将这股“风”推到了高潮。其中学僧发表的文章主要有暮伽的《卷头致词》、大醒的《偶谈曼殊》、通一的《我对于曼殊大师的观感》、慧云的《曼殊大师生平思想之我观》、化庄的《沉在‘祸水’中的牺牲者》等,虽然夹杂批评的声音,但更多的是肯定赞赏之辞,对苏曼殊佛教戒律的松弛也抱持理解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苏曼殊的沉沦是当时恶劣的佛教环境造成的,而学僧作为当时佛教革新的新生力量,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中,故而苏曼殊的遭遇更能激起他们的心灵共鸣和普遍同情,诚所谓借幽谷之思情,抒自己之怀抱。但可惜的是,青年学僧掀起的“曼殊风”,长期隐而不彰,不为世人所知晓。
除苏曼殊外,晚清另一个著名诗僧是八指头陀。较之苏曼殊,八指头陀的研究则显得较为冷清。较早研究八指头陀的,是太虚1921年撰述的《中兴佛教寄禅安和尚传》。1932年,在八指头陀殉教二十周年之际,《海潮音》推出“纪念八指头陀专号”,其中青年学僧大醒撰述的《清代诗僧八指头陀评传》、《清代诗僧八指头陀年谱》最为突出,根据诗歌思想与情感兼具的艺术标准,对八指头陀的诗歌创作给予高度评价。1950年代后,八指头陀长期湮没无闻,直到1980年代初,才重新浮出地表。梅季点辑的《八指头陀诗文集》,是迄今为止收集八指头陀诗文作品最全面的版本,而且还收录了一些早期研究八指头陀的资料,从而促进了八指头陀的研究。钱仲联编著的《近代诗钞》,评价八指头陀诗具有爱国情怀和美好情操,进一步扩大了他的文学影响。相关研究论文,或着重分析爱国情怀,如梅季的《八指头陀的爱国诗篇》、梅季坤的《八指头陀及其爱国诗篇》、耿法的《爱国诗僧八指头陀》;或侧重诗歌艺术的阐释,如苏海洋的《八指头陀诗风初探》、萧晓阳的《释敬安诗歌的艺术:澄明之境中的诗音与诗画》、罗丽娅的硕士论文《论八指头陀的禅诗》;或揭示作诗与成佛的矛盾,如陈平原的《工诗未必高僧:关于寄禅》。
晚清至民国初期,还有两个僧人作家不能忽视,一个是笠云,有诗集《听香禅室诗集》、《东游记》,另一个则是著名佛教活动家宗仰,其作品大多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后经沈潜、唐文权精心收集,1999年整理出版为《宗仰上人集》。前者与晚清文学家王闿运交游密切,诗僧八指头陀是他的徒弟,后者结交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重要革命党人,声名显赫。前者似乎无人涉猎,宗仰研究以沈潜的《出世入世间——黄宗仰传论》为代表。
民国时期,随着佛学热的兴起与佛教宗派的发展,一批著名高僧开始涌现。他们在研佛弘法之余,也时常创作一些旧体诗和散文作品。在这些高僧中,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的研究最为突出。弘一法师出家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金梅编著的《遁入空门:李叔同为何出家》是这方面成果的集汇。传记著作最早始自林子青的《弘一法师年谱》,1960年代台湾先后出版刘心皇的《从艺术家李叔同到高僧弘一法师》、陈慧剑的《弘一大师传》两部传记,到了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弘一法师传记热,先后出版了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柯文辉的《旷世凡夫:弘一大传》、秦启明的《弘一大师新传》等十几部传记,其中,金梅版最令人称道。其作品选集有陕西师范大学的《心与禅》、《花雨满天悟禅机:李叔同的佛心禅韵》、《禅里禅外悟人生》、九州出版社的《弘一大师讲佛》、天津教育出版社的《闽南梦影》等。全集《弘一大师全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弘一法师全集》由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出版。徐承的《弘一大师佛学思想述论》是系统研究弘一法师佛学思想的专著,罗明的《澈悟的思与诗:李叔同文艺创作及文艺思想研究》,是最早以弘一文艺创作为专题研究的著作。
其他著名高僧,如太虚、圆瑛、虚云等,《太虚全书》、印顺的《太虚大师年谱》、《圆瑛文汇》、明旸的《圆瑛年谱》等出版,为研究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料准备。近年来,谭桂林的《佛性与现代性的渗透与融合——论太虚法师诗文创作中的新文化影响》和祁伟的《虚云和尚的文学创作与佛教使命》等文章的发表,表明高僧的诗文创作已引起学界的关注。
(三)五四后青年学僧作家的文学创作研究
五四以后,随着现代僧教育的发展与佛学院的兴办,青年学僧群开始崛起,成为佛教革新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学佛研佛之余,偶尔也从事一些文学写作。陈衍的《石遗室诗话续编》卷四,收录学僧大醒的若干诗作。窦树百的《清凉诗话初稿》专门辑录僧诗,包括学僧静贤、蕴光、澹云的诗作。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高振龙等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高僧与佛学名人小传》等,这些作品虽介绍了一些现代重要学僧,但无关文学研究。整体而言,民国时期,学僧的文学创作未曾真正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基本处于一片空白,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诗僧倍受青睐,高僧有所侧重,学僧则完全忽略;第二,从研究体裁来看,基本以僧诗及诗僧为主,对小说、新诗等新的文学形式没有引起关注;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基本以个案研究为主,缺少宏观整体研究,进而发现到中国现代佛教文学研究的一些“盲点”:首先是五四后学僧作家群的忽视,其次是现代佛教思潮尚未引进到现代僧人创作的研究领域。
二、中国现代佛教文学研究的展望
(一)“僧人文学”独立于“佛教文学”,成为新的文学领域
近些年来,武汉大学吴光正教授主持编写《中国宗教文学史》,他认为佛教文学是佛教徒创作的文学,强调用创作者的身份来标识*参见吴光正相关研究如,《宗教文学史:宗教徒创作的文学的历史》,《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扩大中国文学版图 建构中国佛教诗学——<中国佛教文学史>编撰刍议》,《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等。。这种思路与笔者的“僧人文学”概念是一致的。所谓“僧人文学”不是指那种以僧尼作为主要人物形象的作品,而是从创作主体的身份出发,专指僧人的文学活动及其文学作品。倘若将“僧人文学”进行拆解,发现其是由“僧”+“人”+“文学”三个部分组成的。“僧”是“僧侣”、“僧伽”的简称,强调其出家佛教徒的身份属性。“人”既说明僧侣作为出家的佛教徒,既具有佛教徒的宗教情感,也包含人类共有的情感要素,这种情感或许与佛教因素毫无关联。“文学”则强调僧尼的创作遵循文学自身的某些属性,不能完全排除文学性。这种解释既强调了创作者的僧人身份,也将纯粹的毫无文学性的佛学论文给予切割排除,内涵明确,易于理解。
“僧人文学”概念的提出,离不开诸多有利条件的支撑:第一,从创作实践来看,僧人创作不仅历史悠久,从东晋支遁、慧远开始,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年的历史,而且成就卓尔不凡,仅以著名诗僧为例,中唐有皎然,晚唐五代有贯休、齐己,宋朝有惠洪、仲殊、道潜,近代有八指头陀、苏曼殊等。正是这些诗僧的群星璀璨,提高了僧人创作的文学影响力,成为中国文学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文学群体。第二,僧人在中国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僧人作为“方外”之人,在许多方面均不同于“士农工商”等“方内”之人:他们要剃发,要离弃家室,抛弃财产,穿着袈裟,住在寺院,过着“清净梵行”即弃绝所有世俗欲望和现实利益的出家生活。他们出家后以个体修道者身份,自由组合在一起,成员间从理论上讲是平等的;所受的教育通常是以宗教教育为主,故而“无论是僧团的组织形式,还是僧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和中国传统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等级专制的社会体制是不相容的,其所体现的观念也是和中土观念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尊祖报本、‘学优则仕’等观念与追求截然相异的”[1]。正因为他们的宗教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与文人士大夫存在明显的不同,故而在文学态度、审美观念、题材选择、艺术表现等方面,均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佛教文学”不能涵盖僧人创作的全部属性。“佛教文学”,是由“佛教”与“文学”两个因素构成的。在二者关系的认识与处理上,“佛教文学”明显偏重于前者,构成二者之间的“体用”关系,即佛教是“体”,文学是“用”。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佛教文学”与其它宗教文学一样,具有或蕴含浓郁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意识。如果文学作品含有佛教的因子,宣佛的观念不强,被视为“佛教文学”就显得相当牵强。所以说,“佛教文学”具有强烈的宣教意识,它可以不注重文学的审美追求,却不能不考虑佛教思想或观念的再现。纵观僧人的文学创作,表现佛教观念的或禅悟的作品并不少,将它们归入“佛教文学”,当不会发生争议。然而有些僧人尤其是诗僧在文学创作中,超越佛门弟子的宗教身份,热衷于表现他们的入世态度、世俗情感、山居生活等,而这些文学作品则很难纳入“佛教文学”的范畴。譬如苏曼殊的诗歌、小说,基本以爱情作为抒写对象,尽管蕴含某些佛教意识和宗教色彩,却不宜视为“佛教文学”。也就是说,僧人创作有些属于“佛教文学”的范畴,有些却不属于,这为“僧人文学”的存在提供了学理的必要性。第四,现代僧人创作新门类的增添,也是关键的因素。僧人创作长久以来一直是以诗文作为主要样式,诗歌尤其为他们所钟爱。然而到了清末民初以后,一些僧人作家开始涉猎小说创作,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僧人小说”应运而生;五四后,僧人也零星地尝试白话新诗、戏剧等体裁的写作。这些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虽没有改变僧人以诗文为主导的文学创作格局,但势必突破独尊“僧诗”的研究局限,需要在“僧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其范围,“僧人文学”因而呼之欲出。“僧人文学”与“僧诗”,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拓展,因为“僧人小说”等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僧诗”就显得无法涵盖。从这个意义说,“僧人文学”的概念考虑到现代僧人创作的新变,具有现代意味。
(二)推动现代佛教思潮、民国佛教期刊与学僧创作“三位一体”研究的深入
现代佛教思潮,作为中国现代佛教文学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它的兴起与发展对现代僧人作家的创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和人间佛教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了佛教观念的入世转型,僧人创作的入世倾向和现实关注也随之增强;第二,佛教刊物的涌现,意味着现代僧人文学的创作载体发生新变;第三,民国以后,一种新的群体——学僧在僧界崛起,他们成为现代僧人作家的主体构成,他们的文学趣味、文学观念和文学影响力等方面,均与诗僧迥然不同,这是现代佛教思潮对现代僧人创作最集中的影响;第四,太虚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的失败,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现代僧人文学转型的艰难与挫折。
民国佛教期刊,作为现代佛教思潮的重要表现之一,它不仅推动了佛学研究的热潮,也成为现代僧人作家文学发表的“主阵地”和“重要途径”,影响并规约着僧人创作的文学路向和文学风貌。具体而言:佛教期刊的兴盛与寥落,某种程度上规约着现代僧人文学的发展,佛教期刊兴盛,发表僧人作品的数量也相对增加,反之,佛教期刊变得寥落,僧人作品的数量随之减少;凡与佛教无关或与佛教观念相悖的题材,佛教期刊一律不予采用,爱情文学完全杜绝;佛教期刊主要基于学佛的考量,即便发表文学作品,也是数量有限,篇幅短小;根据文学比重的不同,佛教期刊除不发表任何文学作品的纯佛学刊物外,还包括以《海潮音》为首的佛学研究为主兼顾文学的类型和以《人海灯》为代表的批评、文艺为主的类型,或者说以《海潮音》、《人海灯》为文学阵地,聚集了两大僧人作家群。
随着僧教育的重视和佛学院的创办,一种新的群体——学僧在佛教界崛起。以大醒、芝峰为代表的学僧群,一方面积极利用佛教期刊作为“化俗”“导众”的“利器”,大力鼓吹佛教革新,自觉承担救教、救僧的历史使命。在学佛、宏佛之余,他们对文学写作保持了一定的热情,开始尝试小说、新诗等文学形式的实践。正是得益于他们的小说写作,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僧人小说”出现于文学殿堂之中。就题材主旨而言,它分为佛化小说和非佛化小说;从主题叙事来看,集中表现为“诱惑”和“冲突”两种类型,其中“冲突”小说,可细分为僧俗冲突、新旧冲突、情佛冲突等情形,这类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感伤的年轻的主人公,充满浓郁的感伤情调。僧人写作的新诗,往往呈现出光明与黑暗两类意象,学僧度寰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僧人小说”与僧人新诗的出现,尽管显示出现代僧人文学创作的某种新变,但是数量与质量也差强人意,归根结底取决于学僧在现代佛教思潮影响下接受了“佛学为体,文学为用”的文学观念,在这一文学观念的制约下,文学的工具论、业余论以及不事雕琢的主张为广大学僧所秉持,导致其文学影响力远逊于诗僧。
如前所述,现代佛教思潮是现代僧人作家文学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佛教期刊的创办与学僧的崛起,都是现代佛教思潮的影响产物和具体表现,这样,现代佛教思潮、佛教期刊和学僧创作,三者构成了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故而应给予全面的综合的把握,不仅能拓展学科研究的领域,还能推动学科研究的深入。
(三)运用比较方法,深化现代重要僧人作家的研究
八指头陀、苏曼殊与弘一,作为现代僧人作家的杰出代表,一直是现代僧人文学的研究重点。对他们开展比较研究,有益于进一步梳理出现代僧人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比如,八指头陀与苏曼殊,作为晚清著名的诗僧,诗歌主情,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艺术追求。所不同的是,苏更偏重爱情题材的抒写,喜与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结交,政治态度较为激进,故而为革命型诗僧;八指头陀则更多表现为传统型诗僧,常与王闿运等名士交游唱酬,先效贾岛、孟郊,后习陶渊明,晚年摹杜甫,不仅较为清晰地呈现出自身诗歌的发展演变,也使得诗人的诗艺日臻成熟。爱国情怀的抒发,更令诗名远扬;忧教与“苦吟”的双重态度,表现诗人对佛教命运的忧虑与关切。
更突出的是,苏曼殊与弘一,他们在佛教戒律、佛学贡献、艺术创作、文学贡献等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苏曼殊僧人本色淡薄,时而“袈裟”,时而“燕尾服”,过着亦僧亦俗的生活,但爱情文学的大胆抒写与“佳人情结”的悲剧性命运的呈现,让他赢得现代僧人文学“翘楚”的桂冠,而佛学造诣甚浅。弘一法师的出家原因,是基于“佛教慰藉”的考量,是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出家后潜心律学研究,成为律学高僧,对于文学创作只是偶尔为之,尽管他本人文学素养较高。弘一法师对文学的这种态度,高度契合现代佛教思潮的趋向与需求。
(四)加强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考察
作为中国文学的部分构成之一,僧人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起着边缘的、副属的、补充的作用,它的发展始终受到占据主导地位的文人文学的严重规约。现代僧人文学也不例外。表面上看,部分现代僧人作家感知于五四新文学“大众化”的热潮,开始问津小说、白话新诗等方面的写作,但是他们往往强烈抵制或拒斥个人主义与爱情抒写,而个人主义与爱情抒写却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主题,使得现代僧人创作与五四新文学存在巨大的不合拍,旧体诗的强劲就足以显示僧人创作的惰性与滞后。总体而言,现代僧人文学与五四新文学之间显得相当隔膜,但具体到现代重要僧人作家却表现得不尽一致,如苏曼殊与五四浪漫文学渊源极深,其《断鸿零雁记》作为自传体哀情小说,对五四浪漫作家产生重大影响;弘一出家前曾参加“春柳社”《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现代话剧的表演,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之一,出家后疏离于五四新文学,只是偶尔与“白马湖作家群”保持交往。苏曼殊、弘一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现代僧人文学影响力的下降。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佛教文学或中国现代僧人文学的研究尽管不发达,整体研究、比较研究尚未启动,不少领域基本处于待开发的状态,却也意味着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在研究进程中,“佛教文学”遭遇不能涵盖僧人创作的尴尬,使得“僧人文学”的理论构建就显得很有必要。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方家的注意,推动“僧人文学”研究课题的开辟和构建。
[1]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35.
[责任编辑:郑迦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子课题“中国佛教文学史”(15ZDB069)。
贾国宝,文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现代僧人文学。
I207.99
A
1002-6924(2016)08-004-009
①“佛教文学”在这里被限定为出家佛教徒僧尼创作的文学,“现代”作为时间概念,是指从清末延续到1949年。
主持人语:宗教文学就是宗教实践(修持、弘法、济世)过程中产生的文学;中国宗教文学的研究只有聚焦于宗教实践与文体功能、宗教实践与民族精神、宗教实践与宗教诗学等层面才能深入把握宗教文学的精髓;中国宗教文学研究首先要对宗教徒的文学创作特点加以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文人创作的和宗教有关的作品。本专栏的三篇文章就是这一理念的产物。《中国现代佛教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现当代佛教文学史》的阶段性成果,对现代佛教徒文学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其焦点便是宗教实践与佛教徒文学创作;《名号、谶记、仪相、袈裟:马祖道一与8-13世纪的禅史书写》是对禅史文体功能的深入分析,这篇文章显示,禅师传记是禅师个人的历史,但更可能是禅师圆寂后宗教实践和宗教认同的产物;《别赋:人间爱别离苦的深心体悟》的精彩之处在于作者聚焦宗教思维,从而揭示出了《别赋》的佛教意蕴。《别赋》全篇没有一个佛教名相,作者许云和、饶峻妮却能从宗教实践与文学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该文“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创作风貌,可谓独具慧眼。
显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将会丰富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面相。
主持人:吴光正,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文学。
——岭南历史文化名人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