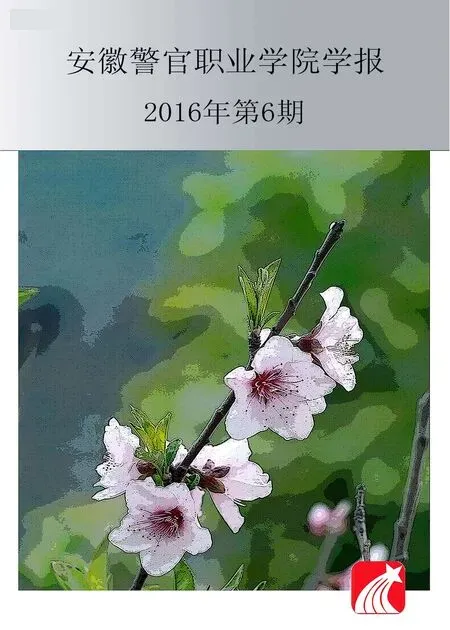论我国多重买卖规则重构之路径选择
张文胜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论我国多重买卖规则重构之路径选择
张文胜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多重买卖是民法领域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其间既交织着物权变动效力和合同履行效力的冲突,又牵涉到对物权变动规则、债权平等原则和公共政策的认知。现行多重买卖规则的研讨和立法规制均存在路径选择的逻辑错误,重构该规则在路径选择上应以维护稳定、安全交易秩序和彰显诚实信用的契约伦理观念为逻辑起点,以尊重既定法律原则和注重规则设计的整体效果为逻辑归宿,以使重构后多重买卖规则在实务中真正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
多重买卖;合同效力;所有权移转;特殊动产;交付
多重买卖之所以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杜绝,就在于买卖合同成立(生效)与所有权变动的时间差[1]及出卖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多重买卖的发生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同时出卖人在订立多重买卖合同之时对标的物享有所有权[2]又为多重买卖的发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最能调整多重买卖的法律规范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法释[2003]7号)第10条、①《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买受人以出卖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另行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交付使用,导致其无法取得房屋为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应与支持。”《合同法司法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15条②《合同法解释(二)》第15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法释[2012]7号)第9条、第10条。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普通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确认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支付价款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支付价款,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10条规定:“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些法律规范分别就不动产、普通动产和特殊动产的多重买卖进行了规制,但上述规则在理论上并未能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相反,学者们从多视角、多维度对上述规则尤其是《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条和第10条提出了较为激烈的批评。本文认为现行多重买卖规则之所以在立法上有如此大的分歧,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律规制路径选择的逻辑错误。本文试图以多重买卖规则中最有争议的多重买卖合同的效力、履行顺位以及登记与交付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效力为切入点,来探究我国多重买卖规则重构之路径选择。
一、关于多重买卖合同效力之检讨
对于多重买卖合同之效力,理论上已形成的共识有:(1)后买受人与出卖人恶意串通或违背善良之风俗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2)后买受人为善意时与出卖人所订立的合同有效,且各买卖合同之间具有平等性,各债权人均享有合同履行请求权。支持上述观点的法律依据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和《合同法解释(二)》第15条。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后买受人单纯知情是否属于“恶意串通”的范畴?
(一)关于“恶意串通”的界定
我国现行民商法律体系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恶意串通”作出明确界定。一般认为,“恶意串通”是指双方当事人为获得不正当利益合谋实施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其构成要件有二:一是双方当事人均有损害他人利益的恶意;二是双方当事人存有通谋。由于“恶意串通”纯属个人内心活动,除当事人自认外,一般很难通过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对于实务中“恶意”的判断,笔者赞同“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将对国家、集体或第三人造成损害而故意为之”[3]的认定标准;同时也认可“恶意串通”中的“恶意”宜采取“观念意义上的恶意”,即明知某种情形的存在,侧重于行为人对事实的认知。[4]对于“恶意串通”的表现形态,本文认为,除双方当事人通谋共同实施损害他人利益构成“明示的恶意串通”外,一方当事人明知对方及自己的行为均会损害他人利益,但为满足自己的私利而以默示的方式予以接受或配合,即构成“默示的恶意串通”。[5]
(二)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与出卖人订立合同的合同效力
所谓后买受人单纯知情,即指后买受人明知有先买卖合同存在或明知标的物已交付先买受人,但为满足自己的私利,真实地与出卖人订立买卖合同或办理登记的情形。对于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所订立的合同效力,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学界争议最大。在理论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第二买受人于契约订立时,纵知其标的物体已为其他买卖之标的,然基于其买卖之自由权,仍不妨碍其先于第一买受人而受交付或登记,并不因其知有第一买受人契约,而带有违法性。”[6]王泽鉴先生亦持相同的见解,认为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取得物之所有权不受前买约之影响。[7]大陆亦有学者认为,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与出卖人订立买卖合同,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8]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与出卖人订立的合同不会因背于善良风俗而无效。[9]概言之,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所订立的合同有效。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后买受人知道先买卖合同的存在,根据这种认知事实的“恶意”即可认定后买卖合同无效;[10]后买受人单纯知情时,先买受人有权以 “出卖人与后买受人的行为有违社会善良风俗(有损社会公共利益)”或“出卖人与后买受人恶意串通损害自身权益”为由主张后买卖合同无效。[11]
本文认为,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所订立的后买卖合同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2款“恶意串通”的范畴,应属无效。首先,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明知自己与出卖人订立合同或抢先办理登记的行为会导致先买卖合同不能履行、且会损害先买受人的利益而仍然为之,其主观上具有恶意;纵其不具有与出卖人共同损害先买受人利益而通谋的明示,但对于其行为会损害先买受人利益则是明知的,却依然以默示的方式予以接受,在客观上配合了出卖人违约,已构成“默示的恶意串通”[12],对于先买受人而言,这与“明示的恶意串通”并无二致。其次,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其出价与先买受人不在同一时空,缺失市场竞争的基础——公平;同时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所订立的后买卖合同其效力本身就存有疑义,与先买卖合同的效力(绝对有效)不在同一层面。因此,那种认为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与出卖人所订立合同行为属于正常市场竞争行为以及判定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所订立的合同无效有违债权平等的观点,实质上是对市场竞争行为和债权平等原则的曲解。再次,笔者认为,市场交易规则的安排,不仅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要注重考量其整体效应。我国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诚实守信不仅是个人品质的评判标准,更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社会一般观念认为,出卖人失信背义,应保护第一买受人”。[13]“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与出卖人订立后买卖合同有效”与社会一般观念相冲突,这样的制度设计势必会造成社会公众对法律适用的抵触,甚至会丧失法律的公信力;我国自改革开放尤其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传统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被“金钱至上,物质第一”的观念冲击得千疮百孔,根本无法担负起规范和制约市场主体行为的重任。此时,法律理应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规范市场秩序、重建诚信体系、维护社会公众对法治信仰的大旗,但“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与出卖人订立后买卖合同有效”的制度安排,则无异于鼓励社会公众背信弃义,这必将使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诚信体系遭致毁灭性打击。再者,诚实守信已被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而“单纯知情的后买受人与出卖人订立后买卖合同有效”的制度安排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
基于此,本文认为,对于多重买卖合同之效力,无论是普通动产、特殊动产还是不动产买卖,除后买受人为善意时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有效外,后买受人与出卖人恶意串通以及后买受人单纯知情所订立的后买卖合同均应属无效。
二、关于多重买卖合同履行规则重构之路径
对于多重买卖合同的履行规则,理论上较有影响的观点有:(1)出卖人选择权说。即由出卖人选择买受人来决定合同履行顺序;[14](2)合同成立在先说。即以多重买卖合同成立的先后来确定合同的履行顺序;(3)买受人竞价说。该说是指在数个买卖合同均有效且买受人均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时,在法院的主持下,通过竞价的方式来确定合同履行的顺序。[15]在司法解释层面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条确立普通动产多重买卖履行规则为 “受领交付——支付价款——合同成立”;第10条确立特殊动产多重买卖履行规则为 “受领交付——登记——合同成立”。但上述履行规则遭到了众多学者围剿式的批评,并要求在立法上重构多重买卖的履行规则。
首先,本文反对理论上出卖人选择说。其理由在于:第一,出卖人一物数卖本就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行为不仅有道德上可谴责性更有法律上的否定性,如果司法裁判再赋予出卖人以选择权,无异于鼓励和怂恿出卖人这种不诚信的行为,这将会极大损害交易安全;第二,赋予出卖人选择权以实现合同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经济的契约伦理观念下是无可厚非[16]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出卖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实守信本就是市场经济契约伦理观念必然要求,那种为满足自己的私利而损害他人利益和市场交易秩序的行为应被法律绝对禁止,赋予出卖人选择权严重背离了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法则,是对社会大众一般法感情的践踏,弊大于利。也正因为如此,该说已被《买卖合同司法解释》所否定。
其次,对于法释义上确立的先支付价款说本文亦不认同。理由在于,第一,该解释并未确定价款的支付标准,是全额支付还是部分支付?先支付较少价款的一方优先于后支付价款较多的一方先履行,还是合同后成立先付款的一方优先于合同先成立后付款的一方履行?该说的不确定性将会带来实践中操作上的随意性,从而导致法律适用上不统一以及权威性的丧失。第二,即使是先支付价款一方,其享有的权利依然是合同债权,与未支付价款一方所享有的合同权利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以此来确定合同履行顺序既有悖于债权平等原则,也欠缺法律上正当性和合理性。
再次,对于法释义上确立的“合同成立在先”说本文亦不赞同。第一,以“合同成立在先”来确定多重买卖合同履行顺位,有违债权平等原则。在多重买卖中,数个合同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彼此间并无对抗效力,各债权人平等地享有合同履行请求权,合同成立在先并不意味着其请求权当然在先;第二,“合同成立在先”说,虽然其意在于保护先买受人的期待利益,以维护诚实信用的市场交易规则。但问题在于当后买受人为善意时,其与出卖人订立合同并非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其所享有的合同权利与先买受人所享有的权利是平等,以“合同成立在先”来确定数个合同履行顺位实质上是剥夺了善意的后买受人之合同履行请求权。而合同履行请求权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最为重要的权利,若没有充分、足够和正当的理由是不可被限制和剥夺的,仅以 “合同成立在先”作为剥夺后买受人合同履行请求权的理由既不充分也不足够;第三,以“合同成立在先”来确定数个合同履行顺位,将会给我国既有债法制度上的诸多规则带来极大的冲击,造成难以协调的后果。如在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之前因可归责出卖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各买受人在行使合同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是否也因合同成立先后而有顺位差异?在出卖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各买受人全部债务时,债务的清偿顺序是以合同成立在先还是按比例清偿?等等。因此,以“合同成立在先”作为确定多重买卖合同履行的顺序,有弊无利。
本文赞同买受人竞价说。该说首先要承认各买受人基于各自有效的买卖合同均享有平等竞价的机会,符合债权平等和公平原则。它克服了出卖人选择说、先行支付价款说以及合同成立在先说在道德层面和法理支撑上不足的弊端,也合乎既有的法律原则。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适用买受人竞价说时,需要法官在诉讼程序上对各买受人予以释明,在各买受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诉求予以变更,以避免判非所请。
三、关于交付和登记在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中的效力
在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中,最具争议的是:登记是否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其与交付的效力如何确定?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四)项确立了“交付优先于登记”规则,但这一规则显然降低了登记的公信力,弱化当事人的登记意识,刺激出卖人一物数卖;[17]而且也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和保护善意的当事人,这当然也违反了《物权法》第24条的本意;[18]交付优先于登记的规则与《物权法》的规定和登记对抗的旨趣有所背离。[19]
对于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之物权变动规则,是法解释上的不合理,还是学者们对登记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效力的误解?笔者认为,要判研这一问题,首先应对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模式有准确认知;其次要厘清登记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效力。
从我国《物权法》第23条、第24条及其他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物权法》在物权变动模式上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①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通说有三种,一是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三是以瑞士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大多数都认为,我国《物权法》从整体上看是采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但是也存有争议。参见:刘保玉.论多重买卖的法律规制[J].法学论坛,2013(6):22-32.王轶.物权变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7.。就特殊动产而言,合同生效说仅适用于特殊动产抵押权设立的情形,如《物权法》第188条,但不适用于其所有权变动。“交付+登记”说以《物权法》第24条属于第23条“法律另有规定”范畴来否认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第23条之规定,是对第23条“法律另有规定”的误解。第23条“法律另有规定”本意是指《物权法》第25条、第188条、第189条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采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以及第27条、第28条和第29条等依事实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的情形,如同该法第9条“法律另有规定”系指该法第127条、第129条和第158条所规定的相关不动产物权变动无须登记一样,而不应是包括第24条的内容;从第24条的文义解释和逻辑解释也并不能直接得出 “登记对抗本意就包括了登记也可以作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的结论,那种认为交付必须配合登记才能导致特殊动产物权完全变动的观点,实质上是以一个自创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交付+登记)来改变动产物权变动的一般规则,有违物权法定原则之嫌。依“或交付抑或登记”说,在特殊动产多重买卖中,如果先买受人受领交付但未登记,而后买受人未受领交付但已登记,此时先、后买受人均可取得该标的物所有权,这不符合一物一权原则。
所以,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为“交付生效+登记对抗”。即交付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登记只是其对抗要件,“将登记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的规定,不是对《物权法》第23条规定的交付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主义的否定,而是对效力强弱和范围的补充。”[21]犹如机动车“登记只是机动车管理机关进行车辆管理的行政手段和措施,而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取得方式”[22]一样。
既然如此,那如何理解登记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过程中的效力?本文认为,《物权法》第24条所指称的“登记”实指已受领交付的登记,即登记应以交付为前提。因为登记是权利变更的登记,特殊动产未交付,其所有权没有发生变动,登记也就失去了对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种认为未交付但办理了登记即可推定当事人进行了默示的占有改定而进行了交付的观点,实际上是学者为了诠释登记也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公示方式而臆定出来的效力,而并非登记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应有效力。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最高法院也认为“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交付是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登记是其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在交付与登记发生冲突时,交付优先于登记。”[23]
就此,本文认为,如果出卖人就同一特殊动产与多方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如果买卖合同均有效,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的,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各买受人就合同履行顺位不能协商一致的,由人民法院通过竞价的方式确定合同履行顺位;(三)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出卖人未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仅为其办理移转登记的,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
四、结束语
与无权处分一样,多重买卖是民法领域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其间既交织着物权变动效力和合同履行效力之冲突,又牵涉到对物权变动规则和债权平等原则的认知。其理论研究在路径的选择上未能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逻辑起点,过分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尽管法释义上所确立的多重买卖规则是基于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所作出的价值考量,并且考虑到社会一般观念,[24]但在路径的选择上,却没有尊重债权平等原则,也忽视了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本文认为,在多重买卖规则重构的路径选择上,应将维护规范、有序的交易秩序和彰显诚实信用的契约伦理观念作为逻辑起点,以尊重既定的法律原则和注重制度安排的整体效果为归宿。鉴于此,在多重买卖中(无论是普通动产、不动产还是特殊动产买卖),除后买受人善意外,其与出卖人订立的后买卖合同无效;在标的物所有权未发生移转之前,各买受人均有权请求履行,先、后买受人因请求履行发生争议并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以竞价的方式确定合同履行顺序;对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交付是其生效要件,登记是其对抗要件,在交付与登记发生冲突时,交付应优先于登记。
[1]马新彦.一物二卖的救济与防范[J].法学研究,2005(2):85-95.
[2]黄茂荣.买卖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
[3]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760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2010(10):15.
[4][5][1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修订版)(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648.
[6]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36.
[7]王泽鉴.民法学说判例研究(第四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52.
[8]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69.
[9]吴一鸣.论“单纯知情”对双重买卖效力之影响——物上权利之对抗力来源[J].法律科学,2010(2):107-116.
[10]翟春雪,翟云岭.论所有权保留中出卖人的一物数卖行为[J].法学杂志,2010(8):142-144.
[11]石冠彬,江海.论一物数卖合同效力与买受人权利救济[J].法律科学,2014(5):150-159.
[13]许德风.不动产一物二卖问题研究[J].法学研究,2012(3):87-104.
[14][16]孙毅.我国多重买卖规则的检讨与重构[J].法学家,2014(6):114-132.
[15]刘保玉.论多重买卖的法律规制[J].法学论坛,2013(6):22-32.
[17]王利明.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J].法学论坛,2013(6):5-10
[18][20]程啸.论动产多重买卖中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评最高人民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9、10条[J].清华法学,2012(6):61—70.
[19]刘保玉.论多重买卖的法律规制[J].法学论坛,2013(6):22-32.
[21]崔建远.再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J].法学家,2010(5):49-55.
[22]韩玉善.关于我国机动车所有权制度的几点看法[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7(5):61-64.
[23][24]奚小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175,157.
Choice of Way to Reconstruct Multi-buy-and-sale Rules in China
Zhang Wensheng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Hefei Anhui 230031)
Multi-buy-and-sale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problems in civil law field,during which is mixed with the effectiveness conflict between the real right change and the contract fulfillment,and involves the cognition of the change rules of real right and creditor's rights,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the public policy.Discussion of current multi-buy-and-sale rules and the legislative regulation shows that they all have logic mistakes.To reconstruct the rule,the path selection should maintain stable and secure transaction order,reveal the honest credit contract ethics,respect the established legal principle,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design rules in the hope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can really stop the dispute in practice.
multi-buy-and-sale;validity of contract;transfer of ownership;special personal property;pay
DF418
A
1671-5101(2016)06-0007-05
(责任编辑:唐世业)
2016-09-23
张文胜(1966-),男,安徽太湖人,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