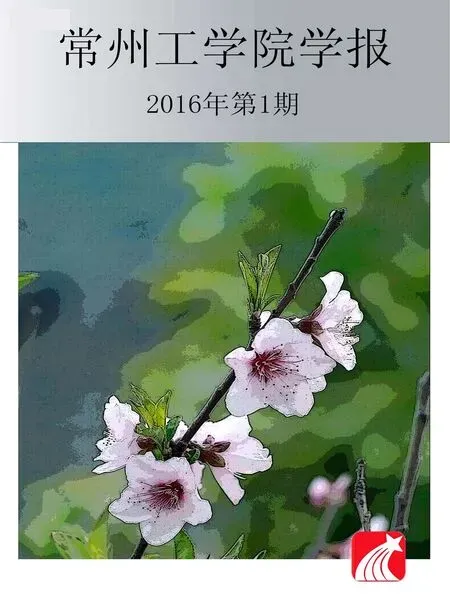论当代电视纪录片叙事的美学策略
方忠平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论当代电视纪录片叙事的美学策略
方忠平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摘要:当代电视纪录片的生产立足于文化消费和审美期待立场,尝试将纪实美学和戏剧美学相互渗透,促成了纪录片叙事策略朝向后现代美学新风的转身。电视纪实娱乐叙事的奇观化策略,凸显影像或场面的视觉奇观及其快感的最大化;电视纪实叙事的碎片化则强调剪辑加工的碎片式的组接链条,构建立体叙事空间,强化纪实叙事的美学体验;电视纪实叙事的工艺化色彩采取技术理性向艺术表现的渗透的工艺美学标准所产生的陌生化视角,拓展纪实画面的视觉张力,造就纪录片画面内在力度和力量缔结成而成的纪录片影像的非凡气质。
关键词:纪实娱乐;叙事策略;奇观;技术美学
新世纪以来,将“纪实娱乐”奉为圭臬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创作正在掀起纪录片商业化乃至产业化发展的国际潮流:从非洲热带草原狮群家族里的舐犊之情到亚洲高原的雄鹰家庭幼子间的猎杀之险,从古埃及金字塔埋藏千年的历史悬案到中国故宫穿越时空的东方传奇,跨越国际的纪录片生产流程和叙事模式,正在改变纪录片以追求真实记录和对社会进行富于思辨性创造性处理、以小众化和高端阶层消费传播的尴尬境地,进入大众审美文化消费的视野。实际上,以Discovery Channel、国家地理频道、历史频道、英国 BBC 以及央视纪录频道等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商业纪录片制作机构大量摄制“娱乐化”的纪录片,已然打破了传统的樊篱,在参阅当代文化消费的时代需求和观众的审美期待视野的基础上,尝试纪实美学和戏剧美学的相互渗透,改变纪实叙事的基本策略,使纪录片美学呈现整体性的后现代美学新风的转身:无论是纪录片呈现的内容奇观,或是剪辑加工的碎片式的组接链条,还是场景细节技术运用的创新和工艺标准,纪实娱乐创造的影像奇观,正在启发人们重新感知影像纪实叙事的本质。
一、奇观:纪实叙事向影像本体的回归
借助于奇观电影的叙事策略和制作流程,电视纪录片以奇观巨制来充分展示纪实影像特有的艺术魅力,从而诞生了诸多纪实娱乐的系列作品:《永远的丝路》让神秘的敦煌勾起了人们对于中国沙漠腹地的无穷想象;《复活的军团》让埋藏地下的古代兵俑穿越时光隧道向人们揭示悬念后的答案;《故宫》让一座静止的古代皇宫殿堂跨越时空向人们展示出精致唯美建筑背后的权力、尊荣的转换和更迭的哲学意蕴;《舌尖上的中国》让平凡的一日三餐的中国食品幻化出蔚为壮观的饮食传奇以及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感知、体味乃至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电视纪实镜头通过“丝路”“军团”“故宫”“舌尖”(美食)等奇观化的影像符号,用画面张力所具备的震撼力,刺激人们的审美感官、激起观众集体无意识的审美感动。当代中国纪录片正是运用奇观化的叙事方式实践纪实娱乐的审美动机。
电视纪录片的奇观化源自电影工业对于非凡的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或是数字手段创作出来的奇幻影像的美学追求。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将电影的奇观特性描述为:奇特影像的狂欢,并认为奇观是电影真正实现了他自身的纯粹视觉的艺术本体。奇观电影的叙事模式充分运用数字时代的影像技术,完全改变了电影史上克拉考尔的“物质复原论”、巴赞的“摄影本体论”对于电影影像的认知。奇观电影超越了镜头再现客观对象的叙事理念,运用摄像技术的优势和特征,实现从“物质世界的还原”转向了比现实还要真实的场景和人物。奇观电影虚拟的形象虽然并不实际存在,但是却非常符合人们的视觉逻辑,重要的是奇观电影引发的视听感受,比现实更加纯净、集中,从而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和诱惑力。奇观电影产生和流行更深层的原因无疑与当代科技、文化、媒介、消费等所谓后现代文化因子的交互作用导致的社会文化的视觉化和图像化的整体性转向是分不开的。“奇观”词源学的内涵指的是人类日常生活经验中罕见的视觉景象,甚至包含一切满足人类好奇心和欲望的视觉和听觉体验。奇观的存在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旅程,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和希腊的神殿庙宇,还是秦朝的兵马俑和万里长城等,这些古今中外既已存在的奇观的实例,受局限于实际建造的层面,只有站在这些奇观面前,我们方能感受到场面的宏大和雄伟的气魄,体验到来自远古的巨大冲击力,或者说在前影像技术时代,人类不仅制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奇观景象,更使奇观保留为一种视觉经验成为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透过古代奇观的审视,不难发现大量的奇观背后,奇观的设计者或制作者总是以文化、宗教、信仰、政治、经济方式影响人们,奇观并非单纯的艺术活动,之所以产生美学经验上的体悟和感知,是由于奇观背后所指代和隐喻的某种权利或人物的合法性、威严性和神秘感。随着影像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奇观则早已从物理存在通过媒介的传播扩展到了影像、虚拟画面领域。但与以往最为不同的是,所有这些奇观,进行媒介化的组织传播,成就了世界奇观之所以为奇观的事实。奇观化除了影像的画面语言冲击力之外,还包括了电影的系统性活动,即电影制作、生产和营销的整体性策略,这是电影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奇观化展现,更多的是从叙事学的角度去链接观众、文本之间的亲密关系进而实现影像传播的有效的途径。也因此,我们才将现在所处的时代,称为“奇观时代”,将展现奇观的媒介现象,称为“媒介奇观”。也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媒介奇观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1]。这些奇观元素的本质,绝大多数就是将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电视纪实娱乐叙事以数字特效为代表的奇观元素,既与故事文本相连,又有其特殊的视听冲击力,“追求影像或场面的视觉奇观及其快感的最大化。这就意味着一个重要的变化,亦即画面的组接更加倾向于表层的、直接的视觉快感,而非内在的、深度的叙事逻辑关系,这就造成了奇观对叙事的解构。为了奇观效果,蒙太奇可以不顾叙事本身的要求,甚至打断叙事的连续性和逻辑关系,凸现出奇观的视觉性”[2]。电视纪录片奇观化叙事与奇观电影不同的是电视纪录片处理的题材是真实的历史留存或事件而非虚构的情节和个性独特的人物性格;电视纪录片播放时间是断续的而非连续的集中时间;电视纪录片观看的氛围是明亮的开放的家庭空间而非黑暗包裹下的白日梦境。因此,电视纪录片的奇观化叙事以探索揭秘为切入点,以历史人物、自然奇迹和动物故事等为表现对象,强调画面造型艺术效果,运用电脑特效、情景再现等元素丰富叙事手段,但一切都建立在客观史实和真实自然基础上。甚至为了表现构建真实的思想形态和意识,人们不仅借助剧情片大师采用的叙事方法还原事件的意义,甚至还不惜完全以拍剧情片的规则和标准拍摄纪录片。电视奇观化的叙事策略符合当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它满足了大众文化影响下电视观众的追新求异的审美需要,能够规避一些因为大众文化而带来的诸如泛娱乐化的弊端,是当今社会文化体系下观众收视的强大动力。
二、碎片:场景段落碎片构建立体叙事空间
从自然主义创作理念引导下的长镜头叙事,到戏剧美学的故事化展现的蒙太奇镜头叙事,当代纪录片创作不仅在尝试打破所谓生活真实的禁区红线,引入情景再现以及数字虚拟艺术等表现手法,丰富纪录片的叙事语言,还在尝试打破传统叙事的完整性,再造心理现实空间,以碎片化的叙事手法,构建立体叙事空间,给观众带来全新的美学体验。如果说纪录片的奇观化产生强烈的视听效果激发受众的求知欲,侧重于内容选择,那么,碎片化的结构方式和方法,则是将受众的心理积极调动起来,主动建构叙事空间,满足当代观众的心理欲求而采取的美学策略。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采取了有别于此前的纪录片叙事方式,令观众耳目一新,《时节》一集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方式,一个接着一个场面经常被人为地切断和阻隔,叙事时间被压缩、叙事空间大幅度的转换和跨越、事件细节被有意识地放大和展示,叙事节奏在快切中迎合了人们的心理节奏。奇观化的视觉场景和画面传达的信息甚至情感,在观众的疑惑并启动联想后仿佛完成了拼图游戏对中断事件的重新组合,观众在还原事件的前后连接中,其心理被纳入整个纪录片的叙事结构中,所获得的观赏快感新颖而又奇特。《舌尖上的中国·时节》碎片化的叙事将江西贑州上堡乡农户的劳作、时令更替与饮食美味的关系主线切分成三个片段:主人公顺应季节更迭按农事经验安排先后顺序,春季里制作美食——米糕过程,乡间习俗满月酒为沈家新一代祈福。人为阻断所填充的是时空跨越幅度极大的习俗、人物故事、细节甚至知识,从鄱阳湖边到台湾兰屿,从北京房山到新疆吐鲁番再到安徽陶辛镇空间地理的转换,或根据同季节的对比参照,或根据自然气候的关联,或根据美味的四季积累,香椿菜、螺丝菜、手抓饭、虾仔小刀面等普通美食千姿百态,蔚为壮观。在隔断的主线段落中楔入的第二层人物故事同样也被人为阻断,形成第三层次的碎片切分和组合。在整个段落结束之际,似乎有些随凌乱的人物故事、美食的发现和制作乃至对饮食的质朴的理解,观众在释然中完成整段影像拼接。这种碎片化的叙事与传统的线性叙事不同,它企图通过人们对季节的感受和对人物故事的好奇,增加画面信息量,在立体的叙事空间中充分发挥观众的想象力。
纪录片碎片化的叙事,似乎就是传统蒙太奇的表现形式的交叉叙事,实际上其美学的内蕴迥异于蒙太奇的画面组接手法。传统蒙太奇叙事像是将各个独立的没有多少逻辑关系的建筑材料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座完整的适合人们居住的“房屋”,“房屋”的组装则是按照一定的结构顺序进行,建筑完成后的整体结构的功能和意义并非单个的建筑材料的简单累积。影视的蒙太奇意义和作用就是将场景和画幅有效地组接起来,并通过这些画幅的连接形式,诸如平行叙事、交叉叙事、对比叙事等产生影片预期的艺术效果。传统蒙太奇画面组接的形式是:“一个镜头和一个镜头组合,就构成了镜头组,表达一个较为复杂的含义;镜头组和镜头组组合成为一个镜头句,表达一个完整独立的含义;镜头句组合成为镜头群,镜头群再进一步组合成为镜头段,完成一次较为完整的叙述。”[3]传统蒙太奇手法通过画面和场景完整的银幕造型衍生意义,但贯穿于画面和场景后的结构却始终是完整和精致的。
纪录片碎片化叙事,与传统蒙太奇相反:在一个完整的叙事场景中,往往插入镜头组形成的影视句子,人为阻断叙事场景链,原有的叙事场景的完整性被打乱,碎片式的新段落故而随即呈现,观众的疑虑和兴趣也随即产生。影视作品的碎片化叙事策略的运用汲取了当代文化视觉化转型过程中,人们对影视作品的认知和解读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更与当代观众生活的文化背景碎片化的感受密切相关。当代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的急遽变化,促使流行文化以游戏、狂欢的方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产生后现代式的碎片感受。影像叙事伴随着高科技的强力介入,扭曲、变形的画面,甚至虚拟的画面,产生新的碎片化影像,正是在迎合审美快感的内在需求过程中,使影像叙事变成了一种模糊了指涉对象的碎片化手段。这种碎片化的特征在当代文化学者杰姆逊看来,是“拉康认为在精神分裂中,‘能指’和‘所指’间的一切关系,比喻性的或转喻性的都消失了,而且表意链(能指与所指)完全崩溃了,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能指’。这是探讨精神分裂的现时感觉的一种方法,即将这一现时看成是破碎的、零散化的能指系列”[4]。杰姆逊所说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切关系消失,留下的只能是一连串破碎的能指,这种碎片成为一种新的结构形式时,其间断性、不确定性、跳跃性将真实与虚幻,当下与过去混合在一起。在当代审美文化消费背景下,一种碎片式的、不完整的建构或叙事往往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碎片化的处理方式容易将一件完整的东西分解开来,观众轻松地玩一个拼图游戏,将原先的场景和故事分成若干个破碎的小段落,让观众随着故事的延续,通过自己的记忆碎片,不断地擦除、填充、编辑、排序和组合,还原故事的完整性,获得新鲜而独特的美学趣味。这种趣味来自碎片影像流的间断性和非连续性。纪录片碎片化叙事策略就是在跳跃的、不和谐的并置的画面组合中,完成结构巧妙的时空拼接游戏,制造立体的艺术时空。
三、工艺:技术理性向纪实艺术的渗透
在纪实娱乐的制作理念影响下,当代电视纪录片的生产不但创造了纪录片商业化的观影奇观,更提升了纪录片作为电视传播和消费品种的文化品质,构成大量的影像符号奇观的强大艺术感染力的恰恰是隐藏其后的影视技术注入的创新动力。为了使普通的纪实长镜头呈现出精致华丽、稳定悠长的美学效果,STEDYCAM的使用早已成了纪实叙事不可或缺的角色;MotionCap-ture动态捕捉技术,能准确捕捉运动轨迹,从而将运动物体的运动状况以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来,经过计算机图像数据处理,由摄像机记录下的数据将演员的动作转化为一系列的3D影像技术,使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大放异彩;高清拍摄、超高清拍摄、水下摄像、高空航拍、微观摄影、升格、降格、微距等各类新技术,高难度创新拍摄综合手段的运用,使电视纪实叙事表现出少有的奇观色彩。影视艺术起源于工业技术,影视艺术成熟得益于技术美学的参与和表现,当代纪实娱乐的纪录片生产从保证纪录片画面精美的视听品质起步到丰富高超的制作技术实现的工艺标准,使纪录片的优势和表现模式,逐渐成为生产过程中普遍遵循的原则,并且随着更新技术的发明和扩散,其技术美学的运用俨然凸显出精致的工艺化色彩和标准。
当代电视纪实美学的工艺化色彩追求,集中体现为造型元素技术品质和画面质感的呼应和提升。高质量的定、变焦镜头,T值恒定,高清、超高清的RAW记录格式,宽色域S-gamut色彩还原和创意,高宽容度工艺技术实现纪录片构图的处理、光线的运用、视角的变化,去发掘历史、现实的美感和诗意,抛弃传统纪实镜头的摇晃、粗糙跟拍镜头中的原始自然主义,克服原生态理念、真实性误导带来的叙事节奏的拖沓、信息贫乏和纪录片叙事固有模式的单一,寻找技术美学产生的陌生化视角,创造新的画面时空,拓展纪实画面的视觉张力,进而造就画面内在力度和力量缔结而形成的纪录片影像的气质。正因为此,纪录片的工艺化色彩和标准实质上体现了数字时代背景下技术逻辑推动的纪录片艺术形式的合法性身份和存在的探索。考察现代艺术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各类艺术似乎在艰难地寻找自身合法性的存在事实,而传统的影视艺术正是借助当代文化形态转型的机遇,逐渐摆脱以语言为中心的传统束缚,以追求影像景观或奇观艺术实践来回应理论的质询,影视技术装置的发展为影视艺术之所以称为艺术的发展增加了技术美学的注解。新的物质手段的不断涌现,影视艺术也在不断延展自身的叙事空间,新的数字多媒体技术出现,更使以真实性为前提的纪实娱乐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了新鲜有趣的艺术表达形式。技术逻辑和技术理性在向纪实艺术渗透的过程中实现了以创作者为中心的辐射模式置换为以观众为中心的消费—生产模式,从而激发观影者的创造性和参与性,并为力比多提供了适当的释放形式,投合了大众的审美意象。技术美学的充分运用使纪录片的画面思维既包含感性思维特点,也包含理性思维的特色。事实上,技术逻辑对应的是理性色彩,而其产生的陌生化的视角和具象对应的是形象思维的特色,因此,这种叙事中的概念、判断、推理、结论,合理而严密。更为重要的是超越模拟技术时代人们想象力的羁绊,突破想象力的固有模式,开发想象力的内在潜能。技术美学已不单单是想象力实现的工具理性,技术美学已然承担了纪实叙事中或描述、或揭示、或创造的功能。从当代文化发展的特点来说,技术美学满足的正是人类社会在远离写真时代,跨越仿真时代,进入造真时代,人类整体的审美经验范式由审美静观迁移到审美震惊的审美需求,
正如本雅明反思现代社会的机械复制艺术的特质时指出:“面对画布,观赏者就沉浸在他的联想活动中;而面对电影银幕,观赏者却不会沉浸于他的联想中。观赏者很难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索,当他意欲进行思索时,银幕画面就已变掉了。电影银幕的画面既不能像一幅画那样,也不能像有些现实事物那样固定住。……基于此,就产生了电影的惊颤效果。”[5]凭借技术美学,纪实叙事将一个以平常眼光无法看到的世界发现出来,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产生的震颤心理体验是当代审美活动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纪录片工艺化追求使影像的假定性美学乃至纪录片的艺术观念问题在当代凸显出来,问题是数字技术在电影的制作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由数字工艺和数字技术突破物质现实的制约,它不仅能够还原记录镜头下的现实世界,还可以创造出人们的想象力可以达到的境界。纪录片的工艺化追求扩大了影视艺术的表现空间,使电视纪录片假定性的美学内涵实现了极大程度的扩张。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
[2]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4.
[3]李稚田.影视语言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0.
[4]弗·杰姆逊.后现代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35.
[5]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60.
责任编辑:庄亚华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1-0044-04
作者简介:方忠平(1963—),男,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5-06-30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