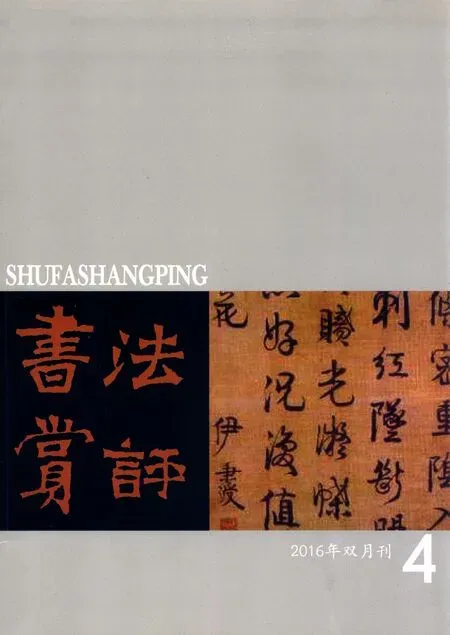两汉简牍书法及对现当代书法研究与创作的影响
■董文强
两汉简牍书法及对现当代书法研究与创作的影响
■董文强
简牍是中国古代用竹、木制成的书写材料,流行于东周至魏晋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是纸张没有大量出现之前最主要的书写材料。[1]二十世纪以来,简牍的出土数量巨大,内容十分丰富。成千上万枚的出土简牍已不罕见,从体裁形式看包括遣策、边塞遗址的屯戍文书、诏书律令、兵书、医术、历谱、辞赋、契约、账册、各种书籍抄件等,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民俗、文化等很多方面。根据汉简的不同用途和形式,可以分为简、牍、觚、检、楬、签、符、削衣等形制,书体包括篆、隶、分、真、行、草等。
一、西汉简牍书法及其特征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简牍不断被发现,可以说二十世纪是简牍学的世纪,简牍学已成为国际显学。在已出土的简牍中,汉简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研究汉简成了简牍学研究的主流。这些简牍除了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外,还是最为直观的书法墨迹,不仅是书法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书法创作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在简牍没有出土之前,人们对汉代书法艺术的研究都是通过碑刻、摩崖、瓦当等铭刻文字来认识的,由于无法见到汉代的墨书真迹,在认识上也有许多的偏差和局限性。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2]这是因未见西汉简牍,只见到传世的东汉碑刻而得出的结论。随着汉简的大量面世,此种观点在今天来看是不正确的。大量汉简的出土清晰地展现了古隶向八分演进的形态。因此汉简的发现对书法史研究的意义可见一斑。
出土的数万枚汉简,是两汉各个时期留下的墨书原迹,大多能确定其年代,其中以西汉的占绝大多数。这些简牍大多出自西北地区和内地各省,内容包括失传的经书古籍,汉代的律令条文,各级政府与军队的文书账册档案乃至汉代辞赋文学等多方面。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献研究价值,是研究汉代历史、经济、民俗及古文字等不可替代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汉代字体,以及汉代地域书风最直接的资料,尤其是西北地区(主要是甘肃地区)汉代书风的真实再现。大量汉简主要出土在西北地区,以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最为典型,简牍能够大量的保存必然与西北地区独特的气候环境有直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这些地区在汉代时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已出土的属于西汉时期的简牍代表性的有尹湾汉简、马王堆竹简、定县竹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和武威汉简等。从这些简牍的风格特征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古隶迅速发展,由篆而隶走向了成熟的分书。
尹湾汉简1993年2月出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汉墓,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元延二年日记、刑德行时、神乌赋、行道吉凶、东海郡吏员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薄、赠钱名籍、博局占、元延三年历谱等。在书法艺术方面,其中《神乌赋》最具特色,赋文标题字体扁方、波磔分明,正文部分用草书写就,运笔细健圆转,行云流水,神采飞扬又凝重古朴。共650余字,是十分罕见的章草精品,从神乌赋可以看出最迟在西汉末期章草已经出现并成熟。
张家山汉简,1983年到1984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简一千余枚,约四万字。其中有西汉早期律令和早已失佚的一批医书、兵书、算数书、历谱等。书体直承奉制、深厚凝重、气韵生动,有些简书写快利果断、节奏感强烈、结体变化自然、线条凝重、点画振迅果断。如律令简书写老练,字形趋扁,布局疏朗,用笔散逸自然,线条活泼,时见变化,其挑法已为分书挑法的雏形。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竹简共九百余枚,其年代在文帝时期(前179年—前157年)。从字形和笔法来分析,许多写法与篆书接近。横画排列整齐,落笔逆锋顿按,运行时逐渐上提,收笔不回锋,有些笔画略有蚕头燕尾的波磔,与出土的战国简牍帛书墨迹普遍接近。[3]其中以78枚遣策为其代表,字形纵长,笔势流动。从这些竹简的字体特征来看,西汉初期的古隶是从秦篆和六国文字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各种文字的痕迹,字体还未发展成熟,对于研究西汉早期古隶向分书演变的轨迹,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
银雀山汉简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共出竹简约4900多枚。一号墓出土4942枚竹简,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及其他佚书。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天光元年历谱》。其中如《孙膑兵法》,共计简440枚,达万余字,其书体为尚无波势但强调磔笔和线条的凝朴与变化的古隶,形态大小不一。由于抄写间断进行,故而用笔、精神、风格以至构形亦不统一。布白疏密随意而无规律,结体右边普遍稍耸,呈右上斜取势,笔力稳健,气韵生动。特别是少量结字的部分连带笔画始见行隶之意,已蕴章草萌发意态。
定县竹简1973年出土于河北定县八角廊村汉墓。定县竹简为西汉末作品,内容包括论语、儒家者言、保傅传、哀公向正义、太公等古书的部分抄本。其中儒家者言所展示的分书样式,与同期简册分书相比是超前的。其用笔逆入平出,主笔皆蚕头燕尾,波磔明显,结体谨严、法度备尽、重心安稳,笔画近乎程式化分书的特征,特别是撇捺的运作态势和字形,和东汉乙瑛碑、张景碑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西汉中晚期隶书已经完全成熟。
居延汉简指在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和甘肃酒泉金塔县破城子地区发现的简牍。居延汉简数量庞杂,古隶、篆、分、真、行、草书体种类无所不有。西汉时期的居延简,与同时代其他简牍的书体大致相同,结体和用笔尚存篆意。而以西汉中期的武、昭、宣时期的简书为多,且变化大、发展快。居延汉简的书写者为守边的中下层军吏和士卒,其丰富的艺术性展示出了汉代书法艺术普及的广度与深度。
敦煌汉简指20世纪出土于甘肃河西走廊敦煌市、酒泉市、玉门市等辖区内的简牍。这一地区在汉代属敦煌郡治范围,出土简牍数量巨大,纪年最早的是武帝天汉三年简(公元前98年),最晚的是东汉顺帝永和二年简(公元137年),重要的有武帝临终遗诏木觚、酥油土木简和悬泉置汉简等。武帝临终遗诏木觚结字横扁,用笔渐向方折,波挑分明,反映出到西汉中期分书已完全成熟。悬泉置汉简无论从数量还是内涵方面都非常具有代表性,20世纪90年代出土自甘肃河西走廊悬泉置遗址。共出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最早纪年简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简牍内容能够反映这两百余年的有关史实。[4]悬泉置遗址所出汉简隶、草、真、行、分诸体皆备,书法风格各具特色,从中可以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能够清晰地展现出从西汉至东汉书体演变的全过程。敦煌汉简其中分书有可以和曹全碑、史晨碑媲美之作,而草书数量最多,也是其精华部分,书体宽绰,用笔婉转自如,奔放流畅有连绵之势,开辟了后世狂草的意蕴和体势。
武威汉简主要有,王杖十简、“王杖诏书令”木简、仪礼简和一批医药简牍。其中大多墨迹如初,字形不拘一格,长方、扁方、正方均有。其中仪礼简,字体典型的代表了西汉向东汉过渡的分书,其用笔率意天真、笔势流畅、逆入平出、古雅端庄,完全具备了成熟汉隶的风格特征,是汉代精写的经书。[5]医药简为简书中的佳作,是隶书规范化的先导,纵横奔放、粗犷率真的特征展现了西北地域文化的质朴风格。
二、东汉简牍书法及其特征
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有一大部分是新莽时期和东汉初期的,东汉中后期的简牍出土数量甚少。新莽和东汉初期的简牍书法承袭了西汉后期的书风。总体来说,东汉时期的简牍书法从书体上来说,往往分中有行,分杂章草。如居延汉简中的劾侯长王褒状、劾王长状等,从用笔及线条上来说,多以率意为之,且波磔舒张、线条奔放,极大地表现出一种朴拙率意的自由精神。[6]其中以东汉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最具代表性。从书风特色看,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书体各样、风格各具,个性化的风格展露无遗,此简牍书法,一简一风格,对我们今天的书法学习与继承、创作与展览等有很大的启发。下面简单介绍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法艺术:
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20世纪70年代出土自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共36枚木简,记载了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甲渠侯粟君雇佣寇恩卖鱼,后双方发生纠纷,由此而发生的一系列诉讼。简册内容包括爰书、都乡啬夫报告和居延县所下文书,是目前为止在出土文献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份东汉法律文书,为研究汉代司法诉讼制度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从书法风格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一简两行,字体较为规整,用笔尖锋直入,一波三折,线条飘逸流畅、洒脱跌宕、动感性十足,结字宽博舒张,比起以往大多横扁隶书的特征,结字大体呈长方形状,从整个简书布局特征来看,飘逸洒脱又不失气势,字里行间透露出汉代人大气磅礴的审美品格;另一类一简一行,字迹较为草化,用笔十分率意,率意之中又不失严谨,线条浑厚,结字随意、十分自然。
东汉简书代表性的还有甘谷汉简和长沙五一广场简。
甘谷汉简于1971年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渭阳乡出土,内容为汉阳郡转发的诏书律令及敕命文书,可分为奏章批诏、中央下发行文、凉州刺史行文及汉阳太守行文等。其中的桓帝延熹元年至二年(公元158—159)的23枚木简,是宗正府卿刘柜所上给皇帝的诏书,大多在末尾署上属、掾,或令史、书佐之名。这些木简的书写者,自然就是当时的令史、书佐一类人。纵观甘谷简书,字的主笔画伸展很长,尤其是横画主笔,一波三折、变化多端,构字扁平匀称、中心紧密,刚健奔放而不草率。有意夸张撇捺,用笔最具特色,刚柔相济、奔放自如,线条放纵飘逸、摇曳多姿,章法参差多变,随意而置。其结体和用笔与《史晨碑》和《曹全碑》有十分相近之处,应是东汉中后期官方文书的典型书体,和碑刻书法相比,可以直观地感受汉人书写的状态。
长沙五一广场简,二〇一〇年六月在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广场发现了一批东汉简牍。总数预计在七千至一万枚,简牍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其中大多是当时使用的公文。主要是下行文及上行文,亦见少量平行文及用于封缄文书的封检及函封、标识文书内容的楬等。也有部分名籍及私人信函。这批简牍形制规整,书体相对端正,隶书居多、结构平正、波挑分明,因大多是官文书,草体较少,有一些字迹趋于楷化写法,部分草书主要见于名籍及批示文字,结构也相对周正,略带隶势,用笔流畅。[7]其中比较端正的隶书简牍,可以说是东汉中期隶书墨迹的标杆之作。对于研究东汉隶书在官方文书中实际运用的情形,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除了上述的几种代表性简牍外,东汉时期有种大扁书现已没有实物可见,而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中有一些写在检、觚、牍上的字较大,如《居延新简》其中之一简“诏书”二字,由于字大而笔画较粗,最大特点是横画粗而竖画细,笔画斩折处多方折,字显得较扁薄,墨气沉重,别有意趣。以现在视角审视,具有典型美术字的特征,可以看出书写者有意通过对比来强化字体美的特征。清代金农自创的漆书隶书风格特征上与此简的风格极为相似。虽未肯定金农是否见过此类简书,但通过比较至少可以说明:虽间隔一千七百年左右,后人和古人在书法艺术美的追求上有相通之处。
根据对出土汉简字体风格的比较,东汉和西汉相比简牍中的草书比例明显地增加了,草法也更为成熟。当时章草书体作品浩繁,风格多样,如居延汉简《误死马驹册》是章草书法的典型,它已经发展成为章草完全成熟且技法熟练的代表作品。今草以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为典型,此册是东汉简书名作之一,从书体发展史的角度看,此作是隶草向规范的章草突变的标志。[8]它以介于今、章、行、分以至楷书之间,又以今草为主流特征的形态,展现了一种自由书写带来的美感。从大处着眼,不计较局部细节特征,字字独立而行气联贯,自然飞动而沉着痛快,真实地表现出今草形成阶段的基本风貌。
三、汉简书法对现当代书法研究与创作的影响
汉简书法是研究汉代书法最为直观的第一手资料,汉简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个性化书风,对我们研究字体书风的发展流变,对当代书法史的研究和书法创作意义非同寻常。20世纪大量汉简的出土,给书法研究者以新的认识,除了汉碑,还存在着一个真实的墨书世界,而这些简牍墨书无论从史料价值还是艺术价值来说,可以和汉碑平分秋色。简牍墨书能更加直观地感受汉代人的书写状态,为研究中国书法书体的渊源流变,提供了实物资料。通过简书墨迹可洞悉汉人的运笔及隶书的真谛,可使我们更加接近两千多年前汉人的笔法、气度与神韵,真实地感受汉代先民书法的风采。从总体来说汉代简牍书法笔法灵动自然、纵横恣肆、方笔圆笔兼而有之,毫无矫揉造作之态,结体丰富多姿,有着天真烂漫、活泼动人的情趣。雄强夸张的笔势,简捷率意、变化多端的章法,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形式感和表现力,充盈着一种动人的大自由精神。简牍的大量出土,让我们认识到“简牍墨迹的书写在汉代甚至战国到魏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比石刻碑版更普及更常见的‘书法史’现象”。[9]
已出土的汉代简牍,从书体上来说,各体咸备是简牍书法鲜明的艺术特色。除少量的小篆、古隶外,还有绝大多数是书体界限并不绝对分明的过渡性书体,这种过渡性的简牍书体真实地再现了汉代书体孕育、变革和发展的过程,这为魏晋时期书法的发展和流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简的书写者大多是社会下层的职业抄书人或中下层士吏,这类书作者比达官显贵少了许多内心的约束和程式化的规范,自由随意,甚至可以漫不经心,所写简书不矫揉造作,以自然为之,其中自由奔放的用笔、富于变化的结体、不加修饰的意趣,不拘形迹的激情,正是汉代人崇尚的大道至简、天人合一等精神的外在显现。相对官方文书、庙堂书法来说这类民间书法虽不很严谨规范,但其中自由奔放的用笔、富于变化的结体、不加修饰的意趣,不拘形迹的激情,与所谓的正统书法、“庙堂书法”一样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强盛的生命力。
简牍书法呈现出动人心魄的自然之美,其笔法和结字处处体现自然天成之趣,笔法活泼灵动、墨法浑洒流畅、布白错落变化。汉简书法的古朴自然、匠心独运、天真烂漫,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创作和研究领域,尤其是对当代书法创作取法与启迪意义重大。著名书法家刘正成在《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回顾》中评价道:“汉简古隶与甲骨文融入书法创作,是二十世纪书法的最大特征。”“由是观之,二王书风、碑学书风、简牍书风,作为书法创作的三大源流,可以说是三分天下,各有其一了。换句话说,由于甲骨文,汉晋简牍的发现,也即我所称的本世纪考古学的大发现。拓展了书法‘传统’的领域。”[10]简牍的发现拓展了我们对传统的新认识,丰富了今天我们书法取法的路径,对当代乃至将来书法创作的影响不可估量。但反观当代我们对简牍书法的学习,其灵动与朴拙的自然流露是今天“展览体”所缺少的。当代书家虽有直接取法简牍书法而有成就者,然而取其形易而洞悉其气息难,我们应当把握历史时代的精神,将汉简的学习放置在汉代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中审视,通过简牍书法的学习与创作,继承汉代优秀的文化传统,让汉简书法的学习与创作自然地生长在汉文化精神的滋养之中。
结语
简牍一经面世即被书家所珍重,王蘧常、胡小石和高二适都对汉简极为倾心,陆维钊先生看到新出土的云梦秦简之后,书风为之一变,开创了风格独具的螺扁体篆书。其简练率意的笔法和质朴自然的风格影响了近现代许多书家,沈曾植、王蘧常、于右任、胡小石和高二适等都对汉简极为倾心,来楚生、陆维钊、钱君匋、孙其峰、刘正成、沃兴华、陈振濂、华人德、张海等书家都将汉简书法引入自己的书法创作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1]著名书法家黎泉是写汉简书体的高手。由此可见,汉简书法古雅质朴的盎然天趣,动人的艺术大自由精神,为我们的书法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随着对简书的深入研究,汉简的书法艺术价值将进一步为世人所珍视。
注释:
[1]《中国大百科·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第二二六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七八〇页。
[3]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四十六页。
[4]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光明日报》,二〇〇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5]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页。
[6]秋子《中国上古书法史》,商务印书馆,二〇〇〇年版,第四百八十五页。
[7]黄朴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概述》,《中国书法》,二〇一六年第五期。
[8]汪永江《书法章法形式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一二三页。
[9]陈振濂《近代三大发现对书法新史观建立的积极影响》,《文艺研究》,二〇〇八年第十二期。
[10]刘正成《二十世纪中国书法的回顾》,《中国书法》,一九九九年第八期。
[11]董文强《汉简书法艺术及其价值概述》,《书法》,二〇一六年第一期。
作者单位:陇东学院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