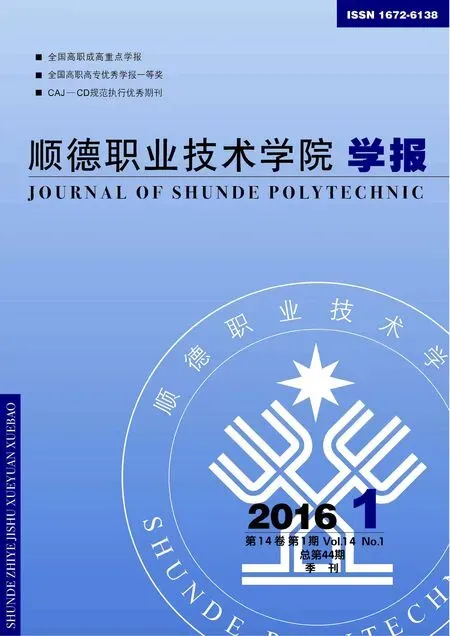试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艺术创新性
刘淑萍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试论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艺术创新性
刘淑萍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摘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综观丁玲的作品,对女性的体察、对中国不幸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刻思考,是丁玲创作的显著特点。丁玲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是丁玲在延安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并且充分体现了她对妇女问题的密切关注与深切体验,是她感情升华的结晶。文章主要从《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艺术创新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从题材选择的创新、艺术手法的创新以及思想的进步性三个方面展开,正是通过不同方面的创新塑造出了这个经典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丁玲;女性形象;贞贞;艺术手法;创新性
丁玲(1904—1986)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她善于书写女性,以女性性别立场的角度,对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进行独到的书写。丁玲笔下始终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表现了觉醒了的新女性对自我意识、自我解放以及人格独立的美好愿望的追求,塑造了不少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20世纪40年代她创作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特殊题材的选择及新颖的艺术构思,表明了作者卓越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丁玲对女主人公贞贞形象的塑造并不是直接描写,而且采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虽然如此,但是其中却一直透露着她对女主人公的同情与爱护。
1 题材的创新
1.1人物素材的选取背景
小说描写的是抗战时期,在日本侵略者扫荡的时候,一个叫贞贞的农村少女不幸被掠走,被迫沦为随军妓女。然而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她忍辱负重,多次为我军送情报。一年多后,组织上送她回家乡霞村养病,村里的人非但不理解她,而且对她投来鄙视的眼光和指指点点的议论,在经过内心一番痛苦的挣扎后,贞贞决定离开家乡,去延安追求光明。作者塑造了贞贞这个遭遇了特别事件的女性形象,却引起了文艺批评界的各种非议。其中,一些人认为,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和人们的寡廉鲜耻的女人”,因为“她自己对敌人并没有什么仇恨”,“可是对解放区的人们呢,却怀着深刻的敌意,讨厌一切的人。”[1]据此有人责备作者对日寇的罪行揭露太少,有“美化叛徒”之嫌。即使有人同情贞贞,也有疑问:作者为什么选择一个这样的人物来描写呢?
丁玲在谈到小说素材来源时,曾说过:30年代的时候,年纪轻,参加群众斗争少,从自己个人感受的东西多些。等到参加斗争多了,社会经历多了,考虑的问题多了,在反映到作品中时,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我写《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那样。我并没有那样的生活,没有到过霞村,没有见到这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人家对我说的。有一个从前方回来的朋友,我们两个一道走路,边走边说,他说:“我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干什么?他说:“我到医院去看两个女同志,其中有一个从日本人那儿回来,带来一身的病,她在前方表现的很好,现在回到我们延安医院来治病”。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就很同情她。一场战争啊,里面很多人牺牲了,她也受了许多她不应该受的磨难,但是人们不知道她,不了解她甚至还看不起她,因为她是被敌人糟蹋过的人,名声不好听啊。于是,我想了好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就写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个时候……无非想到一场战争,一个时代,想到其中的不少的人,同志、朋友和乡亲。所以就写出来了[2]403。一个优秀作家选择什么样题材,总是与她所要表现的主题密切相关。在延安时期,丁玲早已将创作视线投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她不仅时刻关注民族的灾难,也关注着灾难背景下的中国女性的命运。通过对战争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及其命运的书写,进而反映出战争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
1.2备受争议的人物形象
有人认为贞贞是一个丧失了女性贞洁与民族气节却讨厌一切解放区人民的女人,便质疑作者的写作意图,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作为随军妓女的贞贞,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问题。作品中,贞贞在敌人那里遭受的一切,虽然通过群众的议论作了一些零星的交代,但主要还是通过贞贞自己叙述出来的。小说这样写道:“‘苦么’贞贞象回忆着一件辽远的事一样,‘现在也说不清,有些是当时难受,于今想起来也没什么;有些是当时倒马马虎虎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呢……”“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3]34贞贞只是一个普通女子,不幸被敌人掠去做随军妓女,她心里更痛苦,而且她也没有做什么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没有理由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况且,她也没有堕落。虽然她不是那种以死相抗的刚烈女子,但是也不是就甘愿任人凌辱的人。她有自己的想法,她当时的想法是:“我总是得找活路”。她用自己坚强的意志力来抵抗来自身体和精神的折磨,她坚信总有一天会熬到头。当她和“咱们自己人有了联系”受到了党组织的教育和熏陶,她逐渐觉悟到:“还要活得有意思”。于是,她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为游击队传送情报。一次,“人家说我肚子烂了,又赶上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抹黑路我一个人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我看见日本鬼子在我捣鬼以后,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3]69在此,贞贞的性格发生了变化,由默默忍耐到积极配合我军抗日。但是作品并没有在这种变化中着力渲染她在不幸中的忍辱负重,而是注重表现和歌颂了她的反抗情绪,这是作品的描写倾向。
那么要如何理解贞贞在谈起自己遭受的苦难时,“象回忆着一件辽远的事一样”如此平静呢?这并不能说明贞贞完全忘记了耻辱、痛苦和仇恨。这正是她内心痛苦至极表现出的木然平静,这是一种无声的哀嚎。从阿桂听她讲述被她的话所震惊,“她的灵魂被压抑,她感受到了贞贞过去所受的那些苦难。”“我则深深地感到:如果她说起她的这段经历的时候,并不是象现在这样,心平气和,甚至就使你以为她是在说旁人那样,那是宁肯听她哭一场,哪怕你自己也陪着她哭,都是觉得好受些。”[3]105从两位旁听者的感受中,可以感受到贞贞平静的后面,深藏着一颗被仇恨和痛苦灼伤的心。只是因为她的性格内向,才没有把对敌人的仇恨表现出外在的强烈。只有伤心到深处,才会连泪水都没有,也只有痛到深处,连呐喊的力量都没有了。作者通过对贞贞的无声刻画,恰恰深度表现出了战争给女性带来的惨痛,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的声音根本无济于事,人要么奋起反抗,要么默默承受,而贞贞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柔弱女子,只能选择自我忍受。
1.3卓越的艺术胆识
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旨在说明,贞贞的悲惨遭遇虽是个人生活中的偶然,但这正表现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思想压迫的现实下,深受折磨的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是旧中国被压迫妇女的真实写照。通过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反映了中国妇女在双重压迫下的不幸与痛苦,而她的觉醒,也反映了中国新生力量的崛起,预示着民族的希望与新生。这一总体构思,角度新颖,有利于写出人物形象和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有人将这种大胆的艺术构思作了极为形象的比喻,认为作者显示的“宇宙”,“仿佛是崇高的峙立的深涧两旁的峻峰,那峡谷之间有一条险道,而这险道又面临着危崖,走入这境界的读者,只全神贯注在这条险道上了……”[4]有人会同情贞贞,但在别的方面又会有别的理由来责备她,然而作者正是通过这种矛盾的艺术创作手法淋漓尽致地塑造了这个不完美但是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作者截取了贞贞生活里的一个偶然片段,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初期这种历史的真实性,不仅对贞贞给予同情和赞美,而且使她在斗争中获得新生,只有拥有卓越的艺术胆识,才能做到。
2 艺术手法的创新
1)由远及近,由此及彼的艺术情节。
小说线索清晰,我们可以从作者对贞贞这一形象的塑造中看出来。小说不是一开始就描写贞贞,而是先写“我”去霞村,由“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一步一步为贞贞的出场作铺垫,层层推进,烘托出强烈的气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派抗战时期的景象:被鬼子炸毁的小学堂,村子里各种抗战团体的招牌与标语……战争给这个村子留下太多伤痛的痕迹;接着,来到刘二妈家,一群看热闹的人以及他们的议论,引起了“我”的猜想;村干部点出贞贞的名字,并没有消除“我”的疑虑,反而使“我”对贞贞更感到神秘。“我”的同伴阿桂与贞贞谈话后,一下子变得沉默起来,“她把被蒙着头”,“不住地唉声叹气”:“我们作女人真作孽呀”。阿桂的情绪让我对这种神秘感越来越强烈。这里,作者并没有展开阿桂与贞贞的谈话内容,只是从旁听者的情绪来暗示贞贞的不幸命运以及她对敌人的深刻仇恨,同时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这时,读者一定和“我”一样,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能引起人们这样的关注?但是至此作者还没有写到贞贞,而是笔锋一转,又从另一角度为贞贞的出场作铺垫:第二天天一亮,“我”出外散步买东西,听到杂货店和打水妇女对贞贞的种种议论——“风风雪雪”“浪来浪去”“缺德的婆娘”“弄得比破鞋还不如”,再加上刘二妈回忆贞贞的议婚、抗婚以及与情人夏大宝的故事,将贞贞的“谜”团越滚越大,让“我”对贞贞的感情变得更复杂,对她的命运也越来越关心。就这样,在贞贞出场之前,作者已经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人物素描: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女性,她的命运是奇特的、悲惨的;然而在那个具体环境中,她还不能被人理解,因此她所遭受的心灵痛苦将会比常人更加沉重。对贞贞命运焦虑与探询的心情,使我们将同情的目光开始投注在这个不幸的人物身上[5]127。
2)不落俗套,富于变化的艺术表现形式。
开始,我们还以为贞贞可能会是一个多愁善感、悲苦涕零的弱女子,但是作者笔下的贞贞却没有丝毫自卑的感觉,还未出现,我们就听到她“噗嗤”一声天真无邪的笑声。接着,我们看到:她“拿着满有兴致的眼光环绕的探视着”,“那眼珠却被灯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两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里的洞开的窗子,是那样坦白,没有尘垢”,“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也不觉得粗野”,微露出“安详”的神态。她善谈吐,关心学习,对新生事物很敏感,是一个性格开朗,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信心的农村少女形象[3]158。她是一个性格开朗心灵单纯的女孩子。当“我”问起她受过的许多苦难时,她“像回忆着一件辽远的事一样”,“我”与阿桂听着都感到了压抑,为她的话所震慑,而她却“丝毫没有想到要博得别人的同情,纵使别人正为她分担了那些罪过,她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就使人觉得更可同情了。”[3]207作者并没用过多的文字去描写她受侮辱的悲惨过程,也没有去描写她对敌人的仇恨,而是着力描写她在遭遇不幸之后“木然”“平静”的表情,但这并不表示她忘记了这些不幸与痛苦,越是平静越表现出了她是一个性格内向、自尊心很强的女性,这种压抑内心痛苦的表现也说明了她性格中的坚强。在她那平静的心灵深处,隐藏着感情的激流,而且越平静,在读者心里就越感到沉重,让人对她产生深深的同情。而她内心压抑的痛苦终于在夏大宝向她求婚时爆发。可想而知,她是以怎样一种痛苦的心情拒绝了夏大宝的求婚。然而,她说:“到了延安,还有另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重新做一个人……”,最后,这仇恨的灵魂终于受到新生活的感召得到升华,从她那坚定的语气里,我们看到了她有无限广阔的未来。显然,贞贞这一形象已经不同于丁玲以往所创造的妇女形象,从外表到内心,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控制力量,能够正确把握着自己的命运。
3 思想的创新
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解放区,虽然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提倡妇女解放,但是大多解放区“是个山野地方,从前人们说‘山高皇帝远’,现在也可以说是‘山高政府远’”。那个时代,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婚姻问题上还是传统的包办婚姻,大部分女性只能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默忍受着命运的安排,她们在家庭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更没有话语权。而丁玲在这篇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贞贞,不同于那个时代背景下普遍受到封建男权思想影响下的女性形象。贞贞是个有着强烈的自我个性、有着新思想的独立女性。而这种新思想也是作者赋予人物形象的。
首先,思想的进步性表现在,她敢于反抗封建父权制,反抗包办婚姻。虽然父亲帮她说的这门亲事是家道厚实的米铺小老板,但是贞贞却不愿屈从于父亲的安排,她有她自己的选择,她爱的是磨坊小伙计夏大宝。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对自己的父亲哭求,父亲仍旧不同意,但是贞贞并没有就此妥协,她希望夏大宝能和她一起逃跑,但是夏大宝的怯懦,让贞贞感到深深地失望了。当自己爱的人也不和自己站到同一战线时,贞贞宁愿去天主教堂当“姑姑”,也不愿做父权制文化下的牺牲品。她反抗包办婚姻,敢于追求婚姻自主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出对封建婚姻的抗议和不妥协,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最初表现。
其次,还表现在贞贞对整个封建男权社会的反抗。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人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于人们的思想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国,烈女不更二夫”这种传统的贞操观更是深入人心。因此在解放区作品中,作家多是把女性为保贞洁与敌人同归于尽列为壮举。例如,在孙犁的《荷花淀》中,丈夫水生在参军前对妻子的嘱咐就是不要被汉奸抓住活的,被抓住就要拼命。可见,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贞洁比她们自身的性命更重要。因此,小说中,尽管贞贞为革命奉献,带着功绩回霞村,但是人们眼里却只有她失节的事实,到处弥漫着对贞贞鄙视的男权话语:以杂货店老板为代表的男人们说“亏她有脸面回家来”“这种缺德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而同样受到封建伦理道德压制的女人们也说贞贞“弄得比破鞋还不如”,更过分的是“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面对如此尖锐难听的话语中伤,贞贞开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定,默默忍受着人们的鄙视与嘲讽,“使人感觉不到她有什么牢骚,或是悲凉的意味。”而当这些冷眼旁观的“看客们”又聚集在院子里“好像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这次贞贞终于愤怒了,“贞贞把脸藏在一头纷乱的长发里,望得见两颗狰狞的眼睛从里边望着众人,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像一个复仇的女神”,这次,贞贞用“狰狞的眼神”来回应霞村人的鄙视与冷眼,这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面对周遭浓重的封建伦理观念,亲人的不理解,贞贞没有像传统的女性那样最终妥协,她却以女性主义独立的人格姿态,放弃小我,追求大我,带着重生的希望,去延安开始新的生活。有评论家说这是一种逃避,但是在当时周遭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环境下,一个弱女子的力量怎能与之抗衡,所以,贞贞敢于走出去,追求光明,就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的表现,在当时,这也是丁玲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新思想。
“独立,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乃是第一需要。”从刚开始贞贞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男人,想通过私奔来反抗传统的包办婚姻,但是对方却表现出了怯懦,而她伤病痛苦更不被亲人理解,于是她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这真是女性独立人格的表现,与当时广大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思想截然不同。可以说“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性格的”贞贞,完全改变了父亲社会中女性传统命运,开拓了女性反抗精神,以其坚忍和顽强使女性自我独立人格傲然于世。不仅是贞贞,更是丁玲自己对南京三年囚禁生活,别人闲话侮辱的反抗,充分张扬了自尊自强的女性独立人格。
作家是从时代的角度来塑造人物命运的。贞贞的精神重创,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造成的,另一方面,以杂货店老板为代表的人表现出来的封建道德观念又加深了她的心理创伤。而作者重点描写的是后者。霞村的人们对贞贞的冷漠、鄙视,让人对贞贞的的命运更加同情,同时也表现出这些人的落后的思想。进一步说,也从侧面揭示出,人们的愚昧、落后、麻木的性格正是由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统治,近代中国日益衰败的现实造成的。解放区的土地上,尽管封建影响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东西”正在坚韧地生长着,“光明的前途”已经展开。
4 结语
丁玲的这篇小说,无论从艺术方面还是在思想层面表现出了独有创新性,从而塑造出了贞贞这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既揭示了中国妇女在战争年代所遭受的痛苦,又表现出她们的倔强。她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奋力挣扎,思想开始觉醒。从贞贞身上,作家深刻表现了一种强大的新生力量,这也预示着中国女性不可限量的未来。冯雪峰早在解放战争年代,就给贞贞这个形象以肯定的、崇高的评价:“《我在霞村的时候》,作者所探求的一个“灵魂”,原本是一个并不深奥的、平常而不过少许特征的灵魂罢了,但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孩的灵魂,却展开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这灵魂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是在被破坏和损伤中展开的她的象反射于沙漠面上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沙地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在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更非庸庸俗俗的人们所再能换进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贞贞自然还只在向远大发展的开始中,但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6]
参考文献:
[1]华夫.丁玲的“复仇的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J].文艺报,1958(3):25-28.
[2]丁玲.《谈自己的创作》[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3]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4]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J].抗战文艺,1944(9):36-40.
[5]郭成,陈宗敏.丁玲作品欣赏[M].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86.
[6]冯雪峰.从《梦珂》到《夜》[J].中国作家,1948(2):96-99.
[责任编辑:钟艳华]
珠三角研究
A Study of Artistic Innovation of TheTimeWhenIWasinXIAVillageby Ding Ling
LIU Shuping
(Confucius Cultural Institut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Ding Ling is a famous female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Overview of Ding Ling' works indicates certain distinctive writing features, including shrewd perceptions of women, sympathy to unfortunate Chinese women and profound thought on women's liberation. In the 1940s, Ding Ling created When I was in Xia Village,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novel in Yan'an Period, which has profound realistic pertinence, crystallizes her emotions, and fully reflects her close attention to women issues and her heartfelt experien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ovel's innovation in theme selection, mean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thought progressiveness, all of which together shape the classic image of woman.
Key words:Ding Ling; female image; Zhenzhen; mean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innovation
作者简介:刘淑萍(1990—),女,山东临沂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04
DOI:10.3969/j.issn.1672-6138.2016.01.015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138(2016)01-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