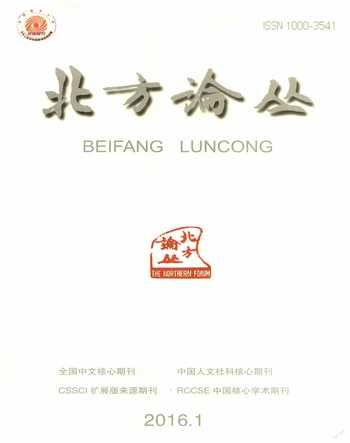古代游冥故事的“实录”叙事特征
郑红翠
[摘 要]游冥故事继承了中国文言小说受史传文学影响的传统,同时也是对文言小说史学“印迹”的扩展延伸。作为以超现实为表现内容的冥界游行故事,在叙述方式、体例等方面表现出史家“实录”的某些特征,显现出受史传文学影响的痕迹。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非常复杂,中国传统文化重史氛围的薰染,汉魏以来社会民众对幽冥鬼神的态度、创作者写作的主观宗旨、小说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小说观念的演变等因素,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游冥故事的创作。
[关键词]游冥故事;地狱观;实录;叙事;史传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19-05
一、游冥故事的“征实”特点
游冥故事继承了中国文言小说受史传文学影响的传统,同时也是对文言小说史学“印迹”的扩展延伸。作为以超现实为表现内容的冥界游行故事,在叙述方式、体例等方面表现出史家“实录”的某些特征,显现出受史传文学影响的痕迹。
1由民间传闻到文人“实录”的转变
游冥故事最初是一些流传于民间的游冥传闻,许多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些有关幽冥世界的传闻是文人笔下的游冥故事产生的基础。在游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游冥故事渐渐脱离了民间故事的某些叙事特征,进入到文人笔下(早期不少游冥故事的作者是佛教徒),开始具备文人“实录”的某些表面上的“史”的特点,经过文人有意地加工修补改造,完成由民间传闻到文人“实录”的转变。还有一些游冥故事是释子文人有意的“编造”,为取信于人,也在表面上达到“实录”效果。在此过程中,游冥故事与民间故事关系密切,许多游冥故事就是民间故事,也有许多文人“编造”的游冥故事在民间流传。民间故事在民众的口耳相传中常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游冥故事在很多方面具有与民间故事不同的特征:
第一,时间地点背景明确化。民间故事的时间背景则很模糊,故事的叙述时间常常是“从前”,或某朝某代,较为常见的难题求婚型民间故事、巧媳妇傻女婿型故事等①;而游冥故事为取信于人则非常明确,具体的年代地点都交待得很清楚。
第二,人物确定化。民间故事的人物一般是不确定的,同一故事在不同年代不同地点的版本中主人公发生讹传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游冥故事的主人公则很明确,人名传讹的情况并不多,如南北朝刘萨何入冥故事、宋朝黄靖国入冥故事多有记载,在流传过程中人名、故事情节没有大的改变。
第三,主题明朗化。民间故事的主题很多,真、善、美,奇、幻、异等都可能成为民间故事的主题。游冥故事的创作主旨非常清楚明确,就是劝教劝善,明鬼神之实有,行教化之苦心。
第四,结局圆满化。民间故事的结局也有很多是令人满意的大团圆结局,但有很多民间故事的结局是令人伤感的悲剧结局,如白蛇传、牛郎织女等。游冥故事的结局几乎全是大团圆结局,以复生为表现形式,“恶人”下地狱得到惩罚,“好人”得以复生延寿。
第五,语体风格的不同。民间故事多为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语言俚俗,叙述简单,具有口语化风格;游冥故事多为高僧或文人,语言古朴简练,较具文学色彩。
因为上述与民间故事的不同,也使游冥故事表现出部分“史”的特征。从汉魏晋始,幽冥怪谈长期在民间说话中流传,不少民间流行的故事经口传至笔录,先经集体口头创造,后由文士记载。所以,这种“记录”的特征非常明显。即使作者注意文采,不能完全摆脱构成过程中已积淀凝固的部分。这种情况与古代小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先天性格有关,耳目相接的传统,很大程度上一直保留至明清小说创作中,成为中国小说的遗传特性[1]。
2叙述方式的“征实”
绝大多数游冥故事的开头写法都很相似,先交代人名、籍贯、身份,然后进入事件的叙述,交代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从各个时代具代表性、记游冥故事比较集中的文言志怪小说集《搜神记》《幽明录》《冥报记》《夷坚志》、“剪灯系列”小说、《聊斋志异》等所记的游冥故事看,这种故事开头的写法几乎没有大的改变。人物、地点、时间都非常明确。这种写法与中国史传文学的代表《史记》列传的开头写法一脉相承。
在事件的叙述上,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以第一人称写法,写某人暴卒复苏后自言冥中经历。这是游冥故事最为常见的叙述方法。死而复生自述经历的写法在增强故事可信性上效果明显。如《冥报记》“李山龙”:
唐李山龙,冯翊人,左监门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冷,家人未忍殡殓。至七日而苏。自说云:当死时,见被收录,至一官署……王问汝平生作何福业……吏即引东行百余步,见一铁城,甚广大……吏曰:“此是大地狱,中有分隔,罪计各随本业,赴狱受罪耳。”……出门,有三人谓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见遗。”……山龙诺。吏送归家,见亲眷哀哭,经营殡具,山龙至尸旁即苏,曰:“以纸钱束帛并酒食,自于水边烧之。”忽见三人来谢曰:“愧君不失信,重相赠遗。”言毕不见。(《太平广记》卷一○九)
第二种情况,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客观叙述方式,以游冥之人的视角来叙述地狱里发生的故事。情节处理上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平铺直叙。 这种叙事方法从《搜神记》到《聊斋志异》游冥故事并没有较大的变化。只是《搜神记》叙事比较简单,至《幽明录》而渐趋复杂,情节渐趋繁复,至《聊斋志异》则记叙更加婉曲细致,情节更加曲折,引人入胜。明清小说中这种写法较普遍。这种写法的优点是由人间至冥界再回人间、由生入死及死而复生非常自然,阴阳两界合为一体,增强了故事的奇幻色彩。《聊斋志异》游冥故事多采用这种写法。如《聊斋志异》卷一“僧孽”:
张姓暴卒,随鬼使去,见冥王。王稽簿,怒鬼使误捉,责令送归。张下,私浼鬼使,求观冥狱。鬼导历九幽,刀山、剑树,一一指 点。末至一处,有一僧孔股穿绳而倒悬之,号痛欲绝。近视,则其兄也。张见之惊哀,问:“何罪至此?”鬼曰:“是为僧,广募金钱,悉供淫赌,故罚之。欲脱此厄,须其自忏。”张既苏,疑兄已死。时其兄居兴福寺,因往探之。入门,便闻其号痛声。入室,见疮生股间,脓血崩溃,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悬状。骇问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则痛彻心腑。”张因告以所见。僧大骇,乃戒荤酒,虔诵经咒。半月寻愈,遂为戒僧。
从叙事方法上看,从第一种写法到第二种写法,可以看出叙述方法演变的痕迹,更加注重情节的引人入胜。游冥故事逐渐挣脱史传文学的束缚,由增强可信性到增强可读性,叙述的方式更加自由灵动。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玄奥的佛教教义是毫无意义的,高深的佛教概念只有化作粗浅的道德说教,才能进入民众的生活之中。这些游冥故事成为宣教劝善的有效工具,为了加强宣佛效果,自然要求此类故事有趣“好看”,情节生动曲折。
在结尾的写法上,多数游冥故事是验证性结尾,交代故事的来源,对故事的可信性作以验证,以增强故事的叙述效果,如:
《法苑珠林》“陈安居”(《太平广记》卷一一三):“说与闻见,与安居悉同。”
《前定录》“柳及”(《太平广记》卷一四九):“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与及相识,具录其事。”
《冥报记》“柳智感”(《太平广记》卷二九八):“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禄卿柳亨说之。亨为邛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之。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数人说如此。”
《博异记》(《太平广记》卷三八零)“郑洁”:“郑君自有记录四十余纸此,略言也。”
《太平广记》卷三八一引《广异记》:“崇简召见问其事嗟叹久之。后月余李适之果拜相。”
《宣室志》“刘溉”(《太平广记》卷三八四):“窦即师锡从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事语于人。”
《太平广记》卷三八○引《续幽怪录》“张质入冥事”:“元和六年(张)质尉彭城李生者为之宰,讶其神荡说奇以异之,质因俱言也。”
这种故事结尾的写法随处可见,至明清小说中基本上没有多少改变。事实上,作为沟通阴阳的传闻故事,是无法验证其真实性的,但游冥故事却要在这一点上画蛇添足,无非是为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加强劝诫惩恶的效果,达到劝善止恶的目的。
3故事来源的“真实”
游冥故事多数是记录作者亲耳听到,以及别人转述的故事,因而摭拾传闻轶事便成为主要的成文途径,即干宝《搜神记》序所言:“收遗逸于当时”。此外还有杂取前代典籍、改编佛经故事等。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在谈到佛教应验故事的编集时说:“六朝后一阶段以佛教应验故事为内容的志怪小说作品,例如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佚名《祥异记》、侯君素《旌异记》等书,大多数并不是记录作者亲耳听到的别人讲的故事,而是从已经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故事集里搜集材料加以编集的。”[2](p84)
创作者广收这类游冥传闻,从而宣传佛教观念,并且为了强化宣传效果,往往强调这些传闻、轶事的真实可靠性。此类故事的虚妄不经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编撰者却一再强调这类传闻的真实性,注明故事的来源出处,以明其信而有征。这种强调故事真实性的做法,显示了游冥故事的一大特色,直至宋以后,依然可以清晰地洞见这种痕迹。
游冥故事多是当时的一些传闻,有的故事流传一时,诸多小说集都有记载。“赵泰”故事在《幽明录》中有记,《冥祥记》中也有记载。刘萨河故事在《冥祥记》《塔寺记》《法苑珠林》中都有记载。宋代“黄靖国入冥”故事是当时广为流传的入冥故事。廖子孟撰有传奇小说《黄靖国再生传》,《青琐高议》中“从政延寿”条叙黄靖国在冥中得冥王告知聂从政因拒绝李氏诱惑,得延寿一纪。黄再生后找到聂核实其事。《夷坚丙志》卷二“聂从政条”叙此事后云:“王敏仲《劝善录》书其事,曲折甚详。”岑象求《吉凶影响录》中“唐武后狱”条叙黄靖国入冥后见武后狱,狱吏告以大瓮贮虿蝎蜇武后事。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王番《褒善录》一卷,称删取本篇而成。李昌龄注《太上感应篇》卷二六“怀挟外心”注也述此事[3](p151)。
有许多游冥故事主人公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还有的故事见于史书记载。韩擒虎入冥为阎罗王故事有唐《韩擒虎话本》,《隋书》卷五十二有《韩擒虎传》亦记其死为阎王事。很多作者在文中强调这些故事是“所闻”“所闻知”。这类故事在流传中难免发生讹误,或故事情节上的不一致,这使得编撰者不得不谨慎小心,以保证故事的可信度。如“杜鹏举”故事,《处士萧时和作传》原文作《处士萧时和作传》,“作”为衍文,故去掉。(《太平广记》卷三○○)记有杜鹏举入冥知将为安州都督事,情节较复杂,文中提及唐相王及太平公主事,结尾记曰:“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践祚,阴骘祥符。启圣期于化元,定成命于幽数。后果为安州都督。”结尾所提到的时间地点人物及事件的实有,让人没理由怀疑故事的真实性。《纪闻》“唐相王”(《太平广记》卷一三五)亦记杜鹏举入冥知唐相王事,较为简略。《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卷三○○)记杜鹏举入冥见武三思、韦温等冥中受罚事,文字简少。对于杜鹏举,检新旧《唐书》并无杜鹏举其人,《新增月日纪古卷》之五上曾言《云笈七签》记有杜鹏举为安州都督。这种谨慎的做法,对于增强这类故事的真实性效果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类故事正为宣传佛教观念、弘扬佛法而产生。刘义庆《宣验记》、唐临《冥报记》等载有大量传闻轶事,但不再执着于强调这类故事的可靠性与可信性,这种情况至《聊斋志异》则更为明显。这种写作态度的差异,归根结底,与编撰者对佛教的态度的关系,也与作者的写作宗旨有关系。
二、游冥故事“实录”叙事的成因
游冥故事史家“实录”的叙事特征是一种刻意向“史”的靠拢,从本质上说,并非“史”家记事,只是一种“史”的某些形式上的表征,是受中国传统史学文学影响的痕迹。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非常复杂,中国传统文化重史氛围的熏染,汉魏以来,社会民众对幽冥鬼神的态度、创作者写作的主观宗旨、有小说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小说观念的演变等因素,这些无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游冥故事的创作。
1游冥故事的“实录”特征与创作者对幽冥鬼神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六朝多鬼神志怪之书,一方面表明时人对这类奇闻异事的好奇;一方面也可能是时人对幽冥鬼神之确信实有。因抱着这样的想法,在“记录”这类故事时也力求“真实”。从创作观念及表现形态上看,今天所称的志怪小说在当时人看来具有史的征实性。早期的志怪小说作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作小说,而是在“真实”地记录。《中国小说史略》谈到六朝人对鬼神志怪的认识时指出:“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4](p29)
晋干宝作《搜神记》,时人目之为“鬼之董狐”。干宝对幽冥鬼神的态度可以代表当时社会多数文人的看法。干宝因其父妾及兄死而复生之事,“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晋书》卷八二《干宝传》曰:“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宝父侍婢死而复生事又见《孔氏志怪》,宝兄死而复苏事又见《文选抄》,《十二真君传》亦载此事。干宝对幽冥之事可能是亦信亦疑。干宝《搜神记序》云:
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若此比类,往往有焉。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册,犹尚如此,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国家不废注记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
这篇序言中,干宝认为,真实是小说最高的原则,他所记也尽量追求真实。但对于自己所记之事因未亲闻睹,并无确实把握,而传闻之辞,未免失实,因而很难保证其叙述的完全真实,即使先贤前儒也不免于此。由于个人见闻的有限性,相同的材料在不同人的手中也会产生变异,故人们可以注意历史文献的鉴别,但不能因为某些异说而怀疑全部的文献记载。此序也有为自己开脱之意,自己记神怪之事也有“寓目游心”方面的原因。这里,干宝把追求真实和“寓目游心”统一起来,可见,早期志怪小说作者的写作态度,既追求真实又难以实证,对于未尝亲见亲闻之异闻怪事,宁信其有,以好奇之心记录下来。抱着这种复杂心态记异志怪,难免刻意地对事件来源的真实性加以说明,在结尾加上与事件无关的“尾巴”。
至于大量以宣佛为主旨的游冥故事,创作者多是佛教信徒或深受佛教影响,因抱着虔诚的信仰,对佛法灵验之事深信不疑,因此,在叙述中也会对事件的真实性加以强调。同时,在事件的叙述中注意细节的真实性,努力在取信与神奇之间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通过对细节真实性的强调来制造全局真实的效果。游冥故事受佛教故事影响很深,一部分游冥故事本身就是佛教故事。“佛教故事往往是征实的。它把宗教幻想说成是现实,把佛、菩萨以至地狱饿鬼说成实有。佛教本生或譬喻的一个特点就是结构上的联结部分,即传说中前世的某人某事就是现世的某人某事。六朝传奇从《搜神记》、《光世音应验记》开始,写到虚幻的鬼神故事则往往指明事情发生在某地,与现实的某人有关,某人可作见证。在这一点上,佛教故事与民间传说显然不同。民间传说中的其人其事是不确定的,只是一种传闻。佛教故事把灵异报应传闻说成实有”[5](p215)。《冥祥记》的作者王琰是佛教徒,曾经撰写过《宋春秋》,因为既是佛教徒,又是一位严肃的史学家,就使《冥祥记》表现出鬼神与“征实”奇妙的统一。“王琰是严格按照史书规范来写作《冥祥记》的,他对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的记载非常正确,甚至可以纠正史之谬,这是《冥祥记》与一般志怪小说不同的地方,这使得小说从‘裨史朝‘正史迈进”[6]。
2游冥故事的创作主旨直接关系到游冥故事的“实录”叙述
早期宣传佛教地狱说的游冥故事,创作主旨非常明确,为证地狱之说并非虚妄,在故事的来源、叙述的方法上刻意求“实”,也使游冥故事显现出“征实”的特征。从《冥祥记》序中可知,王琰幼年在交趾从贤法师受五戒,曾得贤法师所赠观世音像一尊,因梦得观世音像还,后来,此像屡屡显灵,“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觌,缀成斯记”[7](p356)。可知作者既深信不疑佛屠实有,又欲弘扬佛法,因而《冥祥记》的史家记事风格非常明显。至唐临作《冥报记》,在自序中曾提到六朝萧子良《冥验记》、王琰《冥祥记》等书,谓:“临既慕其风旨,亦思以劝人,辄录所闻,集为此记。”显然,唐临所作有南北朝辅教之书的影响,同时,唐临亦言:“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7](p355)可见本书的创作主旨是以报应思想行劝善之苦心。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对其篇目做了详细考证,认为:“唐临此作亦为佛法鼓吹,观其捏造谎说以谤傅奕等人,偏执近狂,正与法琳辈相呼应。至其渊源,则祖《应验》、《宣验》、《冥验》、《冥祥》等记,南北朝释氏辅教书之流绪也。”[8](p201)
隋唐时期,地狱说最为盛行,游冥故事的创作者在“自神其教”的同时,看到对地狱思想对人心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认识到地狱观念对道德教化的作用,自觉地利用游冥故事进行劝教劝善。从唐开始,游冥故事,为达到既劝教又劝善的双重目的,对故事的真实性需要刻意强调,表明不是虚构。在故事的叙述中进行事件真实性的辩解几乎成了叙述模式中必不可少、不断重复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以来,游冥故事的道德劝诫主旨强化,为加强劝诫效果也同样需要强调故事的真实性。这在《夷坚志》中非常明显。洪迈《夷坚乙志》序曰:“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9](p94)洪迈强调自己所记“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事实上,游冥故事本就虚妄荒谬,是无法“表表有据”的,无非是为《夷坚志》的劝惩效果加以说辞而已。
3创作者对地狱的认识
从南北朝至唐代的多数游冥故事中可以看出,故事的创作者是相信地狱实有的,对佛教地狱观念深信不疑,因而以虔诚地态度宣传地狱观念,在游冥故事的叙述上强调“征实”。还有一部分文人对地狱的认识是理智的,认识到地狱对道德人心的警示作用。
《国史补》(《太平广记》卷一○一)记载:
唐虔州刺史李舟与妹书曰:“释迦生中国,设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设教如释迦。天堂无则已,有则君子登;地狱无则已,有则小人入。”识者以为知言。
这种认识代表了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部分文人对地狱的清醒的认识,只是在佛教气氛浓郁的唐代,这种宽容达观理智的见解毕竟还是大音稀声。
明清时期,游冥故事已经脱离了“实录”原则的束缚,小说家们已经熟练应用游冥模式进行神道设教,再加上小说技巧的成熟,“真实”与虚幻已经融为一体了,如《聊斋志异》中的一些梦游地狱故事。小说利用游历地狱进行劝惩教化,一方面是这类故事在世俗传播发展过程中的不断成熟臻善;另一方面,也源于文人对地狱认识的深化与成熟。
明清文人对地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入,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五“事部三”谈到地狱对人心教化作用的有限:
释氏地狱之说,有抽肠、拔舌、油锅、火山、刀梯、碓锉之刑,如此,则阎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无知犯法,圣人犹怜悯之,岂能便加以人世所无之刑,使之冤楚叫号,求自新而不可得哉?盖设教之意,不过以人世之刑,止于黥、杖、绞、斩、凌迟而极,而犯者往往不顾,故特峻为之说,使之惊惧,而不敢为恶,此亦子产“为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张汤、杜周、周兴、来俊臣之徒,其狱具惨酷不减地府,而不闻民之迁善改过也。使冥冥之中,万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罗刹得以为政,其滥及无辜,贻害无类,岂浅鲜哉?老氏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世有一种穷奇梼杌、凶淫暴戾者,即入之地狱而出,其恶犹不改也。小说载:“华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饿鬼狱经数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狱门,即求人肉。其子泣谏。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无人食,何用救吾出来?”世之为恶者,往往如此矣。
清代许多学者都对地狱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卷二中认为:“地狱之说始于释氏,世每疑其妄诞,不知明有王法,幽有鬼神,宇宙间一定之理。以理揆之,地狱轮回之事,在所必有……世有《玉历钞传》一书,所载皆冥府诸狱科条,其词俚俗,稍知文者辄弃不阅,而实足令愚夫愚妇闻之悚息汗下”,并记载了因传录《玉历钞传》一书而得灵验获福之事。梁恭辰的见解比之于谢肇淛相对狭隘。
晚清时代随着人们对佛教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及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文人对佛教地狱观的理解也随之深化。王韬《淞隐漫录》卷九载有《梦游地狱》一篇,记有两则梦游地狱的故事。故事内容依然是宣扬果报轮回,行惩恶扬善之旨。然作者在文中论到:
夫天堂地狱之说出于释氏,为儒者所不言。然世俗人盛称之有,自死复苏者辄为人津津述之,几若身亲历而目亲睹,虽欲辟之彼亦不肯信也。吾以为一切幻境都有心造。平日具有天堂地狱之说在其心中,恐惧欣羡之念往来不定,逮乎疾病瞀乱,由其良心自责,于是乎刀山、剑岭、焰坑、血湖现于目前,恍同身受。无他仍其一心之所发现也,岂真有天堂地狱哉
王韬的见解可谓实见,对佛教地狱说有清醒的认识,是具有科学的现代意味的理解。
佛教地狱说,不过是一种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的内容是无需验证其真实性的。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11](p354)在中国小说以至中国文学中,绝大多数游历地狱故事不过是宗教观念的反映而已,而文人则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在民众中影响巨大的宗教信仰,作为劝善教化和针砭现实的工具,形成了中国小说一道独特的景观。
[参 考 文 献]
[1]张庆民.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通论[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日]小南一郎.观世音应验记:排印本跋[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石昌渝.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5]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6]王青.宗教传播与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J].世界宗教研究,2003(2).
[7]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8]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9]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0]王韬.淞隐漫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系哈尔滨工业大学副编审,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洪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