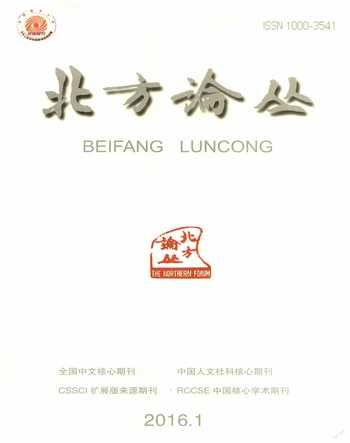从气象到情致:安史之乱期间杜诗风貌转变
唐萌
[摘 要]安史之乱期间杜甫诗歌风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展现恢弘大气的山河气象转变为生活情致的抒写。诗歌气象的展现与杜甫忠君爱国思想及盛世背景相关,而生活情致的抒写则是杜甫在战乱期间历尽人生磨难后寻求的一种情感缓释。这种转变与杜甫个人的生活环境及时代精神的递衰有关。
[关键词]杜甫;安史之乱;诗歌风貌;气象;情致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31-05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改变了唐代社会,同时也改变了众多诗人的命运。由此,很多诗人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诗歌风貌表现出与乱前的不同。其中,杜甫在战乱爆发后经历了北上投奔、授官左拾遗、归家探亲、避难入蜀、辞官卜居等人生经历。随着战乱的持续与生活环境的变化,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的诗歌风貌也从气象的展现过渡为情致的抒写。这一转变是杜甫对唐朝由盛转衰的情感认知,也是世道转关下个人命途的真实再现。认清这一转变对于理解杜诗的多样化风格,以及安史之乱后唐诗风貌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安史之乱期间的杜甫诗歌进行对比,揭示杜诗风貌的不同特征,并对变化的具体原因试作探讨。
一、杜诗之气象
(一)杜甫之“气”
杜甫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早年接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唐代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历仕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终奉天令。从杜氏世系来看,杜甫家世虽不至功名显赫,但始终不乏在朝为官之人。这样的家世背景使杜甫早年就已立定“致君尧舜”的志向。杜甫在《奉赠韦左呈丈二十二韵》中说:“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p.74)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甫对自己的文章学问十分自信,并且立志要辅佐君主再造盛世。特殊的家世背景与学优才敏的个人能力,使杜甫始终以辅臣的身份自居,这种身份促使杜甫形成“忠君爱国”的思想。
从精神层面来说,“忠君爱国”是道义的体现。“道义”在儒家内圣思想中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孟子道:“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2](pp.117-118)赵歧注曰:“言此气与道义相配偶俱行。”[3](p.59)根据孟子所言与赵注可知,道义与浩然正气是同行同在的,道义即为浩然正气的具体表现。浩然正气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道义也存在于天地之间。对于人来说,道义存于人心,是人心之中拥有的浩然正气。所以,“忠君爱国”作为一种精神是杜甫胸中浩然之气的外显。
今人李天保在论述气象时说道:“‘气象被引入诗歌领域内,大体指诗歌给人的整体风貌感觉,是诗人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是属于风格一类的东西。因为这个术语中有‘气这个很活跃、很有生命力的元素,所以他展示出的这个很复杂的‘象,也是很有强健生命气势的东西。因此,‘气象,一般以‘大而论之,并具体冠以各种名词喻之。就诗歌中的‘气象而言,他是一个很有活泼生命内涵的审美概念,所表现出来的乃是‘阔大‘雄浑‘强健‘浑厚之类的强势特征。”[4]
杜诗之所以表现出一种阔大恢宏的气象,与杜甫之“气”密切相关。杜诗一贯表现的心系国家、仁民爱物的情怀,是杜甫道义的体现,也是其浩然正气的体现。亦如孟子所言,“无是,馁也”,若抽掉杜甫心中的浩然之气,那么杜诗之气象便荡然无存。
(二)杜诗之“气象”
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战乱成为整个国家的主题。杜甫用诗如实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个人遭遇与社会乱象。战乱初期,杜甫经历了陷贼、逃难等流亡生活,深刻地体会了战乱给国家与百姓带来的创痛,由此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战乱现实与民生疾苦的诗歌。这些诗歌凝结着杜甫忠君爱国的思想,表现出一种恢宏阔大的气象。
下面以安史之乱初期的一组杜诗为例,考察杜诗之气象。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晚萧瑟,青是烽烟白是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塞芦子》)
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然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重对秦箫发,俱过阮宅来。留连春夜舞,泪落强裴回。(《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
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此行收遗甿,风俗方再造。族父领元戎,名声国中老。夺我同官良,飘摇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恶怀抱。若人才思阔,溟涨浸绝岛。樽前失诗流,塞上得国宝。皇天悲送远,云雨白浩浩。东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极柱亦倾,如何正穹昊。(《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入河蟾不没,捣药免长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月》)
明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徒步归行》)
胡骑潜京县,官军拥贼壕。鼎鱼犹假息,穴蚁欲何逃。帐殿罗玄冕,辕门照白袍。秦山当警跸,汉苑入旌旄。路失羊肠险,云横雉尾高。五原空壁垒,八水散风涛。今日看天意,游魂贷尔曹。乞降那更得,尚诈莫徒劳。元帅归龙种,司空握豹韬。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兵气回飞鸟,威声没巨鳌。戈鋋开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艰方尽,时和运更遭。谁云遗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卫牢。花门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怜子女号。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这一组诗歌写于安史之乱期间。从内容上看,这组诗歌围绕“战乱”主题展开。有记载战争之悲惨的,如《悲陈陶》《悲青坂》;有抒写战事感慨的,如《对雪》;有筹谋战略的,如《塞芦子》;有表达君国之忧的,如《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有感伤国家未宁的,如《月》;有期盼贤良靖难的,如《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徒步归行》;有记载官军获胜的,如《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还有两京收复后早朝唱和的,如《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在反映安史之乱期间的社会境况的同时,杜甫将个人感受融入诗中。在这些作品中,战乱是时代的主题,平乱是全社会的诉求,忠君爱国是诗人的思想主线。
以《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为例,此诗作于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讨贼之际。诗歌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胡骑潜京县,官军拥贼壕。鼎鱼犹假息,穴蚁欲何逃。”首先叙述了叛军寇京,官军至贼境的战事情况,并表达出势在必克的气势。第二部分,“帐殿罗玄冕,辕门照白袍。秦山当警跸,汉苑入旌旄。路失羊肠险,云横雉尾高。五原空壁垒,八水散风涛。今日看天意,游魂贷尔曹。乞降那更得,尚诈莫徒劳。”写官军军容之飒爽,勇猛砥砺之气概。官军渐逼京师,长安在望。有此军威,斩杀叛逆,贼众将灭,乞降无及。第三部分,“元帅归龙种,司空握豹韬。前军苏武节,左将吕虔刀。兵气回飞鸟,威声没巨鳌。戈鋋开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艰方尽,时和运更遭。谁云遗毒螫,已是沃腥臊。”仇注曰:“此言诸将协力征讨。元帅,谓广平王。司徒,谓郭子仪。前军谓李嗣业。左将,谓仆固怀恩。兵气二句,言军势之振。戈鋋二句,言军器之利。”[1](p.419)最后一部分,“睿想丹墀近,神行羽卫牢。花门腾绝漠,拓羯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锋先衣染血,骑突剑吹毛。喜觉都城动,悲怜子女号。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写复京之战,官军借助回纥、安西等地方军事力量,共同平叛。将士们浴血奋战,叛逆终将平定。到官军除贼凯旋日,百姓们争相庆贺。据此诗的写作时间来看,此时杜甫应在蜀地避难。尽管个人命途未定,杜甫依然关心国家战局。杜甫在得知官军即将赴京师收回失地之时,对官军讨贼之战的胜利表现出强烈的期待。从诗歌题目可知,官军仅仅是将赴被叛军攻陷之地,而最终的胜负尚未能定。杜甫为之而喜的是官军赴战,还不是官军的胜利。杜甫着重描写了官军飒爽整齐的军容、“兵气回飞鸟,威声没巨鳌”的军威以及“开雪色、向秋毫”的军备,这些是决定战事成败的关键。杜诗之所以着重描写军容、军备,目的在于渲染官军的气势,可见杜甫对此战抱有必胜的信念,这种信念增强了诗歌的气势。王嗣奭评曰:“此诗二十韵,字字犀利,句句雄壮,真是笔扫千军者。”[1](p.421)
二、杜诗之情致
安史之乱自天宝十四年(755年)爆发到广德元年(768年)平定,历时8年。战乱的持续,流离的日久,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弱,这一切都使杜甫心态发生了变化。从乱起之初对战乱平定抱有必胜的信念,逐渐转变为不抱有盛世复兴的希望。“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世路虽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春归》)在爱国而报国无力,忧世却入仕无门的矛盾中,杜甫将眼光从家国天下转向了个人生活。亲友、亲子、亲邻,关注自然之景,以诗酒相伴。这是历尽人生磨难的杜甫在情感上寻求的一种缓释。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感受到杜诗的另一种风貌——情致。
(一)亲友、亲子、亲邻
杜甫毕生,家人朋友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杜甫写过许多寄赠家人与朋友的诗作。特别是在蜀地避难的日子里,杜甫与朋友亲人相伴相亲,相互慰藉。寄赠亲朋之作是杜甫在沉重的君国之情以外真实细腻的情感倾诉,让我们对杜甫的认识除了忠君爱国的伟岸形象之外,还看到他平凡可爱的一面。这些诗歌表现了他与家人朋友之间的温情。
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疏快颇宜人。有客过茅宇,呼儿正葛巾。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有客》)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宾至》)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
这一组诗写于上元年间,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有客》生动地记载了一段“有客造访”的生活片段。客人不期而至,杜甫喊儿子整理衣巾待客,自己到田里锄来新菜招待客人。小事小诗,精致生动。这样的诗歌与那些忠君爱国的诗歌相比,内容不同、风格迥异。这些作品显然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赵汸注曰:“此诗自一句顺说至八句,不事对偶,而未尝无对偶;不用故实,而自可为故实。散淡率真之态,偶尔成章,而厌世避喧,少求易足之意,自在言外,所以为不可及也。”[1](p.741)诗之率真自然的生活气息让人倍感亲切,轻松自在的诗句流露出杜甫避世自足的心态。
如果说《有客》还是杜甫在偶然的有客造访之时流露出的率真之态,那么,《江村》则充分地表现了杜甫家庭生活的幽然心境。村居之“幽”在于村中之物与村中之人。村中之物之幽,有梁上之燕幽,水中之鸥幽;村中之人之幽,有画纸做棋盘的妻子之幽,有敲针作钓钩的儿子之幽。村居生活无事不幽然,无人不幽然。仇兆鳌注曰:“江村自适,有与世无求之意。燕鸥二句,见物我忘机。妻子二句,见老少各得。盖多年匍匐,至此始得少休也。”[1](p.746)从村居生活的幽然意趣中可以体会到杜甫与妻与子之间的脉脉亲情。
(二)自然与生活的诗化
杜甫在避难蜀地期间不仅有亲人朋友给予生活上的帮助与情感的慰藉,还有自然万物赋予杜甫以诗的灵感。杜甫把自然写入诗中,把平常生活写入诗中,表现出一种热爱自然、贴近生活的情致。
1.自然的诗化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茅茨疎易湿,云雾密难开。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梅雨》
蜀中四月黄梅雨至,杜甫以诗笔记录了这一自然景观。连绵之雨打湿了茅草稀疏的草屋,空中密布的阴云难开。蛟龙遇水则喜,在岸边回旋嬉戏。 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江涨》
江水上涨,儿童来报信,刚下床见江水已高出数尺,倚仗而水没中洲。可见江涨之急。尽管江水急涨,但江边燕子迎风而动,江中鸥鸟逐浪而游,渔人泛舟于宽阔的水面,却分外自如。
这两首诗都是杜甫选取自然之景入诗。“梅雨”“江涨”都是自然现象,杜甫用诗歌记录了这些自然之景,并在景物之中传达出自然之意趣。雨中蛟龙的自由嬉戏,儿童报江涨之着急,迎风而动的燕子,逐浪悠游的鸥鸟,泛舟江面的渔人,在这幅生动的自然画卷之中,所有的物象尽得天然之趣。而这种天然机趣是杜甫内心悠然之情的外化。王嗣奭评之曰:“动而细,摇而轻,因鸥燕之得趣,亦若水便之然。此于无情中看出有情。”[1](p.747)
2.生活的诗化
杜甫除了以自然之景入诗外,还对自己的卜居生活做了诗化的叙写,如《卜居》《为农》《田舍》三诗。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卜居》)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远惭勾漏令,不得问丹砂。(《为农》)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杨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田舍》)
杜甫在浣花溪边的草堂过着平常的生活,已然不见国家动荡的影响。诗歌中已不见家国历乱的悲怆之感,而是悠然自适的生活乐趣。从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到表现个人生活的情趣,杜诗风貌这一转变的背后是杜甫心态的变化。王嗣奭评之曰:“自安史倡乱,遍地兵戈,江村独在烟尘之外。如圆荷细麦,举目所见,景物可嘉,故将卜居为农,有终焉之志。”[1](p.740)王嗣奭所言“终焉之志”是说杜甫已有安身终老之想。无论是否如王嗣奭所言杜甫欲安身终老,从这些诗歌中,我们看到杜甫从关注国家政局到关心个人生活的这一思想上的转变。
(三)诗酒相伴
杜甫说:“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1](p.817)酒对于杜甫来说是终身未弃的事业。酒能助兴,醉能解愁,这两个重要的作用是促成杜甫诗思的关键因素。在避难蜀中的日子里,杜甫对国家政局与个人命途的认识有所改变。对国政中兴不像过去那样怀有饱满的热情与希望。与之相应,杜甫对自己入仕报国的理想也发生动摇。在矛盾与痛苦中,杜甫选择酒与诗来消解。
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
整履步青芜,荒庭日欲晡。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敢论才见忌,实有醉如愚。(《徐步》)
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其二)
稠花乱蕊畏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江畔独步》其二)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江畔独步》其三)
春光飞逝,年华不再,杜甫饮酒宽心;贤才见忌,不被世用,杜甫以醉解愁;春光正好,村野兴浓,杜甫饮酒助兴。在杜甫的世界里,处处有酒,处处有诗。酒对于杜甫来说不仅能够在快慰时助兴,更是在痛苦时宽心解愁的良药。面对国难家贫,人生的种种艰辛,杜甫无力应对,只得“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1](p.883),于是通过醉酒来麻痹自己,销解内心的痛苦。在安史之乱始平的广德元年春天,杜甫辗转多地后再回成都。这一年,杜甫已经52岁了。他写下了《春归》一诗,其中说道“世路虽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从安史之乱起到如今,近十年的流落漂泊,杜甫备尝艰辛。人生道路既然多艰,况且生有尽时,不如托身醉乡,乘兴为家。仇兆鳌注曰:“此有随寓而安之意。”[1](p.1111)
从上举安史之乱期间的杜诗来看,并非所有的杜诗都是忧国忧民之作。只能说,杜甫确实有很多以“忠君爱国”为思想主题的作品,同时,杜甫也有一部分展现个人生活情致的作品。两类诗歌风貌迥异的作品同出杜甫之手,反映出杜甫不同情感之间的互补。此外,杜诗风貌转变的背后除了杜甫个人遭际与情感的变化之外,时代因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从气象到情致的过渡
“杜甫的诗,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巨大变化”[1](p.1)。与此同时,唐代社会也使杜甫的诗发生了巨大变化。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旷日持久的战乱逐渐消泯了杜甫对于叛乱平定,以及国家中兴的期待。杜甫从最初怀着必胜的信念饱含激情地歌颂官军临贼境,到乱平后感慨人世多艰愿托身醉乡,两种心境在诗歌中表现为两种不同的风貌特征——从气象到情致。个人命途的多舛与时代精神的递衰是诗风变化的重要原因。
(一)个人命途多舛
根据杜甫年谱,自安史之乱爆发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广德元年(763年)乱平,八年间杜甫的行迹如下: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自京往奉先省亲。
至德元载(天宝十五载)(756年)五月,自奉先往白水。六月,自白水至鄜州,又至灵武,途中陷贼。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脱贼,至凤翔。八月,放还鄜州。十月,扈从肃宗还西京长安。
乾元元年(758年),任左拾遗在京。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晚,离宫至东都洛阳。
乾元二年(759年),春,自洛阳回华州。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至成都。
上元元年(760年),居成都浣花草堂。
上元二年(761年),居成都浣花草堂,间至蜀州之新津、青城。
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居成都浣花草堂。七月,到绵州送严武,遇徐知道反,入梓州。冬,复归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往射洪之通泉。
广德元年(763年),在梓州。春,间往汉州。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是岁,召补京兆功曹,不赴。
八年间,杜甫为了投奔肃宗、为了生计、为了与家人团圆、为了避难、为了送行友人来往奔波于多地。常年的奔波使杜甫身心俱疲,内心非常渴望得到安宁与稳定的生活。《春归》诗中“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除了托身醉乡的洒脱之外,又何尝不是对家的一种渴求?漂泊西南的人生道路并不是杜甫的自愿选择,而是随着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战局一步一步地演变而无奈至此。对于杜甫来说,他真正渴望回归的依然是生于斯而长于斯的长安。在这样内心无依、生活无着的人生境遇下,杜甫的一腔浩然正气不能不被消磨。当杜甫的生命动力、精神能量之气被个人命途的困窘消解之时,杜诗的恢宏雄壮的气象便失去了根基。
(二)时代精神递衰
安史之乱爆发于唐朝鼎盛时期。战乱给社会带来了巨变,皇权离散,百姓失所,这样的局面与开元盛世“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1](p.1163)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人们在盛世下形成的盛世精神与时代自信都已经随着国家连年的战乱消失殆尽。李唐王朝虽经千辛万苦得以保全,但是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已不再如从前。
1国内的人口经济情况
以山东地区战乱前后人口减少为例。战前,博州52 631户,战后减少了50 201户,降至2 430户,降幅高达95%。德州从站前83 211户,降至9 356户,减少了73 555户,降幅达89%。棣州战前39 150户,降至5 447户,减少了33 707户,降幅达86%。区域内的人口锐减说明了战争造成人口的大量伤亡或迁移,农耕社会中劳动力的减少,无疑会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方面,经济的衰败使国家的整体实力趋于衰败。
2国家的军事隐患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王朝屡次借兵回纥。这使得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一直受挟于外族部落。此外,原本占领一方的叛将在平叛大势之下,与官军妥协摇身一变成为一方割据势力,这些都是国家的重大军事隐患。尽管安史之乱平定,但是唐王朝一直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
支撑盛世的人口、经济、军事力量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所谓的开元盛世已经消失于安史之乱对国家社会的破坏之中。盛世已去,盛世赋予人们的那种自信昂扬、积极上进的时代精神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个人命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
四、结语
杜诗在安史之乱期间,由气象的展现过渡到情致的抒写是时代与个人共同所致,诗歌气象的展现依靠的是强大的国家实力与个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一旦抽掉这些因素,诗歌的气象便荡然无存。杜甫在国运转关之际,对国家命途逐渐丧失信心,将目光投向个人生活,抒写个人生活中的情致。而生活情致的抒写非关国运,偏重于表达个人感受的表达,所以,杜诗表现出从恢宏大气的气象到幽然生动的情致这样一种诗歌风貌的过渡。从家国关注到个体关注是诗歌气象变化的实质,这一点在中唐以后诗风演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参 考 文 献]
[1]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焦循.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本: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
[3]金良年.孟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李天保.“盛唐气象”概念的生成及再审视[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作者系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洪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