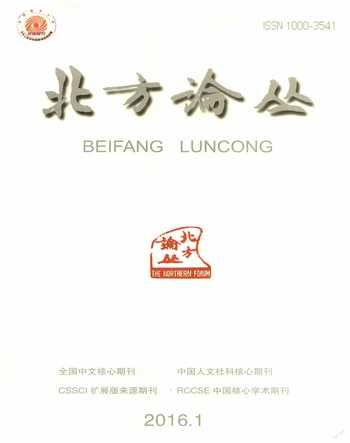对孟子“夭寿不贰”句之解读
李腾
[摘 要]孟子云“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中包含着“夭寿(生死)与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修身立命”这两方面的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在时间的视域下,将此在解读为“向死而在”,与言说“生生之大德”的儒者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命定的偶然性(个体的人必然有具体的实质限定)、必死性(有限个体必有其死)和使命义(人禀受善性而有道德使命)这三者构成了《孟子》中的“命”义。孟子反求诸己,追求人的本然善性和生之尊严;海德格尔则认为面对死亡的决断,是个体成为本真存在的关键,而儒者的生活方式可视作本真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孟子;海德格尔;“夭寿不贰”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103-05
Abstract: Mencius said that long life and early death were not different, the men who keep self-cultivation will build right destiny. There are two meaning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ing-death and destiny, and self-cultivation and destiny-building. Concerning above two questions, there exists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Heidegger and Confucian. Menciuss idea of destiny means occationality, mortality and moral command. Menciu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virtues and living, whereas Heidegger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being-towards-death.
Key words:Mencius;Heidegger;Long life and early death without differeace
晚清以降,如何会通中西思想成了当代学者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西方文化强权的压力之下,学者们多采用以西释中的方式来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解读,进而达到与西方思想建立联系的目的。但这条路径逐渐地引起一些质疑,如:以西释中视角下呈现出来的中国哲学,是否依然是这一思想路径的本来面目?这种解释方式是否合理?中国传统思想到底算不算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这样的质疑自然有其道理,而且也足以引起我们深思。但无论如何,即使到了今天,对于从事中国传统思想研究的学者来说,西方思想体系依然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参照系,如何充分利用这个参照系来挖掘、传承和发展传统思想,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因此,尝试着参照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视角,来解读“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孟子·尽心上》)这句话所包含意蕴,在尽可能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以期获得丰富理解的可能性。
德国哲学家史宾格勒说过:“人类所有高级的思想,正是起源于对死亡所做的沉思、冥索,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哲学与每一种科学,都是从此处出发的。”[2](p.113)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较为明确地讨论了此在(Dasein)的时间性问题——“向死而在”使得本真存在得以可能。在孟子的这句话中,同样涉及儒家对于生死的看法,尤为关键的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探讨不同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那种“理论方式”,而是立足于此在日常生活的生存论结构,中国传统思想在这一点上亦与海氏较为接近。之所以选择海德格尔的思想作为参照,正是基于这些近似之处。
一、“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包含的问题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大体的意思是:无论是早夭,还是长寿,都要坚定不贰地修养自身,这样才能得以立命。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认为:“夭寿,命之长短也……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3](p.349)命与寿命长短(夭寿)、亦即生死是联系在一起的。又如,《传习录》中,王阳明对这句话的理解同样是基于生死的基础:“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4](p.161)另外,《论语》中有借子夏之口明确说出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5](《论语·颜渊》)。“生”“死”显然与命相关,或者可以说就是由命所带来的,故而要想明确地知道“命”究竟何意,从对“生”“死”概念的剖析中或可通达。而这一层面的问题与海德格尔对此在时间性的分析遥相呼应。
除了“命”“生”“死”之外,这句话还包含另一个层面的重要问题,即“修身”“立命”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视作是解决第一个层面问题的途径(这一种看法较为符合海德格尔的思路),或者说,是经由第一个问题所产生的必然要求(较为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无论哪种看法,都应该看到,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不可任意地将它们分裂开来看。“修身”“立命”的问题,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人“面对死亡的决心”,是如何面对“能在的诸多可能性”而本真地存在的问题。
二、“生”与“死”在儒家思想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不同地位
“生”在儒家传统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仅仅在《论语》中就出现了17次之多[6](p.17)。另外,在《易经》中也经常出现。结合这些文本,可以看到,“生”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创生”意,这是以天的角度而言,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5](《论语·阳货》)再如“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5](《论语·述而》)天不言,但创生万物,包括万物之灵的人类,人之生成与否并不由人自身所决定,而是“天命难违”。海德格尔用“被抛”(die Geworfenheit)概念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此在(即人)总是身不由己地被抛于世界之中。
而人即得以生成之后,从人的角度看,天所赋予人的,大概又包含两重含义,结合上文,“生”的第二种意思是:天所赋予众生的每一独特的生命,这一生命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相反地,一旦生命形成,他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实事性质的个体。每个人在禀受性上面是不同的,如:“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5](《论语·季氏》)上智下愚,因天赋不同而生而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就可因此而推卸责任。此外,个体被抛于“世”之后,所面对的生活环境、人生际遇也并不相同,这一点也构成了“命”的重要方面,即“命运”意。诸多生存状况的恶劣和人生挫折,都可以看作是“命运不济”的一个方面,而“运”之有好有坏,也可以看作是天“生”来如此,而非个人所能把握的。海德格尔在此在(即人)的“生存论”结构(操心,Sorge)中认为,一定有一个“实事性”的维度,即总是“已经在……中的存在和寓于……的存在”[7](p.223)。换句话说,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此在,总是处于一个特定的状况中,如某个人的性别、身心状况,这个人的父母、出生地、家庭环境、国家、所处的这个世界等等,都在这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被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给予了,它们对于此在本身是一种构成,同时,也是一种限制。此外,在“生”的这意思中,还包含着生命中一些不可预料的遭际,这些遭遇是偶然的,不受我们自身控制、却能影响我们的生活和事业的成分。总之,在这里,“生—命”我们无法把握。
而个人能够把握的,是“生”的第三层含义:生命价值的赋予和要求。上文也提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在赋予人类以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作为生命的内在的价值。《易传·系辞上》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通过创生将这种创造的德行赋予了人类,因此,这时候的“天命”即天生之命,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德命令,要求我们顺应天道,努力实现天道对我们的道德要求。这一点我们留到下一部分再予以详细讨论。
“生”这一概念本身似乎已经足够复杂,既有对人生的偶然之运意义的揭示,同时还有承受天命之中当然之则的意义,但是,作为人的诸种可能性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可能性,即死亡的可能性,能够揭示出“命”的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死”是生的对立面,但对于作为此在的人类来说,有生就一定有死。有人从《论语·先进》中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中判断儒学只论生,不谈死。实际上死亡问题是作为一个思考的背景体现在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即使不论生、死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相生相连,谈及任何一个都必然暗含着另外一个;在儒家经典文本中也会经常出现生死并提的情况,如“死生有命”,又如阳明所说的“生死念头”——“生”没什么可怕的,而死着实让人恐惧,但对死亡的恐惧又是要破除掉的,这类似于戴震所说的“怀生畏死” [8](p.10),死是对生的否定和限制,但确实,儒家并不正面说死,虽然死亡意识可以被看作是儒家学者进行思考的一个起点。与其不同的是,在海德格尔这里,“死亡”是他着重进行分析探讨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真正意识到“死亡”,是此在能否从沉沦状态(非本真状态)转变为本真状态的关键。先将海德格尔对这一问题的论证简述于此,或许可以作为儒学对此问题论证的一个补充。
此在在世与工具性的存在不同,与动物亦不相同,“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7](p.49)。所谓生存最大的特色是“能在”,此在不像现成存在的东西(作为科学理论研究的对象)那样是固定的,它总是未完成的,具有诸多可能性:“这个为它的存在,而存在的存在者把自己的存在作为它最本己的可能性来对之有所为。此在总作为它的可能性来存在,在……因为此在本质上总是它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以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7](p.50)此在在世总是存在着诸多可能性,因此,就总是在变动不居,那么,海德格尔认为他对此在的分析就是不完整的,但“死亡”也属于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且是一种最为极端的可能性,是一种“必然的可能性”,意思是此在必然要死,但死亡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却是不确定的。这种可能性确保了此在分析的完整性,因为,一旦死亡到来,此在就不再在“此”,因此,就丧失了所有的可能性。这恰恰是终结所有可能性的极端的可能性。这是“死亡”的第一层意思。
“死亡”的第二层意思是关键性的:“死是把此在作为个别的东西来要求此在。”[7](p.302)我们在生活中可以通过很多种途径接触到死亡,如在新闻中或艺术作品中,这是一种纯粹客观性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变成了一个符号或者数据,我们每天熟视无睹,而淡然处之;又如,身边亲人去世,我们会通过一些祭奠性质的活动去缅怀他们。但这些死亡都不足以让我们明白死亡的真正意义,即“任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取走他的死”[7](p.276)。换句话说,我自身的死谁也没有办法去替代我,最本真意义上的死,是面对自己的“有死性”,这种死并不是说有人能够告诉你:大概你到了多少岁就会死掉,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的,其中充满着命运的偶然性(死亡,这时和“生”的第二层意思联系了起来)。日常面对死亡的方式是对死亡的一种逃避。正因为每个人都要独自地承担自己的死亡,所以脱离常人的状态而成为一个个的“个体”。
海德格尔所分析的死亡概念,颇可以补充传统儒家这方面描述的不足。死之必然性和生命短暂的急迫性,可视作儒者为何如此看重生之大德的原因,生命因其短暂而尤为珍贵,也正因为此,追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成了儒者孜孜以求的大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5](《论语·子罕》),因此,这种死亡意识应该也是君子人格所认可和接受的。
以上所分析的“生”(由于“生”的第一层意思是“天之天”[9](pp.96-108)层面的,故而不能纳入此)与“死”的概念,共同构成了“命”的概念。因此,“命”实际上是由三个层面的意思所共同构成:其一是由“生”所带来的“现实性”。我们出生是由于天生禀赋不同,而受到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限制。此外还有生活当中的偶然性境遇所带给我们的限制,均属于“生”所带来的意义;其二是死亡所带来的有限性。这一点是涵盖在儒家哲学之内的,但本文采用了海德格尔的解释,虽然术语系统不同,但其中内含的意蕴却可以相通,每个生命体的存在时间都是有限的,生老病死对于有限的人类来说,谁也摆脱不了,这一点是人类的最大的局限性,因此,要“不舍昼夜”地努力在有生之年,去成就自己;其三是“生”所带来的生命内在的道德价值。这一点可视作儒家“性善论”的来源。天地生物本来就是成德之事,而人类被创生的时刻,就承担了上天所传达的这一道德命令。这里“命”的概念就有了命令的意思,既然是命令,那么,是否有不接受的可能?按照逻辑来看,当然可以不接受,而且在现实当中,也的确有很多人没有去尽自身的努力而成己。但这不符合人所应当是的形象。《传习录》中有这么一则:“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4](p.53)“不可移”是命定论,上智下愚是不用负责任的,但“不肯”,揭示出了个体具备的自由意志,而这是道德行为的基础,没有自由意志,就谈不上道德不道德的。需要注意的是,传统思想中,在不同的场景下,对“命”这一术语的使用会有不同的侧重和选择,需要具体语境具体分析,但不脱这三种意思。
此前学者对于“命”的理解多数分为两个层次,即将命的第二层含义(必死性)放进第一层含义(生之偶然性)之中,而未将其单独分出,这两者均由“生”而来,如王夫之“福命”和“德命”的区分,其中“福命”事实上是包含着上面提到的现实遭际和死亡问题,如其在《读四书大全》中所认为的“福命”就包括以下两点:首先,“谓之‘命,则须有予夺。若无所予而亦未尝夺,则不得曰命……死,命也;不死,非命也。夭者之命因其死而言,寿者之命亦要其终而言也”[10](p.1137)。是指“死亡”问题而言,但并未深入分析其独特的地方;其次,生活中的富贵或贫贱,“富贵,命也;贫贱,非命也。由富贵而贫贱,命也;其未尝富贵而贫贱,非命也”[10](p.727)。撇开死亡问题的特殊性不谈,这种将“福”与“德”两分的做法倒颇似康德。在康德那里,尤其强调道德命令的绝对性:无论现实的遭际多么悲惨,都无损内心意志的自由和道德感的尊贵。
死亡问题本来就是包含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一维(作为时间的有限性),将其单独加以分析,亦有利于将其和西方思想家加以参照。
三、“破”与“立”在儒家思想和海德格尔哲学中的不同侧重
由上文以“生”“死”为进路对“命”的分析,可以得到对“命”的态度:天命实应敬畏,《论语·季氏》有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君子应该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5](《论语·尧曰》),进而去立命。不过,对于组成“命”的三个层面,需要区别对待,生命的限制性(偶在的遭际和必死的有限)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是属于“天”之管辖范围,所以,孔子才会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5](《论语·先进》)不是我们不需要了解死亡之事及其遭际的偶然性,恰恰相反,这些事情同样属于“命”之范围,是君子所必须了解的(“知命”),但了解之后,则必须明确一点:这些事情我们无法控制,同样地也无法改变,只有顺应而采取一种超脱之态,不怨天、不尤人,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做到的事情,而等待它的到来(俟之,这里所等待的应该是死亡)。而应该做到的事情,才是儒家所重点强调的,也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就是“命”所含有的“德”的成分,即天生我命所赋予我的生命尊严。这一点是历代儒家学者着力最多、用功最勤之处。“成圣成己之学”,方是学者们应该努力追求的,而非鬼神之事。就这样,通过对“命”的透彻了解,儒学冷静而现实地将视线转向修身立命:正心诚意、居敬穷理、修齐治平。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生”与“死”统一在“命”这一概念中,“命”本身就包含了限制与创造、实然与应然的维度,在揭露了人生之有限的同时,给予了人类一个无限的可能;在给予人生一个命定的、无法摆脱的禀赋和境遇之后,又恩赐了心灵一个自由的意志,让人类能够成为有尊严的个体。很明显地,在“破”与“立”,“死”与“生”之间,儒家更看重的是后者,即“立”与“生”,一切的痛苦与折磨都可以被生之喜悦和对天道的不懈追求所取代,“朝闻道,夕死可矣”[5](《论语·里仁》),朱熹曰:“苟得闻之(道),则生顺死安,无复遗恨矣。”[3](p.71)死亡无可避免,但要死得其所,人也就足以安然受命,而能够赋予有限生命以意义的,就是“道”。所谓的道,即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1](p.376)这是君子存在的意义与目的。同样地,这也是通过孟子“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这句话所想表达的意思。进一步讲,天道要通过具体的人道而得以体现,即在日用伦常中处处都能得到表现。这样,“道”不再只是抽象的绝对原则,而是学习者可以在生活中得以修炼的“切己之道”。
不破不立,先破而后立,那么,在儒家这里,破与立是否遵循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对“命”限定性方面的体认是道德追求的基础吗?这一点在儒家这里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述,而上文表明,“生”“死”既然具有同一来源,那么,破与立在儒者这里似乎可以一起进行。与之相反,在海德格尔那里,“破”则具有一种优先性和基础性的地位。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先是从此在的日常状态入手,描述了沉沦的非本真存在的“常人”,这种状态将自己消散在日常的操劳中,从而迷失了自我,虽然海德格尔一直强调这是一种积极的生存论状态(事实上此在永远也摆脱不了这种状态),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这种状态显然是要尽努力去超越的。如何成为本真的存在就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时候认识到个体的死亡就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意识到个体无法超越的、向死而在的生存论结构,才有进入本真存在的可能。死亡并非像常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人必然要面对的,但“不是今天”(也不是“我”)。而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和我们如影随形,将这种向死而在纳入个体的生存论体系,对死亡的这种畏之情绪,使得此在重新认识自身的存在根基,才使得“破”之可能性得以出现,然后此在才得以“立”。这一点儒家学说中很少涉及。
而海德格尔最终“立”的那个目标,是一种“普遍的形式”,而无具体的内容。正如《存在与时间》中最终所表达的思想显示的那样:向死而在的个体所做出的决断是成为自身,因此,海德格尔无法给出一个唯一的、确定的伦理学原则。这正是他的学说逻辑上的必然结果:由于死带来的个体化,因此,每个人在独立面对死亡的时候,自行筹划自身的本真性。而儒家学说提供了“立”的具体内容。按照海德格尔对本真性存在的讨论,儒家的道德学说很明显地也属于本真存在的可能性,但他肯定认为这不是唯一的。另外,其学说背后暗含着对个人意志自由的假定和对个体尊严的尊重,在这一点上,和儒家学说又一次达成一致。
四、结语
通过对“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包含的问题的分析看,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某个角度之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海德格尔学说构成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儒家学说更注重“生”(将“死”作为暗含背景),海德格尔更注重“死”(认识到“死”才能更好地“生”);儒家着重于如何“立命”,而海德格尔则偏向于如何“破命”,至于之后“命”是如何立,则看个人的理解,这种“破命”的方式可以提供出一条解决“不肯移”问题的思路。
[参 考 文 献]
[1]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德]史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陈晓林译.台北:华新出版有限公司,1975.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王守仁.传习录校释[M].长沙:岳麓书社,2012.
[5]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释慧开.《论语》“季路问事鬼神”章解读疏证——一个生死学进路的义理探讨[J].生死学研究,2005(1).
[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8]戴震著,章锡深校点.原善 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9]陈赟.化“天之天”为“人之天”及其哲学意蕴——以王船山为中心[C]//陇菲.《国学论衡》第三辑——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学术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10]王夫之.船山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1]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