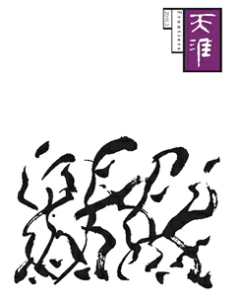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
在新近一期《读书》上,贺照田发文对启蒙与革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李泽厚的相关论述进行了学理性批判。
贺照田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中众多思想光谱中的一支,但它和新文化运动中多数思潮有明显差别。
马克思主义预设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对整个世界史的关键性意义。这使得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工人阶级时,不会有一般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社会时的那种当然优位感。而这种当然优位感,本来是新文化运动中以启蒙者自命的知识分子们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实际上在把自己的建设性意义和他们所要启蒙的中国社会的不理想都绝对化了。
这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不会是单向而是非常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
贺照田说,关于工人阶级之外广大社会阶级都具有革命性、革命潜能的理解和判断特别重要。这样一种判断促发了参与革命或与革命紧密相关的多样社会群体自身内部与彼此之间新的情感—意识—心理感觉状态的生成。以此为前提,中国共产革命所召唤到的各社会阶级,即使没有直接投身革命,很多也已不再是原来的状态,不再是过去意义上自己所在阶级的一分子,而是彼此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很强认同和连带的“人民”。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能帮助我们反思现代中国主流启蒙思潮的经验部分,在于它突破主流启蒙观后所建立的现代知识分子和社会间新的关系样态。
传统启蒙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共产革命的知识分子,虽然都有很强的国家责任感,但有关责任感如何才能有效落实的理解却相差甚远。前者的理解当然是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具有的现代知识和观念启蒙社会,尽可能把更多中国人改造成自己所理解的现代人;而后者则非常不同,他们所关切的不仅仅在用自己所拥有的革命知识、革命思想影响社会,而且还在把社会存在的革命动力召唤出来,并根据社会所表现出的向上品质与智慧来不断自我反观、自我批评、自我充实、自我改善。
中国共产革命的有关经验已向我们清楚表明,这个社会相比现代知识分子对它的期待确实不理想,但也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一些重要的品质和能量可以组织到现代中国所需要的历史进程中去;而这个社会是会更往现代知识分子期待的方向走,还是看起来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呼吁、祈向无动于衷,其实和现代知识分子是否找到了和这一社会有效互动的方式有关。
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描述了他呈现的“救亡”对“启蒙”的压倒后,没有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他所重点描述的最早作为新文化运动一支的中国共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会有这么强的塑造力量。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中共的数量,远远不如加入国民党的数量。很显然,加入国民党的现代知识分子未能真正脱离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观的束缚。
李泽厚这篇文章所支持的启蒙,是把有一定现代观念、现代理解、现代知识启蒙者的优位绝对化,把所要启蒙社会的不理想绝对化的启蒙。而这样一种启蒙结构不仅使启蒙者对其所启蒙社会的认识不能深化,最终影响着它对这个社会的介入改变能力,并且这种对待社会的方式,最终也会深切伤害社会和启蒙者自己。
贺照田进而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思潮也同样没有反省和检讨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他们之所以未能如他们预期的改变社会,固然和他们所处身时代的条件常常限制过大有关,更是由于他们自身所存在的结构性缺失。
(廖述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