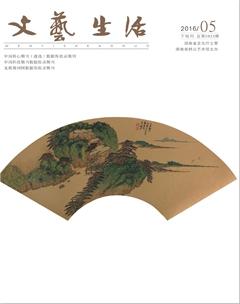孤傲的反叛者
李秀娟
摘 要:美国犹太籍作家塞林格的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隐含了丰富的犹太性特征,犹太文化母题之一的“父与子母题”在小说中得到了一定程度地运用与理解。本文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父与子母题”作为研究对象,全文分为“《创世纪》中的父子之争,以及与犹太经验的贯通”、“ 父与子母题的内涵及意义”和“霍尔顿与家庭、学校、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三章,包括引言和结论共五个部分。
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父与子母题”;犹太文化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5-0007-02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塞林格以现实主义的笔法,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当代美国青年霍尔顿精神的苦闷与彷徨,他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矛盾,揭露了当时社会生活中青少年所有矛盾问题的来源。霍尔顿的形象不仅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在现代社会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以往的研究者们主要分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创作主体意识、文本修辞的艺术手法、读者的接受反应以及文化历史语境等几个方面,对它的“父与子母题”这一创作特点的研究相对来说少一点,而这恰恰成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创世纪》中的父子之争,以及与犹太经验的贯通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父与子母题”是希伯来文化母题中最早的一个。这一历史事实贯穿在这一民族文化典籍《创世纪》中,并直接影响了“创世”后希伯来人的社会和精神文化生活。
上帝在创造了天地和动植物后在第六天方才开始造人。原因之一就是他早已认定有着理性思维的人类会违反他的规定,所以在不符合他的规定的时候他可以告诉人类,即使是跳蚤之类的东西都比人类出生的早。在创造出人类后,他还设置了一些规定,不允许人类触犯,否则会严惩。上帝这一人类的“父亲”和他的孩子“人”在人类产生之时就已注定了是一对永不能调和的对立体。
然而,作为上帝创造的孩子,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像木偶一样地遵从“父亲”的意思,他们有着独立的思维,有着对于客观现实的认同和好奇,也有着由好奇而产生的冒险举动,并在有意无意之间对创造他的父亲进行了无动机的反抗,惹恼了造他的“父亲”。“父与子”的矛盾渊源就这样开始了。
《圣经》中关于上帝与希伯来人及其后裔的对立描述是非常详细的,并且贯穿于这部神圣的文化典籍的始终。虽然上帝曾“教以除恶行善之道”,并许以“悔改则降之福,否则必加以祸”,但在整个《圣经》中,上帝与希伯来人及其后裔的矛盾冲突始终未能调节好,以致这种矛盾对立成为整个《圣经》的一个中心主题。“父与子”的犹太文化母题正是这样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来的。
犹太民族在不断的流浪史程中,父辈与子辈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直处于周而复始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他们总是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在新与旧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交替中,永远处在抉择的状态中,固守还是变革,这种文化的两难一直贯穿在他们生活的始终。当他们迁移到一个新的生存环境时,父辈们担负着沉重的昨天记忆,但子辈们面对新的物质文化生活,表现出趋同的心态,他们渴望很块地融入新生活,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挑战。“父与子”的矛盾冲突永远隐藏在犹太人的历史记忆里,当新的子辈出现,原先的子辈又扮演了父辈的角色,这样一代代的无限循环,犹太子孙们一直重复着他们古老的犹太文化母题。
二、“父与子母题”的内涵及意义
“父与子”母题的基本特征首先在于它是一种关系模式,它体现着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内涵:“父辈因素一方面是子辈因素的本源,另一方面又是子辈因素成长的障碍;子辈因素一方面是对父辈因素的延展,另一方面又是对父辈因素的一种反叛和背离。”①这种矛盾对立的关系模式一直反映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
在“父与子”犹太文化母题中,父与子的矛盾冲突在《圣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上帝是人类的父亲,父亲为孩子设计了一种原始的生活方式。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完全听从父亲的安排,生活在伊甸园里。但是他们却在撒旦的诱惑下,偷食了上帝不准许食的果子。这种革命性的背叛彻底惹恼了造他的父亲,因而上帝与人类之间的这种对立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永恒的基调。撒旦作为人类负罪的引诱者,其实它本也来自上帝的身边,甚至可以说它本是上帝的一部分,他这种对上帝本体意义的背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上帝权威的一次积极地反抗。上帝与其子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一直伴随在犹太人的历史经验和现世生活中。
在犹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在他们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中,父亲的权威意义是不能够被挑战的。刚刚出生的孩子,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他,希望这个孩子能顺从父亲和母亲的意思,做这个世界上最乖最懂事的孩子。严厉的父亲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要听从自己的安排,而且还要孝顺自己的母亲。因为只有孝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这个孩子才会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才会获得一个人的幸福。
反映到犹太籍作家中,每个作家对自己父亲的印象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最典型的代表是卡夫卡对其父亲的印象和感受。卡夫卡评价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善意谩骂的人,他什么人都喜欢骂。他身上似乎总是潜存着一股暴力的因素,他对生活中看不惯的一切都很严厉,对自己的孩子也很苛刻。在这一点上,塞林格、贝娄、罗斯等也十分认同,在他们的“父与子”的矛盾冲突中,父亲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家庭生活中的传统父亲,他所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权威和压力。但是犹太籍作家在对“父与子”母题进行运用的过程中,并不只是阐发了它的特殊性意义,也生发了它的普遍性意义。通过对这种普遍性意义的认知和运用,达到了对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一种普遍认知。
“父与子”这一文化母题是历久弥新的。它在犹太传统文化的沿用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前进与发展。父辈因素总是保持着生命的本源和传统的思想,而子辈因素却总是想冲突传统的限制,去迎接新的生活和新的价值思想的挑战,两者之间的对立冲突将永远地延展下去。
三、霍尔顿与家庭、学校、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麦田里的守望者》最大的艺术魅力就在于霍尔顿的守望者之梦。有一次他在美国百老汇的大街上行走,看到一个六岁的孩子哼唱着歌曲在汽车的飞奔和刺耳的刹车声中走着,而他的父母却一点也不在意他。这一情景真实地写照了当时美国社会父母与孩子关系的缩影,金钱彻底取代了孩子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孩子从父母那里得不到任何的爱和正确的引导。当菲比问霍尔顿喜欢什么时,他想到了男孩嘴里哼唱的歌,“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霍尔顿要在数以千计的玩耍的孩子中做一名守望者、看护者,他希望守在孩子们玩耍的悬崖边上。悬崖象征着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分水岭,纯真善良的儿童一旦失足跌入庸俗不堪的成人世界,从此便没有了快乐和自由。霍尔顿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和幸福,勇敢地担当起保护孩子的重任,替代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给予孩子们温暖的爱。
在家庭生活中,他讨厌他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工作态度。他那有钱的父亲从不肯帮助那些贫穷善良的人。他也疏远他的大哥D·B,曾经他是那么地欣赏大哥的创作才能并为此感到骄傲,可是如今的大哥却沦为一个世俗的撰稿人,这让他懊恼不已。所以他不愿回家面对自己的父母,面对自己的家庭,宁愿做一个孤独的流浪人。
在小说中,塞林格所描写的学校也是同样的粗俗不堪。社会上公认的名校和学校里优秀的学科,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例如霍尔顿的母校潘西中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面上这是间非常有名气的学校,但实际上学校里到处都是藏污纳垢。霍尔顿多次想要逃离虚伪的学校,他的四次辍学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向不喜欢周围的一切,学校操场上激烈的橄榄球比赛他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独自一人寂寞地呆在山顶,嘈杂的球场他完全充耳不闻。这争斗激烈的比赛在他看来是那么得争名逐利,就像当时躁动不安的美国社会,每个人都在趋炎附势,使劲全身的力气往上爬。他绝对不允许自己加入这种虚伪的追逐。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呆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里,阅读喜欢的书或回首美丽的往事。尽管他一向看重朋友,也经常想要给朋友打电话,但是他的电话总是没有拨出去。他的同学和他的关系也很冷漠,他不小心丢了比赛工具,大家的态度只是白眼和排斥。所以他只得戴着他的反抗虚伪的红色猎人帽,逃离开这个他根本无法融入其中的学校。坚守犹太传统的美德,必然会遭到排斥和挤兑,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小说中,霍尔顿一直担忧中央公园湖中的鸭子在冬天的生存状况。这里实际上暗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远。他想尽各种办法逃离开这个他一点都不喜欢的社会,以抽烟、酗酒、叫妓的方式融入美国文化,但他还是失败了,他根本不能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生活。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他像疯子一样被关进了精神疗养院。霍尔顿住在疗养院,似乎看透了生命中的一些东西,他至少接受了医院的治疗。小说开头霍尔顿独自呆在山顶,小说的结尾霍尔顿被送进了精神疗养院,这都说明了犹太人只有活在自己的隔都里才能获得少许的安宁。作品中,塞林格并没有刻意强调霍尔顿的犹太身份,但在小说的整体发展中,我们会发现霍尔顿的身上集中体现了犹太人很多的文化品质和文化特性。他徘徊流浪在纽约街头,使尽浑身解数,却无法融入社会的正常价值体系,他在处理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关系时鲜明地体现了“父与子”的犹太文化母题。
四、结语
本文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作为研究客体,探讨当中隐含的“父与子母题”。在小说中,塞林格刻意隐藏了霍尔顿的犹太身份,大量运用意象化以及象征的艺术手法,以隐性的独特方式刻画了霍尔顿这个现代社会的流浪青年。霍尔顿无法蒙蔽真善美的犹太美德,难以融入庸俗的美国文化,饱受排斥,被迫流浪在纽约街头,他与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矛盾对立体现了“父与子”的犹太文化母题。塞林格将父与子母题运用于《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展现了犹太人的精神一两千年以来历史的沉淀。他使行将湮灭的希伯来文化的古老传统重新焕发光彩,而且使人无不意识到当今美国社会中犹太人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霍尔顿的遭遇就是犹太人历史命运地真实写照。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小说只是塞林格“犹太情结”的展现,更应该察觉到他通过独特体验所表达的“犹太性”在现代西方社会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
注释:
①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9.
参考文献:
[1]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J·D·塞林格,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3.
[3]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
[4]黄铁池.当代美国小说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