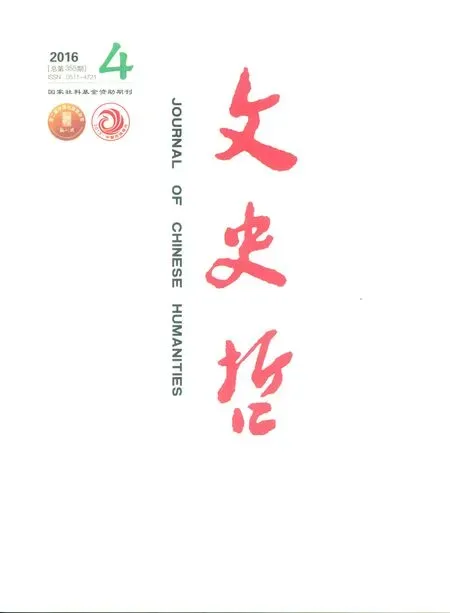《四书》本《大学》与《礼记·大学》:两种文本的比较
李纪祥
《四书》本《大学》与《礼记·大学》:两种文本的比较
李纪祥
摘要:朱熹释“大学”为“大人之学”,郑玄释“大学”为“太学”,前者指学问,后者指学宫。对早期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言,翻译此书时是追随朱熹的观点,因此从马士曼、马礼逊到理雅各,俱以“Great Learning”而非 “Tai School(太/泰学)”来翻译《大学》篇名。朱熹关注的是《大学》的作者问题,“经、传之分”也是从此思考而出现的章句做法;郑玄与孔颖达关注的是“从戴德到戴圣”的编者问题,从《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三礼目录》到《隋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一种书目线索。近现代学人讨论《四书》本《大学》或《礼记·大学》的作者与成书/成篇年代,包括使用郭店儒简文献时,都已受到朱熹的影响而不自知。朱熹提出的三纲领,在孔颖达那里只称为“三在”;朱熹提出的八条目,在郑玄那里是不成立的概念,而在孔颖达视域中的《大学》本文结构,确然并无后世所谓的“八条目”。郑玄认为在“太学”中所学的是一种“博学可以为政”之“学”,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反映的正是戴圣编辑《礼记》的理想:以礼治国。这也是郑玄在《三礼目录》中将《大学》分类为“通论”的原因。
关键词:《四书》;《礼记·大学》;朱熹;郑玄;孔颖达;理雅各
一、《大学》与《礼记·大学》:释名与译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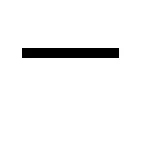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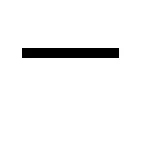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很明显,首句中的“大学”一词,与作为书名的《大学》,理雅各是采取了同样的译词;而在《礼记·大学》中的“亲民”,理雅各也是追随了朱熹的“改字”,改为“新民”,理雅各还特别在译注文中对于朱熹何以“change亲into新”作了解释;对于“亲民”一词,他认为“亲民=亲爱于民”,因此,理雅各的译词是“to love the people”*James Legge, The Great Learning, 356.。理雅各除了《四书》(FourBooks)之外,也译有《五经》(FiveClassics),在《五经》中的“礼经”部分,刚好,他所选择的正是《礼记》,因此我们不免要问,作为《礼记》组成部分的单篇《大学》,本来应当是追随汉代郑玄的注解系统才是,那么理雅各是如何翻译《礼记》中的《大学》呢?我们发现,理雅各对《礼记·大学》,完全是照搬《四书》中《大学》的译法,将此篇篇名亦译作“The Great Learning”,并未遵照汉唐学术体系中郑玄、孔颖达的注疏解题。理雅各的这种做法,并非新创。在中国,从元代开始,对于《大学》的版本与解说,便已经是朱子学的一尊化,从《四书》中的《大学》,进入到《礼记》中的《大学》,都已是采用了朱子对《大学》改动后的新编章句之改本与解释。理雅各在翻译《礼记》时,对《大学》篇名的译名,同于《四书》中《大学》的译名,亦是译作“The Great Learning”。

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孰非精神心术之所寓,故能与天地同其节。四代损益,世远经残,其详不可得闻矣。《仪礼》十七篇,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彰《庸》、《学》,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博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陈澔:《礼记集说》,“序言”页。
陈澔在序文中说得很清楚,原本在《礼记》中的《中庸》与《大学》篇,已经在先儒的表彰下,提升其地位成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二篇另有编纂,与其他四十七篇亦已无可同语。是故陈氏的《礼记集说》只有四十七篇。因依戴圣《礼记》为底本,故书目中仍依原编序次与卷目篇名,然对抽去的两篇之文不必再作集注新说,盖其二篇已在《四书》中也。
陈澔《礼记集说》,在明代为胡广的《礼记大全》所继承吸收。明代作为士子考试的科举举业,如果在考试的内容方面是以《四书大全》与《五经大全》为主,那么定于一尊的朱子学及其著作,显然已通过试子所必读的科举范本,使得《四书大全》与《礼记大全》中的“大学”,都以朱熹的《大学章句》为主。这很可以解释为何明代士子不容易看到旧本《礼记》中由郑玄所注、孔颖达所正义的《礼记正义》之故。换言之,唐代作为官学体系的《五经正义》,至少在《礼记正义》中的《中庸》、《大学》两篇,已经被元明两代的官学——朱子学的《大学》、《中庸》新编文本所取代。

在郑玄注本《礼记》中,《中庸》篇的编目序次在《大学》篇之前,但在《四书》中,《大学》的编次反在《中庸》之前,而且是居于《四书》的四部书之首。朱熹在新编《大学章句》便将二程的这一段话放在全书正文之前,以指示《大学》一书的重要性。其云: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在朱熹引用程子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有两处提到了“大学”的篇籍属性,一是“孔氏之遗书”,一是“独赖此篇之存”,如果细思书名与书中某篇篇名的差异,那么,“大学,孔氏之遗书”的“大学”,究竟是书名还是篇名呢?朱熹似乎在此暴露出了一处“译古为今”意识中未察的小矛盾!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云:“《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1页。(朱熹在这段文字中的第二个“大学”应当读为“太学”)显然确实已将《大学》视为“书”的属性。在北宋二程的时代,纵然朝廷与士大夫都已经开始强调了《礼记》中《大学》的重要性,皇帝亦有亲赐单篇《大学》、《中庸》给朝臣的,但此时《大学》仍然是一篇文章而非一册书籍,因此,程子所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者入德之门”中的“大学”应为篇名,而非书名。当然,程氏之言出现在朱熹的《大学章句》中,而朱熹对于《大学》的尊重又来源自程氏,所以才会尊称其为“子程子”。由是,经过北宋而至南宋的历史发展,我们在朱熹的《大学章句》中,确实可以看到北宋的“子程子之言”在南宋被朱熹引用时,“引文”的历史化姿态已经是作为书名的《大学》而不是作为篇名的《大学》了。理雅各因此在翻译这段引文时,便以朱熹的立足点而将之译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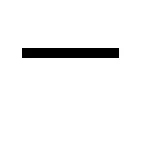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理雅各上述翻译反映的,正是明代耶稣会士以来所见之朱子学影响下的风气:明清以后,无论《礼记》中的《大学》篇还是《四书》中的《大学》一书,都是朱子学式的。这可以解释从马士曼、马礼逊到理雅各,为何俱将一书、一文,均译作“Great Learning”之故。
对于程子所说的“孔氏之遗书”一句,理雅各注意到“孔氏”这一词,不仅能译作“孔子”,单指一个人,也能当作复数词。因此,理雅各在他的译注文中特别标注出“孔氏=孔门”,而将“孔氏”译为“the Confucian school”*James Legge, The Great Learning, 356.。理雅各注意到这一个词汇是有锐见的,对朱熹而言,《大学》一书并非成于孔子一人之手,由于朱熹认为《大学》有“经”有“传”,因而应当是孔子其门人、再传弟子共同完成的一本书籍。理雅各将程子之文“孔氏之遗书”译作“a book left by Confucius”,但在译注中却对“孔氏”一词作了“the Confucian school/孔门”的翻译,值得注意。
作为译词的“learning”,还原到原文中,是指“学习”意涵的“学”,但是在《礼记》中的许多篇中有关于“学”字的使用,却并不是指向“学习”,而是指向于“学习的场所”,也就是“学校”,因之在译法上,就不能译作“learning”,而应当译为“school”,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词语。对于《礼记》中提到“学习场所/学校”的篇章及其文词,理雅各所译大多是使用“school”或是“college”等词,譬如《礼记·祭义》篇,文云: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
这里的“大学”、“西学”,理雅各的译词为“the Great college”,“the Western school”*James Legge, Li Chi:Book of Rites (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Part II,“Ki I/The Meaning of Sacrifices”(祭义),SectionⅡ,第20条,231.。又如《礼记·学记》篇,文云: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
理雅各译文为: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of ancient teaching, for the families of there was the village school; for a neighborhood there was the hsiang; for the larger districts there was the hsu; and in the capitals there was the college.*James Legge,Li Chi: Book of Rite,PartⅡ,“Hsio Ki/Record on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学记),第4条,83.
“国有学”之“学”,理雅各译作“college”。不论是译为“school”还是“college”,都不是指向“learning”,而是指向国家体制中学习的场域。《礼记·文王世子》篇: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
理雅各之译文为:
In all the schools, the officer (in charge), in spring set forth offerings to the master who first, taught (the subjects); and in autumn and winter he did the same.
In every case of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f a school the offerings must be set forth to the earlier sages and the earlier teachers; and in the doing of this, pieces of silk must be used.
In all the cases of setting forth the offerings, it was required to have the accompaniments (of dancing and singing). When there were any events of engrossing interest in a state (at the time), these were omitted.

《礼记·王制》篇:
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
理雅各译文为:

《礼记·王制》篇中的三个词语:出学、入学、视学,理雅各或用“school”,或用“college”译之。特别是《学记》中的一句“大学之教也时”,理雅各译为“In the system of teaching at the Great college, every season had its appropriate subject”,以“Great College”译“大学”*James Legge,Li Chi: Book of Rite,PartⅡ,“Hsueh Chi/Record on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第6条,85.。先秦以前的“学”字可以指向学制中的“学校”,已经在理雅各的译词中显示出两个“学”字的差异:“school/learning”。“大学”,无论是作为篇名或是书名,我们在阅读到《礼记·大学》与《四书》本《大学》时,应注意到“宋明理学”体系形成以后的汉学、宋学之两种学术系统的差异性格。因之,“大学”的“学”在郑玄注本那里应当被译为“school”,译为“Great Learning”只是朱子学兴起之后的一家之言。于是,“大学”一词究竟应当如何训诂或翻译,便成了一个阅读起点(Where is the beginning for reading?)便开始存在的分歧与争议。
二、朱熹《大学章句》中的“大学之道”
(一)《大学》是“入道之始”
朱熹之女婿、高弟黄幹,在朱熹过世之后所写的《朱先生行状》中谓:
先生教人,以《大学》、《论》、《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于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黄幹:《朱先生行状》,《勉斋集》卷三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4页。
其意谓:朱子在教人时,必定是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书作为学习上的“入道之序”,而且必须要阅读完这四部书之后,才能开始阅读《五经》。黄幹这样的表述,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朱熹的另一位高足陈淳,却有着不同的观点,“黄、陈之歧”是许多学者曾经忽略过的主题。陈淳在他的《严陵讲义》之中,曾经以极为精练的语言,表述了朱门何以重视“入道之序”的根本原因,他说:
道之浩浩,何处下手?*陈淳:《严陵讲义》,《北溪大全集》卷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页。
提出了“求道”应当从何处“下手”的问题。在《严陵讲义》的《读书次序》篇也再次提到了“读书”的重要性。“书”,是圣人垂训之所在,圣人已往,存于今者,唯有“书”而已,所以今人必须要“读书”,透过“读书”,才能得到圣人“留下/流传”的“道”。请读者注意,陈淳自题的标题就是“读书次序”,对陈淳而言,“读书之序”就是“入道之序”,对“入道之序”的关注,本来就是朱子为学与朱门教学的重要特色。确实如此,朱熹为学,深惧世人流禅、堕虚,因此不论在修养功夫与读书阶序上,皆主张学有等第,方符合孔门下学上达之宗旨。于是,凡朱门之后学,皆循此而讲求入手之基,从“何处入手”到“入道之序”,都可以是为朱门弟子所重视的大课题。于是,同是朱子门下的两位高弟,竟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重大的分歧与书信式的公开争议。陈淳主张在阅读《四书》之前应当先读朱熹、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他的依据,在于《朱子语类》中的一条记录:

宋理宗时期的重要人物真德秀,显然便是陈淳主张的追随者,他在《西山读书记》中即云:
淳熙二年,东莱吕公自东阳来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与掇周子、程子、张子书,关大体而切日用者,汇次成十四篇。……号《近思录》。先生尝语学者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以言为学者,当自此而入也。*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7页。

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殁,其书始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其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参见黄幹:《书晦庵先生语录》,《勉斋集》卷二十二,第6页。
其一“窃”字,充分显示出黄幹对“记语”之“文”的不信任感。黄幹在《答李方子》中,也正式提出对陈淳的反驳,云:

《答李方子》中所提及的“真丈”,即是真德秀,李方子在《宋元学案》中列于《沧洲诸儒学案》中。依黄幹的观点,一是据“师说”则未尝闻朱子有此言,二是据“师文”则圣门之学的“入道之始”,应当要从朱子所亲笔的文字来寻觅何者才是首先阅读的第一个文本;黄幹更是明确地表示:他从未“听过”朱老师说了陈淳所记载的那些话。显然,黄幹与陈淳在“记言文”与“亲笔文”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而这个分歧,却正好涉及何谓“入道之始文本”的依据。黄幹的重点显然是在《四书》中的“入德之门”,也就是《大学》,这是立足于“程朱学统”的观点;而陈淳则是立足于朱子,在“后朱子时代”提出在学统中置入新文本。“黄、陈之歧”显示的正是朱子过世之后,朱门弟子在如何认知“入道之始”方面产生争议的一个显例。当然,如果我们将“入道之始/入道之序”的研究课题放置在“后朱子时代”的“东亚理学”脉络中来考察,便会发现在不同的国度、地域,古韩国时的著名学者——被尊称为“海东朱子”的李滉,又有着不同于中国境内的“入道之始”观,李滉从不同的角度与不同的立足点所提出者,乃是另一部“入道之始”的文本,此文本既非《近思录》,也非《四书》本《大学》,而系另一部文本“《心经》”,所以李滉连带对于《心经附注》的注者程敏政,也相当推崇,在朝鲜还引起过一段李滉与门人争论的公案。跨地域国度的比较视野,更使此一“圣人之学/入道之始”的议题变得更为复杂也更吸引人。
(二)新的术语:“三纲”与“八目”
“黄、陈之歧”有关“入道之始”的争议,乃是发生于“后朱子时代”的事件。如果回到朱熹的生前,则对其而言,《大学》方是“入德之门”。我们遂可以立足此处,来考察何以朱子如此在意《大学》一书必须编为《四书》之始之故?不仅如此,根据现行各家朱熹的年谱、史传,记载了朱熹易篑之前最后的一件大事,便是他仍在改动《大学章句》的《诚意章》,生时、死前的学术大事,都在《大学》一书,《大学》确实是朱子念兹在兹所欲留于后世的一部名山事业!也只有《大学》的作者是署名为孔子、孔门的圣人之经时,才能吸引朱子如此付出!如果从这点来返观《礼记·大学》文本在汉代的地位,则显然尚未有如此的崇高位阶,《礼记》本的《大学》只是作为儒家文献中“记”文的位阶,迄今笔者未曾读到有任何汉儒将其视为“经”的!
朱熹继承了北宋二程的遗说,将《大学》视为是圣人之亲笔、孔子之遗书,因此,不同于汉人视《大学》只是解经的“记”的位阶,根本上就是应当被解释的“经”。朱熹在《书临漳所刊四子后》云:
圣人作经以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其言虽约,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细,靡不该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书,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影印明刊本,第1493页。
因此,朱熹在《大学》首章之前,便置入了引述于程子的经说之文,曰:
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
所谓“独赖此篇之存”,“独赖”一词已道出了《礼记》中《大学》一篇的无可取代性。正是在汉儒的忽略下,朱熹才必须将《礼记》中的《大学》篇抽出另视为一书。而“独赖此篇”的“独”,其独特性便是在于《礼记·大学》昭示圣人“为学次第”的唯一性。在《礼记》中当然不只《大学》一篇能昭示古人之为学次第,因此,《礼记·大学》能被程、朱慧眼看出它的独特性,便在于它所揭示的“为学次第”与“入德之门”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学或问》上便明确地载录了朱熹设为问答体而写出的再解释,云:
是书垂世立教之大典……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无非切于学者之日用。……此程子所以先是书而后《论》、《孟》。*朱熹撰,[日]友枝龙太郎解题:《大学或问》,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第19页。
《大学或问》又曰:
以是观之,则务讲学者,固不可不急于《四书》,而读《四书》者,又不可不先于《大学》,亦已明矣。*朱熹撰,[日]友枝龙太郎解题:《大学或问》,第20页。
《大学或问》的文字问答已将朱熹对“四书”的安排顺序阐明得很清楚,也对二程将《大学》定位为“入德之门”之义作了十分畅然的解释。《大学或问》中,朱熹进一步阐发《大学》一书所以能为圣人垂世教大典者,完全在于惟此篇能“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在《大学或问》的文字叙述中,我们读到了一组专门语言的出现,支撑起《大学》何以为“孔氏遗书”、“入德之门”、“圣学之始”、“入道之先”:原来在于《大学》中对于“圣学”、“大学”的规模、工夫次第,特别是对于“入道之序”、“工夫次第”的“纲领”与“节目”的阐述。对朱熹而言,《或问》中这样的拟问答书写并不是场面话、夸饬语,而是刻意的书写,因为《大学》一书就是圣人所亲自透过门人的笔书写传下的圣典,“大学之道”的精义就是在于其“纲领”与“节目”。“纲领”是“三纲领”,这是孔子在《大学》文中的垂教昭示,此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的纲领有三:“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注曰:
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
朱熹明白地在其“注”中,指出了“此三者”即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而此三者便是“大人之学”的“纲领”。《大学或问》中也一再申释何以此三词为《大学》全书的“纲领”之故。
所谓节目、条目,则是曾子所述所释的八节目,此即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此八个条目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彼此间存在相互作用,朱子在《大学或问》中所谓“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者,便是指此。在《大学章句》“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下,朱熹注云:
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所谓的“此八者”,指的便是《大学》本文中所出现的八个成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此“八者”,朱熹用的是“节目”、“条目”的术语词汇,由于其成词之数是“八”,相对于“纲领”之有“三”,因此亦可以对称之而为“三纲领”、“八条目”或“三纲”、“八目”。其中“汉魏以来,朱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所论则正好针对上了《礼记》中的郑玄之注、孔颖达之正义,在郑玄与孔颖达那里,是没有这一组成对的术语概念的。
《大学》中本文之破题在“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朱子释之为“大人之学”。“大人之学”的“大人”并非先秦古文的“君”之义,而系指成人成圣的“大人之学”。而如何能成其为“大人之学”的“大学之道”,朱熹认为:《大学》本文在“道”下明白指示了三个“在”字,此即是“三纲领”!而在“三纲领”的经文之后,《大学》本文立即接以“八条目”之示。《大学或问》中,朱熹并且明言“八目”就是“三纲”的“条目”。则“大学之道”,其“纲”言“规模”,其“目”言“次序”,有阶有序,有等有第,因此,为学之次第,依朱熹的《大学章句》所指示,在于“八条目”,而“八条目”之始,则在于“格物致知”,这是朱熹认为汉魏儒者所未能发明的圣学之精义所在。
在理雅各的译书中,对于《大学》中的“纲领”、“条目”,也一开始就在译注中特别提出来:对于“纲领”,理雅各的译词是“the heads”;对于“条目”,理雅各的译词是“the particulars”;《大学》本文中的三个“在”,指示出了朱熹的“三纲领”,对于本文中的“在”,理雅各的译词是“is in”*James Legge, The Great Learning,356.。
(三)“经、传之分”与“作者/述者”问题
在《大学章句》中的另一个必须要注意之处,便是朱子对于《大学》一书所作的“经、传之分”。将《大学》区分为两大部分,是我们阅读朱熹《大学章句》文本时,所需留心者,这不仅与朱熹诠释《大学》的基础深相关联,也与“经、传”之作者/述者及其所构成的“道统”深相关联。首先,“三纲”与“八目”都出现在“经”,因此,三纲八目是孔子的遗言与遗文。其次,经的部分为孔子所述,曾子所记;传的部分则是曾子所述,门人所记。“传”的文本孰记之,在朱注部分未有明言,但在《或问》中却说得明白分了:门人是指子思!不仅如此,子思还以此一经传文本传授孟子。于是,《大学》一书便同时含括了四子,也造述出了一个源自孔子的道统与学统,它不仅是圣人孔子之遗书,也是“孔孟”之书,更是“孔曾思孟”的学统与道统之书!在《大学章句》中,朱熹曰: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
《大学或问》中则曰:
曰:子谓正经盖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何以知其然也?
曰:正经辞约而理备,言近而指远,非圣人不能及也。然以其无他左验,且意其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质。
至于传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与《中庸》、《孟子》者合,则知其成于曾氏门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无疑也。*朱熹撰,[日]友枝龙太郎解题:《大学或问》,第18页。
在朱熹的章句化之下,《大学》之本文中,有经,有传,有三纲领,有八条目,其所以支持朱熹如此为之的源头,却仍要溯至北宋的二程。对于经与传、纲与目的发明,以及用三与八之数词来作出强调的组合、序次,正是朱熹所以章句化《大学》的基础。于是,三个“纲领”、八个“条目”,便成了后世完全与《大学》联结在一起的“三纲”、“八目”。注释的影响已经诠释了本文,本文的阅读全然被注释所笼罩。朱熹所言汉唐儒者未闻有以此说《大学》者的自负,已经成为继承“孔孟圣学”的一家之言。

1.两人的改本均有三纲、八目的概念出现。在“《大学》改本史”上,以“三纲八目”作为《大学》一篇之主体结构,其首出首见者,应当便是二程的《大学》改本。
2.程明道的《大学》改本之结构形式为:三纲、三纲释文、八目、八目释文。而程伊川的《大学》改本之结构形式为:三纲、八目、格致释文、三纲释文、诚正修齐治平释文。
3.对于《大学》的改订,是否有经传之分,清人朱鹤龄以为确然,《大学》之分经、传,当始自程伊川*朱鹤龄:《与杨令若论大学补传书》,《愚庵小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5页。。若然,则朱熹的《大学章句》之有经、传,其源头便在程伊川。
4.在《伊川先生改定大学》中,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之下,伊川自注云“当作新”,可见伊川主张“三纲领”中的是“新民”。这亦影响《礼记·大学》篇中“汤之盘铭曰……无所不用其极”一段文字,自本来释“诚意”的脉络中,被抽出而视为是专释三纲领中的“新民”之专文。
5.既然二程改本均有提揭出“八目”的概念,则有关“格物、致知”两目也应当有释文,比较特殊的是程伊川改本中的“格致”释文,自其改本结构推之,伊川应当是以“子曰听讼”一节作为“格致传”的释文,此当与此传文之下有“此谓知本此谓之之至也”有关,故也。
朱熹显然是熟稔二程之改本的,尤其是对程颐的《大学改本》更是如此,《大学或问》中详细讨论二程改本的文字甚多,特别是对于程颐改本更是讨论的一个焦点,朱熹以问、答方式呈现他对程颐改本追随与否的情况。《大学或问》云:
曰:程子之改亲为新也,何所据?子之从之,何所考而必其然耶?

《大学或问》又云:
或问:“听讼”一章,郑本元在“止于信”之后“正心修身”之前,程子又进而置之经文之下,“此谓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从,而置之于此,何也?
曰:以传之结语考之,则其为释“本末”之义,可知矣。以经之本文乘之,则其当属于此,可见矣。二家之说,有未安者,故不得而从也。*朱熹撰,[日]友枝龙太郎解题:《大学或问》,第30页。
以上《大学或问》所述问、答二则,一从伊川改本之改“亲”为“新”,一则不从伊川改本之移“听讼章”于经文之下,而视为释经文“本末”之传文;凡此,皆可见朱熹之作《大学章句》,成其“朱子改本”,虽曰新意,然实有所承,依然有一个历史的脉络,是故,朱熹的“章句化”《大学》,便可被视为一“经学史”的事件而寻其源。
三、《礼记·大学》篇与郑玄的注释
(一)考订《礼记·大学》篇作者与年代的思想史意义
有关《礼记》中所收《大学》一篇的近代考订,可以分为两个面向,一是对于《大学》篇的年代考订,一是对于《大学》篇的作者考订。晚近以来,由于郭店儒简的出土,引发近代学人的关注,纷纷发表论文争立新说,《礼记·大学》的考订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类别,这批学者的论文有一个趋向,便是回归到孟学,上溯至孟子师门来重新检视《大学》篇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以致追随了朱熹的故说。其胜处在于有新出土文献作为合法驰骋的场域,任何观点都可以联系到这批新史料,只要言之成理,言之成说,但由于这些学者大都对宋明理学的背景不够熟悉,因此在确立考证文题时,对于究竟系《礼记·大学》篇还是《四书》本《大学》,往往便未能自觉。

先儒每谓:颜子殁,唯曾子一人传道之统,因传子思以及孟子。余曰:此影响之论也。*管志道:《子思亲承尼祖道统说》,《重订古本太学章句》,明万历丙午年(1606)管志道自序本,东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本,附录(此本为抄本,无页码)。
又曰:
孔子以六十八岁归鲁,至七十三岁而终,子思朝夕祖席旁者五年,此时之传道岂不真,而又待曾子续传之耶!*管志道:《子思亲承尼祖道统说》,《重订古本太学章句》,附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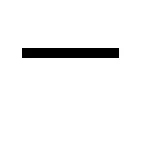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大学》、《中庸》,子思一人所作。……贾逵云:孔汲穷居于宋,惧圣人之学不明,而先王之道息,作《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王文禄:《大学石经古本序引》,王完编:《百陵学山》,《丛书集成初编》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3册。
郑晓《古言》亦云:

此即是明代著名的“子思经纬说”。笔者推测丰坊之所以要提出“子思经纬《学》、《庸》”的新说,不只是对朱熹“曾子录、授”说法的反驳,亦与丰坊对传统经学史上《礼记·中庸》作者为子思的认知有关。而《中庸》为子思所作,最早见之于司马迁的《史记》,犹在汉宣帝时期戴德、戴圣辑大、小《礼记》事件之前。《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生鲤,字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台北:宏业书局,1987年,第747页。
张守节《史记正义》注云:
《中庸》一卷,在《礼记》中。又作《子思子》八卷。*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747页。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儒家类”下亦载:
《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
《曾子》十八篇。名参,孔子弟子。
《漆雕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后。
《宓子》十六篇。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
《景子》三篇。说宓子语,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名硕,陈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公孙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34页。
由刘向、歆以来迄班固对先秦诸子中儒家所著录书的排列,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属于孔子亲授的门人七十子之流,或七十子所传而属孔门之再传、三传弟子,皆有作、述篇籍于汉代犹存而被载录入《汉书·艺文志》中者。更重要的是,作为朱熹所言的《大学》“经”之述者曾子、“传”之受者子思,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中,亦皆有著述传世于汉代犹存焉:《曾子》有十八篇、《子思》为二十三篇。于是,我们很难说朱熹的考订《大学》之“作者”与“述者”是全无根据的无稽之考察。同样,丰坊造说“子思经纬《学》、《庸》”及管志道造说“子思亲承尼祖”,我们亦很难说这样的造说是没有考订依据与史源的,特别是我们将之与近代学人之重启对《礼记·大学》篇作者的考订作出联系时,便会发现近代学人对《大学》篇的考订也是在孟学、荀学间打转,或是将其年代设定在战国时代的儒家后学,其史源的最早依据,不也是《汉书·艺文志》么!正是对近代学人的考订《大学》篇之作者作了历史的纵向观察,我们才能看清何以近代学人所考订的对象皆为“《大学》篇”,而非“《大学》书”,同时也更可看出近代学人的脉络,其实仍来自于清代学术中“汉学式”、“反朱子”的学术动向,而返回汉代《礼记》中寻思、考订、重读《大学》篇,正是清代“汉学”的特色,近代学人便系承继了此一动向,由清代而迄于民国甚至当代。一旦我们将近代学人的考订寻其更早的历史脉络之渊源时,不仅必须落点于丰坊、管志道的“子思说”,抑且,更应当溯至源头之所,即朱熹有关《大学》“经/传”的作、述、授、传之考订说。
是故,正是立基于此,丰坊遂得造说《大学》亦为子思所撰。管志道的《子思亲承尼祖道统说》显然便是在此一脉络下,继承丰坊而进一步“考订”之造说。管志道提出之新说观点,可以分两方面言之:一是以子思为《大学》作者,明系针对于朱熹,但其说仍然在北宋二程的“孔氏之遗书”的影响下立论;二是就近代学人们的考订《大学》作者而作出“明人之说与近代学人之说”的联系。就前者言,笔者谓管志道的观点针对朱熹,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明代对其近代朱熹之说的反弹”。管志道所论,不啻在提出一种“孔子家学”的观点,谓孔门之学的文本若在《学》、《庸》,则此传当传在血缘性关系中,亦即传于“其孙子思”,而非传于“曾子门人”。依管志道所论,则孔子居家,晚年授学,系在“鲁城城内”的家居之所,故子思常得侍于其祖。管氏此说与朱熹所云传于曾子说最大的不同,不仅是在于孔门圣学之所传,究竟传在血统亲缘还是传在非血缘的异姓弟子门人之别,同时,也将孔子与孔门的授学场域,移转到了位在鲁城城内的孔府之中。但孔子授学与孔门弟子来学的场所,实在“鲁城城外”筑庐舍以安弟子门人之处,亦是子贡守庐三年之处。管志道的《子思亲承尼祖道统说》将“子思”的双重角色朝向“孔子孙”而非“曾子弟子”方向移动,使得其说成了“孔氏家学”而非“孔门之学”!此一说法未免对于程朱与陆王的重视“学统之传”、“道统之传”中的师徒授受造述之心,有所轻忽!
就近代学人之考订《大学》作者而言,管志道以子思为《大学》之作者的大胆性以及其所提出的证据,恐怕较诸近代学人的考订,不遑多让,但在近代学人与朱熹之间,尚有许多明代人的著作考订篇章,包括丰坊的伪魏三体石经本在内,也都不妨视同与近代学人一样,皆系针对朱熹的观点而发。如此,“《礼记·大学》/《四书》本《大学》研究史”的内在延续性是否因此便被抽去了中间的一段呢?近代学人的事业与南宋的朱熹“之间”,于是产生了因为被忽略而来的一段空白,空白本不是空白,只是因为未曾衔接!
现在,笔者追问的是:为什么郑玄在注《礼记》时,没有对《大学》篇的作者有其敏感度,没有讨论《大学》篇的作者问题呢?郑玄的“没有考订”显然并不是郑玄的学问出了什么问题。笔者提出这一追问,只是想经由一种对比,凸显出另一时代的学问特色,并不一定是在于“作者是谁”上;反之,近代以降的学人之考订《大学》篇的作者,反映的也未必是先秦时代或是汉代学人的治学特色,而可能只是自身对于新史料、新视野、新方法的迫切性,迫切性下的议题寻找,尾随的仍是宋明理学大叙事框架内的朱子建构“作者/述者”的课题,近代学人本欲承接清代汉学之新考订,结果自身仍然接续了宋学的后段议题而不自知!
孔颖达于《礼记》之大题“礼记”下,疏云:
《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没后,七十二(子)*阮元:《礼记注疏·校勘记》云:“惠栋校宋本有‘子’字,此本‘子’字脱,闽、监、毛本同,卫氏《集说》亦作‘七十二子之徒’。”参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一,《阮元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25页。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参见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一,第11页。
因此,重要的是,古人本有一种认知,认为《礼记》便是有关于《礼》之释记,这种解释“礼”的文体成文,称之为“记”,本出自孔门,由孔子授受,经七十子之徒而递传,遂成儒家者流的一项专业;这便是古人,特别是汉代迄唐人对于“礼记”的属性及其如何从“孔氏”开始而传递下来的基本认知。
(二)郑玄注本的诠释要义
1.郑玄《注》与版本
(大)旧音泰,刘直带反。文公云:今读如字。
(亲)程子云:当作新。*郑玄:《礼记郑注》卷十九,台北:新兴书局,1971年影印校相台岳氏刊本,第212页。
显然,在上引两条郑玄注文中,新兴书局所据的南宋相台岳氏刊本,竟羼入了不应出现的文字,其一是“文公云”及其以下,其二是“程子云”及其以下,此当是明人覆刻相台岳氏刊本时所擅自羼入,要之此必后来者所为,非相台岳珂所刊之旧。然新兴书局所刊行的黄色封面之十三经各本,在台湾学界流传颇广,具有一定之阅读量及影响,但至少就《礼记·大学》篇之郑玄《注》而言,此本实不可据。
另外,台北的学海出版社所刊题为“宋绍熙建安余氏万卷楼校刊本”的《礼记郑注附释音》,则是经注本中之善者。其所据印者,乃是1937年的求青阁影印本。此本共别为二十卷,每卷之后皆有“校记”,末附《王苍虬跋》、《王大隆跋》、《杨彭龄跋》*郑玄:《礼记郑注附释音》,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建安余氏刊本。。据《王苍虬跋》文所云:
此宋余仁仲万卷堂刊《礼记郑注附释音》二十卷,每半叶十一行、行大十九字、小二十七字,白口双鱼尾,上鱼尾上间有数字,细鱼尾下记叶数,每卷后记经注、音义字数及余氏刊于万卷堂余仁仲刊于家塾仁仲比校讫等字样。*郑玄:《礼记郑注附释音》,第861页。
跋文又云:
岳倦翁九经三传沿革例谓:九经有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称为善本,廖氏世彩堂更合诸本参订版行,倦翁复据廖本采唐石经以次二十三本反复参订,刻梓家塾,即所谓相台本。是岳本源出余本,多经刊正,宜为传世经籍最佳者。然以此礼记本与岳本对勘,多有岳本误而此不误者。*郑玄:《礼记郑注附释音》,第861页。
相台岳本为世所传九经刻本中号为善本者,传世亦广,然据王苍虬跋文所云,可知王氏对此本之评价,是知此本犹在相台岳氏本之先且为其源底本一据。建安余本《礼记郑注》之《大学》,系编次于卷十九中,其大题为“大学第四十二”,下附双行小字,曰:
陆曰:郑云“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再下则题“郑氏注”三字。遂即接以经文,经文皆大字,注文与释音则双行小字,如王氏跋文所云。经文“则近道矣”之下,郑玄所注云:
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止,犹自处也。得,谓得事之宜也。*郑玄:《礼记郑注附释音》,第792页。
又云:
大,旧音泰,刘直带反。近,附近之近。*郑玄:《礼记郑注附释音》,第861页。
相较于明覆刊之相台岳氏本,最可勘见明覆刻本已羼入朱注。
本文于本节所据,则仍以阮元所刻附《校勘记》的《礼记注疏》为主,一者阮刻本为清人在返汉意识下所刻之《礼记》最有代表性者,二者则阮刻本有孔颖达之《正义》疏文,而建安余氏刊本则无。以阮元本为据,俾以诠释郑玄所注的《礼记·大学》之义,同时,下文所云之郑玄《注》要义,仍须以朱熹《大学章句》为对象比较,将视野移动于汉、宋之间,以诠郑玄所注、孔颖达所疏之《礼记》本《大学》初义。
2.郑玄《注》与阅读
清人陈澧于《东塾读书记》中,以为《礼记》之四十九篇应当以“分类”方式来阅读,并举孔颖达所引郑玄《三礼目录》为据,言郑玄《目录》引据所云“此于《别录》属某某”者,知“礼之记”有“分类”,当始于刘向,而郑玄从之,孔颖达引之。则刘向时校雠诸《记》之文共二百一十四篇,已有订其篇属性的分类之举;然则大戴之纂集《大戴记》是否亦如此,小戴之更为减删为四十九篇,而成《小戴记》,是否亦有所据之理,其理则与分类意识有关?要之,清儒陈澧发此意,并提出读《礼记》之法,谓当循孔颖达《疏》、郑玄《目录》、刘向《别录》,从“礼”的“分类”切入来作“阅读”的依循策略,其有功于今本《礼记》也无疑!陈澧云:

若然,则据陈氏疏理,《王制》、《礼器》、《深衣》属“制度”,《月令》、《明堂位》,《别录》属“明堂阴阳记”,陈氏谓亦是“制度”之属,《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别录》皆属“丧服”,此最可见今本《礼记》之重“丧制”也。《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别录》则属“祭祀”,《坊记》、《表记》、《缁衣》、《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学记》、《中庸》、《大学》等,《别录》皆属“通论”。是则吾人所欲论之《大学》并朱子抽取之《中庸》,于刘向,于郑玄,于孔颖达,其视《礼记·大学》,盖属于“礼学”之“通论类”。由孔颖达对此分类情况的保存及陈澧的发明,我们得知了郑玄对于《礼记》是有“分类”意识及阅读途径的,这与朱子的“以慧眼抽取”且置于“入道之始”的阅读意识,显然是不同的。
近代日本京都学派学人武内义雄尝撰文考略大、小戴《礼记》,曰《两戴记考》,其中复引陈澧之说而更为扩充,并整理出今本《礼记》四十九篇在刘向《别录》中分类属性,其文云:
陈澧《东塾读书记》谓“《礼记》当从刘向《别录》之法,分类而读”。刘向聚《礼记》四十九篇,分作十门:曰制度、曰明堂阴阳、曰世子法、曰子法、曰丧服、曰祭祀、曰吉礼、曰吉事、曰乐记、曰通论是也。其中自制度至乐记九门,皆礼学专家之记,异于一般儒家之著述。吾人得补儒家著述之阙者,皆属通论一门。刘氏列于通论者,为《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等十六篇。*[日]武内义雄:《两戴记考》,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第175页。
由武内氏所云可知,其将“礼学专家”与“一般儒家”作了区别,这显然是误将元明以下史志艺文著述中的分类意识,也是受到《宋史》中别《儒林》与《道学》传经、传道之区别所误,早期儒家者,本以来自孔门之礼乐《诗》、《书》之学为宗,焉有所谓“礼学专门之学”可以别于“一般儒家著述”外之说法,武内氏此一认知意识显然有所误解也。

皮锡瑞于《经学通论》中对于陈澧所提倡的“分类而读”《礼记》,亦深表赞同,惟其推尊郑玄门人魏孙炎,又盛称唐魏征,则与陈澧有异耳。其此论之标题为“论礼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征之书不传”,云:
《礼记》四十九篇,众手撰集,本非出自一人,一篇之中,杂采成书……故郑君门人孙炎已有《类钞》,而书不传;魏征因之以作《类礼》,而书亦不传。……锡瑞案,戴《记》不废,张说有存古之功;《类礼》不传,说亦有泥古之失。当时若新旧并行,未为不可。朱子惜《类礼》不复见,是以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吴澄作《礼记纂言》,更易次序,更以类从;近人惩于宋儒之割裂圣经,痛诋吴澄,并疑《通解》之杂合经传。平心而论,《礼记》非圣人手定,与《易》、《书》、《诗》、《春秋》不同,且《礼经》十七篇,已有附记,《礼记》文多不次,初学苦其难通,《曲礼》一篇,即其明证。若加分别部居,自可事半功倍。据《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则其书唐初尚存。炎学出郑门,必有依据,魏征因之,更加整比,若书尚在,当远胜于《经传通解》、《礼记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学矣。*皮锡瑞:《三礼》,《经学通论》,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第72页。
如此,在“分类而读”意识下属于“通论”类别的《大学》篇,郑玄又是如何来看待此篇的功效呢?先儒亦有引于郑玄之言者,曰“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据陆德明《经典释文》与孔颖达《疏》文,均引此而曰郑玄之言。陆德明曰:
陆曰:“郑云‘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四,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第220页。
孔颖达则疏曰:
正义曰:“郑《目录》云:‘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3页。
何以郑玄云《大学》此篇之总义在“博学为政”?笔者认为,这要与《礼记·经解》之疏文一起参看,孔颖达于此篇题下疏云:
正义曰:“郑《目录》云: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义政教之得失也。此于《别录》属通论。”*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十,第845页。
陆德明《经典释文》亦云:
郑云:“《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得失。”*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三,第209页。
将陆氏《释文》与孔氏《正义》两相比较,可以发现《释文》均无“名曰”二字,尤其无“此于《别录》属某某”之文,而孔氏《正义》则有之,此则牵涉后人考据郑玄《三礼目录》、刘向《别录》对《礼记》诸“记”之分类观点所据处。《经解》一篇之解题,则陆德明《释文》作“六艺政教”而孔颖达《疏》作“六义政教”,当以陆德明之“六艺”为是,盖班书《艺文志》即以“六经”称“六艺”,此盖汉时复古之旧名而以之称新名也,故即以“古六艺”称孔子所传之“新六经”,一示其王官学为法周复古,一示其王官学为尊孔所传诸经。班固《汉书·儒林传》云:“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何以需“博学六艺”?班固又云:“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是“博学乎六艺之文”,其目的即在“致王教至治”,故曰“博学可以为政”。孔颖达《疏》文释《经解》篇何以入于“礼”类之故,云:
正义曰:“《经解》一篇,总是孔子之言,记者录之。以为《经解》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体教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记者录入于礼。”*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五十,第845页。
则于彼朱子曰理学、曰道学,于郑玄、孔颖达则曰礼学。陈澧则并尊之,云理学即是礼学,反之则礼学即是理学。然礼、理以释《礼记·大学》或《四书》本《大学》之首句“大学之道”,两者之视野与路径及立足点,必有其异同,在这个有异同的立足点及其视野下的文本及章句、训义之阅读,亦有其文本世界观的整体、部分之异同,是故双方在阅读或是解释首句的“大学之道”时,所引发的阅读体知感受亦自有其异同。之所以将《经解》之篇收入《礼记》,是因为作为总析“六艺五经”的《经解》,其根本当在于“礼”,所以将此篇入于“礼类”之中。同样,如果《大学》之篇是对中央层级的“太学”之所学作出“总类式”的篇属定位,则“太学”所学为“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事亦总以“礼”为本,自然《大学》之篇是应当入于“礼类”了。“通论”有着相当于今日“图书目录学”上的“总类”之意,但更有著作为“总论五经”、“总论六艺”的“通论总义”之归类意涵。因此,对郑玄而言,“以礼为本”视野中的“博学”,便与后世宋明理学中“以理(心)为本”的“博学”之义不同。“以礼为本”下的“大学”与“大学之道”,便是《大学》中所述“止于至善”的关怀,而如何可以自“治国者/为人君”的位阶达到此一关怀理想之道的实践,郑玄的理解系认为必须要自“大学如何可以博学为政”来思考。对郑玄而言,“为政”是指治国治天下,“大学”是指“学宫”,故是一专门教授世子学习“为人君/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之场所,其所学即是在天子、诸侯之“博学可以为政”。“博学”是由为人君的位阶向外推拓,期能将明明德外推外治时达于“止于至善”之目标,然此尚不能有“本”,尚不能明作为“为人君”位阶上的“明德”如何才能够与外推的“至善/天下”相联系且互为保证,故阐释其“本”,作为其“本”者当然是“礼”,但作为其本的“礼”,又是什么呢?于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语言便交待了惟有人君之自能“明明德”,才能为民之典范,而风化天下,令天下归一。要之,在“为人君”的位阶上者,必须要先要求自己,先自自己做起,方能外推于天下,这也就是“太学”所以要教导世子在此所学习的。
从孔颖达来说,只谈“修身为本”的实践法够吗?比“修身为本”更为先行可为根柢的,孔氏认为,是“诚意为始”。是故言博学,言明明德,必须归约于“诚意”,惟诚意方可以使博学有所践履得其德功。
3.孔颖达《疏》文以“三在”为“三事”
无论是郑玄注的《礼记》本《大学》篇,还是朱熹注的《四书》本《大学章句》,两种文本的本文之首句,皆是: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3页。
除去内容性的“亲”抑或“新”不论,就两部文本的本文首句而视之,两者在语言结构上,同有三个“在”字,并由此带出所谓“大学之道”的“三在”。对于此“三在”与“大学之道”的关系,郑玄并未下注,而仅仅是在“则近道矣”之下,注曰:
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止犹自处也。德谓得事之宜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3页。
由此,可知郑玄于注中不仅未显示其有朱熹所谓的“三纲领”之概念,即便是作为《大学》篇本文结构所出现的“三”个“在”字,郑玄也并未特别予以重视其“在”之为“三”的语义。
倒是在孔颖达的《正义》中,将《大学》篇本文的三个“在”句,作了一番义疏,且称其为“三事”。孔颖达《正义》疏曰:
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此其一也;在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是其二也;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学之道,在于此三事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4页。
并总论此“三在”、“三事”云:
此经大学之道在明明得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积德而行,则近于道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4页。
是故世子于“大学”所学,当以己身之明德为本,彰明己德于行,则能爱民,能行于天下,此正孔氏于篇题所疏者:“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德于天下。然欲己身之有明德,则身修必自诚意为始,方能止处于至善,推本而行于天下,故君子必慎其独。”
4.郑玄《注》、孔颖达《疏》本无“八目”但以“诚意”为“知本”
在郑玄《注》、孔颖达《疏》中,没有朱熹于《大学章句》之“经”中所揭出的“八条目”之概念及其成词。郑玄在《礼记·大学》篇本文“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之下,注曰:
知谓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3页。
而在本文“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下句“致知在格物”下,郑玄则仍本上句以“知善恶吉凶”之“知”为说,谓此句之义为“知事之善恶”且“知深则善深”。郑玄注云:
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3页。
是故郑玄意谓“致知”当须“至知”,故“致知在格物”或当为“至知在格物”,而“致知”则在能知善恶,能知善恶则可以“至知”,一旦“至知”则“事之善恶缘人所好而来”。《礼记·大学》本文虽有“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但郑玄显然不认为“致知”当成一词,只有“至知”能成其词,是故《大学》本文在反说之文中亦只有物格,只有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同时,对于朱熹于《大学章句》的“经”中所强调的“三纲领”与“八条目”之概念,我们在郑玄的注释中,是完全领会不到的。能够领会到的乃是郑玄对于“至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训解,完全在于知善、行善,乃至于止于至善的主轴上。而这一切的根本,都是在于“诚其意”。是故郑玄同时亦将“知本”之“本”训作“诚其意”。特别是经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的章句,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系将之作为释《大学》经文“物有本末”的“本末”之“传”*朱熹云:“右传之四章,释本末。”并云:“此章旧本误在‘止于信’下”。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6页。,而郑玄将“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完全视作对于“诚意”的释词:
情犹实也。无实者多虚诞之辞,圣人之听讼与人同耳,必使民无实者,不敢尽其辞,大畏其心志,使诚其意,不敢讼。*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6页。
尤其是在本文“此谓知本”下,郑玄则以为只是接续“子曰听讼”一段申释“诚意”之义,系《礼记·大学》本文中专释诚意之章句的总结,故经文“此谓知本”,郑玄注曰:
本,谓诚其意也。
孔颖达疏云:
此谓知本者,此从上“所谓诚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诚意之事。意为行本,既精诚其意,是晓知其本,故云“此谓知本”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8页。
又云:
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言圣人不惟自诚己意,亦服民使诚意也。孔子称断狱犹如常人,无以异也,言吾与常人同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8页。
由此,更可证郑玄《注》与孔颖达《疏》,两者皆无所谓“八目”之“八”义在。经文“此谓知本”与其上“子曰听讼”一节的衔接,在郑玄、在孔颖达看来均极为合理,且均在申释“诚意”之事。经文所欲反复申说者,只在如何透过以诚意为本,而使之能正心能修身能齐家能治国与平天下。是故就本篇经文“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以及“至知在格物”两句而言,实无所谓“格物”与“致知”之“两目”,而亦不能成其为“两目”。
《大学》篇本文另一个“此谓知本”,系连读“此谓知之至”也而出现于经文“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之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对于朱熹而言,他的《大学章句》之经文便系止于“未之有也”处,而对于其下的一句“此谓知本”,则从程颐之说:“程子曰:衍文也。”*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6页。并保留下句“此谓知之至也”作为其自撰的《格致补传》之结句,故其注云:“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6页。因有阙文,故作补传,补传之结语二句为:“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7页。朱熹并云:“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6页。又自注曰:“此章旧本通下章,误在经文之下。”*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6页。对此,朱熹《大学或问》中有更详尽的解说:
或问:“此谓知本”,其一为听讼章之结语,则闻命矣,其一郑本元在经文之后,“此谓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为衍文,何也?*朱熹撰,[日]友枝龙太郎解题:《大学或问》,第31页。
盖朱子自设之问,亦是注意到了《大学》本文中原有两个“此谓知本”,为何郑玄不以为有衍文,可以成其解释,朱子却从程子认为是衍文呢?对于朱子取以为“格致补传”结语的“此谓知之至也”,《大学或问》中亦有其问:
然则子何以知其为释“知至”之结语,又知其上之当有阙文也?*朱熹撰,[日]友枝龙太郎解题:《大学或问》,第32页。
对此问,朱熹则答:
以文义与下文推之,而知其释“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为结语也;以传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阙文也。*朱熹撰,[日]友枝龙太郎解题:《大学或问》,第32页。
在朱熹的《格致补传》传文中,有一句极为重要,亦与朱熹成立“八条目”之序有关者,即:“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对于“格物”、“致知”必须在“诚意”之先的观点的论证和发挥,《大学或问》中之“再问”,亦触及此处:
此经之序,自诚意以下,其义明而传悉矣。独其所谓格物致知者,字义不明,而传复阙焉,且为最初用力之地,而无复上文之语绪之可寻也。子乃自谓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则程子之言,何以见其必合于经意?而子之言,又似不尽出于程子,何耶?*朱熹撰,[日]友枝龙太郎解题:《大学或问》,第32页。
《大学或问》之所问,其实已经道出了其所欲回答的要点所在:何以自朱熹的角度,郑本《大学》只有诚意以下有“所谓”的句法,而独于格物致知无此句式出现?如是,导致《大学》篇本义的蒙昧不清,尤其至为关键处有二:一是阙了传文,一是少了对“格物致知”的阐义,遂致《大学》“八目”之首二目不明,大学之始教与最初用力之地亦不能明。
有意思的是,朱熹在《大学或问》中的设问,却并非郑玄与孔颖达看待《大学》篇的焦点,郑玄与孔颖达显然既不认为《大学》篇本文中有两个“此谓知本”是个问题,也不认为在“大学之始教”有个所谓“在诚意之前”的问题。自朱熹以下迄于元明两代,两个“此谓知本”历来号称难解,难解之故即在于自程子、朱子以来即以为此句之上或有阙文,或为衍文,故朱熹自作《格致补传》以补之。朱熹此举,遂更启南宋董槐以下元明两代儒者有关“新格致传”的探讨。但对于郑玄而言,《大学》篇之本文于“未之有也”之下接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是极为明白的章句,无需训解,是故郑玄仅对“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何谓“壹是”而下注,曰:“壹是,专行是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3页。故知郑玄仅欲对何谓“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作注,则此一“此谓知本”之“本”,即指经文“修身为本”为言。“修身为本”与“诚意为本”,两者各有所重。经文之意,由一人之身以至天下人之身,皆同此“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治国平天下”既以“修身”为“知本”,则比“知修身为本”还要更根本的,便是在于“知诚意为本”,故经文随即在“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之下接以释“诚意”之本文,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则经文之意,当在使受教者受学者能明惟毋自欺方能诚其意,若能诚意,则身自修矣。云“诚其意”之功与“此谓知本”之关系,则以能知能明善恶,方能行道为善,若知善愈深则能使来事成其善也深,善益深则恶益浅,故曰止于至善。孔颖达《正义》云: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本乱谓身不修也。末治谓国家治也。言己身既不修,而望家国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4页。
《正义》又云: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者。本谓身也。既以身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极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4页。
然则,除了以《大学》本文的阅读来作阅读者的“自证”,证明在《大学》篇本文中有两个“知本”,而以“诚意”为本的“知本”,较诸以“修身”为本的“知本”,是一个“诚意为修身之本”的语意诠释,我们如何能证明此“自证式”的“阅读”?若然人人皆以“自证式”阅读来读本文,则朱熹果然便能在不同时代与背景下重读出不同的“三纲八目”脉络?对此,笔者以为,孔颖达在《大学》之篇题下的疏文解题,很可以视作是对《大学》总篇旨的阅读,《正义》云:
此《大学》之篇,论学成之事,能治其国,章明其德于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从诚意为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3页。
依此,孔颖达《正义》在两个“此谓知本”经文的比较上,已经作出了“诚意为始”的解读。在两个“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之间的《大学》篇本文,皆是阐明“诚意”之经文,故孔颖达《正义》:
所谓诚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谓知本,广明诚意之事。*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4页。
不仅是“诚意为始”,而亦更是“诚意为本”。在孔颖达视域中的《大学》篇本文结构,确然并无后世所谓的“八条目”。虽然《大学》篇经文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然后接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直至“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之后便反之复说“物格而后知至”,继接以“知至而后意诚”,直至“国治而后天下平”,然而,上句主旨在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下句主旨则在言“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上句言“明明德于天下者”,其结语在于“致知在格物”,依郑玄《注》,则实应为“至知在格物”,仍须结穴于“致其知”与“至知”,而归本于“知善恶”,下句则结穴于“修身”为本,故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作结。上言之“致其知”与“至知在格物”,与行其事有关;下言之“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依郑玄《注》,“壹是,专行是也”,亦言其行事。是故经文于反说既毕,遂即接以“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这是在《大学》篇本文中首度出现的“所谓”之句法。在《大学》篇经文中,共有五次出现此句法之形式,继“所谓诚其意者”之后,分别是“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在正心与诚意之间,并未以“所谓正其心在诚其意者”之“所谓”句式来联结,在诚意与致知之间,亦无“所谓成其意在致其知者”之句式,而且在五句的“所谓”之句式中,唯有“诚意”是以“所谓诚其意者”的单说方式来提揭“诚意”,与其他四句系联结两者关系的句法不同。可见,对于《大学》篇本文而言,在提出第一个“知本”为“以修身为本”之后,接着便是阐说何以“诚意”是第二个“知本”,以及何以“以诚意为本”是“以修身为本”之本。
孔颖达《正义》又云何以“慎独”为“诚意之本”,其曰:
所谓诚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谓知本,广明诚意之事。此一节明诚意之本,先须慎其独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六十,第984页。
孔颖达所谓“此一节明诚意之本,先须慎其独也”,其义则在“广明诚意之事”的大段大章之诸节经文中,阐明经文何以须言诚意以慎独为本之义。然堪注意者,为孔颖达所言诚意之本须先慎独,只能于诚意系统内言说,而不能就整个《大学》篇来作总题之提揭,其原因在于慎独与“此谓知本”并无联系,是故孔颖达在篇题之下只作“从诚意为始”的提揭。
四、结论
不可否认,学者要在今天研究《大学章句》,难免会受到朱熹的影响,包括他所建构的“三纲”、“八目”、“经传之分”、“格致补传”、“作者与道统”、“入德之门”等等,笔者亦然。笔者以“两种文本”为题,已经反映了此点。如何研究朱子的《四书》本《大学》以及郑玄注的《礼记》本《大学》,是一个比较进路下的课题。笔者在本文中已经尝试着将几个对照的聚焦比较出来,这样的比较虽然系在“后朱子时代的思考框架与视野”中完成,但笔者认为,通过“朱子如何”以看待“郑玄没有如何”或是“郑玄的特色为何”,未始不是一个研究郑玄传下的《礼记》本《大学》的一条途径,同时,本文的若干对比,也可以将过去学者在《礼记》本《大学》研究上的不足,作出阙页的填补。以下便是笔者的结论条列,试图以清楚简洁的文字,再度作一次表述:
对朱子而言,“大学”是一本书,郑玄则视为一篇文章。朱熹释“大学”为“大人之学”,“大”读音为如字;郑玄释“大学”为“太学”,“大”读音为“泰”。前者指学问,后者指学宫。
对早期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言,翻译此书时是追随朱熹的观点,译名的取向以“Learning”为主,几乎没有翻译为地点或是场所的。理雅各将《大学》的书名译作TheGreatLearning,在理雅各之前的英国伦敦会会士马士曼,将首句“大学之道”译作“The path or course of Learning proper for Men”。理雅各将《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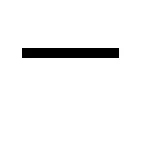
显然理雅各也是追随了朱熹,用的不是“亲民”而是“新民”。
朱熹关注的是《大学》的作者问题,“经、传之分”也是从此思考而出现的章句做法。郑玄与孔颖达关注的是“从戴德到戴圣”的编者问题,从《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三礼目录》到《隋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一种书目线索。清代人讨论的“辑佚学”,因为许多书在孔颖达时仍能见到,所以有它的局限,不可尽信。
近代学人讨论到《四书》本《大学》或《礼记》本《大学》篇的作者与成书/成篇年代,包括使用郭店竹简文献时,都已受到朱熹的影响而不自知。尤其是丰坊的“颜渊说”、管志道的《子思亲承尼祖道统说》,都被近代学人所忽略。
朱熹死后朱门出现了“读书之序”与“入道之序”的分歧,笔者称之为“黄、陈之歧”。黄幹站在朱子的立场,仍以《大学》作为“入德之门”;而陈淳则站在“后朱子时代”的视野,意图将朱熹、吕祖谦(元明以来的《近思录》只题作朱子编)的《近思录》也纳入到“入道之序”中,使得《近思录》成为学子应读的第一本书。陈淳的依据在于《朱子语类》中的一条“记言”之“文”,而黄幹则否定“听到”的可信度,认为仍应当以朱熹亲笔之文才为可信。“黄陈之歧”不仅是《大学》与《近思录》孰先孰后的分歧,也是相信朱熹之“言”还是相信朱熹之“文”的分歧。
朱熹提出的三纲领,在孔颖达那里只称为“三在”,“三”的数字是相同之处。朱熹提出的八条目,在郑玄那里是不成立的概念。因为,郑玄与孔颖达都主张以“诚意为本”,以“诚意为始”。《大学》篇本文中的两个“此谓知本”,郑玄与孔颖达都认为第一个“知本”是“以修身为本”,而第二个“此谓知本”则是阐说何以“诚意”是第二个“知本”的“本”,以及何以“以诚意为本”是“以修身为本”之本。
孔颖达在《礼记·大学》之篇题下的疏文解题,可以视为对《大学》总篇旨的阅读。据前分析,孔颖达《正义》在两个“此谓知本”经文的比较上,已经作出了“诚意为始”的解读。孔颖达疏云:“所谓诚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谓知本,广明诚意之事。”这不仅是“诚意为始”,而且是“诚意为本”。在孔颖达视域中的《大学》篇本文结构,确然并无后世所谓的“八条目”。
对郑玄而言,他只承认有“致其知”、“至知”,不同意有“致知”这一词,所以他注“致知在格物”为“至知在格物”。郑玄认为在“太学”中所学的是一种“博学可以为政”之“学”,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反映的正是戴圣编辑《礼记》的理想:以礼治国。这也是郑玄在《三礼目录》中将《大学》篇分类为“通论”的原因。
[责任编辑李梅]
作者简介:李纪祥,台湾佛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宜兰),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山东曲阜 273100)。
——《四书释注》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