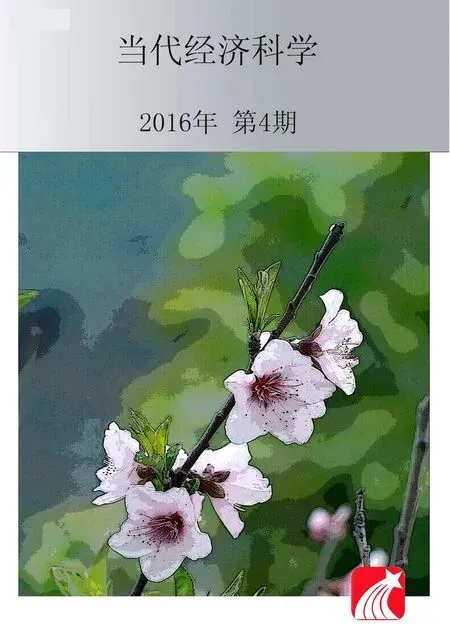回归医疗服务本质:从“医药分开”看医疗服务供给
王文娟 ,南孟哲
(1.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2.中央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北京 100081)
回归医疗服务本质:从“医药分开”看医疗服务供给
王文娟1,南孟哲2
(1.中央财经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2.中央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北京 100081)
本文在构建中介变量模型并实证分析“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影响的基础上,研究了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医疗服务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源自两个分离:一是医方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离;二是需求者与支付者角色的分离。前者解释了效率不高的问题,后者解释了费用较高的问题。进一步研究表明,优化医疗服务供给亟需回归医疗服务本质:把握关键要素,将改善医院和医生收入作为突破口;树立正确导向,将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作为长久之策;平衡各方利益,将财政补贴作为医药分开的主要手段;扫除制度障碍,逐步消除不合理的合约形式。
医疗服务本质;影响因素;医药分开;医疗服务供给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逐步改善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11次提到“公共服务”,并提出“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李克强总理为《经济学人》撰文,指出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之一。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强调“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增强政府职责,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一时间,“共享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社会政策托底”等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研究领域的关键词。
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服务供给在“十二五”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医疗卫生机构数较2010年末增加5.3万个,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229.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数增加215万人,增幅分别达到5.7%、47.9%和36.6%;重大疾病防控、国民健康行动计划、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持续推进;居民健康状况继续改善,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均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然而,这些举措与成就离“共享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一是医疗服务供给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激发的医疗服务需求,供求之间缺口巨大,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仍是医改的当务之急[1];二是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了医疗服务市场的混乱,改革需要把输出医疗资源的要素解放出来[2];三是公立医院改革仍是医改的重中之重,牵住公立医院这个牛鼻子,把医院创收的机制破除了,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3];四是改革涉及医院内部的利益结构调整,更涉及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变革[4]等等。针对这些延续性的问题,早在1997年国务院便开始主导“医药分开”;2002年国务院八部委联合发文,提出“解决当前存在的‘以药养医’问题”;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将破除“以药养医”作为关键环节,明确了“医药分开”的改革方向;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试点城市所有公立医院“医药分开”。那么,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解决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将通过考察“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来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剩余部分将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从理论上阐述“医药分开”、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方式,以及“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第三部分构建模型并实证分析“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第四部分总结并提出优化我国医疗服务供给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一)“医药分开”的本质与具体内容
“医药分开”的本质是从医院、医生两个层面切断其与药品之间的利益联系,做到公立医院利益与药品脱钩、医生利益与药品脱钩,公立医院不依靠药品收入来维持日常运行和发展,医生不从开具处方的药品中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5]。“医药分开”的具体内容包含取消药品加成和建立配套补偿机制,其中建立补偿机制包括增设医事服务费和增加财政补贴两个方面。因此,本文从取消药品加成、增设医事服务费、增加财政补贴三个方面讨论“医药分开”政策:一是医疗费用中药品所占比例过高是不争的事实,取消药品加成切断了医院药品销售收入的经济利益,对控制医疗费用无序上涨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二是取消挂号费、增设医事服务费,更加合理地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激励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三是取消药品加成对医疗机构收入带来一定影响,医院亟需补偿以保证服务质量,而增加财政补贴是改革试点中普遍采用的补偿措施。
(二)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及评价方式
影响医疗服务供给的因素主要包括投入产出因素、内部管理因素和外部政策因素[6]。投入产出因素上,郭晓日指出门诊人均费用、出院者人均医药费用与医院效率负相关,病床使用率、床日成本对医院效率有积极影响[7]。戴平生指出个人卫生支出比例的提高倾向于增加卫生技术人员数、医疗机构床位冗余值,可能造成更多卫生资源的浪费[8]。内部管理因素上,卞鹰等研究发现奖金制度、人员聘任、竞争上岗、全员目标责任制的实施对医院单元成本、住院日和DEA均有显著作用[6]。Yasar A. Ozcan等指出营利性护理院效率比非营利性护理院效率高,大规模护理院比小规模护理院效率更高,控制规模和所有权不变,政府补助医疗保险计划可以提高效率[9]。外部政策因素上,林皓等指出政府投入占医院总支出比重下降、无法补偿成本的情况下,医院行为会发生扭曲,片面追求自身财务利益最大化[10]。Shen Yu-Chu通过研究美国来自预付费制度(PPS)和卫生维护组织(HMO)带来的财政压力,发现财政压力对医疗质量有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和中期尤为明显[11]。Nikolaos Maniadakis等通过对英国90年代医疗内部市场化改革效果研究,指出内部市场化改革大大提升了医疗机构产能,但却以质量降低作为了代价,旨在创造动机提高医疗服务供给效率的政策只对效率产生一次作用,而难以产生稳定的长期效应[12]。
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评价方式,学界广泛地应用DEA和SFA方法。Sherman首先将DEA方法应用于医院效率的分析中[13],Wagstaff首先将SFA方法应用到健康医疗领域的效率测量中[14],两种方法随后被各个国家诸多学者广泛应用。但是DEA方法和SFA方法都只是对医疗服务供给技术效率的评价,即对医疗机构自身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评价,欠缺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可及性、充足度以及配置效率等综合的社会总效应的评价。Patrick M.Bernet从消费者视角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进行了随机前沿分析,使用DEA方法同时评价了医疗服务供给的技术效率和可及性,结果表明资源供给的可及性对社会总效应有正向作用[15]。Gary D. Ferrier通过研究样本医院费用效率、技术效率、分配效率和规模效率,指出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低下都将导致费用的增加,造成浪费[16]。事实上,卫生经济学一般选取四个效率评估指标:准入壁垒、技术效率、供给充足度、分配效率。准入壁垒指在接受医疗服务中遇到的障碍,比如价格、时间和交通因素;技术效率指在给定产出质量和数量的情况下以最小的费用来完成产出,一般用货币指标衡量;供给充足度指给定效率和质量要求,充足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可利用性,主要依赖财政补贴实现;配置效率指给定的资本和劳动是否投入到社会上最有价值的地方,即资源利用是否达到帕累托有效,准入壁垒和不充足的资源供给都会制约分配效率[17]。
(三)“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
“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给出了积极的评价。YJ CHOU等通过总结台湾“医药分开”改革经验,指出“医药分开”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药品支出并且影响医生开方行为[18]。宋杰等通过研究北京试行医药分开改革对医患双方的影响,指出门诊患者次均费用和次均药费均大幅下降,患者满意度提高,并且患者就医更加理性,专家号需求下降,专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19]。另一部分学者给出了更加审慎的评价。徐敢指出“医药分开”能直接产生使医院用药均衡数量下降的效果,但是对药品价格虚高并未产生直接的效果[20]。李大平在分析药价虚高成因时质疑“医药分开”的作用,指出供药方和医院的“变相协作”不能根本上切断医生处方与医生经济利益的关系,不能解决药价虚高[21]。蒋建华指出药品加成政策只是医疗费用高的表面原因,医疗费用高的真正原因是医疗系统的垄断,降低医疗费用必须采取放松政府管制、引进民间资本、维护医疗市场秩序等综合措施,政府取消医院药品加成政策、增加对医院的补贴、增设药事服务费的做法在降低医疗费用方面难以取得理想效果[22]。朱恒鹏指出不改革公立医院的行政管理体制,不解决医生的身份定位问题,无论是取消药品行政定价,还是提高医疗服务价格,都无法彻底解决药价高、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23]。
(四)医疗服务供给的优化路径
一是政府主导的路径,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财政补贴是促进医疗服务供给者与需求者有效交流的关键,消费由供给支付转为需求支付、由隐性合同转为显性合同、由服务付费转向风险分担支付都能够有效降低医疗费用[24]。曾雁冰指出加大政府对医疗服务的投入力度、提高业务收入收益率实现医疗费用的大幅度降低,可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25]。G.A.Melnick等通过对比加利福尼亚州与美国其他地区情况,指出政府规制的管理式医疗比竞争机制的管理更能够改善医疗服务供给和规范医生收入水平[26]。二是市场主导的路径,詹国彬、王雁红从英国NHS改革中得出启示,医疗服务供给中引入市场竞争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流趋势,应倡导医疗服务中的顾客导向,提升医疗服务的回应性并追求顾客满意[27]。陈钊等指出只有在医疗筹资市场化的同时实现医疗服务价格的市场化,才能彻底消除“以药养医”现象的同时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特别要在医生的收入决定中充分引入竞争机制[28]。三是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路径。周志忍指出政府责任市场化的倾向应予以校正,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大力度;没有管理制度和服务提供机制改革带来的微观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即使政府财政投入扩大数倍也不一定得到期望的结果,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29]。王延中、冯立果指出政府“甩包袱”的市场化改革只能解决“寡”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均”的问题,建议继续市场化改革,但政府必须鼓励医疗服务竞争、打击垄断、维护好市场秩序,并承担起公共卫生和最低层次基本医疗服务的责任[30]。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笔者认为:第一,当前对于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的总结,从而导致改革实践中难以抓住关键影响因素并对症下药;第二,对提升医疗服务供给效率的策略缺乏动态研究,无论是政府主导、市场主导或者是两者结合,都需要从动态的视角看,针对不同阶段不同情况应有具体的政策引导;第三,研究提出的观点缺乏针对性,部分研究指出提高政府补贴,却没有指明应该补贴给谁、以多大力度补贴;第四,缺少对医院收入和医生收入作用的研究,很多研究对医院收入和医生收入避而远之,然而理顺医院和医生收入是医改的关键所在,医院收入、医生收入问题不可回避。因此,本文将引入医院收入和医生收入作为中介变量,从充足度、可及性、技术效率、配置效率四个维度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进行系统地研究,揭示“医药分开”政策的传导机制,并结合我国医疗服务供给现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三、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如上文所述,为了揭示医院收入和医生收入在医药分开改革政策中的作用机制,本文参照Mark Pauly[31]、徐敢[20]等人的研究建立中介变量模型。用x1,x2,x3分别表示门诊次均药费,挂号费,财政卫生支出;m1,m2分别表示平均每所综合医院年收入和医师年人均收入;y1,y2,y3,y4分别表示卫生总费用占GDP百分比,总诊疗人数,门诊次均费用,病床使用率,依次建立回归方程并建立结构方程组:
yj=πij+cxi+εij(i=1,2,3;j=1,2,3,4)
(1)
mk=πik+axi+εik(i=1,2,3;k=1,2)
(2)
yj=πijk+c′xi+bmk+εijk(i=1,2,3;j=1,2,3,4;k=1,2)
(3)
在回归的基础上检验系数、构造soble统计量,判断y1,y2在结构方程组中的中介效应。
(二)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2—2012年为研究时间段,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研究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外生潜变量、内生潜变量以及观测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进一步对回归系数进行sobel检验,研究统一选取90%的置信度对模型各项假设进行检验。同时,本研究使用Amos17.0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与分析。图1显示的是医药分开三个维度分别对医院和医生收入影响的标准化系数,以及医院和医生收入分别对医疗服务供给四个效率维度影响的标准化系数。


图1 回归的标准化系数
1.医药分开对医院和医生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医药分开政策的三个构面对医院收入和医生收入均产生了显著正效应。其中,门诊次均药费产生的影响最大,而财政卫生支出产生的影响效应最小。这与我国“以药养医”和财政卫生补助不足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在没有实施“医药分开”政策的情况下,医院和医生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药品收入,其次是挂号费,最后是财政卫生支出。此外,门诊次均药费、挂号费、财政卫生支出对医院收入产生的影响比对医生收入产生的影响大,这反映了我国公立医院管办不分、医院收入捆绑医生收入的现象。由于门诊次均药费对医院收入产生的影响比对医生收入产生的影响大,医院因为取消药品加成受到的损失将比医生更大。同理,挂号费对医院和医生收入产生的影响比财政卫生支出产生的影响大,所以实施“医药分开”政策后,通过增设医事服务费补贴医院和医生收入会比卫生财政补贴更有效。
2.医院和医生收入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医院总收入和医师年人均收入分别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四个维度的度量指标都产生了显著正向效应。其中,医院收入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充足度的影响比医生收入更大,而医生收入在可及性、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三维度的影响比医院收入大。说明当前情况下,补贴医生比补贴医院更能够提升配置效率,但不利于增加总供给和控制费用。
3.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医药分开政策的三个构面分别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的四个构面产生了显著的间接正效应。具体而言,门诊次均药费、挂号费和财政卫生支出分别对医疗服务供给充足度、可及性、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均产生显著影响。医药分开政策通过医院和医生收入的中介作用,产生的最显著效应是总诊疗人数的变化,即改革最突出的效果是提升了可及性,“看病难”的问题将得以缓解。此外,综合考虑财政卫生补助对医院和医生收入的影响,医院和医生收入对医疗服务供给充足度影响的乘数效应,相比补助医生,补助医院将对医疗服务供给充足度产生更显著的效果。
4.医院和医生收入的中介效应。表1显示的是医院和医生收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医院和医生收入在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影响的部分维度下中介效应显著。医院收入(m1)和医生收入(m2)在医药分开三个维度(x1,x2,x3)对医疗服务供给可及性即总诊疗人数(y2)的影响中均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如果降低门诊次均药费,但医事服务费和财政卫生补助没有满足医院和医生收入增长的诉求,总诊疗人数就不会按计划调整,医疗服务供给的可及性也不会改善。此外,医院和医生收入(m1,m2)在财政卫生支出(x3)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四个维度(y1,y2,y3,y4)的影响中均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说明医院和医生受到有效的财政补助时,将对医疗服务供给产生显著作用;否则,医疗供给主体(即医院和医生)就不能提供高效的医疗服务。另外,医生收入(m2)在挂号费(x2)对医疗服务供给配置效率(y4)的影响中表现出完全中介效应,说明通过挂号费改革、增设医事服务费可以提高医生收入,从而使得医生劳动力资源、医疗设备资源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地方。

表1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同时,研究还发现,医院收入(m1)在取消药品加成(x1)和增设医事服务费(x2)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充足度(y1)、技术效率(y3)、配置效率(y4)的影响路径下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医生收入(m2)在取消药品加成(x1)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充足度(y1)、技术效率(y3)、配置效率(y4),以及增设医事服务费(x2)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充足度(y1)、技术效率(y3)的影响路径下中介效应均不显著。进一步说明,当前情况下,取消药品加成和增设医事服务费,对于改善医院和医生收入状况,进而改善医疗服务供给的充足度、技术效率及配置效率的作用有限,现阶段仍需维持和增加财政卫生支出。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增设医事服务费等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的措施,相较财政补贴更有利于提升医疗服务供给效率;而现阶段维持和增加财政补贴更有利于增加总供给和控制费用。此外,医院和医生收入对医疗服务供给效率有显著影响,且在医药分开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显著;同时,对这两个维度的研究表明,在当前历史条件下,补贴医生比补贴医院更有利于提升配置效率,但不利于增加总供给和控制费用。本文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主要源自医疗服务供给中的两个分离:一是医方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离;二是需求者与支付者角色的分离。前一个分离更多地表现为产权问题,是根本问题,解释了效率不高的问题;后一个分离更多地表现为制度问题,是从属问题,解释了费用较高的问题。两者分离的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其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离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医方掌握剩余控制权,而政府掌握剩余索取权;二是医生掌握剩余控制权,而医院掌握剩余索取权。这就是为什么医院和医生收入成为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的决定因素之一,而补贴医生更有利于提升效率的原因所在。长期以来,医疗服务的行政定价,在限制医院和医生在医疗服务供给上的选择的同时,具有对特定医疗服务供给的导向性。此外,医生与医院之间的声誉机制和责任机制倒挂,行政手段建立的医院声誉耗散了医生本身的声誉,行政手段形成的医院责任分散了医生应当承担的责任。医生赖以谋求高收入的两大重要因素——声誉和责任,难以由自身掌控。然而,声誉和责任必须依托具体的医疗服务,而医疗服务由医生直接供给而非医院。然而,医院作为医生群体的一个非人格化的“医生”代表,承担了为医生谋求高收入、同时分散责任的角色;而作为医院管理层,则通过掌握“渠道”获得了相较其他医生更高的收入。我们认为正是医生这些以减少自身收入租值耗散为目的的不规范行为,造成了医疗服务行业、药品行业不合理的资源配置[32]。
需求者和支付者角色的分离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医保和政府补贴的支付功能;二是医院本身的支付功能。而这也是为什么相较于增加财政卫生补贴,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更能够提升医院和医生收入;而在当前条件下财政补贴仍是优化医疗服务供给的最有效方式的原因所在。医保和政府补贴无疑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然而,其所具有的“花别人的钱为其他人办事”的属性,使其社会效益远高于经济效益。本文认为,提高社保和政府补贴的经济效益,亟需实现医疗服务需求者与支付者的统一,即“花自己的钱为自己办事”。因此,享受医保和政府补贴的需求者,要么支付了相应的价格,要么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如排队、接受公益性宣传等。同时,政府应立足将这一支出项向收益项转变,发挥社保和政府补贴人群巨大的优势,开发其经济价值,通过“交叉补贴”的方式,提高医保和政府补贴的收益。此外,医院本身所具有的支付功能,模糊了医疗责任应对的需求者和支付者。在医疗服务整体处于“经验医疗”阶段的历史背景下,医疗责任应对的需求者和支付者应为医生,通过行政手段将医生捆绑在医院,模糊了这一责任的归属,甚至使得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成为这一责任的承担者之一。因此,引入第三方评估和保险主体,回归医疗责任的本质属性,对于发挥其在医疗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认为,优化医疗服务供给亟需回归医疗服务本质,弥补两个分离。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握关键要素,坚持正确导向,平衡各方利益,扫除制度障碍。
一是把握关键要素,将改善医院和医生收入作为突破口。医生收入分配制度影响整个医疗系统的绩效。新医改要从根本上瓦解“以药养医”,就需要将改善医院和医生收入作为医改的重要目标之一。政府应逐步放开对医疗服务市场的管制,尽可能增加医院和医生的选择,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供需关系调节,将医疗服务价格、医生收入与当地收入分配状况相协调。参照发达及新兴国家或地区的医疗服务价格水平和医生收入水平,结合医疗服务在我国特定社会条件下的重要地位,划定具有“底线公平”意义的阶段性医疗服务水平,“底线”之上的部分,由医院和医生依据市场规律自行决定。此外,扭转不合理的声誉机制和责任机制。顺应新的历史发展潮流,尤其是“经验医疗”向“精准医疗”的转变、零边际成本社会和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提升医生在医疗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其维护声誉、承担责任的积极性,逐步提升医生在剩余索取权上的优先性,从而改善医生“减少人力资源使用”、“拓展人力资源使用”或者“转让人力资源使用”等不规范现象。
二是树立正确导向,将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作为长久之策。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虽然短期内会增加医疗费用,但从长期来看,将使价格维持在合理的均衡价格上。目前试点的挂号费改革、增设医事服务费、药事服务费等,本质是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的探索。在医药分开过程中,理顺医疗服务价格的改革将比财政补助更加有效地改善医院和医生收入。这些举措,为提升医院和医生收入创造了有效条件。
三是平衡各方利益,将财政补贴作为医药分开的主要手段,且侧重补贴医疗机构。政府投入不单单是投入,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推进制度变革的杠杆[33]。医药分开政策实施之初,取消药品加成将使医院面临比医生更严重的收入亏损,会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正常经营,短期内财政卫生支出的补助对象应主要指向医院而非医生,从而首先解决医疗服务供给不足、供需缺口巨大的问题。但长期来说,当我国医疗服务市场成熟以及价格体系健全以后,财政卫生补助的对象应该转移指向医生。财政补助医生能够更有效地提升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效率,在解决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是扫除制度障碍,逐步消除不合理的合约形式。目前,医方与政府之间、医院与医生之间存在诸如医生编制问题、职称评定问题、医生自由执业问题,医院与医生间的声誉机制与责任机制等,这些特定的形式,对医院和医生行为都产生了特定的导向。只有顺应历史条件、技术条件的发展,适时改变不合理的合约形式,为医疗服务供给的优化扫除制度障碍,才能更好地使全社会共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果。
[1]周其仁. 中国医改的根本问题[J]. 中国医院院长, 2011(21): 66-67.
[2]朱幼棣. 朱幼棣谈中国医改为什么这么难?[EB/O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xfe/2015/0311/122074.
html,2015-03-17.
[3]李玲. 2015两会再谈医改,公立医院才是医改的牛鼻子[EB/OL]. http://www.guancha.cn/liling2/2015_03_04_311011.shtml,2015-03-04.
[4]朱恒鹏. 药价降低七成,毋需财政掏钱[J]. 财新周刊,2015(23):34.
[5]王贤吉,付晨,金春林,等. 医药分开的内涵与实现途径探讨[J]. 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3(1):36-39.
[6]卞鹰,张锡云,葛人炜,等. 卫生经济改革对医院经济效率影响研究[J]. 中国卫生资源,2001(4):153-156.
[7]郭晓日. 我国公立医院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山东:山东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2012.
[8]戴生平. 医疗改革对我国卫生行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分析[J]. 厦门大学学报,2011(6):97-103.
[9]Ozcan Y A, Wogen S E, Mau Li Wen.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skilled nursing facilities[J].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1998,22 (4):211-224.
[10]林皓,金祥荣. 政府投入与我国医院效率的变化[J]. 经济学家,2007(2):77-83.
[11]Shen Yuchu.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pressure on the quality of care in hospitals[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3,22(2):243-269.
[12]Maniadakis N, Hollingsworth B, Thanassoulis 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l market on hospital efficiency, productivity and service quality[J]. Health Care Management Science,1999,2(2):75-85.
[13]Sherman H D. Hospital efficienc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empirical test of a new technique[J]. Medical Care, 1984, 22(10): 922-938.
[14]Wagstaff A. Estimating efficiency in the hospital sector: a comparison of three statistical cost frontier models[J]. Applied Economics, 1989, 21(5): 659-672.
[15]Bernet P M, Moises J, Valdmanis V G. Social efficiency of hospital care delivery: frontier analysis from the consumer’s perspective[J]. Medical Care Research and Review, 2010,68(1): 36S-54S.
[16]Ferrier G D. Rural hospital performance and its correlates[J]. The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1996, 7(1): 63-80.
[17] Feldstein P J. Health care economics [M].7th edition. New York, NY: Delmar Publishers Inc, 2011.
[18]Chou Y J, Yip Winnie C, Lee Cheng-Hua, et al. Impact of separating drug prescribing and dispensing on provider behavior: Taiwan’s experience[J].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2003,18(3):316-329.
[19]宋杰,陈航,吴家锋,等. 北京试行医药分开改革对医患双方的影响观察[J]. 中国医院管理,2013(9):3-5.
[20]徐敢. 公立医院医药分开路径和补偿机制系统建模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管理学院,2010 .
[21]李大平. 药价虚高的成因分析与治理对策——质疑医药分开[J]. 卫生经济研究,2011(4):584-585.
[22]蒋建华. 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5):44-46.
[23]朱恒鹏. 取消以药养医能让看病便宜吗?[EB/OL].http://opinion.caixin.com/2015-05-25/100812288.html, 2015-05-25.
[24]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ealth system:improving performance[R]. Geneva,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
[25]曾雁冰. 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问题建模与控制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2011.
[26]Melnick G A, Zwanziger J. State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under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1980 through 1991[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995, 85(10):1391-6.
[27]詹国彬,王雁红. 英国NHS改革对我国的启示[J]. 南京社会科学, 2010(9):36-42.
[28]陈钊,刘晓峰,汪汇. 服务价格市场化: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未尽之路[J]. 管理世界, 2008(8):52-58.
[29]周志忍. 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辩[N]. 健康报, 2007-04-05.
[30]王延中,冯立果. 中国医疗卫生改革何处去——“甩包袱”式市场化改革的资源集聚效应与改进[J]. 中国工业经济, 2007(8):24-31.
[31]Pauly M, Redisch M. The not-for-profit hospital as a physician’s cooperative[J].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1973,63(1):87-99.
[32]毛克宇. 医疗服务政府定价下医生行为的经济分析[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1):40-46.
[33]顾昕. 走向全民医保:中国新医改的战略与战术[M].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校对:李斌泉
2016-05-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我国医药卫生体制协同改革模式研究”(项目编号:71473284)。
王文娟(1965-),女,山西省大同市人,管理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公共卫生管理;南孟哲(1994-),女,陕西省富县人,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数学与应用数学。
A
1002-2848-2016(04)-0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