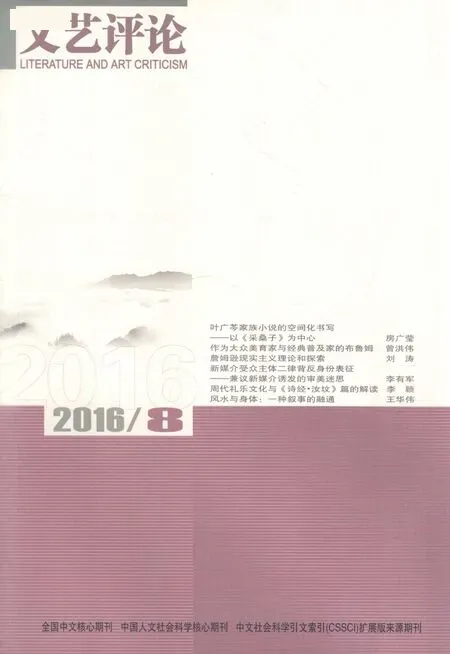论《古诗十九首》士人的悲态心理
○覃素安
古典诗学
论《古诗十九首》士人的悲态心理
○覃素安
《古诗十九首》是汉末士人的集体悲歌。钟嵘说:“意悲而远。”“诗多哀怨。”①。这给十九首定了一个悲怨的情感基调。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的文艺思潮尤其是悲剧美学理论传入中国,评论者以之为武器对十九首进行了批评,产生了不少论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古诗十九首》悲剧意识的体现及其原因。从士人的心态去论述组诗的有王轶群的《汉末士人心态与〈古诗十九首〉》、石红的《从士人心态分析〈古诗十九首〉》等等,它们阐述了汉末士人心态的转变与《古诗十九首》创作的关系。这些都给本论题的探讨提供了有益资源和研究视角。悲剧与悲态虽都强调审美对象与人的敌对性关系,但对于《古诗十九首》的士人而言,悲态心理的描述与表达更为合适。本文以现代美学中的悲态理论为依据,论述《古诗十九首》士人悲态心理的表现、悲态心理产生的根源以及悲态心理的意义。
一、士人悲态心理的表现
张法认为:“悲态是由人生失意的沉痛升华为对宇宙人生本体询问的感伤情怀。”②悲态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喜怒哀乐的悲,它要从宇宙人生的高度去感受、观照而令其具有哲学意义,这种意义的本质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在悲态中,人无法怪罪于给自己造成失意沉痛的自然和社会,因为“悲态所面对的一般是无形的必然律”③,它不具体化为有形的事物。因此,人对待悲态的态度,“不是一个决裂和拼搏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解和顺应的问题”④。“理解和顺应”,对遭受沉痛失意的人而言,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为,表现为对不能把握的东西先了解、认识、明白、懂得,然后顺从、适应它们,整个过程就是对冲突与不可把握的东西的理性确认与接受过程。心理则是人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那么,悲态心理就是人面对社会、自然与自己的对立,面对不能把握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柔顺性心理。以现代美学的悲态理论观照《古诗十九首》士人面对人生失意的反映,他们表现出的柔顺性心理即悲态心理。下面从两大方面逐一阐析。
(一)士人面对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冲突的悲态心理
《古诗十九首》随处可见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的强烈冲突,这是羁旅在外的士人生命体验的常态。“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⑤丘陵上的松柏可以长青,山涧里的石头亦可永存,唯有天地之间的人一如从不知名的远处而来的匆匆过客,转瞬即逝。“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⑥人生如寄,一生像尘土,刹那间被疾风吹散。生命的短暂与卑微令人悲不胜禁。“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⑦游子在外,奔波劳碌,汲汲皇皇,悠悠的路途难以到达,茫茫的旷野漫无边际,春风又吹绿了枯萎的野草,人如草还不如草,虽都会由盛而衰,但草可以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而人的生命不可逆转。人不是坚固的金石,寿命有限。死亡是人的命定,不可逾越:“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迭,圣贤莫能度。”⑧相对于宇宙的永恒,人类的生命如白驹过隙,但转瞬即逝的生命还要承受无尽的愁苦:“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⑨在《古诗十九首》士人生存的空间里,到处呈现出人生如寄、生命苦短与宇宙恒远、自然不朽的强烈冲突,洋溢着浓得化不开的悲凉意味。
面对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的冲突,士人没有决意于与它们作斗争以改变现状,也无法和它们展开斗争,因为“在悲态中,与人对立的自然和社会不具体化为有形的对象,人说不出离别、失意、死亡应该怪谁,它就是一种自然大化和人生命运”⑩,所以只能理解、接受与顺从它们,这就是士人的悲态心理。既然生命如寄,那么就及时行乐,在物欲享受里提升生命的密度。“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⑪都市里到处都是达官贵人灯红酒绿的玩乐,士人也不甘落后,虽然没有美酒,但区区斗酒也足以娱乐,驾起破车赶着劣马也照样在宛洛之间游玩。“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常苦辛。”⑫既然生命苦短,为什么不想办法捷足先登,先高踞要位而安享富贵荣华呢!不要因贫贱而常忧愁失意,不要因不得志而辛苦地煎熬自己。“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⑬生命苦短,人生不可逆转,与其过多地约束自己的性情,不如放开情怀,涤除烦恼,与燕赵之地的如玉美人玩乐,人生就具有了趣味。“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⑭服药求仙不可靠,饮美酒,穿丽服,人生的实在意义不可丢弃。还有诸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⑮“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⑯在士人看来,生命的长度已无法企及,那么追求生命的密度倒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所以秉烛夜游、斗酒娱乐、美人相伴成了他们生命中的重要内容。在汉末乱世,士人——这些本来的社会精英群体,面对生命的失意沉痛,已失却了与之斗争拼搏的能力,只能在生命苦短的宿命里顺从它,“悲态,不是一个决裂和拼搏的问题,而是一个理解和顺应的问题”⑰,士人的悲态心理显而易见。这样的心态和生于乱世的庄子面对生死穷达豁达的悲态心理是一样的,即:“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⑱
(二)士人面对人生追求与人生失意冲突的悲态心理
人生追求是人生意义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追求的事物,总是闪耀着理想的光芒,而它与现实总有距离,人们孜孜以求但很多时候都会落空,这就是人生追求与人生失意的冲突。《古诗十九首》的士人起初帯着传统儒学的入世理念去求仕谋事,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仕途与人事的诸多羁绊中,他们饱受知音稀少、同窗见弃、归家不得、人生失意的打击。“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欢,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⑲在外漂泊的士子听到从华丽居所里飘出来的忧伤曲子,心有深感,他听出了曲子的悲哀,感受了歌者的孤寂,因而愿与他展翅高飞,相互慰藉。但楼高人远,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罢了。陆时雍评此诗说:“空中送情,知向谁是?言之令人悱恻。”⑳其实,孤寂的并不仅是歌者,更是听者,“但伤知音稀”恰是羁旅在外士子的共同遭遇与深沉体验。在乱世里,他们空有理想抱负,而不获知音的欣赏,在求仕谋事的路上孑孓独行。“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㉑,他们正如幽兰一般空有优雅的姿色,只能孤独地开放,无人品鉴。同门在人生追求的路上本可相互扶持,但他们一旦高举,即弃人如遗迹:“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㉒同门见弃,士人在感叹孤寞之余,更添悲愤,求仕不成,陡增失意,此时对家园亲人的归依之情尤为迫切,但“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㉓“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㉔“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㉕家园亲人可望而不可即,思归不得的沉痛在士子的心头不断积淀,日渐发酵。在求仕谋事人生追求的路上,人生的失意煎熬着士子,让他们备受精神的折磨,心灵的悲怆越发浓重。
面对人生追求与人生失意的冲突,士人也无法具体怪责谁,归根到底这是人与社会的对立,它也只能是一种人生命运,因而士人除了默默承受与理性确认,此外别无他法。在外漂泊的游子能听懂楼中幽居歌者的琴调,领悟“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知音稀少才是痛苦的根源,但楼高人远,歌者与听者处在隔阂状态,正所谓“空中送情,知向谁是?”故歌者依然苦,听者也不会因隔空送情而减少漂泊之路上不遇知音的孤寂。“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展翅高飞只是美好的意愿罢了,它恰是士子现实里知音稀少的真实反映。面对飞黄腾达同窗的无情无义,士子无力改变现状,他只能看清事实的真相聊以安慰:“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㉖夜空中名为“箕星”“斗星”“牵牛”的星辰,它们既不能颠扬、斟酌和拉车,为什么还要取这样的名称?真是虚有其名!想到当年友人说同门之谊坚如磐石,而今却荡然无存,虚名又有何用呢?这就是同门之间的真相,虽然残酷,但看清是士人接受现实的基础。羁旅在外的游子对家园亲人的归依情感虽强烈,但他们也无以改变归家不得的现实,反而要更加冷静地面对事实,明白自身的困苦处境:“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㉗“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㉘故乡在漫漫的路途之外,欲归不能,亲人相爱却相离,忧伤到老。朱熹在《诗集传》里说:“居而相离则思,期而不至则忧,此人之情也。”㉙离愁别绪虽人之常情,但当离别永无会期或永久的失去时,就变成了人生的否定性,就成了人生的悲态。《古诗十九首》的士人在人生追求的路上遭遇人生失意的沉痛,他们无法改变人生的悲态,只能理解和顺应,恰是这些理性确认和顺从适应,让他们在面对冲突时表现出悲态心理。
二、士人悲态心理产生的根源
《古诗十九首》的士人处于汉末桓灵之世,他们已失却两汉时期知识分子通往政治权力的道路畅通,又没有建安时期文人士子为理想奋斗的热情与力量,加之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导致他们在面对社会、自然与自己的对立,面对不能把握的东西时产生悲态心理。
(一)信仰危机是士人产生悲态心理的内在动因
信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众多力量之一,若是没有它,便意味着崩溃。《古诗十九首》的士人处于汉末乱世,时世的转变令他们原来极度信奉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念已经动摇,又没有新的精神信念来支撑,在人生失意沉痛侵蚀之际,失却了与之斗争的武器,于是内心深处的悲凉不断涌现,因而信仰危机是他们产生悲态心理的内在动因。汉末,儒学衰落,“末俗以来不复尔(西汉儒家鼎盛状),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㉚。儒学已无法在现实中解决问题,尤其是无法解决知识分子求仕谋事所遇的困惑与阻挠,因此越来越多的文人对儒学不满,对董仲舒以来天人合一的儒学理念怀疑,对儒学所设定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否定,汉末士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原来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动摇了。汉末桓灵之世,政治腐朽,选士制度日益流弊,以财物多寡、身份高低、党派强弱来选拔人才。葛洪在《抱朴子·.审举》言:“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有直者无分而径进,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货多者其官贵,其财少者其职卑。清贫之士,何理有望哉!”㉛《古诗十九首》的士人身份卑微,要跻身仕途谈何容易!政治环境险恶,公元166年和169年发生的两次“党锢之祸”,令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无辜受戕害,生命不保的士人政治参与的热情迅速褪减。现实政治的残酷与仕途谋事的无望加重了士人对儒学的信仰危机。信仰危机令《古诗十九首》的士人在面对生命苦短、人生失意时失去了对抗的武器,没有力量与之抗争,只能理解和顺应,从而产生悲态心理。建安时期文人的心态则不同,虽则他们身处乱世,也有生命苦短、抱负难展的悲凉感慨,但因为他们有执着理想的信念,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抱着坚定的信念与现实的悲凉抗争,所以他们在感慨悲凉之余,更多的是胸中有慷慨之气,形成铮铮风骨。曹操吟诵“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㉜,顿觉悲凉,但那是统一天下的理想未能实现的焦虑,“周公吐哺,天下归心”㉝的慷慨豪情一下子就冲淡了这些悲凉。所以两相比较,更有理由相信,信仰危机是《古诗十九首》士人产生悲态心理的内在动因。
(二)个人人生的有限性是士人产生悲态心理的根本原因
汉末儒学衰落,老庄思想复苏。老庄之学贵生,对生命的关注与珍视是其重要的哲学内容。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不能回避的是对死亡问题的思考,生命的有限性凸显在他们面前,而一切人生失意深悲的根源都在于个人人生的有限性。“离愁别绪、追求不得、抱负难展这些日常情感之能上升到人生深悲和美学悲态的高度,从根本上说在于个人人生的有限性,只有在人的有限性、暂时性和不可重复性这一背景上,人生失意才与哲学的本体意义有了联系。短暂人生使离愁别绪的悲触伸到本根上;个人的不可重复性使理想失落的幽怨带上了永恒性。美学的悲态,其深处包裹的就是个人的有限和宇宙的无限性问题。”㉞《古诗十九首》的士人正是在个人人生有限性这一特质上去面对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人生追求与人生失意的冲突。他们发现在自然的博大永恒面前,人是如此的渺小短暂,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层面,加之他们无法像建安时期的文人那样用理想信念去超越生命的短暂,冲淡生命的悲凉,因而只能在及时行乐的麻醉里去顺应这一不可更改的自然规律,更显其内心深处的悲态。《古诗十九首》的士人因生命意识的觉醒而思考生命的有限性,而无法超越的有限性令他们在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冲突,面对人不可把握的东西时表现出悲态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个人人生的有限性是《古诗十九首》士人产生悲态心理的根本原因。
三、士人悲态心理的意义
悲态,对于不可把握的东西,不是进行决裂和拼搏,而是理解和顺应,所以悲态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理解,加深了悲态的哲学意义。这种意义的实质在于让人明白自己与自然、社会的对立关系,从而能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把握自己的情感;二是通过理解,使情感的深悲能趋于平静。这正像张法所言:“理解虽然不能改变悲态,却可以把握悲态,使情感的深悲通过理性的把握而平静下去。”㉟正是基于此来探讨《古诗十九首》士人悲态心理的意义。并非说他们理解了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就能改观现实,改变命运,而是在于能清楚状况,面对现实,理解处境,然后顺应它,不做无谓的努力。他们理解了人生失意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范畴。既然无可奈何,唯有安之若命,那种深悲的情感就会在士人理性确认的过程中趋于平静。这与冯友兰先生所说“以理化情”能减轻人的痛苦的理念有共通之处:“若有知识之人,知宇宙之真相,知事物之发生为必然,则遇事不动情感,不为所束缚,而得‘人之自由’矣”。㊱十九首的士人当然还未能到达“人之自由”的境界,但其深悲的情感倒是会在理性确认的过程中逐渐减轻,趋于平静。要之,《古诗十九首》的士人虽然无法在理想的追求上超越生命的短暂,但他们转而追求俗世的享乐,在有限的生命里不负生命,这其实是对生命的关注和正视,比起之前的文人思想心性的规范,主要关注家国天下大事而导致个人意识的相对淡化,更显示出十九首士人对生命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古诗十九首》士人的悲态心理恰恰是他们生命意识的觉醒,这个觉醒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古诗十九首》士人在面对生命短暂与宇宙永恒、人生追求与人生失意冲突这些不可把握的东西时,表现出一种柔顺性心理,即悲态心理。这种悲态心理产生的根源在于士人信仰的危机和意识到个人人生的有限性。士人悲态心理的流露和表达虽然无法改变其人生的悲态,但那是他们对生命的关注和重视,体现出个人意识的增强,实则是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它为魏晋时代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吹响了前奏曲!
(作者单位: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①钟嵘撰《诗品译注》[M],周振甫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页。
②③④⑩⑰㉞㉟张法《美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第99页,第99页,第99页,第99页,第98-99页,第99页。
⑤⑥⑦⑧⑨⑪⑫⑬⑭⑮⑯⑲㉒㉓㉔㉕㉖㉗㉘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古典诗歌基本解读》[M],北京:人民武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第44页,第53页,第56-57页,第59页,第41页,第44页,第55页,第57页,第59页,第53-54页,第45页,第47页,第46页,第51页,第58页,第47页,第46页,第51页。
⑱郭庆藩撰《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9页。
⑳陆时雍《古诗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㉑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㉙朱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页。
㉚颜之推撰《颜氏家训全译》[M],程小铭译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㉛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96页。
㉜㉝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第235页。
㊱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