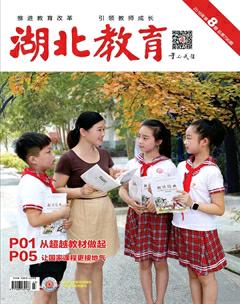质疑:文本另类解读之捷径
谢德敏
“另类”在《现代汉语词典》里解释为:另外的一类,指与众不同的、非常特殊的人或事物。文本的“另类解读”指对传统的、大众的、权威的解读进行质疑和批判,并得出一种新解读的文本解读法。另类解读不是对经典、传统的随意解构,而是对文本中的人物、思想等深度透视后,有理有据地对大众解读进行质疑和批判,其目的是解放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多元化、广角度的理解文本。
一、质疑文本的留白处
留白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艺术手法,它能给读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审美空间。补白是文本解读的重要方法,它能还原作者表述方面的空白,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人物形象,理解文本内涵。很多经典作品的补白内容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被固化下来,成为教师解读文本的“拐杖”,但这种解读却不够严谨。
如,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八年级语文上册《桃花源记》(同版本教材以下只注明年级与册数)中,渔人“既出”,“处处志之”,可为何再“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呢?传统的文本解读要么不能对这处留白做出合乎情理的解读,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地指出桃源民风淳朴。备课时,笔者反复研读文本,得出这样的结论——渔人“不复得路”与桃花源中的人有关。
教学中,笔者抛出这个观点,让学生寻找证据。学生兴趣高涨。一名学生率先分析,桃源中的人虽然纯朴,但并不愚笨,渔人在桃源中做客数日,桃源人在与他交谈的过程中定然能看出其人品,因而临行前反复叮嘱他,“不足为外人道也”,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知道渔人会“为外人道”。另一名学生进一步指出,既然桃源人知道渔人会“为外人道”,那么,他们会做些什么?他们肯定会暗中跟出,把渔人的标记消除。不少学生反对这种观点,理由是渔人第二次来时,“寻向所志”,说明标记还在。那名学生想了想,高兴地叫嚷:“不是‘消除,是修改。因为桃源人把渔人的标记做了修改,所以渔人走错了方向。”
学生的这段分析可谓精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师课前对文本留白进行了合理的质疑。这样的质疑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帮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文本。
二、质疑文本的新解读
当前,多元解读似乎成为热潮。在这个潮流下,有些解读确实给经典文本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但是,误读、浅读、曲解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如解读《背影》时,说“父亲的行为违反交通规则”,解读《皇帝的新装》时,说“骗子是义骗”,等等。这就需要教师在面对文本的新解读时,要有足够的定力,不趋众,不盲从,而是贴紧文本主体和主题,引导学生正确把握文本的思想内涵,感悟文本的艺术魅力。
如,九年级下册《愚公移山》中“愚公”的形象,近几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解读,有认为愚公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的,有疑惑愚公为什么不搬家而非要移山的,还有认为愚公破坏了自然环境的,等等。从学生认知的角度和生活体验来看,这些想法不足为怪,但个别教师也以诸如此类的问题来启发、诱导学生,就彰显出教师在文本解读方面的肤浅。
《愚公移山》选自《列子·汤问》,选入教材时虽然脱离了原文的语境(《列子·汤问》充满了朴素的哲学思想),但作为一则寓言故事,其独立、完整的意义内核仍然完备。什么是寓言?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拟人的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拟人和借喻是寓言惯用的手法,其目的在于使富有教训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情节高度凝练的故事中得到揭示。《愚公移山》讲述的是立志移山的故事,但对本文的解读不能仅仅停留在故事的本身。换句话说,“移山”不是关注的焦点,作者是假借“移山”来承载像“移山这样的顽强意志”的主旨。(孙绍振语)因此,教学这篇文章,重点应关注和思考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寓意或道理。如果我们让学生联系现实经验来探讨愚公移山的行为是聪明还是愚蠢,来探讨绕山开路或搬家等,岂不和我们读完《伊索寓言·蚊子和狮子》后,去探讨蚊子和狮子究竟谁的战斗力更强一样肤浅吗?
虽然课标指出“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但是,这种“独特”应建立在正确理解和把握文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之上,如果随意架空文本的样式和主题,一味求新逐异,多元解读就有可能变成误读和曲解。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教师的重视。
三、质疑文本的语言层
文本不是平面的、单一的,而是具有多层次结构的语言组合体。所谓“多层次结构”,包括了文本的表层和深层,主要可分为语言层、现象层和意蕴层三种。其中,语言层是我们接触文本时首先感知的层面,它主要用语言符号来创造形象,营造意境,表达内容,传达情感,是启发读者思维,引领读者进入文本所营造的艺术境界,体味文本深层意蕴的根基和抓手;同时,语言层形式本身(如文本言语的语音、字形、词义、句式、段落结构等)也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质疑文本的语言层,就是引导学生关注文本的行文,通过咬文嚼字或置换推敲等方式探究、了解文段中重点句子或词语的字面含义,在此基础上,启发学生发挥想象,大胆质疑。
七年级下册《伟大的悲剧》中,茨威格这样评价英国探险家斯科特:“一个人虽然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的搏斗中毁灭了自己,但他的心灵却因此变得无比高尚。所有这些在一切时代都是最伟大的悲剧。”这个评价是符合西方悲剧理论的:悲剧性就是指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悲剧主体具有强烈的自我保存和维护独立人格的欲望,往往因为对现状的不满而显示出强烈的不可遏制的超越动机,并能按自己的意志去付诸行动,即使命运使他陷入苦难或毁灭境况之中,他也敢于拼死抗争,表现出九死不悔的悲剧精神。这一理论的关键词是“抗争”,但在《伟大的悲剧》中却没有斯科特一行与暴风雪进行殊死搏斗的描写。我们来看看文本中叙述死亡的几个片段。
埃文斯之死:
他站在一边不走了,嘴里念念有词,不停地抱怨着他们所受的种种苦难——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他的幻觉。从他语无伦次的话里,他们终于明白,这个苦命的人由于摔了一跤或者由于巨大的痛苦已经疯了。……2月17日夜里1点钟,这位不幸的英国海军军士死去了。
奥茨之死:
冰冷的黑夜,周围是呼啸不停的暴风雪,他们胆怯地睁着眼睛不能入睡,他们几乎再也没有力气把毡鞋的底翻过来。……他们中间的奥茨已经在用冻掉了脚趾的脚板行走。……奥茨突然站起身来,对朋友们说:“我要到外边去走走,可能要多呆一些时候。”其余的人不禁战栗起来。谁都知道,在这种天气下到外面去走一圈意味着什么。但是谁也不敢说一句阻拦他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敢伸出手去向他握别。他们大家只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感觉到:劳伦斯·奥茨——这个英国皇家禁卫军的骑兵上尉正像一个英雄似的向死神走去。
威尔逊、鲍尔斯、斯科特之死:
他们知道再也不会有任何奇迹能拯救他们了,于是决定不再迈步向厄运走去,而是骄傲地在帐篷里等待死神的来临……凶猛的暴风雪像狂人似的袭击着薄薄的帐篷,死神正在悄悄地走来,……斯科特海军上校在他行将死去的时刻,用冻僵的手指给他所爱的一切人写了书信。
文本中多处写了斯科特等人在暴风雪中的束手无策。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一连几天畏缩不前,勇气渐渐被大自然的巨大威力所销蚀;他们身上有惊慌和胆怯,他们在无助中祈求上帝保佑,最后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爬进睡袋,从容、坦然地等待死神降临。
斯科特一行在暴风雪的考验下,在不可战胜的厄运面前,展现的不是战风斗雪似的武士精神,更多的是英国人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质。他们身上凝聚着人类美好的德行:威尔逊博士在生死考验的边缘,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在个人生命和科学之间抉择的时候,选择了科学,这种献身科学的精神令人敬重。奥茨为了不拖累自己的战友,像英雄一样向死亡走去,这种勇于担当、自我牺牲的精神可歌可泣。斯科特接受了一项残酷的任务,那就是要在世界面前为另一个人完成的业绩作证,而这一事业正是他自己所热烈追求的。这一点尤其能考验出他的道德水平。虽然心有不堪之痛,但是最后他勇敢地接受了失败的现实,履行了神圣的使命。这种忠诚和守信,正是英雄的气质。
他们的身体虽然被毁灭了,但是美好的品质却永远被人们记住。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两个词语:有价值和毁灭。斯科特一行“毁灭”了,他们的遭遇是悲剧性的,那么,他们的价值在哪里?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既然没有写斯科特一行与恶劣的天气做拼死抗争,为什么茨威格评论他们是在同不可战胜的厄运做搏斗呢?那些胆怯、无助、绝望、祈祷神灵护佑的行动,这些在灾难面前的生物本能不是拼死抗争,又怎么可以称得上最伟大的悲剧呢?依据鲁迅先生对悲剧的定义,我们是否可以将茨威格对斯科特等人的评价做一点修改呢?你觉得怎样评价更合适?
这样的质疑激起了学生的兴趣,激活了学生的思维,他们在深入的阅读与讨论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斯科特等人的精神品质,更加准确地把握了文本的主旨。
(作者单位:恩施市屯堡乡初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