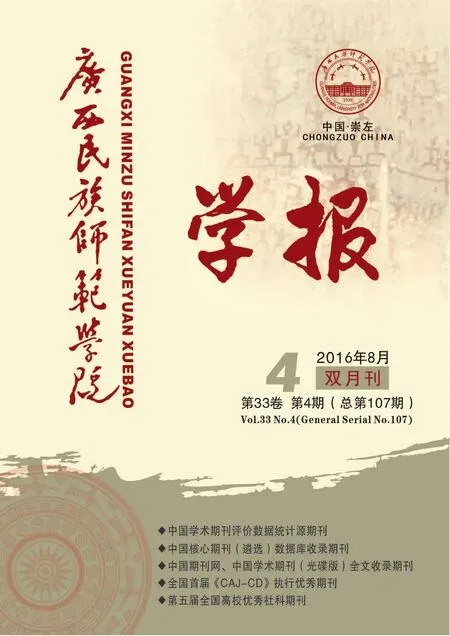一场文明之火的争夺战
——中国诸民族的盗火神话母题
李 鹏
(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
一场文明之火的争夺战
——中国诸民族的盗火神话母题
李鹏
(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
盗火神话作为世界性的文化获取类的母题,在传承民族进取精神和探索文明之源方面都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诸民族盗火神话主要流传于汉族、满族、蒙古族、羌族等数十个民族之中。笔者通过目前搜集的文本资料对盗火神话中的盗火原因、方法和结局进行了对比研究。各民族盗火神话在幻想背后隐藏有真实的成分,可通过比较研究方法对各民族盗火神话所蕴含的文化内蕴进行剖析。
盗火神话;中国诸民族;母题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对世界的独特思考和认知,其中蕴含着先民们对客观事物由来的探究和思索。神话并不能完全说明事物或历史的真相,但它所反映原始先民的认知体验却是客观真实的。神话流传演变至今已发生较大变化,对其原型的探究尚需综合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力量,对各民族的神话进行比较分析,以挖掘蕴藏于神话背后的真实,探寻原始先民创作相关神话过程中的思维观念、情感表达和价值取向。
原始先民在探究世界奥秘的过程之中,逐渐认识到“火”的重要意义,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时代,从刀耕火种到电子信息化,人们越是处在文明之中,就越无法与“火”切断联系,火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先民更是将火视作神圣之物,与水的固态形式相比,对“火”的探寻和拥有已成为人类探寻自然、征服自然的重要表征。在没有科学知识背景的先民时代,许多民族都对火的起源产生了种种疑问,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人们渐渐掌握了生火的技巧和本领,提高了自身的生活质量。“许多神话与教仪都缘火而生,以火为中心”[1]44,火神话的产生正反映了先民社会对火的崇拜观念。在火神话之中,盗火神话作为世界性的母题,是较有特色的一类神话,它广泛留存于世界神话之中,因为它取火方式的独特、取火情节的曲折、取火精神的伟大、取火内涵的丰富,所以盗火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美国民俗学家汤普森曾将“盗火”归入母题分类体系中,中国学者王宪昭也曾对盗火神话进行母题编目[2]1159-1163,其他如张振犁、汪玢玲、那木吉拉等学者都对中国多民族的盗火神话进行过系统的比较研究。通过对现有的中国诸民族火神话文本资料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在中国至少有44个民族之中存在有火崇拜的观念,而在125篇的火神话文本资料之中,涵盖了40个民族的盗火、取火、造火、送火、换火等神话形式,而盗火神话母题则广泛流传于汉族、满族、蒙古族、羌族、水族等数十个民族之中,具体详见表1。对中国多民族盗火神话母题的研究,此文试通过对盗火的原因、方法、结果的比较研究,来发掘蕴藏于盗火神话内部的文化意蕴。

表1 笔者目前搜集到的火神话的篇数分布表
一、盗火的原因
依据神话叙事文本所述,盗取火种的行为对民族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火种的出现改变了本民族茹毛饮血的时代,提高了民族整体的生存质量,增强了民族同自然抗争的力量,因而盗火的原因自然与转变民族恶劣的生存状态有关,通过比较分析,神话中对于盗火原因的阐释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火是抵御严寒的法宝
火与地域有着紧密的关联,相对于南方民族而言,北方的汉族、满族、蒙古族、裕固族等民族所处的地域在冬季更为寒冷,正如满族神话所讲“北方的气候变得寒冷刺骨,冰河覆地,雪海无垠,万物不生”[3]758,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下,他们需要以火取暖,“火”决定着北方民族的生存命运。在寒冷的环境中,火更与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联,如藏族神话说没有了火,“人们不能烧茶,天冷不能烤火”[4]960,便道出了藏族用火烧茶、取暖的用途。南方诸民族虽亦有对寒冷的恐惧,但更多的则是需要用火提高生存质量。
(二)火是结束茹毛饮血生活状态的有力工具
南方的水族、普米族、布朗族、景颇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先民的饮食多是采用生食冷饮的方式,“人们过着生吃冷喝的生活”[5]702,这样很容易带来疾病,影响先民的生存质量,可以说“人间没有火,日子很苦”[6]283,如哈尼人认识到“因为天下没有火,饥寒和病魔总是纠缠着我们哈尼人”[7]188,这便点明了火的作用不仅能够使百姓从饥饿和寒冷中解救出来,更可以使人们免受饥寒所带来的病痛。
(三)火是不存在于人间的神圣之物
很多民族的神话都认为人间本就没有火,这是产生盗火的主观原因,因为已有敬火的观念深入其中,像蒙古族、水族等民族认为火藏于天上,壮族认为火潜于地下,布朗族认为火在很遥远的地方。出于对火的神圣的认知,先民将取火的重担交付文化英雄,他们需要从人间之外的地方寻找或盗取火,这样获得的火才更有珍贵的意义。
(四)火种未能得到保存
先民获得最初的火应为自然火,也就是神话中的“天火”,人们防止火熄灭的方式是使火不断燃烧,而当火种被洪水熄灭(如壮族)或雨水浇灭(如佤族)之后,便发生了这样两种情况:其一是等待天火再次降临;其二是与其他氏族“借火”。火种的保存一方面在于有特定的保存方式;另一方面在于掌握造火的方法,懂得存火和造火是免于“借火”的重要手段,而当这种手段尚未获取之时,只能采取“借”的方式。
(五)火消失于大洪水之后
此时火的消失与保存火种的方法尚未获得,而火与洪水的关联又是存在的。洪水神话是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的神话,大洪水造成的灾难也较为可信,火与水属于相生相克的一对物质,火为水所灭而消失亦有可信之处,毕竟水在自然状态下的实体可见,而火则需要靠外界的力量才可取得,若没有生火的方法,就只能从外界取火或学习造火方法,如彝族神话说洪水退后,青蛙偷看天神点火而为人类获得取火方法。
通过对神话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应当思考盗火背后的意义。对于崇拜和守护火的先民而言,盗火本身便是大忌。纵观诸民族的文化英雄,不难发现除了盗火,神话之中还有盗水、盗土、盗粮种等神话,偷盗母题亦是在神话中普遍流行。从古至今,偷盗是违背道德原则和法律准则的,更何况是象征着生存意义的火、土、粮种等。在原始先民所处的社会之中,偷盗的意义则远非如此。人们所熟知的盗火、盗粮种神话之中,大多是对该类偷盗行为的肯定,普罗米修斯盗火是为了人类的生存,狗盗取谷种是为了人类的生计,此类行为完全符合我们的道德认知。但这些所见的神话,多半已经被披上了道德的外衣,透过这些含有偷盗母题的神话,可见在原始社会中掳掠或偷盗行为的存在是较为明显的。一方面战斗力强大的氏族部落为了本部落的生存而掳掠较为文明开化的部落,在部落与部落的争夺之间没有法律的制约与道德的约束,为了部落的生存和繁衍,而战胜另一部落获得象征文明的火种或粮种,取得区域性的胜利;另一方面战斗力弱小的氏族部落为了能够在弱肉强食的部落征战中获得一丝生的希望,便对生产力发达的部落进行策略性的盗窃,盗取有利于其生存发展的生产生活资料,火种和粮种便是其中重要的资源。所谓的“盗火”,其实也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盗取真正的火种或盗学取火的方法;其二是赢得以火种为象征代表的区域文明统治。
“盗”发展至今已经从“河水泛滥之义”演变为“私利物也”[8]558,“盗”虽为贬义,但盗的行为并非都是贬义,是要依据客观情况而定,如“盗火者”,对拥有火种的集团而言,他们毋庸置疑是盗贼,但对于需要火种的集团而言,他们就是英雄式的人物。因此强调盗火行为本身的意义要远大于“盗”的含义。
二、盗火的方法
盗火神话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便是对盗火过程的介绍,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盗火的特色,不同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盗火方式,在这过程中民族的智慧、坚韧的精神、拼搏的状态、独特的想象、热情的歌颂都彰显无疑。纵观中国诸民族的盗火神话,盗火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大体有如下五种。
(一)他人点拨出盗火的方法
有些民族的盗火神话中盗火的思路与方法是源自外界人或动物的指点,多数是动物对盗火者的引导,且方式各有不同。如哈尼族的阿扎在小白鹿的指引之下来到了魔王所在的石洞,小白鹿化作少女指点阿扎,告知阿扎要拿掉魔怪头上的金鸡毛才能使它动弹不得。布朗族的岩多在小松鼠的指导之下,将一百支竹筒扔进火魔的屋中,九十九支装满了水,一支装着小松鼠,小松鼠趁机盗出火,而火魔怕水便把水竹筒扔了出来,这样便得到了火种。回族的阿当在野马的指点下得知恶龙守护的雷公斧能够通过大河,而战胜恶龙则要兜圈子使它卷做一团,在阿当降服恶龙之后,恶龙告知他需要将火种放在雷公斧背的盒子里才能取回火种。畲族的雷豹在雷老爷爷的点拨之下,找到了能够帮助他从魔宫里取火种的姑娘。
(二)利用特定的意象完成盗火
各民族盗火过程各有特色,这里仅就哈尼族的金鸡毛、布朗族的水竹筒、回族的雷公斧、畲族的羽衣仙女等意象进行说明。
哈尼族魔王头上的金鸡毛是较具特点的象征物,它一方面象征着魔王的灵魂,只有控制金鸡毛才能将魔王的行动抑制,金鸡毛可能是灵魂的外化形式;另一方面金鸡、火、太阳三者之间又有着特定的关联,像纳西族掌火的昂神是大公鸡的形象,畲族神话中后羿所射的九个太阳中的一个变成了鸡[9],民间更有“月中住玉兔,日中住金鸡”[10]的说法,公鸡在一些民族的观念之中已成为太阳的使者,而太阳作为光明与热量的源泉,同样被视作火之源,同时很多的少数民族神话中太阳神多与三趾乌、凤凰、鸡等联系起来,太阳与禽鸟的结合较早地体现了先民的太阳崇拜意识观念,从如今可见的诸如马家窑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器物来看,太阳神的形象当为凤鸟,太阳与禽鸟的复合已经成为部分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不过,中国诸民族神话中太阳与金鸡的结合,古代已有认同,如《太平御览》中引“《春秋说(解)[题]词》曰: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11]351,吴裕成认为“鸡为积阳”是对雄鸡啼晨“颇富中国哲学韵味的解释”[12]107。而鸡鸣与太阳复生之间又有象征关系,司晨之鸡的鸣叫能够使落日重新升起,看似是使太阳复生,金鸡与太阳之间神秘的关系成为先民崇拜金鸡的根源,各民族的射日神话之中“公鸡喊太阳”母题的留存也为公鸡崇拜提供了佐证。因此,深入理解哈尼族、纳西族盗火神话中出现的金鸡或公鸡的意象,才能更好理解神话本身的内涵。
布朗族的水竹筒的意象的选取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竹子在西南少数民族之中运用得较为普遍而且也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竹筒不仅用于取水,在某些民族中还起到了沟通鬼神的作用,如哈尼族的竹筒出现在丧葬活动中,“哈尼族贝玛送葬时必须敲响一个特殊的竹筒,‘博妥',此物意为与鬼神搭话的竹筒”[13]。侗族的竹筒舞蹈是在节日仪式上较为常见的一种舞蹈。可见,竹筒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这又与北方萨满手中的鼓的某些意象颇有相似之处。布朗族神话中出现的一百个竹筒,既是作为该民族普遍使用的工具而出现,又有可能具有驱邪禳灾的功用,对有着六只脚、八只手的火魔而言,百只水竹筒中的水和竹筒对火魔都有一定的克制作用。因此,布朗族盗火神话所选取的水竹筒有其特定的含义。
回族的雷公斧意象的选取与火也有着重要的关联。雷公、雷神、雷师、雷王等称呼在各民族之中并不相同,是在万物有灵观念下创造出来的自然神祇。雷神的相貌不一,《元史》中对雷公的形象有这样的记载:“雷公旗,青质,赤火焰脚,画神人,犬首,鬼形,白擁项,朱犊鼻,黄带,右手持斧,左手持凿,运连鼓于火中”[14]1962,其中已经出现雷公斧,雷击与钻石取火有若干的相像,而斧凿意象的出现正与此相吻合,后世的雷公斧也渐渐成为取火的重要工具。在回族的神话中,雷公斧的斧背更是成为存放火种的位置,雷公斧内藏有火种与其他民族神话中树皮、石头内藏有天火又有着一定的联系,先民认识到火是神圣的,摩擦取火的缘由在于树木、石头、斧凿本身就带有上天赐予的火种,这也更增加了对火的崇敬。
畲族的羽衣仙女形象融入了盗火神话之中,作为复合型神话,故事情节的发展和结合得较为合理,满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中都有羽衣仙女的神话,但盗火神话中出现此情节却显得较为独特,在目前所搜集到的神话资料来看,很少有民族会将类型差异较大的两类神话复合在一起。畲族神话中雷豹偷去了在湖中沐浴的云仙子的衣服,使她无法飞升上天,云仙子既成为了盗火英雄的妻子,也变成了盗火的协助者。盗火英雄既收获了爱情,也为人类收获了光明的火种。神话寄托了畲族人民的美好愿望和憧憬,英雄于公于己都应当获得完美的结局。而这种双赢而美满的结局在其他民族的盗火神话中却不为多见。
(三)依靠团队合作盗火
当人们认识到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完成盗火重任的时候,便会联合外界的力量共同完成任务,比如藏族的《登巴取火》,登巴召集青蛙等动物,按照一定的路程间隔分配每个动物驻守于特定的位置,从离村子不远的草地上的青蛙到马、猫、狗、老虎,盗火成功后,守火的巨人追逐偷盗者,而此时等候的动物们则采取接力奔跑的方式先后传递火种,最终将火种传到部族之中。纳西族的昂姑咪同样得到了各方力量的帮助,在蚕子、蜘蛛、蝴蝶、蜜蜂的帮助下才得以上天,并将守火的神羊、神狗转化为帮助自己的力量,让它们引领自己找到火种。这种方式比较注重团队的力量和配合,也是人们思维观念的一种进化,真正的英雄需要善于运用智慧,按照各自能力的不同来调度各方力量。
(四)邀请有能力者进行盗火
盗火神话的英雄均有人们看重的过人之处,足以完成盗火的工作,从而成为人们仰仗的力量。如蒙古族的盗火神话中,人们因无法飞达上界取得天火,而派出了燕子,因为它“敏捷,身材又小,正合适”[15]16,同样当人间拥有了火之后,下界的生灵因无法来到人间而派出灯蛾在夜晚盗火。燕子和灯蛾都具有飞行的本领,其中燕子是蒙古族神话中出现较多的一类意象,它在盗火和盗谷种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深得蒙古族人民的喜爱和尊敬,而灯蛾的习性是出没于夜间,正是下界生灵盗取蓝火的重要选择。羌族的盗火神话中,燃比娃是接受母亲阿勿巴吉的命令而为部族盗取火种,阿勿巴吉之所以能够派出孩子远征盗火,是因为他既是火神之子,有着神的血统,同时在燃比娃尚未出生之时,火神蒙格西便有意让阿勿巴吉的孩子为人间取火。燃比娃盗火具备有良好的内因和外因,他有取得天火的条件和能力。
(五)舍己献身获得火种
有些民族的盗火英雄为了顺利将火种带回人间,采取了同火种合二为一的方法。如手捧火种回人间,纳西族的昂姑咪手捧昂神赐予的火种,全身烧焦而把火种带回到人间。还有像吞食火种,满族、哈尼族和普米族的盗火神话中英雄都将火种吞入腹中,满族的拖亚拉哈怕神火熄灭而吞食火种,哈尼族的阿扎怕魔怪夺回火珠而吞食火种,普民族的少年怕天兵夺回火而吞食火种。然而盗火英雄要吐出火种则要付出代价,拖亚拉哈变成了怪兽才可以口吐烈焰,阿扎和普米少年回到人间都变成了火球。吞食火种的方法与先民尚未学得存火的方式有一定的关联,而英雄吞火回人间的功绩也得到本族民众的世代铭记和认可,这种民族精神通过神话叙事的力量得以传承。
(六)屡败屡战进行盗火
上述的盗火方法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然而盗火英雄的盗火行动并不都是一次性成功,有的盗火过程通过至少两次的尝试才最终得以成功,这也体现了盗火的艰难。如满族神话《托阿恩都哩》和羌族的《燃比娃取火》在盗火方面有诸多的相似,学者那木吉拉曾在《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中对两个民族的盗火神话进行了深入的比较[16]496-499。而彝族的盗火神话中也存在着多次取火的过程,亦当属此类型,但其盗火过程却与满族、羌族盗火神话有着较大的差异,笔者试通过表2对几则神话作比较。

表2 满族、羌族、彝族盗火神话的比较
从表2所列可见,相对于彝族的盗火神话而言,满族和羌族的盗火情节都较为曲折,这种三段式的神话叙事中增添了故事的可阅读性,故事的矛盾性也较为集中,人物性格也较为突出,神话的神圣叙事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与故事的叙事元素逐渐融合。三则神话的主要共同之处有五点:其一,火最初源自天上;其二,火的执掌者都是天神;其三,盗火的协助者和阻碍者多是动物和神灵;其四,人们最终掌握了取火的方法;其五,取火的方式都是打石取火。
作为不同语系的几则神话由于民族心理、生存环境的不同,神话所表现出的差异也较为明显,这其中大体有如下四点:首先,盗火者的身份不同,满族的托阿在天神的选择下由人变成了火神,羌族的燃比娃是半兽半人形象的神人之子,彝族的勒眯是动物;其次,盗火的帮助者和阻碍者不同,由表2可见其中差异;再次,盗火的次数不同,满族和羌族都是三次盗火,彝族是四次取火;最后,盗火的方法有所不同,彝族是偷看到打石取火的方法,满族和羌族的三次取火过程都是利用特定的工具进行盗火,满族利用了葫芦和白石,而羌族利用火把、瓦盆和白石,两个民族所选取的意象也有着特定的含义,火把和瓦盆是较早盛放火种的实用工具,相比而言葫芦是“农耕社会的产物,野生葫芦的发现以及利用或种植葫芦并利用是较晚近的生活反映”[16]499,裕固族的神话中也有火葫芦的形象,神话中葫芦作为一定的象征物已然成为盛火的神器,可见象征物的选择是有独特的民族认同在其中。而满族和羌族同样选择藏火于石的方式成功取出火种,这既表现出先民认识到打石取火的可能性,又反映出两个民族有“相同的白色石头崇拜习俗文化”[16]499。
除此之外,汉族和普米族的盗火神话则经历了两次取火的过程。如《商伯盗火》中商伯初次向人间偷着投放火种而未能成功,当他被贬下凡时便趁机再次盗出火种,他把点着的蒿绳藏在了衣服下面,这样人间便有了火种。汉族商伯的第二次盗火行为与满族的托阿恩都哩第三次盗火有着些许的相似,他们都是趁下凡之际采用了“藏”的方式,才从天上带来火种,只是“藏”的手段不同而已。而普米族《盗火记》中的普米少年上天向天神求火,天神派人考察人间后决定不给少年火种,少年无奈之下便趁天兵天将寻欢作乐之际从金房偷出火种,由于天兵追杀而被迫吞下火种,将火种带到人间。普米少年的取火行为也是两次,盗火行动却是一次,神话将盗火的主观原因作了较为合理的阐释,对于掌火者不愿借火的行为,只能采取偷取或者武力争夺的方式。普米少年在求火失败后,独自面对庞大的天神势力只能采取偷盗的方法。
各民族盗火的手段各有特色,其方法不能一一尽述。盗火的过程是盗火神话的关键环节,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因地域、语言、历史、文化的不同,又体现出了各自较有差异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
三、盗火的结局
作为盗火神话的最后环节,盗火的结局大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盗火者的结局,另一方面是盗火结局所产生的关联性。
(一)盗火者的结局
盗火者的不同结局决定着盗火神话的文化影响力和民族精神的传承。这里仅从三个方面论述盗火者的结局。
1.理想的完美结局
人们希望为人类成功盗取火种的英雄都能收获完美的结局,神话中的结局便是对这一殷切希望的最好回答,如畲族、回族、羌族、满族等民族的盗火神话,都有着类似的完美结局。如畲族的神话赋予盗火英雄双赢的结局,盗火者雷豹不仅成功偷出火种、制服火魔,同时也收获了与云仙子的爱情。满族的女英雄日吉纳姑娘与火魔争斗,本已葬身火魔腹中,但满族人却认为她并未牺牲,而是在降服火魔之后成了王母的第七个仙女。神话中所增添的这些情节,恰恰是人们对英雄不死的期望,也促使了美好结局的产生。
2.悲情色彩的结局
相比较而言,中国诸民族盗火神话的结局多数是较为悲情的,有的盗火者承载着身体上的煎熬,如满族的拖亚拉哈女神本是美女神,而在吞下火种之后则变成了“虎目、虎耳、豹头、豹须、獾身、鹰爪、猞猁尾”[3]760的怪物,苗族的盘老大盗火后受到了玉帝的惩罚,使他的肚皮、肠子和心被老鸹和老鹰啄食。有的盗火者则为盗得火种而付出生命,如汉族、满族、裕固族、哈尼族、纳西族、普米族、水族等民族的盗火者,他们付出生命的方式大体有四种:一是吞火而死,如哈尼族的阿扎将魔怪的火珠吞进肚里,最后用竹片刀扎进自己的胸膛而取出火种,普米族的少年吞下火种变成了火球而将火种带回人间;二是以身制火,如满族的日吉纳姑娘钻进火魔的肚中,裕固族的莫拉用自己的身子压住火葫芦的喷火口而变成了红石山;三是葬身火中,如纳西族的昂姑咪手捧火种下界而被烧焦,水族的阿晅仙女争斗不过雷公而投火自尽,化为大黑岩山而终年燃烧烈火;四是以身护火,如汉族的商伯筑起高台保护火种而被饿死,赫哲族的都热马林老人把木炭抱在怀中保住火种,却牺牲了自己。
3.较为平淡的结局
盗火的结局当然也有较为平淡的,神话之中由于过多关注盗火的方法而忽视了盗火者的个人结局,如彝族的勒眯、布朗族的岩多、藏族的登巴均消失在盗火之后,如藏族的盗火者登巴将偷取的火炭交给协助动物之后便不再出现。此外,盗火神话的最后往往能与动物特定部分的来历相衔接,像藏族盗火神话中的青蛙被追赶的巨人扯掉了尾巴,蒙古族的燕子在盗火之后被天上的主妇剪掉了一块尾巴。虽如此,对盗火者而言,这也算是较为平淡的结局。
(二)盗火结局所产生的关联性
盗火神话结局所产生的关联性在部分民族的神话中也曾出现,这其中体现了各民族对火传承的民族精神与态度,盗火的最后是各民族都获得了火种,但由于各民族都体验到了获得火种过程的艰辛和祖先取火的不易,因而产生了围绕盗火英雄的种种民俗事项、祭祀礼仪、节庆活动,这里仅就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1.盗火结局与民族风俗的关联
通过分析诸多民族盗火神话的结尾,不难发现很多民族的盗火结局都与本民族特定的民风民俗有紧密的联系。如羌族的燃比娃用白石给本民族带来了第一堆火,羌族人们为此而把白石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灵而崇敬,同时也将尊重火的习俗流传下来,并为此而解释了跳锅庄的起源。普米族的少年舍身取火后,普米族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少年,流传下围着火把唱歌跳舞的活动,被称为“查蹉”。布朗族岩多取火成功后,人们为了感谢岩多和松鼠的贡献,而专门诞生了“松鼠节”,以此铭记他们盗火的功绩。
2.盗火结局与特定的祭祀活动有关联
盗火者为盗火事业付出了生命或因盗火而获得了悲惨的下场之后,本民族便流传下来相关的祭祀活动,以此纪念盗火英雄的业绩。如纳西族的昂姑咪以身取火后,摩梭人便在火塘前方摆放锅庄石,他们认为昂姑咪的灵魂住在锅庄石内,也因此传承下来世代祭拜锅庄石的习俗。汉族的商伯为保护火种而被饿死在高台之上,中原广大地区的百姓每年都会有三次相对固定的时间对火神商伯进行祭拜。满族的拖亚拉哈女神盗火后变成怪兽,满族人民为了感谢她,每年定期都会有对盗火女神的祭祀活动。
3.盗火结局与火神的认定或火的命名有直接的关联
盗火结局还与火神的认定或火的命名有直接的关联。如赫哲族的都热马林在护火死后,人们将其尊为火神。哈尼族的阿扎献身取火后,哈尼族人为了纪念他而将火的名字称作“阿扎”。
当然,盗火者作为各民族的盗火英雄,他们的行为对本民族而言都是正义的,他们的付出是为民族所认可的,但是对于非正义行为的盗火行为,盗火者却有着别样的结局。如门巴族的盗火者萨被天神截断之后,萨因受水珠的影响而变成不死之身,其上半身成为造成日食月食的九头龙,下半身则变成了蛇,萨是力量较为强大的盗火者,是盗取文明之火的入侵者,这样的形象既表达了门巴族人民对以萨为代表的盗火者的憎恶之情,又忌惮其残忍的性情和强大的力量。其实,美好的理想是神话所寄托的祝愿,英雄的存在与否和结局的成败也许只存在于先民古老的记忆之中,透过神话人们所能感受到的是先民所传达的民族精神和对文明之路探求的执着。
盗火神话作为世界性的文化获取类的母题,在传承民族进取精神和探索文明之源方面都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所蕴含的信息量较为丰富,传递的民族情感符合时代精神,歌颂的主题较为明确和积极,因此国内外有不少学者都对盗火神话进行过分析研究,目前笔者所搜集到的中国盗火神话及其变体的文本资料,存在于汉族、满族、蒙古族、哈尼族、羌族、瑶族等19个民族之中。从盗火神话的文本叙事来看,该类神话主要由盗火的原因、过程和结局等三个环节组合而成。首先,盗火的原因是发生盗火行为的前提,先民一方面认识到火具有御寒和提高生活质量的作用,同时也认为火不存在于人间,但他们不懂得保存火种和取火的方法,因此采取必要的手段为本氏族夺得火源。其次,盗火的过程是盗火神话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主要围绕守火者和盗火者之间的斗智斗勇展开,各民族不仅在盗火的方法上展现出了独特的聪睿智慧和顽强的民族精神,而且在守火者和盗火者的甄选上也与各民族不同的思维取向、价值认同、民族习俗和文化心理产生了必然关联。最后,盗火的结局是盗火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和影响,这里既涉及盗火者的结局,也涵盖了盗火行为对后世的影响,如部分民族的盗火神话所产生的结果,都与本民族特定的民俗与祭祀活动联系起来。此文对盗火神话的三个环节着重进行了比较研究。
盗火神话还原了特定阶段先民对文明之火的争夺之战,神话的幻想之中涵盖着一定的历史真实,正如弗雷泽所言“火起源神话虽具有夸张和幻想的特点,掩盖和歪曲了很多事实,但实质上仍旧是包含着现实的成分的”[17]186,弗雷泽同时将人类进化中对于火的发现分作三个阶段:无火时代、用火时代和燃火时代[17]185。盗火神话出现的时代应在从无火时代到用火时代的过渡阶段,为了获取自身生存的可能,在与自然和其他氏族部落的抗争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火存在的重要意义和以火来提高生存质量的可能性,经过较为漫长的岁月和较长时期的探索,火将原始先民带到了文明社会,野蛮与文明的生活方式区别开来,人类的文明史开启了新的时代,人们也渐渐接受了文明之火。盗火神话将人们带入先民探索人类文明的时代,但神话毕竟与历史的真实有着反差,它其中较为奇特的幻想之中虽有真实的成分,然而还原神话的现实原貌则需要一定的阶段。人们从最初认识世界上第一个普罗米修斯,到在世界各地发现形形色色的普罗米修斯们,各地盗火神话的发掘已经为揭开神话的神秘面纱提供了可能。先民追求文明的执着精神正凭借神话的力量传承至今,而对于盗火神话的探索尚需进一步展开,笔者希望能够在更多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对盗火者和守火者的甄选加以论证,对盗火神话的文化精神进行深入探究。
注释:
①这里包括关于火神、火崇拜、火的保存等神话。
②盗火神话中的实际掌管火种的和守护火种的并非都由一神或一人来担当。
[1]路威.《文明与野蛮》(第2版)[M].吕叔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陶阳,钟秀.中国神话(中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4]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M]//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下册).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8.
[5]谷德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6]张振犁.华夏族系“盗火神话”试探[M]//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神话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姚宝瑄.中国各民族神话·十二·哈尼族[M].太原:书海出版社,2014.
[8]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
[9]陈建勤.日本鸟(日)文化溯源——稻作鸟(日)崇信的发生和流变[J].民间文学论坛,1998(2).
[10]龙耀宏.鸡的神话和鸡的文化[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11]李昉.太平御览(卷第九百一十八·羽族部五·鸡)(第八册)[M].夏剑钦,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2]吴裕成.酉鸡有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3]王亚军.云南哈尼族白宏人“磕竹筒”习俗考释[J].兰台世界,2015.
[14]宋濂.元史(卷七十九·志第二十九·舆服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史习成.东方神话传说(第八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6]那木吉拉.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0.
[17]弗雷泽.火起源的神话[M].夏希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谢雪莲
The Motif of Myth of Stealing Fire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LI Peng
(Department of Mongo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81)
Myth of Stealing Fire,as a motif of worldly cultural acquisition,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 of civilization.The Myth of Stealing Fire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spreads mainly in the Han,Man,Mongolian,Qiang,and dozens of ethnic groups.This paper comparatively studies the reasons,methods,outcomes of Stealing Fire through text data currently collected.There is truth behind the fantasy of Myth of Stealing Fire of all nationalities.It can analyze the various inherent cultural connotation by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Myth of Stealing Fire,Chinese nationalities,motif
C954
A
1674-8891(2016)04-0014-06
2016-05-2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研究生科研项目,项目号:10301-01500202)。
李鹏(1986—),男,蒙古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方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