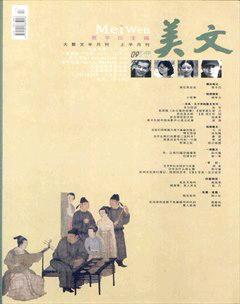粉丝与知音
大陆与台湾、香港的交流日频,中文的新词也就日益增多。台湾的“作秀”、香港的“埋单”、大陆的“打的”,早已各地流行。这种新生的俚语,在台湾的报刊最近十分活跃,甚至会上大号标题。其中有些相当伧俗,例如“凸槌”“吐槽”“劈腿”“嘿咻”等等,忽然到处可见,而尤其不堪的,当推“轰趴”,其实是从英文 home party 译音过来,恶形恶状,实在令人不快。当然也有比较可喜的,例如“粉丝”。
“粉丝”来自英文的 fan,许多英汉双解辞典,包括牛津与朗文两家,迄今仍都译成“迷”;实际搭配使用的例子则有“戏迷”“球迷”“张迷”“金迷”等等。“粉丝”跟“迷”还是不同:“粉丝”只能对人,不能对物,你不能说“他是桥牌的粉丝”或“他是狗的粉丝”。
Fan 之为字,源出 fanatic,乃其缩写,但经瘦身之后,脱胎换骨,变得轻灵多了。Fanatic 本来也有恋物羡人之意,但其另一含义却是极端分子、狂热信徒、死忠党人。《牛津当代英语高阶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第七版为此一含义的 fanatic 所下的定义是:a person of extreme or dangerous opinions,想想有多可怕!
但是蜕去毒尾的 fan 字,只令人感到亲切可爱。更可爱的是,当初把它译成“粉丝”的人,福至心灵,神来之笔竟把复数一并带了过来,好用多了。单用“粉”字,不但突兀,而且表现不出那种从者如云纷至沓来的声势。“粉丝”当然是多数,只有三五人甚至三五十人,怎能叫作 fans?对偶像当然是说“我是你的粉丝”,怎么能说“我是你的粉”呢?粉,极言其细而轻,积少成多,飘忽无定。丝,极言其虽细却长,纠缠而善攀附,所以治丝益棼,欲理还乱。
这种狂热的崇拜者,以前泛称为“迷”,大陆叫作“追星族”,嬉皮时代把追随著名歌手或乐队的少女叫作“跟班癖”(groupie),西方社会叫作“猎狮者”(lion hunter)。这些名称都不如“粉丝”轻灵有趣。至于“忠实的读者”或“忠实的听众”,也嫌太文,太重,太正式。
粉丝之为族群,有缝必钻,无孔不入,四方漂浮,一时啸聚,闻风而至,风过而沉。这现象古已有之,于今尤烈。宋玉《对楚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究竟要吸引多少人,才能称粉丝呢?学者与作家,能号召几百甚至上千听众,就算拥有粉丝了。若是艺人,至少得吸引成千上万才行。现代的媒体传播,既快又广,现场的科技设备也不愁地大人多,演艺高手从帕瓦罗蒂到猫王,轻易就能将一座体育场填满人潮。一九六九年纽约州伍德斯塔克三天三夜的露天摇滚乐演唱会,吸引了四十五万的青年,这纪录至今未破。另一方面,诗人演讲也未可小觑:艾略特在明尼苏达大学演讲,听众逾一万三千人;弗罗斯特晚年也不缺粉丝,我在爱荷华大学听他诵诗,那场听众就有两千。
二
与粉丝相对的,是知音。粉丝,是为成名锦上添花;知音,是为寂寞雪中送炭。杜甫尽管说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有知音出现,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这寂寞的寸心还是欣慰的。其实如果知音寥寥,甚至迟迟不见,寸心的自信仍不免会动摇。所谓知音,其实就是“未来的回声”,预支晚年的甚至身后的掌声。梵高去世前一个多月写信告诉妹妹维尔敏娜,说他为嘉舍大夫画的像“悲哀而温柔,却又明确而敏捷——许多人像原该如此画的。也许百年之后会有人为之哀伤”。画家寸心自知,他画了一张好画,但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没有知音来肯定、印证,只好寄望于百年之后了。“也许百年之后会有人……”语气真是太自谦了。《嘉舍大夫》当然是一幅传世的杰作,后代的艺术史家、评论家、观众、拍卖场都十分肯定。梵高生前只有两个知音:弟弟西奥与评论家奥里叶,死后的十年里只有一个:弟媳妇乔安娜。高更虽然是他的老友,本身还是一位大画家,却未能真正认定梵高的天才。
知音出现,多在天才成名之前。叔本华的母亲是畅销小说家,母子两人很不和谐,但歌德一早就告诉做母亲的,说她的孩子有一天会名满天下。歌德的预言要等很久才会兑现:寂寞的叔本华要等到六十六岁,才收到华格纳寄给他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附言中说对他的音乐见解十分欣赏。
美国文坛的宗师埃默森收到惠特曼寄赠的初版《草叶集》,回信说:“你的思想自由而勇敢,使我向你欢呼……在你书中我发现题材的处理很大胆,这种手法令人欣慰,也只有广阔的感受能启示这种手法。我祝贺你,在你伟大事业的开端。”那时惠特曼才三十六岁,颇受论者攻击。苏轼考礼部进士,才二十一岁,欧阳修阅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欣赏,竟对梅圣俞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众多举子听了此话,哗然不服,日久才释然。
有些知音,要等天才死后才出现。莎士比亚死后七年,生前与他争雄而且不免加贬的班琼森,写了一首长诗悼念他,肯定他是英国之宝:“全欧洲的剧坛都应加致敬。/他不仅流行一时,而应传之百世!”又过了七年,另一位大诗人米尔顿,在他最早的一首诗《莎士比亚赞》中,断言莎翁的诗句可比神谕(those Delphic lines),而后人对他的崇敬,令帝王的陵寝也相形逊色。今人视莎士比亚之伟大为理所当然,其实当时盖棺也未必论定,尚待一代代文人学者的肯定,尤其是知音如班琼森与米尔顿之类的推崇,才能完成“超凡入圣”(canonization)的封典。有时候这种封典要等上几百年才举行,例如邓约翰的地位,自十七世纪以来一直毁誉参半,欲褒还贬,要等艾略特出现才找到他真正的知音。
此地我必须特别提出夏志清来,说明知音之可贵,不但在于慧眼独具,能看出天才,而且在于胆识过人,敢畅言所见。四十五年前,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在美国出版,钱钟书与张爱玲赫然各成一章,和鲁迅、茅盾分庭抗礼,令读者耳目一新。文坛的旧观,一直认为钱钟书不过是学府中人,偶涉创作,既非左派肯定的“进步”作家,也非现代派标榜的“前卫”新锐;张爱玲更沾不上什么“进步”或“前卫”,只是上海洋场一位言情小说作者而已。夏志清不但看出钱钟书、张爱玲,还有沈从文在“主流”以外的独创成就,更要在四十年前美国评论界“左”倾成风的逆境里,毫不含糊地把他的见解昭告世界,真是智勇并兼。真正的文学史,就是这些知音写出来的。有知音一锤定音,不愁没有粉丝,缤纷的粉丝啊,蝴蝶一般地飞来。
知音与粉丝都可爱,但不易兼得。一位艺术家要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才能兼有这两种人。如果他的艺术太雅,他可能赢得少数知音,却难吸引芸芸粉丝。如果他的艺术偏俗,则吸引粉丝之余,恐怕赢不了什么知音吧?知音多高士,具自尊,粉丝拥挤甚至尖叫的地方知音是不会去的。知音总是独来独往,欣然会心,掩卷默想,甚至隔代低首,对碑沉吟。知音的信念来自深刻的体会,充分的了解。知音与天才的关系有如信徒与神,并不需要“现场”,因为寸心就是神殿。
粉丝则不然。这种高速流动的族群必须有一个现场,更因人多而激动,拥挤而歇斯底里,群情不断加温,只待偶像忽然出现而达于沸腾。所以我曾将 teenager 译为“听爱挤”。粉丝对偶像的崇拜常因亲近无门而演为“恋物癖”,表现于签名、握手、合影,甚至索取、夺取“及身”的纪念品。披头士的粉丝曾分撕披头士的床单留念;汤姆·琼斯的现场听众更送上手绢给他拭汗,并即将汗湿的手绢收回珍藏。据说小提琴神手帕格尼尼的听众,也曾伸手去探摸他的躯体,求证他是否真如传说所云,乃魔鬼化身。其实即便是宗教,本应超越速朽的肉身,也不能全然摆脱“圣骸”(sacred relics)的崇拜。佛教的佛骨与舍利子,基督的圣杯,都是例子,东正教的圣像更是一门学问。
“知音”一词始于春秋:楚国的俞伯牙善于弹琴,唯有知己钟子期知道他意在高山抑或流水。子期死后,伯牙恨世无知音,乃碎琴绝弦,终身不再操鼓。孔子对音乐非常讲究,曾告诫颜回说,郑声淫,不可听,应该听舜制的舞曲韶。可是《论语》又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么看来,孔子真可谓知音了,但是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岂不成了香港人所说的“发烧友”了?孔子或许是最早的粉丝吧。今日的乐迷粉丝,不妨引圣人为知音,去翻翻《论语》第七章《述而》吧。
不惜歌者苦,
但伤知音稀。
粉丝已经够多了,且待更多的知音。
失帽记
二〇〇八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变化,其间有得有失。这一年我自己年届八十,其间也得失互见:得者不少,难以细表,失者不多,却有一件难过至今。我失去了一顶帽子。
一顶帽子值得那么难过吗?当然不值得,如果是一顶普通的帽子,甚至是高价的名牌。但是去年我失去的那顶,不幸失去的那一顶,绝不普通。
帅气,神气的帽子我戴过许多顶,头发白了稀了之后尤其喜欢戴帽。一顶帅帽遮羞之功,远超过假发。丘吉尔和戴高乐同为二战之英雄,但是戴高乐戴了高帽尤其英雄,所以戴高乐戴高帽而乐之,也所以我从未见过戴高乐不戴高帽。
戴高乐那顶高卢军帽丢过没有,我不得而知。我自己好不容易选得合头的几顶帅帽,却无一久留,全都不告而别。其中包括两顶苏格兰呢帽,一顶大概是掉在英国北境某餐厅,另一顶则应遗失在莫斯科某旅馆。还有第三顶是在加拿大维多利亚港的布恰花园所购,白底红字,状若戴高乐的圆筒鸭舌军帽而其筒较低:当日戴之招摇过市,风光了一时,后竟不明所终。
一个人一生最容易丢失也丢得最多的,该是帽与伞。其实伞也是一种帽子,虽然不戴在头上,毕竟也是为遮头而设,而两者所以易失,也都是为了主人要出门,所以终于和主人永诀,更都是因为同属身外之物,一旦离手离头,几次转身就给主人忘了。
帽子有关风流形象。独孤信出猎暮归,驰马入城,其帽微侧,吏人慕之,翌晨戴帽尽侧。千年之后,纳兰性德的词集亦称《侧帽》。孟嘉重九登高,风吹落帽,浑然不觉。桓温命孙盛作文嘲之,孟嘉也作文以答,传为佳话,更成登高典故。杜甫七律《九日蓝田崔氏庄》并有“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之句。他的《饮中八仙歌》更写饮者的狂态:“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尽管如此,失帽却与风流无关,只和落拓有份。
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为我八秩庆生,举办了书刊手稿展览,并邀我重回沙田去签书、演讲。现场相当热闹,用媒体流行的说法,就是所谓人气颇旺。联合书院更编印了一册精美的场刊,图文并茂地呈现我香港时期十一年,在学府与文坛的各种活动,题名《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学生命》,在现场送给观众。典礼由黄国彬教授代表文学院致词,除了联合书院冯国培院长、图书馆潘明珠副馆长、中文系陈雄根主任等主办人之外,与会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卢玮銮、张双庆、杨钟基等,令我深感温馨。放眼台下,昔日的高足如黄坤尧、黄秀莲、樊善标、何杏枫等,如今也已做了老师,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讲的听众多为学生,由中学老师带领而来。讲毕照例要签书,为了促使长龙蠕动得较快,签名也必须加速。不过今日的粉丝不比往年,索签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签书、签笔记本、签便条、签书包、签学生证,还要题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赠言,当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签人即兴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什么 whay?恩惠的惠吗?”“不是的,是智慧的慧。”“也不是,是恩惠的惠加草字头。”乱军之中,常常被这么乱喊口令。不仅如此,一粉丝在桌前索签,另一粉丝却在你椅后催你抬头、停笔、对准众多相机里的某一镜头,与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夹缝之中又有第三只手伸来,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这时你必须全神贯注,以免出错。你的手上,忽然是握着自己的笔,忽然是他人递过来的,所以常会掉笔。你想喝茶,却鞭长莫及。你想脱衣,却匀不出手。你内急已久,早应泄洪,却不容你抽身疾退。这时,你真难身外分身,来护笔、护表、护稿,扶杯。主办人焦待于漩涡之外,不知该纵容或喝止炒热了的粉丝。
去年底在中文大学演讲的那一次,听众之盛况不能算怎么拥挤,但也足以令我穷于应付,心神难专。等到曲终人散,又急于赶赴晚宴,不遑检视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川流不息,始终无法定神查看。餐后走到户外,准备上车,天寒风起,需要戴帽,连忙逐袋寻找。这才发现,我的帽子不见了。
事后几位主人回去现场,又向接送的车中寻找,都不见帽子踪影。我存和我,夫妻俩像侦探,合力苦思,最后确见那帽子是在何时,何地,所以应该排除在某地,某时失去的可能,诸如此类过程。机场话别时,我仍不放心,还谆谆嘱咐潘明珠、樊善标,如果寻获,务必寄回高雄给我。半个月后,他们把我因“积重难返”而留下的奖牌、赠书、礼品等等寄到台湾。包裹层层解开,真相揭晓,那顶可怜的帽子,终于是丢定了。
仅仅为了一顶帽子,无论有多贵或是多罕见,本来也不会令我如此大惊小怪。但是那顶帽子不是我买来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为人子继承得来的。那是我父亲生前戴过的,后来成了他身后的遗物,我存整理所发现,不忍径弃,就说动我且戴起来。果然正合我头,而且款式潇洒,毛色可亲,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顶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后高,戴在头上,由后脑斜压向前额,有优雅的缓缓坡度,大致上可称贝瑞软帽(beret),常覆在法国人头顶。至于毛色,则圆顶部分呈浅陶土色,看来温暖体贴。四周部分则前窄后宽,织成细密的十字花纹,为淡米黄色。戴在我的头上,倜傥风流,有欧洲名士的超逸,不止一次赢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睐。但帽内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气愈寒,尤其风大,帽内就愈加温暖,仿父亲的手掌正护在我头上,掌心对着脑门。毕竟,同样的这一顶温暖曾经覆盖过父亲,如今移爱到我的头上,恩佑两代,不愧是父子相传的忠厚家臣。
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双亲之爱,才有今日之我。当年父亲爱我,应该不逊于母亲。但小时我不常在他身边,始终呵护着我庇佑着我的,甚至在抗战沦陷区逃难,生死同命的,是母亲。呵护之亲,操作之劳,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没有为我做过?反之,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打过我,甚至也从未对我疾言厉色,所以绝非什么严父。不过父子之间始终也不亲热。小时他倒是常对我讲论圣贤之道,勉励我要立志立功。长夏的蝉声里,倒是有好几次父子俩坐在一起看书:他靠在躺椅上看《纲鉴易知录》,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国演义》。冬夜的桐油灯下,他更多次为我启蒙,苦口婆心引领我进入古文的世界,点醒了我的汉魄唐魂。张良啦,魏征啦,太史公啦,韩愈啦,都是他介绍我初识的。
后来做父亲的渐渐老了,做儿子的越长大了,各忙各的。他宦游在外,或是长期出差数下南洋,或担任同乡会理事长,投入乡情侨务;我则学府文坛,烛烧两头,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自中年起他就因关节病苦于脚痛,时发时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于失明。二十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学之聘,由香港来高雄定居。我存即毅然卖掉台北的故居,把我的父亲、她的母亲一起接来高雄安顿。
许多年来,父亲的病情与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顾,并得我岳母操劳陪伴。身为他的独子,我却未能经常省视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母亲临终时的泪眼,谆谆叮嘱:爸爸你要好好照顾。实在愧疚无已。父亲和母亲鹣鲽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赖。只记得他们大吵过一次,却几乎不曾小吵。母亲逝于五十三岁,长她十岁的父亲,尽管亲友屡来劝婚,却终不再娶,鳏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还是忍年,九十七岁。
可怜的老人,以风烛之年独承失明与痛风之苦,又不能看报看电视以遣忧,只有一架古董收音机喋喋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么呢?除了亡妻和历历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独子为什么不常在身边。而即使在身边时,也从未陪他久聊一会,更从未握他的手或紧紧拥抱住他的病躯。更别提四个可爱的孙女,都长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听得见谁的声音?
长寿的代价,是沧桑。
所以在遗物之中竟还保有他常戴的帽子,无异是继承了最重要的遗产。父亲在世,我对他爱得不够,而孺慕耿耿也始终未能充分表达。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遗憾,而自他去后,我遗憾更多。幸而还留下这么一顶帽子,未随碑石俱冷,尚有余温,让我戴上,幻觉未尽的父子之情,并未告终,幻觉依靠这灵媒之介,犹可贯通阴阳,串连两代,一时还不致径将上一个戴帽人完全淡忘。这一份与父共帽的心情,说得高些,是感恩,说得重些,是赎罪。不幸,连最后的这一点凭借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来时,风势助威,我站在岁末的风中,倍加畏冷。对不起,父亲。对不起,母亲。
故国神游
五月中旬去西安讲学。那是我第一次去陕西,当然也是首访西安,对那千年古都神往既久,当然也有莫大的期待。结果几乎扑了一个空。当然那是我自己浅薄,去投的又是如此深厚的传统,加以为期不满五天,又有两场演讲、一场活动,所以知之既少,入之又浅,谈不上有何心得。“五日京兆”吗?从西周、西汉、西晋一直到隋唐,从镐京、咸阳、渭城到长安,其中历经变化,史学家甚至考古学家都得说上半天。自宋以来,其帝国之光彩就已渐渐失色,所以轮到贾平凹来写《老西安》一书时,他的副题干脆就叫作“废都斜阳”了。
从头到尾,今日西安市中心的主要景点,例如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等,都过门而未入。倒是听西安人说,钟楼与鼓楼正是成语“晨钟暮鼓”之所由,而古人买东西得跑去东市和西市,因此而有“买东西”一词。最令我感动的是,西安还有一处“燕国志士荆轲墓”。矛盾的是,我对这古都虽然所知不多,所见更少,可是所感所思却很深。这么多年,我虽然一步也未踏过斯土,可是自作多情地却写过好几首诗,以长安为背景或现场。
我在西安的第一场演讲就叫作“诗与长安”:前面一小半多引古人之作,例如李白的《忆秦娥》、杜牧的《将赴吴兴登乐游原》、白居易的《长恨歌》、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和《世说新语》日近长安远之说。
后面的大半场就引到我自己所写涉及长安的诗,一共七首,依次是《秦俑》《寻李白》《飞碟之夜》《昭君》《盲丐》《飞将军》《刺秦王》。我用光盘投影,一路说明并朗诵。《秦俑》颇长,从古西安说到西安事变,从桃花源说到十二尊金人和徐福的六千童男女;中间引入《诗经·秦风》四句,我就曼声吟诵出来,颇有三维效果。《寻李白》有赞谪仙三行:“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入选许多选集。《飞碟之夜》用科幻小说笔法想象安禄山的飞碟部队如何占领长安。《昭君》讽刺,卫青与霍去病都无法达成的事,竟要弱女子去承担。《盲丐》写我自己在美国远怀汉唐盛世的苦心,结尾有这样两句:“一枝箫哭一千年/长城,你终会听见,长安,你终会听见”。《飞将军》为汉朝的名将李广抱不平,其事皆取自《史记》。《刺秦王》也本于《史记》,但叙事则始于荆轲谋刺失败,伤重倚柱时的感慨。这些事,凡中国的读书人都应知道,而这些诗,凡中国的心灵都会共鸣。行知学院礼堂上坐满的两千五百人,虽欠空调,却无人离席。
另一场演讲在西安美术学院,题为“诗与美学”,情况也差不多。更值得一记的,是该校活泼的校风与可观的校园。在会议室与长廊上,一排排黑白的人像照吸引我左顾右盼,屡屡停步,只因照中人都有美学甚至文化的地位,就我匆匆一瞥的印象,至少包含蔡元培、陈寅恪、鲁迅、胡适、徐悲鸿、朱光潜、梁思成、林徽因、蔡威廉(蔡元培之女)、林文铮(蔡元培女婿,杭州艺专教务长);外国人之中还有法兰克福学派主角的哲学家马尔库色。
至于校园何以特别可观,却只消一瞥就立可断定。远处纵目,只见一排排一丛丛直立的方尖石体,高低参差,平均与人相等,瞬间印象又像碑林,又像陶俑。其实都不是,主人笑说,而是“拴马桩”。走近去看,才发现那些削方石体,雕纹或粗或细,顶上都踞着、栖着、蹲着、跪着一座雕品,踞者许是雄狮、栖者许是猛禽、蹲者许是圉人、跪者许是奴仆,更有奴仆或守卫之类跨在狮背,千奇百怪,难以缕陈。人物的体态、面貌、表情又不同于秦兵的陶俑,该多是胡人吧,唐三彩牵马的胡圉正是如此。主人说这些拴马桩多半来自渭北的农庄。看今日西安市地图,西北郊外汉长安旧址就有罗家寨、马家寨、雷家寨等六七个寨,说不定就来自那些庄宅;当然,客栈、酒家、衙门前面也需要这些吧。正遐想间,主人又说,那边还有不少可看,校园里有好几千桩。我们夫妻那天真是大开眼界:这和江南水乡处处是桥与船大不相同。
我去西安,除了讲学之外,还参加了一个活动,经“粥会”会长陆炳文先生之介,认识了于右任先生(1879-1964)的后人。右老是陕西三原县人,早年参与辛亥革命,后来成了党国大老,但在文化界更以书法大师久享盛誉。他是长我半个世纪的前辈,但是同在台湾,一直到他去世,我都从未得识耆宿。我更没有想到,海峡两岸对峙,尽管历经反右与“文革”的重大变化,陕西人对这位远隔的乡贤始终血浓于水,保持着敬爱与怀念。因此早在二〇〇二年,复建于右任故居的工作已在西安展开,七年后正值他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终于及时落成。
右老乃现代书法大家,关中草圣,原与书法外行的我难有联想。但是他还是一位著名诗人,在台所写怀乡之诗颇为陕西乡亲所重。有心人联想到我的《乡愁》一诗,竟然安排了一个下午,就在“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内,举办“忆长安话乡愁”雅集,由西安文坛与乐界的名流朗诵并演唱右老与我的诗作共二十首。盛会由右老侄孙于大方、于大平策化,我们夫妻得以认识右老的许多晚辈,更品尝了于府精美的厨艺,领略了右老曾孙辈的纯真与礼貌。
对这位前辈,我曾凑过一副对联:“遗墨淋漓长在壁,美髯倜傥似当风。”为了要写西安之行,我读了贾平凹的《老西安》一书。像贾平凹这样的当代名家,我本来以为不会提到意识对立而且已故多年的右老。不料他说于右任曾跑遍关中搜寻石碑,几乎搜尽了陕西的魏晋石碑,并“安置于西安文庙,这就形成了至今闻名中外的碑林博物馆”,他又说:“西安人热爱于右任,不仅爱他的字,更爱他一颗爱国的心,做圣贤而能庸行,是大人而常小心。”最后他说:“于右任、吴宓、王子云、赵望云、石鲁、柳青……足以使陕西人和西安这座城骄傲。我每每登临城头,望着那南北纵横井字形的大街小巷,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他们。”
贾平凹这本《老西安》写得自然而又深入,显示作者真是性情中人。书中还有这么一段,很值得玩味:“毛主席在陕北生活了十三年,建国后却从未再回陕西,甚至只字未提过延安。这让陕西人很没了面子。”我在西安不过几天,偏偏碰上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七十周年纪念,不但当地还有纪念的活动,北京的《诗刊》也发表了特辑。为何尚不切实反省,真令人叹息。
西安之行,虽然无缘遍访古迹,甚至走马看花都说不上,幸而还去了一趟西安博物院,稍稍解了“恨古人吾不见”之憾。博物院面积颇广,由博物馆、荐福寺、小雁塔三者组成。我存十多年前已来过西安,这次陪我同来,也未能畅览她想看的文物,好在我们还是在此博物馆中流连了近一小时。秦朝的瓦当、西汉的鎏金铜钟、唐朝的三彩腾空骑马胡人俑、鎏金走龙等,还是满足了我们的怀古之情与美感。我存在高雄市美术馆担任导览义工已有十六年,去年还获得文建会的服务奖章。她对古文物,尤其是古玉,所知颇多,并不太需要他人解释,几次开口之后,内地的导览也知道遇见内行了。
另外一件事,她就不陪我了。先是在开花的石榴树荫下,我们仰见了逼在半空的小雁塔,我立刻决定要攀登绝顶。导游的是一位很帅气的青年,他说,很抱歉,规定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不准攀爬。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几乎无塔不登,两年前我在佛罗伦萨登过的百花圣母大教堂和觉陀钟楼都比眼前这小雁塔高,我怎么能拒绝唐代风云的号召呢?于是我对导游说,何妨先陪我爬到第三层,如果见我余勇可贾,就让我一路仰攻到顶如何。他答应了,就和炳文陪我登上第三层,见我并无异状,索性让我放步登高。一层比一层的内壁缩紧,到了十层以上,里面的空间便逼人愈甚,由不得登高客不缩头缩颈,收肘弓腰,谦卑起来。同时塔外的风景也不断地匍匐下去。这时,也没人能够分神去扶别人了。如是螺旋自拔,不让土地公在后拽腿,终于钻到了塔顶。全西安都在脚底了。足之所苦,目之所乐,登高三昧,不过如此。我总相信,登高眺远,等于向神明报到,用意是总算向八荒九垓前朝远代致敬过了。诸公登慈恩寺塔之盛事,不能与杜甫、岑参同步,也算是虚应了故事,写起游记来至少踏实得多。
导游历史熟稔,谈吐不凡,看得出胸怀大志,有先忧后乐的气概,令我油然想到定庵的警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问其姓名,答曰“继伟”。我对他说:“将来我还会听见你的名字。”
这次去西安,错过的名胜古迹太多,只能寄望于他日。但是其中竟有一处平白错过,尤其令我不释。那就是在唐诗中屡次出现的“乐游原”。最奇怪的是:每次我向西安人提起,反应总是漠然,不是根本不知其处,就是知有其处却不在乎。也有人说:这地方有是有,还在那儿,可是你去不了。
李白的词《忆秦娥》,后半阕云:“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王国维赞其后两句,曾说:“寥寥八字,关尽千古登临之口。”此地所谓“登临”,登的是乐游原,临的是汉家陵阙。杜甫七古《乐游园歌》咏当时长安士女春秋佳节登临之盛,前四句是:“乐游古园崒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亟言其地势之高,视域之广。诗末两句则是:“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能够让人“独立苍茫”当然是登临胜地。
到了晚唐,又有一对伤心人,也是李、杜,来此登高怀古。李商隐的《乐游原》非常有名:“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杜牧有两首七绝咏及其地,《登乐游原》说:“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消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另一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又说:“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前引盛唐与晚唐各有李、杜吟咏其地。乐游原在长安东南,诗人登高所望,都是朝西北,那方向不论是汉朝的五陵或唐朝的五陵,都令人怀古伤今,诗情与史感余韵不绝。初唐的王勃有《春日宴乐游园赋韵得接字》一诗,因为是春游,而大唐帝国正值发轫,就没有李、杜甚至陈子昂俯仰古今之叹。
我去西安,受了李、杜的召引,满心以为可以一登古原,西吊唐魂汉魄,印证自己从小吟诵唐诗的情怀。结果扑了一个空。西安的主人见我不甘死心,某夜当真为我驱车,不是去登古原,而是到西安东南郊外,一处上山坡道的起点,昏暗的街灯下但见铁闸深闭,其上有一告示木牌,潦草的字体大书“西安乐游原”。如此而已,更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