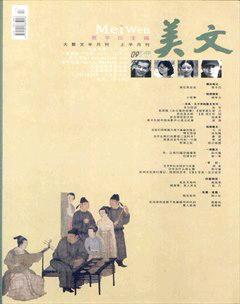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
吴义勤

莫言获奖和当代文学评价的分歧
其实2012年莫言获奖之前,当代文学评价的危机就已经是一个显著的话题。我记得在2012年10月诺奖公布前几个星期开始,莫言的手机就已经关了,找不到他了。为什么?因为他躲在高密的家里。那个时候,博彩公司的排位他一度冲到第一位,后来虽下降到第三位,但媒体已开始炒作他了。每天有记者给他打电话,问他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说我怎么回答呢,说不得也不行,说得也不行,总归是不好回答,因此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
很有意思的是当天的媒体。有学者当天接受采访说中国作家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但是大概再过10年到20年有希望能得诺贝尔奖。这话的潜台词其实就是莫言当年还不能得奖。这里有很复杂的心理因素。莫言得奖之后,《文艺报》当晚就组织一个整版对中国一些著名作家进行电话采访,很多作家除了表示祝贺,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话好讲。大家会发现,文学界其实对获奖也准备不足,没有想到真的会得奖,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但是慢慢地沉淀到现在,种种很复杂的情绪倒表现出来了。
2000年高行健获奖,中国作家普遍的情绪是不屑,觉得如果高行健可以得奖的话,中国至少有100位作家可以获奖。莫言获奖之后,刘震云说中国至少有10位作家可以获奖,降了90位,但是还有10位可以得奖。这种姿态其实可以理解为代表的是对中国文学的高度自信。而社会上,对莫言获奖的说法则是千奇百怪,冷嘲热讽颇多,什么怪话都有。可以说,对莫言获奖,我们整个文学界或者整个社会的反应并不统一,从专业的作家、文学研究者到网络,分歧很大。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既没有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赢得全社会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高度认同,也没有消除我们对于当代文学评价的分歧。相反,这个分歧因为莫言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标志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是因为中国作家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否定当代文学。大家会说你有本领为什么不获诺贝尔文学奖呢。我们每次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网络上都是骂声一片,都说中国评奖如何的不公平、不透明,然后说人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得多么好,多么公正、透明,说人家的历史多么悠久,价值观多么坚定等等。后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实行全透明投票,每一轮的投票,61个评委谁投谁,全部现场直播。这一方面确实是公开透明了,另一方面也给评委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即使这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完之后,网络上还是有连篇累牍的批评,有的人连写八篇批评文章,叫“八评茅八奖”。可以说,拿诺贝尔文学奖来否定当代文学、否定中国文学早就很平常了;但莫言获奖之后情况就反过来了,大家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来否定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了。说诺贝尔文学奖如何腐朽、价值观如何陈旧等等。甚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受贿、人品等话题也开始见诸媒体了。反正,诺贝尔文学奖是不给中国作家不行,给中国作家也不行。这也使得我们看到,莫言获奖之后,整个是非常低调,没有喜形于色,更不要说狂欢了,只是躲在家里吃水饺,出了门都板着个面孔,然后,每次在电视上都特别小心,只说获奖是幸运,甚至说“谁说我是大师,那就是骂我”等等。因此,莫言获奖之后,受夸赞最多的反而不是他的文学,而是他的接受采访的水平,他的低调,他的谦逊,他说话的得体。
有时候,我们确实很困惑,当代文学在今天,几乎看不到真相,我们不知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有多大的成就。按理,我们会认为莫言获奖是当代文学成就达到一个被世界认可的高度的标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然,有很多人极端肯定中国当代文学。比如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回答外国记者的时候,他就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是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一些学者像陈晓明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当代文学已经走到一个比较高的、辉煌的时期。刚刚获安徒生儿童文学奖的曹文轩在多年前就说过,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也就是世界文学的高度。余秋雨、刘再复甚到宣称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当然,他们的判断跟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比较近似,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的判断总体上是很自信的,认为到了文学发展繁荣最好的时候。但是也有极端的否定,认为即使像莫言这样获得诺奖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也是很低的、卑微的,语言都不通,语法都有问题等等。顾彬甚至宣称中国当代文学全是拉圾。
肯定判断的依据当然很多。首先是当代文学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文学GDP的产量是世界第一。比如说长篇小说,原创长篇小说年产量是4000部,这里面还不包括网络长篇小说,网络长篇小说据说一年就有十几万部。4000不是一个大的数量,但只要进行纵横的比较和分析,就会发现这个数字非常了不起。建国后到粉碎“四人帮”30年,我们生产多少部长篇小说?427部。过去30年的时间才生产了427部长篇小说,现在我们一年就4000部,这是纵的比较。从横的方面来说,在世界范围内,跟那些传统文学强国相比,我们也会有某种自豪感,比如俄罗斯,他们的年产量现在是1500部长篇小说;现代主义文学的发源地法国,一年长篇小说的产量是700部;而我们的近邻日本,现在年产量只有400部。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说今天中国文学创造力、生产力空前解放是有根据的。不管怎么样,这是文学生产力解放的标志,是很多人对当代文学充分肯定的依据。
第二个依据是中国作家队伍的空前强大。我们现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有一万人,过去每年只有100多人申请,今年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是1500多人。除了中国作协会员有一万人,各省的会员有近四万人,还不包括那些业余写作者,还有网络写手350万人。因此,中国现在各个层次从事文学创造的人员,数量之多可以说是世界罕见的,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对中国当代文学充分肯定的依据。
第三个依据是对我们文学制度的自信。很多人会说今天文学已经边缘化了,或者商业化对文学的冲击很大,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制度仍然保证着文学的光荣和尊严。整个社会对文学重视的程度,对作家尊重的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仍是首屈一指。在整个文学系统内部,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内部,对于作家的文学创造仍然非常重视。很多作家可以享受跟大学教授一样的职称系列,一级作家相当于大学的教授,享受的待遇也是一样的。政府还会拿出很多的钱来投入文学,比如文学评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骏马奖,这些奖每一次投入都非常大。另外还有重点作品扶持,作家培训等。作家培训制度也是西方很难想象的。
但是我们讲的这些肯定的一方面,很多人恰恰不屑一顾。比如顾彬,对莫言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莫言写得太长,写得太快,只会讲故事,没有思想。但是其实顾彬作为一个德国学者,他读的中国当代作品非常有限。80年代以来,文学界似乎特别重视国外汉学家的观点,从夏志清的文学史引进开始,认为西方学者的观点很重要。他们确实有很好的视角,但是他们接触汉语、中国文学,有的主要是靠他们娶的中国太太。因此很可能他对这个文学作品的认识水平其实是他太太的水平,不是他本人。因为你跟他交流,他汉语都讲得结结巴巴,你说他能够把中国文学研究得多深?张炜的《你在高原》450万字,你叫他怎么读。所以,为什么顾彬特别推崇中国的诗歌,因为诗歌字少至少他读着方便。所以,我觉得汉学家的观点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许多中国的作家和学者倒是借他们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真的都是垃圾。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没有精神高度,没有思想高度,没有对于现实批判的力度,作品数量多但是没有经典,作家人数多但是没有大师,不是连莫言都否认自己是大师么。很多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但不能跟西方文学比,不能跟古代文学比,甚至跟现代文学比的资格都没有。认为跟鲁迅等文学大师相比当代文学作家都是侏儒,连给大师们提鞋倒洗脚水的资格都没有,这其实就是很极端的否定当代文学的一种情况。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两种极端根本就无法调和,无法对话、妥协。这种无法对话的极端造成了我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认识的误导,也造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学真相的遮蔽,导致当代文学陷入了评价的危机。
全民的阅读危机是导致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社会根源
从历史上看,现代文学才30年,当代文学已经60多年了,但对二者的认识向来难以统一。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可能会说是不同的文学观点,不同的文学认识,不同的文学判断或者是思维造成的。但是文学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仅仅从文学内部来看,我们要看到文学背后很复杂的社会背景,这个社会背景就是全社会弥漫的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蔓延到了文学领域,影响了我们对文学的判断。
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中国文学存在危机的话,不是创作危机,而是阅读危机。阅读的高度实际上决定了文学的高度。总书记说我们有高原没高峰。但高原和高峰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去丈量,只能以我们阅读主体的高度做参照,一个巨人和一个侏儒,其对应的高原和高峰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曾经是一个对文学有着异常热情的国家,文学阅读曾经是我们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商品化和娱乐化时代的到来,我们的文学热情迅速下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反阅读、轻阅读、浅阅读的时代。可以说现在与阅读相伴的就是一个反文学的时代。北村曾经写过一个中篇小说《水土不服》,写的是80年代,一个文学的时代,全民文学化的时代,所有人都有一种文学梦,所有人都有写作的冲动。但90年代之后,诗人就水土不服了,只能一次次自杀。主人公康生,在80年代写诗。80年代校园诗人能发表作品,那就是一个文化英雄,一个精神贵族。虽然康生家里很穷,出生在山区,但是他会写诗,班上的女生们都追求他。女主人公是一个校花,老板家的女儿,很有钱,但是她只看上康生,然后他们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之后康生仍然写诗。但进入90年代之后,房子、生活、工作都来了,靠文学已经不能养活他们一家了,他们的爱情也没有了,最后康生自杀了,就这样一个命运。80年代刚刚兴征婚的时候,征婚广告的最后一条一定是“热爱文学”,因为这是一个人基本品味的保证。但是我们今天会看到,文学和诗歌已经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非诚勿扰》一有男嘉宾朗诵诗歌,24盏灯就全灭,这其实是对这个时代文学处境的象征性的表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经做过一个文学阅读的调查,结果让我们大跌眼镜。这个时代文学阅读最正常的是什么人呢,是小学生,进入中学,文学阅读状况就严重恶化,只有12%的中学生有课外阅读的习惯,而大学阅读状况也不理想,甚至中文系的学生坚持课外文学阅读的也只有43%,普通民众更是远离了文学阅读,电影、电视、网络、娱乐已经完全占据了文学阅读的时间。这个可以说是很可怕的状况。
我在大学教当代文学课时,曾经做过一次实验。大学里每次到了学期考试的时候,学生都要求划重点。我说这次不要划重点,也不用去复印女同学的课堂笔记,不用复习,考最简单的,大家都很高兴,充满期待地进入考场,然后我就出了一道题目,请你写出这两年读过的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作品,写对一个得一分。这个题目很简单,我们一年有4000部长篇小说,两年就有8000部长篇小说,而诗歌、散文、戏剧更是多得无以复加,要写出100篇按道理是很容易的。但是考试下来,没有一个人及格,而且更可怕的是连当代文学这个概念都发生了混乱,把《西游记》《红楼梦》全写上了。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题目,大家都已经崩溃了,后来全体补考。
这确实就是今天全民阅读危机的现实。一方面国民的文学阅读量迅速下降,甚至专业读者、文学工作者的阅读量也少得可怜,根本不可能跟上当代文学发展的节奏,大量的文学作品无人问津,细读作品、分析作品的能力更是在下降。据统计中国的年人均读书量是6本,而发达国家最多达到了60本。另一方面,电子化的阅读方式,也造成了文学感觉的消退和文学性的流失。读书或者读文学书应该是有某种仪式感的。应该是拿着一本书去读,慢慢地、细细地品味,对细微的、深层的东西有体会和思考。电子刷屏追求一目十行的加速度,必然会忽略文学许多本质的东西和深层的东西,文学性其实是流失了。
因此,阅读危机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文学审美能力和判断能力下降。文学审美和判断能力并不是一个知识体系,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综合的感觉,是一种感觉的积累,是在潜移默化的文学阅读中逐渐形成的,没有中外古今大量的文学阅读,你的文学感觉不会形成,你的文学审美能力和判断能力也不会形成。
阅读危机是当代文学面临的最大敌人。极端肯定和极端否定的无法对话,也在于双方都没有阅读作为支撑,失去了文学判断的自信,只剩下自己的姿态和理念。因此双方争执的时候只有一种方式,要维护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只有放大自己的音量,放大自己的极端,通过提高声音来证明自己,通过极端来证明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全民性的阅读危机是导致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社会根源。
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是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表现形态
当代文学评价危机是通过文学批评体现出来的,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今天表现得非常充分。在一个好的文学时代,文学创造和文学批评常常是互相促进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批评却陷入了严重的话语危机或者说是伦理危机,文学批评日益失去了公信力和权威性,很少有人相信评论家的话。这是我们批评家的悲哀。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文学批评的代言人意识取代了个体意识,文学批评家掩盖了自己的真实感觉,作为代言人为时代与公众进行文学判断。这样的判断因为缺少个体的审美观照,因而就缺乏感召力,缺乏说服力,也缺乏真实性。批评家本人带着面具,站在时代、公众的道德立场上来进行一个抽象的文学判断,这种没有自我出场的文学评价话语是不真实的话语,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话语。我想这是文学评价话语危机的一种表现方式。
二、畸形的社会文化心理导致了文学批评话语的扭曲、变形。文人相轻,同行相轻,这样一种畸形社会心理进入了文学批评领域,造成了对文学批评说真话能力的扭曲。现在,否定当代作家、否定当代文学的话语行为被视为“讲真话”的标志,被视为文学批评正义化、崇高化的标志,被视为批评家勇敢、有担当的标志,我们的社会舆论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氛围。相反,肯定当代作家就成了讲假话的标志,就会变得很自卑,小心翼翼,缺乏自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讲今天我们对同代作家的苛刻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文学批评话语危机的第二个方面。
三、批评话语的伦理化和道德化成了某些评论家否定当代文学的借口。我们很多的批评家,其批评话语往往伦理化、道德化,不是阅读之后进行分析,而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以巨大的优越感来否定当代文学。以道德判断取代审美分析成为趋势,这在今天已经构成了对当代文学的某种压抑和压制。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崇敬的眼光面对现代文学,而拿着显微镜去找当代文学的局限。1998年的时候,南京新生代作家就有一个关于文学“断裂”的问卷,要对我们的整个文学评价体系发动革命。青年作家要在这个评价体系里面取得成功,他们设想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早死”,非典型性死亡。像王小波死了,现在对王小波的评价很高了;像海子自杀了,海子也成了一个诗坛偶像。第二个是长寿,活到100岁以上。因此南京、上海的年轻作家就发起了一个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健身,跑马拉松。现在年轻作家都是马拉松运动员,每天跑。这也可以看出,文学批评的话语危机在今天对作家本身、对文学创作确实构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对作家的心理、认识都造成了很多干扰。
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滞后以及对经典理解的误区是当代文学评价危机的理论根源
当代文学其实有很多理论误区,比如说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当代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时间的检验,不能经典化,没有经典;当代人与当代文学之间没有必要的距离等等。这些观念和认识都是阻碍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理由。
关于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理论误区主要有三个:一、对于经典的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误区。我们把经典这个词神圣化和神秘化了。其实我们讲的经典这个概念,就人类文学史而言,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没有办法证明什么是经典,什么不是经典。不能说字数长,张炜的450万字就是经典,不能说字数少,北岛的《回答》就不是经典。文学经典是无法测量的,只是一个修辞。不同的人因为各自的背景、趣味、修养不同,完全可以有自己对于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理解。经典有它客观性、绝对性的一面,也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一面。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很多因素,都会影响经典的标准。因此在对经典这个概念的认识上,我们应该明确,经典一定不是十全十美的代名词,也不是无可挑剔、所有人喜欢的代名词。说经典十全十美,说经典所有人喜欢,只不过是把经典乌托邦化的一种表现。把经典乌托邦化,把经典神圣化的结果,就是遮蔽和否定了当代文学。他们假定了一种遥远、神秘、完美的经典的形象,并且对这种神秘、完美的形象进行无限的崇拜和拔高,从而构成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否定。
二、所谓经典会自动呈现的误区。很多人说当代文学有经典,但是有经典也不需要你来说,不需要你来说它是不是经典,如果说它是经典,它就会自动呈现,呈现其价值,所谓金子总是会发光的。这个观点表面上是正确的。自身有价值它才会有价值。但是他们恰恰忽略了文学经典有它的特殊性,文学经典一定是在阅读的意义上才体现其价值,没有被阅读的文学经典没有任何价值。一个没有被发现的经典,一个没有被阅读的经典,一个没有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产生影响力的经典,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类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多我们知道的经典,但还有一大批被埋没了的同样优秀的经典。过去文学有一个出版的机制、发表的机制,很多经典都有九死一生的经历。比如说卡夫卡,如果他的朋友按卡夫卡的意见把他手稿全烧了,我们今天就没有卡夫卡了,没有一个现代文学的大师了;比如说《洛丽塔》,我们现在把它视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经典杰作,但是《洛丽塔》在美国6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作品能出版,可能成为经典,但是写得再好不能出版,就不可能成为经典。人类历史上能正式出版发表流传的作品,只是极少数,那些无法面世的作品中可能隐藏了无数的经典杰作。
因此经典无论多么伟大,其前提就是现实化,能够出版发表,能够供人阅读。没有现实化就没有经典。另一个方面,即使已经被认可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它的价值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阅读者,经典完全可能呈现不同的价值。阅读是创造作品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方式。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通过阅读去创造和赋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的价值不仅不能自动呈现,而且需要不断被发现,被赋予、创造、命名。
三、经典命名权的误区。在经典命名权的问题上我们其实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同代人和后代人谁更有命名权,一是普通人和权威谁更有命名权,包括像我们评论家、文学史家、普通的读者谁更有命名权。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文学经典是一个过去时代的东西,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好像当代人不能命名经典,好像当代人与经典发生关系的方式就是回忆和缅怀,甚至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力都没有。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把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的责任推给后人,那么我们会发现这里存在两个疑问:第一是后人的命名是不是比同代人更可信,对同时代人的理解是我们更准确,还是后代人更准确;第二是,我们是不是那么相信时间,因为时间也不可能是公正的,时间会被意识形态污染,而且还会把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磨损掉。因此,我们宁愿意更相信同代人对本时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作为亲历者一定比后代更准确,我们不能够相信后代人以考古的方式来挖掘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同代人、当代人的命名更可靠,更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文学权威对经典化的意义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迷信权威。如果把一个时代对于文学经典的命名筛选仅仅交给几个人是很危险的,少数人的偏见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偏见,少数人的失误会放大为整个时代的失误。大家太相信评论家也不行,因为评论家一方面他不是那么敬业,另一方面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即使是一个敬业的批评家,一年4000篇长篇小说,如果把它们都读完,365天,一天要读10部长篇小说,怎么读?因此,这是无论如何敬业、如何道德高尚都不可能做到的。我觉得,对于经典,强调文学评价的民主化,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呼唤每一个作家都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作家何必太低调,我就是要成为经典,我就是要写出伟大的作品,狂一点又如何?有什么不好的呢?这也是中国梦,我觉得是好事。而每一个读者也应该是经典的确立者和命名者。实际上文学经典化的过程,既是历史化的过程也是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经典应该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这个阅读者当然包括权威,也包括普通的读者。每一个阅读者都有命名的权力,每一个研究者、读者都有参与文学经典化的使命和责任。其实,在今天,网络、微博、微信,包括我们大家宿舍聊天,其实都是文学发声的方式。今天的发声方式是非常多元的,这种多元化的发声方式会影响我们对整个时代文学的判断,是文学评价民主化的基础。每年4000部作品,就需要大家互补性的阅读。不是奢望一个人读了所有作品,而是所有人共同完成对一个时代所有作品的阅读。这是文学民主化的前提与基础,也是科学的文学评价体系得以确立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