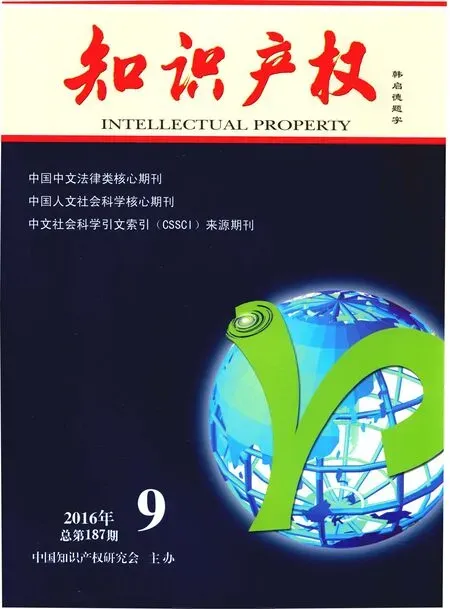论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以《商标法》第63条为中心
钱玉文 李安琪
论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以《商标法》第63条为中心
钱玉文 李安琪
内容提要:惩罚性赔偿是一种不同于补偿性赔偿的民事赔偿制度,具有惩罚和威慑侵权行为的作用。因其赔偿金数额超出了实际损失的数额,而被看作是对民法 “损害填平原则”的一大突破。2013年修订的《商标法》第63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即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可以按照实际损失额的一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该规定旨在遏制社会生活中屡禁不止的商标侵权行为。但就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尚未出现一例针对商标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案例。究其原因有四:一是惩罚性赔偿的“惩罚性”缺失;二是法定赔偿的“惩罚性”日渐凸显;三是惩罚性赔偿举证难度较大;四是法官缺乏具体裁判标准,存在制度路径依赖的惯性。惩罚性赔偿并非法定赔偿可以替代,为此需要明确惩罚性赔偿应当优于法定赔偿得到适用。为使《商标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实际发挥作用,同时需要细化“恶意”、“情节严重”的裁量标准,改进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模式。
商标法 惩罚性赔偿 法定赔偿
长期以来,商标侵权案件的审判往往出现以下结果:商标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合理花费无法被覆盖和弥补,“打赢官司输了钱”。与之相对应,面对侵权行为的打击过轻,不少侵权行为人又另起炉灶继续侵权。为此,《商标法》(2014年)第63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旨在遏制屡禁不止的商标侵权行为,有效弥补商标权利人的损失。a《商标法》(2014年)第63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三百万元以下的赔偿。”但就目前我国现行商标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来看,相关规定还很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以致在商标侵权纠纷中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例如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实际损失时,惩罚性赔偿数额如何计算?法院判赔惩罚性赔偿金时,计算的基数和标准又该怎样确定?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渊源及发展
惩罚性赔偿是对传统补偿性赔偿的一种补充,也被称为报复性赔偿或者是示范性赔偿。“它是加害人给付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之外的金钱赔偿。”b关淑芳:《论我国立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第82页。从传统的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视角看,民事赔偿的目的就是补偿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即追求原告损失与原告所获赔偿金之间的完全对等,这一原则又被称为损害填平原则。所以,以多倍赔偿金为表现形式的惩罚性赔偿被视为是对该原则的一种突破,并不被民法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纳。
惩罚性赔偿制度起源于1763年英国法官Lord Camden在Huckle V. money一案中的判决。cWils.K.B.205,95 Eng.Rep.768(C.P.1763).该制度早期在英国的适用范围极其狭窄,且适用对象一般限于政府等公共机关,目的是为了打击权力滥用行为。故而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国侵权法中被称为exemplary damages(示范性赔偿),更为强调赔偿的社会指引作用。这一制度真正得到发展是在美国。美国最早在1784年的Genay V. Norris一案中确认了惩罚性赔偿制度,dGenay V. Norris, 1SC.L.3,1 Bay 6(1784).制度设立之初是为了弥补在非具体的损害中难以用金钱量化损失的不足。到了17、18世纪,该制度又拓展到了恶意诽谤、侵害他人名誉权的案件中。从20世纪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惩罚性赔偿制度又被运用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案件中,在对因不合格商品而遭受损害的消费者进行保护的同时,也对在商品交易中处于强势地位的生产商进行惩戒。
我国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针对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实行双倍赔偿的规定第一次确立了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消法》(2014年)第55条变双倍赔偿为退一赔三,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该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从《消法》扩展到了其他法律中,如《食品安全法》(2009年)第96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第8条、第9条和第14条。2010年《侵权责任法》更是将“惩罚性赔偿”五个字明确写入第47条中,正式宣告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侵权责任领域普遍适用。相应地,在知识产权领域,针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呼声日渐高涨。
(二)功能
惩罚性赔偿制度自诞生以来,便受到了激烈而广泛的质疑。在英美法系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经受的质疑与大陆法系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排斥出自同一原因,即当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失已经得到了补偿,额外增加赔偿额是否具有相当的正当性。但随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广泛适用,其所具有的独特功能愈来愈得到广泛认可,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对其发挥功能的评价已经形成了几种主流学说。
1.惩罚与遏制功能
在Corey V. Colbaugh一案中,美国法院将惩罚性赔偿的作用进行了明确:“法院判处惩罚性赔偿,并非在于计算多少精神上的损害或实际上的损害,而是为了确立典范,以避免将来再有同样不法行为的发生。”e陈聪富著:《侵权归责原则与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5-276页。惩罚性赔偿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着重强调惩戒作用,即便是提出颇有影响的“七功能”说的埃利斯教授,亦认为诸如补偿原告权利人未获赔偿的其它损失,支付原告合理开支等作用都是惩罚和遏制两大功能的副产品。fDorsey D. Ellis.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Law of Punitive Damages .S. Cal. L. Rev,1982(56):11.相比之下,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局限于惩罚和遏制功能。在我国,惩罚和遏制一般是通过行政罚款的手段得以实现。
2.弥补和平衡功能
“与其说惩罚性赔偿是对行为人恶意与恶劣行为的惩罚,不如准确地说,是对恶意、恶劣行为所造成严重损害的全部填补。”g马新彦、邓冰宁:《论惩罚性赔偿的损害填补功能——以美国侵权法惩罚性赔偿制度为启示的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 122页。在我国,惩罚性赔偿发挥着重要的损害填补功能,尤其在商标法领域。2013年商标法修正案的说明就明确提到“针对实践中权利人维权成本高,往往得不偿失的现象,草案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h《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3年第5期,第725页。可见,在我国商标法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和平衡受害人的全部损失。
3.激励功能
激励功能是指鼓励合法权益者提起诉讼以捍卫自己的权利。英美法系的理论将原告因惩罚性赔偿获得的额外的金钱,视为其积极维权而应得到的奖励。但不得不提的是,惩罚性赔偿所体现的奖励有别于一般的奖励。通常而言,奖励是由政府或有关的公共事业部门给付的奖金,但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下,奖励是法院强制违法者以支付赔偿金方式向权利人作出的赔偿。所以准确来说,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原告体现激励功能,对被告体现惩罚功能。
二、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困境及成因
(一)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的困境
我国新《商标法》于2014年5月1日起实施,针对实践中商标维权成本过高,该法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制度在引入之初,被视为有效打击商标侵权行为的一剂强心针。以《商标法》第63条为关键词,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商标纠纷民事判决书的检索发现,适用《商标法》第63条判决的商标侵权案件一共是24件,但截至2016年6月30日,全国各级法院尚未作出一份关于商标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案例的判决。原告在起诉时,主动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进行救济的都比较少见。
(二)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适用困境的成因
1.惩罚性赔偿制度中“惩罚性”的缺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i《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将商标权人因侵权所受的损失,量化为商标权人商品销售的减少量或侵权商品的销售量与单位利润的乘积。该规定直接将销售量的增减等同于原告的损失或者被告的获利,但在实际中,商标侵权的表现通常是混淆或者淡化商标。换言之,侵权行为对商标权的侵害是潜移默化的。从商标是无形资产这一特性出发,需要明确有形损失和无形损失。j参见曹静:《商标侵权案件中的损害与赔偿》,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63-64页。依照现有的计算模式计算惩罚性赔偿金,显然无法覆盖原告商标显著性减弱、商标声誉受损等无形损失,即便判处基于补偿性赔偿金三倍的数额,在某些情况下也远低于侵权所获的高额回报,无法体现出制度的惩罚性。
2.法定赔偿制度“惩罚性”的日渐凸显
《商标法》(2014年)将法定赔偿金的上限提升到了300万元,此次修改使得法定赔偿金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惩罚性,而不再是单纯的补偿性赔偿。法定赔偿金通常认为是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损失或者获益的情况时的“权宜之计”,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审判意见中,也提及应尽可能避免随意适用法定赔偿制度。k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载《司法业务文选》2009年第23期,第8页。但是参照《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例实证研究报告》,l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2012年第8期《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实证研究报告》。法定赔偿制度在2008年6月以来的商标权益纠纷处理方式中占有97.63%的比例,处于主导地位。该制度的广泛适用与操作必然有其原因,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海高院网以及最高院颁布的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中选取针对商标侵权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进行了实证研究,亦发现不少在裁判理由中强调侵权行为恶意或情节严重的判决(见下表)。

表:高级人民法院(以上)针对商标侵权适用法定赔偿的部分案例
由此可见,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的大小在法官裁量法定赔偿金时已成为一大重要的考量因素,且也有裁判结果突破法定赔偿上限的判罚。这使法定赔偿在实务中兼具了补偿性和惩罚性的双重特质。虽然适用法定赔偿判罚的金额少有完全等同于原告求偿金额的,但惩罚性赔偿应然具有的惩罚性在当今法定赔偿普遍适用的形势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
3.举证难度较大
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以精确的被侵权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为依托。依照传统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在商标侵权纠纷中应当由原告举证被告存在侵犯其商标权的行为。但商标侵权往往呈现出极高的隐匿性,原告在举证时存在两大难度:其一,证明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存在难度。在判定是否侵权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复杂繁多,如行为的性质,持续时间,原被告的具体位置,经营规模,客观后果等。原告在证明被告行为属于《商标法》(2014年)第57条规定的几种侵权行为时就得投入非常巨大的资源成本。其二,证明被告应给付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存在难度。即便认定了被告构成侵权,原告也无法证明被告侵权行为对其造成的不利影响。正如上所言,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的规定,商标权人所受的损失可以通过商标权商品减少的销售额或是侵权商品的销售额来量化。但是,侵权行为的后果并不直观反映为销售量的减少,所以自证所减少的销售量并以此为依据主张惩罚性赔偿数额的做法并不为多数商标权人所采用。而原告采集被告实施侵权行为期间的财务报表或销售记录等信息,进而证明侵权人的获利更是难上加难。
4.法官缺乏具体裁判的标准,存在制度路径的依赖
现行商标法将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条件描述为“恶意”和“情节严重”,但对“恶意”和“情节严重”具体怎么认定,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同样,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倍数,范围为“一至三倍”,而到底是赔两倍还是三倍,也没有相关条款对法官的判罚给予指导。在《商标法》(2014年)出台前,针对补偿性赔偿数额较难认定或认定数额难以填平原告损失的情形,法官一般依照自由裁量酌定赔偿数额,长期依赖的审判习惯让他们倾向于继续适用法定赔偿金制度。一边是通过十分细致的论证分析,耗费巨大时间精力查明损失或获利,最终往往还是会出现原告不服上诉的情况,一边是赔偿上限提至300万,赋予审判者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两者权衡,显然是适用法定赔偿制度更受青睐。
三、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完善
作为知识产权领域首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商标法》第63条还有许多存在争议、亟待完善之处。为了使惩罚性赔偿能在实际处理商标纠纷时能发挥功效,不至成为一纸空文,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极有必要。
(一)明确商标法中适用惩罚性赔偿优于法定赔偿
在《商标法》(2014年)出台前,据学者的相关统计,商标侵权案件中法院裁判的赔偿数额仅占权利人主张的1/4至1/3。m参见弗兰克·A·哈梅尔:《中国法院对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兼论对损害赔偿和费用承担的主张》,载《中德法学论坛》2010年第8期,第322页。而另一份统计了1049份商标权法定赔偿判决的调查显示,法定赔偿数额仅仅占商标权人求偿金额的24%。n参见徐聪颖:《我国商标权法定赔偿的现状及反思》,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77页。这更为直观地反映了适用法定赔偿金判罚的结果与原告的预期存在巨大差距,说明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额是倾向于依补偿性原则而确定的。此外,依凭自由裁量而确定的法定赔偿金缺乏严密的逻辑证成,在绝大多数的判决中,我们只能看到法官将酌定的因素简单罗列一番,而未仔细阐明。尽管惩罚性赔偿较之法定赔偿的可操作性低,但在两种制度比较之下,惩罚性赔偿的优越性更为明显。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挥的惩戒、弥补功能是我国目前商标权发展形势之下打击商标侵权,保护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现实需求,仅靠法定赔偿制度显然无法实现。
(二)细化“恶意”、“情节严重”的衡量标准
1.恶意的衡量标准
从文义上讲,恶意的主观过错程度大于故意,但“恶意”在法律语境中很少被加以使用,现实中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对恶意与故意之间的程度差异加以区分。本文认为,立法上采用“恶意侵权”概念后,在司法实践中“恶意侵权”的认定和适用是极易产生分歧的,这样一来,各法院,甚至不同法官的判罚标准就很难统一。对于“恶意”两字的解释应当谨慎。现有法条中的恶意,理解为具有恶劣性的、在道德上应受谴责性的“故意”较好,而重大过失和简单的明知侵权而为之不能包括在内。恶意代表了侵权人过错程度,这与惩罚性赔偿中的惩罚功能直接对应,所以有可能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商标侵权应当与一般侵权的适用条件严格加以区分。在《商标法》中侵权行为的“恶意”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侵权人被告知侵权时仍然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的;(2)侵权人明知侵权且采取措施掩盖其侵权行为的;(3)参照2014年6月《著作权法》草案中有关适用惩罚性赔偿以侵权人多次侵权为前提的条款,o《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76条第2款:“对于两次以上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前款计算的赔偿数额的二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是判断侵权人主观恶意的一种较好方式。
2.情节严重的衡量标准
商标法中对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的正式表述是“恶意侵犯商标权,情节严重的”。这里的情节严重,是指“恶意”的情节严重,即恶意的程度大,还是指侵权行为情节严重,即构成了较大的损害结果呢?对于该法条的语义解读亦是存在争议的。如果是恶意的情节严重,则该表述有多余之嫌,上文已述,“恶意”一词本身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判断,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如果将恶意理解为主观恶性极大的故意,那情节严重的恶意又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呢?因此,把“情节严重”解释为“侵权行为情节严重”较为适当。依照第二种理解方式来看,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与否就会与权利人的损害结果有直接关联。同时,基于惩罚性赔偿具有的惩罚和遏制侵权行为的目的,惩罚的程度应当与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相当。结合这两方面的考量,情节严重可以由以下几种标准判定:(1)侵权人长期处于侵犯他人商标权状态的;(2)商标权人因侵权行为受到极大甚至难以弥补的损失的;(3)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
(三)改良计算模式
1.优化惩罚性赔偿金的倍比
美国《兰哈姆法》在第35条(a)款、《美国法典》第15篇第1117条规定,原告有权获得:(1)被告侵权所得利润;(2)已被原告证明的任何赔偿金;(3)诉讼费。评估利润时,原告应该只证明被告的销售额,被告必须证明所有支出或要求扣除的部分。评估赔偿金时,法院可以判决已认定的赔偿金的任何数量的总和,但不得超过该数量的三倍。p参见[美]罗伯特·P·墨杰斯等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0页、第431页。根据《商标法》第63条的规定可知,《商标法》中惩罚性赔偿额度是以补偿性赔偿金作为基数进行计算的,最高不得超过三倍。依据第63条第1款可知,填平性赔偿的数额是通过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商标许可费等计算而得出,归其根本,是由商标本身的价值决定的,与侵权人恶性并无直接的关联。从本质上来说,惩罚性赔偿是附加在填平性赔偿之上的加重责任,即先要求侵权人对权利人进行填平性的弥补,再对其实施惩罚性的判罚。反对补偿性赔偿作为基数的观点,无疑是将两者割裂开,如若此法官又该怎样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判定惩罚性赔偿金额?以什么作为计算标准?如果是完全依靠自由裁量,那又与法定赔偿有何分别?所以,把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分离是不可取的。最轻的惩罚性赔偿应在补偿性赔偿之上即可,只是现有法律中的“一至三倍”的倍数规定较为宽泛,可以考虑结合具体情节采纳几个典型值,如主观恶意加情节严重则适用三倍判罚,主观故意加情节严重则适用两倍判罚。
2.改进计算基数的参照标准
目前商标法中计算惩罚性赔偿金基数的参照顺序是:(1)被侵权人实际损失;(2)侵权人所获利润;(3)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举证确定被侵权损失与侵权获利数额的难度前面已加以阐述,而较之这两种参照标准,商标许可费是直观具体的,并不存在难以确定的困扰。但是,商标许可费倍数作为赔偿基准的情形在实务中并不多见。例如发生在全国的多起“开心人”商标侵权纠纷案,其中在江西开心人药房与怀化市开心人药房的侵害商标权一案中q(2015)湘高法民三终字第82号二审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就持有这样的观点:“‘开心人’注册商标在湖南是否具有知名度与商标侵权判赔时能否参考商标许可使用费并无关联,两者都只是确定赔偿数额的考量因素”。但在江西开心人药房与宁波童王开心人大药房侵害商标权一案中r(2015)甬鄞知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法院则认为,原告至今未进入宁波市场进行经营,商标在宁波地区内尚无较高知名度,所以商标在其他地区的品牌效应、市场信誉与其在宁波区域范围内并不相同,最终认定不宜将商标许可费作为赔偿的数额。可见,虽然商标许可使用费是一个明确且既定的数值,但在依照其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依然存有争议。针对这一现象,应当由法官结合商标在侵权行为发生地的市场影响力等因素,对商标的价值进行市场评估,继而得出当一个侵权人意欲使行为合法而理应支付的商标许可使用费,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惩罚性赔偿金。
Punitive damages is also a kind of civil compensation system, but different from general compensatory damages. It has two distinctive features: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in respect of infringement behavior. It is regarded as a breakthrough to the basic civil law principle of “make whole”, because the compensatory sum exceeds the actual damages. In 2013, China revised the Trademark Law and stipulated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Art. 63.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serious trademark infringement behavior can be imposed on punitive damages as much as one to three times of compensatory damages. Its purpose is to stop the repeated trademark infringement. However, as far as the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s concerned, there is not yet a case employing punitive damages throughout China. Four reasons can answer for this phenomenon: fi rst,the shortage of adequate punishment in the punitive damages; second, the punishment derived from statutory compensa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ird, proof burden is heavy for punitive damages claim; fourth, the shortage of uniform judicial judgment standard. Punitive damages cannot be replaced by statutory damages. It should therefore be clearly stipulated in the Trademark Law, that the punitive damages should take priority over statutory damages. Besides, the criteria for “malice” and “severity” should also be specifi ed. Finally, the calcul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also calls for reform.
trademark law; punitive damages; statutory damages
钱玉文,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教授
李安琪,德国慕尼黑大学德国法方向硕士(LLM)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消费安全的法律规制研究”(13BFX095)和中国法学会2015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网络消费安全的多元规制研究” CLS(2015)B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