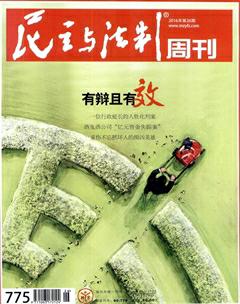有效辩护的时代悄然到来
刘桂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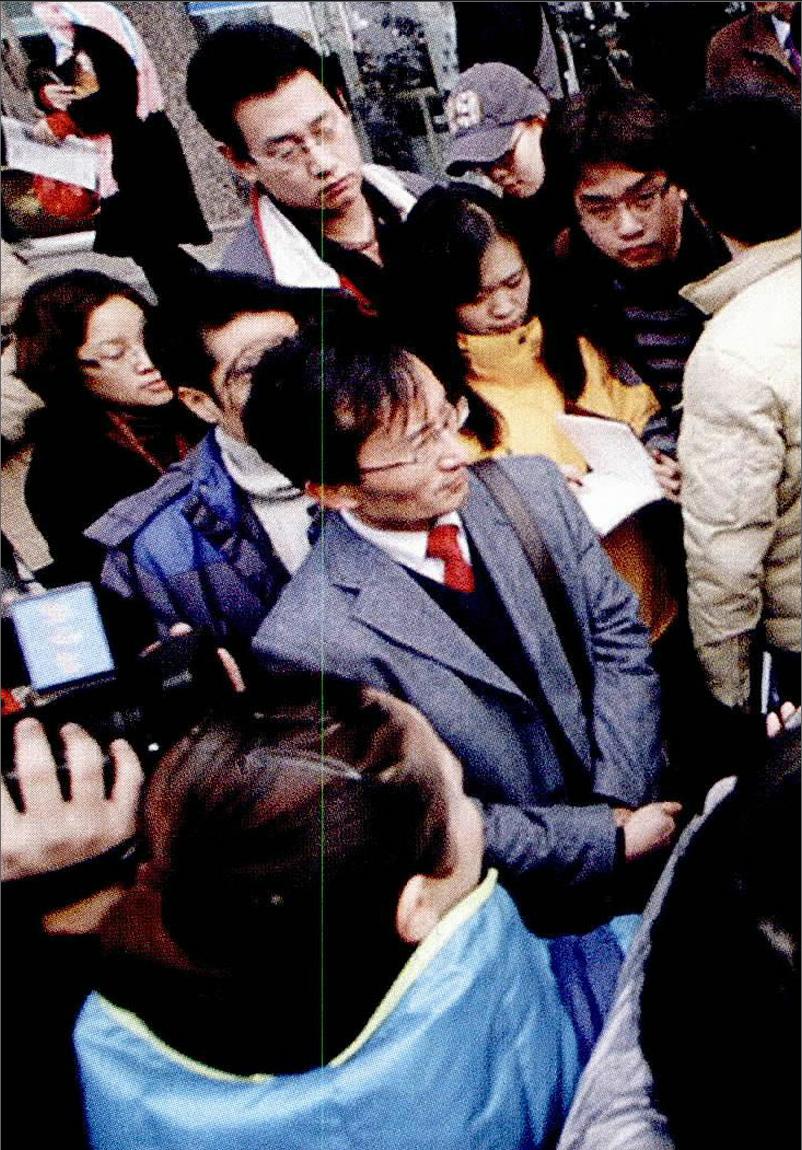
2016年6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对广大刑辩律师乃至所有法律人来说,此次会议最大的亮点是通过了《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会议强调,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发挥好审判特别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发生,促进司法公正。要着眼于解决影响刑事司法公正的突出问题,把证据裁判要求贯彻到刑事诉讼各环节,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建立更加符合司法规律的刑事诉讼制度。
一次中央深改会议、一个中央重要文件,竟然通过了一项非常具有法律专业色彩的决定。动作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远,不要说是少见,甚至可以说罕见。无论是叫做“意见”还是称为“决定”,总之,其核心内容将标志着一个有效辩护时代的到来。
从1979年我国颁布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经过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再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我国已经颁行过三部刑事诉讼法。可以说,每一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带来了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同样可以说,每一次刑事辩护的改革,都是为了使刑事辩护能够真正有效。
于是,一个叫做有效辩护的命题在这30多年里始终萦绕在我国法律人的脑海,尤其是广大刑辩律师更加关注与期待何时真正实现有效辩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由此可见,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人权保障,有效辩护不仅是一种状态,而且更是一种常态。
但是,为了实现这种状态,也为了追求这种常态,我国刑事辩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有位辩护到有人辩护、从有人辩护到有序辩护、从有序辩护到有据辩护、从有据辩护到有形辩护的发展历程。
一是从有位辩护到有人辩护的阶段(1979年-1989年)。在这个阶段,从中央到地方,从理论到实务,强调的就是有一个“辩护人”的位置。什么是有位?是地位还是座位?是让位还是空位?在当时来说,其实这个问题一直明确。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在林彪、“四人帮”两案的特别法庭位置设计中,开始出现了辩护人的位置。从当时的位置设计看,辩护人几乎是与审判员并排设立。以至于现场出现了有一位由功底深厚的老学者而担任的老律师,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加之缺乏法庭辩护的临场经验,在最初的法庭调查和辩护阶段竟然好几次出现了辩护人角色的错位,在法庭上对被告人比审判官、检察官还严厉,没有全力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当然,在这个阶段最具时代意义的是“辽宁台安三律师案”。
发端于1984年的“辽宁台安三律师案”,使王力成、王志双、王百义相继身陷囹圄。在第一位律师界的全国人大代表王工律师的呼吁下,在法律专家的论证下,在司法部与全国律协的努力下,在《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关注下,在彭真、万里、习仲勋、陈丕显、彭冲、黄华、廖汉生、王汉斌等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多次过问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下,最后达到了由检察院撤案并向三位律师道歉的圆满结果。
1989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新华社记者周长新、《人民日报》记者吴恒权采写的《一次很有价值的较量》的重头报道,同时还配发了著名法学家张友渔撰写的评论文章《法律应保护律师执行职务》。此前,《中国律师》主编张思之还在《中国律师》创刊号上发表卷首语《何故捕我律师?》。
二是从有人辩护到有序辩护的进程(1989年-1996年)。在这个进程中,无论是社会眼光还是司法实践,只是满足于辩护人席上有人即可。至于这个人是执业律师还是非执业律师及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是不重要的。显然,湖南彭杰律师案是这个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在律师会见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逃跑,竟然导致会见律师彭杰被县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为此,全国律协在京召开首都法学界刑法学专家座谈会,一致认为彭杰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全国律协还向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发函,详细汇报了此案情况,请求批示。司法部编写《司法部情况反映》增刊,将彭杰一案情况向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央纪委各领导同志及有关各部、委、室、会、院作了反映。彭杰的二审辩护人王海云律师前往最高人民法院刑庭,进一步反映了此案详情及意见。最高人民法院也非常重视。1996年5月24日,终于由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撤销原判、彭杰无罪的终审判决。
1996年3月17日通过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可以说是这个进程中我国刑事诉讼进入程序正义的标志性大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不仅出现了对刑事被追诉对象从人犯到犯罪嫌疑人的称呼转变,确立了被追诉对象在程序上无罪的地位,与无罪推定原则相适应。同时,还第一次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又对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作了专章规定。
至此,我国法律界开始思考:什么是有人?是人的称呼变化还是人的权利提升?是获得律师帮助还是获得国家帮助?
三是从有序辩护到有据辩护的转折(1996年-2007年)。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司法改革,我国逐步转变“有罪推定”“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传统理念,并倡导和培育“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结合”“控辩平等、对抗”等现代诉讼理念。因为杜培武案、余祥林案等案件的发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疑问:什么是有序?是工作顺序还是法定程序?是实体正义还是程序正义?
四是从有据辩护到有形辩护的变化(2007年-2012年)。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可以说是我国法律制度最具普遍意义的司法改革举措。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使我国刑事辩护实现了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到“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原则的深化。而以赵作海案件为由头的思考,开始关注到底什么是有据,究竟是事实依据还是证据依据、是证据优先还是证据排除之类的重要课题。
五是从有形辩护到有效辩护的发展(2012年至今)。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以庭审为中心,让庭审实质化。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因为李庄案与北海案的发生,使刑事辩护的“旧三难”与“新三难”变得更加怨声载道,也使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变得越来越刻不容缓。尤其是“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提出与要求,如何实现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判决结果形成在法庭的目标,就成了众所周知的职业追求。
什么叫有形?所谓“以审判为中心”组合的诉讼架构,究竟是等腰三角形还是流水作业型?到底是以审判为中心还是以法院为中心?显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现实问题。
因为有形辩护的改革要求,有效辩护就感觉已经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了。所谓有效辩护,就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委托的辩护人或接受法律援助的律师,出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利益,通过实体性的辩护和程序性的辩护,及时充分行使辩护权,使得辩护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制度。可以说,有效辩护至少应该包括效率、效能、效益、效果等基本内涵。
其实,有效辩护的理论首先来自美国。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任何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都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这一宪法权利既包括了被告人自行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也意味着那些无力委托律师帮助的被告人,有权获得指定律师辩护的机会。从1932年到1963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判决,逐步为那些因为贫穷而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人,确立了获得政府所指定的律师辩护的权利。但是,被告人仅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还是不够的,法院还有必要保障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
作为一项基本宪法权利,要实现有效辩护,就要求做到诸如“获知指控罪名和理由”“获得陪审团审判”“获得正当法律程序”“要求法院以强制手段调取证据”“对对方证人进行质证”等事项。因为这一权利并不是联邦宪法所明文确立的权利,而是联邦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有关“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所发展出来的宪法权利。可以说,在美国宪法中,“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就等于“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权利”。
在我国,尽管还没出现有效辩护的具体规定,但从制度设计意义上说,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有关司法解释、律师法及《律师执业规范》所确立的各种制度改革,都具有实现有效辩护的意义。同样,从本文开头所提到的诸如“以审判为中心”之类的制度改革意义上看,所有的司法改革事实上都是为了实现有效辩护。
关注管理学的人都知道“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这位被《纽约时报》赞誉为“当代最具启发性的思想家”,连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等人都深受其思想影响的管理学大师,曾在《有效的主管》一书中指出: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看起来这是对企业管理提出的论断,但对刑事辩护来讲,显然同样适用。“正确地做事”强调的是效率,其结果是让我们更快地朝目标迈进;“做正确的事”强调的则是效能,其结果是确保我们的工作在坚实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
在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中,设立律师这个角色,正是为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与弱小的被告人之间不均衡的天平上特别设置的一个砝码。换言之,法律体系如此设计律师角色,就是为了壮大孤立的被告人的力量来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以避免因国家机器的强大而导致个体弱方的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的合法权利被侵犯。为此,辩护律师既要“正确地做事”,更要“做正确的事”。如此而来,才有真正的有效辩护。
于是,作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就是利用“现有法律的所有可能性”(包括现有法律的漏洞)来帮助刑事被告人摆脱嫌疑,从而使被告人获得“最大利益”。于是,如何使被告人获得“最大利益”,如何真正实现辩护的最快“效率”、履行辩护的最高“效能”、完成辩护的最大“效益”、达到辩护的最好“效果”,就成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最终目标。于是,一个有效辩护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可以说,一个有效辩护的时代,一定是一个依法治国的时代。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