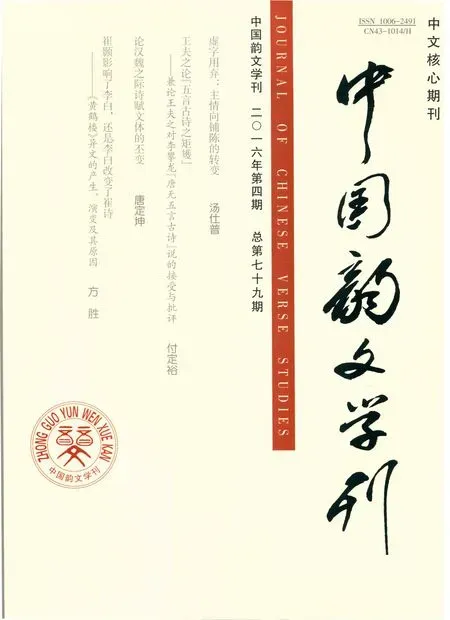汉魏诗歌交叉传播与“古诗十九首”性质及年代的争论
吴大顺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汉魏诗歌交叉传播与“古诗十九首”性质及年代的争论
吴大顺*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汉魏诗歌生成方式具有多元性,传播方式存在音乐与文本的交叉性,从而导致后世文献对其著录或“古诗”或“乐府”的矛盾。对“古诗十九首”性质认定及其作者和创作时间的长期争论是后世学者忽略了汉魏诗歌多元的生成方式和音乐、文本交叉的传播方式造成的。“古诗十九首”与其他汉魏古诗一样,应是在多人、多时、多度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体现了汉魏诗体初兴时创作的集成性特征,并非一人、同时、独立创作的组诗。
汉魏诗歌;交叉传播;古诗十九首;集成性
一 汉魏古诗的交叉传播与历代文献著录的矛盾
《文选·杂诗》类收录的十九首古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诗文本。因《文选》的广泛传播,“古诗十九首”被作为一个“诗类”概念被人们接受,其实,《文选》问世前汉魏古诗已经存在文本传播。《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著录排在《文选》之前者有挚虞《文章流别集》、谢混《文章流别本》、孔甯《续文章流别》《集苑》、刘义庆《集林》、沈约《集钞》、孔逭《文苑》等诗文的合集。[1](P1081-1084)《隋书·经籍志》总集是分类别、按时间“次其前后”的,挚虞《文章流别集》也是“自诗赋而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的。《晋书·挚虞》载:“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2](P1427)据《晋书》所言,挚虞《文章流别论》大概原是附于《文章流别集》之后,按照各种文体分别进行评论的,后因摘出别行,才成为文体专论。现存挚虞《文章流别论》中有关于古诗的评论,如:“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古诗之三言者,‘振振鹭,鹭于飞’之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谐倡乐多用之。”[3](P1905)等,挚虞《文章流别集》当收录有古诗。又谢灵运《诗集》《古诗集》《六代诗集钞》、谢灵运《诗英》等诗集排在昭明太子《古今诗苑英华》之前,这些诗集其实是谢灵运等编纂的总集,而非谢灵运个人别集,均有可能著录汉魏古诗,特别是《古诗集》九卷,当是集中收录的古诗。可惜这些总集皆已失传,所收具体作品不得而知。钟嵘《诗品》曰:“陆机所拟十二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4](P45)看来,钟嵘时代古诗尚存近六十首。
此后,《玉台新咏》《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注》《太平御览》《乐府诗集》,以及历代诗话等诸多文献对汉魏古诗或著录或选录或引用,其称名却出现了“古诗”或“乐府”的矛盾。*各书收录汉魏古诗的具体情况,见拙著《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451页之“汉魏古诗流传表”。对“古诗”著录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诗歌作者的矛盾,如《玉台新咏》著录在枚乘名下的8首诗歌,其余文献均未注明作者;《北堂书钞》称“今日良宴会”为曹植诗,其余文献未注明作者。二是对诗歌性质判定的矛盾,如同一首诗歌,有的文献称“古诗”,有的文献称“古乐府”。
其实,这种矛盾与汉魏古诗的多元生成方式及其音乐、文本的交叉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汉魏古诗,有的是文人对民歌的加工,有的是乐府诗失去音乐而成,有的又是文人拼凑乐府古辞的创作,有的纯为文人创作,其生成方式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远非后世文人诗那样的自由创作。因此,在结集传播之前还存在音乐、文本并行、交叉传播,以及互相转化的情形。如《驱车上东门》,《文选》《艺文类聚》《乐府诗集》《合璧事类》《广文选》等文献均有著录,《文选》称“古诗”,其余文献或称“古驱车上东门行”,或称“古乐府”“杂曲歌辞”。萧统编纂《文选》时,将“驱车上东门”选入古诗,当有该诗的文本传播依据,而《艺文类聚》《乐府诗集》将之著录为古乐府,亦当有该诗入乐歌唱的文献依据。又如“迢迢牵牛星”,《文选》称古诗,《玉台新咏》称枚乘杂诗,可见齐梁时期该诗当以文本传播为主,而杜台卿《玉烛宝典》称之为“古乐府”。《玉烛宝典》成书于周末、隋初,杜台卿晚年双目失明,《玉烛宝典》的文献当是其早年所见,由此可以推断,“迢迢牵牛星”在北方可能曾作为“乐府”流传。因古诗多元的生成方式及其音乐、文本交叉并行传播的特点,很多古诗在流传过程中获得了“乐府”和“古诗”的双重身份。后代文献著录者往往依据一种文献著录,矛盾由此产生。明人徐世溥《榆溪诗话》对几首汉魏诗歌作者和性质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
汉《折杨柳》“默默独行行”与大曲之《满歌行》“为乐未几时”,杂曲之《伤歌行》“昭昭素明月”皆曹氏兄弟诗也。《君子行》“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思王集载之,明是思王作,而梅禹金收入汉乐府。又《善哉行》“仙人王乔,奉药一丸。惭无灵辄,以报赵宣。淮南八公,要道不烦”,此确然子建作,而钟伯敬《诗归》选入古辞,并非也。[5](P12)
《折杨柳》“默默”、《满歌行》“为乐未几时”,《宋书·乐志》作古辞,列为大曲,徐氏认为两首歌辞“皆曹氏兄弟诗”,不知何据;杂曲《伤歌行》“昭昭素明月”,《文选》卷二七作古辞,《玉台新咏》卷二作魏明帝辞;《君子行》,曹植《豫章行》有“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两句,六臣本《文选》作古乐府,李善注《文选》未收,明梅鼎祚《古乐苑》作汉乐府;《善哉行》,《宋书·乐志》作古辞,《艺文类聚》卷四一作陈思王植《善哉行》,引干、欢、翩、丸、寒、宣、干、餐等前八韵,明钟伯敬《诗归》选入古辞。梅鼎祚、钟伯敬、徐世溥三人均为明代人,他们对这些汉魏乐府歌辞的认识虽各有不同意见,但均有一定的文本依据。其实,这种现象也是因汉魏乐府古辞在魏晋时期的多种传播方式而造成的后世对其认识上的矛盾。诚如梁启超所说:“广义的乐府,也可以说和普通诗没有多大分别,有许多汉魏间的五言乐府和同时代的五言诗很难划分界限标准。所以后此总集选本,一篇而两体互收者很不少。”[6](P182)
二 关于“古诗十九首”性质的讨论
“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历来受到重视,刘勰《文心雕龙》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称其“一字千金”,是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但是,自“古诗十九首”概念形成以来,对其认识就有诸多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古诗十九首”性质;二是“古诗十九首”作者与创作时间。
“古诗十九首”究竟是文人古诗,还是乐府歌辞?(明)胡应麟《诗薮·内编》曰:“至汉《郊祀十九章》,《古诗十九首》,不相为用,诗与乐府,门类始分,然厥体未甚远也。如‘青青园中葵’曷异古风;‘盈盈楼上女’靡非乐府。”[7](P13)在这里,胡应麟主要指出了古诗与乐府门类始分不久,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并未明确指出乐府与古诗是不分的。清乾隆年间的朱乾在其《乐府正义》中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8]此后,冯班《钝吟杂录》曰:“《文选》注引古诗多云枚乘乐府,则《十九首》亦乐府也。”[9](P39)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孙楷第《沧州后集》、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等均认为古诗“大都是乐府歌辞”[10](P7)。遗憾的是,以上学者称《古诗十九首》为乐府,多是从个别乐府歌辞与古诗混杂不清的现象,以及古诗与乐府在主题、语言整体风格上的相似性而进行的“假定”,并未对每首古诗逐一进行考索、辨正。属于类推式和直觉性判定,其结论值得推敲。
近年有学者重申“古诗十九首”为“乐府”的观点。如刘旭青《〈古诗十九首〉为歌诗辨》,论文根据《沧浪诗话》《诗薮》《钝吟杂录》《汉诗总说》等关于“古诗十九首”为乐府的论述、乐府与古诗概念的关联,以及宋代《事文类聚》《合璧事类》两书收录“古诗十九首”多称“古乐府”的记载,得出“《古诗十九首》曾经就是“入乐可歌之诗”[11]的结论。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与此前学者基本一致,可贵的是补充了大量文献资料,但文章以《事文类聚》《合璧事类》两书对“古诗十九首”性质的著录为依据似可商榷。
《事文类聚》成书于南宋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2),《合璧事类》成书于宝祐年间(公元1253—1258),这两部类书对“古诗十九首”的性质判定深受郑樵《通志》“乐府”观念的影响。郑樵《通志》成书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早《事文类聚》《合璧事类》两书近一百年。《通志·乐略》曰:“古之诗今之辞曲也。”郑樵《通志》以这种“诗乐一体”的观念为依据著录歌辞乐曲,使得很多徒诗都被著录成了曲调。如《通志》“遗声序论”曰:“遗声者,逸诗之流也。今以义类相从分二十五正门二十附门,总四百十八曲,无非雅言幽思,当探其目,以俟可考。今采其诗以入系声乐府。”其“古调二十四曲”中著录“古辞十九曲”(无名氏),接着著录“拟行行重行行”(陆机)。[12](P631)其“古辞十九曲”当是指“古诗十九首”。晚于郑樵《通志》近一百年的《事文类聚》和《合璧事类》直接将“古诗十九首”著录为“古乐府”。可见,对“古诗十九首”全为乐府的判定,其始作俑者当是南宋的郑樵。*参拙文《论汉魏五言古诗的生成与流传》,《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第111-115页。
杨合林《〈古诗十九首〉的音乐和主题》一文开宗明义地提出:“《古诗十九首》原是合乐而歌的。”[13]接着引述朱乾《乐府正义》、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和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等有关诗乐配合实践中宰割辞调现象加以说明,至于《古诗十九首》合乐的理由,文章并未展开论证,而是将重点放在“古诗十九首”所合之乐是“以赵音为主体的新声”的论述上。
针对以上观点,赵琼琼撰文提出相反意见,文章从创作原则、组织风格、抒情特点、内在节奏与格律意识等方面对“古诗十九首”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古诗十九首”并非为入乐而作、用于表演和传唱的乐府歌辞,而是文人经过深思熟虑创作的五言徒诗。[14]文章重点分析了“古诗十九首”与乐府的区别,而忽视了二者的密切联系。从学理上说,徒诗和乐府虽有各自不同的创作机制,但在社会用诗活动中,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的交叉,如曹植的《七哀诗》,就曾配楚调《怨歌行》传唱;相反,曹丕的《明津诗》则源于《长歌行》古歌辞。这些都很难从创作原则和文本特点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古诗十九首的生成方式具有多元性,其传播方式具有复杂性,对其是否为乐府的判定要根据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作具体考察。因为古诗十九首并非一开始就是严整的一组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零散的、杂乱的,不知作者和诗题的,《文选》编定后才成为一组诗类的概念。关于这一点,我们从陆机“拟古诗”12首与《文选》“古诗十九首”的对比中可以得到说明。西晋陆机曾根据古诗拟作了12首,现存于《陆机集》卷六,《文选》卷三十“杂拟上”也选了这12首诗歌。《文选》与《陆机集》中的12首诗歌从编排秩序、诗歌标题到诗歌文句没有任何差别。而《文选》卷二九选录的“古诗十九首”与陆机所拟的12首古诗有11首标题相同,而这11首相同标题的诗歌在二书中的排列顺序却完全不同。*陆机“拟古诗”12首之《拟兰若生朝阳》,《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无,其余11首全有,且标题相同。通过比较,透示出的信息是:其一,萧统编撰《文选》时陆机的个人文集已经广泛流传,《文选》卷三十“杂拟上”选录的陆机“拟古诗12首”很可能就是根据陆机个人文集选录的,所以二者没有差别。其二,萧统编撰《文选》时,传世的汉魏古诗远不止19首,“古诗十九首”是萧统从众多古诗中选出来的,陆机12首“拟古诗”也是从众多古诗中有选择性地拟作。
汉魏古诗的生成方式存在两大类别,即:乐府歌辞的徒诗化和文人的徒诗创作。“古诗十九首”亦不例外,至于哪首作品是乐府或古诗,应根据文献著录情况,对每首诗歌作出具体分析,而不能以一首类推其他,因为这些诗歌生成方式和产生时间不同,传播方式也不同。从“古诗十九首”具体作品看,有些作品可能就是乐府,因为后来音乐环境的变化,辞与乐分离,久而久之人们无从认识其乐府身份而归为古诗。如“驱车上东门”,《文选》《玉台新咏》称古诗,《艺文类聚》称“古驱车上东门行”、《乐府诗集》称“杂曲歌辞”,“冉冉孤生竹”《乐府诗集》称“古辞”等;此外,“迢迢牵牛星”《玉烛宝典》称“古乐府”;“青青陵上柏”《北堂书钞》称“古乐府”;“明月皎夜光”李善《文选注》称“古乐府”。如果以上著录的文献来源可靠,则此五首诗歌有入乐的历史。“生年不满百”则是简化汉大曲《西门行》古辞而成的古诗。汉魏古诗生成的复杂性和传播方式的多样性,远非一个“古诗”或“乐府”的称名能够表达清楚,回归其生成和传播的历史语境,当是一种可行的思路。
三 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及产生时间的讨论
关于《古诗十九首》产生的时间,主要有两汉说、汉末说和建安说三种,汉末说最通行。李善《文选·古诗十九首》解题曰:“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15](P1343)皎然《诗式》曰:“‘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为汉明矣。”[16](P29)近代学者梁启超、罗根泽、俞平伯、逯钦立、朱自清、陆侃如、游国恩、马茂元、叶嘉莹等人承其说,并进一步将之归结为东汉末年。80年代以来,李炳海以秦嘉三首《赠妇诗》为参照,推定《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认为秦嘉《赠妇诗》明显受《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断定《古诗十九首》的写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二十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17]。
汉末说主要根据有四:一是钟嵘对西汉说的否定。《诗品序》曰:“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4](P8)二是李善《文选》注“辞兼东都,非尽是乘”的论断。三是文人五言诗发展历史。四是《古诗十九首》情感基调与汉末动乱现实相吻合。但汉末说存在明显的几处疑点:其一,对《文心雕龙》“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18](P66)不能解释。其二,对李善《文选》注的误读。前引“古诗十九首”解题,李善对古诗十九首作者是枚乘的说法有质疑,其理由是《青青陵上柏》“游戏宛与洛”之“洛”指东都洛阳,《驱车上东门》之“东门”指东都洛阳最北的头门,两诗“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非尽是乘”即“不全是枚乘”所作。可见,李善是否认“古诗十九首”全为枚乘之作,并未否认“古诗十九首”中有枚乘之作。其三,汉末说对西汉或东汉初中期出现的与古诗风格相近的乐府古辞,如班婕妤《怨歌行》,也不能圆满解释。徐中舒认为此诗为颜延年作[19],而六朝的刘勰、钟嵘、萧统、徐陵等人均持班婕妤作。若《怨歌行》确为班婕妤作,与之相关的《长歌行》古辞、“客从远方来”古诗也当为西汉成帝时期或稍后的作品,与《怨歌行》产生的时间相差不远。
朱偰、黄侃、隋树森等人是较早持两汉说的学者,90年代以来,有赵敏俐、张茹倩等人力主两汉说。两汉说的主要文献依据有三:一是《文心雕龙·明诗》称:“邪经章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18](P83)范文澜先生认为,此处的“两汉之作乎”当为“固,两汉之作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赵万里语曰:“‘两’上有‘故’字,‘乎’作‘也’。案《御览》五八六引‘两’上有‘固’字,‘固’‘故’音近而讹。疑此文当作‘固,两汉之作也。’”。在刘勰看来,五言古诗佳作,是两汉之作,当时有人认为部分作品是西汉枚乘的,《冉冉孤生竹》一篇是东汉傅毅所作。二是《诗品序》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4](P6)三是《玉台新咏》杂诗八首,署名枚乘,其中七首与《文选》《古诗十九首》同。《文心雕龙》成书于梁天监年间,[20](P39)《玉台新咏》成书于梁中大通年间或以后,[21](P65-88)《文心雕龙》成书在《玉台新咏》之前。《文心雕龙》关于古诗作者“或称枚叔”的观点当不是依据《玉台新咏》,《玉台新咏》收录八首古诗系于枚乘名下,也不是依据《文心雕龙》,因为《文心雕龙》没有具体著录作品。可见,六朝当还有其他关于部分古诗署名枚乘的文本存在。两汉说的困难是难以确证作品产生的具体年代。有学者从历法、避讳、史书、诗歌文本中寻找根据,论证一些古诗的产生年代,如有学者从历法与自然节候的矛盾,推断“明月皎夜光”是太初改历前的作品,但汉末说举出反例予以反驳。[22]也有学者从李善《文选注》所引材料,推论古诗十九首的年代,[23]但证据也欠充分。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从分析《诗品》评价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一语的原意和班诗自身入手,认为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已经成熟,并推断“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艺术成就的《古诗十九首》,有个别诗篇可能出自西汉,个别诗篇可能产生在东汉末年,其中大部分诗篇则是东汉初年到东汉中期以前的产物”[24](P245)。
建安说的主要文献依据有二:一是钟嵘《诗品》曰:“《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4](P45)在钟嵘看来,《去者日以疏》等四十多首古诗,有人怀疑部分是曹植、王粲的作品。二是《今日良宴会》“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如神”二句,在《北堂书钞》中著录的作者是称曹植。建安说的较早支持者是胡怀琛、徐中舒等人,胡怀琛接钟嵘《诗品》的说法,进一步补充道:“子建、仲宣作,不肯自承,所以他人不知。”[25]徐中舒依据钟嵘《诗品》“《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的说法,认为“不但西汉人的五言全是伪作,连东汉的五言诗,仍有大部分不能令人相信”,“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19]。近年来,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力主建安说,分别从五言诗发展历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在主题、题材、情调、总体艺术特征、语言及篇章结构等方面的相关性,分析了《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如依据魏明帝景初年间历法用“丑正”,推断《明月皎夜光》等三诗大抵写在景初二年(239),作者可能是曹彪;又据“弹筝奋逸响”二句,认为“新声”应是铜雀台清商乐之“新声”,《今日良宴会》作者为曹植;又从语汇及篇章结构的比较,提出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诗是曹植于建安十七年至黄初二年之间写作的,主题大多与甄氏有关[26](P166);其后分专章从写作背景的角度论证了《涉江采芙蓉》《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的作者为曹植。通过这些论证,从而建立起《古诗十九首》“应该是建安、黄初及其之后的作品”[27]和“曹植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26](P158)的结论。不管其结论是否正确,木斋关于“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关系的研究颇具创新意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从方法论而言,作者将“古诗十九首”作为关系密切的一组诗歌看待值得商榷。“古诗十九首”是《文选》以后才形成的一个“类”概念,“十九首”诗歌并非生成之初就在一起。其题材内容也十分广泛,有伤别思乡、叹时嫉俗的痛苦,也有知音难遇、爱情未遂的感慨,还有行乐及时的愿望,几乎涉及汉代社会和文人生活的各方面,与汉代其他五言诗的题材内容基本相同。“古诗十九首”在《文选》之前并非关系密切的组诗。其次,在梳理五言诗发展进程时,未能客观对待诸如李延年《北方有佳人》、班婕妤《怨诗》、汉成帝时歌谣“邪径败良田”、秦嘉《赠妇诗》等汉代比较成熟的五言诗作品:一是无视《北方有佳人》等五言诗的存在;二是将秦嘉《赠妇诗》视为伪作,从而将五言诗的成立定于建安时期,为“古诗十九首”作于建安建立逻辑前提。第三,论证方式上存在“循环论证”,把一代诗风与历史上某一个诗人的爱情事件作因果联系,其论证逻辑值得商榷。作者以曹植、甄后人生经历与“古诗十九首”做比附,论证“古诗十九首”的部分作品为植甄传情之作,曹植是“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其结论似嫌牵强,仅可备一说。*参张末节《古诗十九首的诗学主题及诗学史意义》,《长江学术》2011年第1期。
究竟如何看待“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创作时代问题?杨慎《丹铅总录》曰:“《文选》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28](P33)此论虽显中庸,但最符合历史实际,惜其缺少最起码的时代断限。根据现存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成果,本文的基本态度是,“古诗十九首”当产生于西汉、东汉、建安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大部分可能产生于汉末。作者也非一人,但不能排除“古诗十九首”中有枚乘、傅毅、李陵,甚至曹植、王粲等人的作品。
通过对历代“古诗十九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知,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时代和性质问题是历代争讼的焦点,且观点分歧较大。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现存文献的严重缺失,使“古诗十九首”作者、时代与性质的研究成为学术史上难以破解的问题。除此之外,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也值得反思,最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推论加直觉式的研究方法。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古诗十九首”作为一组诗歌看待,并根据其中一首或两首诗歌的性质和创作时间推演其他诗歌。二是封闭与孤立的研究视角。以往的研究多将“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其生成的多元性和传播的复杂性。或持徒诗论、或持乐府论,各持一端,没有从文学行为及存在方式等“文学生态”的角度关注“古诗十九首”生成、传播等行为过程中与乐府交叉、更替和转化等复杂情况,缺乏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相互参照。“古诗十九首”研究历史和现状给我们的启示是:
第一,在充分认识“古诗”与“乐府”生成机制、传播特点的基础上,将“古诗十九首”放在五言诗发展变迁的历史长河中整体关照,既关注其与民歌、乐府的区别与联系,又考虑与其他文人五言诗的联系,多方参照、综合考察,不失为有效的方法。
第二,审慎对待相关史料,没有足够的证据,不轻易怀疑史料的真实性。在“古诗十九首”或者汉魏五言诗的研究中,对两方面史料尤其要审慎:一是李苏诗和秦嘉《赠妇诗》,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认定是伪作;二是关于《文心雕龙》《玉台新咏》《诗品》等文献对“古诗十九首”时代和作者的判定,若没有足够证据,宁可信其真,不可定其假。
第三,“古诗十九首”作为一个“类”概念是从《文选》才开始的,对其作者和产生时代的探讨,应还原其历史生态,对其生成机制也不能等同后世的文人独立自由创作,“十九首”均无题,具有文体初兴时集体创作的特征,应是多人多时多度创作的结果,而非一人一时一度的独立创作。*参欧明俊《〈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4期。
[1]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曹旭.诗品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5]徐世溥.榆溪诗话[G]//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35.
[6]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7]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8]朱乾.乐府正义[M].乾隆五十四年秬香堂刻本.
[9]冯班.钝吟杂录[G]//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0]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1]刘旭青.古诗十九首为歌诗辨[J].中国韵文学刊,2005(4).
[12]郑樵.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3]杨合林.古诗十九首的音乐和主题[J].文学评论,2011(1).
[14]赵琼琼.古诗十九首非乐府论[J].浙江学刊,2011(5).
[15]李善注.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7]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J].东北师大学报,1987(1).
[1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J].东方杂志,二四卷18号.
[20]周绍恒.文心雕龙散论及其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21]刘跃进.玉台新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2]朱偰.五言诗起源问题[J].东方杂志,第二三卷20号.
[23]张茹倩,张启成.古诗十九首创作时代新探[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0(4).
[24]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25]胡怀琛.古诗十九首志疑[J].学术世界,1935(4).
[26]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木斋.古诗十九首“东汉”说质疑[J].中华文化论坛,2006,(2).
[28]杨慎.丹铅总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赵成林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诗词曲源流史》(11&ZD105)阶段性成果,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之五。
吴大顺(1968— ),男,苗族,湖南保靖人,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I207.22
A
1006-2491(2016)04-0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