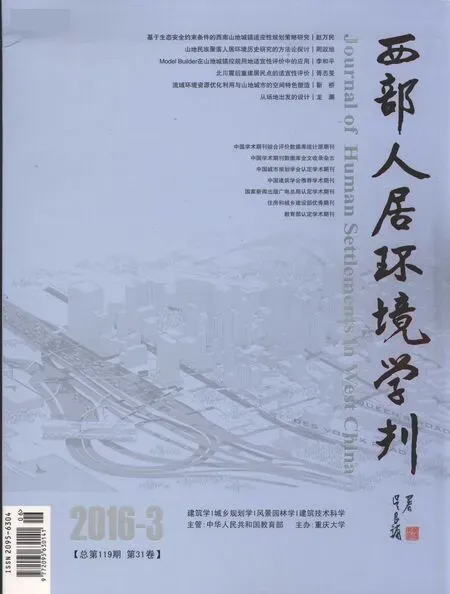基于农户满意度评价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以重庆市大柱新村为例
王 成 张 列 叶琴丽 杜相佐
基于农户满意度评价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以重庆市大柱新村为例
王 成张 列叶琴丽杜相佐
结合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构建满足农户需求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提高农户满意度,已成为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亟需解决的难题。以新型农村社区示范村——重庆市大柱新村为例,在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内涵与构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CSI评价法对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进行评价,进而剖析公共空间存在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以共生理念为指导重构公共空间。结果表明:受广场空间功能单一化、院落空间“城市社区化”、巷道空间功能衰退制约,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农户综合满意度为“一般”;重构后的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心、两区、三带”的空间布局结构。CSI评价法与“资源共享、环境共建”的共生理念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既能有效破解公共空间现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又能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新型农村社区;大柱新村
0 引 言
自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和村集体以此为契机,大力开展以农村集中住房建设为主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公共空间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农户对新型农村社区的认同、增进农户交流、提高农户精神文明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虽然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已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因乡村规划起步较晚,且缺少相关理论指导,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实践中常常存在“城市偏向”思维,不加区别地建造标准化的“城市社区”违背了农村不同于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忽视了农户的实际需求[2-5],降低了农户满意度,导致社区农户入住率低且后期建设的阻力加大。如何结合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营造满足农户需求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提高农户满意度,成为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亟需解决的难题。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传统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类型[6]、形态特征[7]、空间演变[8-9]、更新与重构[10-11]等方面,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研究较少,且从农户满意度出发重构公共空间的研究尚未见报道。重庆市作为统筹城乡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广泛开展并卓有成效,因此本研究以重庆市整村推进新型农村社区示范村——大柱新村为对象,在剖析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形态构成的基础上,运用顾客满意度调查(CSI)评价法对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进行评价,进而剖析公共空间存在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以共生理念为指导重构公共空间,以期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 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ZH068);西南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培育(14XDSK2004)
王 成: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乡村人居环境研究室验室,教授,wchorange@126.com
张 列: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叶琴丽: 江西省土地开发整理中心,助理工程师杜相佐: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图1 公共空间形态Fig.1 the form of public space
1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内涵与构成
1.1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内涵
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特定名词,最早出现在社会政治领域,后来逐渐进入城市规划以及其他领域[12]。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是“公共领域”的载体和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自发的公众聚会场所和机构[13]。“纯粹”的公共空间为不同人群提供活动、言论自由的场所,公园、活动广场、人行道、商场、社区中心及校园操场等均为公共空间[14]。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共空间的定义被认为“过于狭窄而很难阐释公共—私有空间的关系”[15]。奥登伯格(Ray Oldenburg)提出“第三种场所”概念[16],Acinta Francis等在其基础上,提出公共空间是存在于住宅和工作地之外的,让大众自由进入并促进居民一起活动、增加交流机会的集会场所,强调居民的广泛参与性[17]。我国一些学者认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内涵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指社区内的居民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寺庙、戏台、祠堂、集市、院坝等;二是指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的活动形式,如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活动、祭祀活动等[18-19]。综合现有研究并从规划视角出发,本文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可以理解为农户可自由进入并进行各项活动和交流的公共场所,表现为一种物质实体空间。
1.2大柱新村公共空间的形态构成
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形态一般可分为点状公共空间和线状公共空间。院落在农村社区中连接着住宅私密空间和外部开放空间,是一个半私密半开放空间,在公共空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有学者将院落从点状公共空间中分离出来,将其单独划分[20](图1)。经实地调研,大柱新村内的公共空间主要有以下几类。
院落——最基础的点状公共空间。院落空间是农户住宅围合而成的半封闭式空间(图2a),是农村社区中最初级的公共空间。在传统村落中,院落是农户晾晒物资、日常交流、举办红白喜事等的重要场所,承载着农户的地缘与血缘关系(如劳动力交换、资金交流、生产工具共享等),在农村社区公共空间中有着很强的农户心理认同感。但大柱新村受住宅设计局限性及土地集约利用号召的影响,院落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院落内部多由狭小的硬质路面和花坛构成,形态单一、死板,且不再被用来晾晒衣物和粮食等。院落空间承载的传统文化底蕴丧失,多样化的空间功能遭到忽视。
活动广场——规模最大的点状公共空间。大柱新村内的活动广场是所有公共空间类型中占地面积最大、可承载人口最多的,其位于新村入口处,设置了少量木椅、宣传栏、绿地等设施,被规划为社区公共活动开展的核心场所,力求丰富农户的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图2b)。

图2 大柱新村的公共空间形态Fig.2 patterns of public space in Dazhu New Village
巷道——最普遍的线状公共空间,巷道交织而成的网络使社区的各个公共空间形成相对紧密的空间层次。大柱新村以一条主干道纵贯南北(图2c),辅以若干东西向次巷道联通(图2d),形成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次巷道两侧栽种行道树,形成天然的巷间节点空间,是村民交往、休闲纳凉、驻足观察的重要场所。
2 农户对公共空间的满意度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作为农户集中生活的载体,既需满足农户对休闲、健身、娱乐等生活功能的需求,还需满足农户进行粮食晾晒等简单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功能需求,具有多重功能的特征。借鉴国土空间三生功能理论及乡村空间功能的相关研究成果[21],将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划分为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并据此将农户对公共空间的使用需求归纳为生活需求、生产需求、生态需求。由此,本文将农户对公共空间的满意度用生活功能满意度、生产功能满意度、生态功能满意度三个维度表征。
CSI评价法即顾客满意度调查(Customer Satisfaction Investigation,CSI)评价法[22],主要通过调查统计顾客满意度来评价某项产品的市场接受程度,被广泛应用于产品的市场评价及环境质量改进[23-25]。农户作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服务对象,即公共空间的“消费顾客”,其满意度评价可有效揭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存在的关键问题[26]。在遵循客观性、科学性、代表性和有效性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中反映三生功能的构成要素和研究区实际情况,从农户生活功能满意度、生产功能满意度、生态功能满意度3个层面选取15个指标,构建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
2.1.1生活功能满意度
座椅等休憩设施、单双杠等健身设施、读报栏等文化娱乐设施、垃圾箱等卫生设施、路灯等照明设施与巷道等通行设施是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中反映生活功能的主要构成要素,对满足社区内农户的日常生活需求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选取休憩设施满意度等6个指标来测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给农户生活功能需求带来的满意程度。
2.1.2生产功能满意度
尽管当前大柱新村农户生计来源多样化,但务农收入仍是部分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农户对粮食晾晒、蔬菜种植、家禽饲养、农具储存等农业生产空间的现实需求较强。由此,选取晾晒空间满意度等4个指标来测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给农户生产功能需求带来的满意程度。
2.1.3生态功能满意度
绿化覆盖率与植被多样性直接影响到公共空间生态功能的发挥,足够的花坛面积、良好的卫生与景观维护能间接增强公共空间的生态功能。由此,选取绿化覆盖率满意度等5个指标来测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给农户生态功能需求带来的满意程度。
2.2指标权重的确定
由于各指标的重要程度不同,为避免主观因素影响与客观赋权法对数据的过分依赖,本文采用AHP法和熵权法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熵权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ej是指标j的信息熵;dij是农户i的第j个指标分值;pij是第j个指标下第i个农户的特征比重;wj是指标j的熵权权重;是农户数;n是指标数。
依据AHP法和熵权法得出指标权重,通过式(4)-(6)式计算指标组合权重。


式中:α为熵权法权重的组合权重系数;β为AHP法权重的组合权重系数;wj是指标j的熵权权重;hj是指标j的AHP法权重;zj是指标j的组合权重。指标体系与权重具体见表1。
2.3满意度综合评价值的计算
根据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李克特量表测量法,将农户满意度划分为五个等级,即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很不满意,五个等级分别赋值为5、4、3、2、1。农户满意度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重庆市合川区大柱新村的逐户调查数据。为获得更加真实可靠的调查资料及增强研究过程的系统、深入和独立性,通过“驻村体验”式调查策略,入驻大柱新村,对当地农户日常生活进行深入了解,并采取参与式农户调查法进行农户调研,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表1 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Tab.1 peasant household’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ublic space in Dazhu New Village

表2 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等级划分Tab.2 peasant household’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grade of public space

表3 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结果Tab.3 peasant household’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results of public space in Dazhu New Village
2.3.1问卷设计
在入驻大柱村前,首先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问卷涉及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特征、农户生计来源、农户对公共空间的满意度及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情况4个大项、91个小项。
2.3.2预调研
2015年8月入驻大柱村,一个月内走访大柱村所有农村居民点聚居地,掌握大柱村及大柱新村农户生活习惯与公共空间布局等情况,期间通过与农户的交流及在大柱新村抽调20户农户调查情况,修改与完善调查问卷,最终确定问卷内容。
2.3.3调查实施
2015年9月初,对大柱新村已入住的300户农户开展参与式农户调查。由于前期与农户情感的培养及对社区建设了解的深入,通过与农户点对点式访谈,历时10天完成所有问卷调查及资料收集工作。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300份,有效率达到100%。对通过参与式农户调查法获取的农户满意度数据进行统计计算,获得满意度综合评价值。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j为第j项满意度评价指标的满意度均值,vij为被调查的第i个农户第j项满意度评价指标的满意度值,n为有效调查农户总数,p为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综合评价值,m为评价指标总数,Zj为指标的权重。根据“差松优严”原则并参考相关研究成果[27],将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结果划分为满意、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四个等级,分别赋予各等级对应分值,见表2。
2.4评价结果与分析
经过计算,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农户综合满意度为2.69(表3),综合满意度等级为“一般”。其中农户生活满意度为3.18,处于“较满意”状态,相较于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前,交通、照明与卫生设施给农户生活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改善,但广场空间休憩、健身、文化娱乐等设施不完善使农户生活功能满意度未达“满意”状态;农户生产功能满意度为1.94,处于“不满意”状态,部分农户占用院落空间饲养家禽、堆放杂物,扰乱了空间秩序,晾晒设施的缺失也给农户晾晒粮食带来不便,使其生产功能满意度普遍很低;农户生态功能满意度为2.91,处于“一般满意”状态,巷道空间作为社区内主要的绿化空间,其植被单一、绿化覆盖率较低、卫生与景观维护不到位等使农户对绿化设施发挥的生态功能满意度较低。不同指标反映了公共空间中不同的构成要素,不同要素又构成了不同形态的公共空间。大柱新村公共空间由广场空间、院落空间和巷道空间三类典型子空间构成,从表征各功能满意度的指标值来看,各指标的满意度值不同,反映出不同形态空间存在的关键问题各异。据此,下文分别从广场空间、院落空间及巷道空间入手,基于评价指标满意度值剖析各子空间存在的关键问题。
2.4.1广场空间功能单一化
活动广场中的公共设施主要有座椅等休憩设施、单双杠等健身设施、读报栏等文化娱乐设施、垃圾箱等卫生设施和路灯等照明设施。除卫生设施、照明设施满意度值处于“较满意”状态外,休憩设施、健身设施、文化娱乐设施满意度值均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活动广场空间配套设施简陋,缺乏篮球场、乒乓球台、广场舞场地、凉亭绿廊等多元化的生活功能设施;同时,广场空间已有设施数量与质量严重不足,且因后期维护不当,设施损坏严重。社区公共空间的使用者以中老年人与中小学生居多,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影响的加深,其对多样性生活功能设施的需求日益增强[28],这就导致功能单一化的广场空间与规划设定的社区休闲、健身、交往等公共活动开展的核心场所的营建目标相去甚远。
2.4.2院落空间“城市社区化”
院落空间由狭小的花坛和硬质铺地构成,与传统院落相比,面积大大减小,以粮食晾晒及蔬菜种植为主的生产功能、以农户交往为主的生活功能逐步消失,所以表征生产功能满意度的各指标值均很低。大柱新村规划片面借鉴城市社区的设计模式,仅考虑农户对居住和生活功能的需求,忽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对粮食晾晒、蔬菜种植、家禽饲养、农具储存等设施的现实需要,导致农户的生产功能满意度处于“不满意”状态。狭小的花坛不能满足农户在院落中种植蔬菜的需求,院落内部较差的采光又不能满足农户晾晒粮食的需求,院落空间“城市社区化”的直接后果是部分农户占用公共空间饲养家畜、停放农具、堆放薪柴,严重破坏了公共空间环境和运行秩序,是影响社区农户和谐共生的重要因素。
2.4.3巷道空间功能衰退
大柱新村门户前6m宽的钱金路与其周围3.6m宽的硬质水泥路构成了其与外界之间的联系通道,村内主巷道与次巷道则形成了社区内部纵横交错的路网。传统巷道空间是承载农户日常通行、交往、驻足观景等行为活动的场所。调研发现,社区外围交通干道未设绿化隔离,社区受外界噪音和灰尘污染较大,农户公共活动的安全性受到影响,因此这部分交通空间的交往功能逐步衰退。社区内部主巷道因无任何绿化与休憩设施而显得呆板、空洞,与传统自然乡村地域景观相比,带给农户的归属感与亲切感不强;次巷道两侧行道树缺少对植物季相变化的考虑,树木单调整齐,缺乏层次丰富的灌木与草丛,可观赏性不足。加上卫生与景观维护不到位,绿化植被普遍存在存活率低、幼小、稀疏、庇荫效果差等问题,导致农户对绿化覆盖率、植被多样性、卫生维护、花坛面积、景观维护的满意度值均不高。
3 大柱新村公共空间的重构
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结果表明,广场空间功能单一化、院落空间“城市社区化”、巷道空间功能衰退是当前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存在的关键问题。在公共空间既有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合理配置各子空间的构成要素,是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农户满意度的关键所在。共生理论作为研究空间系统的微观性质及宏观表现的重要理论,既能阐释不同空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又能诠释空间主体间的竞合关系,为合理有序地进行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重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下文以共生理论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重构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并分别以广场空间、院落空间、巷道空间为代表予以阐述。
3.1广场空间的重构
根据广场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进行功能植入,增设晾晒场、篮球场、乒乓球台、广场舞场地等设施,并根据“资源共享”的共生理念,合理配置设施数量。其次,运用功能分离法将空间不协调的功能空间分开,避免因在功能上相互干扰的空间交叉而产生安全隐患。同时,为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利用时间差将功能复合的空间进行功能融合,以实现不同功能空间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协调共生。具体重构结果如图3所示,活动广场共分为四个功能区:(a)是体育运动区,其内设有篮球场、乒乓球台,并配有休憩凳、路灯、垃圾桶等便利设施,满足农户对健身设施的需求;(b)是功能复合区,农忙时节白天用作晾晒场,其他时间可用于农户举行大型集体活动如跳广场舞、红白喜事等,实现不同功能空间的协调共生;(c)是社区门户区,用于提升空间的层次感与景观效果;(d)是休闲娱乐区,设置休闲座椅、文化宣传栏、跷跷板、单双杠等休闲文化娱乐设施与全民健身设施,满足中老年和儿童对多元化生活功能设施的需求。此外,在广场外围栽种行道树并设置曲线花境作为屏障,在保障广场空间公共活动安全的同时,提升空间的景观效果。重构后的广场空间突破了功能单一的困境,可真正成为社区公共活动开展的核心场所。

图3 广场空间的重构Fig.3 square space restructure

图4 院落空间的重构Fig.4 courtyard space restructure
3.2院落空间的重构
根据院落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把“环境共建”的共生理念融贯到空间环境整治中,拆除违章搭建的棚屋(如鸡棚),清理院内堆放的杂物,规范公共空间用途。其次,在院落空间中规划一块自留地,根据“资源共享”原则,按户数平均分配,以满足农户对蔬菜种植的现实要求。第三,增加绿化设施,发挥院落的景观与生态功能。此外,在院落节点处设置休憩凳椅、路灯、垃圾箱等,构成极具活力的开放空间,保障院落公共活动,促进良好邻里关系的形成。具体重构结果如图4所示,以庭院小道为界,院落空间被分为两大功能区:(a)为蔬菜种植区,农户根据各自需求种植蔬菜或花草,在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的同时实现农户间的物质与空间共享;(b)为硬质铺地的休闲区,配置休憩凳椅、路灯、垃圾箱等设施,为农户的休憩与交往创造积极的空间环境与氛围,促进邻里关系和谐。
3.3巷道空间的重构
根据巷道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采用功能分离法将社区外围功能不协调的空间以绿化隔离带进行有机分离,以保障公共活动的安全。其次,根据社区内部主巷道空间的布局规划绿化景观带,改造次巷道空间的绿化设施并加强后期维护,以恢复巷道空间中绿化设施应发挥的景观与生态功能。此外,在巷道空间节点处设置一定数量的休闲座椅,以丰富巷道空间的界面层次,进而促进邻里交往活动的发生与农户间的和谐共生。具体重构结果如图5所示:(a)为社区与外围公路间的绿化隔离带,其一方面隔绝了公路灰尘、噪音等污染,满足了农户对公共空间安全性与舒适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绿色空间和生态屏障;(b)为社区内巷道空间中的绿化景观带,银杏、山茶、绿篱等具有层次与色彩变化的植被恢复了巷道空间绿化设施景观性与生态性的双重功能。
重构后的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呈现出“一心、两区、三带”的布局结构(图6):“一心”即广场空间重构后形成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心,其辐射范围为整个社区,服务于大柱新村所有农户,是农户休闲、健身、交往等公共活动开展的核心场所,对丰富农户文化生活、促进社区内农户交往与和谐共生有重要作用;“两区”为院落空间重构后形成的两个住宅组团——院落西区与院落东区,重构后的院落空间既破解了简单移植城市社区模式的弊端,又满足了农户对传统院落生产与交往功能的需求,延续了传统文化,实现了乡村与城市生活的完美结合;“三带”是巷道空间重构后形成的三条绿化景观带,作为社区绿化空间的骨架,其中的绿化与休憩等基础设施既发挥了景观与生态功能,又体现了公共空间“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4 结 语
运用CSI评价法从农户生活功能满意度、生产功能满意度、生态功能满意度3个层面构建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表明,广场空间功能单一化、院落空间“城市社区化”、巷道空间功能衰退是当前大柱新村公共空间存在的关键问题。评价结果符合新村现状,表明引入CSI评价法建立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能够较好地反映公共空间存在的问题,为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公共空间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研究方法。基于农户满意度评价结果,以“资源共享、环境共建”的共生理念为指导,将大柱新村公共空间重构为“一心、两区、三带”的空间布局结构,重构结果既有效破解了公共空间存在的关键问题,提高了农户满意度与社区认同感,又实现了不同空间的均衡与协调发展、农户间的空间共享与和谐共生,能够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农村的集中居住地,其公共空间建设应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在满足现代化生活功能需求的同时,更应遵循自然规则,尊重村民的习俗与生产生活习惯,突显农户的主体地位,真正将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农户需求紧密结合,寻求公共空间更新的策略与途径,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独具特色的宜居、宜游、宜业的美丽乡村。另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呈现出动态化、多样化特征,静态地选取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农户满意度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何根据农户多样且不断变化的需求测评农户对公共空间的满意度尚需继续探讨。

图5 巷道空间的重构Fig.5 alley space restructure

图6 大柱新村公共空间重构Fig.6 public space restructure of Dazhu New Village
[1] TALEN E. Measuring the Public Realm: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Link Between Public Space and Sense of Community[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2000(17):344-360.
[2] 王立, 刘明华, 王义民. 城乡空间互动——整合演进中的新型农村社区规划体系设计[J]. 人文地理, 2011(04): 73-78.
[3] 刘彦随. 中国新农村建设创新理念与模式研究进展[J]. 地理研究, 2008, 27(02):399-400.
[4] 叶琴丽. 基于农户视角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4.
[5] 吴燕霞. 村落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福建省屏南县廊桥为例[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6(01): 99-106.
[6] 曹海林. 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05(06): 61-73.
[7] 刘兴, 吴晓丹. 公共空间的层次与变迁——村落公共空间形态分析[J]. 华中建筑, 2008, 26(08): 141-144.
[8] 王东, 王勇, 李广斌. 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特征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3(02): 57-63.
[9] 李彤玥, 周波, 张碧玮, 等. “细胞分化”:解析社区公共空间的演变——针对街巷式居住片区和现代居住小区的对比分析[J].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12, 38(04):231-234.
[10] 王伟. 转型时期乡村公共空间的重构研究[D]. 西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
[11] 张健.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更新与重构——以番禺大岭村为例[J]. 华中建筑, 2012(07): 144-148.
[12] NADAI L. Discourses of Urban Public Space, USA 1960-1995 a Historical Critiqu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2000.
[13]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 译.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9.
[14] ALTMAN I, ZUBE E. Public Places and Spaces(Vol. 10)[M]. New York:Plenum Press, 1989.
[15] NEMETH J, SCHMIDT S. 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Measuring the Security of Publicly Accessible Spac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7(73): 283-297.
[16] OLDENBURG R. The Great Good Place: Cafes, Coffee Shops, Community Centers, Beauty Parlors, General Stores, Bars, Hangouts and How They Get You Through the Day[M]. New York:Paragon House, 1989.
[17] FRANCIS J, CORTI B G, WOOD L, et al. Creating Sense of Community:the Role of Public Spa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2(32):401-409.
[18] 曹斐. 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规划模式研究[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5.
[19] 许家伟, 何长涛, 乔家君, 等. 村落公共空间的农户认知与支付意愿——以河南省双沟村为例的经验研究[J]. 经济地理, 2012, 32(03): 120-125.
[20] 赵之枫, 曹莉苹. 农村社区公共空间规划研究[J]. 小城镇建设, 2012(08): 61-65.
[21] 李广东, 方创琳. 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定量识别与分析[J]. 地理学报, 2016(01): 49-65.
[22] FORNELL C, MICHAEL D J, EUGENE W A, et al. 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Nature, Purpose and Finding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6, 60(10): 7-18.
[23] 乔家君. 中国乡村社区空间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24] 李燕. 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构建研究——基于公共财政的视角[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25] 李伯华, 刘传明, 曾菊新. 乡村人居环境的居民满意度评价及其优化策略研究——以石首市久合垸乡为例[J]. 人文地理, 2009(01): 28-32.
[26] 余亮亮, 蔡银莺.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J]. 自然资源学报, 2015, 30(07):1092-1103.
[27] 罗文斌, 吴次芳, 倪尧, 等. 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及区域差异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08): 68-74.
[28] 柴彦威, 郭文伯.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路径[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04): 466-472.
图表来源:
图1、3-6:作者绘制
图2:作者拍摄
表1-3:作者绘制
(编辑:郑曦)
Public Space Restructure of New Rural Community Based on Peasant Household’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of Dazhu New Village in Chongqing Municipality, China
WANG Cheng, ZHANG Lie, YE Qinli, DU Xiangzuo
How to construct a new type of rural community public space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of the rural areas to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easant household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rural communities. This study takes Dazhu New Village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public space in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using CSI evalu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satisfaction of public space of peasant household in Dazhu New Vill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key problem of public space can be analyzed. Th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ublic space can be restructur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mbiosis idea.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due to a series of problem, such as the function simplification of square space, the function deterioration of alley space, and the unreasonable copy of urban community pattern of the courtyard space, the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of public space in Dazhu New Village presents a “general” level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econdly, after restructuring, the public space of Dazhu New Village presents a spatial layout shape like “one center, two zone, three belts”. Thirdly, the CSI evaluation method and the symbiotic idea of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benefit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is strongly suitable for the public space restructure of new rural community. Not only can they efficiently solve the key problem of public space, 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oriented new rural community.
Public Space; Peasant Household’s Satisfaction; New Rural Community; Dazhu New Village
10.13791/j.cnki.hsfwest.20160311
王成, 张列, 叶琴丽, 等. 基于农户满意度评价的新型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以重庆市大柱新村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6, 31(03): 68-74.
K901.8
B
2095-6304(2016)03-0068-07
2016-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