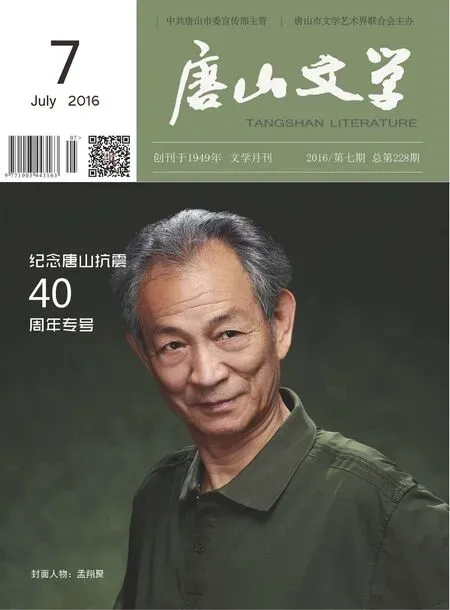震后40年点滴
徐国强
散文诗歌类
震后40年点滴
徐国强
进入丙申年,我便仿佛被神灵驱策着一样,开始写唐山震后40年内容的诗。陷入忆念和冥想中的我,显得有些恍惚;我提醒自己,明确起来,不要轻易走失;40,到底是怎样一个数字,竟然不惑得让我有些茫然。
我正儿八经地坐在电脑前,开始敲第一个字——键盘所有的按钮都被设计好了似的,全部直通过去的日子。
1.
渤海湾畔、燕山脚下、长城围挡内的唐山,其实有着4万年的生息史,而这座城真正闻名于世的由头主要在于两样:煤和大地震。一个是倾覆的森立在地下经过亿万年形成的能够燃烧的太阳石,一个是24万人瞬间寂灭、百年城转眼成一片墟土的生存之火几乎被吹熄的大悲剧,唐山,包裹着生命之力也包裹着生命之痛被世界所知道,幸也不幸。
我是一个“震漏”,地震那年我17。
我在诗中写道:“身上带着小伤,我从废墟里爬出/我带着我的十七岁爬出/我带着凌晨倒塌屋顶压住的黑和天上凄清的亮爬出/迎头碰上,父亲正在淌血的一声欣慰的叹息/迎面,是破碎的全部和全部破碎/我的身子下/一座重要的城/比趴着的我还低,也趴着/在百年上,在已经破烂的繁荣上,在意外的疼痛上//
“侥幸是一双手,它将我从毁灭的子宫里/拽出。我翻过身子仰面向天/一缕新鲜的风告诉/我新生/开阔的废墟的产床上/升起的朝霞是流出的羊水//
“只是没有哭声/大地一片寂静/突然的灾难夺走了我们所有的语音/我们哑巴着,响声是急匆匆扒人的手/掀开房顶;是急匆匆追赶关键一秒的脚步/踩踏着火和雷霆;是急匆匆生火做第一顿饭的木柴/爆裂的火花开放,水开滚烫滚烫大朵大朵的白花//
“1976年7.28/我第二次生命的生日。”
说到40年前那场天灾损失的惨重,除了因为发生的时间是在大家熟睡的凌晨之外,还因为当时的房屋都是四墙砖石垒码、椽檩榫卯相接、厚厚的焦子顶压盖,禁不住摇晃;楼房的建造水平和条件都在那儿,谈不上抗震。我甚至认为,也与备战备荒呼声中家家户户在院子里“深挖洞”的掏空做法有关,还涉及到我们天灾意识上的空白和对地震预兆的无视、漠视和轻视。
地震发生了,我们最先认定的是爆炸了原子弹。那个时代,就那种思维,没办法。
我家曾养一猫,毛色蓝白相杂,雌。因为我妈妈爱猫,当时还没有宠物这一概念,家人就觉得应该对它好。地震发生前那些日子,这猫便总是不愿进屋,老往外跑;偶尔进来,就往我怀里扎,并一直不安静地翻滚。它肚子鼓鼓的,妈妈说它要生了。那些天,我经常小心地摩挲着它,给它安慰,试图让它不那么烦躁,从未想到这是一个凶兆。地震了,我与死神擦身而过从废墟里爬出来,没来得及想到猫和它烦躁的原由就开始为运走遇难母亲的尸体而奔走。听姐姐说,这猫原来躲进了院里的小棚才没被砸着,震后第二天,它从小棚里出来,悄悄舔净了母亲满脸的血污,就又悄悄回去了。我去看,这猫圈卧在小棚一角,怀里有三四只小猫,哦,它生过了,什么时候的事?运走了母亲的遗体,又过了几天,等我想起它走过去掀开小棚时,却发现它和它的孩子都不见了。它走了,它带着它的孩子一起走了。是随它的主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还是怪我们照顾不周负气远离?去了哪里?为什么要抛下曾经的家?我一直不解。直至这时,我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敏感的精灵曾经对我们有过急切而善意的提醒,我们一直在辜负着它的聪慧和美意;顿时明晓这一点是多年以后的事,那已经太晚太晚了,可见当时我和我们多么无知。
话说回来,即使看出来了是预兆,我们又能怎样?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有局限的,一块砖、一枚钉子、一个大脑,都属于相应的时代,我们摆脱不了,这就是无奈;时代在更替,等我们进入到另一个环节而回望原来的枝蔓时,我们才能看清许多当时不明晰的东西,虽然滞后,但也有益,还是一种无奈。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来谈论问题,但可以跨越历史时期去看待问题,因为我们需要进步,尽管这进步总是那么艰难,像经历一场重生。
我在诗中写道:“这是一种特殊的降生/来到这个世上就要直接站立着生活/没有摇篮,没有催眠曲/没有学步阶段//我努力睁开眼,我头顶上的残星一岁/门口被坍塌的墙压弯的树一岁;大地的裂缝/张着嘴待哺,一岁/都一岁;我母亲却错过这一岁/永远闭上的眼睛,关上了她63岁的门//我十七,也一岁/刚刚长出胡须的一岁/心里骚动的爱也被爱迷惑的一岁/已经挺高个子、挺大身躯的一岁/这样那样的一岁,缠着绷带/光着脚,眼睛空洞得比深渊还深,比麻木还麻木//
“好几天才缓过神儿来/眼泪、哭声、叫喊都来了/解放军来了/粮食、鞋、慰问来了/草味儿和丰富起来的饭味儿来了//”
震后第一个春天,“靠血先暖过来自己的躯体/从这样一个人身上开始,一座城/开始呈现起初的绿意、蓬勃和繁荣”。
2.
像当今不断有奇怪的网络用语产生一样,那时的民间也会时常冒出几个新词语,只是量小,传播范围有限。这正是我们古老汉语的活力所在,也是任何一种语言都需要的在漫长进化过程中的自我良性补给。那时,街坊间比较流行两个词语,一是“震了”,一是“超平”。前者表效果惊人且影响力大,后者表不一般,二者勉强可以算近义词。
那时是一个乏味的时代,两个新词语给我们带来的新奇和喜悦是难以言表的。就在这两个词语火到顶峰的时候,唐山“震”了。真是一语成谶,二词成谶。是巧合,还是嘴与大地的呼应,甚而至于是语言和地球的一次密谋?无关迷信,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甚至连这两个词语生成的缘由和时髦起来的道理都还没弄明白,我们的家乡就变成一片废墟,彻底“平”了。鬼使神差的大震,令人痛心疾首的大震。
“死神盯上你并不跟你打招呼/它注意你,你就出不来了;它放过你/你就有了生的幸运也就有了活的艰难和快乐。”
刚活下来的我们,碰面打招呼,都是这样一种情景:
“‘没死呀你,还活着。’/‘嗯,杨志平和小芹没了。’”
“我们”之外,只不过换上了另外一些人的姓名,语气和嗓音也有异,但内容一致。
“我们衣冠不整地踩在破碎的家的上面/呼一口灰烬吐一口死的气息,表情/脱离了脸,木木地对话/你的一滴泪见到我的一滴泪/我的一滴泪问候你的一滴泪/都是看不见的泪/我们的泪/早已在红红的眼睛里被无奈和愤怒烧干//一切都塌了/我们,立着。”
大地震让我对“活生生”这个词有了充分的感知,活生生的生离死别,活生生的死亡惨状,活生生的鲜血泪眼,痛苦活着面对你,痛苦活活生出一根手指,痛苦用那根手指活生生指给你看:“我就在这儿。”
生存的第一要务是吃喝,第二当然就是遮风避雨,所以要盖房子。唐山人至今感谢解放军,成排的、像样的简易房都是他们给大家盖的;我父亲是退休矿工,有生存本领,他要自己盖。
“以原来房子为基础/让散落的一切重新回去,让砖头和油毡压住风雨//
父亲干活的时候,是一瘸一拐的/爬出废墟时,一个大钉子冒将他的腿划出一个大口子/有一尺多长,他用家里的白酒为自己消毒/没见他说疼/就开始搭帐篷/开始惦记着我,饿与不饿//
“旧家上的新家盖好了/每一块红砖与每一根檩柱都带着昨日的体温/抱着我们父子;春节前,转院到石家庄的姐姐/回来了,我们一宿未睡,躺在炕上说话/炉子烟筒快被烧红了,我从被窝伸出手/不小心碰到了它,我被烫伤//
“我在炉子上熬粥/一边在锅里搅拌一边哼唱歌曲/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还唱//
“我的豪宅呀,塑料布当窗玻璃的豪宅/我的豪宅呀,藏着深情和故事的豪宅/除却这样的豪宅/世上还有哪一间/能让一场大灾悄悄安睡/能让大悲和大喜发出一样的鼻息,同住”。
震后残破的废墟上,弥漫着一种人们相互怜悯、相互体恤、相互照料的温情。地震让我们失去了一切,也让一生带不走的那些东西变得更无所谓了,人在,心在,情在,这样活才更对。
“哪一年的哪一个节日,邻居姐姐/给我家送来一绺韭菜和两个青椒/两样都是绿的,青青的/恩情//
“在这座城,将你扒出来的人你也许不认识/救你的人也从不将过去的事挂在嘴边/有命垫底/命上面:轻的重了,重的变轻//
唐山市一座懂爱也具备爱心的城市,这主要在于大地震中唐山亲身攥住过从四面八方伸来的援手,感受过救命的恩情。知恩图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和心理,所以爱着你的爱、奉献着你的奉献就变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四川汶川发生地震时,唐山人有过不俗的表现,就是说明,对此,我深以为耀。只是,唐山的感恩是以命为基础的,这起始面太宽厚又太广大、着眼点太集中又太深邃,
不易让人承受;唐山的感恩还讲究“瓜子不饱是人心”,命有时就是一口水一粒米的事,不完全是舍身得身的那种重量级关系,所以,在唐山人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小恩小惠也具备大爱的意义。唐山认识事物的辩证性和通达性极高,这体现着民风,也反映出这一带人淳朴爽直的天性。
“我一直想回报回报我那位邻居姐姐/就是觉得不自然,没有合适的机会/存世的恩情/应该就是这样多起来的/多起来的恩情/让存世的我们觉得活着还有些意思”。
欠着别人一份情,这份情会成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念想,也会成为我们继续努力生活下去的一种动力。你欠着别人呢,他们对你那么好,你应当变得更好,否则,多亏心哪。这就是恩情的逻辑。大家都认。
“生活进入正轨,我们就容易恢复常态/牛角尖里就会产生一些拥挤/无法回去也不用回去了/那就叫上40年前那段震波/一起去地震纪念馆看看,坐坐吧。好法儿”。
这是后话。
3.
大地震已经过去40年了,40年,说短也短说长也长。说短,是因为时间如白驹过隙,放到宏观的人类历史发展中去衡量,的确算不上久远;说长,是在于其间的每一日都是我们生命中珍贵的经历,在一些关键点上又盘亘着我们太多的思虑和耗费了我们太多的心血,我们一直是在难以自拔中奋力迈动着向前的脚步的。对一个人来讲,40年,本就已是高估的寿命的一半了。
我写自己,“40年,我一边唱着流行歌曲/一边沉溺在思想的尽头。爱上过一段领带西装/学习过一段电脑打字,浸泡过一段酒吧/焗染过一段头发/写过一段诗歌/走过一段边缘”。
我写这座城,“10年重建:盖新家/10年振兴:让肌肉更结实/10年发展:把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路修宽/10年转型:亲海听海踏海,找回蓝天白云”。
我写自己和这座城市,“以40年为一眨眼,我是翻天覆地中/躲过铲土机的蚯蚓,耕地,泥土上开别人的花/以40年为一唏嘘,我是高楼大厦旁的矮子/没能长成巨人也不耷拉着脑袋在花园里散步/以40年为一抖擞,我晃不回自己的青春/
我留在你身上的青春却能让40岁的你看上去更显年轻/以40年为一个我,你怆然而歌/以我的40年为一个今天的你,我愿将多出来的年岁抹去”。
经历过地震的人,对搬家都十分习惯。地震把家砸没了,收拾收拾躲进简易房是第一次搬;基本的一次是,从简易房搬到新楼房,新居新生活;选择性的应该也有一次,是从震后第一代楼搬到改造后较为宽敞的楼里;还有改善性的一次,从已经较好的住处搬进更为舒适和可心的高楼大厦。不算更新意识强而来回挪窝或随市场行情变化不断倒腾房子玩儿的,三或四,该是唐山人搬家次数的基本单位。我要说的意思是,生活环境和空间的移换对人的存在感和思想意识影响很大,即使是在一座城的小范围里,我们由此至彼的挪腾也会带来情感和意念上的撕扯、断裂和复合式的新滋生、新确认。这种小游牧式的迁徙,将我们根的范围扩大,牢固的一对一的认定被斩断之后,我们死守的稳定的故旧的一切都获得了某种解放,实现了虽痛苦但自由的多点换位生存,因此,我们和这个世界变得两开阔。
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唐山人婚丧嫁娶、生孩子多喜热闹,倒不是大操大办,而是乐意整出点动静。不像雅气的一线城市,保持有节制的欢乐度和对往生的肃穆,唐山人敞开了欢乐和悲戚的大门,少有压抑和低沉的掌控。这当然与风俗和民情有关,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一种生命态度和生存心理。在这片生死曾经混杂在一起的土地上,死,正常,应当向老天爷和邻居们通报一声;嫁娶,生命之转折,建立新家庭,就是要庆贺;生孩子,血缘延续,生生不息的现实,酒和诚挚的祝福都不能少。由于有大地震这个背景在,这里正常的生命起止和日常的家庭喜事就都多出来另外一层意义。
我在诗里写过一场婚宴:“我好友孙子的满月宴在豪华的大酒店举行/我坐下的时候酒已经提前斟满//酒开始掌控全局:鼓捣人出洋相,调大/说话的音量,染红众人的笑脸//一个乐子/生一百个乐子/一百个乐子都在一杯酒里晃荡/请尽情品尝吧,不用去找什么/乐子,从来就没有应当或不应当的落点//
“碰杯时,玻璃悄声告诉你:东家是一个地震孤儿/夹菜时,筷子偷偷探到底细:他独自一人将两个妹妹养大/直至姐俩一一出嫁;如今他当上了爷爷/根儿长出了根儿;他媳妇地震没了哥/就把他当哥,结了连理,有了今天//
“那我还不知道,我们俩是发小/我熟悉他就像我熟悉自己//
“饭桌上没人公开说东家是一个地震孤儿/没人公开说他独自一人将两个妹妹养大,直至姐俩一一出嫁/喝!但大家都在心底里庆贺他当上了爷爷/根儿长出了根儿。喝!地震没了哥哥的姑娘/如今也当上了奶奶。喝!一对苦孩子家的甜/百味齐全//
“我醉在40年前的云头,往下打量/我朋友当时也就十五六岁/他当爸还要当妈/他多么伟大//
“一场酒/一场梦/一场戏/一场不空。”
其实这是一个真事儿,我试图以这样一个故事和场景来概括我们悲喜交集的40年经历,品咋40年岁月逼我们品尝和我们自身努力烹饪出的生活滋味。这里面有不屈和负责的生活态度,有勇于承受和担当的使命意识,有相濡以沫、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但我主要想表达的,是一个人对震后40年生活的感慨。现场浓缩历程,我们因难言内心的苦痛而醉,我们在醉中清醒着,心里头跟明镜似的。
4.
一定的社会环境、一定的时代条件、一定的家庭背景,在这些外在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一个人受一定历史进程的裹挟和一定个人性格、潜质和爱好的决定,而在有限范围内主动做出自身生活方向上的选择,并由此形成一种既定的生命现实,我们称之为“命运”。意外的偶然事件发生和体内的遗传基因内驱,在一个人命运的形成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就造成了命运的神秘性和难料状态。这不是迷信,恰恰相反,命运十分真实,就摆在我们眼前。
唐山这座城和这里面的人又是怎样一种命运呢?
我写了《死死记住1976》:
“站在断崖绝处,我望见绝望的纵深/迷茫吞噬的山河里,一个17岁的孩子正饱经沧桑//沧桑是命运强塞给他的,让他无法摆脱/让他眼睁睁看着:这一年
先后三位伟人和他24万乡亲一起走了/送一场十年浩劫/队伍中/有他的母亲//
“一场浩劫需要一场灾难作结/一场浩劫的惨痛需要一场灾难的惨象呈现/一场灾难将难言、悲苦和伤痛都推给了我们和这座城/难言、悲苦和伤痛都进入了我们的体内和这座城的角角落落/要知道,一座城的难言、悲苦和伤痛/就是13472平方公里的难言、悲苦和伤痛啊/这是谁的主意,谁的安排?/天哪,我的天//
“他的祖国就是要通过一些人这样表达自己/她的民族就是要通过一座城这样表达自己/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躲//
“一阵十月的锣鼓,敲打在我的命门上/整整敲了一下午,都是以4计为一组
1976,1976/1976,我们用摔碎又攒起来的灵魂记住这个年度/我们用撕心裂肺的痛感记住这个年度/记住死/也记住生。”
我曾不厌其烦地强调过唐山大地震发生在1976年的典型性,以及这场大地震与国家和时代的关联。不只是巧合,还有客观上的对应、默认以及契合,这就是“命”。我们无奈时会说到这个字,深刻时也会说到这个字。有了这个字,不是为了让我们逃到里面去,可以躲到宿命的树下乘凉,而是能够烙印出我们人生岁月的标题,写出生存旗帜上的名号,让我们带着自己的编码去闯新的漫天风雨。
都说性格即命运,我更欣赏这样一种准确的表达:命运影响性格,性格影响命运。那么,唐山和她的人民又是怎样一种性格呢?我在诗中写道:
“不说死过一次,不说缺角的饭桌上热腾腾的饭/是伴着眼泪咽下的,不说24万集体的忌日/欠一场42万人/集体的哭号//
“一个当时17岁的幸存者,40年来/左脚1岁右脚18岁地踉跄着走到今天/也就是一眨眼的事/他也不说//
“冷静漠然的表情不给火山的岩浆留下任何出口/我们的嘴/封闭灾痛//非要说/就一句:没啥。”
每一个经历过大地震的唐山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把那场伤透了我们心的灾害挂在嘴边,不是特别的需要,更是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诉说自己的不幸、委屈和缺憾。至交间彼此询问,也就一两句话,在点头、摇头和唏嘘间交流,然后就会陷入深深的沉默;再然后,就改变了话题;再然后,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经历空白的样子,无所谓地嘻嘻哈哈起来。唐山人的痛苦都装在自己的内心。在特别的日子和时刻,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和暗处,尽情去想那些惨痛,尽情去诉说那些憋闷,尽情去释放那些泪水,而且只是自言自语地念叨一下,独自深潜浩瀚的苦海,以奋力遨游的方式让自己筋疲力尽,让泪,断,然后,站起身,进入正常。
唐山人讲究有苦自咽、有难独当,推崇有痛自疗、有关独闯,这种勇于独立于世的自强精神,是这块土丰富的煤炭之火性、经火钢铁之刚性以及火后水泥散而能聚、火中陶土转眼新生的物质现象在人们身心上的反映。一个地域的生产、生活环境塑造出一类人的气质、风貌和心灵取向,此话应当不假。相传,一只凤凰飞落到这里,在中心区化成一座山,叫凤凰山;唐山也就有了一个别名----“凤凰城”;总结有突破性的一个发展时期,唐山也爱用“实现了一次涅槃”进行概括。在这里,似乎一切都与火有关。小时候,家家生火,做饭取暖都靠火,我们非常熟悉灰烬,我总觉得,灰烬,是一个相当美丽的词。
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下,又经民俗民风的熏染,唐山人就形成了厚直、刚硬、豁达和通爽的性格,能豁得出去、舍得出来,能扛得住、挺得过去。人们称唐山为“英雄城”,恰当。
5.
震后盖楼,以4层为准;现在是楼越盖越高,越来越密。气势和时尚范都有了,林立着白天的高雄和夜晚的璀璨。植树上也升层次,飞絮的杨、柳被银杏、合欢所取代,风景一新。几经改造,如今震后第一代楼已经不多,新唐山真是新上加新。
我所在意的,还是那些与地震有关的景象。我从前上班的办公室对面,栽有一院子玉兰树,这种先花后叶的树在春天特别显眼,在春深之后又显得特别平实,甚得我心。我赋予了这一院子玉兰树特别的意义:
“叶还未生出,光秃秃的枝顶上,一批玉兰花/就抢着打开了这座城市又一年的春天/像小孩扒开门缝仅露出一张脸,身子/还隐在往昔,先来瞅瞅这世界的情况//开红花,也开白花/懂事的一院子玉兰树/将我的心思都挂到了枝上:红白齐全着/日子就完整;就不会只顾着一样而丢掉另一样//地上,每一株玉兰树的影子都黑亮黑亮/泛着沉重的光明。移动着将身边的一切抚平/以暗覆盖暗,擦去尘土和铁锈/让金子见到黄,让黄找回金子//表达完忆念或盼头之后/才开始长叶,尽情掏出内心的情书,翠绿着/灿烂随即汹涌而来。在更全面的翠绿里/玉兰树仿佛消失了一样,翠绿着,存在”。
另一处就是抗震纪念碑广场。这里碑体高耸,有废墟形状的一方碑文刻着纪念的文字;开阔的广场却成为宣传活动和居民健身的地方,生死同台,悲喜一地;大概经过了允许,常年有卖风筝的摊点“在此零售飞翔”,特别让我关注。
“卖风筝的摊点是一个色彩的漩涡/紧抱着冲动。白云和天空就压缩在包装袋里/就等你顺好飘带,亲自送它们重回我们的头顶//手牵飞天的意愿,憋是憋不住的:早有凌空的风筝/一边得意地晃着脑袋一边首肯大地/为眼皮子底下的一桩小买卖做托//关键是开阔,从死到生的空间完全被打开了/风和风就形成了连贯的追逐,天上和地上的对望/才互为风景。一根线,一根弦/弹着欢歌也弹着悲曲,随便听//风筝越来越高——让你扬起头还不够,直至让你的脸/几乎与天空平行,让你的胸膛/尽量对向天/成为广场上的广场//常见断线的风筝挂在树上/挂在了树上也还是彩色的。”
新唐山今年40。
我“皮肤上的伤早已长好,甚至没有疤痕/曲皱地忆念曾经发生的灾难/平整的皮肤/比阳光的表面还要光滑,无法截留住任何坎坷的往事//但一直在疼,与阴天无关;一直在流血/没有出血口;一直在缝合与结痂的过程中/身体睡着裂缝醒着;衣衫清洁/内脏上却压着砖石和灰尘/就是在这样明确的隐痛里/我若无其事地去仰望月亮/仰望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满城楼宇//疼痛找不到伤口/存在的伤口,没有具体位置/痊愈的肢体病在健康的日子/我的呻吟/是槐花上蜜蜂的歌唱;我的抽搐/是一阵风吹来时广场风筝的一抖一抖/在好看得让人想哭的风景前/我伤痕累累地替那些不在场的人会心微笑//十分清楚:一道伤/从命中你的那一刻开始/就望不见底,没有终结的尽头/即是你消失了,诡异的天灾/也会将这道伤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延续//”
的确,每当听到世界上有灾难发生,我就会想起自己所经历的大地震。自然灾害是我们人类共同面临和永远无法解决的生存难题,这一方面使我们需要不断面临难料的生存困境和产生难以排解的生命隐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充分感知天外的力量,从而学会谦卑、敬畏,不至于让我们自大得失重。
新唐山今年40。
以70年代为一条线,对于地震的记忆及其在人们情感上的占据,上一拨人与下一拨人之间已生鸿沟。从80后开始,这拨人已基本摆脱掉大地震的震波、烈度的影响,“身上没有阴影地谈论着雾霾”。唐山大地震对于他们来讲,是底色,是发黄的传闻,是父辈、爷辈所刻骨铭心而于自己则关联不大的遥远的陈年旧事。这就是社会的进程:下一代的脚步撵着上一代的脚步,下一代的脚步声越来越铿锵有力,上一代的脚步声越来越疲沓稀疏;这就是时代的推移:下一代的人潮淹没上一代的人潮,下一代人的故事更新上一代的故事。历史的进步其实十分残酷,但我坚信,这块土上新的一代又一代不会完全等同于其他城市的同龄人,因为他们生在唐山这块土,呼吸着唐山空气。
新唐山今年40。
40年应当写一部大事记,而我只是记录了一些细节。尽管,更多的时候,漫长和悠久就是靠细节存在的。
快到唐山大地震40周年了,我像一个负债人,伏案写诗,动情处泪为标点,诗行支付身心的本金和情感的高息;我像一个遗世的老艺人,怀里抱着一把三弦,像在街头演唱,大风吹着我褴褛的情绪和投入的表情,我一厢情愿而略显孤独;我像一个笨拙的弹琴人,手指在键盘上舞蹈,光标将汉字从我的心里一一拽出,呈现在亮面的显示屏上。
我写诗,震后40年,唐山该是怎样一首诗呢?想到此,我有些惶惑,有些不安。我想,唐山这首诗,该比我写的更为精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