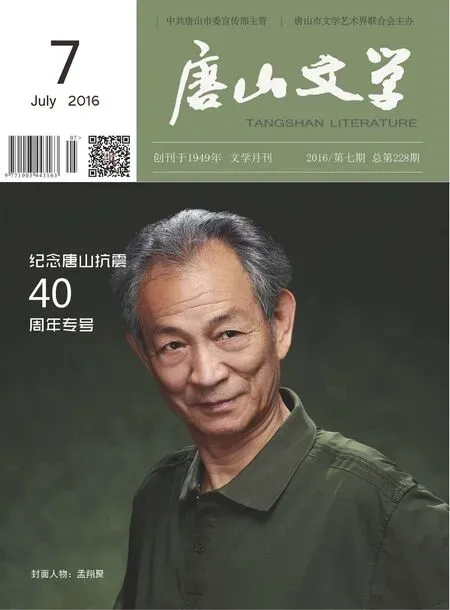大院记忆——写在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
么秋胜
大院记忆——写在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
么秋胜
1963年8月,我出生在丰南县城以北不到一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十三岁以前,我家住的那个院子是一个有三十多口人的热闹而又和谐的大院。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美好和难忘的时光。1976年那场大地震结束了我在大院里的生活。其后,跋涉于远非自己擅长的喧嚣、繁缛、虚伪、贪婪的世事,离那个平静、简单、朴素、纯真和容易满足的大院越来越远了!
从1976年“七.二八”大地震算起,至今蓦然逝去整整四十个寒暑!如今我也由当初那个大院里懵懂的小男孩步入了知天命之年。然而,其后不论我学习还是工作,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踌躇满志还是沮丧落寞,生活拮据还是富裕,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大院里的前前后后,角角落落,一草一木;院子里一起玩耍的伙伴以及那个院子里每个人的身影和容貌,说话声、笑声;与伙伴们一起玩过的还有那些常常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有趣的童年游戏;对于稍稍改善衣食带来的满足以至于喜悦……在我或忙或闲的日子里,在独自于某一角落发呆和陷入遐想的时候,在被种种或隐或显的思想情感困惑和搅扰的心神不宁的时候,在睡梦中,它们常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们或清晰或模糊,或强烈或平淡,或使我身心顷刻间变得愉悦,或使我更加坐卧不安……我的思想常常在这样的回忆中得到矫正,情感常常在这样的回忆中得以平复,意志常常在这样的回忆中变得更加坚定!那个大院虽然早已消失并且在时间上离我愈来愈远,回忆它的频度却有增无已!
正是这个原因,让我无法不用我拙劣的文笔记录下那些儿时存留在脑海里的记忆和今天由此生发的一些感想!我确信,我的这些记忆和感想一定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在唐山大地震过去整整四十周年的时候,就算以此来怀念那些曾经在那个大院里生活过以及那时在相似的大院里生活过的逝者!与从那样的大院里走出来仍健在的人们一起分享!
一、我的老家——位于两个“河头”之间的村庄
胥各庄(2009年以前丰南区政府所在地)曾因1881年修建长9.7公里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而闻名于世。马拉火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古老的胥各庄借唐胥铁路由农村迅速嬗变为繁华的城镇。同样为承担开滦的煤运而挖掘的,是比唐胥铁路更早些的煤河。煤河于1880年从蓟运河旁的阙庄向东开挖,原计划是始于天津蓟运河,引蓟运河水通往唐山开滦煤矿承担煤运功能的人工河。可是往东挖掘到胥各庄附近的时候,地势逐渐加高,引入下游的水需要挖掘的土方越来越多,且同时挖掘遭遇流沙,在当初的胥各庄以南1.5公里处工程停止。这里及附近被称为“河头”。
挖掘煤河八十年之后的1959年11月20日,计划承担津唐两地水运功能的津唐运河破土动工,挖至胥各庄以西1公里的时候,因类似当年挖掘煤河的原因,工程停止。这再一次提醒人们,唐山是一座有山的城市,地势明显高于其西部和南部的冲积平原。
从胥各庄七街往西,经过一条两边是高起庄稼地(因胥各庄地势较高)、对头勉强可以错过两辆马车的狭窄的土路,走大约五百米;或者,从河头的商业街往北走大约走同样的路程,就到我的老家——清庄湖。
津唐运河在胥各庄以西是南北走向。我的老家就在煤河以北、津唐运河以东距离两条人工河各不到1公里的地方。因此,在我村的村西北和村东南有两个“河头”。 津唐运河的“河头”几乎无人知晓,煤河的河头在很多时候则是丰南县城的别名。
二、童年居住的大院
我的家乡清庄湖是一个被池塘环绕、绿树掩映的美丽村庄。村庄的四周满布着大大小小、连续不断的池塘。池塘与池塘之间由或宽或窄的水沟相连(水沟与道路交叉的地方搭着石板或者石桥),再由较宽较长的“西沟子”往西与津唐运河相通。村里的街道、院落明显高于南、北、西三个方向村庄外围的土路,与池塘岸边的土路之间大约有三、五米高的落差,只有朝胥各庄方向的村东例外。因此,从村里到南、北、西三个方向村外的几条路都有比较大的向下的坡度。可以推测,村周边的池塘是当年祖先建村时取土垫庄留下的。在当时条件下,完成如此之大的工程量和建设如此完备的环村水系,可见当年老祖先建村时的艰辛与智慧!
村中间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胡同把清庄湖分割为东、西两个行政村。我家在西清庄湖。
我家住在宽敞的东西主街道北边的一个大院里:院里住着7户、35口人;院子南北长约七十米,宽十三、四米的样子。院子的南半部是由土坯砌墙、苇草铺顶的几套低矮住房组成的居住区:中间是一层稍高的正房(正常的三间,加上西屋跨一间约两米的套间),正房将居住区隔成南北(或前后)两部分,南边和北边分别是低矮窄小、东西相对的两套厢房(每一套三间)。每一套厢房和邻居之间有一条只能容一人行走的胡同,房顶上边的苇草斜申下来,遮住大半个胡同。胡同的主要功能是承接房屋滴水,平时很少有人进里边去,夏天每个胡同里边都会有几张蜘蛛网。北院地势高于南院约一米的样子,所以,从前院到正房需要垮上四五块石板搭起的台阶。南院东西厢房的南边各有一棵高大的洋槐树。东边那个树的树干低矮而粗壮,略带弯曲,胡乱长着的大大的树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沧桑而又略显邋遢的老人;西边的那颗长着笔直高挺略细一些的树干,树冠略小、呈整齐的圆形,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英俊的小伙。院子的居住区内除了这两棵树,几乎就没有别的植物了。
我家(父母、三个姐姐、妹妹、弟弟共八口人)住前院的西厢房,对面是父亲四伏的大哥和他的三个儿子,七口人(其中大伯的大儿子、我的大哥成家,生有两个儿子)。平时我叫他对屋大伯,以与我的亲大伯区分。大伯和二伯两人住后院的西厢房,对面的东厢房住的是对屋大伯的五弟,我的五大伯、五妈(对“五伯母”的称呼)和他们的五个儿子,七口人。正房西半边一间半(住正房的两家共用中间的堂屋)加两米的套间住的是父亲三伏上的大哥,我记事的时候大伯早已过逝,只有大妈(对大伯母的称呼)和他的儿子儿媳一家七口人。正房的东半边一间半住的是对屋大伯的六弟,我的六伯、六妈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四口人。
院子的北半部是被分割成小块的各家的菜园和堆放柴草、杂物的地方,有的用秫秸圈着,有的没有;菜园的中间是一条狭窄略带弯曲的小道,宽度可以勉强推过独轮车的样子,通向北小街。这条小路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是最熟悉的路,那时感觉它长长的!这个菜园里各家种着各种蔬菜;也有不少洋槐、垂柳、榆树、桑树、椿树等。一到夏天,树上有各种鸟类,许多叽叽喳喳的麻雀、敏捷地在树枝间蹦蹦哒哒的“小柳叶”(不知学名为何),偶尔还能看见一两只喜鹊和不知道名字的鸟类;掩映在树影下的开花的植物(萝卜籽、白菜籽之类)、各样的蝴蝶、蜻蜓、知了,热闹极了!
三、简陋的居所、单调的衣食
大院里的生活条件非常简陋。据老人说院里几套草房的房龄那时已有五、六十年到一百年,我家的三间厢房墙壁和屋顶受损严重,靠小修小补已经难以维持,六十年代末就地翻盖了砖混结构的三间平房。整院五套正房、厢房总共建筑面积不过200平米,人均大约只有6平米。晚上睡觉一家人人挨人。不过,那样低矮的土坯草房还是冬暖夏凉的。人们夏天用芭蕉扇纳凉,冬天除了一日三餐生火做饭烘一烘土坯炕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取暖手段,也就勉强能够维持了。
衣着是简单的。多数成年人和小孩子是没有适宜春秋穿的衣着的,棉袄棉裤一直穿到入夏。记得每年都要等到初夏的某天中午,突然觉得燥热难挨,浑身的汗弄湿棉衣棉裤的时候,才急忙赶回家换上单衣;盛夏的时候穿一阵子背心、短裤,初秋再换上单衣,就一直穿到深秋或者初冬换棉衣。谁省吃俭用卖一件秋衣穿上是很让人羡慕的!
吃的同样单调。一年的主食以玉米为主。通常中午玉米面饽饽,早晚玉米粥。好一点的年份粮食比较充足,玉米粥就稠一点,差一点的年份玉米粥就稀一点,中午吃一些红薯干或者红薯饽饽。麦秋的时候吃几天面食:烙饼、馒头、面条。一年买几斤大米只有过年和过中秋节才能吃。副食就更将就。夏季的蔬菜丰富些,韭菜、黄瓜、西红柿、土豆等,冬季的中午通常就是白水熬大白菜,早晚腌咸菜丝。不年不节不生病很少吃到鸡蛋,更不用说肉食。
大院里的生活虽然是清苦的,但是,只要伙食稍有改善,孩子们就会欢天喜地的高兴!不用说吃鱼、吃肉、吃鸡蛋,就是偶尔吃一顿面食,吃一顿玉米面菜饽饽,早晚的咸菜丝里拌上一小块豆腐,都会有一种真切的满足感!
除了过年、过端午和过中秋节以外,我家每个人过生日家里都会吃一顿蒸饺子,给过生日的人煮一个鸡蛋;除此以外,就只有生病的时候可以开个小灶,征求病者的意见,做一碗面、摊一块咸食(面和葱花、盐、五香面和在一起摊的饼),或者煮一个鸡蛋。这种情况,其他人是没有份的。所以,这时孩子们对病者竟还会有几分羡慕。当然,病者就这样从中得到一些慰藉!
就衣食住行的条件而论,如今与那个大院里的生活相比,简直就是到了天堂!不少人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出门坐汽车,冻不着,晒不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衣食无忧。然而,他们就是不觉得快乐!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思考吗?
四、大院里的欢乐
大院里的人们是最普通、最平凡的农民,父辈们几乎都没有文化。他们或许一生都没有作出过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他们中的每个人身上都具有那个时代普通农民的思想感情,具有那个时代农民的弱点。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很多,差异却很少。他们贫穷,几乎没有任何财富积累,所以他们特别在意眼前利益,胆小怕事;他们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也乐于助人……
院里的大人们似乎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节奏:男的白天下地干活,回家多数时候躺在炕上休息,解乏,偶尔聚在一起唠唠地里的嗑。记得只有五伯有时在炕上翻一本破旧的小学生词典,积累一些诸如“旮旯”那样的生僻字偶尔难一难上学的半大孩子们。女人们做饭、洗衣服,整天有干不完的家务,时而边干活边扯些家里和村里发生的闲事。高兴的时候比我大几岁的半大孩子时不时爱跟嫂子们开个玩笑,逗个乐子。这时,气氛就显得特别活跃。
大院里让所有人高兴的事,就是电影队来村里放映露天电影。在孩子们的催促下,各家提前做饭,吃过晚饭天还大亮,孩子们就搬着板凳去占地儿。如果是冬天,穿着棉鞋也会冻得直跺脚。不过,那样的等待是令人兴奋的!片子就是那几部样板戏和战争片;有时在放映前还加一些幻灯片。不论什么影片,都会受到一样热烈的欢迎!村里放电影的时候不多,一个村一年大约就两次,因为东西湖是两个行政村,次数要加倍。
端午节和中秋节也是整个大院快乐的日子。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冬季是寒冷而又漫长的,一年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冬季。端午节正是每一年温暖决定性地战胜寒冷的时候!因此,端午节在我心中不仅是吃粽子,享用一顿难得的美食,它更是温暖的同义词!中秋节要比端午节隆重一些,不仅要吃月饼,中午还要吃米饭、炖肉和炒菜,是一年中仅次于过年的节日。
过年是整个大院欢天喜地的时候。大约从腊八那天吃腊八粥起就有了些年味。之后,一直到大年三十,孩子们一天比一天兴奋、活跃,大人们唠嗑也比平时多。腊月二十三小年,家家中午吃蒸饺子,然后几天,炸炸饼、蒸馒头、蒸年糕、炖肉、熬鱼,忙个不停!父亲是腊月二十六的生日,我家中午吃蒸饺,所以,那几天我家显得更忙。每到这时候,对面屋大伯就会买几张红纸来,剪好精致的窗花,送给各家贴在玻璃窗户上,偶尔还能听到大伯吊几嗓子皮影戏!腊月二十九中午还是吃蒸饺子。
过年三十那天,孩子们一大早摸黑起来穿新鞋。一定要换掉入冬穿上的已经破旧的棉鞋,穿上母亲新做的假鞋。新鞋的鞋帮鞋底硬硬的,把脚裹得紧紧的,脚趾在鞋里一点都不能动,不光冻脚,穿上它,跺脚都不管事。但是穿上新鞋还是那样高兴!然后就放鞭炮。孩子们舍不得成挂的放鞭,就把一挂小鞭拆开,一个一个的放。一般是点着一根香,再用香火去点鞭炮。先在院里放,然后去大街上放。有时也买些摔炮(花生米大的小纸包里包火药,大的一头朝石头等坚硬的地方用力一摔就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换个花样。再晚一些,会有好多大人燃放成挂的小鞭、雷子、二踢脚。这时,鞭炮声响成一个点儿,把早上的年味推向高潮!就这样折腾半天天才亮!我家过年的早饭一般是煮大米粥,白菜熬冻豆腐,还可能放一些炖肉的肉汤。早饭后,上午仍然是放鞭炮。自己放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先歇一歇,看别人放。上午放鞭炮的气氛比起早上要差很多。中午饭是过年的重头戏。不论家里富不富裕,平时怎样省吃俭用,年三十中午饭家家都会竭尽全力!除了有炖肉,一般还有熬鱼,几个炒菜和几个荤素凉菜:蒜薹炒肉、土豆炒肉、松蘑炒肉、白菜炒肉、葱头炒肉、饹馇炒肉,猪肉灌肠、猪头肉……满满的摆放一桌,一家人放开吃!当然,此时男人们是一定要喝酒的!大伯平时从来不喝酒,可是每到这时候,只要父亲一撺掇,就喝上一两盅。吃过午饭,一般下午休息,男人们可以串串门。女人收拾完午饭的碗筷,稍作休息,就赶紧忙乎晚上的煮饺子。年三十晚上的饺子一般是白菜猪肉馅的,肉多、菜少、面白,个头小。对于好多人家来说这是一年中仅能吃上的一顿煮饺,因而,包的特别精致!吃完这顿饺子以后,就是五介黑介打灯笼,放鞭炮。据说有的人家守夜,我家从来不守夜。
大年初一院里大人小孩挨家串门拜年,吃各家的瓜子糖块。从记事起,初一先跟着母亲去给本村(东清庄湖)的姥姥和三姥姥家拜年,回来再给院里和村里的长辈拜年。大概在每一年的正月初五以前,姥姥家和三姥姥家会分别请我们一家吃一顿像过年那样的饭(大伯二伯不去,就给他们送过来一些饭菜)!
俗话说,“好过的年,难过的春”,或许有人疑惑,在物质条件那样贫乏的时候,在距离下一个收获季还需要熬过漫长日子的时候,这些平日里省吃俭用的农民们,为什么要那样铺张的过春节?我在读过罗素关于审慎与热情的论述以后似乎找到了答案:“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 “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着某种沉醉的成分,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注: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的成分,生活便会没有趣味”(见《西方哲学史》)如果说平日里的节俭是他们对于现实的审慎与屈服,那么过年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热情里则蕴含着追求未来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院子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记得十几年前,一位大学要好的同学,在刚刚移居美国的时候,曾经给我写过几封信,感慨那里的人际关系简单而冷漠。只要有工作就什么都不用愁,不像在国内事事都要求人!大院里人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简单而又和谐。在那么多年里,七、八户人家三十多口人居住在一个院子里,却几乎不记得发生过几次争吵,这放在今天,是何等的不可想象!
院子里当然不仅仅有欢乐。可是,在我的这篇文章里我却只想记录欢乐。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除那场大地震以外,很少有让整个院里的人们陷入痛苦的时候;更因为我在前边所记录的那些欢乐是比较纯粹的!
当富裕或者清贫是普遍的常态的时候,它并不是构成某一个人快乐或者痛苦的要素,因此,大院里的人们虽然贫穷,但是只要遇到一点点高兴的事就会使人感到纯粹的快乐!快乐也没有大小之别,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高兴事,只需遇到一点点烦恼,就会取消他的全部快乐!洛克说:“因为你把一点点苦味搅在杯里,就能把甜味取消了”“稍有一点痛苦就足以把我们的一切快乐消灭了”(《 人类理解论》1959年2月第一版第246页)。一个人赚了一大笔钱,如果他身边有一个人赚了比他更多的钱,他的快乐就大打折扣!如果他被骗走他刚刚赚到的那笔钱的百分之一,或者随后他买到一份伪劣商品,或者他与人发生争执……他的快乐就会被完全取消,并且陷入苦恼中!这时,不论他再吃什么高档大餐,穿什么名牌衣服,都无助于消除他的烦恼。一般来说,一个人无论做多大的官,拥有多少财富,只要他一直不能够摆脱某一类的痛苦(例如过高的官欲和财富欲),那他就永远与真正的、纯粹的快乐无缘。所以,我在上面记录的大院里的那些快乐之于当今反而是很奢华的,就不足为奇了!
五、童年快乐的游戏
津唐运河的东岸是一片平均几十米宽的宽阔的树林,村里的耕地主要集中在这片树林与村庄之间。我居住的大院、村周边的池塘、津唐运河东岸及其与村庄之间的那片开阔的耕地就是我幼年和童年的主要活动场所。
可以说入小学以前我完全浸泡在游戏中。按说,在当时别人家的孩子从能跑的时候起,就要帮大人干些活,干完活才能去玩。但是我家的情况有点特殊。解放前我家是地道的贫苦农民,因家庭条件很差,父亲兄弟三人中,大伯、二伯是单身,我父亲生有两男四女。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有一弟一妹。在我七岁以前,弟弟还没出生,我就成了父亲兄弟三人的独苗。上面又有三个姐姐。所以,父母亲对我管得不太严,不论跟邻居家的同龄人比,还是跟我的姐姐比,干活都是最少的。即使在我稍大一些的时候,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大改变。
有些游戏是大伙一起玩的:军民打贼,藏猫猫、弹玻璃球,打钢珠,丢铁球,游泳等;还有一些常常是我一个人玩的,粘(套)知了,豆蜻蜓等。在夏天玩的游戏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常常自己一个人玩的“粘知了”和“豆蜻蜓”;与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游戏最开心的是游泳。
粘知了: 盛夏时节,在人们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就早早起来,开始属于我一个人的游戏:挑一根笔直的高粱秸秆,把最上端最细最长的一节(我们叫它剑杆)的上端用手指或用刀劈开一部分,再用一节适当长度的高粱杆撑住两端,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间。然后,就走遍院里的每一个胡同寻找蜘蛛网,将那个三角形空间罩满蜘蛛网以后,回屋把高粱杆戳在墙角的某个地方备用。吃过早饭,当大人们下地干活,女人们在屋里干活,同龄的伙伴们或睡懒觉,或跟大人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大大的院子里特别安静,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似的。这时候,我就开始在院子里仰着脖仔细寻找落在树上的知了。找到以后,就迅速用高粱秆前端黏黏的蜘蛛网按住它,被黏住的知了折腾一阵就被我捉了。这样的游戏是忘情的、投入的,一玩就是半天,玩的大汗淋漓,常常忘记吃午饭!每当这时,我就觉得整个大院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豆蜻蜓:夏天,捕捉池塘里飞来飞去的蜻蜓是我小时候一项钟爱的游戏。最容易捉到手的是个头较大的绿色蜻蜓。首先,去路上捡一根马尾毛,一头系上留出小孔的结,另一头从小孔穿过,系在一根一尺多长的细竹竿上,就形成一个可松可紧的套。然后,用扫帚拍到一只母蜻蜓,用做好的套套在蜻蜓的两对翅膀中间,这样它再飞也跑不掉了。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以后,只需看到公蜻蜓出现就用一只手左右晃动竹竿,母蜻蜓一飞,公的就会追过来和母的扭在一起,准备交配。这时,用另一只手立刻将两只蜻蜓一起轻轻捂住,公的就捉到手了!如此反复,很快就可以捉到很多只公蜻蜓!
游泳:稍大一点的时候,游泳成了夏天最得意的一项游戏。开始,和伙伴们一起在村周池塘的水里嬉戏。不记得什么时候,先学会了狗刨,然后是仰泳,自由泳,潜水等。学会游泳后,游泳的地点就改在了津唐运河。津唐运河距离我们村最近的地方,离“水簸箕”(京唐运河“河头”的标志,是高悬在河的北端供北边各村向津唐运河排水的水利工程,因形似簸箕而得名。因其高,即使在丰雨年份河水距离水簸萁还有很远的距离)只有几百米远。那个地方的河水在雨季之前有大约几十米宽,到了正值游泳的雨季,连续的降雨使水面逐渐加宽,一般年份河水最宽时可以达到一百多面宽。在一些丰雨的年头,水面离岸边只有几米远的样子,估计河水可达二百多米。这时,一般水性的人就不敢下水游泳了。
那里是我和伙伴们夏天的乐园!一般都是好几个伙伴结伴而行,因为各家吃饭的时间不同时,谁家饭晚的时候就顾不得在家吃饭,拿起一个饽饽就和伙伴们一起跑,跑到津唐运河再吃。吃的噎得慌就喝一口河里的水。河岸河床和附近的地里都是细沙,可能是细沙过滤的缘故,河里的水清澈见底,齐肚脐的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踩在河底的脚趾头,河水也不苦。我们在河里一泡就是两三个钟头,经常赶不上下午上课;赶上礼拜天,一玩就是一下午!
在伙伴们中间,我的水性算是最好的,一是耐力强,可以在一人多深的水中一呆就是两三个钟头;二是游泳的速度比较快,在追拿的游戏中没有人能追的上我;三是我有一项绝技,可以露出脸、肚皮、腿和脚趾在水中漂浮任意长时间,还可以在附近没有人打搅的地方这样睡着呢!
记得一九八四年的暑假,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从学校回到家里,我急切想去津唐运河游泳。这时,当年一起游泳的伙伴都已经长大,有的在家务农,有的在外打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伙伴要他和我一起去。他却告诉我,河水太脏,无法游泳了!我不信,非要他和我一起去看看。我们来到了河边,看到原来清澈见底的河水已经变成一池污水,水面漂着油污和垃圾!我大失所望。我的伙伴中没有一个比我在这条河里游泳的次数和时间更长,我不相信有谁由此受到的伤害比我更大!从那以后我就再不想到那河边去看一眼!
近些年,我有几次去泳池里游泳,也去过海里游泳。但是总觉着海里的水里有盐,上岸以后还要用谈水冲洗,怪麻烦的;泳池则太窄,里边游泳的人又太多,游不出多少情趣来。可是到哪里去找当年的津唐运河呢?
六、上小学
我像多数小伙伴一样,七岁入小学。不一样的是,我临近入学不几天的时候还咬舌(发不准音)。给姥姥拜年总是说“姥姥(发音“袄袄”)过年好”。记得六岁那年过年在姥姥家吃饭,比我大几岁的一个表舅问我几岁了,我说六岁(发音“又睡”)了,他就跑去跟我妈说,秋头(我的小名)又睡了!我妈赶紧过来,看我没睡,就明白了,满屋人大笑。我就要入小学读书了,还咬舌,我妈着急,连夜帮我矫正发音。把我咬舌的那些字找出来,教我说那个字的时候舌头放在嘴里的哪个部位,一个一个矫正。还好,赶在入学之前全部矫正过来了!
从1970年春节过后入学开始,到1976年年底,在村小学(当时两年的初中称作六、七年级,在小学连读)整整读了七年。玩野的心哪里容易收敛?七年时间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学习与游戏之间的纠结!小学的课程主要是语文和算术。因为在入学前就从大人那里学了一些算数,学起来比较容易;语文里的生字则需要下点功夫记住,我却不肯下功夫,又不善应付,不用功就一点都不用功。所以,那时我的数学还算比较好,语文却极差。记得有一回考试,数学满分,语文零分!
入小学是我走出大院重要的第一步,是从我熟悉和喜爱的游戏向完全陌生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客观一点说,不管当时怎么不情愿迈出那一步,我至今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建立在那一步的基础上。从那以后,在一点点逐渐远离那个大院,直到2010年平改彻底告别原来那个大院当中的每一步,有多少是自己不知不觉的,有多少是很不情愿的,有多少是我努力争取的,好些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清楚知道的是,自从入小学以后,之前几乎占据我全部时间的游戏和由此带来的纯而又纯的童年快乐就越来越少了,代之以边学习边游戏。有上课和写作业的压力,以后玩游戏的快乐中就一直掺加了杂质。而且,离那样的纯而又纯的快乐竟愈来愈远,只有在占据内心一角的童年记忆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尽管如今我深知人不能拒绝长大的道理,可是当初那种不情愿却仍然不能完全从心里抹去。
七、几样简单的农家活
在自留地(生产队按人口分给各家经营的少量土地,一般是离村庄较近,适于种菜的园子地)干过一些简单的农活:割韭菜,看(读一声)畦(浇水的时候用锄头开畦口,浇满水关畦口),打辘轳……我学会打辘轳大概是在十二岁那年的夏天。我和母亲去浇自留地的韭菜,帮母亲看畦。刚安上辘轳,母亲有事回家,我自己就试着学放辘轳,那天学打半斗的,过些天又浇韭菜的时候就学会了打满斗的。那时我个子很矮,学会打辘轳还是很得意的。不过,地震以后,土井被震坏,修建了机井,打辘轳的手艺也就用不上了。
此外干的比较多的活是挑水、採菜、割草,还养过两只兔子和一只羊。在家务活中,最让我骄傲的是在做饭的时候帮母亲烧火,特别是在烙饼、烙火烧的时候,我掌握的火候恰到好处,是最让母亲满意的,姐姐们都比不上我!现在想来,我之所以擅长干这些活,主要是因为我干活特别专心。
这里,特别想说一说我曾经养过的两只小兔子。记得地震那年的春天,在化肥厂上班的二姐从同事那里拿来两只小兔,银灰色的,耳朵长长的,眼睛亮亮的,走路一蹦一蹦的,一个颜色深些,另一个浅些。二姐说单位一个女同事是邻村的,弟弟养着很多只兔子,听说二姐也有个弟弟,就说服弟弟从家里拿两只小的送给我。我喜欢至极!当天先放在一只筐里,第二天就和二伯一起搭了个兔窝。从此,我就每天去地里挑它们最爱吃的苦麻子喂它们,没事就去兔窝前边看它们,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时不时还给它们称称重。很快它们就都长到六七斤重。可惜,不久地震了,把兔窝震塌了,它们跑出来。当时也没心思管它们,后来就不知跑到哪去了。
提到那时的农活不能不提到生产队。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每一年或多或少都在生产队参加过劳动。对于我来说,在三次高考没有考上到每一次次复读(当时的大中专学生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一旦考上就有了铁饭碗,因此,当时考不上大学复读是很普遍的)的间隙,会在队里参加一两个月的劳动。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复读之前,曾犹豫还要不要复读,在队里干的时间更长。我在生产队从事的是一些简单的农活。间苗、除草、牵埫(牵耕地的牲口)、跟车(帮车把式装车卸车)。在生产队里的劳动总的说是轻松愉快的!
八、地震
地震时我和大伯父、二伯父一起住后院的西厢房。
1976年7月27日,也就是地震的前一天,天气闷热得很。屋里燥热,没有风,外边也不凉快,让人坐卧不安!不知几点躺到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入睡比平时晚了很多。
后半夜起一次夜还没睡沉,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立刻睁开眼看见窗外巨大的闪光照亮了整个视野里的天空;随着巨响和巨大的闪光,大地先是水平晃动,紧接着是强烈的上下抖动,然后更强烈的东西方向的水平晃动,晃动和抖动交替,频度和强度越来越高且不间断……我就随着一次水平晃动顺势从炕上爬到地下。我大伯和二伯和我同时从炕上爬到地下。这时,屋顶掉下来砸到炕上!我们三人走出里屋的门,打算再往外走的时候,发现外屋的屋顶也已经塌下来了,只有里屋的那一扇门没有倒(后来发现是门外放着冬季挖菜窖用的一些木棍支撑住了这扇门)。屋顶的苇草被这扇门支开一条缝,我们扒开这条缝钻了出去。
在这场地震中,院子里除了前院父母住的三间平房外,全部倒塌。当时在院里居住的人有四人震亡,一人受重伤;我家只有当时住姥姥家的二姐伤势比较重。我们村是那次地震的重灾区,院子里这样的伤亡在村里是比较轻的。原因大概是草房屋顶比较轻,再加上房屋低矮,屋顶落下来的冲力比较小吧。还有就是我父母住的砖混结构的平房没有倒。震后不久,村里的重伤员被转移到外地治疗,不长时间就都痊愈回来了。这场地震姥姥家损失惨重,姥姥、大妗子和一个表弟在地震中阵亡,这对母亲的打击很大,记得她从那时开始吸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情绪才稳定下来。
这次地震是我和院里的人们生活的重大转折。地震以后,院里的人们多数陆续到外边盖简易房,在几年时间里又陆续在外边盖新房,原来热闹的大院里就剩我们一家和大伯、二伯,我们于1980年和1981年在院里盖起了南北两层共六间正房。院子的中间(紧挨原来的居住区北边)开通了一条东西方向的道。再后来,2010年村庄平改,那个载满着我童年无数的欢乐的大院就彻底消失了!
九、父辈
父母和两个伯父是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的长辈。
父亲: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在大队、生产队当干部,1975年到1983年当村支部书记。他对家里的事管的不多,尤其是对几个孩子,基本上是放任的。在工作方面,父亲比较务实,据说,在挖津唐运河的时候,父亲是村里的连长,带工干活。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饭,稍往前抢一点进度,就会有人承受不了,有累死人的。为避免自己的工地累死人,父亲在施工中顶着压力,量力而行。父亲成份好,进度慢一点上边也拿他没啥办法。
在家里,父亲虽然不管小事,但是,有些事还是管的很严的。记得地震以后,我读高一的时候经常不去上课,年底考试五门功课不及格,需要留级。跟母亲说不想上学了。父亲知道以后坚决不同意!说我性格老实,个子矮没有力气,不读书就没出路,硬要我继续读书,我只好听他的。当时正赶上延长半年学制,留级以后读初三。还好,经过半年的努力考上了一中。后来高考不顺利,我几次复读都得到父亲的全力支持。父亲是好面子的人,我几次高考没有考上,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一九八三年我考上大学,改变了我人生的方向。那年父亲已经五十六岁,他在一九八四年11月28日去世!看着我考上大学,或许是他最大的期盼吧!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实在太不懂事了,如果再多用些功,早一点考上大学应当也是有可能的。父亲去世对于我的打击很大,原来我就想读完大学找个工作挣钱孝敬他和母亲。他去世了,这个目标就再不能实现了!那时我就想,只有树立远大的目标,干成大事,才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母亲是家里的总管。每天要为十来个人做饭(大伯二伯一直跟我们一起吃饭),缝补洗涮,照料孩子,还要抓空侍弄自留地。好在母亲干活有基础。在她十一岁的时候外祖父因病过世,姥姥做猪鬃加工,顾不上地里的活,十几亩地从种到收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家里的这些活难不倒她!母亲是急脾气,几个孩子谁不听她吩咐,干活慢,干的不如意,就会挨批评,有时候还会挨掐屁股。我考大学不顺利,她的压力很大。父亲去世以后,家里陷入困境,当时只有二姐结了婚,三姐、妹妹、我和弟弟还都没有成家。父亲在世时,母亲主内,父亲主外,这一下家里家外的事都落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的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好在大家一起努力挺过来了!如今我们姐弟五个的日子过的都很好,她才逐渐熬出头来,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大伯:在我七岁的时候弟弟出生,从那以后,我就搬到北院厢房和大伯二伯一起住。我和大伯共用一条褥子,冬天天冷的时候有时就钻进大伯的被里取暖。这样一直持续到地震,总共有六年时间。所以,我和大伯的感情不同一般!他的钱我花着最方便。记得那时大伯一年从队里分三四十元钱的红,因为他不怎么担负家里开支,这些钱还算挺经花的。可是我知道他收入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我要他就给,反而不舍得花。那年月有几次他带我去饭店吃饭,都是我竭力阻止他多花钱!可惜大伯1992年过世,那时虽然我和他住对屋,但是当时的条件不算好,只是偶尔吃一回炖猪肉,给他和二伯送过去,别的就没有沾上我什么光!
二伯:二伯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干农活方面。二伯干活很讲究门道,对跟着他干活的孩子们要求也比较严,开始跟他一起干活感觉到有压力。但是后来,成人以后我基本上能跟得上他的节奏,挨的批评就越来越少,在只有我们两人一起干活的时候,偶尔还能得到他的表扬。要不是我最后考上学走出农村,相信会从他那里学到齐手的庄稼活手艺。
十、家人眼里的我——一个心眼的人
在母亲、姐姐、妹妹和弟弟的眼里,我是个一个心眼的人。如今,回想自己的经历,对于这样的评价我是很认可的。
小时候孩子们玩的游戏,不管是粘知了,还是豆蜻蜓,开始是大家一起玩,后来别人都不玩了,就剩我一个人,我还在玩。玩的上瘾的时候,谁叫吃饭也不回来。中午总是玩的又渴又饿,错过吃饭时间。
记得大概我三、四岁的时候,刚过完年就把过年压岁的一块多钱交给母亲保管。从那开始就认上了攒钱。大家买零食吃的时候自己不吃,把省下来的两三分钱交给母亲赞起来。大人每次都劝我别攒钱了,赶紧和大家一起吃。越劝我越不听。每一次把省下的钱交给母亲时都要跟母亲核实一下攒下的钱数。一直攒到那年秋天,攒了三块二毛四,跟母亲核实钱数时,发现她只是嗯了一声,没怎么在意。我觉得不对劲,就要母亲拿出那些钱来看看。母亲说给你攒着呢,还用看啥?我说就看一眼!母亲知道我不肯罢休,就说实话了,说她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急了!掏母亲的兜,她把兜翻出来果然是空的!我哭了好半天。母亲劝我说以后有了钱会还给我。还要我以后别这么死心眼,说大人忙得很,哪记着你那点帐。再说别人都吃零食你不吃,自己多亏!
童年的我是自卑的。上学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一些别人没有的错误想法,让我确信自己是愚钝的。例如,在我的印象里,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别是一个正方形,身体的高度是宽度的两倍(最早的模糊印象可能是在冬季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的时候形成的。那时我长的矮矮的,仰脸向上观察大人们的时候的角度显得人们比较矮)。这样的记忆虽然模糊,却很顽固。每天都摆在眼前的事实并不能够改变当初的记忆。直到若干年以后,大概是在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不知那位年轻的女老师从我跟前走过的时候,她修长的体型才使我翻出那最初的记忆,与眼前这个人作比较: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都远远不是正方形!从此,改变了我对人的体型的最初记忆。过后我就想,我怎么会有这么错误的认识呢?还有一次,一个同学说起他大伯的媳妇的事,我说你大伯还有媳妇?回来跟母亲学,母亲说你大伯没有媳妇别人家的大伯也没有?
与同龄人比较,我开化的比较晚。除了前边说的我直到上学前还咬舌以外,还有性意识形成的晚。那时候,儿童阶段,同龄的男孩和女孩之间几乎是不在一起玩耍的,男女同学在学校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我的性意识开化的尤其晚,读七年级的时候听到大一点的或者同龄的男孩说到男女之间的事,自己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说那些。直到一九七六年地震,我十三岁的时候对于女孩的认识还只是一个概念,觉得女孩就是不可以在一起玩的另一类人。用欣赏的眼光观察异性,在头脑里形成异性偶像形象还是到了大约十五六岁读高中的时候。从那时起,开始留意自己认为漂亮的女孩;学着心目中帅气的男性老师的样子,把趴在额头上的头发竖起来,露出额头。从那时起,我才从思想感情到形象一步步走向成熟!
回想自己至今走过的路,一个心眼也并不一定是缺点:不懂权宜,不知变通,不管其余,不顾后果,当然是缺点。它的另一面不仅不是缺点,而且是成就事业所需要的:一旦认定的人,认定的事儿,认定的理儿,一辈子不改;爱就一个心眼的爱,爱到底;恨就一个心眼的恨,恨到底;逮着一件上心的事就干到底!
十一、题外话
如今,在很多人无利不起早的时候,我却成了一个书虫,我用大把的时间来读书写作。可能很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值得,而我却要坚持!正是自己一个心眼,逮着一件上心的事就干到底的精神,使我最适合钻研一门学问:哲学。经过三十年的思考,十年写作,于2014年完成42万字的原创哲学著作《存在论》,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坚信自己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更远!
关于金钱与学问的关系,有很多人提出过学问更加重要的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有知识和学问的人当然更有能力赚钱。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就曾通过自己赚大笔的钱来证明这个观点。这种见解未免让知识和学问承载了额外的压力。还有一个学者在回答“为什么总是看到有学问的人跟在有钱人后面,而不是相反”的问题时说:有学问的人知道财富的价值,而有财富的人却不知道学问的价值。我觉得这样的回答仍然没有说出学问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还是培根的话让我觉着更有说服力:“支配知识比支配意志是更高的荣耀,因为支配知识就是支配人的理智、信仰和理解,而这些是人的心理活动中最高的部分,它们能指导意志的活动”“总结我们关于知识和学问的尊贵和优越的讨论,我们认为,知识和学问的价值在于人们最渴望的不朽的延续……智慧和学问的纪念碑比权势的纪念碑或人工的纪念碑要持久得多。”